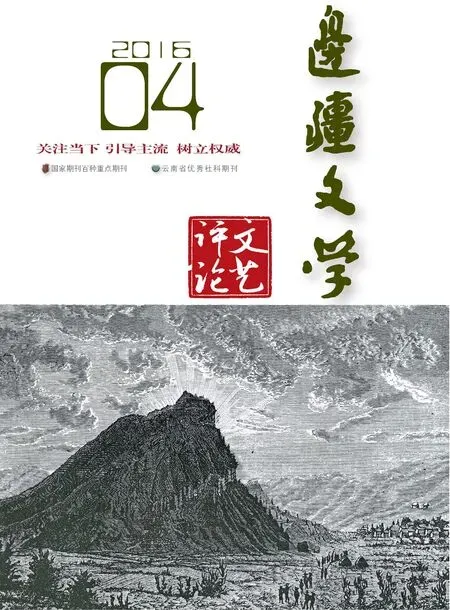接受美学:张爱玲的创作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以《金锁记》《倾城之恋》为例
2016-11-14◎翟悦
◎翟 悦
接受美学:张爱玲的创作观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以《金锁记》《倾城之恋》为例
◎翟 悦
二十世纪西方的接受理论富有启示性地从读者理解和接受的角度进行文学研究,实现了西方文论研究从“作者中心”向“文本中心”再向“读者中心”的转向。我们通过对张爱玲创作态度的了解,发现她的小说所呈现的特色与其接受美学相联系的创作观密不可分。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姚斯和伊瑟尔为代表的联邦德国的康斯坦茨学派,着意于文学的接受研究,将文学研究的重点放在读者的接受上。在接受美学看来,读者对文本的接受过程就是对文本的再创造过程,文学作品不是由作者独自生产出来,而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创造的,可见读者对作品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具有能动的创造力,因此读者的地位不容忽视。然而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满足和期待是最常见的两种心理状态,它们的出现也使得读者和作者之间产生一种张力,作者从中获得了使用创作技巧的空间,读者和作者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正如英伽登所认为的那样,一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必然和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意识和创作才能有关。但同时英加登也提出,作者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不仅仅是为了反映他的价值观念,而且也是为了让他创作的这部作品去接受读者对它的具体化,由此可见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和作者的双向互动使得作品的价值变得丰富起来。张爱玲小说之所以拥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一方面得益于独具匠心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就是她“读者至上”的文学创作观。
一、创作观里的“期待视野”
张爱玲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说:“作文的时候最忌自说自话,时时刻刻都得顾及读者的反应。”“要迎合读书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是说人家所要说的,二是说人家所要听的。”可见她很在意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而张爱玲小说拥有一批特定的读者群,他们多半是上海小市民,传统戏剧,通俗小说,礼拜六派的鸳蝴小说对他们的阅读习惯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张爱玲小说风格必然要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才能获得读者的青睐。从这一点来看,不得不说她的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读者兴趣的影响和限制。而读者对文学类型,风格和语言的审美经验实质上是他们的阅读经验所构成的思维定向,姚斯称其为“期待视野”。接受美学认为,在阅读活动中,与接受主体的期待视野相对的是接受对象即作品的客观化。任何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与一个客观的标准相符,才能获得接受,而这种超主体的客观标准恰好又是期待视野。那么张爱玲在创作时就会尽力满足观众的期待视野,说他们想听的故事。因此她坚定地说道:“要争取众多的读者,就得注意到群众兴趣范围的限制。”她深知大众对文学作品的取舍并不完全基于文学价值,她也了解家传户诵的更多是感伤温婉的小市民的道德爱情故事,她对自己的创作方向和风格清楚得很。我们可以看到张爱玲小说从形式到内容上都有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影子,中国传统小说多根据悲欢离合的故事情节来安排内容且结构完整,人物形象生动鲜明。张爱玲小说也是如此,她笔下的人物命运,故事结局都交代得很清楚,内容上也多是男女日常家庭生活和婚姻爱恋等一系列故事,延续了旧小说的言情传统。但仅仅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又是远远不够的,要想能够吸引读者并且使作品的艺术魅力得已长久的保持下去,就必须“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张爱玲又似乎准备在大众所要求的客观标准内给他们的审美趣味多添些什么,而这点也正好是她的作品与传统通俗文学作品的不同之处。张爱玲对她个人创作观的细致把握使其作品受到大众青睐,尤其是对小说中冲突环节的设计是她作品创作特色大放光彩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小说在描写人物复杂的心理时,往往正是结合着动作化的叙述来进行的,可见在这里,张爱玲确实汲取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精髓,迎合了读者大众的审美期待。例如小说《金锁记》向我们讲述了家里开麻油店的曹七巧由哥哥做主把她嫁给了有钱的姜家二爷,可惜她的丈夫患有骨痨,嫁过去的七巧虽然有钱了,但是在姜家依旧遭受排挤并且得不到正常的婚姻生活,在她和三爷季泽的调笑中我们看见了她被压抑的情欲,在对儿女生活无情的控制中我们看见了她被金钱扭曲的人性,曹七巧套在身上那“黄金的枷”把她的人性消磨殆尽。作者在《金锁记》中设计了多个冲突场景,并且在描写冲突中人物的状态时恰恰就遵循了传统小说从过程叙述中突出动作细节同时把人物的心理活动一起表现出来的手法。例如姜季泽和曹七巧具有代表性的一次冲突是分家后的季泽日子过得开始没落,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决定去找七巧帮忙,想利用七巧对他的感情来卖掉田地去买他的房子。在七巧的小心试探下,他的目的最终暴露出来,而曹七巧也恼羞成怒将季泽哄赶出去。文本中作者对曹七巧在金钱和爱情间纠葛的心理描写可谓是下了一番功夫“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露起来。”同时面对季泽的离去,七巧失魂落魄的心态通过几句简单的动作刻画就变得更加生动起来。“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站了大块的淡色的灰。”这句伴随着人物心理的动态化叙述,使人物描写质感增强且富有神韵。当然,除此之外我们更多的是看见张爱玲的别具匠心之处,也就是她多给观众的那么“一点”。姚斯说过:“新艺术手法打破了旧有的小说传统。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物的道德判断隐约流露于描写之中,作者的主观意志全然退入背景。然而,小说却依旧能够激化或提出新的社会生活问题……”显然张爱玲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精细的刻画以及对中国传统意象采取新的使用手法,将使读者原有的审美阅读经验遭到破坏,群众必须建立起新的期待视野才能重新认识和思考世界,同时换一个角度来看,她的创作特色也因此得到了体现。例如《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命运通过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心理刻画以及意象象征的方式烘托出来。当七巧将兰仙气走后,她和季泽有了一次单独对话的机会,七巧将心底对丈夫失望向季泽倾诉之后并质问到:“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这里还有一段是对曹七巧身上配饰的描写:“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配饰其实象征着她生存状态的一种表现,实心的小金坠子就像是黄金的枷锁,将七巧牢牢的钉在远处,她想得到爱却无法靠近,她的命运会像蝴蝶标本一样被永远的束缚住,所有的欲望都将动弹不得。面对质问的季泽,作者给予了一段从男性视角出发的心理特写,姜季泽虽心有所动,但是他把七巧为人看了个透,随后便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可见七巧的爱是注定不会有回报,她的命运也是注定被金子永远囚禁住。此外,小说中长安和七巧的几次冲突也是通过人物复杂心理表现出来的,例如长安在多次听到母亲对她婚约的诋毁后经过几番思想斗争终于下定决心同童世舫解除婚约等。
在对中国传统意象描写时,作者也有新的突破,像镜子,月亮和饰品等均融入了人物的主观感受并且伴随着他们出现,这样一来物品就具有了暗示人物命运发展的特殊功效,使故事情节充满了象征色彩。张爱玲在正面描写戏剧冲突时所采用的心理描写和象征手法等使故事情节变得生动起来,而读者既能从中捕捉到人物的性格也能对剧情的发展产生更多的期待。在满足了读者阅读期待的基础上,张爱玲超越了大众心中的客观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她对传统读者大众对于小说所期待的那种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团圆式结尾的突破,也是她独有的创作风格。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会发现故事里的人物的人生虽然结束了,但故事仿佛不会结束。就像《金锁记》的结尾,七巧在回忆过去的泪水里死去,而作者却在结尾附上这样一段话:“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又如《倾城之恋》的结尾:“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故事——不问也罢!”恋爱结婚、爱无回报、生老病死的循环在张爱玲的小说里好像真的是一辈子都写不完,这样的结尾让人读后感到回味无穷。同时,在读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发现她的故事更多的会有一种“悲”的氛围,而在组成中国传统小说情节的喜,怒,哀,乐四个喻像中,张爱玲为何偏偏对“哀”情有独钟?这从她的创作观中我们可以得知其中缘由。“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出戏能够用快乐为题材。”在她看来,只要是故事就须有点戏剧性,就要有冲突,有麻烦,还要有隐隐的悲凉感,否则就无从打动读者,引发他们的情绪。在中国传统小说里,人物虽然经历了种种磨难但结局总是美好的。而张爱玲小说中的那些男男女女即使在历经世俗情爱的折磨和苦难后,疾病和死亡的阴影也随之而来。正如她所说的那样:“生命即是麻烦,怕麻烦,不如死了好。麻烦刚刚完了,人也完了。”可偏偏打动读者的就是她给的这些冲突,磨难和苍凉。她笔下的那些男女主人公们在历经沧桑后大多都并没有收获到他们所期待的幸福,无论是《金锁记》里的曹七巧还是《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她们的爱情和命运都像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轻轻一划,便缓缓落幕了。即使是给予了圆满结局的《倾城之恋》,读起来还是能感受到一股子悲惘的冷劲,在时代洪流的涌动中,人是渺小的,他们的命运岂能由自己把握?那些过往无论是美好还是不堪,无论是否为争取幸福而做过努力,战争都会在一瞬间将所有抹杀,最后留下的终究是悲欢离合,曲终人散。打破了传统小说阅读的审美标准,使人们既定视野和文本之间出现不一致,在增强阅读感受的同时赋予人们新的感觉方式,产生“视野的变化”,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据此表现出来。正如姚斯所说的那样:“作品的艺术特性取决于“期待视野与作品间的距离,熟识的先在审美经验与新作品的接受所需求的‘视野的变化’之间的距离”张爱玲对作品冲突的设计以及对所谓给读者“多那么一点”的恰到好处,使她的小说即符合读者大众的审美期待又在结局时引发读者沉思,从而主动去追寻作者想传达的观点和想法,形成了文本和读者之间的有效互动,使作品创作的价值和意义丰富起来。
二、创作观下的“召唤结构”
“召唤结构”这个术语是由接受美学派人物伊瑟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文本和读者之间没有建立意图的调节语境,两者之间就产生了不对称性,然而要克服这种不对称性,读者必须在一定范围内由文本引导,而文本控制交谈的方式是读者和文本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因此他提出“召唤结构”作为主要调节方式。
在分析张爱玲的作品时,我们依旧能够发现,这位以“读者至上”为创作理念的作家,巧妙地运用了“召唤结构”召唤读者通过想象把小说中存有的不确定性或空白与他们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从而进行填充和解释,使读者在这样的空间里享受阅读的乐趣。而她本人创作风格也因使用“召唤结构”的方式而再次变得明朗起来。首先,张爱玲小说的题目大多都含有类似于像金锁、红玫瑰、 第一炉香、 茉莉香片等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所以看见题目时,读者第一感觉就是很熟悉,他们自然就会把题目和生活中与这些事物相接触时的经历联系到一起,从而进一步想知道作者为何会以这样的日常事物为题,她拟设这样一种看似与主题毫无联系的题目究竟有什么目的?作品题目中所提到的事物是否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那些事物…….读者对于作者精心设置具有模棱两可性的命题产生了好奇心,他们将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文本进行细读。在其阅读完作品后,意识到小说题目其实与人物性格及其命运相联系时,这就与读者当初的设想多少有些悖离,因此便会产生对日常生活进行重新认识和反思的想法,这样文本内容变得意味深长起来,“召唤结构”的作用得以发挥。
其次便是张爱玲对小说故事情节安排时“召唤结构”的使用。就像伊瑟尔认为的那样,空白主要还在于联系文本的不同部分,在大多数叙述中,故事线索突然中断,又从另一个视角或预料之外的方向继续下去,其结果造成意义的空白,有待读者补充完成。《金锁记》中曹七巧把来到姜家探望她的哥嫂送走后,回忆起自己还是黄花闺女时的往事,当笔触延宕到床上睡着的没有生命活力的七巧丈夫时,作者笔锋一转,紧接着出现的下一段便是描写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回文雕漆长镜,镜子里的翠竹帘子在第二次定睛看时早已褪了色,看镜子的七巧也老了十岁。这里作者仅用镜子等意象就把岁月流逝简单明了的引了出来,显然和前一段的小说内容产生了时间差,由此在文本中也造成了一定空白。同样情况还出现在小说《倾城之恋》中,当白流苏第二次去香港做了范柳原的情妇后,他们在巴而顿租下了一所房子,而此时范柳原回了英国,在空空荡荡的房间里,白流苏被寂寞和空虚紧紧的围着动弹不得。写到这里,随后的一段便是“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战争的爆发打破了白流苏日日夜夜循环往复的寂静和孤独,然而作者在里有意添上了时间点,使得之前的叙述时间变得模糊起来,白流苏究竟在这里住了多久是一个月还是一年使人不得而知,此后小说情节的叙述也开始加快,这样一来也同样使文本产生了空白。“空白”的出现将召唤读者对文本进行不断的探索和追问,从而调动自己的想象力和个人经验去努力填补空白,使文本内容在阅读过程中变得更加具体化。同时这些空白又服从于作品的完成部分,并在已经完成部分的引导下,使作品实现意义的建构传递出作者想要阐述的观点。在分析张爱玲的创作原则时发现,她曾经说过自己喜欢参差对照的写法,因为这种写法在她看来是贴近现实的。那么通过对《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 第一炉香》等阅读,可看见张爱玲在塑造人物时有意加强了女性形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对男性形象的一种弱化。中国传统道德中对女性的束缚是极为严厉的,尤其是对女性欲望方面的压抑。传统女性的贞洁保守的形象仿佛是一道标杆深扎于每个人的心里。但是张爱玲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是曹七巧还是白流苏或者是梁太太,都与中国传统意识中的形象大相径庭。她们要么是伶牙俐齿,刁蛮善妒,要么就是主动追求异性,与男性在情感上展开周旋。男性形象大多都是遗老遗少,不论是《金锁记》里的姜季泽和长白,还是《倾城之恋》里白流苏的三哥,四哥,他们仿佛一个个都找不到明确的生存目标,不是吸鸦片逛窑子就是坐吃山空流连赌场,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在中国传统父权制度“庇佑”下他们把生命消磨了个干净。这种人物呈现的强烈反差,似乎否定了长期以来在读者生存环境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标准和社会规范,这些人物形象的塑造对社会原有的价值体系提出强有力的挑战。这就与伊瑟尔提出的另一种重要“空白”即由所谓“否定”引起的“空白”有异曲同工之处。而读者在填补空白时,能够获得一种视点,通过这个视点来看那些曾经被接受的社会规范就会变得腐朽不堪了。因此好的文学作品在唤起读者阅读期待时更应该否定它,从而能使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去重新审视生活,发现他生存环境中流行规范所固有的缺陷。从这个意上说,张爱玲“参差对照”的创作观无疑会形成这种由“否定”造成的空白,读者在填补空白时其实也是在改变过去既定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对社会重新进行审视。
三、创作观下的“审美交流”
在张爱玲谈其创作时我们看到这样一句话:“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所谓的“滥调”其实就是她笔下有关于饮食男女的衣食住行,婚姻恋爱等平凡简单的一系列市民生活。作为这一类的普遍社会现象,作家安排什么样的题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读者是否能够从那千篇一律的日常百态中有所领悟。“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的作品,原本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后,原来的主题早已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现了新的启示,是那作品成为永生的。”文学作品的价值如果脱离了读者的参与,是无法独立产生意义的,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读者所做出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和永无止境的解读。所以张爱玲的创作理念最终还是希望通过文学文本达到与读者进行交流的目的,通过对文本的构建去指引读者发现她对生活的感悟,进而他们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获得对个人的理解,也只有这样她的创作才具有永恒意义。就像姚斯所认为的那样一部过去作品不断延续的生命是通过疑问与回答动态的阐释而形成的并不是通过单方面永久的疑问或是回答。可见张爱玲“读者至上”的创作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和姚斯的见解也是不谋而合的。为了使观众能够通过作品的阅读获得对自身的一个理解,张爱玲想必也是考虑到她读者大众群的实际阅读水平,所以创作时并没有一味地采用繁复的技巧,相反在她的小说中我们往往更能看到一些自然朴实贴近市民生活的细节描写,而这其实和她说过喜欢“素朴”的观点是一样的。用简单的笔触还原复杂的生存状态是最容易走进读者内心世界的方法,张爱玲对于生活细节的刻画往往更能使读者大众深有感触,并能够更好地与他们形成交流。例如她对笔下男女人物服饰的精细描写,不仅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状态,同时也暗含了作者想要表达的生存观念。例如《金锁记》中对曹七巧在不同时期装扮的描写:“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绸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两件不同风格的服饰,表现出曹七巧不同时期心理状态的改变。显然在第一句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七巧刚嫁入姜家不久,色彩的精心搭配看还是很明亮的,这其实就能反映出她作为一个年轻女子内心的柔情。丈夫患有软骨病,她缺乏情感的滋润,但越得不到温情就会越想要得到,内心欲望的不断涌现也伴随服饰的穿着表现出来。第二个句子中“青灰”“龙”等简单的字眼就能展现出此时此刻七巧的生活状态。青灰属于暗色系,曹七巧服饰色彩从鲜艳到灰暗,说明她的精神状态必然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暮年时期的她已经一无所有,她知道儿女恨透了她,也不再有什么情感上的欲望有的只剩下连自己也弄不懂的扭曲心态。服饰上的“龙”也能体现出七巧在家中地位的改变,她不再是受排挤者,而是生活在这个独立门户里的掌权人,可以操控着儿女的人生。从服装款式和颜色的变化,暗示出七巧的生命逐渐褪去光彩,灵魂也渐渐被黑暗所吞没。此外文中对长白长安服饰的描写也颇有意味。“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有七八岁光景。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长白长安身体瘦弱却被安排穿上厚厚的棉袍把全身裹得严严实实,实际上这是七巧对儿女精神和肉体上的一种控制和约束,两人即便是在“缎棉袍”“锦棉袍”华丽的装扮下也依旧透露出一股“死气沉沉”,像纸糊的人儿似的活着。有人说张爱玲是彻底的悲观主义者,她看透了人们在奋斗过后得到的始终还是人生的虚无和幻灭。可即便如此在我看来张爱玲始终是个对生命抱有向往,对生存抱有信念的人。正如她自己所说“人生的结局总是个悲剧。老了,一切退化了,是个悲剧,壮年夭折,也是个悲剧。但人生下来,就要活下去。没有人愿意死的,生和死的选择,人当然是选择生。”张爱玲本人就像她在作品中反应出来的那样喜欢色彩明艳的服饰,胡兰成在《今生今世》谈到她“爱刺激的颜色”,连房间布置都是“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张爱玲对这种俗艳色彩的垂爱,其实就是她想传递给读者的人生观的一种折射。俗才是市民生存的本来面目,“俗人俗事”才会让人感到热闹亲切,在作品中她把角色对金钱物质迷恋以及爱欲肉体渴望的展现也正是对现代都市市民人生底子的还原,脱去华丽的服饰,俗就是他们真实而朴素的底子。也正是这些世俗间的俗事才是在末世文明的废墟夹缝中最具有生命力的,最能体现生命永恒的力量。“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她想传递的信念就是在时代如影子般要沉没下去时,每一个人要能够坦然自若的面对死亡,同时也要活在当下,哪怕是以一种最低生活标准也要尽情的释放生命精彩。张爱玲用细致的笔触所描写平凡市民的衣食住行,使文本扣动读者内心最深处的弦,因此与读者交流的过程中更好地产生共鸣,大众在被作品中人物悲欢离合的情绪打动时,也能结合自身的审美经验和生活经历对故事内涵细细品味从而达到净化心灵的目的,实现有价值的审美交流。
四、总结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作品的价值常常是由两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具有不确定性的文学文本,一方面是读者阅读过程中的具体化。任何文本都具有未定性,如果没有读者的参与,它是无法产生独立意义的。文本意义的产生,只有靠读者阅读具体化才能实现。同时读者的解读也不能完全离开文本,要想发现文本的审美特征读者就必须要依循着文本的引导和暗示,从而结合着自身经历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对文本进行再创造。张爱玲秉承“读者至上”的创作原则,这对她的文本构造和创作特色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是“期待视野”还是“召唤结构”的使用,这都使其文学的接受效果即对社会常规惯例的否定以及读者大众的心灵解放得以发挥,也正是因为她的这份执念,使其小说的生命魅力一直延续至今并深受大众喜爱,张爱玲本人也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作家。
[1] H·R·姚斯 R·C·霍拉勃著,周宁 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朱立元著.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3]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上海三联书店,2008.
[4]邓如冰著.人与衣:张爱玲《传奇》的服饰描写研究[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李欧梵、夏志清、等著,陈子善编.重读张爱玲[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
【注释】
[1][3][4][11][12]张爱玲 .论写作[J].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1944.
[2][7][14] H·R·姚斯 R·C·霍拉勃著,周宁 金元浦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5][6][8][9][18]张爱玲著. 金锁记[M].哈尔滨出版社,2005.
[10][15][19]张爱玲著. 倾城之恋[M].花城出版社,1997.
[13]朱立元著.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16]张爱玲. 写什么[J].杂志月刊第13卷第5期,1944.
[17][22]张爱玲著. 流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20]殷允芃著. 那些年,这些人[M]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
[21]胡兰成著.今生今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作者:云南民族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