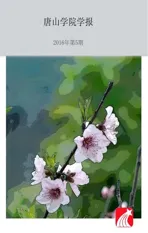从符号学角度看先秦名家对“名”的变化性的关注
2016-10-19刘琪
刘 琪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从符号学角度看先秦名家对“名”的变化性的关注
刘琪
(唐山学院 社科部,河北 唐山 063000)
名实关系是整个先秦时期诸子争论的中心问题。对名实相符关系的追求实际上是在名实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因此,“名”的变化性思想是正确理解名实关系的理论前提。先秦名家对名实关系的分析尤为注重分析“名”“实”的变化。文章从符号学角度研究先秦名家“名”的变化性思想,阐述了先秦名家的“名”“实”思想。
符号学;先秦名家;名实关系
先秦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交替时期。旧体制下的政治经济秩序和社会伦理纲常观念发生了变化,造成“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样“名实相怨”“名实散乱”的社会现实。这种“名”“实”相离的现象不仅会影响到人们正常的思维交际,而且涉及到政治伦理秩序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因此,重新厘定名实关系,使名符其实,便成了思想家和统治者所关注的社会问题,也成了学者们竞相争论的核心。实则,“外界事物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因而我们用来标志外界事物的名称的内涵或含义也在不断变化、充实和丰富”[1]。可见,“实”是不断变化的,作为指称“实”的“名”理应亦随之不断改变以符合其所指称的对象。对名实相符关系的追求实际上是在“名”“符合→不符合→符合→不符合→……”“实”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寻求一个平衡点,一个“名”“实”相对应的稳定时期。先秦各家中,名家四子邓析、尹文子、惠施、公孙龙在探讨名实关系时运用了变与不变的辩证思维方法。可以说,“名”的变化性思想是正确理解名家思想的理论前提。随着近二三十年现代符号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符号学的基本理论为有效探讨“名”的变化性思想提供了较为合适的研究方法。本文试以现代符号学理论为工具,对先秦名家关于“名”的变化性思想作一基本梳理,以期不仅充分展现先秦名家丰富的名实思想,而且为进一步深化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一、符号学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优范式
“范式”这个术语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库恩(Kuhn)从语言学里借用来的,原意是语法中词形的变化规则,由此可以引申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的序中给“范式”下的定义是:“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2]
符号学(Semiotics)是20世纪初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ssure)和美国哲学家皮尔士(Peirce)是世界上公认的现代符号学的两位奠基人。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中,索绪尔将符号定义为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为了将符号、音响形象和概念区分清楚,他在保留“符号”这个词表示整体的基础上,用“能指”(signifier)代替“音响形象”,用“所指”(signified)代替概念。这两个术语的好处就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至于‘符号’,如果我们认为可以满意,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该用什么去代替,日常用语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术语”[3]。“能指”是指符号形式,亦即符号的形体;“所指”是指符号内容,也就是符号能指所传达的思想感情,或曰“意义”。实则,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就是能指和所指,亦即形式和内容之间的二元关系。相对应于索绪尔的符号二元关系理论,美国哲学家皮尔士提出了符号的三元关系理论。皮尔士曾给“符号”下过一个简明的定义:“符号是对某人来说,在某一个方面,或者有某种能力代表另外某一事物的东西。”[4]2继而,他对“符号”进行更为具体的解释:“对于符号,我的意思是指任何一个真实的或塑造的东西,它可以具有一种感性的形式,可以应用于它本身之外的另一个已知的东西,并且可以用另一个我称之为‘解释’(interpretant)的符号去加以解释,以转达可能在此之前还不知道的关于其对象的某种信息。这样在任何一个符号、对象与解释之间就存在一个三元关系”[4]2。在皮尔士看来,正是这种三元关系——符号形体(representamen)、符号对象(object)和符号解释(interpretant)决定了符号过程(semiosis)的本质。虽然索绪尔和皮尔士各自给出了不同的符号定义,两个定义之间存在着差别,但二者之间也有一定的联系。实则,索绪尔的“能指”相当于皮尔士所说的“符号形体”,人们通常称之为“符形”;索绪尔所说的“所指”,大体上相当于皮尔士的“符号解释”,人们通常称之为“意义”或“讯息”。可以说,索绪尔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理论,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从而也就澄清了两千多年来对于“符号”一词的混乱解释。进一步而言,索绪尔和皮尔士关于符号的“二元关系”和“三元关系”学说,奠定了现代符号学坚实的理论基础。
综上,“符号”并不是某个单独的事物或现象,它体现了一种关系,一种解释者的心灵与所指称对象间的对应关系。
20世纪初,我国学者以西方传统形式逻辑为范式研究先秦名辩学。传统形式逻辑的主要内容包括概念、判断和推理三大部分。与此相对应,学者大多把先秦名辩学中的“名”理解为“概念”。这种理解自有一定的道理,但把“名”理解为符号更接近其本意。
首先,从“名”的表现形式来看。“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汉]许慎:《说文解字》)这可能是“名”的初始意谓,它缘于“冥”而出于“口”。“命”原在于称呼、告诉,“自命”即自呼、自告;只有自呼、自告方能在晦昧夜色中明示自己为何人,所以“名”由“命”而与“明”通。“名”和“命名”自始就同语言的发生关联着。而文字是将语言以特定的书写形式来表达思想的。因此,“名”的存在形式就是字或字的复合体。与拼音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相比,汉字属于表意体系的文字,或称为“语素音节文字”。不管用什么名称,只要是汉字,就一定离不开意符,汉字总是既表音又表意的,文形与字义有密切关系。拼音文字与词的音、义联系,是线性的;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同词的音义联系,则是环状的。具体如下所示:

拼音文字汉字字形→词音→词义字形词音→↓词义→
从上述关系中可以看出,拼音文字的字形和词义,都只同语音形式发生直接联系,而它们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联系;而表意文字体系的汉字,字形和词义不仅通过语音形式发生联系,而且词义和字形之间也存在直接的联系[5]。英国符号学家特伦斯·霍布斯的论述也有助于加深对这一观点的理解。他说,“语言符号的特性可以根据符号的‘概念’和‘音响-形象’这两个方面的关系来确定,或者可以用索绪尔著作中的话来说,就是所指和能指。因此,一棵树的概念(所指)和由词‘树’(即能指)形成的音响-形象之间的结构关系就是一个语言符号,而一种语言正是由这些符号构成的”,但他又认为在“音响-形象(或能指‘树’),亦即概念(或概念所包括的所指)和在大地上生长着的实际的物质的树之间并无必然的符合之处。简言之,‘树’这个词没有‘自然的’或‘像树那样’的性质,为了认可这个词,不可能诉诸语言结构之外的‘现实’”[6]。可见,拼音文字符号与它的所指之间的关系是十分任意的,对此,索绪尔的论述则更加形象。他说:“既然我讲英语,我就可以用‘dog’(狗)这个施指来指具体的一种动物,但是这个声音序列决不比另一个声音序列更适合来表达‘狗’这个概念。如果我的语言社团的成员同意,‘lod’,‘tet’,‘bloop’也能起同样的作用。”[7]汉字的表意特征,是由古文字的象形性质所决定的。古文字的象形性质可从殷代甲骨文的基本词汇中得到说明、验证。例如,甲骨文中的“马”字,就是以客观存在的马类动物的马头、马鬃、马尾为突出特征而造出的象形文字。在当时,人们看到“马”字,就不只是看到一个代表“ma”(马字的今音)音的符号,而且还从这个字的形状上知道它的含义。它所指称的对象,决不会误解为与ma音相同的其他事物。在这里,“马”字的形状起到了一种决定性的约束作用。由于“基本词汇是语言的基础之一,是构成词汇的核心。可以说,一种文字怎样记录基本词汇,这集中地表现了文字的性质”[8]。甲骨文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汉字,周代金文同甲骨文相当接近,只是形体变得圆润、方正、匀称。秦统一中国后,对篆文(大篆)加以简化,成为中篆,但它仍然保留着象形的特征。因此,对于我国古文字的象形性质及由此所决定的表意特征,是不容怀疑的。先秦辩学的“名”,诉诸视觉有其形,诉诸听觉有其声,“名”的形状本身又表达一种既定的思想和观念,因此,“名”是形、声、意的结合体,它集能指与所指于一身。也就是说,“名”是一种符号。
其次,符号和概念的区别在于: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是思维领域内的东西,是索绪尔所说的“所指”。而符号是符形(能指)和符义(所指)的结合体,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先秦时期所用的诸如“马”“牛”“人”等“名”并不是事物本质属性的反映。这可从《墨经》《荀子》的论述中找到依据。“以名举实。”(《墨经·小取》)“举,拟实也。”(《经上》)“拟”的含义就是摹拟,即按照事物的样子画下来。这如同许慎说的象形字,许慎说:“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出,日月是也。”《经说上》讲得更明白:“名若画虎。”也就是说,写“虎”字,就像画虎一样。显然,《墨经》中所讲的“名”不是概念,而是符号。荀子关于“名”的定义是:“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荀子·正名》)根据许慎《说文解字》,“期”有约定之义,“累”有附加之意。荀子所理解的“名”就是通过约定,附加在“实”上的符号。此外,“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名”和“实”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某个“实”用什么“名”来表达,某个“名”表示什么“实”,既没有自然的法则,也没有固定的模式,而是约定俗成的结果。这无疑更进一步证明了“名”即符号。
综上可以看出,符号学方法是深化先秦名辩学研究的更合适的范式。
二、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
根据索绪尔的观点,语言是一种独特的机制,这个机制的本质是建立在任意性的关系之上的。因此,语言符号同时具有两个看似截然相反的性质——不变性和可变性。要准确理解这两个看似矛盾的性质,除了需要结合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之外,还要考虑语言的社会性和连续性等因素。
任意性(arbitrariness)是存在于语言符号的两面(即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存在于语言符号之内的性质——一种客观的性质,不论人们怎样感受它*许国璋曾强调人们对任意性的感受;赵元任也曾谈及普通语言使用者对任意性可能存有的无知。两相对照,会发现二人的论述有所不同,后者清晰明了,前者似值得推敲。分别参阅许国璋的《许国璋论语言》第31页,赵元任的《语言问题》第3页。。所谓任意性就是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之间事实上没有自然的联系,或也可说,二者之间没有固有的或逻辑上的联系。索绪尔称其为语言符号的“两个头等重要的特征”之一、“第一原则或基本原理”。当今,有学者将所谓“象似性”(iconicity)与任意性对立起来,用前者挑战后者,认为“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主要关系是象似性,而不是任意性,象似性具有自然的、本源的、主要的性质”[9];象似性主要就语言的结构而言,指“句法结构跟人的经验结构之间有一种自然的联系”[10]。虽然索绪尔没有使用“象似性”的概念,也没有这方面的讨论,但他明确认识到语言具有可论证性(相对任意性),指出没有一种语言是完全不能论证的。他将不可论证性与可论证性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并没有顾此失彼。此外,他明确指出某些着重于词汇的语言具有较少的可论证性(较多的任意性),而着重于语法的语言则有较多的可论证性[11]。关于象似性还有类似的观点:“语言中的词是象似性度最低的符号,词与物的联系有极大的任意性,而词与词之间的组合和聚合关系好比图画,其象似度比较高”[11]。可以看出,二者虽使用了不同的术语,但基本含义是一致的。当然,需要明确的是,一旦一个符号已经在语言社团中被确立下来,任何个人都很难对它进行任何改变。因此,任意性并不意味着说话者可以任意选择能指,而是指现实中跟它没有任何联系的所指是任意的。
在理解任意性的基础上,对“不变性”(immutability)和“可变性”(mutability)的解释就顺理成章了,所谓“不变性”就是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对固定或者二者在某一段时间相对不变的状态,由不得个人或大众随意对其加以改变。这种性质主要来源于语言被众人使用时所产生的社会规约性或约定俗成。而“可变性”就是指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变化或转移的性质。可见,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同时提供了条件。
另外,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与语言社会性、连续性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语言是一种存在于集体之中的社会现象。它主要作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际过程,因此没有使用语言的大众就没有语言。这种社会性意味着语言的变化必然取决于大众而不是个人。这些众多的语言使用者不愿意也不可能突然改变他们熟悉且融于他们日常生活的交际方式。个别语言使用者可能会偶然创造某些词,但究竟能否被大众接受并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惯用语言,还有待证明。也就是说,语言的社会性有利于在一定时期内维持语言相对稳定的状态。更进一步说,社会性必然引出“时间”这个语言无法回避的因素。首先,语言与过去相联系,是历史的遗产或延续。这就必然阻碍或限制语言的自由变化。其次,语言使用者从来没有年龄的界限。语言代代相传,绵延不断。这种通过时间体现出的连续性必然有助于语言符号的不变和稳定。然而,同样的延续性,即时间因素,又会引出恰恰相反的结果:语言符号的可变性。索绪尔说过,“变化的原则建立在连续性的原则上”[12]。也就是说连续性本身就意味着变化,变化寓于连续性之中。语言符号的变化不能脱离社会因素。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语言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两种性质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不变性与可变性处在一种辩证关系中。索绪尔主要致力于从理论上阐述语言符号的性质,以期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语言的本质。我们也将此作为探讨先秦名家关于“名”的变化性的理论依据。
三、先秦名家对“名”的变化性的关注
“夫名,实谓也。”(《公孙龙·名实论》)这里名是指称实的。实变化了,名也必然发生变化。按照符号学的观点,没有一成不变的符号,对象变了,指称对象的符号和符号的解释也必须变。因此,探讨“名”的变化首先要从分析“实”入手。
公孙龙主要是结合“物”“位”“正”这几个核心概念来定义“实”的。《公孙龙·名实论》说到:“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把“天地”及其“所产”称作“物”,即是把时空中存在的一切称作“物”。但既有的形形色色的物并不都是“实”,称得上“实”的物,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物其所物而不过”。谭戒甫在给公孙龙子的定义作解释时说,“夫天地之为物,以其形也;则凡天地之所生者,亦皆以其形为物”[13]。“所物”就是指物体以它的物理形态为标志,不同的物其物理性状是有差别的。王绾也解释道:“实必有其界限标准,谓具有某种格程,方为其物。”[14]可见,所谓“实”就是那些占据一定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存在,是符合客观事物本性的那种“物”,那些不完全符合或背离客观存在本性的“物”都不能称为“实”。具体而言,“实”就是对于某类事物的实质或共相的体现。当“实”完满到它应有的程度而没有欠缺时,称其为“位”。此即他所谓“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位”意味着一种分际,它标示着在以某名称谓个体事物时与同一名所指称的此类事物共相契合无间而至为完满的那种情形。所谓“正”即是“物”之“实”当其“位”,亦即当以某“名”称谓的某物体现了由此“名”指称的这一类物的共相或实质,并且被这“名”指称的共相或实质近乎完满而达到极致状态时,方可谓之“正”。可见,公孙龙理解的“实”是一类事物的共相。
共相总是由某一“名”来称呼的。特殊的是,称呼某一个别事物所用的“名”往往与表述它所属种类之事物的共相所用的“名”是同一个。如果某事物体现了某一类事物的共相或实质,用指称其共相或实质的“名”称呼此事物可谓“名”“实”相符。然而物是不断变化的。作为物的派生物“实”,按照“实随物变”的原则,也必然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某事物不能或不再能体现某一类事物的共相或实质,即“实”发生了变化,那么用指称某共相或实质的“名”称呼此物便是“名”“实”不相符,这时,“名”的意谓在对个体事物的称呼和对一类事物的共相或实质的指称上就大相径庭了。如,一块岩石因风化或其他缘故虽然保持了岩石的外观,但已不再有坚硬可言,“石”所指称的那类存在物所具有的“坚”的共相或实质已不为它所有了,虽然仍称为“石”,但已名不符实了。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符号是落后于符号所指称的对象的,当能指没有变而所指随着其所指称对象的改变而有所改变时,应格外注意此符号的前后区别。公孙龙看到这一点,他提出“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彼谓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道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强调名实的对应性。这种情况下名虽同然义不同,如果不加注意任由其发展,就会出现“不当而当,乱也”的现象。为防止混乱现象的发生,公孙龙进一步提出了正名实关系的准则,“其名正,则谓乎其彼此”,做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公孙龙·名实论》)。即“名”必须具有单义性和确定性,实则关于理想语言的设想,具有明显的理想主义的特征。这种理想语言只有在数学和逻辑学中才能得到实现,在自然语言中尤其是汉语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古代汉语中没有注意区别词性,即名词、动词、形容词等,经常会出现一词多义、词语混用的现象。
先秦诸子中,公孙龙是第一个从符号学角度提出要区别词性的学者。他在不同文章中都对此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他在《白马论》中区别了“不定所白”和“定所白”:“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就是说,当说“白马”的时候,这个“白”是“定所白”的“白”,而这个“定所白”的“白”与那个“不定所白”的“白”是有区别的,前者不是后者。简言之,所谓“不定所白”就是说作为抽象名词的“白”,相当于英文的“whiteness”;而“定所白”的“白”是指作为附在名词之前的形容词的“白”,相当于英文的“white”,如“白马”“白纸”等。他在此区别了处在一定语境中的“白”与抽离一定语境中的“白”。在《坚白论》中区别了“定所坚”和“兼”,即“不定所坚”:“物坚焉,不定其所坚。不定者兼,恶乎其石也?”说某物是坚硬的,坚硬性却并不限定在这一物上。不限定在某一物上,即是说它可以为其他物所兼有。在《指物论》中区别了“指”和“物指”,“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莫非指,而指非指也”。正是因为人的“指物”这一认知活动把“指”和“物”关联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不定所指的“指”与作为指认事物时定其所指的“指”是同一个名。
词性的问题长期为人们所忽视。一直到两千年后的清朝末年,严复在翻译穆勒(Mill)的《逻辑体系》一书时,才再次提出这类问题。严复在翻译该书的“论名”一章的第四节“言名有玄、察之别”时说:“名之分殊莫要于玄、察。察名何?所以名物也。玄名何?所以名物之德也……名可玄可察,视其用之如何。若‘白’。前云‘雪白’,其‘白’为察名,此尤言‘雪为白物’,凡白物之名也。今设言‘白马之白’;前‘白’为区别字,合‘马’而为察名;后‘白’言色,谓物之德,则为玄名,不可混也。”严复于此专门加了一个注,说:“案玄、察之名,于中文最难辩,而在西方固无难,其形音皆变故也。故察名之‘白’,英语‘淮脱’也;玄名之为‘白’,英文‘淮脱业斯’也。独中文玄、察用虽不同,而字则无异,读者必合其位与义而审之,而后可得。”[15]可以说,严复是直接继承了公孙龙的理论,而公孙龙在两千年前就已经注意到玄名(抽象名称)与察名(具体名称)的区别,这是中国符号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进一步言之,在语符或能指不变的情形下,语义或所指会因为它与其他语言搭配状况的不同而不同。“白马”之“白”不同于“白石”之“白”,也不同于“白羽”之“白”,作为能指的“白”字在“白马”“白石”“白羽”中并无不同,但其所“白”的意谓已经有了微妙的差异。在现代语言学领域内,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错落不定,用俄国形式主义者的话说,即是“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是不同的色泽。”[16]公孙龙对同一能指因为“相与”(与其他语词相搭配)情境不同而引致所指内涵、外延变化的发现,是纯然中国式的。这也就说明了自然语言中的“名”并非完全不能做到单义和确定,只要将它结合在一定的语境之中,它是可能实现“彼彼止于彼,此此止于此”的,即在一定的语境中,一个符号只与一个特定的对象相联系。这时人们在使用和理解时是不会产生歧义的。
上述主要是针对某一个单名的能指或所指而言的,而不同的单名亦可以互相结合形成新的名称即兼名。当两个不同的单名组合成兼名之后,兼名中的单名就只是作为构成兼名的两个有机部分,而不再作为有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的名称符号存在。关于这个问题,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有过论述,在论及“白马非马”时,他说:“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马”与“白”这两个名称在未组合之前,“马”名就是“马”名,“白”名就是“白”名;“马”名和“白”名相与、结合,就组成了一个新的名称符号即兼名“白马”。在此基础上,他在《通变论》中更为详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所谓“通变”,变化之通例之谓。《通变论》即论述了两符号(“名”)相与(相结合)成一复合名称后其内涵变化的某种规则。《通变论》云:“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与右可谓二乎?曰:可。”这里的“一”“左”“右”分别喻指不同的单名,两个不同的“一”(或“左”与“右”)相与就生成一个新的名称符号即兼名。所谓“二无一”(“二无右”“二无左”)用现代符号学来解释就是兼名中的单名由结合之前的具有确定指称对象的独立的名称符号,变成了失去自己特定指称对象的不具有独立名称符号性质的东西,即变成了兼名在能指上的组成部分。虽然,从表面上看,兼名“白马”中的“马”(“左”“右”)在能指上仍保持原有的笔画形状,但相对于作为单名的“马”(“左”“右”),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通变论》中“二无一”思想的内容。此外,为了使“二无一”思想更为明确、深入,公孙龙又提出了两个辅助命题加以验证:“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青以白非黄、白以青非碧”。从形式上看,这两个命题将单名扩大到两个任意单名,从而也就扩大了“二无一”思想的适用范围;从内容实质上看,这两个命题与“二无一”表达的思想无根本性差异,都是强调原本具有特定能指和所指的单名在相与构成兼名后,在性质、功能和地位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这一变化并不影响原来作为独立名称符号而存在的单名的地位和性质。
相比较于公孙龙对“实”的明确定义以及对名实关系的详细论述,惠施虽无一言提及“名”“实”,然审其“历物十意”十个命题(见《庄子·天下》),终不过示人如何用“名”映“实”最为得当。实则,惠施对“实”的界定或可从庄子对他的评价中看出,庄子谓其“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无已”,“弱于德,强于物”,“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见《庄子·天下》),这些评论从侧面反映出惠施将世界万物作为理论探讨的对象,他所谓的“实”就是“各各实在的事物的实际情形”。只不过,他选择了与常人相异的论述角度,他从事物绝对运动的观点出发,提示人们事物的含义呈开放增长的状态,“其‘实’并不重在对某个确定的标准或尺度的凭靠或依赖”[17]。因此称呼事物之名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事物之名是可以相互转换、不断改变的,不可无条件地拘泥原有的符号之名。现选取几个典型命题论述之。
命题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唐代杨倞注《荀子》一书,其注所引“山渊平,天地比”一语如下:“或曰:天无实形,地之上空虚者尽皆天地也,是天地长亲比相随,无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则天亦高,在深泉则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远近皆相似,是山泽平也。”此处被引述的“或曰”,是对该命题的不易之论。该命题重在陈述由于人们观察事物角度的不同,会产生有别于与以往的认识结果,不可执拗于事物固有的名。
命题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现代学者杨俊光援引恩格斯所谓“运动本身是矛盾”以理解“日方中方睨”,援引恩格斯所谓“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而“生就意味着死”论述“物方生方死”的方法颇具一格[18]。日中和日睨,生和死都是相对的。该命题重在强调人们应该随着事物的变化而更新对事物的认识,名随实变。
命题六:“南方有穷而无穷。”和命题七:“今日适越而昔来。”这两个命题分别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强调事物存在的相对性。任何一个被称作“南方”的地方对于比它稍南的地方来说都是北方,在“实”的世界或经验的世界里,永远不会有绝对意义的“南方”。“南”“北”在空间维度上是相对而存在的。同理,“今”与“昔”的相对就是当下的相对而不只是某个较长时间段的相对。在时间之流中,“今”即是“昔”,刚说是“今”,就已变成了“昔”。再次强调了实体变了,名也必须随之改变。
综上可以看出,惠施对事物的认识是灵活变通的。其历物的相对性,明显体现了实的变化,同一事物由于命名主体“历”的观点变化或对象环境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命名结果。事实上,常识中总是将“中”和“睨”、“生”和“死”、“南”和“北”等名置于静态的没有转换的境地,用既有的名严格限制事物的状态。实则这是将名实关系本末倒置了,并没有随着事物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名以适应之。在这种态度中起作用的是多数人日用而不察的形式逻辑。如果习惯于甚至依赖这种形式思维,那么必然认为惠施的这些思想异乎寻常、不可理喻,甚至批评其为“不法先王,不是礼仪,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荀子·非十二子》),“惠施为诡辩主义的有力开创者”[19]等等。这着实埋没了作者灵动的智慧。惠施与公孙龙一样,都表达了名随实变的思想。但两者不同的是,公孙龙认为名的变化在于人的认识能力不断趋近事物的本质,而惠施认为“名”变化的原因在于“实”本身位置的改变以及人的观察角度的不同。
无独有偶,邓析对“名”的变化性的论述与惠施的上述思想互为映射。他肯定了认识主体的“知”“察”随事物的变动而变化。再有,“世间悲、哀、喜、乐、嗔、怒、忧、愁,久惑于此,今转之:在己为哀,在他为悲;在己为乐,在他为喜;在己为嗔,在他为怒;在己为愁,在他为忧;在己若扶之与携,谢之与让,故之与先,诺之与已,相去千里也。”(《邓析子·转辞》)这些名有各自的所指,由于主、客、己、他的差异,即使相类似的情绪反应,如悲哀、喜乐、嗔怒、忧愁,在使用上也应该有严格的界定。即使是同一主体,不同的情态、语气,也都有差别,如扶、携、谢、让、故、先、诺、己等。《邓析子·转辞》对“名”对应的“实”所作的精微分析,体现了只有名随实变,才能真正做到名实相符。
此外,《吕氏春秋·离谓》记载的“两可”之说更是体现了邓析注意到语言符号含义的可变性,就是“同名异谓”这种现象。“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尸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买矣。’得尸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谈话的语境发生了变化,即符号和解释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因此,同一个表达“安之”就可以回答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两可”中,此可和彼可虽同名,但具体使用者的解释(含义)是不同的。这也深化了对“名”的认识。
当然,肯定名的变化性无疑是正确的。但名的变化并不是随心所欲,没有任何限制的。因为名一旦制定出来,就具有确定的含义和指称,一名指称一实,一实对应一名,名实必须相称相应。这种确定的关系具有一定的规范性和约束力,是不能随意更改的。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名不称其实,实不改其名,而名实散乱。正如索绪尔指出的那样:“符号对它所表示的观念来说,看来是自由选择的,相反,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不是自由的,而是强制的。……一旦语言选择了一个符号,它就不能自由地被另一个代替。这一事实某种程度上包含着自由中的非自由矛盾,(这一事实)可以通俗地叫做霍布森(Hobson)选择*霍布森选择,意思是任何人只能选择“这个”,没有其它选择,要么就什么也不能选择。这个术语起源于英国马车出租人霍布森(1544-1631)特殊的经营策略。他开办了一个小旅馆,养了40匹马供顾客享用,但为了体现公平公正,需租用马的顾客必须选择距离马厩门最近的那匹马。每一顾客必须这样做。实际上,霍布森选择是服务行业给顾客提供公平选择的一种经营方式。现象。人们对语言说:‘你选择罢!’但是随即加上一句:‘你必须选择这个符号,不能选择别的。’已经选定的东西,不但个人即使想改变也不能丝毫有所改变,就是大众也不能对任何一个词行使它的主权;不管语言是什么样子,大众都得同它捆绑在一起。”[20]对此,《尹文子》一书中举出了大量反面例子加以验证。如:“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尹公子·大道上》)“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吏,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易。”“康衢长者,字僮曰善博,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子是改之,宾客往复。”(《尹公子·大道下》)“美”“丑”“盗”“殴”“博”“噬”等语词符号一经产生就具有了约定俗成的含义,这种含义被社会所认可。忽视符号的普遍规范性和社会共约性原则,就会重现黄公、庄里丈人和康衢长者的闹剧,阻碍交际的正常进行。此时要想消除混淆,就需要“通意后对”(《经下》),即分辨符号的含义再进行交流。
四、代结论
先秦名家对事物变化性的探讨,是一种灵活变通的认知态度的体现。他们不满足于事物的固有状态,而是力图指出(事物)A并不总是A,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变成非A,强调A存在的条件性和变化性。事物的变化必然引起名称的变化。而这种关注事物、名称存在的条件性和变化性的思维方式实则是辩证思维的具体体现。辩证思维作为中国古代思维最显著的特点之一,这种日用而不察的思维方式着实对先秦名辩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发挥着重要的刺激作用。实则,不论是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抑或是从符号学的角度,都是力求为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提供尽可能多的分析工具,从而使多种分析工具相互融贯,达到全面深化中国逻辑史研究的目的。
[1]克里普克.命名与必然性[M].梅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7.
[2]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3]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02.
[4]皮尔士.皮尔士手稿[M]//中国符号学会.逻辑符号学论集.上海:百家出版社,1992:2.
[5]苏宝荣.词义研究与辞书释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9.
[6]特伦斯·霍布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M].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16-17.
[7]卡勒 J.索绪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0.
[8]周万春.汉字部首例解[M].北京:知识出版社,1991:20.
[9]王寅.论语言符号象似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4-7.
[10]沈家煊.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3(1):2-8.
[11]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New York,London:Mcgraw-Hill Paperbacks,1959:133.
[12]Saussure F de. Saussure’s third course of lectures on general linguistics(1910-1911)[M]Oxford:Pegamon Press,1993:98a.
[13]谭戒甫.公孙龙子形名发微[M].北京:中华书局,1963:57.
[14]王绾.公孙龙子悬解[M].北京:中华书局,1928:88.
[15]穆勒.穆勒名学[M].严复,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26-27.
[16]梯尼亚若夫.诗歌中词的意义[M].方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1.
[17]黄克剑.“名”的自觉与名家[J].哲学研究,2010(7):31-41.
[18]杨俊光.惠施公孙龙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54-55.
[19]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424.
[20]Saussure F de. Coru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1:71.
(责任编校:夏玉玲)
The Focus of Literary Masters in the Pre-Qin Period on Change in Words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LIU Qi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Tangshan University, Tangshan 063000, Chin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is the center of debate among the Pre-Qin period scholars. Actually,the focu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is to seek a balance in the process of constant changes in the relationship. Therefore,the change in words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The pre-Qin literary master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in words and the world when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tudies pre-Qin literary masters’ view of change in words from the semiotic perspective, and expounds their opinions on names and the world.
Semiotics; Pre-Qin literary master;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ds and the world
B811.2
A
1672-349X(2016)05-0054-08
10.16160/j.cnki.tsxyxb.2016.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