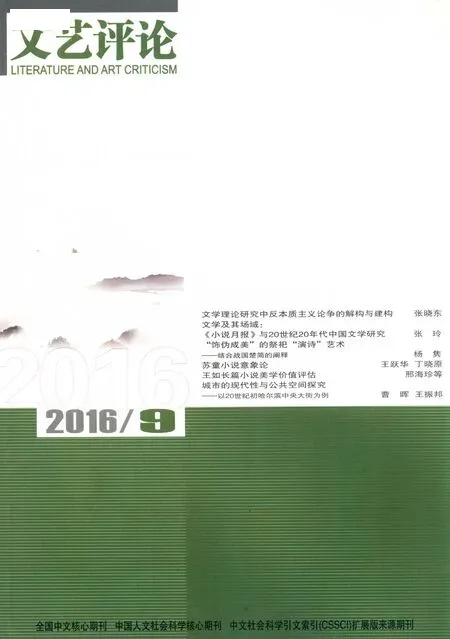“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
2016-09-29徐勇
○徐勇
“后爱情时代”的匮乏及其欲望叙事──论韩东的《欢乐而隐秘》及其都市小说写作
○徐勇
说起韩东,读者会想起他的那首著名的名叫《有关大雁塔》的诗,而不自觉地把他和诗人联系起来,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因为,就韩东而言,他写得更多、用力更大的却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作品常常作为晚生代的代表作品而被举例,某种程度上,他的小说见证或者说表象了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的深刻转型。只是在他那里,这一转型,是以欲望的书写的形态表现出来。欲望或爱情的幻灭,是韩东思考时代和世界的方式方法与支点,这一思路在他的近作《欢乐而隐秘》(2015)仍有延续。在这部小说中,韩东一如既往地发挥他的想象力和编织情节的本领,女主人公也极尽本能地生活在“欢乐而隐秘”之中,沉溺其间,忘乎所以。这部小说初看起来,同作者的其他小说并无二致。但终究,在这部小说中,还是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韩东,一个在禁欲和纵欲、张扬和内敛、挥霍生命和自我救赎之间徘徊,进退失据,而又试图弥合与企图敞开日常生活的平庸、诗意和矛盾,并努力达到一种混合着人生回顾与彻悟之后的平静的韩东。这是否是韩东的蜕变的表征?抑或迷途知返立地成佛?
一
这一小说的开端让人不禁想起陈忠实《白鹿原》的开头:“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白鹿原》)《欢乐而隐秘》中则有这样的表述:“他们在一起大概有三年多了,果儿堕胎不下五次,也许已经六次了,多到我已经记不清了。”(《欢乐而隐秘》)这都是在强调数字的多,就像白嘉轩娶过七房女人并不表示他的生殖力强大一样,果儿堕胎六次甚至更多也并不表明她的生殖力旺盛,恰恰相反,她的生殖力的旺盛背后,是青年男女沉溺于肉欲的表征。在这里,纠缠于六次抑或七次,是没有意义的,虽然七次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常常不免有其特定内涵,诸如七夕、祭七等等。“七”之为数只是一个象征,果儿因受叙述者秦冬冬“我”——也是次要主人公——礼佛的影响之故,而想到去须弥山超度被她打掉的孩子的“婴灵”,于是便有了尔后的一系列“奇遇”。说是奇遇一点都不夸张。在去须弥山的路上,果儿和他的男友张军阴差阳错遇到了齐林,齐林对果儿一见钟情,果儿和齐林间的情感纠葛于是而生,而这个齐林,竟是果儿在14年前偶然救过的故交。所谓“前世今生”的佛教式的宿缘在这当中逐渐演绎为一场精神之爱与纵欲之间的竞逐。最后,精神胜出,欲望败北,果儿也修成正果,立地成佛。从这个角度看,小说女主人公取名“果儿”,是否也有修成正果之意?是耶非耶?
小说在情节主题上始自纵欲,终于精神上的自我救赎,这是韩东小说创作的新变的表征。韩东的小说,向来是以对欲望的毫不掩饰的表现为乐事。他既不是那种窥欲狂式的欲望猎奇,也不是剥除诗意掩盖下的欲望凸显,欲望之于韩东,就像穿衣吃饭一样的本能,既没有刻意被夸大,也没有遮遮掩掩。就欲望书写而言,韩东的小说的贡献正在于那种对欲望的日常视角的展示,欲望的呈现,就像人有弱点一样平常,让人既感可亲又觉真实。但这也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当欲望只是被当作欲望表现的时候,这样的欲望书写能走多远?
事实上,沉浸在欲望书写中的韩东,也一直在思考性之欲望的表现问题。当谈欲色变的时代过去之后,欲望如何表现以及如何对待欲望,一直是韩东思考的问题。《美元硬过人民币》中把欲望的表现放在世界格局的角度展现,小说中“小姐”通过对美元的想象而获得的满足,让人回想起郁达夫在《沉沦》中把欲望的满足置于国家强弱的背景中展现,两者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在韩东的年代,欧美国家的话语优势不再仅仅体现在军事、经济或政治殖民上,更是体现在以货币为代表或象征的文化殖民上,人们在美元上获得的想象性自足直可以比拟身体上的欲望的满足。这篇小说没有孤立地对待欲望问题,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表象,也确实联系着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和市场化的商业逻辑。韩东在这篇小说中,把欲望的满足放在美元的坚挺的层面表现,确有其不可否认的象征色彩。这样一种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背景下的爱欲表象,在他的《中国情人》(2013)中有进一步延续。只不过,在这部小说中,对美国文化的想象不再是通过美元这一中介形式,而是在一个去国/回国的中国男人张朝晖身上呈现。当年瞿红同张朝晖之所以有高潮的性爱体验,莫不源自于手握画有张朝晖的画盘的存在。可一旦对美国的想象付诸实践呢?结果又会怎样?张朝晖费尽心机地要“到美国去”,可当如愿以偿到达美国后却发现美国并不如想象的那样遍地黄金,他在美国十数年,只能身处边缘始终不能融入到当地的主流社会中。反讽的是,当他回国寻找商机,竟又恍惚,中国的开放包容竟然比美国更显得美国,他的落后于时代可见一斑!成为美国人后的张朝晖在面对中国女人的身体和心理时两皆茫然无措,此时,张朝晖与瞿红的旧爱重拾也因为这种所谓的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而被延宕至无。小说中,瞿红离开张朝晖后摔碎画盘这一象征行为某种程度上就显示了想象的终结及其向实践的转变。在这里,可以看到,从《美元硬过人民币》到《中国情人》显示出韩东对欲望表象及其空间关系的思考的转变:如果说欲望不仅指涉对空间差异的想象的话,那么此时中国人也不应成为涉及美国的欲望对象或自我指涉物。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情人》表现出了韩东对自近现代以来有关空间和欲望之间关系的文化政治想象的祛魅。这也说明,韩东其实是把欲望的表现问题放在其他问题的背景下展开的,他并没有孤立地表现欲望。欲望是他的表现角度而非目标。
对韩东而言,对欲望的“祛魅”式表现是他的欲望书写的价值所在。在《我的柏拉图》中,从主人公王舒同三个女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窥见作者对爱欲问题的思考方向。妻子的背叛让主人公感到了爱情的虚妄,但他对费嘉的爱里,也并不仅仅包括“柏拉图”式的精神之爱,其更多涉及到知识分子的软弱、虚伪和一厢情愿,实际上,这已经是一种所谓的精神上的自慰,因此,一旦这种精神上的自慰不能得到满足,费嘉拒绝了他,其结果就会从精神向肉体的层面演变:对钟建珊的利用和从她身上获得的赤裸裸的欲望的满足。在这里,韩东是把欲望放在爱情的对立面的角度加以表现的,其结果自然是表现出对欲望的“祛魅”。就中国当代小说而言,爱/欲是联系在一起的,欲望往往是置于爱情的次等地位的,可有可无的(如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更多的时候,欲望又是同爱情合二为一的,也就是说,没有爱情的欲望,往往是不合法的或者说不道德的(如艾伟的《爱人同志》《爱人有罪》)。虽然说,在这一脉络中,又有王安忆等从欲望的张扬的角度表现欲望,但她是从爱与欲的分裂的角度表现欲望,爱欲表现中的爱情神话并没有被打破(如王安忆的“三恋”系列)。在这一小说中,韩东把欲望放在精神之爱的对立面的角度加以表现,其既让人看到了爱情的虚妄性,同时也呈现出欲望的赤裸裸,也是真实的存在。在这里,爱情神话的破灭与欲望的真实面目的呈现之间,是一体两面的,同时共存的。循着这一思路,他又开始思考欲望在摆脱爱的精神束缚后的演变方向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交叉跑动》可谓意味深长。小说的男主人公李红兵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欲望解放而带来的欲望的无限膨胀,但当他因此而锒铛入狱并开始反省自身,转而寻求一种在欲望的满足当中爱的精神上的付出的时候,却发现其实是南辕北辙,他与他的女友毛洁是在两个方向上“跑动”。所谓“交叉跑动”即是指欲望解放之后这一“后爱情时代”中的爱和欲的悖论的象征:欲望恰如“潘多拉的魔盒”,一经开启,便难以原来的面目呈现。
但这也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当欲望仅仅是欲望的时候,这时的爱情又以何种面目表现自身?对这一问题,韩东在他的另一部长篇《我和你》中有进一步的思考。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也是韩东的小说中最富有深切体验,某种程度上也最能代表他的思考深度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的是一个叫做徐晨的作家同几个女孩之间感情纠葛的故事。在这部小说中,韩东没有简单地把爱和欲关系割裂来表现,他把两者放在一个辩证的角度表现,因而也更复杂而让人深思。在认识苗苗之前,徐晨同朱晔之间有过多年的恋爱关系。但这一恋爱关系更多时候是以无欲之爱的形式呈现,朱晔的性冷淡和身体上的排斥,让徐晨难以接受以至于最后分手。如果说爱必须依附于欲望的形式表现自身,韩东又发现,两者之间往往又并不总是一致与协调。徐晨和苗苗之间,既有爱的纠缠,又有身体上的愉悦,两者很难两分。虽然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受伤害和弱者的角色给予了男性主人公徐晨,但其表现却是真切而让人唏嘘的。他和苗苗之间的错综纠葛,几度反复,皆因为爱欲的关系中还掺杂着某种可以称得上是情感体验的神秘东西,情感的复杂性赋予了欲望的多重内涵,也让爱与欲望本身具有了某种悲壮性色彩。
二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韩东之所以执着于欲望的表现,似乎想告诉我们,欲望的满足不仅仅指涉欲望本身,而是联系着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欲望的满足程度及其表现方向,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文化冲突的表征。但韩东又似乎感觉到了难以为继。纵然欲望的满足涉及到文化冲突,这一文化冲突下的主人公却并不自知,他们沉溺于欲望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这样的爱欲终究不过是自焚或自我毁灭。或许,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韩东在他的新作《欢乐而隐秘》中才开始思考禁欲的可能及其欲望的自我救赎等问题。在这部小说中,这一思考的方向是放在主人公秦冬冬“我”这一视点人物身上得以呈现的。“我”是一个对女性没有欲望,但又十分关心女性的男性。有意味的是,这一无欲的身体,又是一个礼佛的身体。参照秦冬冬和女主人公林果儿的闺蜜关系,这一无欲和礼佛,显然是针对欲望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韩东是把秦冬冬放在一个果儿的“他者”的位置来表现的,这是一个旁观的、审视的视角,因而就带有对欲望的审视的味道了。
林果儿本是一个快乐、简单而凭本能生活的人。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她生活在本能的层面,追求的是快乐原则,其虽说不上是纵欲,但也毫不加以节制,故而就有了六次或七次的堕胎。对于生活在本能层面的人来说,堕胎并不算什么,而中国的法律、法理也似乎不像西方的法律那样,会就堕胎的合理性争论不休。但民间的说法则可能又是另一回事。胎儿也是生命体,因此堕胎亦被认为是杀生,这一说法让人想起莫言的《蛙》中女主人公姑姑听到初生婴儿哭声的幻景:“姑姑说她原本是最爱听初生儿哭声的,对于一个妇产科医生来说,初生婴儿的哭声是世上最动听的音乐啊!可那天晚上的蛙叫声里,有一种怨恨、一种委屈,仿佛是无数受了伤害的婴儿的精灵在发出控诉。”(《蛙》)虽然看不出姑姑有什么宗教信仰,但从莫言这里,却可以明显感觉到佛教思想的显现。灵魂不灭和转世投胎的思想在他的另一部小说《生死疲劳》中则展现为一个不屈灵魂在不断的生死轮回中的“生死疲劳”。莫言当然不一定是真正的佛教徒,他只是借助佛家的轮回观以表达他的人生、历史感悟。这与韩东这部小说中佛教的作用显然不同。在这部小说中,佛教是被作为引渡尘世众生迷途知返的利器。佛教讲求素食、静修、禁欲和灵魂不灭,而这些恰恰都是同果儿的现世人生态度截然相反的,所以秦冬冬总是引来果儿的嘲笑。
就韩东的城市题材小说及其日常生活叙事来看,他是把日常生活的问题放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语境加以表现的。因此这部小说不妨做这样的衍生:果儿所代表的“张牙舞爪”的张扬的生活,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在经历了理想的溃散后的资本主义式的日常生活形态。这是一种没有(全民)宗教所节制、约束下的日常生活,而随着理想溃散,欲望登场,欲望的无节制就以一种本能的形式张扬。这样一种日常生活,就其发生学的意义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一俟挣脱束缚便会极度膨胀而至漫漶,这时其负面的意义就会显示出来。因此,问题也转化成这样一种追问方式:如此张扬的日常生活,是否值得提倡?如果不值得提倡,又该如何引导到一个正常合理的轨道上来呢?就韩东的此前的小说创作及其近作《欢乐而隐秘》来看,他显然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这部小说中,他从一以贯之的欲望的角度切入,尝试引入佛教之说加以解救,小说因此而具有某种象征色彩,其成败得失也皆源于此。当然,小说不是学术著作,它并不追求知识的完备,它只是代表一种观念、一种思路和一种展望。秦冬冬也并非什么得道高僧,他充其量只是生活在俗世中虔心礼佛的居士。在小说中,他的存在,只是作为林果儿所代表的生活方式的对立面、旁观者乃至批判者的角色。他之所以充当果儿的闺蜜,也只是作为在关键的时刻引渡果儿的角色而显示其存在的功能,这一关键时刻就是果儿的六次或者七次的堕胎。果然,在经历了这次堕胎后,林果儿见到秦冬冬“我”,表现大不相同了:“大概是次数的确太多了,果儿的精气神大不如前,振作起来也不会那么快了。”(《欢乐而隐秘》)她很在意这打掉的胎儿是否有生命,佛家讲究参悟和点化,“我”也乘机因势利导:
“胎儿也是有灵魂的。”我说:“不仅妈妈肚子里的胎儿有灵魂,被打掉以后仍然有。没准我们说话的时候就有小婴灵在这个空间里飞呢,只是我们看不见。”
……
以此为契机,我对果儿说起了因果报应,说起了六道轮回和地狱。我甚至把果儿领到供佛前跪拜礼敬了一番,教她诵了一遍《地藏经》。
自此,果儿开始了她的断断续续的禁欲之途,她要为被她杀死的胎儿的“小婴灵”超度以求救赎她所犯下的罪愆。当然,如果小说沿着这一轨道发展,自是波澜不惊,引不起读者多少兴趣。果儿的这一改变只是一初始情境,目的是为了引出另一个主要人物齐林的出场。
于是,小说逐渐演变成常见的三男一女的传统模式。三男一女或三女一男的模式,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小说创作中比较常见,《红楼梦》最是经典,贾宝玉同薛宝钗、林黛玉和袭人三个女性之间的关系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的人生选择的三种方向。建国以来,这一典型代表是杨沫的《青春之歌》。《青春之歌》中,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的出现,都是为了使女主人公林道静顺利走上革命之途,因此,他们的存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阶段性的特征。同样,《欢乐而隐秘》中张军、齐林和秦冬冬的存在也是为了引渡女主人公走向精神上的自我救赎之路。事实上,两部小说也确实具有某种“隐秘”的神秘关联:张军就像余永泽,虽充当了女性主人公人生第一个阶段的启蒙者,但也是最先被否定的对象,他们的被否定,都与第二个主人公的出场有关,是卢嘉川和齐林的存在,使得女主人公终于选择离开他们。但也正如卢嘉川的中途缺席一样,齐林也是作为过场人物出现在果儿的生命中,他们虽然占据了女主人公的心灵的更深层,但也正是因为其重要,他们的死亡似乎就不可避免,因为不如此,小说的女主人公就不能达到精神上的升华——一个走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一个走向佛家式的静修——在这里,主体精神上的升华是必须以“他者”肉体上的毁灭作为前提或代价的。因而两部小说中,江华同秦冬冬一样,都是作为精神人物的形象出现。江华代表的是纯而又纯——出身纯正的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理想追求,秦冬冬则象征了物欲横流时代中无欲的精神上的灯塔和坐标。
虽然说两部小说在三男一女的模式中有其神秘的相似性,但两部小说的叙述却千差万别。《青春之歌》中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时代背景的结合,既令人憧憬也让人信服,《欢乐而隐秘》中的生硬造作、想入非非则让人生疑。在小说中,作者似乎并不想让读者真的相信有齐林这样一个主人公的真实存在。他的神秘且轻而易举的发家,发家后的洁身自好,对员工的体贴关心,以及对待果儿的毫无保留的奉献,简直就是一个完人形象,看不到现实生活的复杂和多面性。因此,在小说中,他作为一个富豪身份的价值,似乎只是为了等待果儿的出现。在这之前,他则保持着单身的状态而且是童男。他单纯,不懂得如何同女人交往、恋爱,只知道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可以说,他的行为,他的发家史,他的纯粹,都已经超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而事实上,韩东向来都不是一个远离日常生活写作的小说家。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我们只能认为这是韩东的臆造,他的存在只是一个符号。在这里,他的真实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存在唤起果儿遥远的记忆和人性中静美的一面,让她幡然悔悟,人生从此升华。或许也正是因为这种自我意淫式的想入非非,小说中才充满了某种神秘主义的氛围。那落在张军车上的须弥山的神秘的七朵樱花和樱花树(与婴灵之婴同音),鬼使神差地把果儿带到了齐林身边,同样也是这樱花,最终又神秘地把齐林从果儿身边带走(车祸身亡)。而且,诡异的是,这一车祸某种程度上恰是14年前那一场未竟的车祸的重演。14年前,同是这棵樱花树,见证了作为一个小姑娘的果儿如何在无意中救了齐林免于一场车祸,因此,这14年后的旧路重回和再一次的车祸就带有宿债偿还和轮回报应的意味。小说自此兜了一大圈,其实只是为了表达佛教式的宿命论、轮回观及其报应说。而这,也似乎是想告诉读者,既然命运不可挣脱或者前生底定,超度和自我救赎就显得尤有必要。
三
韩东在《我和你》的“后记”中曾明白无误地表明,“我一向反对所谓的‘宏大叙事’以及一切以‘大’为目标的文学理想,《我和你》即是一个说明。它以‘小’见长,以‘小’为是……有时候我不禁想,‘小’或细微不仅是小说的必要手段,甚至就是它的本质,否则也不会叫‘小说’而叫‘大说’了”①。诚然,韩东始终是一个以“小叙事”为自己写作目标的作家,他往往拒绝从宏大意义上去描写日常生活,他的日常生活往往只能在远离宏大叙事的层面才能被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小叙事”就是一种日常生活的还原或原生态。就像前面分析所看到的,对韩东而言,他笔下的欲望总是有所指涉,有所针对,可见,欲望并非纯粹的欲望,而毋宁说是一种被重新符码化的欲望。
事实上,欲望并非仅仅小问题,它其实可以从很宏大的层面加以理解。正如“米歇尔·福柯在他富有影响的三卷本《性经验史》中特别指出:欲望与各种社会的和制度的实践以及话语联系在一起——也就是同法律、性别和性特征,以及医学、神学和经济学等联系在一起。探讨文学文本中的欲望——对欲望的表征——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历史语境的问题”②。换言之,它是人的本能,与人性的善恶关联;它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与人性的深度、厚度及其复杂性之间往往构成某种对应关系。此外,欲望还涉及到道德、伦理和宗教的层面。简言之,欲望不仅仅是欲望本身,它涉及的面、指涉的意义都很广大。但韩东却表现出简化的倾向。他把欲望置于远离宏大叙事的层面加以表现,因而往往归之于小叙事中的一种。他一方面解放了欲望,但又把欲望引导到一个狭窄的表现空间,他竭力从日常生活的层面理解欲望,但又表现出把欲望重新本质化的倾向。这就难免陷入一种自我指涉的游戏或困境当中,进退失据,顾此失彼;同时,也使得他的主人公陷于爱与欲望的悖论中不能自拔(《我和你》),或者隔断同人性的勾连,而在本能的表层游弋(《障碍》)。总而言之,拒绝宏大叙事的结果是,欲望逐渐演变成为一种表演和被展示的对象,其虽有所意指但却既无力度、广度,更无深度可言,这样的欲望叙事,终只能止于自我指涉的层面,很难有大的突破。而事实上,正如拉康所言:“欲望就是要求在掏空自身的空当显现的东西。”③欲望实际上处于一种永远的匮乏和悖论之中,“欲望,虽然严格说来并不存在欲望这种东西,却又总是已经存在于任何决定的剩余之中,在各处流动,充斥于各种生产方式”④,这就形成了欲望叙事的“无法弥合的鸿沟”,欲望及欲望的满足一方面被无限延宕,同时又无所不在,依次循环,没有止境。
这样来看《欢乐而隐秘》就格外意味深长了。韩东也似乎感觉到了欲望的无限繁衍的本质,但他又决绝宏大叙事,对于这样一种矛盾,他的解决之道,只能是纵欲之后的禁欲,及其寄托于宗教(佛教)意义上的精神上的升华。其虚妄自是明显,佛教在古代即不能达到对欲望的升华,对于我们这一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时代,其意义又何在?但韩东通过他的对欲望的叙事,也似乎明白了一点,即所谓的爱与欲望的“匮乏”本质,既然欲望永不能被满足,欲望及其叙事实际上就是一种不断的延宕过程,所以才会有果儿的六次或七次的堕胎,才会有作者韩东对这一空虚或匮乏的试图填补。从这个角度看,《欢乐而隐秘》与韩东此前的小说都不同。他写的是一个欲望的无止境及其自我救赎的象征和寓言。韩东似乎明白了欲望是一种“缺失”,但他却又似乎想填补这“缺失”,这就是他的悖论,也是他的发现。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①韩东《我和你》[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65页。
②[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③④[美]沃尔夫莱《批评文学与文化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6页,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