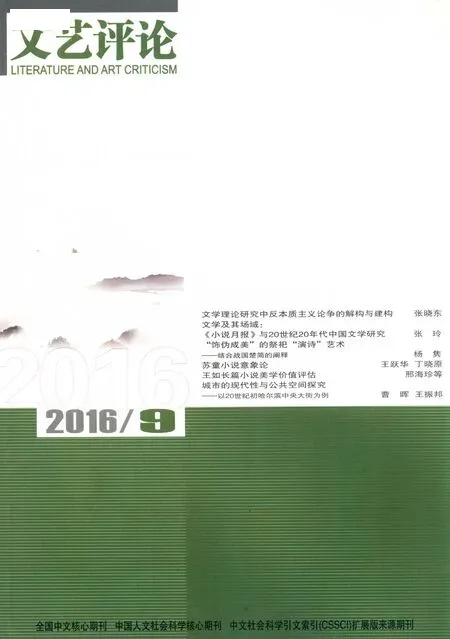魏晋咏物诗人的“通变”观念
2016-09-29钟志强
○钟志强
魏晋咏物诗人的“通变”观念
○钟志强
刘勰《文心雕龙·通变》曰:“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篇末的赞又曰:“变则可久,通则不乏。”对于《文心雕龙》的“通变”,学界普遍认为与“文学的继承与发展”相关。如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就说:“《文心雕龙·通变》篇专论文学的继承与革新问题。”①因为《文心雕龙》全篇涉及总结前世文章创作规律,对作家、作品的观照和论述之中时时贯彻“通变”观念,所以这一观念甚或对周秦汉魏及六朝各期文学思想递延脉络的考察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推论,魏晋咏物诗的创作必会涉及创作主体的“通变”观。钱志熙《性情与通变——唐人诗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即曰:“诗学之根本有两点,一是诗人对诗歌本体的体认与追求,二是诗人对诗歌中通变规律的自觉运用。”②虽然,学界对先唐诗人的通变观有所认识,但对于具体诗类(如咏物诗)的诗人群体在创作中如何继承与追求新变的论述,却尚未及见。
那么,魏晋咏物诗人是继承、批评,还是批判的继承?又是如何在继承基础上创新呢?本文将分别从魏晋诗人所持的通变态度、对“赋、比、兴”观念的继承和创新、诗歌创作的具体表现等方面,考察魏晋咏物诗人的通变观念。
一、魏晋诗人所持的通变态度
魏晋时期,咏物诗的创作虽然并未达到鼎盛,此时的咏物诗也不能代表六朝咏物之作的最高水平,但它却为六朝咏物诗创作的高潮阶段的到来作了铺垫。魏晋咏物诗创作相关环境发生了什么变化呢?有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魏晋的士人已经不再轻信儒经和盲从政教,而是开始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自己的个性与自身喜怒哀乐上了。这种思潮在文学方面的反映,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归结为: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求华美的文学思想。这种非功利、主缘情、重个性的文学思想,必会影响创作主体逐渐以自我为中心,形成以我眼观世界,而以我诗写我心的创作习惯。这种创作习惯与本文所关心的魏晋诗人所持的通变态度关系如何?现我们具体剖析一下,在摆脱政教对思想的束缚后,魏晋诗人对待前人、前人作品与创作经验,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
据笔者对现存文献资料考察,魏晋诗人对前代为数不多的咏物诗,并未留下什么评论。即便如刘邦、刘弗陵等留下的《鸿鹄歌》《黄鹄歌》,汉末蔡邕所作的《咏庭前石榴》,魏晋文人也鲜有评论。或许魏晋诗人评价过却未能依靠那些断简残帛保留下来,抑或是这些诗歌还未引起他们的重视。总之,我们只能另辟蹊径。
笔者罗列了一些魏人对待前人和前代作品的评价,或许可以稍稍弥补一些文献缺失的遗憾:
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
——曹丕《典论·论文》
曹丕《典论·论文》是魏晋时期第一篇文论作品,文章不仅提高了文学的价值,而且还论及了对前代和当世文人的相互关系。“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指出了魏晋文人对周围创作群体的态度是“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在这里“贵远贱近”既可解释为对只闻名声而未曾接触的文人重视而轻视身边的文友,又可解释为轻视同时代的创作群体而尊崇前代文人。那么,在曹丕看来,当世文人总体上所持的是一种这样的态度:自命不凡,对待周围其他文人普遍轻视,至少在自己周围的小圈子里争着“谓己为贤”而对前代文人尚能尊崇。除了曹丕外,我们还可从其弟曹植《与杨德祖书》中找到相似的描述:
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还为狗者也。前为书啁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敢妄叹者,畏后之嗤余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割断。刘季绪才不逮于作者,而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砦五伯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所好尚。兰芷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曹植《与杨德祖书》
从曹植的论述中,我们看到了当世文人对自己的态度是“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也”;对前代文人以为楷模,表面尊崇古人,实则标榜自己“(陈琳)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对待周围文人则要苛刻得多“好诋呵文章,掎摭利病”。当然,为避免纷争,有的魏晋文人也不愿随便评论他人文章: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尝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能过若人,辞不为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
当然,曹植其实并不认可这种态度。他认为文人应该改变这种弊帚自珍、互不交流的状态:
敬礼云:“卿何所疑难乎!文之佳丽,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春秋》,游、夏之徒不能错一字。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曹植《与杨德祖书》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三点:第一,曹魏文人对待前人及其作品还是抱有尊崇的态度,并不因儒学政教的衰退而对前人及其作品进行否定。至少是保持了较为宽容的态度,这与对其当世普遍的诗人间相互轻视之态度形成鲜明对比。第二,曹魏文人并不喜欢评论其他文人和作品,特别不愿意指出别人文章的缺点,但都自视甚高,希望立言于后世;第三,魏人一般态度比较客观,有自己的判断,指出好的作品也存在缺陷。由于曹魏国祚都较短,且西晋本身就是在曹魏的基础上建国,所以西晋和曹魏文士的通变观理应变化不大,本文不再细述。
二、魏晋诗人对“赋、比、兴”的通变观念
本文现以魏晋文人对“赋、比、兴”,特别是比兴观念的继承和新变为例,论证曹魏和西晋咏物诗人的通变观。比兴之名源于《周礼·春官·大师》,其文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后来汉儒《毛诗序》亦言:“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关于“六诗”的本义,因《周礼》并未明确说明,以致后人多有分歧。虽然如此,但周人对“赋比兴”的理解显然与提出“六义说”的汉人是有差别的。应该说,周人所说的“六诗”:“绝非凭空而出,也不源于宗教,而完全是根据上古诗歌实践所作出的一种理论上的概括,具有相当深刻的意义。”③从《诗经》等先秦诗歌的创作实际来看,赋、比、兴作为文学表现手段,已经得到广泛的运用。
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汉儒在继承周人对“赋比兴”认识的基础上,也增添了新的内涵。继承的方面就是,汉人认可赋、比、兴是诗歌的表达方式。东汉郑众就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④新变的方面就是汉人并没有把赋、比、兴单纯视为文学表达的手段,而是着重强调它的政教意义。如提出“六义”的《毛诗序》,其对同为六义之“风、雅、颂”的解释就有浓厚的政教色彩:“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故曰风……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毛诗序》全篇都与政教有关,赋、比、兴作为六义的组成部分,其政教意义是汉儒强调的部分。
那么,对于赋比兴,魏晋时期的文士又是怎么看的呢?曹魏现存文献,并未留下当世文人对赋比兴的看法。仅有与曹操生活年代相近的经师郑玄的《周礼》所做的注。其《周礼·春官·大师》注云:“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之。”上文对赋、比、兴的解释表明,作为经师的郑玄偏重的仍然是赋、比、兴的政教意义,而非赋、比、兴作为诗歌表达方式的一面。此即可证,作为经师的郑玄,在儒家的经学体系对文人思想的控制愈趋衰弱的态势下,仍然尊崇先儒偏重于赋、比、兴政教阐释的观点。郑玄作为建安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学大师,其这番注重“赋比兴”的阐释似并未获得魏晋时期文人群体的认可。如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就专门强调赋比兴的文学性:“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从挚虞的解释看,其已不再强调赋比兴的政教意义,赋、比、兴在他看来应是较为单纯的诗歌的表达方式。因此,魏晋文人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不再是权威大师可以禁锢得住的了。他们更希望能够客观地看待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新见解。六朝后期,文人对于赋比兴的看法逐渐稳定下来,梁文论家刘勰亦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意。”⑤从挚虞和刘勰对“赋、比、兴”的解释来看,整个六朝时期,文人将“赋、比、兴”视为一种铺陈描摹或抒情言志的表现手法。
这个观念是在魏晋文人从经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后,对前人或同时代不同个体思想的通变下,不再强调“赋、比、兴”的政教意义之后,逐渐形成和固定的。
三、通变观念与魏晋咏物诗
在以与诗歌关系密切的“赋比兴”创作观念于魏晋的通变情况为例基础上,本文具体分析魏晋文人的通变观念与咏物诗创作的关系。在诗歌创作上,魏晋文人对《诗经》《楚辞》等前代作品的赋、比、兴的创作手法,持认可并继承的态度。这在现存的魏晋咏物诗上,就得到了很好的印证。只不过《诗经》的绝大部分诗歌的情况是:一句就有一个本体一个喻体,下一句又是另一个本体和喻体。而魏晋咏物诗则是整首诗就只有一个本体—全诗的中心意象。这些魏晋比兴体诗歌中的大部分,我们称其为比体咏物诗。比体咏物诗是魏晋咏物诗最主要的类型。如建安时期,除了几首同题的《斗鸡诗》、繁钦的《槐树诗》,都是比体咏物诗。晋代纯粹的赋体咏物诗也寥寥无几,这些上文已述及。
徐盛《魏晋至盛唐咏物诗研究》就说:“建安以来比体咏物诗创作的构思沿袭着前人的比兴观念,与比兴手法紧紧结合在一起,从整体上看咏物意识是在比兴创作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⑥本文认为,虽然魏晋诗人对赋比兴作为创作手法采取继承态度,但在魏晋咏物诗人的观念中,他们对“赋、比、兴”有着自己新的认识,就是他们解释“赋、比、兴”不像汉人那样偏重于它们的政教意义,这就是魏晋文人对前人“赋、比、兴”观念的继承和新变。其客观上也为“赋、比、兴”作为诗歌表达方式广泛运用于六朝咏物诗创作扫清了障碍。魏晋咏物诗,尤其是西晋咏物诗,就出现了许多使用“比兴”寄托与政教无关,而与个人喜怒哀乐情怀相关的例子。如王粲《诗》(鸷鸟化为鸠)、曹丕《杂诗》其二(西北有浮云)、曹植《吁嗟篇》、张华《荷诗》《诗》(橘生湘水侧)、陆机《园葵二首》、郑丰《鸳鸯六章》、司马彪《诗》(百草应节生)等。
总的说来,比起六朝后期的咏物诗人,魏晋人对待前人及其作品尚持较为宽容和推崇的态度。但他们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通变观,对一些不符合文学潮流的前人思想,如政教与文学的不分,魏晋诗人也是不会继承的。这点从他们对咏物诗创作理念和作品来看,就可以知晓。
(作者单位:南昌师范学院中文系)
①袁行霈、孟二冬、丁放《中国诗学通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②钱志熙《性情与通变——唐人诗学的基本思想与方法》[J],《长江学术》,2006年第45期。
③黄霖《赋比兴论》[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6期,第76页。
④[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毛诗正义》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70-271页。
⑤[梁]刘勰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01页。
⑥徐盛《魏晋至盛唐咏物诗研究》[D],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第17页。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编号:15WX21);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ZGW1518);南昌师范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编号:NSBSJJ2014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