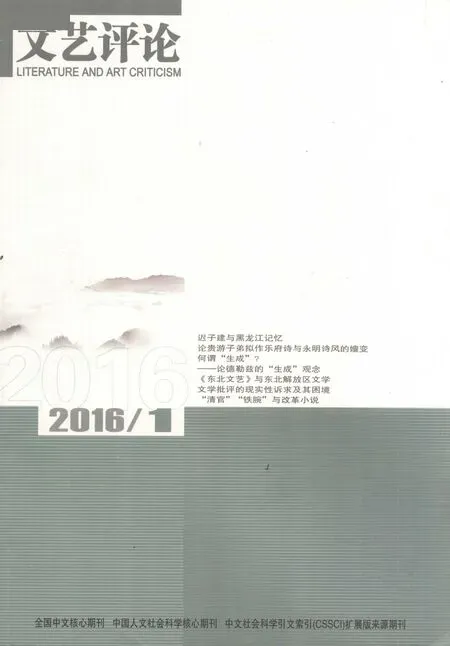何谓“生成”?
——论德勒兹的“生成”观念
2016-09-29张中
○张中
何谓“生成”?
——论德勒兹的“生成”观念
○张中
一、混沌
在一定程度上,我们说德勒兹制造出了一个含混不透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差异是主导,生命之流任意游走,而新的事物和思想不断生成。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在这里被解除,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虚假也在这里无处藏身。如此一来,叔本华所谓的“摩耶之幕”将不再存在,剩下的都是充满力量和差异的生命流动。作为一个激进的批判主义者,德勒兹甚至认为不存在生物界,也不存在人类思想界,普遍存在的只有同一个机器界。那么,难道这不是一个混沌的一元性的多元世界吗?从尼采那里,德勒兹发现世界是由无数生命的自我运动构成的,生命的力量和强度不为外界所改变,它以无限的差异化运作展开自己的生成。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他者?这是德勒兹给我们留下最难解的谜语,但也是他对主体进行解构,以及对生命力量加以强化的最激进表现方式之一。问题是,什么是德勒兹意义上的“生成”?它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①有研究者认为,与巴迪欧的分析迥异,德勒兹全部写作都是在强调“生成”而非“存在”。确实,存在的根深蒂固导致了“生成”的不可能,而柏拉图对实在和模仿的区分也限制了生成的力度和强度。也正是因为这样,在《意义的逻辑》一书中,德勒兹将自己的哲学描述为对柏拉图主义的根本性清除。在颠倒了柏拉图主义之后,德勒兹强调生成的内在性,亦即生成的无根基性和无基础性。事实上,虽然德勒兹并未将生成置于存在之上,但他却至少消除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德勒兹认为,那种预设的、位于生成之流背后的真实世界并非存在的稳定世界。在生成之流外无物“存在”,所有的“存在者”都只是“生命—生成”之流中相对稳定的时刻而已。②生成本质上是创造,亦即制造差异,制造新事物。所谓“创造”,它是一种除了致动因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原因的活动。按照斯宾诺莎的看法,被创造的事物是这样一种事物——它的存在除了神之外,不以任何东西为前提。那么似乎“生成”乃是凭空而来的创造——这样看当然不对——但“生成”确实又是对模仿、再现和重复的拒绝和否定。
如巴门尼德所言,“有”和“无”都是一种“存在”。那么对生成来说,有和无、有限和无限、实在和潜在共同构成了差异化运动,而它们乃是“生成”的前提。尼采认为,“对于生成来说,存在者和不存在者都是必不可少的。当它们共同起作用时,就有了生成”③。由此可见,生成乃是生命在力量作用下所进行的综合运动,它会协调一切(甚至是相对的)力量进行创造。此外对尼采来说,生成决不是道德现象,而仅仅是一种艺术现象。其实对德勒兹(和加塔利)而言,生成是一个动词,它具有其自身的容贯性。这就意味着,“生成”必然抛弃一切“成见”,它以当下的现实和生命意志为其本源进行自由创造。在这一情状之下,生成必然也抛弃人道主义,抛弃道德伦理,甚至放弃主体。最终,生成之流所造成的世界就是一个“混沌”的世界。它是一个无主体、无他者的世界,也是一个纯粹内在性的世界。根据德勒兹,尼采是第一个以“前个人的特异性”来构想世界的思想家。他不是以语言所能够组织的普遍性形式,而是以混沌的和自由漫游的流动性来构想世界。④是的,差异和流动性是生成特征,也是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难道这样的“生成”不会造成混乱吗?难道它不会反过来危及生命吗?按照尼采和德勒兹,这自然不是问题,因而无需顾虑。对他们来说,生命开端于纯粹的差异、生成和差异化倾向,它本身就应该是模棱两可的。甚而至于,在生命的起源处,一切都是混乱无序的。在此,我们有理由发问:是谁给我们以确信,让我们认为事物应该是明晰和秩序化的?又是谁让世界从混沌变得如此清晰的?事实上,哲学家的所作所为不仅没有让世界变得如其所是,反而让它脱离了原先的一元浑整之状态。尼采制造“混乱”,强调欲望、权力和差异,他在事实上将世界和生命还原到其原有的可能状态之中。也正是因为这样,福柯、德勒兹和德里达等人对尼采爱不释手。
在尼采之前,莱布尼茨曾经吁请所谓“和谐”的光临,但这一“和谐”并非是要整饬和废弃那非确定性和偶然的事物。毋宁说,莱布尼茨的要求是让事物的正反两面都具有意义。按萨特的说法,存在的就是合理的;那么,万物为我们展现的都应是其本然(状态)。比如,你能说三叶虫很可笑吗?你能说仙人掌毫无“用处”吗?你能说康德只剩下了个骨架吗?我们目前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应该就是综合一切无序和混乱,综合无限与有限,按照生命内在力量的指引创造新的生成,而非否定那些所谓“非我”之物。否则,我们将重新走进柏拉图精心设计的思维陷阱。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发现其实古希腊和前苏格拉底时期的世界正是这样的世界,因而尼采也就不遗余力地试图重返希腊。我们知道,米歇尔·塞尔十分赞赏莱布尼茨,这是因为后者从不否定混乱无序、喧嚣与躁动、噪声和狂怒。甚而至于,塞尔宣布要将“混乱”引入哲学;而且他认为,这一概念时至今日依然受到理性(主义)的蔑视。对这位思想家来说,“混乱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系统,它半开着。为了编码,必须闭合起来;为了分类,必须加以确定,或者划定界限。混乱是不容置疑的,它不是一种系统,而是繁多性……”更为关键的是,混乱是流动的,它是一种无定向、无规律的流动。但正因如此,塞尔认为混乱乃是肯定的,亦即纯粹的可能性。⑤事实上福柯对那些非理性、混乱无序和非正常之事物也充满敬意,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疯癫、精神错乱和不正常的人更是其礼赞的对象。虽然福柯的关注点可能并不在于上述事物本身,但他的精准分析却在一定程度上解开了一个隐藏已久的秘密——真理是被制造出来的,而人也是被建构起来的,因而需要恢复事物本来的面貌。如海登·怀特所言,本质上福柯赞美的是那种创造性的乱序(disordering)、解构(destructuration)和非命名(unnaming)精神。重要的是,福柯在客观上回应了德勒兹的“生成”主题。我们知道,与赫拉克利特一样,尼采的终极词是“生成”,亦即生成着的生命或干脆说生命。⑥这一“生命”在尼采看来是不可替代的,它是一切生成之流的本源,也是生成的归宿地。德勒兹指出,重要的事情是理解生命:每一个生命之个体性不是一个形式或形式之发展,而是在不同的速度之间,在微粒子之减缓与加速之间的一种复杂的关系,在内在性之层面上快与慢之组合。举例来说,音乐的形式就依存于声音微粒子的快慢之间的一种复杂关系。而这不仅是音乐之事,也是生活方式之事:人们正是通过快与慢而溜入诸事物之间,与别的东西相结合。⑦按此逻辑,音乐欣赏、绘画创作等都体现了一种速度或节奏,一种“在……中”之生成,以及一种自我释放的自由生命。
尼采曾说,一切生成均产生于对立面的斗争。按此逻辑,生成就是排斥同一,制造差异。此外按福柯的理解,生成和差异一样,是接受分歧的思想,是有关杂多的思想。当然,它更是一种游牧的、散布的杂多,它不受相似物的束缚的限制或局限。其实,无论是尼采还是海德格尔,他们都在强调生命/存在的一种差异化的紧张运动。不过对德勒兹而言,这一差异十分明显,以至于他要突出一种流动性的“生成”。以文学为例,文学既是一种无限的“生成”,也是一种源自于生命内在的生成。在《文学与生命》一文中,德勒兹认为写作是一个“生成(性)”事件。它永远没有结束,永远都“正在进行”中,并且它超越任何可能经历或已经经历的内容。因之,一个作家在其创作时必然将其生命内化于整个写作过程之中,它将使生成不断涌现和非形式化,同时作家自身的生命也会由生成而流转或变易。比如,为什么福楼拜会为包法利夫人之死而哭泣?为什么阿尔托要将生活变成舞台,同时也将舞台变成生活?其真实原因可能就在这里。准确地说,(在)写作中,人(作家)生成女人,生成动物或植物,生成分子,直至生成不可感知之物。由此来看,卡夫卡难道不是个经典范例吗?文学是生成,它事关创造和自由。如德勒兹所言,“文学是一种生成问题;与其说它是一种模糊场域的发生,不如说是创造认同、模仿;文学同时是实施实践原则的能力”⑧。在“生成”之中,文学形成无限的自由;经由持续不断的拓展性“生成”,文学最终生成愈加广阔的自由空间。除此之外,文学的本质之一还在于不断地制造“差异”,虽然也许这是一种“重复的差异”。不过重要的是,这一“差异”既是文学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文学自身皱褶和回返的模式之一。
按德勒兹的说法,“差异”既无时间性也无规则性,它处于两种个体化的模式和两种时间性的模式之间。如此说来,“生成”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它在有限和无限之间穿梭,它是未定性和可能性的含混综合。关键还在于,文学生成始终是“现在时刻”的行为,而它却又吊诡地形成绵延性。也许我们无法真正体验这一惊心动魄的时刻,但只要你进入写作之中,一切就将条分缕析并使我们信之确然。德勒兹指出,“生成总是在‘之间’或‘之中’:女人之间的一个女人,或者其他动物之中的一只动物。但是只有当生成中的名词没有了让它表示那个(‘你面前的那只动物……’)的形式特征之时,不定冠词才产生真正效力”⑨。这就意味着,生成就是时刻的运动和变易,就是生命力量的现实运转与流动。这种在“之间”或“之中”的“生成”其实既是文学的特异性之所在,也是“生成”自身的根本特征。文学生成向我们展示出一个运动的状态,在这里,文学空间所展现的其实就是一种无主体、无规则和非理论化的游牧空间。宕开一笔,这种空间应该就是布朗肖所谓的“文学空间”吧?!按照德勒兹,“生成”不是一种带有既定目标的征程,而它也从不以到达某一目的地为根本目标。毋宁说,“生成”乃是一种不断游走、不断虚拟的“游牧”空间和未定性创造过程。它从事物的裂隙处越出,从词语的破碎处逃逸,从而指向比域外更遥远的域外。文学以其虚拟性展现出纯粹的内在性,从而也实现了其自身和思想的皱褶。如同一把随时随地可以打开与闭合的折扇,文学的生成造就一种自我的“褶皱”,而其体现的不可决定性和未知空间则显示了“生成”迷人的魅力。在德勒兹看来,马拉美、尼采、荷尔德林和萨德都是这种“生成”观念的代表,都是自由精神的持有者;而他们自身(及其写作)也均体现为“褶皱”的化身。对这些人而言,文学就是如同马拉美所昭示的“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之物,它在无限的生成运动中走向对生命的展示和回归。⑩事实上,对德勒兹来说也并不例外。按照德勒兹,“生成既仅仅不是事件的起源,也不是一种中间状态,而是一种极具生产特征的事件”(11)。因而生成意味着“遗忘”,意味着生产和创造。正因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千高原》中反复重申:生成是一种反—记忆;生成是缠卷(involution)性的,而缠卷则是创造性的。
在《意义的逻辑》一书的开篇,德勒兹借用《爱丽丝奇境漫游记》中爱丽丝时而变大时而变小的故事来讨论,并认为这就是一种纯粹的“事件”、纯粹的“生成”。他指出:“在同一时刻,一个人比原来大了,也比将来小。这是生成的同时性,其特点就是逃避当下(在场)”(12)。这就是说,生成牵涉过去与未来,它同时向两个方向运动。在如此情状之下,生成伴随生命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始终生成一个个新的存在。不过德勒兹也指出,生成不是通过“过去”和“未来”这些概念而被思索的。事实上,它在二者之间进行,每次生成都是一个共存的断块。如此说来,生成之物其实并非德勒兹关注的中心,他真正关心的是这一运动本身。然而,这是怎样的运动啊?事实上,德勒兹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内在折返运动,而生成之流所带来的乃是一个混沌元整的世界。它不仅沟通了有限与无限,也通达内在与外在的界限处。事实上,德勒兹精心描绘的是一个出自内在,而又回返内在的纯粹内在性世界。德勒兹认为,内在性世界并非仅存于内部,它是一个从内部出发指向外界的特殊场域。这个场域是内在性的产物,也是纯粹内在性的标志:“内在性的场域不是内在于自我的,但同样也并非来自某个外在的自我或某个非我。毋宁说,它是作为一个绝对的外部,这个外部不承认自我,因为外在和内在都同样归属于那个(它们被融合于其中的)内在性。”(13)故而,德勒兹的“内在性”是源发于内在的生成之流,它是来自域外与域内的一种交织或“互逆性”。当然,生成之“力(量)”在其中是一个根本因素。事实上,德勒兹对人的理念(即作为基础性的存在者)的解构是对更为普遍的“生成”的肯定的一部分:思想是生成。(14)对他来说,思想本身即是生成、创造和自由的显现。或许在德勒兹那里,“‘思想’不是建立在来自内部的必然性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随感’(不得已的、天上掉下来的念头,或所谓‘外部的思想力’)即偶然遇见的因素基础上”(15)。那么这种“外部之力”也必将是“生成之力”。
二、内在性
众所周知,德勒兹在坚决拒斥柏拉图同一性与二元论的同时,也反对超越性,强调内在性。那么,何谓“内在性”?(16)什么又是内在性生成?对德勒兹来说,内在性就是差异化、多样性和肯定性;就是生成之力的表现,亦即生命力量的流转。其实,“生成”也有内与外、积极与消极、肯定与否定、能动与反动之分。比如,植物也拥有一个“生成”过程,但它却是消极的生成。植物对光、热、湿度、授粉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接受,它会在此基础上凝合这些因素从而促使自己生长。需要注意的是,动物虽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生成,但其消极性与植物相比并无根本上的差别。准确地说,这一“生成”过程其实并非主动的生成,而是包含着太多的被动、甚至是反动的因素。我们知道,德勒兹真正热爱的是一种内在性生成,这种“生成”就是一种反中心、多元化和解辖域化的“生产”。它是块茎、皱褶,是机器、游牧民,也是一个无器官身体。德勒兹指出,在斯宾诺莎看来,身体和心灵都不是实体或主体而是样式。如果你将身体和思想界定为一种施加影响和遭受影响的性能,那么许多事物都将发生改变。因此,我们需要将感受之性能放在第一位,从而形成一种生成性和流变的事物。如此说来,德勒兹以一种差异本体论为根基,从而颠倒了柏拉图基要主义,也最终体现出一种多元生成的、关于“力”和“流变”的自由思想。我们说,所有这些既是德勒兹的思想游牧或探险,也是对“自由”的最恰适表达。按照德勒兹,“生成”体现的是一种“分子”模式,它拒绝一切构成和被构成的行为,它最终生成所谓“不可感知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必然陷入虚无主义;毋宁说,它其实改变了我们自由的观念。我们认为,德勒兹的内在性生成带来新的自由思想——它不是那种可以与生命的力量相分离的人类自身的自由,而是通过不再将我们自身视为与生命相分离的视角而获得的自由。进一步来说,通过感知生命的力量和权力,我们与生命一起变易和创造,而这种内在性自由又会反过来强化内在性生命本身。(17)总之,内在性体现的就是生命和自由。
在一次访谈中,德勒兹指出,“去生成从来都不是去模仿,不是去‘做得像’,也不是遵循一种模式——不论它事关正义或真理与否”(18)。再说一次,德勒兹的“生成”是内在性的,不过也是指向外部的。按照德勒兹,“生成”就是不断制造差异,形成循环,永不停歇……因此之故,“生成”必然也就是自由的。“生成”拒绝再现、模仿和重复,也弃绝规则、理论和道德。甚而至于,“真理”在德勒兹这里也是需要被重新检视的。德勒兹曾在《普鲁斯特与符号》一书中说:真理不是被呈现的,而是被泄露的;它不是被传播的,而是被解释的;不是被意欲的,而是无意识的。由此可见,真理乃是生产性的;不过它却是被构造出来的,它只能依赖于生命的内在性生成。正因如此,德勒兹并不重视这种所谓的“真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现实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19)事实上,马克思这里所讲的思维的力量其实与德勒兹对思想的迷恋,以及对内在性生成的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从这一角度来看,德勒兹所谓的“真理”强调的一定是“实践”,以及运动中的“真实”。他不愿停留在意识的空想状态中,他真正渴望的就是内在性的生成,亦即变动不居的“真理”。回到内在性问题,我们发现其实早在柏格森那里德勒兹就找到了知音——他认为“绵延”就是一种“生成”。重要的是,“绵延”恰好体现了“内在性”。从直觉到绵延,柏格森看到的是生命的差异、运动与创造,而德勒兹从中看到的却是“差异”和“生成”。德勒兹认为,“它(绵延)涉及的是一种‘过渡’、一种‘生成’、一种‘变化’,然而却是一种连续的生成,一种实在本身的变化”(20)。由此可见,自由是生成的关键;自由是“生成”的应有之义,因为绵延从根本上说是记忆、意识和自由。如果从这一角度看,我们就会看到德勒兹与胡塞尔和现象学的真正差别其实就在这里。
然而,“生成”首先是对僵化之线的阻断,是对旧事物的拒绝,更是对形而上学的逃离。生成所伴随的是生命的运动,而非一个僵死的世界。在德勒兹看来,生成即创造,但创造不是一个附加在稳定的和惰性的生命之上的变量行为。换言之,并非先有生命,然后才有事件或创造行为。所有的生命本身就是创造,但却是针对它的特定性或“特异性”的倾向的创造。(21)在一定程度上,生成就是逃离,就是那种摆脱生命僵化之线的努力。阿甘本认为,德勒兹赞赏并推崇“逃离”主题。“逃离”的概念并不意味着一个我们可以到达的别处,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逃离——不逃往别处的逃离。不过,重点在于思考一种并不意味着逃避的逃离:在此地的运动,在原有情形中的运动——而这是逃离可以具备政治意义的唯一途径。(22)德勒兹在阐述福柯时对“域外”的倾情书写,以及此前对“逃逸(线)”的仔细描摹,实际上都体现出“逃离”这一内涵。德勒兹认为,在塞尚、克利等画家那里,对现实世界的逃离是真正的主题。他认为,“在所有的艺术中,绘画可能是唯一一种必然地、歇斯底里地将它自身的灾变融入内部的艺术,并因此而成为一种向前逃亡的艺术”(23)。当然,从内部“出逃”意味着对生成的渴求,以及对生命的重新展布。故而,德勒兹的“逃逸线”似乎强调得更多的是“生成”或“自由”,而并非仅仅在于“逃离”。德勒兹在分析菲茨杰拉德小说《崩溃》时认为,主体已然崩溃,欲望将重新分布。那么透过“逃逸线”,我们直接进入到生成—动物之中,进入到生成—分子之中,最终进入到生成—难以知觉之中。事实上,德勒兹认为所有的生成都是分子性的。我们所生成的动物、花或石头是分子的集合体,是个别体,而不是克分子的主体、客体或形式。那么这种生成显然是一种自由的生成,不过德勒兹认为它应是一种“临界自由”。它发生在新旧主体交替的时刻,处于突破旧主体向着新主体逃亡的征途上;并且,“这是一种生成过程中的自由,一种与传统自由极不相同的无与伦比的自由”(24)。如前所述,这是一种事关生命的自由。
德勒兹说:“所有的生成都开始于并经历了生成—女人,它就是所有其他生成的关键。”(25)事实上,这是德勒兹(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句子。它既是德勒兹“生成”思想的主线,也是从《卡夫卡》到《千高原》的真正主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知道,生成—女人意味着成为“少数”,成为“他者”,成为“不可感知者”。它是“生成”过程中必然经历的阶段,也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按照德勒兹,生成—女人是对欲望的开启,它是前个人的、反俄狄浦斯的和直接就是革命性的事情。(26)在一个生成运动中,凭借对生命力量和强度的内在性体认,主体越出自身成为一个“逃离者”、“反对者”和“少数派”。在这之后,主体已经不再是原先的那个传统僵化的主体了,他会不断改变自身,形成自我的主体化风格。关键在于,成为“生成—女人”意味着首先要努力将自己变成为“少数”,变成为自己生命的自我评判者。如上一节所述,德勒兹曾经在谈论卡夫卡时提出“少数(的)”概念,这一概念指的是“个别的事件而不是个体本质,通过‘亲在’而不是通过实在性的个体化”。它与以“成为”和“强度”为逻辑的“分子(的)”概念比较接近,它是无序的、片断的。关键还在于,“少数”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种生成,或一个进程。“生成”就是要成为“少数”,而任何人都会卷入在这种生成“少数”之中。(27)唯有如此,生成才能成为“生成—女人”,也才能真正体现在生命的每一个环节之中。当然,内在性生成首先强调的是差异、运动和变易。也正是因为这样,生成自身也就变成了一个难以把握的东西。那么,是什么攫住了我们的思想?又是什么让我们畏葸不前?按照德勒兹,破除克分子之线,驱逐逻辑和理性,赶走一切僵死之物,然后你将会走上“生成”之路;而你也会在生成之流中体验生命分分秒秒的震颤、感动、狂喜和哀伤。这就是“生成”的风格化,亦即生命风格化的必由之路。德勒兹说,“生成,它们是最难以感知的事情,它们是仅能在生命中被容纳和风格中被表现的行动”(28)。如此说来,所谓“内在性生成”即生命的自我塑造,亦即生命之力的自我涌现。
虽然德勒兹赞赏思想和生命运动,但他更愿意将其看作是一种实践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德勒兹从斯宾诺莎那里学到的就是一种“实践哲学”。当然这一哲学方法并非像马克思那样强调一种外在的实践活动;毋宁说,德勒兹看重的是思想本身的内在性实践运作。故而按照德勒兹,生成是作为实践的内在性的实现。同时,一个生成产生于许多“层”相互作用的地方。(29)有鉴于此,德勒兹的生成思想往往被理解为一种实践美学。相对于古希腊思想传统,德勒兹的生成论美学的要义在于对柏拉图主义及摹仿论传统的颠覆,即认为不再有某种源头或存在作为生成的基点。德勒兹倡导内在性的生成,以无根基的类像否定柏拉图所预设的基要主义,对其原本/摹本、真实/虚假的二元摹仿论加以解辖域化。(30)不惟如此,作为一位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与福柯、巴塔耶一样关注那本真性生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德勒兹的哲学又可以被称为一种生命(主义)哲学。这种生命哲学关注的重点是思想与生命、创造和自由,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如同尼采和福柯般的审美主义(或生存美学)。其实也正因如此,德勒兹才说思想从来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按他的理解,哲学正是创造生命的普遍性概念的力量,以及赋予生命的混沌以形式的力量。柏格森认为,哲学就是一种思想的运动,亦即不间断的生命创造。那么,“思想所特有的所有行动的运动带领着这个思想,通过它本身的一个不断发展的细分,渐渐地展开在精神的连续层面上,直到思想可以触及语言的层面”(31)。如此一来,思想本身即是运动的生命之征象,那么哲学也因而有权来理解那潜在的世界。当然,这一潜在世界不是指如其所是的世界,而是指那个超越任何特定观察和经验的世界:即,生命的可能性。(32)如所周知,德勒兹从尼采那里汲取“力(量)”,并将其演化为“生成”,演化为尼采式的“永恒轮回”(33)。在他眼中,所谓“生成”乃是一种自由与差异的“生成”,一种既无起点、也无终点的内在性“生成”。关键在于,通过再现生成,永恒回归必然会使生成趋向能动。因此之故,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中指出,永恒回归意味着存在就是选择。只有那些肯定着或被肯定的事物才能进入回归,而否定的回归是不存在的。此外,永恒回归是生成的复制,但生成的复制也是能动的生成过程的产品。换言之,既然生命绵长久远,那“生成”又怎么会短暂易逝呢?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①根据德勒兹,有研究者将其“生成”观念概括为如下几个特点:生成本质上是强度性的;生成不是模仿也非认同,更非类比或相似;生成即感受(关涉力与身体);生成意味着崭新的个体性;生成即运动;生成具有多样性和居间性(在……之中)。参见胡新宇《德勒兹差异哲学与美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86—97页。
②④(14)(17)(21)(26)(32)[英]克莱尔·科勒布鲁克《导读德勒兹》[M],廖鸿飞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51—152页,第22页,第152页,第156页,第32页,第175页,第16页。
③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M],李超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8页。
⑤[法]米歇尔·塞尔《万物本原》[M],蔡鸿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4—144页。
⑥马克思·舍勒《哲学人类学》[M],魏育青,罗悌伦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2014年版第6期。
⑦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M],冯炳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49。
⑧John Marks,Gilles Deleuze: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London:Pluto Press,1998,pp.12—125.
⑨Gilles Deleuze. Essays Critical and Clinical .Trans. Daniel W. Smith & Michael A. Greco,London & New York:Verso,1998,p.2.
⑩作为马拉美名诗之一,《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显示了马拉美所谓“纯诗”实践的路径。他从绘画中汲取灵感,将书页“空白”与诗本身看作一体(“纸页参与了诗”);而且他认为诗歌意象的关键是
“思想在棱面镜中的反射”。参见《马拉美全集》,葛雷、梁栋译,浙江文艺出版社,第115页及以下。经此路径,诗歌于是变得恍惚迷离、意义繁复多变、溢于言表——而这也是作为象征主义的马拉美诗歌绝妙之处。那么,这种诗歌(或文学),显然也就是德勒兹所谓的“皱褶”(或“褶子”)。
(11)The Deleuze Dictionary,Ed. Adrian Parr,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22.
(12)Deleuze,The Logic of Sense,Trans. Mark Lester,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0,p.1.
(13)(25)德勒兹,加塔利《千高原》[M],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217页,第392-393页。
(15)尚杰《“外部的思想”与“横向的逻辑”》[J],世界哲学,2009年版,第3期。
(16)从流溢因与内在因的异同谈起,德勒兹认为内在因指涉一种纯粹的本体论,即存有的理论。纯粹的内在性要求存有的平等性,也要求一单义的存有。内在性就是多样性和肯定性,它“反对原因的所有超越性、所有否定神学、所有类比方法以及层级次序的世界概念”。德勒兹认为,斯宾诺莎哲学的重点就在于——他将内在性视为基本原则,并使表现从流溢说或范型说的因果性中解放出来。那么,新的内在性原则就是“表现”观念:内在性相应于包含和展开、固有性和暗含的统一性;内在性具有表现性,表现性就是内在性;表现既表现为多的统一,也表现为包含的多,以及一的展开。当然,表现具有双重内在性:一是表现自身的东西中的内在性,二是表现中被表现的东西的内在性(参见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中译本,第166—184页)。德勒兹还认为,一切形(身)体、心灵,以及一切个体都建立在内在性之上。这个内在性或一致性层面不是内心的念头、打算、规划之意义上的方案,而是几何学意义上的方案:截面、交集、图解(参见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中译本,第148页)。阿甘本认为,德勒兹把“内在性”的起源从“留存”转换为“流出”,从而将流动性和生命归还给内在性。不过,内在性的这个向前涌动,与离开自身相反,无休止地、令人晕眩地留在其自身之内(参见阿甘本《潜能》中译本,第414—415页)。也正是因为这样,德勒兹认为“内在性是哲学的晕眩”,它与表现概念密不可分(参见德勒兹《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中译本,第178页)。
(18)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Dialogues,Trans. Hugh Tomlinson & Barbara Habberj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2.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20)德勒兹《康德与柏格森解读》[M],张宇凌,关群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4页。
(22)汪民安,郭晓彦《生产》(第7期)[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页。
(23)德勒兹《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M],董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页。
(24)程党根《游牧思想与游牧政治实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5页。
(27)Deleuze,Negotiations(1972—1990),Trans. Martin Joughi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173.
(28)Gilles Deleuze & Claire Parnet,Dialogues,Trans. Hugh Tomlinson & Barbara Habberja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3.
(29)Reidar Due,Deleuz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7,p. 142.
(30)麦永雄《德勒兹:生成论的魅力》[J],文艺研究,2004年版,第3期。
(31)柏格森《思想和运动》[M],杨文敏译,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页。
(33)尼采将永恒轮回看成至上的思想,或无上的情感,最高的情感。科罗索夫斯基认为尼采在这里强调的是欲望和必然性,它涉及巅峰情绪——灵魂的高度基质——亦即,强度的一种波动(参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四辑):新尼采主义》第8页)。与之相似,德勒兹将尼采的“永恒轮回”解读为一种绝对差异的思想,一种无限生成的思想(参见德勒兹《尼采与哲学》中译本,第68页及以下)。此外德勒兹还认为,尼采的永恒轮回也是一种内在性的过程,它将差异性与同一性连接在一起。甚至,在永恒回归中差异性回归改变了同一性(Adrian Parr. The Deleuze Dictionary,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Ltd.,2005,p.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