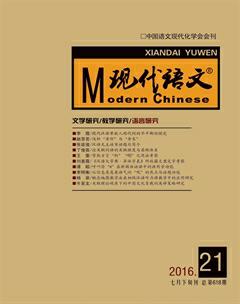论司马相如抒情赋中的私人情感
2016-09-29○吴娱
○吴 娱
论司马相如抒情赋中的私人情感
○吴 娱
摘 要:司马相如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他的《子虚赋》《上林賦》标志着汉大赋发展到鼎盛阶段,所以前人对司马相如赋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天子游猎赋上。本文关注的主要是除《子虚》《上林》之外的司马相如的抒情赋作,分析其讽谏之外的私人情感。
关键词:司马相如 抒情赋 失意文人 私人情感
西汉时期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天下稍安,物阜民丰。到了武帝时期达到鼎盛。汉赋作为汉朝最具代表性的文体,以其错综古今、包罗万象的特点反映了大一统王朝的强盛。武帝时期的汉赋大家司马相如无疑是生在黄金时代的命运宠儿。司马相如是西汉有名的辞赋大家,他奠定了汉赋天子游猎的主要内容以及劝百讽一的主要形式,在整个汉赋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于司马相如,历来关注的重点都是他铺张扬厉的天子游猎赋,比如《上林赋》《子虚赋》,后来的辞赋家如扬雄,模仿的也主要是司马相如这类润色鸿业的鸿篇巨制,这是由他文学侍从的身份所决定的。侯柯芳先生在《司马相如其人其文》一文中指出“润色鸿业,歌功颂德,劝百讽一,虚构夸饰以谀帝,堆砌藻饰以逞才,皆文学侍从之行也。” 但是司马相如的赋作并不是只有天子游猎的大赋一种文风,他也并不是只有文学侍从一种身份和心态,正如侯柯芳先生所说,司马相如的著作“亦可分为帮闲驰辞、写实抒情、论证如理者三类”。并且在现存的司马相如赋作中,抒情赋占有较大的比例。《汉志》记载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但现在仅存《子虚》《上林》《哀秦二世》《大人》《长门》《美人》六赋。其余的只有《魏都赋》张载注引《梨赋》一句,《北堂书钞》引《鱼葅赋》有题无文,剩下的二十一赋无从考证。在这现存的六篇赋文中有四篇都是抒情赋。前人大都认为《长门赋》《美人赋》《哀二世赋》和《大人赋》均有讽刺意味,主文而谲谏。孰不知者几篇赋文在讽谏之外也有个体内心情感的表达,赋家之心包括宇宙,但也是在特定的主体心境下形成的。盛世之下的司马相如所有的未必仅是润色鸿业之心。所以,本文关注的主要是盛世中的辞赋大家司马相如在气势浩荡的天子游猎赋之外所作的抒情赋到底抒发了何种情感。
我们所看到的司马相如形象都是生活在《子虚赋》《上林赋》那种民丰物阜、国力强盛的盛世中的得意文臣,但是,司马相如的仕途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就为他写就抒情赋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感情基础。
关于司马相如的抒情赋在讽谏之外到底抒发了什么情感,这就要联系他一生的仕途经历。首先,从宏观的角度看,汉代赋家的地位也许并没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那么高,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春风得意。《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记载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被汉武帝征召,但据万光治在《汉赋通论》中考证,汉代并没有明确的以赋取士的制度,除了考课经术和举荐入仕外,汉人还以身份或财产作为选士的标准。景帝后二年五月颁布《重廉士诏》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不必众。有市籍不得宦,无赀又不得官,无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 司马相如在景帝时也是“以赀为郎”的,可见其家小有资产,并非以辞赋作为进身之阶。其次,从司马相如自身的经历来看,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司马相如以赀为郎,在孝景帝身边做自己并不喜欢的武骑常侍,由于景帝不好辞赋,遂客游梁王。后因《子虚赋》被武帝征召为郎,其间是有过一段春风得意的日子,后又因人言相如出使时受金而失官。相如晚年为孝文园令,久居茂陵,不得重用,可谓郁郁不得志。所以纵观其一生,司马相如并不是一直仕途顺利的。由于汉代集权社会对知识分子规范严格,也因为汉代《诗》的经学化,所以汉代抒情文学并不发达。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删诗,就提出了诗歌兴观群怨的教化和美刺作用,就是强调诗歌在抒情之外还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功能。到了汉代,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上也实现了大一统,至此确立了儒术的官学地位。汉儒解诗,就出现了经学化和教条化的趋势,具体表现在把孔子提出的诗歌教化功能作为排斥诗歌本身的抒情功能和片面强调诗歌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的依据。对于诗的曲解附会,是汉儒过分迷信文学对政治的干预功能而导致的,同时也导致了汉代诗歌创作的萎靡。锺嵘《诗品序》称:“自王、扬、枚、马之徒,词赋竞爽,而吟咏靡闻。”也就是说时人也意识到了汉代诗歌创作萧条的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汉代文人对儒家经典迷信的同时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所以就忽略了文学本身的抒情作用,从而贬低了诗这一抒情文学体裁。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提到:“古之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五言者,‘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之属是也,于俳优倡乐多用之。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属是也,乐府亦用之。七言者,‘交交黄鸟止于桑’属是也,于俳偕倡乐多用之。”四言以外的诗都是乐府倡乐所用,注重政治教化的汉儒自然不屑一顾,他们热衷的是做诗颂美统治者的功德。可见这正是王朝统一和思想专制给文学带来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司马相如抒情赋作较少见,以至于大家普遍看到的是其讽谏意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和众多受规范和重压的知识分子一样的司马相如内心没有丝毫的失意、苦闷和愤怒。只是因为汉代文学的特殊情况,诗赋都往歌颂方向发展,往往主体情感就淹没在其中了。但即便如此,司马相如还是委婉地抒发自己或无奈或抑郁的情感。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到“汉武帝时文人,赋莫如司马相如,文莫如司马迁,而一则寂寥,一则被刑。盖汉武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盖以维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然相如亦作短赋,则繁丽之辞较少,如《哀二世赋》《长门赋》。”可见,司马相如这种繁丽之辞较少的短赋才更体现他的真性情,是摆脱了文学侍从身份以及润色鸿业任务之外内心私人情感的直接表达。所以研究这些抒情赋有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司马相如其人其文。
《美人赋》本事见于《西京杂记》:“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可见此文的写作目的是自刺,劝诫自己切勿沉迷美色,同时也是以赋明志,提醒自己时刻“心正于怀”。此赋是传统的赋作形式,用对话的方法结构全篇,只是与《上林赋》《子虚赋》相比更短小而已,但其内容和语言并不逊色。《美人赋》所描写的际遇和感情,与长卿文君情事有关,所以司马相如的赋不仅是赋才,更是赋心。所谓赋心,不仅是写亲身经历之事,更是抒发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明朝王世贞提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长门》一章,几于并美。”《长门赋》首见于萧统的《文选》一书,关于此篇赋文的作者问题一直有较大的争论,主要是因为《文选》中收录的序言与史实不符。本文根据其文辞风格的特点,偏向于认为序言为他人所作,正文仍是司马相如所作。关于此文真正的写作目的,笔者认为并不是所谓的“千金买赋”,而是为了抒发自己仕途失意的苦闷心情。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因《子虚赋》而被征召,约在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陈皇后在元光五年被废,即公元前130年,所以《长门赋》的写作年份应该在公元前130年之后。《史记》中提到司马相如在作《难蜀父老》“其后,人有上书言相如使时受金,失官。居岁余,复招为郎。”《难蜀父老》开头即云“汉兴七十有八载”,不难推出此文的写作时间为元光六年,即公元前129年。由此可以推出,公元前129年,司马相如有过一段失官落拓的生活。前人多认为《长门赋》是司马相如作于任孝文园令时,但据《史记》记载,司马相如是在写过《谏猎疏》和《哀二世赋》之后才由郎迁至孝文园令的,所以中间肯定隔着一段时间,前人认为因为孝文园距离长门宫较近,所以引起司马相如的感慨。而本文则认为,《长门赋》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公元前129年,即因人上书言其受金而免官期间。因为此间司马相如由天子近臣突然成为庶人,心中一定积郁太多不平之气,加之一年前陈皇后被废,退居长门宫,时间相去不远,使相如有契机借此事抒发自己心中的苦闷之情。借思妇之口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这一文学传统可以追溯到屈原,屈原的《离骚》就已经为后世文人创造了香草美人的象征性文学形象,以骚体赋为代表的文学体裁正是屈原及楚辞对汉代文学影响的结果。同时,《长门赋》也正是利用骚体赋这一哀感凄恻的文体来抒发感情的。历来文人认为《长门赋》哀怨悲凉,为千古闺思之祖。历来闺怨之辞向来是文人借以抒发自己不平之情的。《长门赋》缘情发义,托物兴词,所谓缘情发义,托物兴词,发的就是失官不平之情,兴的就是无奈悱恻之词。
关于《哀二世赋》的写作背景,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的记载来看,“上善之。还,过宜春宫,相如奏赋以哀二世行失也”。宜春者,本是秦离宫,阎乐杀胡亥之地。所以司马相如随武帝过此地,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才写下了这篇赋文。此篇赋文讽谏意味较强,但其怀古叹今情绪也为浓烈,笔者以为与长卿年岁逾长有关。前文提到《难蜀父老》的写作时间在公元前129年,岁余,相如复召为郎,在写了《谏猎疏》之后才写了《哀二世赋》,所以《哀二世赋》的写作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28年以后。此时的司马相如已过知天命之年,距离去世也不到十年的时间了,加之其一直有消渴疾,身体状况不佳,仕途不顺,见到前朝遗迹,在讽谏之余难免会有古今之感。所谓“精魍魉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哀哉!”也是对人生短暂、世事易变的感叹。
《大人赋》是司马相如由郎迁至孝文园令后写就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相如拜为孝文园令。天子既美《子虚》之事,相如见上好仟道,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尝为《大人赋》,未就,请具而奏之。’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仟意也,乃遂就《大人赋》。”前人对于此赋的理解,多是主文谲谏,讽刺武帝沉溺于求仙之事。但笔者认为,此文在讽谏之外也有相如抒发自己宦海沉浮、烈士暮年的慨叹。司马相如一生多为天子近臣,居任郎官时间较长。郎,为天子侍从之臣,备顾问,可作为天子私人代表出使四方。郎之品秩,从比三百石到比六百石不等,中郎将为郎官群体的中层管理者,比二千石,他们与天子十分接近,地位显要(《汉书•百官公卿表》)司马相如由郎为中郎将,复为郎,最后迁为孝文园令。按《后汉书•百官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虽为东汉制度,其地位与执掌应与西汉差别不大。孝文园令品秩略高于郎,但其主要任务却是“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与郎官清要之职比较起来,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也就是明升暗降。司马相如本人“未尝肯与公卿国家之事,常称疾闲居,不慕官爵”,但并不说明他没有政治理想。武帝朝关于封禅制度的讨论极为激烈,但互相抵牾,久议而难决,“司马相如病死,有遗书(指《封禅文》),颂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表明他时刻在思考封禅等国家大的礼制的建设。“公卿国家之事”是琐碎的公务,这是司马相如不愿意做的。实际上,司马相如希望能够参与国家要事的讨论,为上建言献策。孝文园令是司马相如生前最后的官职,后因病免,久居茂陵。《大人赋》的写作时间正是他迁至孝文园令时,且年事已高,难免会感慨人生短暂,壮心不已。“矐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事不足以喜。”“乘虚无而上假兮,超无有而独存。”这些都是长卿在《大人赋》中抒发的内心情感,仕途失意,有志不获骋,让他不禁发出即使如此能活万世也不足喜的感叹。
以上所叙四篇赋文大体按照写作时间先后排列,此四文均在《子虚》《上林》之后。本文认为,造成此四篇赋文与天子游猎赋之流光溢彩风格相去较远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因为司马相如年岁逾大,所历仕途亦有浮沉坎坷,所以难免呈现出一副迥于天子游猎赋中意气风发与铺张扬厉的低沉哀伤与幽怨悱恻。以上四篇赋文中最能体现盛世盛名之下长卿的苍白与无奈的,当数《长门赋》了。这篇赋文很好地继承了《诗经》的风比兴传统,所谓风就是长卿借陈皇后幽闭长门宫之事言自己仕途失意,是敢怨而不敢言;比就是“天漂漂而疾风”,及“孤雌峙於枯杨”之类;兴就是文中对陈皇后上下兰台,徘徊不前等动作描写,从而衬托其内心的抑郁不安。司马相如有碍于文学侍从的身份,所以是“敢言而不敢怨”,但长卿终究不是依附皇权的附庸,他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真实的情感,所以隐藏在汉赋张扬恣肆、体大物博之下的,实际是司马相如与后世大多数文人相类似的敏感之心与身世之感。虽不易发现,但如果加以体会还是可以察觉出长卿细微的叹息。
参考文献:
[1]李孝中.司马相如集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0.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4]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刘熙载.艺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6]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7]马积高.赋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1.
[9]万光治.汉赋通论[M].成都:巴蜀书社,1989.
[10]曹明纲.赋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吴娱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