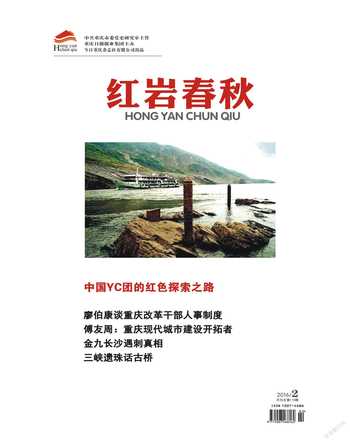童年生活忆趣
2016-09-10翟允洪
翟允洪
歌乐山保育院于1938年在重庆歌乐山建成。我4岁多进入歌乐山保育院,时间大概是1940至1941年。虽然日子很艰苦,但现在回想起来,它却是那样地亲切,那样地甜蜜,那样地风趣,又那样地充实。
自制的得螺转得好
爱玩,是孩子们的天性。在保育院,玩的较普遍的东西,要算是陀螺了,我们都以它的方言名字“得螺”称之,做法与一般的陀螺也不太一样。一般的陀螺都把木头的下端削成锥形,由于我们缺乏得心应手的工具,对粗一些的木头,根本无法加工,当然做法就简单得多。一开始是用一寸来粗的小木棒进行加工,但这种小木棒做出的得螺太小、太轻,一鞭子抽下去常常跑很远,甚至还飞了起来,可一掉到地上就不转了。
不知保育院的哪位大哥哥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在这种小得螺的外面,套上一节两寸来长、两三寸粗的竹筒,竹筒一头开口,另一头带有竹节,再把小得螺放在竹筒的中央,四面用废纸或者布条、湿泥土塞紧,下方只露出小部分的得螺锥体。为了耐磨,有的同学还在锥尖上钉上一颗钉子,并将露出的钉头打磨光滑,这样一来,得螺达到三四寸粗,也够重了,抽起来不会乱跑,而且鞭子抽上去会“啪啪”作响,不但转得稳,而且抽一鞭可以转好长时间。玩法也多了,除了一个人抽,还可以两个人同时执鞭,面对面,你一下,我一下,轮流抽。甚至还可以一人一个得螺,在鞭子的控制下,使两个得螺相互碰撞,谁的得螺被撞倒在地,谁就输了。当然,往往是得螺个头大的取胜。
大一点的同学还爱在晚上放天灯。他们先用竹篾扎三四个二三尺直径大的圆圈,再用细线把几个圈连成桶状,然后用浆糊和白纸,把顶上和四壁都糊起来,形成一个大白纸桶。又在最下面的竹圈上横栓一根铁丝,在铁丝的正中间,绑上棉布、纱布条。晚上放灯前,在纱条上面浇上一些油,由两个人面对面将纸桶提起来,另一个人在下面把油棉纱点着,不一会儿,纸桶里的空气加热到一定程度,一松手,天灯就冉冉升起。在繁星闪烁的夜空,一个个又白又亮的天灯在歌乐山的山风吹拂下,越飞越高,轻盈起舞,那光景,真是令人欢呼雀跃,魂牵神往,又遐想万千……
童趣来自大自然

我们这帮年纪小的难童娃,由于制作能力差,只好去找一些不费力又不花钱的玩法,比如逗蚂蚁打架。歌乐山的蚂蚁品种不少,个头大小悬殊,颜色也各不相同。有一种体形细长的黑蚂蚁,约一厘米长,我们叫它“蛇蚂蚁”,它的尾端长有像蜜蜂一样的刺,如果被蛰一下,也是很疼的;还有一种体形很小的棕色蚂蚁,它们各自的窝,相距也就三五尺,只要在两个窝之间,放上一些葫豆沫子、饭渣之类的吃食,往往就能令它们打起仗来。
观察蚂蚁是一件有趣的事。先是出来几个巡逻的蚂蚁,它们缓缓地逡巡前进,当发现有吃的后,就急忙掉头回去报信。不一会儿,双方就会领着各自的队伍,顺着我们洒下的食物前来搬运,搬着搬着,两队蚂蚁就短兵相接了。它们互相碰碰触须,立即知道不是一家人,于是很快就打起来。接着,双方又回去搬来更多的“兵力”,“大将”(即兵蚁,比工蚁个子大好几倍,头上有大钳子)也纷纷出动,投入战斗。再过一会儿,两窝蚂蚁倾巢而出,兵对兵、将对将地杀成一片,互不相让,直至尸横遍野、两败俱伤。我们兴奋地围着看它们打仗,一面吱吱喳喳,一面指手画脚。小蚂蚁们哪里知道,这只不过是几个小淘气为了看热闹而一手策划的把戏。
我们也喜欢抓蜻蜓。歌乐山的蜻蜓很多,红的、黄的、蓝的、花的,既有个头很小的“豆娘”,也有个头很大的“老虎蜻蜓”,真是五花八门,品种繁多。通常,我们会在一根小竹竿上插一个竹篾小圆环,圆环上粘满厚厚的蜘蛛网,等蜻蜓停下后,便举起小竹竿将网轻轻朝它背上一贴,翅膀就牢牢地粘住了。捉住蜻蜓后,我们把它的尾巴揪下来,换上一根小小的细竹棍儿,一放手,任它飞。但它的尾巴是个小棍儿,很快就掉下来了,反复折腾,蜻蜓精疲力竭。这时,我们开始想办法怎么吃它们了。蜻蜓的脑袋上是两只大眼睛,不能吃。细长的尾巴只是一层皮,也没吃头。只有胸脯上一块长方形的瘦肉,插上竹签,用小火烤一烤,十分可口。听大人说:昆虫的肉是高蛋白,吃一块,你就长一块肉,比猪牛羊肉强得多呢!
草地里有一种头很尖的蚂蚱,俗名叫“扁担”,我们也经常捉些来玩。在我们保育生中有一个传说:有几个小难童因为误吃了一些桂圆核,在中毒去世后,一个个都变成了“小扁担”。可是怎么才能区别哪些“扁担”是保育生变的呢?这时,我们会问一问被抓住的小蚂蚱,方法是用两个手指捏住它的大腿后半截,然后问它:“你是不是我们保育生变的?”如果它的大腿一伸一弯,身体上下摆动,这就是“点头”,表明它在说“是”;如果它一动不动,就证明它“不是”保育生变的,必须立刻放掉。
儿童的玩法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但当时却浑然不觉。
保育院轶事多
初冬的一天,阴雨连绵,天气奇冷,我们都冻得发抖,但身上仍穿着单衣。其实衣服就摆在寝室中的木案上,洗得干干净净,叠放得整整齐齐,只是没有老师的命令,不得擅自穿着。当时老师不在,同学们实在冷得受不了,不知哪位同学带头,大家都跟着把衣服穿上了。老师回来一看,十分生气,当即决定每人打三板屁股。
打屁股是有“标准”姿势的:先跪下,再趴下,把屁股撅高,以迎接板子的降临。我们全屋十几个小孩排成长队,先有三四位同学,在挨打之后不声不响地揉着屁股走开了。轮到一个叫侯有田的同学时,只见老师打一板,他一面“哎呦”直叫,一面向前爬几步;再打一板,又一叫,又向前爬幾步……三板子打完,他早已爬到了床底下,同学们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声大作,连打板子的老师也笑起来。这一打一笑,老师的气也消了,其他同学也就免去了惩罚。由于这个同学挨板子的样子,颇像老牛耕田,农夫向牛屁股上抽一鞭,牛就朝前走几步。再抽一鞭,它又走几步。这个同学姓侯,又叫有田,正好“对上号”,自此之后,同学们都叫他“猴子耕田”。他也不反对,每当有人叫“猴子耕田”,立即大声回答道:“哎”。好像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似的。
生活在保育院,难童们基本上都能吃饱饭,虽然也到外面弄些诸如青菜、小鱼、青蛙什么的来吃,但多半是好玩、好奇。由于经常躲警报,饿肚子还是免不了的,这时,吃饭问题就变得重要起来。从一首由同学们自填的《上饭堂》歌词中,可见一斑:“上饭堂,上饭堂,大家上饭堂!离了课堂,别了操场,拿起筷子碗上饭堂,拼我们的命,尽我们的力,不管,干饭有好多,不怕,稀饭有好烫,拿起筷子碗就开抢!”
后来,每次开饭,就由4个帮厨的同学坐在两个装满了米饭的大甑子旁,手持一把木勺,向排成长队的同学们的碗里,一勺一勺地盛饭。早来的早盛、早吃,晚来的晚盛、晚吃,容易产生差距,特别是来晚了的人,往往得吃着碗里,还要留心甑子里的“新动向”,随时调整吃饭的速度,否则,填饱肚子的计划就落空了。有时吃不饱,只得去外面弄点能吃的东西“垫补垫补”。
印象最深的要算拾野板栗。离伙房不太远的地方有一个厕所,不知哪位哥哥把厕所后面的竹篱给抽掉了,形成一个离地一二尺的豁口,我们这些小不点从这里钻出去是很方便的。从这里可以偷偷上歌乐山的云顶寺,那里林木繁茂、野草丛生,其中有一种树,长得十分高大,每当深秋,树上掉下许多小果,其果形、皮质、果肉和板栗一样,只是果实比胡豆还小,我们都叫它野板栗。有时我也带上自己缝制的小布包,和同学们去捡些回来,到伙房铲一些很烫的炉灰倒在地上,然后把野板栗摊在上面,再铲些炉灰盖到板栗上。只需要几分钟,就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当炉灰崩起一股股烟尘,就说明野板栗熟了,吃起来味道和板栗没有两样。只是捡野板栗的人多了,三五天里就很难再捡到。
偏方治好了癞痢头
不知是营养不良,还是由于水土不服,保育生中患上夜盲症、疥疮(重庆人称它为干疮)、癞痢头(癞子)的人特别多。保育院的妈妈们治癞痢头有一个偏方:先用烫水、刷子给他们洗头,把头皮刷得红红的,然后用布擦干,再用一块白布,里面包上用生姜、麻油、硫磺混合成的糊糊,在头上用力地擦。我当时虽然没长癞痢,但长了一头癣,痒得很,一抓就掉白屑。可能这种药是头癣、癞痢兼治,所以几乎大部分男生都要“治一治”。生姜多辣啊!发红的头皮上再擦上它,就像好多虫子在咬、蜜蜂在蛰,人人疼得“哎哟”直叫,但效果奇佳,几次就治好了。
夜盲症当时也较普遍,此症也是重庆人口中的“鸡公眼”。这叫法太形象了。只要太阳下山不久,即使天还很亮,公鸡们就看不清了。癞子好识别,俗话说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但夜盲症就不是这样了,人若患上这个病和公鸡类似,一到晚上,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就是看不清楚。妈妈们想尽一切办法,每天给患夜盲症的同学喝一碗猪肝汤,还有半个皮蛋。当时保育院不具备检查夜盲症的手段,有些同学为了这份伙食优待,就假装得了此症。后来,优待取消了——是经济不支?还是病治好了?还是假冒人士太多无法分辨?就弄不清了。
一般的感冒头痛,我们从不去找医生,顶多是去伙房抓把盐,泡点盐水喝下去,再到太阳下晒晒就行了。一天,我感冒了,头晕鼻塞,浑身没劲,我又如法炮制,到开水房舀了一大瓢开水,放点盐,准备端到外面边喝边晒太阳。但是,头小瓢大,挡住了我的视线,正巧路上有个煤坑,我端着瓜瓢刚走两步,就一脚踏空,掉进坑里,一大瓢开水“哗啦”一下从前胸直浇到下腹,当即烫出长长的一串水泡。这一烫一惊,感冒也吓没了,赶快往医务室跑。医生用红药水先把我身上的水泡弄破,挤掉积水,用纱布浸上红药水贴在伤口上,再用绷带从右肩到胸腹包裹了好几圈。幸好伤口没有感染,半个多月后就好了。只是身体上留下长长的一块“地图”,成为我在保育院的“永久性纪念”。
热闹的嘉陵江边
有时候,我们还悄悄跑到山下的嘉陵江边去玩。尤其是冬天到初春时节,江水较浅,水流较慢,清澈见底,这时的江边也热闹起来。有耍把戏的、拉“西洋镜”的、卖凉粉凉面的、卖炒米糖开水的、卖担担面的、吹糖人的、卖膏药的(我曾见有人把盘成圈晒干后的小蛇,放在锅里熬成黑糊糊的膏药)。沿着江边,有一排排的大瓦缸,上面盖着棕片,下面装着黄豆——生豆芽的。缸下面有個洞,可以把水漏出去。人们一天数次从江里舀起一桶桶水倒进一个个缸里,只见水从缸下面的洞又流回江里去,如此反复数天之后,缸里的黄豆就长成了白白胖胖的黄豆芽。
另外,江边还有一些竹竿和竹篾搭成的临时棚户,是专门做撑杆(用于撑船和撑木排)的作坊。人们把一根根长竹的弯曲处,先放在小火炉上烤,烤的时候不能只烤一处,要不断地旋转、移动,使竹子弯曲处的周围温度均匀上升。等到竹子烤得黄里带黑,好像烤出了一层油时,将弯处放到一个架子上别一别。把它别直后,立即用一个像衣服掸子那样的东西沾上冷水,淋到烤好后又别直的地方,只要用水立即把它浇凉,它就不会再弯回去了。直到整根竹竿都弄得直直的,再在粗的一端钉上一个锥形的铁帽,这样,一根撑杆就算做好了。我们学着用这个办法做挖耳勺也颇为成功,做好后就在自己耳朵上试验,我就是这样养成了挖耳朵的毛病,几天不挖,耳朵就痒得难受。
江边停着许多木船和运输木材的木排,有一天,我们在停木排的浅水处,手扶木排,两脚交替着打水玩。不知怎么搞的,我的手一滑,什么也抓不着了,两脚又够不着江底,于是“扑通扑通”一阵手忙脚乱,一面“咕咚咕咚”地喝着水。周围竟无一人发现我被淹了,幸好,扑腾了一阵子,不知怎么又抓住了一个木排,就这样保住了一条小命。
(责任编辑:韩西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