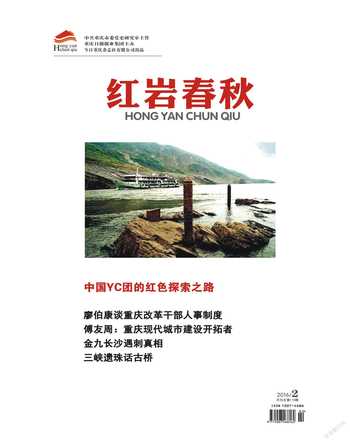上山砍柴
2016-09-10朱芸锋
朱芸锋
重庆市荣昌区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曾获重庆新闻奖。
犁完了用于来年春耕的冬水田,油菜籽也种下了,马蹬坝的庄稼人逐渐闲了下来。毕竟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该收拾的还得收拾,该筹备的还得筹备。农家烧的都是柴火灶,燃料之需当然很重要,更何况,农家屋檐下堆放着簇新的柴禾,更是新年到来“财源丰足”的好兆头。于是,人们三三两两地上山砍柴,成为这个时节的主要农活。
马蹬坝坐落在一个四面环山的平坝里,所谓的上“山”,其实也没有多高,出了后院沿着山坡往上走,经过10多分钟路程,庄稼人便进入属于自己产权的山林里。几个山头之间,树木葱郁,冬天白霧僚绕,只闻“乒乒乓乓”的砍柴声,相互之间却不见人影。偶而有人感觉到劳累,便一声长长的吆喝以解乏,声音还在山谷间回荡之际,来自其他山头的吆喝声也响起,权当相互问好的方式。
虽然只是一年辛劳的收尾部分,但砍柴从来都是农家的一件大事。此时上山砍的柴禾,弄回家后通常要供应来年的300多天,所以何时上山砍柴、家里需要砍多少捆柴,首先要计划好。家里有多少劳力,谁负责砍柴,谁负责背运,还有家里谁负责做饭、喂猪、牵牛喝水等,都得在上山之前,开一场“家庭会议”作出安排。
砍柴绝非简单的粗蛮体力活,它包含着很多技术问题。首先入门的常识,就是要正确识别柴禾的品种及生长年份。青冈丫等杂柴,通常是砍生长1年左右的,为什么呢?年份长的可以用于栽种四季豆、豇豆时搭架子,年份短的则经不住火烧,用处不大。至于松树、柏树丫子,一般都是砍生长2年左右的。
小时候常听父母谈论砍柴,或提到某人手脚麻利,一天能砍好多捆。原来这个“麻利”也是需要技术含量的,比如,每捆柴在捆绑之前,通常在地上放3根青篾条子,相互间隔30公分左右。这时,砍下1米多长的松树枝条,事先铺上去作为“底柴”。然后,将长短不一的杂柴,成堆成捆地按序放上,再在上面覆盖几根长长的松树枝作为“面柴”,最后才像扎粽子一样捆个结实。

如果父母当天要上山砍柴,早饭时通常会交待孩子:放学回家后,自己取放在某处的钥匙,进屋弄饭吃。所以待到下午三四点放学回家,饥肠辘辘的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生火做饭。这个时节,好在红苕多已收挖回来,而农家孩子所谓“做饭”,不过是挑选出一二十个红苕,清洗干净后装进铝锅用火蒸煮。更懂事的孩子还会淘几把米装进饭盒,加上适当的水,放在红苕上面。约莫半个小时后,红苕熟了,饭盒里的米饭也蒸好了。但是无论自己多么饥饿,锅里的香味多么诱人,孩子都不会在父母回来之前自行吃饭。我们会用一个盆、三五几个饭碗,加上一些咸菜和开水,一股脑儿地背到父母砍柴的地方,全家人一起享用。
就是这样简单的一餐,在我看来却是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美食。吃完孩子送来的饭菜,父母也到了一天该收工的时候。很多时候,孩子在前面提着马灯或举着火把,替后面背负柴禾的父母引路。彼时彼景,最适合用一个充满温情的词汇来生动概括,那就是——“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