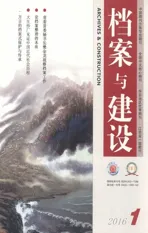甘福与晚清藏书名楼
——津逮楼
2016-09-05潘彬彬南京市博物总馆江苏南京210001
潘彬彬(南京市博物总馆,江苏南京,210001)
甘福与晚清藏书名楼
——津逮楼
潘彬彬
(南京市博物总馆,江苏南京,210001)
甘福生平概况
甘福(1768—1834),字德基,号梦六,清代学者,藏书家。南京名士甘邦钦之孙,甘氏“友恭堂”奠基人甘方栋长子,继为友恭堂家督,乡人称其为“孝义先生”。清廷例授文林郎,钦加布政使司都事,加按察司经历衔记录一次,覃恩敕封修职郎、安徽太平县教谕,敕赠奉直大夫,候选知县加三级;晋赠朝议大夫,中宪大夫,户部广东司郎中加二级;累赠通议大夫三品封典。性喜书画,工赏鉴,搜集乡邦掌故及金石雅训之学。
甘福生有四子一女,长子甘煦,次子甘熙,三子及四子均早卒。甘煦、甘熙在《梦六府君(甘福)行述》中记载:“道光壬辰(1832)冬,督浚秦淮,夜寐夙兴,备极劳瘁,遂患失音。然力疾从公,绝无倦态。”甘福热衷于乡里公益事务,且能尽心尽力而为之。1832年的冬天,在他督办浚理秦淮河工程时,因日夜操劳过度,以至失音,连话都说不出来。即便如此,他仍带病扶杖督办河工,直至工程圆满完成。
甘福长子甘煦因在外地为官,曾顺道归家省亲,见父亲总是忙于里中公事,又不顾惜自己身体,家人无不为之担忧。一天,甘煦与弟弟甘熙商量,乘父亲难得空闲在家时,兄弟俩一起“谆请节劳静摄”。甘福听罢,则瞿然正色道:“大丈夫达则善天下,穷则善乡井。凡有益于世者,力所能为必为之,断不可存因循推委之念。予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众所周知,儒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甘福从小聪明颖异,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儒家学说中的理想主义和入世精神对其影响不言而喻。甘福的言行举止令人钦佩,成为甘氏后人立身处世的楷模与表率。
甘福赋性慷慨,且好施予,以利扬济人为念。他平日案头放置一本袁了凡先生的《功过格》,以之自励。他见一义,闻一善,必踊跃图成,若不成则恤身家而为之。嘉庆甲戌(1814)春,甘福倡捐五百金,创建望江楼,设立男女堂并造救生船。他筹划章程,编造简册,继而与同道者在烈山、三山营、龙潭等各险要口岸增设分局,统归于城内长乐渡总局,以综其成。道光癸未(1823),龙潭局经费出现支绌,甘福再捐五百金相助,使龙潭局赖以继续。救生局成立后的20多年,被拯救者不可胜计。当时民间流传着称赞甘福善举的一句话:点夜灯以照人行,造河船以济人渡。

甘氏宅院中的津逮楼
嘉庆丁卯(1807),南京饥荒,米价腾贵。甘福捐四百余金,施救饥民。他的夫人阮氏,为助其一臂之力,“脱簪珥、质衣裙”,不惜代价。嘉庆甲戌(1814),又遇大饥荒。甘福慷慨捐六百金。他尤其怜悯因受灾“或无父母可依,或无家室可托,流离失所,乳哺靡从,啼饥号寒,填于沟壑”的孤儿弱女。道光辛卯(1831)水灾之后,乡里乐于善事者,在回光寺、五显寺、翔鸾庙、永庆寺等处收养男童。自冬迄春,被救活的男童甚众。甘福见受灾男童虽得以救助安置,但女童尚无所依,未免善举行之有偏。他倡捐钱米,与乡绅设局尼庵,广为收养女童。癸巳(1833)冬,上元邑侯冯晓江刺史捐俸银,收育婴孩于养济院。甘福又捐衣履等物相助其善,“恤孤之惠,抑足风已”。[1]慷慨济世为甘氏家族传承之家风,甘福父亲甘方栋在世时即便如此。据《同治续纂江宁府志》记载,甘方栋早年虽家境贫寒,但敦厚尚义,乡里有人借了钱而无力偿还的,他会焚其借据,并给予资助。家风传承之关键在于上行下效,加之甘氏子孙仁孝,以甘福为代表的甘氏族人慷慨济世的美德受到广泛赞誉。
甘福注重人伦教化,对民间忠孝节义之事倍加推崇。嘉庆二十二年丁丑(1817),甘福出资于小丹阳故里,设义塾、请教师,免费教育当地本族贫寒者子弟。道光癸未(1823)春,甘福为寻觅收藏古籍善本,赴浙江客居石门,他见当地善士在建育婴堂,异乡临时驻足的甘福随即捐银二百两。此后,他每年捐寄洋银,以周济育婴堂日常所需。
甘福曾对长子甘煦说:“人生以节义为尚,女子守节义,较男子尤难。自古清议出于学校,凡孝子、义士、贞女、节妇,例由学官加勘详办。汝幸得校官,当以此为要务,不可逡巡推诿,视为故常,致辜职守。”甘煦任宝应学篆时,甘福在家书中再三示及此事。甘煦后又调任安徽太平教谕,甘福又教诲道:“以此地居万山中,虽属石肥土瘠,而闻其妇女,亟重名节。汝亟宜留心。”甘煦谨遵父命,查当地县志所载,未旌贞孝节烈妇女及修志后无力请旌者,共三千六百余口。甘煦协同当地绅士,采访确实,捐俸造册,详办于道光十年(1830)。经相关部衙复核,准建立总坊。甘福闻知此事后非常高兴,曰:“表潜德,即以激人心。吾志慰矣。”[2]甘福多年为商的经历,加上嘉道年间国势转衰,内乱不休,社会激烈动荡,使甘福切身感受到社会政教无常,人多失节。因此他在家族子弟教育、风气教化方面提出了某些具有民本色彩的主张,身体力行或要求后人努力践行之,难能可贵。
津逮楼及其收藏的社会价值与影响
甘福之所以名留青史,除了他的品德、声望、传习家风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他的文化贡献。甘福曾遍访吴越,搜集书籍十余万卷,并建成饮誉江南的私家藏书楼——津逮楼。“津逮”二字出于《水经注·河水》:“河北有层山,其下层岩峭壁,岸无阶,悬岩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积卷矣。而世士罕有津达者,因谓之积书岩。”清代著名学者戴震校曰:“达,近刻作逮”。“津逮”意指求知的入门之路。该楼建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毁于咸丰三年(1853)的兵火。
一、为甘氏藏书世家地位的确立奠定基础
南京甘氏家族自两晋以来,皆以诗礼传家,世代书香。在中国古代,大凡读书人家都渴望拥有自己的藏书楼。所以说,津逮楼的出现不可能为孤立偶然。清乾嘉年间,甘家始立友恭堂,并择儒学精髓之“友恭”二字立为堂号,折射出其家族的儒雅风范。因家族古有读书传统,在筑建新宅以前,甘家的历代藏书已有近万卷。或许是当时为建新宅耗费过甚,而暂时无力再建藏书楼,甘家宅院内仅建有两个藏书小舍——“桐阴小筑”与“保彝斋”。据《甘泉里甘氏族谱序》记载,甘家自明代进入南京城,是以经商起家,也就是“亦商亦儒”。乾嘉之时,甘方栋与其四子甘福、甘遐年、甘鹤年、甘延年同心协力,多年经商,共创家业,数十年如一日,为甘氏友恭堂积攒下可观的家产,也为后来家族营建藏书楼津逮楼和搜集购置古籍善本、金石书画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嘉道年间,随着甘氏后裔的逐年增多,家中原有的书舍已不能满足所需;加之甘福在先祖藏书的基础上,又积年收藏了大量古籍善本以及金石彝鼎,都散存于家中各书舍和其它房间。为解决家中读书、藏书需求的日益增长与现有设施不足的矛盾,以甘福为代表的甘氏族人经过周详考虑,最终商定仿宁波“天一阁”制式,在宅院的东南隅兴建津逮楼。道光十二年(1832)津逮楼落成,甘家遂将历代收藏的古籍集中存放于此楼,以利后世永保,被当时南京藏书界传为美谈。平日极少赋诗的甘福,欣然于该楼落成之日作七律二首,其中一句为“为语儿孙勤世守,此中滋味最悠长”。他语重心长地告诫甘氏子孙,要勤勉世守津逮楼所藏,细心品味其中蕴藏的深邃学问,以延传书香至久远。
根据南京历史文献记载,甘氏藏书在建津逮楼之前,甘家历代先祖均“累有收藏”,津逮楼建成后甘氏族人又不断续藏,津逮楼藏书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品质上,都决定其在清代南京私人藏书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甘熙在《白下琐言》中描述道:“家大人(甘福)性嗜书,往来吴越间,遍搜善本,积书达十余万卷”。粗略估算,甘家鼎盛时期津逮楼的藏书规模应在十六万卷以上。甘福生前“尝八游吴越,访求善本载以归”,“四十年来费苦搜”,其中三十卷宋版《金石录》这一罕世巨著即为甘福游历吴越之时花费重金搜罗所致。道光年间,大学士朱兰坡在《甘氏津逮楼藏书目录序》提及甘福收集善本的艰辛不易,说甘福本人酷爱书画,并精于文物鉴赏,尤其嗜好收藏图书,甚至被虫蛀鼠咬的图书都亲自修补好。甘福还将藏书一一整理,并“辑成目录凡十六卷,分门别类,条绪井然”。[3]由此可见,嘉道时期甘福成为南京甘氏藏书世家地位得以确立的关键与核心人物。
二、发挥藏书的教育作用,惠及乡邦学子
对于中国绝大多数藏书楼来说,皆遵循以藏为主的原则。例如当时的“天一阁”就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子孙不得无故开门入阁,更不得私领亲友入阁。然而,作为南京私人藏书界之翘楚的津逮楼,不仅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古籍善本与金石彝鼎,更是在管理和利用藏品方面享誉江南。道光年间,以甘福为代表的甘氏族人就已对传统藏书楼“以藏为主”的原则进行了突破性的改革,从而促进南京地域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造就。
对于费心搜罗、来之不易的藏书,甘福十分珍惜。津逮楼建成后,他曾亲订训约,“至亲密友,不得私自借书下楼,愿就读者听。违者以家法治。”其中的“愿就读者听”五个字,体现了甘福与其他藏书家的不同,即不是为藏而藏,将书束之高阁,供自己欣赏。他在诗中言道:“插架非徒供秘玩,研经愿与企前修。”家族子弟甚至是亲朋学友都可以到楼中读书,经过允许还可借出。可见甘福已经具备最初的文化资源社会共享和服务意识,大大激发了津逮楼藏书教子、惠及乡邦的社会作用。据《梦六府君行述》记载:“陆心兰方伯纂辑国朝理学名臣言行录,慕甘福之名,而至津逮楼访载籍。”甘福之子甘熙还与南京另一藏书大家开有益斋主人朱绪曾多有往来,并相互借阅秘笈,以相订证。甘元焕(甘熙堂弟)在他的《读书续志跋》称:“先生(朱绪曾)所居秦淮水榭,藏书十数万卷,丹黄斠画皆精审。先石安仲兄,喜搜乡邦掌故及金石雅训之学,时从讨证。先生辑《金陵诗征》,亦假余家津逮楼书,瓻借往还,几於置驿。”当代国学大师徐复先生曾推崇曰:“甘福父子,有功士林”。津逮楼对乡邦人才的教育激励作用在南京古代私家藏书楼中,可谓首屈一指。
甘福父子藏书过程中,尤其重视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甘熙曾说:“前贤著述有关乎是邦考证者,近多失传。家大人留心掌故,凡此类书,搜访尤殷。”津逮楼中收藏的南京地方文献相当丰富,有唐许嵩《建康实录》二十卷,宋陈彭年《江南别录》一卷,郑文宝《江表志》三卷,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二卷,周应合《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十五卷等,总计有四十多种。其中不乏孤本秘籍,如明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即为孤本。甘福去世后,甘煦、甘熙兄弟同样是嗜书之人,甘熙更是利用津逮楼所藏,编写了南京地方文献的经典之作——《白下琐言》。
津逮楼的另一功绩是为甘氏族人刊刻和出版家中所藏的善本秘笈提供了诸多便利条件。在清代,藏书家刻书几成风气,南京的刻书业十分繁盛,将自己所藏善本秘笈刊刻出版,使之化身千万,惠及学林,是每个藏书家的愿望,但刻书之费,非一般人家所能为。甘福虽在津逮楼落成两年后离世,但其子侄亲属仍继续坚持藏书刻书的事业,直至清末,津逮楼陆续整理出版了许多文献典籍。如刊刻了盛时泰的《栖霞小志》,校刊了宋版的《建康实录》以及《金陵诸山形势考》《金陵水利论》《津逮楼地书九种》《金陵忠义孝悌祠传赞》《帝里明代人文略》等。[4]
三、成为收藏和考证金石书画的学术殿堂
嘉道时期甘家是殷实富裕的收藏之家,甘氏族人不仅收藏了十多万卷的古籍善本,对历代珍贵的金石彝鼎、名人字画也甚为青睐,悉心搜购。晚清著名文人陈作霖撰《运渎桥道小志》云:“缥缃彝鼎,充栋庋藏。”甘炳有《保彝斋钟鼎款识歌》:“老人百物俱不好,坐拥缥缃自摩抚”。津逮楼落成之后,楼上存放古籍善本,楼下收藏金石书画。甘福欣慰之余,赋诗感慨:“云烟供养邀清泽,金石摩挲发古香”。甘煦亦有诗云:“云蒸几席恒春树,花晕钟彝太古香。”笔者通过查阅《白下琐言》及相关文献得知,尚有津逮楼的部分古物器有据可依,略举如下:商父甲尊、周纪伯钟、周楚公钟、兽啮环耳汉壶、吴天玺纪功碑拓本、南宋三十六砖、元铜簠、宣德炉、顾与治墨迹、明代殿试墨卷、史忠《卧痴楼图》、姚鼐书画册及折扇、程春海书札等。《续纂江宁府志》记载:“至今谈收藏者,犹称甘氏津逮楼焉。”上述藏品,或许不及当年津逮楼所藏的百之一二,但可略窥其观,其中不乏国家级珍贵文物,可谓价值连城。
值得一提的是,甘福父子除了对家中藏书潜心研读之外,对收藏的金石书画,特别是三代彝鼎、砖瓦器物,每获之,视为至宝,必仔细鉴赏,遇有铭文,便查阅古籍,以相考证。甘煦曾在诗中写道:“尤嗜金石学,考订心力专。三代秦汉下,钟鼎刀剑泉。凡有题咏者,探讨穷丹铅”。究其原因,清乾嘉时期,朴学盛行,金石之学亦深受影响,学者攻训诂、习考证渐成风气。在《白下琐言》中还记载了甘福的收藏经历。甘福曾经收藏了一百多件宣德炉。宣德炉为明代宣德年间宫廷制造的器物,当时就十分珍贵,到清代,更是被人视为宝物。甘福先将其陈设在书室中把玩,后来他又收藏到商周彝鼎,认为这些上古之物“青绿斑驳,悉出本真,而时代先后,铭词异同,足以资考核而广见闻”,其与宣德炉之类供人把玩的器物相比,真有天壤之别。于是甘福就将宣德炉装进箱子束之高阁。甘福父子对津逮楼所藏的纪伯钟、楚公钟、父甲尊、祖丁爵等三代彝鼎上的铭文都细加考证,并都收录在《白下琐言》中。如今,这些器物虽已无处寻找,却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资料,津逮楼也无可置疑地成为甘氏家族收藏和考证珍贵金石和名家书画的学术殿堂。
甘福父子所建之津逮楼,是承载南京厚重的历史及其人文精神的文化宝库。尽管其存世短暂,却在南京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1][2]甘櫯编著:《金陵甘氏考》[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
[3](清)甘煦、甘熙:《梦六府君行述》,清道光刻本。
[4]马麟、杨英:《甘熙宅第史话》[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