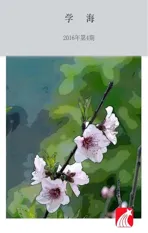“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2016-08-29吕方梅琳
吕 方 梅 琳
作者简介:吕方,社会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梅琳,地理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武汉,430079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基础秩序”重建*
吕方 梅琳
内容提要社会基础秩序,指的是基本的社会联结机制,包括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问题关联的方式、制度与文化。以单位体制的确立为坐标,晚清以降的百余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前单位社会”、“单位社会”及“后单位社会”三种不同形态。与此相应,社会基础秩序也在不断演进。社会基础秩序的形成,既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国家与社会关系设置的产物,亦对社会运行的其他方面产生着显著的影响。“后单位时代”中国社会在一定范围内出现了值得警惕的“社会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缺乏关联的管道,社会领域出现无序互动和失范频仍的乱象。究其实质,在于“后单位时代“社会基础秩序尚不稳固。是故,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建,乃是当下社会治理的核心议题。
“后单位社会”社会基础秩序社会原子化社会治理
在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洪流中,以单位体系为核心的“总体性架构”逐渐消解与变异①。如果说,单位社会代表了国家借助单位系统垄断性配置社会资源,将所有社会成员吸纳到单位组织的一体化架构中,进而扮演着全能主义的父爱角色,看护与照料其社会成员的关系形态②。那么,“后单位时代”社会治理的深层命题便在于,走出单位社会理想城堡,失去了单位组织“庇护”的个体,如何在日渐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流动性的时代,重建个体之间以及与公共问题的关联③。
现象与问题
在社会治理研究领域,如何生产社会、守卫社会,已然是知识界关于“后单位”时代讨论的重要论题④。研究者发现,虽然我们在作为理论工作的社会治理研究和作为政策领域的社会建设实务方面,均着力良多。但社会失范、无序互动的情形,仍屡见不鲜,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参与和影响公共事务的能力大相径庭,尤其是边缘群体在利益捍卫、利益实现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制度化渠道,往往采用一些“越规”的做法;一定范围内,社会戾气弥散,暴力与强制成为社会互动和秩序形成的主导法则。一方面,社会成员在面对个人烦扰或一般困境时,不是诉诸法律和社会组织,而是仰赖政府,寄期望于贤明的官僚能够俯察民情,但另一方面,公众对于公共权力的不信任感亦较为普遍地存在。
在既有的研究看来,对于上述现象的解释,大致形成了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上述现象之所以出现,根源在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既有的社会规范失灵,而新的社会规范并未有效建立起来,由此出现了道德滑坡、价值体系解组的问题。因此,对社会失范、无序互动的矫正,对社会戾气的化解以及信任的重塑,重在公民道德建设,进而将道德与价值观念内化到每个社会成员的动机体系中。但恰如涂尔干指出:
道德是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并受历史动因的制约的,……只有条件变了,道德才能随之改变,并且只能在特定的可能范围内改变,这是确切无疑的。⑤
只有建构完整的社会才能拥有道德和物质的最高地位,它不可避免地要为个人立法,同样,也只有机体构成的道德实体才能凌驾于私人之上。而且,除了人们日复一日形成的短期关系以外,唯有上述那种连续性,即不断延续的特性,才能维持规范的存在。……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⑥
换言之,道德不应仅被理解为个体“修己内圣”的内在精神完满状态,作为一种社会事实,道德是一种社会现象,道德的形式、内容都是由特定的时空条件所规定。更为重要的是,道德秩序的形成,建基于稳固的社会联结机制,在涂尔干颇有点浪漫主义怀旧情绪的观点看来,这套联结机制是历史久远的“职业群体”。依此而论,离开对社会变动和社会联结机制的考察而谈论道德建设,所得出的结论亦往往感慨多于启发,遗憾多于顿悟。
另一类观点认为,中国正在经历规模空前的治理转型,国家、市场与社会的边界正处在重新界定的过程之中。一方面,国家对市场领域的规制(regulation)在不断强化,另一方面,社会建设取得可喜进展,不仅社区组织的公共服务传递能力得到提升,社会组织也快速发展。未来,中国将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作共治社会治理新格局。但问题在于,这种颇有点目的论意味的叙事框架,在中国转型社会复杂而丰富的经验现实面前,显现出解释力不足的困境。单位社会消解的过程中,单位组织原来承担的社会职能,逐渐分离出来,回归到政府的科层体系。政府和知识界期待着社区组织,能够取代单位,成为社会整合的基本单元。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作为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建设快速推进,各种地方模式纷呈,社区建设的内涵也逐渐扩展到社区党建、社区中介组织、社区自组织等多项内容。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运动,虽然强化了国家公共服务的传递能力,但其社会自治和社会整合能力却相对有限,社区所能动员和辐射到的人群,相对而言是比较有限的,主要限于老年人、志愿者等社区活动的骨干力量,从而很难成为社会成员联结与协作的平台。此外,社会成员的公共需求,时常溢出了社区常规运行的边界,无法得到及时而有效地回应。近十年来,社会建设受到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得到了快速的发育。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36.6万人,社会团体28.9万个,基金会3549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⑦。但现实地看,受制于资源和能力的约束,社会组织并没有成为吸纳社会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载体。换言之,无论是行政化色彩浓重的社区,还是力量孱弱的社会组织,都与“治理”理论所预言的转化过程大相径庭,恰恰相反,对于政府主导公共性的依赖,依然是较为普遍的社会心理。
那么,如果说公民道德建设理论和“治理转型理论”对于回应我们所提出的经验现象,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回答。我们又该如何解释当下较为普遍存在的社会治理困境?文中提出的这些看似独立的社会问题,是否分享着某种共通的社会结构性根源?缘何我们关于社会治理的种种舶来理论和模式总结,在实践层面经不起时空变动的考验?最后,单位社会的研究传统,对于理解“后单位时代”的个人困扰和公共议题有怎样的启示?带着这样的思考,文章将首先从“社会基础秩序”的概念出发,探讨其对于社会成员有序互动,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衔接的价值与意义,进而讨论随着单位社会消解与变异,中国社会出现的社会原子化趋向对社会基础秩序重建提出的新挑战。
何谓“社会基础秩序”?
对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追问,是社会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按照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界定:“秩序的意思是单一性(monotony)、稳定性(regularity)、重复性(repetitiveness)以及可预见性(predictability)。”⑧换言之,所谓社会秩序,是社会成员之间稳定的社会关联状态,并且有一系列与该社会关联形式相应的文化、制度和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动,并且社会成员能够对自己和他人在特定情形之下的行动,有稳定的期待。



回到我们文章一开始提出的现象。道德滑坡、社会失范、信任危机等看似孤立的社会现象,却分享着共同的结构性根源。随着单位社会的消解与异变,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秩序,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实现管道、公共协作和价值整合的功能逐渐丧失,加之快速的市场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社会风险激增,社会生活领域出现了值得警惕的原子化现象,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协作的困境,以及应对公共议题能力的匮乏。
“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秩序


新中国通过单位制度将社会成员组织起来,获得了国家主导工业化,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组织基础。而从基层社会的视角来看,单位组织在其实践层面,稳定地与城市地域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城市中一个个封闭的“共同体”,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互动提供了制度化的形态,并且作为一个没有陌生人的城市共同体,单位空间是一个全息的社会空间,社会成员对单位空间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换言之,单位制的实践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基础秩序,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理解这种社会基础秩序的特征:
其一,单位组织为基层社会构架了一套社会成员之间交往、彼此关联的方式,并且形成了公共议题与社会成员之间互动的基本秩序。单位组织把社会成员组织在一个集体中,并且在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对社会成员负有责任。单位组织,不仅是个人谋求生计的职场,是国家赶超式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同时也为社会成员提供全面的看护与照料,举凡生活中衣、食、住、行、保、教、养、医等公共事务,都是由单位组织来提供。当然,以单位为中心的公共性,实际上是由单位组织扮演“微观国家”的角色,代表国家来回应社会成员的社会需求。这种个体与公共议题的联结构造,被封闭于特定的组织边界之中,使得单位社会时期的中国社会形成了独特的“蜂窝状结构”。每一个单位组织,在其实践层面,规定了单位成员的利益组织化边界,通过一定规章制度和正式程序的设置,来分配公共福祉。

总而言之,单位制作为一种社会基础秩序,为“单位人”提供了彼此关联、协作,以及参与公共问题、公共事务的基本管道和价值观念体系。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组织到单位体系中,成为单位人,并且以单位人的身份展开社会互动和公共生活。“单位社会”不仅意味着一套组织架构,更内化到单位人的精神世界和动机体系中。
“后单位时代”的社会原子化困境





社会基础秩序的“生产”


在经验场景中,社会基础秩序的生产的本质在于,通过重要社会联结机制的重建,走出“社会失灵”的困局。在国家主导的“公共性”构架之外,激活社会自我组织、自我服务和自我发展的潜能。依此视角,回望过去十余年社会建设的历程,不难发现,通过自上而下的社区建设、网格化社会管理、社会组织发展等社会建设运动,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在基层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联结渠道,社会成员之间有序的社会联结、积极的社会参与,仍显不足。换言之,“公”与“共”之间,存在明显的失衡现象。所谓“公”指的是国家公共职能,而“共”则指涉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互助和社会参与。“共”的薄弱,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体困扰的解决,要么诉诸于慈爱的国家来照料,要么借助时常有些偏激的个体行动。其后果是,社会的无序互动、利益无序表达,缺乏解决公共问题、应对社会风险的制度化形式。
大致而言,我们可以从载体重建、制度重建和观念重建三个层面来认识社会基础秩序重建的命题。首先,社会基础秩序是公共性格局中的重要组件。市场经济改革和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社会基础秩序的实现形式包含,但不限于以下的内容:社区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自治团体、公共议论等。多元而丰富的实现形式,是社会基础秩序的经验载体,为社会成员之间的“公共联系”提供了基本的组织框架。其次,社会基础秩序能够真实而有效地运转,尚需要完善的制度支持。知识界多有对社会自组织社会性不足的忧虑,恰是指某些社会领域存在名实分离的现象。使“社会基础秩序”运转起来,不仅意味着“数字”方面的社会建设成就,而在于真正赋权社会,社会联结真正具有其实际的意义。最后,通过“共”来解决公共困扰,应对社会风险,成为托克维尔意义上的“民情”。即关于社会联结的价值体系、规范体系和道德准则,内化至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成为影响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惯习”,而这种“内化”,并不外在于社会基础秩序的生产过程,恰在于对社会基础秩序持续不断的追求和维护过程之中。
必须承认,社会基础秩序的重塑,将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过程。“后单位时代”,在多重社会变迁因素叠加的影响下,在社会空间剧烈分异、重组的时代背景下,各种传统和新型的社会风险激增,并且前单位时代、单位时代的制度和文化遗产也依然发挥着影响,朝向新型社会基础秩序生产难以一蹴而就。但毫无疑问,通过社会基础秩序的“生产”,尤其是激活其所承载的“共”的职能,构筑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成员与公共事务之间关联的制度化管道,从而结束社会原子化的局面,是新时期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主要着力点。
①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吉林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②田毅鹏、李佩瑶:《计划经济时期国企“父爱主义”的再认识》,《江海学刊》2014年第3期。
③张静:《通道变迁:个人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
④沈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
⑤⑥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三联书店,2000年,序言第7、17页。
⑦民政部:《2013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民政部网站,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406/201406006 54488.shtml。
⑧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84页。
⑨孙立平:《守卫底线——转型社会生活的基础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⑩田毅鹏:《注重社会基础秩序建设》,《吉林日报》2006年1月4日。
















作者简介:吕方,社会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梅琳,地理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武汉,430079
〔责任编辑:毕素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国家专项扶贫政策执行的治理结构及其绩效分析”(项目号:13CSH08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跨国机构与地方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与效应:基于我国四城市的实证研究”(项目号:4140116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