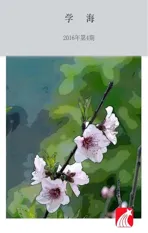“我”只在作品中呈现:保罗·克利的绘画和理论
2016-08-29陈忠强
陈忠强
作者简介:陈忠强,笔名陈忠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在站博士后,安徽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chenzhongcun@126.com。上海,201620
“我”只在作品中呈现:保罗·克利的绘画和理论
陈忠强
内容提要在20世纪所有的艺术家中,保罗·克利是一位让人敬畏又有距离感的绘画高手和理论大家,是一座让人仰止的高山。当今是一个图像泛滥的年代,绘画何为?他这句“艺术并不是呈现可见的东西,而是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可为一剂良药,克利是把绝对精神性的领悟放在首位,以时间凝聚获得张力,从内心深处和自然深处开始是克利绘画与理论的出发点,克利在生前始终在寻找他自己理论的高度,尽可能地把它运用到艺术创作或者再思考之中,他的新形式每一次曲折变化总是伴随着一次色彩的变化,而每一次色彩的变化又导致一种绘画形式的诞生。
保罗·克利自我与绘画呈现与创造
“‘我’只在作品中呈现”是德籍瑞裔的艺术家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的绘画与理论重点,正如他自己所提出:“艺术并不是呈现可见的东西,而是把不可见的东西创造出来。”这是克利思想与心灵领域的独特的感受,是克利与其他的艺术家不同之处,也是他对20世纪现代艺术做出的极大贡献之处。
“我”展示出所有法则
在20世纪所有的艺术家中,克利的绘画与理论“最坚定的探索了令人激动的幻想领域。他仿佛一边在探索潜意识,一边搜寻纯粹真正的独一无二的实践。”①在这一过程中他忍受着自我的那份孤独,在他死亡来临的那一瞬间,他最终走向自我终极而真实的呈现。克利讲过“最微小的叶子也能展示所有的法则”,了解这些后,艺术家才能展现出事物的普遍法则,克利懂得如何理解和应用辩证法,比如有形与无形、静止与运动、主动与被动、意识与潜意识等的相互关系。欣赏者希望展现在自己面前的是现成的综合体,而不愿意自己动脑筋思考或去探究发现。克利习惯于向我们展示创意的整个过程,强调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会让很多人疏远他的理论或绘画,艺术作品“不是规则,它凌驾于规则之上——艺术是事物的原始基础的投射,存在于三维/空间之外,是呈现、预感与神秘的象征。但人们必须不停得寻找它。”②在《克利谈艺录》中他告诉世人,门外汉和艺术家的区别是,门外汉是没有用任何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表达或没有机会通过创造形式来得到释放自己的思想,而艺术家在生活中有很多困难,唯一的优势是“这个生命不同于你的地方只在于他能够用自己特殊的天赋去控制生活,这个生命可能比其他生命更幸福。”③他在努力寻找打开艺术正确方向大门的金钥匙,很多人都在寻找这枚万能钥匙,如何能做到这种“自我”的呈现,克利认为“一个画家运用语言真正的合理性在于通过刺激转变成一种新的视角方法,解除一些重点或故意让步的正式元素,把更多的强调放在内容上。”④在克利的理论中认为“在最小的叶子中,与整个规律的相似性被准确的再造出”,人只有通过这种深刻的认识才能有独到的思考,所以在艺术家那里,相似于宇宙的秩序行为也就被再造出来了。
克利的最伟大的之处是“克利能够深刻洞察自己及整个世界(Klee possessed a high degree of insight into the world and himself),”⑤克利在成熟期后就连续不断地反复研究离本质更近的主题和形式。1902至1906年,克利在伯尔尼期间有一个重大发现,它是“我现在的目标并不是在创作精美的绘画——我还没有那样的造诣——而是(至少)成为一个人……我应当向任何一个略懂技艺的初学者一样,掌握绘画技巧。相对于来自目的本真性的限制,我更不愿意自己为绘画技巧所限(《克利的日记》)。”⑥现实中的艺术家多为绘画技巧所限,甚至痴迷其中,并享受绘画技巧给他带来的所谓“幸福”,这就是克利与其他艺术家的不同,他能深刻的洞察自己甚至整个世界,学习绘画技巧,突破绘画技巧,建立自己的独立的艺术语言和思想体系。
1914年,他与好友马克一起旅行突尼斯,是他寻找到“我”的转折点,对克利精确的表达是“他在这里找到了他已经在他的生存中建立起来的那个精神中心的物质对应物。艺术家的天才和当地的精神相一致。”⑦克利的成长和变化是他用自己理论来保驾护航,是水到渠成和自然而然的事情,他对待世界的态度应该说基本上是理性的,在克利的理论中能够感受到包豪斯的环境对他的影响,他更倾向于抽象与构造——克利却将其称之为“纯的”,他“认为抽象是十分具体的,缺乏精神的,而纯的表示自我与内在,是一种本质的、与心灵而非理论有关的状态。”⑧克利在包豪斯的教学中,箭头的符号他用来表示力线,这样在不经意中这种“力线”就进入了他的作品,横的、竖的和图案的等,然后克利把“这种体验转换成一种不可思议的思想。”⑨
“我”在作品中的呈现


克利经常的写生练习使他没有脱离自然的轨道,另一方面他讲过不能由于畏惧自然透视而失掉写实的机会,真正的艺术家肯定不是一部高级的照相机,他应该超越照相机,视野更广阔、复杂和丰富,艺术家是万物中的一个特别群体,但他是地球中的一个分子,是一个爱思考和常思考的积极分子,把看到了真正的“我”并产生了更多的空间概念,自然界的万物各种方式通过人眼变成形式,形成外在视象与内在幻象的综合体。克利的理论是来自他的作品创作,同时他的创作又验证他的理论,这样阳性原则(恶、激动、情欲)和阴性原则(善、生长、平静)的同时并存,导致了他绘画与伦理的稳定状况。


“我”的绘画是用线条去散步
克利称自己绘画是用线条去散步,他笔下的线条自由、机敏、满载生机、情致和诱惑。他的线条不仅勾画轮廓表明心迹,而且常常用来代替被省略的明暗变化,成为明暗及光感的分界,甚至是色块的分布、色调关系的界限。用刺激转变成一种新的视角方法,这也是克利理论描绘出如何得到打开艺术正确方向大门的金钥匙的方法,它又具备哪些特征呢?克利在《谈艺录》中认为金钥匙特征之一是线条、色调值和色彩(或尺寸、重量和质性)。克利在《谈艺录》中谈艺术作品创作时讲:“创造一件艺术作品——像树冠的成长,由于进入特定的绘画艺术(维度)空间(dimensions)的结果,必然得伴随着自然形态的变形。”绘画作品完成后,在这幅作品中“蕴含着自然的重生”后的“我”。“我”是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重生,这个空间有些什么呢?这个空间中或多或少的拥有线条、色调值和色彩——但它是通过重生(艺术创作)的线条、色调值和色彩。
创造中产生的线条是有限的,只是一些简单的尺寸度量。关于线条,克利将线条视为“独立的绘画元素”,坚持“素描风格”与“即兴创作”的原则。根据艺术的世界历史,无论西班牙阿尔塔米拉洞窟里壁画上的野牛,还是野兽派造型艺术中的物体轮廓,甚至中国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等,线条是造型艺术的重要表现技法,艺术家赋有它抒情性、抽象性和表现性,克利充分认识到线条在作品中的创作地位,把它当作造型艺术的基本要素。克利在梵·高身上看到了“最高意义的线条”,在他的作品或理论中要求线条变得更结实而且更完美,并且应该吞咽和消化我的细小的笔迹。
英国著名画家威廉·布莱克也强调:“艺术作品的好坏取决于线条。”克利在艺术理论中特别强调线条,如“弹性的线条越是独特、鲜明、坚韧,艺术作品就愈是完美。”事实上线条本是毛笔下最好的产物,它是中国画的灵魂,可以见的线条在克利身上十分可贵,以笔达意、以形写神、直抒胸臆,克利认为是“谋求一种艺术性表现上的存在形式”,这样线条和色调值/明暗配置成为作品的主导因素。
关于色调值/单色画,克利认为以轻重为特征,这个阶段可能以白色能量为主,下一个阶段或许黑色为主,色调是通往色彩王国的第一步。1914年的突尼斯的旅行,让他发出这样的感慨:“色彩已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灵。”突尼斯的旅行对克利的影响至关重要,后来可以证实对克利的艺术发展的很大的推动,为他后期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使“克利喜好新奇的天性再一次得到满足。”克利把空白处当作高光点,再渐渐达到最深的色度,“这一举动是通过一种不宜觉察的中间色调的调整”用来加强的,并且最终在“明暗配合的相互依存中”发现了这一特征。“我”如何在作品中呈现?在克利绘画与理论中特别强调的提出色调,色调是一种十分微妙的视觉感受,由物体和环境之间的冷暖关系中产生,克利强调它受明暗对比的层次与空间的大小因素影响。我们可以将克利的色彩理论恰当的描述为,由处于静止和运动状态的有机整体构成的色彩系统,这一理论开辟了两个新领域即“色彩运动与色彩相对性”。



“我”心灵深处的意念


在克利的绘画与理论中认为作品应从虚无开始,通过具有魔力的线条、色调值、色彩等,最后达到终极神秘的“我”。本能地自我创造生命与自我创造的艺术相融合,最神奇的作品应该展现出“人与宇宙”的联系。克利理论中形成的“我”是他“付出‘在他的创作中放弃自我’的代价”换到的,克利在理论中强调的“我”很多时候保持在无意识的状态中,就像生活中的吃饭一样,但对于克利无意识是一种自然状态,是一个积蓄心理体验的深深的蓄水池,是一个理性以及日常生活的砝码。

“我”是造型艺术的核心


在克利“我”的艺术呈现中预设的通道特征之一是:以时间凝聚获得张力,其实“时间过程离了主题便粉碎,便化为乌有(布雷莱)。”在这个“我”中克利让他的作品展开了独有的旋律。这种旋律没有规则可寻,其实不规则形意味着更大程度的自由,而且丝毫不会破坏规则。



③Paul Klee, Paul Klee on modern art, Translated by Paul Findlay, Faber and Faber ltd, 1966, p.11: “A being who differs from you only in that he is able to master life by the use of his own specific gifts; a being perhaps happier.”
④Paul Klee, Paul Klee on modern art, Translated by Paul Findlay, Faber and Faber ltd, 1966, p.9.
⑥转引自Will Grohmann, Paul Klee, Translated by Norbert Guterman,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p.1.
⑦赫伯特·里德:《现代艺术哲学》,朱伯雄、曹剑译,百家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168页。
⑨H.H.阿纳森:《西方现代艺术史》,邹德侬等译,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256页。
⑩海德格尔:《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页。







作者简介:陈忠强,笔名陈忠村,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当代艺术研究所所长,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在站博士后,安徽省青年美术家协会副主席,chenzhongcun@126.com。上海,201620
〔责任编辑: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