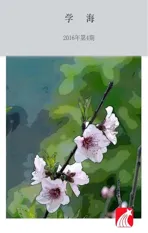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探讨*
——基于对毛泽东自我界定的解析
2016-08-29陈昭启
陈昭启
作者简介:陈昭启,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46
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探讨*
——基于对毛泽东自我界定的解析
陈昭启
内容提要从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得知,1920年夏毛泽东已认定自己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这种自我界定式的话语中,包含了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基本评判标准,暗含着这种标准包括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也透露出了这种标准会随着他的具体革命实践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不断深入而产生相应的变化。这些问题恰恰是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可回避的难题,需要详加考察,并加以严肃阐明。
毛泽东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观自我界定
在1936年与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自我解剖和自我界定,他指出自己在1920年夏天从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转变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由此也产生了诸多疑问。诸如毛泽东缘何认定自己在这一时间段转变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域中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标准分别是什么?这一标准形成的依据和思想渊源何在?这种评判的标准在1920年前后与1936年前后乃至毛泽东思想成熟时期有何不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在研究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观过程当中不可回避的难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讨论历史考察
回顾浩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群,我们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在这一坐标系上的每一个阶段所得出的不同结论,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界定和认识。处于这一发展谱系的毛泽东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对此问题的看法和标准的影响,尤其受列宁的结论的影响较为直接而又深远。
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曾说过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这并不是说他试图从真正意义上否定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要与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教义的、教条主义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区分。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易言之,真正的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视“改变世界”为己任,而不是充当“事后诸葛亮”的角色,进行纯粹的理论思辨和闲暇阶层的爱智活动。当然,这一哲学宣言并不是也不可能彻底否定“解释世界”的重大意义。马克思之所以突出地强调“改变世界”这一命题,其实也是为了反对当时忙碌于“解释世界”的资产阶级理论家及其理论形态。离开从现实出发把握客观规律以“解释世界”这一重要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改变世界就成了无源之水。要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致力于发现和总结深藏于历史进程之潜流的客观规律以全面而深刻地“解释世界”,并以此为基础,力图通过参与活生生的现实实践以“改变世界”。
恩格斯在《致威·桑巴特》中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②因此,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的不是研读和背诵马克思所指出过的具体结论,而是要将其中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加以深刻领悟并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不仅如此,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们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以发展这一理论体系,使之不断趋于完善。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身就极力反对理论权威,而将他们的理论当作教义加以死记硬背、轻易套用、生硬阐发都是与他们的初衷相背离的,因为这种做法无异于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不可怀疑、不可撼动的绝对权威并试图拿此消除其他理论存在的合法性。在他们看来,这甚至比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本身更加可怕。明确否定和质疑马克思主义,质疑反对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双方近乎依照约定激战沙场,是立场鲜明的双方进行的显性争论与斗争,而将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的做法其实质是表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进行隐性斗争。“马克思主义者”们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做着践踏马克思主义的事情,有着极强的、隐匿的破坏力,恩格斯多次强调应杜绝这种做法。
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列宁起初指出:“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所提示的结论,并且彻底地贯彻了这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阶级斗争学说。”④马克思、恩格斯立场鲜明地将自己置身于无产阶级队伍一边,并为这支新生队伍的发展倾注了全部精力。他们一步步揭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深层的经济根源,以此激发无产者的广泛联合进而举行有组织、有计划的运动。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汗牛充栋的文本群中首先总结出了阶级斗争学说,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首先深刻领会这一学说。但是,后来列宁逐渐认识到仅有阶级斗争这单一维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就会流于片面。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仅仅看作阶级斗争理论的做法,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强行肢解和以偏概全,是阉割和歪曲马克思主义。这种做法从本质上而言,仍未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套路和思维框架,因为对于阶级斗争而言,资产阶级也并不完全排斥,他们的阶级地位及相应的利益最初也是通过阶级斗争获取的。因此,仅从阶级斗争的维度对马克思主义加以框定,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理论之间的界限就会变得十分模糊。列宁后来在《国家与革命》中补充强调:“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⑤列宁结合俄国的具体实践,将“何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评判标准概括为了两个重要维度: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明确强调,必须是两者兼有,而非任选其一。当然,列宁对马克思主义者的界定还有发展的空间。他说:“我们并不苛求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者知道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一切具体情况。”⑥这就意味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固守和简单占有原有的结论,而是要借助实践的力量,拨开层层的理论障碍和迷雾,根据新情况得出必要的新结论。
毛泽东的自我界定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回答




再思“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
“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因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本身就极其复杂、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加以回答。但是,以毛泽东的自我界定话语作为解读与思考的“入口”并由此将问题展开,梳理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关于“何为马克思主义者”问题的不同回答,却能够大致地归纳出其中的主要评判标准。



第四,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才能更好地被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代发展变化的步伐保持一致。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分析和解决新问题的实践过程,又为马克思主义生发新的具体理论观点提供了新的实践基础和历史资源。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从归根结底意义上说是由于人类社会永不停息地发生着深刻变化决定的。仅仅套用马克思主义原有的结论,拿具体结论去“强抱”实践的做法,实质上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纵使有内容和形式的深刻变化,却也无法抹去它自身的内在连续性,只不过这种内在连续性通常以一种隐性逻辑结构的形式深嵌于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话语体系中。这里所说的丰富与发展体现为内容和形式上的深刻变革,却不是巴迪欧所指出的那种对马克思主义内在连续性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从基本理论体系开创伊始到苏联的实践论证与发展,再到中国共产党人丰富与发展,始终存在着一条内在的逻辑中轴和历史线索——方法论的继承和延续,使马克思主义在不同国度、不同历史境遇、不同时代所赋予的多样性形式和内容背后隐藏着由历史连续性本身所规定的理论连续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随意拼贴和强行植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并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而是要以方法论意义上的继承和内在的科学逻辑连续性为基础。
①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页。
②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A),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6页。
③中共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84页。
④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8页。
⑤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2页。
⑥中共中央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1页。
⑦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10年,第147页。
⑧金韧、李坚:《关于青年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两个问题》,《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73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2页。












作者简介:陈昭启,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南京,210046
〔责任编辑:吴明〕
* 本文系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国外毛泽东学的历史逻辑及其当代评价”(项目号:15JJD710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