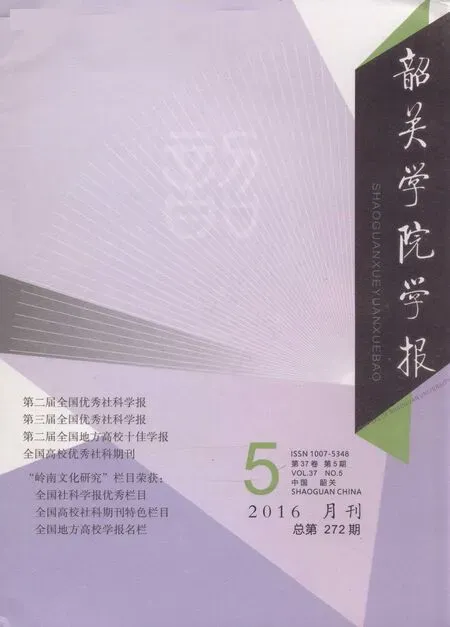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以扩招前后为研究样本
2016-08-22薛亚涛肖雪山
薛亚涛,肖雪山,陈 伟
(1.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540;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广州510303;3.华南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研究——以扩招前后为研究样本
薛亚涛1,肖雪山2,陈伟3
(1.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基础部,广东 广州 510540;2.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广州510303;3.华南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根据崔玉平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基本模型,以1999年高校扩招为界,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96-2001年间的2.4%下降至2002-2011年间的1.36%。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欠平衡、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层次结构和科类结构失衡、师资的质和量双重不足等导致高等教育软实力亟待提高;而外省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入部分地遮蔽了扩招之前广东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
广东省;高等教育;经济增长贡献率;比较研究
经济先行、高等教育随后紧跟是广东省发展的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率先发展且GDP 自1989年起跃居全国第一并保持至今,但广东高等教育在全国的地位与水平长期以来一直与其经济地位和水平不相称。1990年以来,广东大力发展教育以尽力协调平衡高等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1994年在全国率先提出“教育强省”战略、1999年开始高等教育大众化变革、2004年提出“教育现代化”战略、2013年提出“创强争先建高地”战略等。所有这些“战略”,唯独高等教育大众化战略与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张、外延变化有关,且可定量计算、能够客观表征。为了更为清晰地评价广东高等教育系列发展政策的现实价值,同时也为尝试探索广东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本文拟选择高等教育大众化、高校扩招这个关键事件,运用经典的教育经济学定量计算方法,通过对比计算高校扩招前后广东经济领域的发展状况,审慎研究以下问题:如何估算、如何解释以及如何提高广东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一、理论基础与基本模型
(一)理论基础
舒尔茨在计算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之前,假设经济增长主要是土地、劳动力、资本等三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他在分析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时发现,在经济增长总量中,扣除土地、资本和劳动量投入带来的增量后,还有710亿美元的剩余。对于这些“余额”,他的研究指出是由于劳动力质量或素质的提高而取得的。
丹尼森认为,经济增长的“余额”部分不应该全部归功于教育的贡献,其中仅有3/5是教育的贡献,另外2/5是其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主要有: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的合理和适度;知识进步及其在生产中的作用。根据他的因素分析法,教育程度的提高对美国1929-1957年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是23%[2]。目前世界上仍广泛采用丹尼森的因素计算法。
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和数学家柯布于1920年提出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公式为:Y=AKαLβ。其中,Y代表产出,K代表物质资本投入,L代表人力资本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α代表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后来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为了计算教育在产出量增长中的作用大小,将上述公式调整为:Y=AKαLβT。T为技术变量,包括教育在内。这样,当资本投入量和劳动投入量的变动被认为不能完全说明产出量变动的原因时,可在技术进步和教育因素中进一步寻找原因。
苏联学者斯特鲁米林、科马洛夫和科斯塔年等,主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计算教育对社会经济效益的贡献率[3]。他们认为,社会产品及其增长是由具有不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劳动创造的,而不同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又是与他们受教育程度的不同相联系的;复杂劳动等于加倍的简单劳动,两者在量上是可以换算的。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罗默建立了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增长模型[4]。自此,人们开始把技术进步、政府支出、研究与开发和人力资本 (包括教育投入)当作内生变量,内生化经济增长理论为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基础。
学者们用于表示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尺度有所不同,其中计算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比例,即计算由教育投入所带来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ye)占国民产值总增长速度(y)的比例(ye/y),是比较受欢迎的方法。丹尼森等美国学者即为明证。
丹尼森首先把经济增长因素分为生产要素投入量和生产要素生产率两大类。前者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劳动力在数量上的增加和质量上的提高(包括教育水平提高);二是资本在数量上的增加。生产要素生产率包括三个方面:(1)资源配置的改善;(2)规模的节约;(3)知识的进展在生产中的作用。
关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他是这样计算的:根据1950年美国人口普查资料,把25岁以上的男性工人按教育年限分组的货币收入数字(不同受教育年限的工资差别)加以分类,把受过8年学校教育的工人的收入作为基准,定位100%,再用其他受教育年限工人的收入和基准数相比,算出其相对的百分比。如中等教育1至3年级劳动者的平均工资,相对于初等教育8年级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就是115。依次,便得到中等教育4年级为140,高等教育1-3年级为165,高等教育4年为235;初等教育5-7年为80,1-4年为65,未受教育者为50。但是他认为,受不同教育劳动力的工资差别并不完全是由教育的不同造成的;因此,只把其中的3/5当作是教育的作用。于是他便将实际工资差别的百分比乘以3/5进行调整。再把调整后的数字按教育年限各组在劳动力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加以平均,推算出某年的各级教育程度平均收入系数。有了基期和报告期的平均教育程度收入系数,便可以找出教育水平提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丹尼森得到的数字是0.93%。根据1929-1957年的资料,丹尼森算出在总投入量中的比例为73%,因为教育因素属于劳动投入量,国民收入年增长率中,由于提高教育水平的作用应为0.93% ×73%=0.67%。教育水平提高因素在国民收入增长率中的百分比则应是:
0.67/2.93×100%=23%
丹尼森对其他因素也一一作了计算,最后总加起来还有0.59得不到解释,他称之为剩余因素,把它归为知识进展和它在生产上应用的作用;而知识的进展和应用,丹尼森认为也有3/5是教育的作用。因此,0.59×(3/5)=0.35,再加上因教育水平提高的0.6则为1.02%,占国民收入年增长率2.93%的35%。也就是说,这时期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额的贡献为35%。
(二)基本模型
以上研究成果,几乎都是探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方法,但没有专门关注并研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学者崔玉平教授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他以丹尼森和麦迪逊(主要对下文所提到的β值进行了计算)等人的计算方法为基础,把高等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率的贡献从原计算方法中分离了出来,使进一步研究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成为可能。
本文采用崔玉平教授计算中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基本模型[5]。具体如下:
第一步,计算全期(即“报告期”至“基期”)年平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e;
第二步,计算全期年均高等教育指数增长率占全期年均教育综合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
第三步,计算全期GDP年均增长率y;
第四步,通过回归分析,求出产出对教育投入的弹性系数β,并计算出教育所致的GDP增长率,然后,再计算整个教育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Re,公式为:Re=βe/y;
第五步,计算高等教育对产出增长率的贡献率Rh,公式为:Rh=Eh·Re。
β系数的确定方法采用时间序列回归法。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基础上,构造回归模型∶1nY=1nA+ A1nK+B1nL,分别求出α和β的数值。本文采用麦迪逊的β系数值,即β=0.7,也就是认为劳动对产出的弹性为0.7。具体而言,劳动投入每增加1%,产出增加量为0.7%。在我国,实际β值可能低于0.7。
二、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估算
广东省自1999年开始正式扩招,扩招之后的首批高职高专毕业生2002年进入工作岗位,故可将2001年确定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界限;扩招之后可查阅相关资料至2001年,扩招之前的相关研究资料,仅能以1996年为最早年限,因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里并无1996年之前的在业人口受教育程度数据。据此,有关广东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比较研究,可划分成1996-2001年、2002-2011年两个时段。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时段的划分,以扩招的首批毕业生就业时间为界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根据是否可以查阅相关研究资料来确定时段的长短,存在一定的缺陷。另外,2008年前后,由于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广东经济倍受影响。这些影响可能对本文的计算结果产生间接干扰。
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年份的数据,计算出1996-2001年间的相关数据,见表1。

表1广东省1996-2011年各年间经过教育综合指数调整的劳动总量①资料来源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1997-2012)(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年版);参见崔玉平《区域高等教育的经济学分析》(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1版,第154页)
表2中,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根据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计算出地区生产总值指数。

表2广东省1996-2011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DP)①资料来源同“表1”。
估算1996-2001年间以及2002-2011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1.计算起止年间人均教育综合指数平均年增长率e
其中E1、E0分别为起、止年的人均教育综合指数;n为终止年与起始年之间的间隔年限,1996-2001年的间隔为n=5,有:

2002-2011年的间隔为n=9,有:

2.计算高等教育占年均总教育指数增长率的百分比
(1)排除高等教育后的教育指数
1996年:5.562+1.226×1.968=7.975;
2001年:5.788+1.226×2.556=8.922;
2002年:5.85+1.226×2.868=9.366;
(2)排除高等教育后的教育指数年增长率
1996-2001年的教育指数年增长率:

2002-2011年的教育指数年均增长率为:

(3)高等教育占总教育指数年均增长率的百分比
1996-2001年:
Eh1=[(2.64-2.27)/2.64]×100%=14.02%
2002-2011年:
Eh2=[(1.43-1.18)/1.43]×100%=17.48%
纳入标准:所有患者均符合西医慢性萎缩性胃炎诊断,同时属于中医辨证标准中脾胃虚寒型,且临床资料完整、准确;无合并严重心脏、肝、肾等重要器官疾病者;无严重感染者。排除标准:(1)不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标准者;(2)处于妊娠期及哺乳期妇女;(3)严重的精神障碍情况;(4)合并有严重心、肺等重要器官严重疾病者。
3.计算广东省年经济增长率y
用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表征经济增长。以本国货币不变价格计算的增长率习惯上称之为实际增长率。据表2,广东以1978年为不变价格计算出1996-2011年可比价格GDP,1996年为2 131.33亿元,记为Z0;2001年为3 561.26亿元,记为Z1;2002年为4 001.91亿元,记为Z2;2011年为11 891.61亿元,记为Z3;采用几何平均法,得到1996-2001年广东省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

2002-2011年间广东省GDP实际年平均增长率为:

4.计算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率的贡献Re
根据教育对经济增长率贡献的表达式Re=βe/y,将β=0.7,e1=2.64%,e2=1.43%
Y1=10.81%,Y2=12.86%代入,有∶1996-2001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
Re1=(βe1/y1)·100%=(0.7×0.0264/0.1081)·100%
=17.10%
2002-2011年间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率
Re2=(βe2/y2)·100%=(0.7×0.0143/0.1286)·100%
=7.78%
5.估算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计算公式Rh=Eh·Re,将Eh1,Eh2,Re1,Re2代入得:
1996-2001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Rh1=Eh1·Re1=0.1402×0.1710×100%=2.40%
2002-2011年间广东省高等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Rh2=Eh2·Re2=0.1748×0.0778×100%=1.36%
以同样的方法,选取东部地区的山东、上海、江苏、浙江、辽宁,中部地区的河南、安徽、湖南和江西,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陕西,估算出其高等教育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高等教育发达地区的北京市、湖北省分别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和缺乏数据,这里暂时未能计算出其结果),见表3。

表3国内重要省份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①资料来源同“表1”。 (单位:%)
三、结果分析
(一)计算结果
1.全国总体情况呈现出正相关关系。从全国总体来看,扩招之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此前的2.11%增长至2.93%。这说明,我国自1999年以来实行的高校扩招政策确实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推动作用。
2.沿海发达省份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许多省份,主要是东部沿海地区省份,通过高等教育扩招,提高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其中,上海从1.53%提高到6.49%,辽宁从0.97%提高到2.43%,浙江从1.06%提高到3.06%,江苏从0.78%提高到3.01%,湖南从1.77%提高到2.86%,陕西从0.86%提高到3.43%。
3.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呈现出负相关关系。中西部省份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扩招之后大多出现了下降。河南从2.37%下降到1.04%,安徽从2.20%下降到2.05%,江西从4.46%下降到1.34%,四川从3.32%下降到1.36%。
4.广东、山东意外地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广东作为沿海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在扩招之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意外地出现了下降。1996-2001年,广东省高等教育对广东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40%,2002-2011年下降为1.36%。与广东情况类似的是山东。山东同样是沿海地区,且近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速度极快,但其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从3.35%下降到1.47%。
(二)广东高校扩招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关系的归因分析
一般的规律是,在高等教育和经济尚未达到极高水平、两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出现边际效应之前,高等教育越发达,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会越高。这个规律,得到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省份的证实。但问题在于,广东作为经济发达但尚未极度发达、高等教育发展但未产生边际效应的省份,本应与其他东部省份一样,形成“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的格局,但事与愿违。对此悖论,拟以辽宁、浙江、上海、江苏四省为比较对象,尝试进行归因分析。
1.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欠平衡
高等教育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是保持并提升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的关键。但是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近十多年间,一直存在着不平衡状况。
首先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速度不平衡。始于1999年的高校扩招,让广东的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2002年,全省高等教育共招生31.04万人,在校生规模达到79.16万人,毛入学率达到15.3%,跨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门槛。2010年,广东高校在校生规模突破了200万大关,达到205万人,是1998年的6倍;从1998年到2010年的12年间,年均增长16.1%。不过,同期的广东省GDP年均增长15.08%,扣除物价因素、按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年均增长则更低,仅为12.5%。由此可见,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已经高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见图1。

图1广东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和高等教育在校生数增速对比
由于扩招之前的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于经济发展,因此广东高校扩招,在一定程度上可算是一种补偿性增长。但问题在于,广东高校扩招之后,在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尚未得到妥善解决之前,先是遇上广东省的“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等“双转移”战略,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然后又遇上2008年前后的美国次贷危机、世界金融风暴对广东出口经济的影响。广东经济本身遭遇挑战,进而影响到广东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成果的消化。
其次是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不平衡。1989年起GDP就位居全国第一的广东,社会发展也相对较快,其中珠三角地区已经逐渐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达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现代化”水平。但是广东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并没有因为增速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而得到极大提高,也没有达到满足广东社会发展需求的程度。目前,衡量一个区域高等教育程度高低、反映区域内高等教育人才密度大小的重要指标就是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比较研究发现,上海市是五省区中每十万人口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最高的地区,2012年达到了3 481人;辽宁紧随其后,为2 811人;江苏、浙江分别为2 786人、2 288人;广东省屈居末位,仅为2 082人。
日本学者金子元久认为,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过剩会浪费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加剧社会矛盾,导致生产成本上升及生产力下降,同时也影响着高等教育对地区经济增长率的提高[6]。
2.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尚待优化
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的解释,结构决定功能,功能的强化依赖于结构的优化。提高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以看作为广东高等教育功能的强化,其可供选择的道路只能是结构的优化。数据分析表明,广东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尚待优化。
首先是层次结构尚待优化。在广东,本科生的占比一直居高不下。其中仅2001-2005年专科生占比短暂超过本科生,2006年起本科生占比再次超过专科生。截止到2011年,广东研、本、专比例为4.8∶52.5∶42.7,见图2。

图2 广东省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变化情况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应该是金字塔形[5],即专科生处于塔基,占比最大,他们在一线岗位成为从事基层工作的劳动者;研究生处于塔尖,占比最小,主要从事顶层设计、研究开发工作。但与此不同的是,目前广东的情况是中间大、两头小的“纺锤形”,突出的问题是本科生占比过高。这就可能造成两种结果∶一是由于本科生的职业期望较高,他们会在就业不理想的情况下选择深造,继续攻读研究生。但可以预见的是,尝试通过提升学历层次来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做法,可能会进一步加剧过度教育的恶性竞争,进一步恶化良性就业环境。而且,这种由于本科生就业问题而被动扩大的研究生教育,会盲目扩大学术型人才的占比。尽管研究生教育已经开始尝试按照学术型、专业学位型等两种方式分类培养,但由于专业学位型人才培养模式尚待探索,研究生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检验。二是高职高专的占比过小,不仅会不利于提升高职高专的社会声誉,而且也难以真正缓解“技工荒”的问题。无论是哪一种结果,都会降低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其次是科类结构尚待优化。目前广东尚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亟需大量的工科类人才。但是,在广东省高校的在校生中,工科类人才占比不到30%,低于全国工科类在校生的平均比重(37%),也低于国内的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等省份。2010年全国工科专业人才占高等教育学生总数的37%,GDP总量排前五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工科类人才分别占各省高等教育人才总量的29.88%、39.95%、34.22%、35.88%、37%(因为数据缺失,山东和浙江的数据以2008年代替)。可见广东的工科类人才无论是从全国总体来看,还是与其他省份比较,其工科类专门人的在校生数占比都比较低,这与其工业大省、经济大省的地位显得不相匹配,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十分不利,所以为了扭转广东工科人才培养不足的现状,应该采取相应措施来推动工科人才的培养。
3.高等教育的软实力亟待提高
扩招以来,广东高校的在校生数急剧增加,学生培养的配套性支撑条件亟待跟进。随着大学城、新校区在全省范围内的快速建设和投入使用,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硬件条件,以较快的速度基本得到解决。但是,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软件建设仍然面临较大的压力,其中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尤其突出。
首先,生师比不断提高,师资队伍年轻化倾向较明显。2005年,广东高等学校在校生874 684人,专任教师54 257人,生师比为16.1:1;到了2012年,广东高校在校生数为161 683 8人,专任教师数为87 402人,生师比为进一步提高到18.5:1,见图3。

图3 广东省高等学校情况
随着生师比的提高,广东大量新进高校教师,属于刚从高等院校毕业的硕士生、博士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学历高、平均年龄低,教育教学方法欠缺,且由于职称晋升压力较大,“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较为明显。受此影响,高校教育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面临挑战。
比生师比更准确的数据是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数比值,它反映的是高校教师的密集度,密度越大说明该区域高等学校的教师越丰富、教育质量就越有保障。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上海市一直都是教师资源丰富的地区,辽宁次之,2012年两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数与专任教师数比值分别为12.9∶1和15.4:1,江苏、浙江分别为16∶1、17.4∶1,而广东为18.4:1,高校教师的工作量最大。
其次是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与正高级别的专任教师数比值较低。这个比值反映的是区域高等教育教师的质量和水平。教师质量的高低是影响高等教育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其比值越大,表示一定数量的专任教师里具有正高级别的教师数越少。据中国统计年鉴(2013)的数据测算,2008年以来,上海市普通高校专任教师数与正高级别的专任教师数的比值一直最小;2012年,上海的比值为5.9∶1,辽宁次之,比值为7.3∶1,浙江再次之,为7.5∶1,广东为8.5∶1(但是江苏比广东高,为8.8∶1)。
4.外省人力资源的大量流入部分地掩盖了扩招之前广东高等教育发展不足的问题
由于改革开放较早、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体制相对灵活、各方面的机会较多、待遇较高,广东历来是全国的人才洼地,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吸引了大量的毕业生前来就业、创业,并不存在“因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所以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状况良好”的逻辑。应该明确的是,一方面,由于外省人才向广东的流动,弥补了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相对不足,也掩盖了广东高等教育发展的诸多问题。
上述诸种原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互为因果,相互影响:对于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欠平衡来说,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过剩既是原因又是表现;高等教育的结构性过剩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的不协调又致使广东对外来人员严重依赖,让广东出现了外来人力资源补充现象;外来人力资源的补充让广东忽视了对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的调整、优化和配置,使广东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进而延续了结构性过剩和不协调的周期。结构性过剩、不协调以及外来人力资源补充这三大原因互为因果,循环更替,共同导致了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升反降。
总之,根据经典的计算方法,扩招之后广东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增反降的结论是确实成立的,但如何针对这个问题、紧扣诱发问题产生的诸种原因进行总体改革和有效发展,有待继续开展研究。
[1]西奥多.W.舒尔茨.教育的经济价值[M].曹延亭,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2]武毅英.高等教育经济学导论[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4.
[3]科斯塔年.教育经济学的对象与方法[M].丁酉成,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4]孙芳.浅析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内生化历程[J].北方经济,2009(7):21-22.
[5]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1):31-37.
[6]金子元久.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学[M].刘文君,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0.
Study on Guangdong'Higher Education to Contribution Rate of Economic Growth——A Research Sample before and after Enrollment Expansion
XUE Ya-tao1,XIAO Xue-shan2,CHEN Wei3
(1.Department of Basic,Vocational College of Dongzhou,Guangzhou 510540;2.The Journal Editorial Office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510303;3.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Vocational Education,Guangzhou 510631,Guangdong,China)
Calculation Prof.Spanned basic model Chinese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Rate According to college enrollment in 1999 for the sector,the economic growth rate since 1996,Guangdong Higher unexpectedly-Down by 2.4%in 2001 to between 2002-2011 1.36%-year period.Analysis found that the reasons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balanced,hierarchy and disciplin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of internal imbalances,teacher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higher education due to insufficient double soft power needs to be improved,etc;and Human provinces massive inflow of resources is partially masked before enrollment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higher education.
Guangdong province;higher education;contribution rate;a comparative study
G40-054;G640
A
1007-5348(2016)05-0112-08
2016-04-2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基于社会转型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广东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研究”(GD13CJY05);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委托研究项目“广东高校分类发展及其对高职教育发展模式创新的影响研究”(TJW2013002)
薛亚涛(1986-),男,河南固始人,广州东华职业学院基础部教师,硕士;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理论。
(责任编辑:廖铭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