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水城出土《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探微
2016-08-10赵阳
赵 阳
黑水城出土《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探微
赵阳
摘要《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刊有题名为《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写本文献一件,编号TK252号。在各家针对后晋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的研究论著中鲜有提及此本。在对黑城本《随函录》的考证过程中可以看出,其版本并非简单抄录原本,而是信徒在参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过程中,以原本《随函录》为参照,自行增订摘抄之物。而黑城藏本仅存《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部分的现象,则与西夏当时的佛教背景相契合,此种背景亦是受到辽代佛教的影响。
关键词《可洪音义》西夏佛教辽代佛教华严宗
佛经音义作为解释佛典字词读音和意义的训诂学作品,自魏晋末期肇始,历唐五代兴盛,而没落于宋元之后。其中较为著名的有玄应音义、慧琳音义、希麟音义等等。这类作品不仅反映了佛教在彼时传播发展的状况,更保留了当时的语言、艺术、哲学以及文化交往等各方面的信息,从语言学、文献学及传统文化等角度讲,佛经音义类作品有着极高的价值。
后晋汉中沙门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又称《可洪音义》,后文简称《随函录》)作为佛经诸家音义之一,其“规模巨大,注释简要精当,可谓后出转精,不仅训释了许多以前没有训释的佛经文字,而且纠正了诸家音义在文字考释上的不少谬误,同时还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当时所见的写本佛经文字。”*郑贤章:《〈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研究》,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页。但也因其体例单一,且俗字众多,未得后世学者重视,自宋元后便逐渐亡佚。*谭翠:《〈可洪音义〉宋元时代流传考——以〈碛砂藏〉随函音义为中心》,《中国典籍与文化》,2009年第3期。今仅于《高丽大藏经》中存有全本,另于敦煌遗书中存有部分写本残卷,且有证据表明,《碛砂版大藏经》中部分条目亦引自《随函录》。《俄藏黑水城文献》TK252号文献,编者定名《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在众多关于《可洪音义》的研究论著中,都未曾提及此版本。且于各《随函录》之版本中,黑水城本在俗字、注音以及版本方面都具有其独特的价值,本文据以考之,并就教于方家。
一、黑水城本《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卷貌及特点
《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载于《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四册中。虽刊布已久,却少人问津。据《俄藏黑水城文献·叙录》载:“TK252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宋写本。蝴蝶装。白麻纸。共4个半页。纸幅高16.9 cm,半页宽13.2 cm。字心高12.9 cm,半页宽11.5 cm,天头2.5 cm,地脚1.8 cm。每半页7行,行字数不一。大字下双行小字注直音或反切音。四周单边。楷书,墨色浓。首尾缺。中有题:第七十七卷,第七十八卷。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的语音注释。”*孟列夫、蒋维崧、白滨: 《俄藏黑水城文献·叙录》,《俄藏黑水城文献》(第六册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1页。黑城本《随函录》为手抄本,字迹尚可称之工整,有若干俗字,起于“唱缚”,终于“渗”,共有音义78条。而在《高丽大藏经》所载全本中,由“唱缚”至“渗”例,共有音义85条,且二者相较,所列音义条目也不尽相同。现将黑城本《随函录》原文迻录于下,以明其状貌。
(前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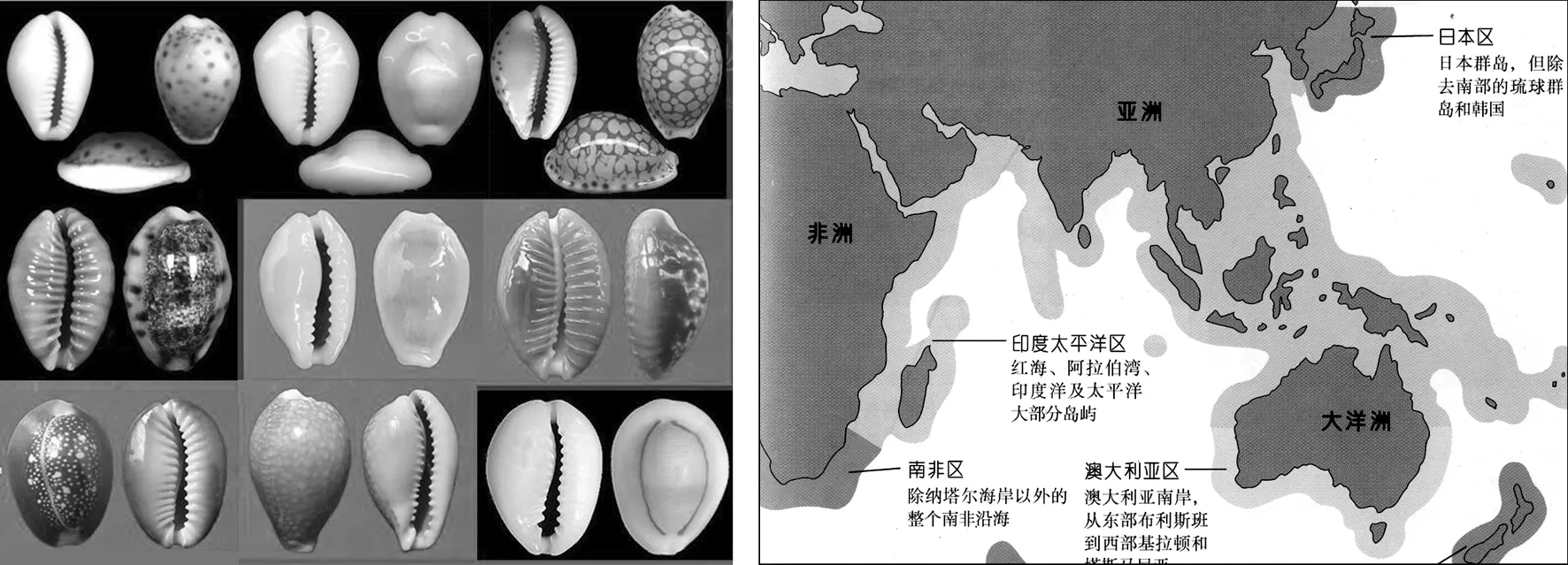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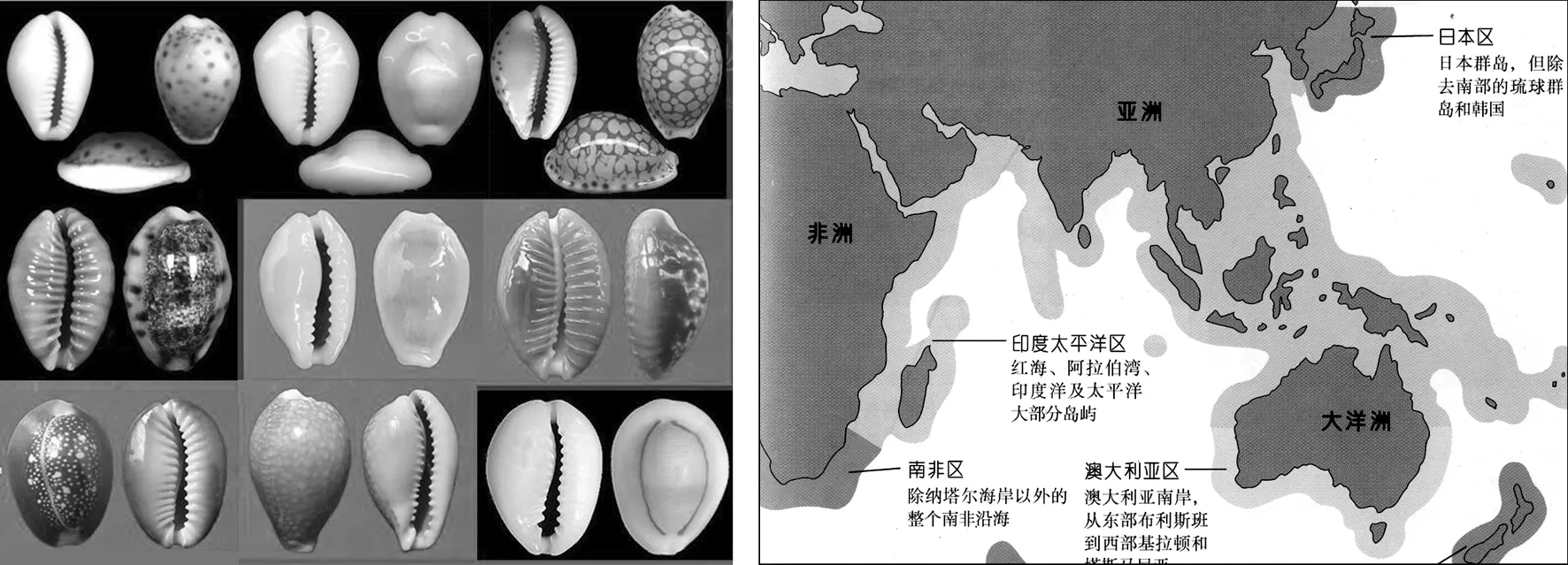
唱侘恥加反音訍譇 / 咸綜 音錝祖宗切理經也謂整理經偉之都本也/
唱攘下音禳輕呼 婆咀 音坦/多達反擯 音殯儐第七十七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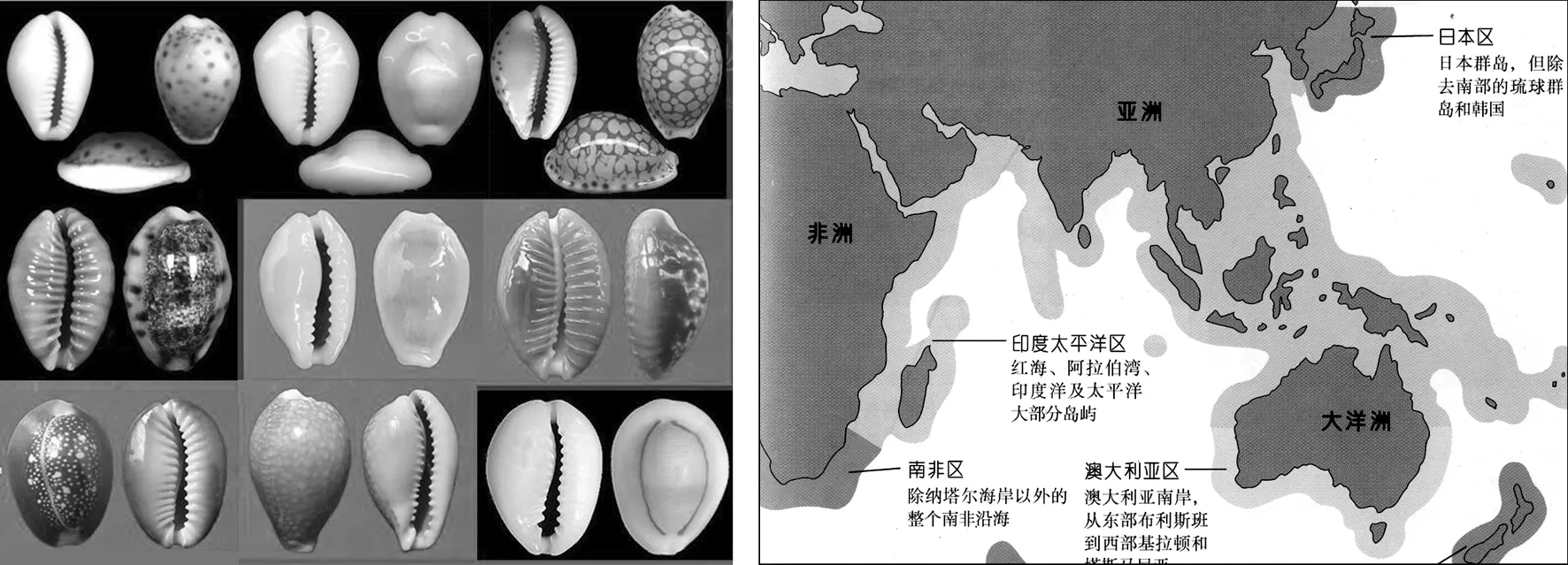
第七十八卷 /


鋸 音據斧 音府鉗鑷 上音/鈐下銸鉤鉺上句下刵貿 音茂
貓貍 上猫下狸鼠/音黍暑音相似 礠 音瓷慈耆 音蓍其音相似
楔 音屑/□音相似繕 音善饍疱 音胞技藝 上妓下蓺義/音相似
(后缺)
注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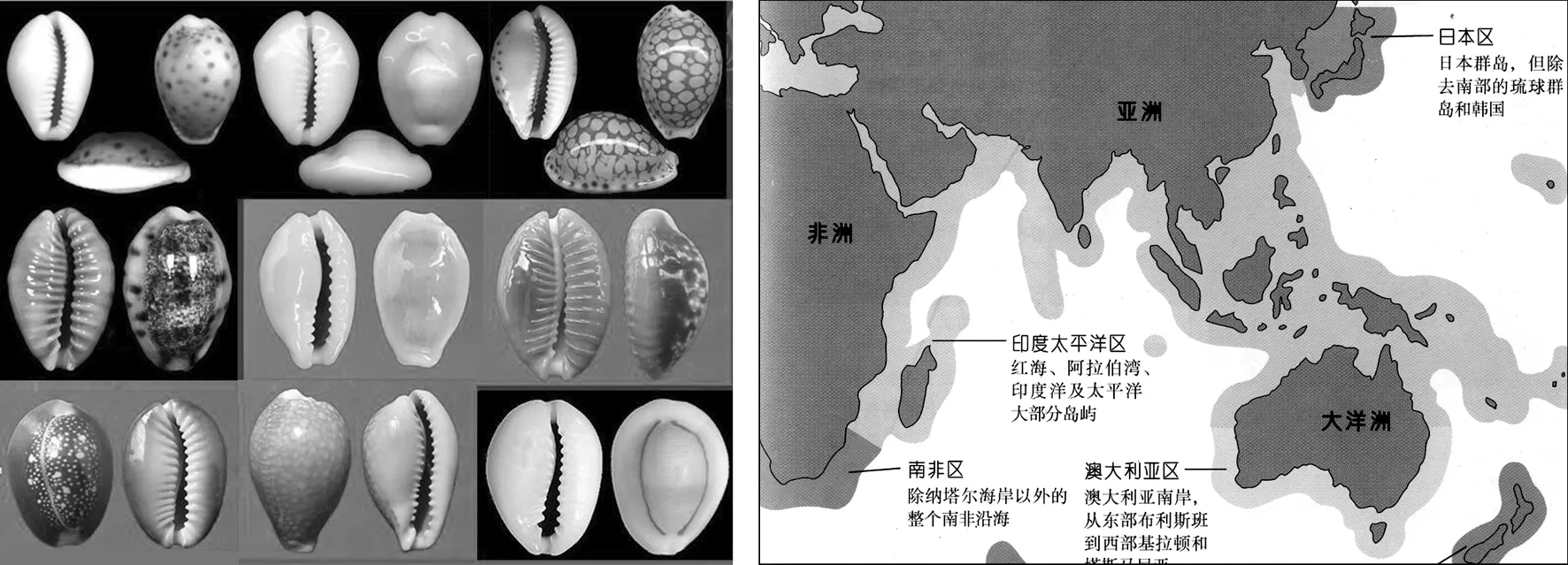












《高丽大藏经》所载《随函录》原就以俗字众多为其特点,但黑城本《随函录》的七十八条音义中仅见于黑城本而不见于高丽本的俗字却多达十一例,其中三例可查于各类正俗字典,八例却无从查找,且多为形近致误,可见黑城本更加充满“俗”气。除俗字众多外,黑城本《随函录》尚有一些别字,如“唱义,楚我反”,义字本应为“叉”;“唱挐,好可反”,挐字应为“拏”,好字应为“妳”;“婆咀,音坦/多达反”,咀字应为“呾”;“旃荼 上栴下茶”,误将“荼”识为“茶”。
由上可以看出,黑城本《随函录》在卷面书写上的特点是俗、别混行,且多为各类字书未见之字。从这种文字书写上的随意性与卷面的工整度来看,此件文献的抄写者文化水平应该有限,不似为高僧大德的精心之作,反而更像是布衣居士或底层沙弥在诵读经典时的随手摘抄。
二、黑城本《随函录》与高丽本《随函录》的结构差异与版本考证
黑城本《随函录》虽篇幅不多,但也独具特色。除上文所述的俗字、别字众多这一卷貌特点外,经参照《大方广佛华严经》八十卷本的相关内容,且与高丽本《随函录》比较后,发现二者差别甚多,并非是同一系统下的版本。下文依例析之。
(一)音义条目的差异
黑城本《随函录》残存佛经音义78条,高丽本《随函录》在相同范围内,有音义85条,数量上相差虽然不多,但在可见的条目中,仅有56例条目是对同一字或词语进行注音解释,黑城本其余22条皆未出现在高丽本中,如“唱也”、“唱娑”、“ 摈”、“猫狸”等条。反之,高丽本中也有部分音义条目未载于黑城本,如“渔人 上牛余反”(《华严经》:“悉入其中而济拔,此善渔人之住处。”)、“金翅 音施鸟翼也亦作翄”(《华严经》:“从诸有海而拔出,此金翅王之住处。”)、“曩于 上奴朗反”(《华严经》:“此长者子,曩于福城受文殊教,展转南行求善知识……”)。
不仅如此,相比于高丽本《随函录》,黑城本音义条目还存在顺序上的混乱与对象选择上的删减。
黑城本“咸综”、“癫痫”、“呪诅”三条,对应的华严经经文为“殊方异艺,咸综无遗;……有诸众生,鬼魅所持,怨憎呪诅,恶星变怪,死尸奔逐,癫痫、羸瘦,种种诸疾,咸能救之,使得痊愈。”高丽本音义的顺序则为“咸综”、“鬼鬽”、“呪诅”、“癫痫”;又如“撤”、“鞅”二条,对应经文为“断贪鞅,解见缚,坏想宅,绝迷道,摧慢幢,拔惑箭,撤睡盖。”高丽本顺序为“贪鞅”“撤睡”。另尚有几处例证,不再赘举。
另外,黑城本“峙”“佣”“艥”“炷”“汩”等条目,在高丽本中分别作“齐峙”“佣作”“舟艥”“信炷”“漂汩”,皆为将注音对象删减,只选择所注之字。此种删减现象,在黑城本中随处可见。
(二)注音方式的差异
二者虽都以《大方广佛华严经》为注音对象,但在注音方式上却有很大不同,综合来看,黑城本侧重实用性与简洁性,而高丽本则侧重规范性,表现在注音方式上则是前者多直音,后者多反切。黑水城所见78条音义中,直音注音的出现多达64例,反观高丽本《随函录》相关的85条音义中,直音仅有18例,二者相较,多寡立判。就注音方式来讲,直音虽不如反切那般精准,却也具有一目了然、操作简便等特点,从黑城本为手写的特点来说,直音法也更加便捷。不仅是直音法数量上占据多数,黑城本的注音方式还具另外两个特点。一是在部分注音中,直音与反切并存。如“曷攞 音罗郎可切”、“鞅 音怏于两反”、“娑 苏舸反音鏁”等条,既有直音又现反切。二是在注音中,不仅注出读音,且标明音调。如“多 上声”、“ 诃婆诃婆字并上声呼之”、“唱攘 下音禳轻呼”等条。这两种现象在高丽本中是未曾见到的。
(三)反切字使用的差异
在黑城本《随函录》的音义中,虽然反切注音不是主流,但在为数不多的反切注音中,又有反切字使用上的独特之处。如“唱缚 无可反网声相近”,高丽本作“伏可反”,中古“无”为微母虞韵,“伏”为奉母尤韵;“唱哆 都我反”,高丽本作“都可反”,中古“我”为疑母歌韵,“可”为溪母歌韵;“唱他 他可反之上声”,高丽本作“徒可反”,中古“他”为透母歌韵,“徒”为定母模韵,这些差别反映出了黑城本抄写者自身语音系统的状貌。反切法在黑城本的使用中,另一个特点是部分反切注音并非为作者的自身创作,而是看似偷懒的直接抄袭《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经文。如“唱哆 都我反”、 “唱也 以可反”、 “唱娑 苏我反”等条目,所对应《华严经》原文为:“唱哆都我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圆满光。唱也以可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差别积聚。……唱娑苏我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名降霔大雨。”经统计,黑城本所列条目中,与佛经原文中所现注音相同的例子共有15条,而高丽本所涉及内容中仅见4例。且高丽本的音义中,还有不少对《华严经》原文中的反切字进行注音的现象,如《华严经》中,“唱奢尸苛切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高丽本注:“尸苛 户可反”;唱娑蘓纥切多上声呼字时,入般若波罗蜜门……”,高丽本注:“蘓纥 恨没反”。这样的现象在黑城本中仅见一例,并非主流。
(四)缺乏对字体的校勘与定形
五代时期,读书识字的人逐渐增多,但水平参差不齐,因此造成了正俗混用、俗字大行的情况,这种情况也反映在经书的抄写过程中,因此当时各路佛教音义作品盛行。《随函录》作者可洪即感于佛经用字混乱不堪,讹误随处可见,对佛经的阅读带来了很大困难与障碍,由此集各家音义之所长,撰写《随函录》。在可洪撰写的过程中,对字体的校勘与定形下了颇多功夫,也有了一套较为完备的勘定系统以及校勘的相关术语,如“正作”、“亦作”、“或作”、“俗、俗作”、“非”等等*关于可洪《随函录》对字形勘定的术语整理研究,可参见韩小荆《可洪音义研究》,巴蜀书社,2009年。。但于黑城本《随函录》的78条音义中,仅有“呪詛”、“捃”2处字形勘定术语“亦作”,在原本中出现比例最多的“正作”却无从发现。这虽然也有黑城本篇幅过小的原因,但更明显的情况是,黑城手抄本《随函录》对字形勘定这一重要任务似乎并无太大兴趣,不仅对很多别字、讹字并无注解,且其本身就存在很多于各类字书中查不到的俗字,这进一步说明了黑城本抄写者的抄写目的并非为纠正经文中的俗字、讹字等,且大量条目只有注音并无释义,证明其目的似乎仅在于为阅读发音之便利,而非为参透经文而进行深入注解。
这类摘抄版本的佛经音义并非黑水城所独有,除在敦煌写本如S.5508号、P.3971号中有所体现外,更为相似的版本是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汉文佛教典籍》(吐鲁番学研究丛书甲种本之一)中编号为80TB1∶002a的佛经残片,于亭先生将其拟名为“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第十二卷中阿含经音义抄”, “摘抄的方式,大致上是将多数双字辞目简化为单字辞目,注释中保留切语和俗字异体的字形解说,而删省义训。”*于亭:《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所出小学书残片考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年第4期。其卷貌和书写风格与黑城本高度契合。由此可以得知,在阅读佛经时,为不失原音,不误原义,广大信徒便以做笔记的方式,以经为本,以佛经音义类作品为参照,摘抄一些有助于阅读的音义,不仅可以便于自身的学习,也可和同行相互交流,从而也在客观上推动这类工具书的流传。可洪所撰《随函录》在黑水城、敦煌以及吐鲁番文书中的发现,充分证明该书因其在参修佛经时的便利作用,曾广泛流传于西北地区的佛教信徒中。
关于黑城本《随函录》的版本来源,文献页面并无信息。孟列夫将其定义为宋版写本,但也仅据页面材质判断,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俄)孟列夫著,王克孝译:《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5页。。从书写内容来看,倒也存在为西夏当地写本的可能。如第一条音义“唱缚,无可反网声相近”,“缚”字中古时为全浊奉母,七世纪《切韵》系统拟音尚为b’v,罗常培先生在《唐五代西北方音》中对八、九世纪的拟音也为b’v,至十世纪时送气现象已消失,变为bv。李范文先生在《宋代西北方音》里根据《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记载,拟音为v。而在黑城本中,“无可反”中声母“无”与“网”均为微母字。又如“唱他 他可反之上声”,高丽本作“徒可反”。“徒”为定母模韵,“他”为透母歌韵。据《宋代西北方音》中记载的例证反映,当时的全浊音定母已逐渐清化为透母,而《随函录》中这一例正是定母清化的表现。韵母方面,《宋代西北方音》中歌韵开口一等字共31例,反应出的现象是a韵在宋夏西北方音中已经开始变化为o韵。《随函录》中第二条“唱哆 都我反”,高丽本中记为“都可反”。“哆”为歌韵开口一等字,“我”字本为a韵,但在《掌中珠》中,以“我”记音的西夏字凡五例,李先生对其中三字的韵尾拟音为o,可见西夏时汉文“我”字的发音已逐步向o韵靠拢。而用“可”字记音的西夏文韵尾拟音仍为a韵。又如“铦 音铁繊”一条,“铦”为透母添韵,“铁”为透母屑韵。高本汉、王力等先生对“铦”的拟音均为thiem,而在《宋代西北方音》中对“铁”注音的西夏字拟音为thie,韵尾-m已经脱落。李先生在书中说道:“从我们引用的夏、汉、藏三种语言的资料来看,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鼻韵尾显然处在消失阶段。”*李范文:《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以“铁”注“铦”所反映的正是这种鼻韵尾消失的情况。
当然高丽本与黑城本在注音上也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们并不能就以上文这些例证断言黑城本《随函录》必定是西夏本地人所抄,毕竟可洪创作《随函录》时已是五代,且其本为秦人,难免其在撰写时就带有五代时西北方音的痕迹。但就黑城本所反映的信息来看,就算它是宋人甚至辽人所抄,其作者至少也是生活在西夏附近受到西夏语音习惯影响的人。
三、黑城本《随函录》与西夏佛教发展的关系
可洪所撰《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全本共30卷。在敦煌本《随函录》残存的几个卷子中,其内容出现了P.2948《莲华面经》、《诸法无行经》,P.3971《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等音义,这种多样性,虽有卷数多于黑城本之因,然遍检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黑城本《随函录》却仅存《大方广佛华严经》之音义部分。这种现象,也许需要从西夏与辽代佛教的关系进行分析。
从时间上讲,辽代佛教与宋一样上承晚唐五代,但由于统治阶层的喜好与支持,辽代佛教更加注重义学与世俗并行,充分保留了唐五代的佛教特点。正因如此,教义繁冗的华严宗在辽代得以成为主流。据《辽史》记载,道宗耶律洪基对佛教极为痴迷,尤其推崇华严:咸雍四年二月癸丑,颁行《御制华严经赞》;咸雍八年秋七月丁未,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因为上层的推动,华严宗在辽代的发展不仅表现为统治者对华严义理的重视,更表现为僧众对研习华严义理的热情,如鲜演、法悟等,都是精修华严的法师,乃至修持密教的觉苑、道硕,也都是精通华严且倡导密教与华严的融合。而同时期的宋代佛教,不仅义学没落,且趋于平民化与世俗化的禅宗与净土宗在中土广为盛行,造成了唐五代佛教传统在中原的凋零,反而于辽的土地上得到了传承。
再说西夏佛教的发展。西夏立国之前就与辽互为盟友,且为姻亲,政治关系十分密切,这就为西夏地区与辽代的文化交流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西夏历代统治者都推崇佛教,国内释学大盛,从而辽代繁盛的佛教文化与西夏佛教的交流就变得顺理成章。西夏仁孝期间,佛经翻译工程已有大量成果,所以校勘事业为此时重任。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记载:“后奉护城帝敕,与南北经重校,令国土盛。”*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2页。西夏称辽为“北朝”,因此其中的“北经”当为辽代刻印的“契丹藏”。辽代佛教华严学与密教并行,与华严密切相关的《释摩诃衍论》在辽的影响也颇为巨大,不仅道宗耶律洪基“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第一并序》,《卍续藏经》第72册,第831页。,且法悟也因上命,结合华严为《释摩诃衍论》作注。黑水城出土TK79、TK80两件文献,即为法悟《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卷二的内容,可为辽代佛教与西夏交流的印证。
对于西夏佛教的特质,索罗宁*关于索罗宁先生对于西夏佛教特点的研究,可参见《西夏佛教的“真心”思想》(《西夏学》第5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3-172页)、《辽与西夏之禅宗关系:以黑水城〈解行照心图〉为例》(《辽金元佛教研究》(上),大象出版社,2012年,第72-85页)两篇论著。先生认为,北宋禅宗及天台宗文献鲜见于西夏佛教文献之中,而以清凉澄观(738-839)和圭峰宗密(760-841)为代表的所谓“华严禅”传统文献却屡见不绝。“就西夏文禅宗文献的内容而言,可以说典型的禅宗文献比较少,主要的部分则是以‘真心’或‘一心’为主的华严禅思想。”史金波先生在《西夏佛教史略》一书中也提到,西夏曾将汉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旧译、新译、后译本全部译为西夏文。不仅如此,辽代许多华严高僧的论著都在西夏得以发现。如有TK134《立志铭心诫》、A26《无上圆宗性海解脱三制律》、A6v《究竟一乘圆通心要》等,俱为辽代高僧通理恒策大师(1049-1099)之著作。上京开龙寺圆通悟理大师鲜演所著《华严经玄谈决择记》也在黑水城地区发现了西夏译本*孙伯君:《鲜演大师〈华严经玄谈决择记〉的西夏文译本》,《西夏研究》2013年,第27-34页。。由此可以看出,辽代佛学以“华严为业”的主旋律被西夏佛教很好地吸收进来,而西夏佛教发展的中后期注重密宗的现象,或许也不仅仅是与吐蕃、回鹘交流的结果,辽代佛教显密融合的特征应该也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辽代佛教显密融合的情况,可参考魏道儒《辽代佛教基本情况和特点》一文,载于《佛学研究》2008年第1期。。因此可以说,西夏佛教的形成之初,除自身与宋之交流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受到辽代佛教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随函录》所残留的内容仅有《大方广佛华严经》之音义应该也是情理之中。虽然残页所记载的内容并不多,但《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在西夏曾经有过流传则已是不刊之论,或许可以蠡测是因西夏佛教自身发展的特点,当地佛教信徒在选用或是摘抄过程中,产生了佛教宗派的分明与侧重,因此仅存了《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部分,而不见哪怕只是残片的其它卷帙。
学界早期对于西夏佛教的认识,大都倾向于与中原赵宋文化交流频繁,并且认为其与敦煌佛教关系密切,但通过对黑水城文献的分析可以看出,西夏佛教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似乎并不是很密切,包括西夏邦内密宗的流行,都显示出其与辽代佛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黑城本《随函录》尽管只是残件,但所包含的信息却很丰富,比如俗字的众多,可以与敦煌俗字进行比较研究;比如它书写形式上的简易性与直观性,也代表着西夏当时民间佛教的发展状貌以及与上层佛教的差异性。总之,黑城本《随函录》的出现,为进一步研究西夏佛教的特点与系统提供了价值颇高的材料。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New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Glossaries of Buddhist Sutras unearthed from Khara-Khoto
Zhao Yang
Abstract:There is a manuscript named the New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Glossaries of Buddhist Sutras in the book of Khara-Khoto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Russia, which was numbered TK252. There are many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book of the New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Glossaries of Buddhist Sutras which had been written by Ke Hong, who lived in the Later Jin Dynasty (936-947), but there are very few people mentioned the edition which was found in Khara-Khoto. The research of the New Collected Record of the Glossaries of Buddhist Sutras unearthed from Khara-Khoto shows that this edition is not a simple copy of the Ke Hong’s book, but the emendation by the followers of Buddhism, when they were in the process of reading the Avatamsaka Sutra, and referenced the Ke Hong’s book at the same time. The phenomenon that there is only the Avatamsaka Sutra part in the manuscrip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Buddhism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Western Xia regime, which was affected by the study of Buddhism in the Liao Dynasty.
Key Words:The Glossaries of Ke Hong; the Buddhism of the Western Xia regime;the Buddhism of the Liao Dynasty;Huayan S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