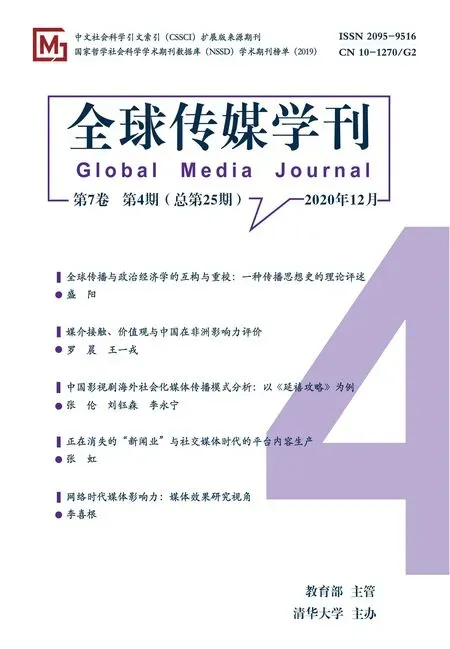国际多边组织的公共外交:欧盟实践评析
2016-08-03张莉
张 莉
国际多边组织的公共外交:欧盟实践评析
张 莉
公共外交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传播大发展的背景下,已成为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一门显学。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公共外交已经不仅仅是一国政府的行为,一些国际多边组织也纷纷开始从事公共外交活动。本文以欧盟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公共外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回顾其在欧洲内部实施公共外交的方式和实践,并对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公共外交的机构、方式及其效果进行评析。
欧盟;公共外交;国际多边组织
DOI 10.16602/j.gmj.20160043
公共外交在当今全球化和国际传播大发展的背景下,已成为国际关系学和传播学领域下的一门显学。它通常被认为是政府通过各种努力与外国受众沟通、接触、交流以影响其对本国的看法,从而推进本国国家利益,有利于实现政府外交政策等。因此,很多学者把公共外交看成是一种塑造国家形象的政府战略,以提升国家软实力(Anholt, 2005; Melissen, 2005; Van Ham, 2008)。实际上,在过去的十多年内,公共外交已经不仅仅是一国政府的行为,一些国际多边组织也开始从事公共外交活动,比如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和东南亚国家联盟(以下简称东盟)等。然而,相对而言,学术界对国际多边组织的公共外交研究却比较少,探讨非常不足。本文以欧盟为研究重点,对其公共外交实践活动进行探讨和评析。
一、国际多边组织的公共外交和欧盟的公共外交定义
公共外交的概念形成于“冷战”中期的美国。1965年,马赛诸塞州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莱彻外交学院(Fletcher School of Diplomacy)院长美国退休外交官艾德蒙德·古利恩(Edmund Gullion)创建了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Edward R.Murrow Centre for Public Diplomacy)。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苏“冷战”的国际关系已发展到需要通过新的手段,比如与国际公众接触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其外交目的和实施外交政策。古利恩创立的爱德华·默罗公共外交中心正是为了反映当时国际关系的这个新维度,同时也满足了当时美国新闻署急需用一个比宣传有更少负面联想的新词来概括其工作内容的需求。当然,不同于单向传播的宣传,公共外交强调双向传播。公共外交的目的是告知,与外国受众和政府沟通以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而不是控制信息以使他们接受宣传者的欺骗。古利恩当时对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公共外交旨在处理公众态度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形成和实施所产生的影响。它包括超越传统外交的国际关系维度,政府对他国公众舆论的教化,一国私有利益团体和他国私人利益团体间的互动,国际事务报道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外交官与驻外记者之间的传播沟通和跨文化传播过程”(Cull, 2006)。
这一定义虽然被不同学者进一步解释和发展,但定义中公共外交的实施者都是国家政府,实施目标与政府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直到2005年,有学者提出“新公共外交”的概念,指出公共外交发展到新阶段包含的新变化,比如实施主体不再仅仅是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多边组织等也成为公共外交的实施主体,新的传播技术在公共外交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特别是互联网等(Melissen, 2005)。在这种情况下Cull (2009)对公共外交的新定义是“公共外交是国际行为者(international actor)通过与外国公众(foreign public)接触而管理其国际环境的努力”。
然而,作为超国家的国际多边组织,它的公共外交实施者是谁?它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根据不同多边组织的具体情况而定。而且,重新定义的公共外交仍然没能解决新公共外交主体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国家利益的定位。一些国家认为本国的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在海外的公共外交活动也可以服务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但这实际上忽略了这些公共外交新主体自身为了管理和维护它的国际环境而做出的努力,而且国家与这些组织的关系也不可能像与自己的公共外交机构那样密切,最多只能算作是类似于有着共同意识形态利益的同盟关系(Cull, 2009)。对于包含多国政府的多边组织,“国家”利益的内涵有所不同。它强调成员国、区域甚至全球都关心的更广泛的利益,因为大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Melissen, 2011)。
此外,对于国际多边组织的公共外交,还有一个必须回答也饱受争议的问题是:谁是公共外交的实施对象?谁可以被定义为它的外国受众?研究者把2004年北约继信息和文化关系委员会之后成立的公共外交委员会(Committee for Public Diplomacy)作为北约开展公共外交的标志,把2004年欧盟驻美国使团建立的新闻和公共外交部门(Press and Public Diplomacy Section)作为欧盟开始公共外交的标志,把2008年东盟领导人宣布该组织将实行“人民外交”(People’s Diplomacy)为东盟开始公共外交的标志(Pagovski, 2015)。可实际上,也有研究表明东盟的公共外交实践实际上更多关注其在东盟成员国内部的政治目的,而不是为了在东盟之外建立国际同盟(Pagovski, 2015)。Melissen (2011)也指出对于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区域性多边组织,它们公共外交的关注点包括它们的内部公众和外部公众。
那么,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多边国际组织,欧盟的公共外交定义是什么呢?从1952年由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六国成立的“欧洲煤钢共同体”到1967年的“欧洲共同体”,再到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欧洲人一直梦想有一个“欧洲外交政策”。然而,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国际多边组织,“共同外交政策”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中才得以确立。虽然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利益”有诸多不同的想法和界定,欧盟需要建构一个欧洲身份认同和与此相关的欧洲利益已成为成员国的共识。
即使成员国之间并不是在所有外交政策上都能达成一致意见,欧盟各机构的工作人员希望这个世界能知道欧盟是什么以及欧盟是如何运行的目标是一致的。2007年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第一次正式给欧盟的公共外交做出定义,它指出:“欧盟的公共外交致力于影响公众态度,争取通过理解、告知和影响来促进欧盟利益。欧盟公共外交要清楚解释欧盟的目标、政策和活动,并且通过与单个民众、组织、机构和媒体的对话来促进对欧盟目标的理解。” 在这里,我们看出,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对公众的地域归属给出明确界定。也就是说,欧盟公共外交要影响的公众对象,既可以包含欧盟内部的公众,也可以包含欧盟外部的第三国公众。对于欧盟的对外公共外交,时任欧盟委员会对外关系委员的瓦尔德纳(Ferrero-Waldner,2006)曾说,欧盟公共外交是为了“把欧盟的政策更好地告诉给广大第三国受众,而且告诉他们这些政策所蕴含的欧盟作为一个全球行为者的价值和目标”。
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区域性国际多边组织,欧盟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是否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其希望的作用取决于欧盟的内部能力和外部影响力(Bretherton & Vogler, 2006)。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在欧盟成员国内部,欧盟希望各成员国的公民能够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欧洲身份认同和欧洲社会凝聚力;在欧盟成员国之外,能够发展成一个全球力量。本文以下部分将分别对欧盟为提升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影响力而进行的公共外交实践活动进行探讨和评析。
二、“传播欧洲”(Communicating Europe)的必要性及其实践
虽然欧盟从正式成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可是一直以来,欧盟和其成员国公民之间的交流并没有期待中的好。这一点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实施之前就已显现出来,之后也有《里斯本条约》(2009年)实施之前各国关于欧盟宪法的讨论。当然,更近的还有2016年6月23日英国的退欧公投。多年来,欧盟的民调显示,有很高比例的欧盟公民对欧盟的了解很少,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自己在欧盟的决策中没有发言权。欧盟认为,给予其公民充分的信息,让大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欧盟事务对欧洲民主十分重要,因此在2005年制定了一份《行动计划》以期提升在欧洲范围内的传播能力。《行动计划》指出,传播不只是提供信息,而是需要与欧洲公民建立一种对话关系,认真倾听民众,并把大家联系起来;认为这不是中性的无价值的行动,而是欧盟政治进程的必要一步(European Commission,2005a)。由于欧盟的决策大部分需要其成员国全票通过,因此,让欧盟公众知道并认可欧盟的政策和行动就变得十分必要。《行动计划》公布的同一年,旨在促进民主、对话和讨论的D计划也随后出台 (European Commission, 2005b)。接着2006年欧盟发布《欧洲传播政策白皮书》和《合作伙伴传播欧洲》,这一系列文件的出台奠定了欧盟委员会在欧盟对成员国实施公共外交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虽然欧洲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在理论上也有公共外交的职能,比如,欧洲议会为欧洲民众提供民主和法制的保证,确保欧盟各机构的运作,但实际上欧盟公共外交的最重要实施者是欧盟委员会。
欧盟委员会中负责“传播欧洲”的部门是传播部(DG Communication)。为了让成员国公民参与欧洲事务,传播部致力于在公民中建构一个“欧洲人”的身份认同。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身份认同通常跟自己的国籍或国家属性相关。欧盟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多边组织,如果能使成员国的公民有一个超国家的“欧洲人”的认同,对其一体化进程十分有利。当然,“欧洲人”的身份与原来“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比利时人”等的国别身份认同并不矛盾。Risse(2010)认为它可以是一个二级隶属关系,欧洲化的国家身份可以是二级身份。对于欧洲身份的认同一个最重要的象征是“你是谁?你怎么生活?你怎么长大的”,作者认为,那些年轻、富有、受过较高教育、属于较高社会层次的人往往有更强的“欧洲人”身份认同;反之,那些年龄比较大、教育程度较低、对外国人有排斥感的蓝领阶层,往往“欧洲人”的认同较少。越是在精英阶层,“欧洲人”的认同感就越强,所以欧洲一体化基本上是欧洲的精英层发起并引导的运动。对于普通人来说,欧洲更多的是意味着在欧盟内部可以自由地旅游、工作和学习,就像在自己的国家一样。作为二级身份认同,“欧洲人”与国别身份认同不矛盾,公民可以认为自己是法国人、德国人,同时也是欧洲人。“欧洲人”身份是对原来国家身份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不同文化和语言的障碍也不会给身份认同造成障碍,因为很多欧盟成员国本来就是多语言国家。因此,欧盟公共外交可以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欧盟是“多样性的结合”(united in diversity),并以此作为“欧洲人”的统一身份,从而增强其对外形象的合力。
为了让成员国公民能更好地了解欧盟,传播部建立了欧罗巴网站。欧罗巴网站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共网站,提供了关于欧盟的丰富信息。传播部指定专门的人员负责欧罗巴网站的编辑工作。
虽然传播部是欧盟内部公共外交的主要实施者,个别其他部门在特定情况下也会承担一部分公共外交职能。扩展部(DG Enlargement)在欧盟几次东扩时就曾经有过最多的传播预算,用于对成员国和候选成员国进行以告知和沟通为主的传播战略。因为这些国家的公民有对欧盟相关信息极强的需求,欧盟需要对他们进行关于东扩的舆论对话,以消解他们对东扩的负面理解。
此外,教育和文化部(DG Education and Culture)的大部分活动也以欧盟成员国为主,只有一小部分延伸至周边国家。欧盟教育方面的伊拉斯谟项目以欧盟成员国为主,但现在也扩展到欧盟外的第三国。
2005年欧盟成立了“欧洲直通”(Europe Direct),其工作内容是为欧洲公民提供关于欧盟的基本信息,包括回答关于欧盟政治活动的问题,推进欧洲一体化,为公民实施相关权利提供实用性建议等。“欧洲直通”为公民提供24种欧盟官方语言的服务,公民可以通过电话、电邮和网络聊天的形式获取关于欧盟的相关信息。
“传播欧洲”的政策和行动让欧盟公众更加了解欧盟,对欧洲事务有所认知,促进欧洲身份认同的形成,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欧洲社会凝聚力。这些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欧盟公众和欧盟各机构在欧洲利益上达成共识。
三、欧盟对外公共外交
在欧盟成员国以外,欧盟投入更大量的经费和精力实践公共外交。欧盟成立后很长时间以来,欧盟对外公共外交的目标一直很简单,那就是提升欧盟的可见度和认可度。比如1994年欧盟委员会发布的《新亚洲战略》就提出:“欧盟需要实施协调一致的公共关系项目来提升欧盟在亚洲的认知度。”(European Commission, 1994)直到新世纪,有学者提出欧盟如果想要被公众看成是重要的全球力量,一定要明确传达出欧盟是规范力量(normative power)代表的关键信息,以及它对民主、人权和法制的规范。之后几年,欧盟也一直在思索这一问题。2007年,欧盟在其50周年庆祝活动时出台了《实践中的欧盟公共外交一瞥》,首次比较明确地表明欧盟公共外交的目标是要对外传达出以下几个信息:欧盟是一个内部多样化程度高的政治实体;欧盟是和平保护者;欧盟模式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区域所效仿(European Commission, 2007)。
相对于个别已经实践了几十年公共外交的成员国,比如英国、法国和德国,欧盟的公共外交实践显得非常不成熟,不仅在组织机构上十分模糊,而且缺乏对实践活动的协调规划。与欧盟对内公共外交相同,欧盟各机构都可以是公共外交实施者,但是他们的实施方式并不相同。欧洲议会比较强调文化外交的作用,但是由于有文化和语言的差异,文化方面的公共外交需要欧盟与成员国携手进行;而且欧洲议会对外虽然跟很多欧盟成员国以外的国家和政党建立联系,但是它对外国公众的舆论影响力微乎其微。欧盟理事会实行每半年更换一次的轮值主席制,每个成员国的任职主席或多或少在任期内会多考虑一些自己国家的利益,这也使欧盟很难做到公共外交政策的统一性和一致性。真正施行公共外交的最重要的部门仍然是欧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通过其在世界各地第三国使团(Delegation)、对外关系委员会(DG RELEX)、教育和文化部,成为欧盟实施公共外交的核心阵地。
1.欧盟使团(EU Delegations)
第一个欧盟使团成立于1954年,是由当时的煤钢共同体在英国伦敦建立的,其目的只是作为欧洲煤钢共同体在英国的信息和传播办公室,并没有外交功能。之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煤钢共同体在美洲和亚洲陆续建立起更多的信息和传播办公室。目前,欧盟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了139个长期使团。
由于欧盟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因此没有在第三国的使馆,使团开始逐渐承担欧盟委员会在第三国的使馆职能。“使团行使的是没有国家支持,没有国家元首,并且包含欧盟外交政策全部缺点的职能”(Bruter, 1999)。从官阶合理性角度看,使团团长的级别等同于大使。然而,作为一个国家的大使,他/她可以在第三国代表母国的首脑。但是,欧盟使团团长的上级是欧盟委员会,然而即使是欧盟委员会主席,也不能说是欧盟的最高首脑,并且级别比国家首脑要低,这让欧盟驻第三国使团团长的身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但是,第三国仍然把使团团长看成是大使级,只不过不冠以“大使”的头衔(Bruter, 1999)。
欧盟委员会驻美国华盛顿使团最早使用公共外交这个词来概括其工作。2006年1月该使团设立了媒体和公共外交部门(Press and Public Diplomacy Section),这也被公认为欧盟作为国际多边组织开始公共外交的标志。而其他欧盟使团一般只强调信息和公共事务。比如欧盟驻日本使团有媒体、公共和文化事务部(Press, Public and Cultural Affairs Section),欧盟驻华使团有媒体和信息部(Press and Information Section)。使团这些部门主要负责和所驻第三国媒体沟通,和外国记者联系,召开新闻发布会,组织参加欧盟计划活动,维护双语网页(英文和当地语言),监测当地媒体对欧盟的报道等。各地使团人员和经费差异很大,因此公共外交的实践成效也不同。
在欧盟的139个使团中,8人以上可以归为大使团,3人以下可以归为小使团,约有三分之二的使团是中等规模,人员在4~7人之间。使团的工作人员,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外交人员。他们并不是从各国外交部派遣过来的外交官,而是普通的文职公务员,被派到第三国工作,一般一个任期四年,最多两期。但这些派驻人员不是随机选取,而是有相关职位要求的,按照国际组织的方式招募,工作语言要求为英语。使团工作人员主要来自英法德意,而使团团长经验比较丰富,年龄一般在50~60岁。
欧盟之前对使团的关注,主要是其前殖民国家,这些前殖民国家一般官方语言为欧盟官方语言的一种,运作比较便利,比如拉丁美洲很多说西班牙语的国家。但是近十年来,欧盟更关注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巴尔干地区等。
2.对外关系委员会(DG RELEX)
公共外交是欧盟对外关系的一部分,欧盟委员会里的对外关系部中有一个专门协调信息和传播的单位(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Unit)。每月在布鲁塞尔召集欧委会其他涉外部门,包括发展部(DG Development)、贸易部(Trade)、援助部(AIDCO-European Aid)、扩展部 (DG Enlargement)、媒体部(PRESS)、经济和财务部(ECFIN-Economic and Financial Affairs),当然还有对外关系部自己。这七个部门的对外传播相关成员大约有70人,组成了一个对外信息委员会(Information Committee)。虽然不同部门涉外事务中会有不同的优先排序,比如有的以地缘政治排优先性,有的以项目排优先性,但欧盟委员会的各部门对加强欧盟在第三国的传播能力有很强烈的共识。
至于预算,欧委会前对外关系委员瓦尔德纳曾经提议欧盟每年用三千万到四千万欧元用于对外传播(Ferrero-Waldner, 2006),对外关系部至少每年有七百万欧元的传播经费,其中五百五十万欧元用于各地使团(de Gouveia & Plumridge, 2005)。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10月成立了外交政策机构(FPI-Foreign Policy Instruments),隶属对外关系部,专门负责第三国使团信息传播部门的预算。不过该机构直接由欧盟高级代表领导,经费由欧委会负责。
3.教育和文化部(DG Education and Culture)
由于欧洲议会在文化外交上的强调,欧盟委员会的教育和文化部在对外公共外交上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欧盟的文化教育交换项目伊拉莫斯项目已经扩展到非欧盟成员国,通过给学生提供奖学金,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提供经费让欧盟内和欧盟外学者进行科研交换,在欧盟之外建立研究机构的方式,提升第三国对欧盟价值的认知和理解。欧盟的让·莫奈项目、教授、卓越中心和课程等在第三国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虽然欧盟设置它们的最初目的是促进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学术研究,而非公共外交活动,但随着它的知名度的提升,让·莫奈相关项目的进展,实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欧盟公共外交的功能。因为做这些项目的同时,不仅欧盟之外的国家对欧盟历史、政治、经济、法律、外交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有更大进展,更重要的是欧盟的相关知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相关知识也随着项目进展而广泛在欧盟之外传播出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欧盟在世界各地成立的欧盟中心(EU Centre)。欧盟中心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欧盟为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的倡议。为了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提升大学生对欧盟及其政策的了解和对欧盟的认知,欧盟在美国大学里建立欧盟中心。其实,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项目,而是欧盟对外行动的一部分。到1998年,欧盟已经在美国建立了12个欧盟中心,在加拿大建立了3个欧盟中心。2004年,欧盟在日本一桥大学成立亚洲第一个欧盟中心。自2004年以来,亚洲已经建立11个欧盟中心,促进了亚洲对欧盟及其政策的研究、理解和支持。
4.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虽然欧盟委员会是欧盟公共外交的核心实践者,可是它的身份却令人尴尬。欧盟委员会并不能代表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所以它能做的只是“满足客户需求式”的外交,为需要的国家和地区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Bruter, 1999)。但是,这样做使欧盟的公共外交缺乏全局观,缺乏战略性,所以有评论者说,欧盟“根本没有公共外交。其公共外交的基本哲学只是简单的信息传播。整个欧盟的公共外交活动是被动的,着重于‘我们说什么’而不是‘他们听到什么’”(Lynch, 2005)。
为了解决欧盟在对外政策和行动中不一致性的尴尬,欧盟做了诸多努力,《里斯本条约》的最终通过和实行是目前在这方面最重要的一步。《里斯本条约》之后,欧洲对外行动署(EEAS)于2010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从此,欧盟公共外交的实践,不仅仅有原来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及其秘书处、欧洲议会,更重要的是,新成立的欧洲对外行动署将发挥更大作用。欧盟《里斯本条约》实施后的首位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 Van Rompuy,2010)曾表示“欧盟需要讨论欧洲作为整体该怎样和世界其他国家相处”。《里斯本条约》之后的首位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 Barroso,2010)也认为欧洲如果各成员国不集体行动,欧洲就不可能成为一支全球力量,世界不会等欧洲,他们会继续前进,把欧盟落在后面,也把成员国落在后面。这是欧盟面临的一个战略挑战。
从此,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最高代表(High Representative for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以下简称欧盟高级代表)和欧洲对外行动署成为欧盟对外的代表。欧洲对外行动署对外代表欧盟的共同外交政策,负责对外所有战略,在理论上它包含从维和行动到对外援助的所有对外事务,甚至包含欧盟公民的领馆职能。它把所有成员国的外交人员纳入其中,而且也包含欧盟委员会的文职公务员以及欧盟理事会的相关工作人员。目前有员工3400多人,规模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成员国的外交部。
在欧洲对外行动署成立的第一年,行动署和欧盟高级代表就对外发布了593条决议和声明,其中欧盟高级代表发布了328条,新闻发言人发布了128条。欧盟高级代表也有权代表成员国发布声明。2012年,也有差不多600条的声明和决议。欧洲对外行动署里还专门设立战略传播部(Strategic Communications Division),负责协调欧盟对外信息。战略传播部会整理“每日要点”发给各国使团。这便于驻外使团及时了解布鲁塞尔的动向,对他们的公共外交工作十分有帮助。由此,我们看出,《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极力试图解决之前公共外交缺乏核心领导和系统性的问题。
此外,之前由欧盟委员会成立的使团,在《里斯本条约》之后也变成整个欧洲联盟的使团,这意味着它可以在第三国代表欧盟。不过绝大部分使团工作人员仍然隶属于欧盟委员会而不是欧洲对外行动署。2012年12月欧洲对外行动署的战略传播部和欧盟委员会的DG DEVCO(Communication and Transparency Unit)共同发布了《欧盟使团信息传播手册》(European Union, 2012),强调欧盟对外行动的可见度。基于推广欧盟价值和对和平、安全和繁荣观念的传递,《欧盟使团信息传播手册》强调欧盟使团发布的信息和行动要重点围绕五个方面,即提升欧盟的五种形象:①欧盟是(与欧盟邻近的)民主转型国家的重要伙伴;②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的合作和发展援助者;③欧盟是全球应对危机和以贸易为引擎促进变化的经济力量;④欧盟通过与战略伙伴及战略合作项目的高层政治对话来促进人权发展;⑤欧盟是应对全球安全威胁的安全提供者。《里斯本条约》之后,欧盟公共外交的总经费只有10%用于欧盟内部,剩下的由各地使团使用(Duke, 2013)。
不过以上这些并不代表欧盟可以给公众一个清晰的方向。其实欧盟原本想在欧洲对外行动署成立一个专门的信息和公共外交部门,但是这一提案被欧洲议会否决,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排除欧盟日后成立这样的部门的可能性。不过因为这一部门尚未成立,目前欧盟公共外交在对外行动署中的责任仍然比较分散。而且欧盟委员会的外交政策机构和欧洲行动署的战略传播部和欧盟各相关部门在公共外交实践也还不太协调。
从以上对欧盟公共外交实践的探讨和评析我们可以看出,相对于民族国家的公共外交,作为一个超国家的国际多边组织,欧盟在其公共外交的实践上既要对内让成员国公众有对“欧洲人”的认同感,对“欧洲事务”的关心和对“欧盟利益”的共识,又要对外让国际公众对“欧盟”是什么,做什么有认知,还要树立欧盟是一个全球力量的形象。要做好这两方面是很有难度的,尤其在欧盟各机构在公共外交实践中仍然有权责不明和协调不力的情况下,要做得好实际上比一般的民族国家更有难度。虽然欧盟一直在强调各机构应该采取更积极的国际传播策略,传达正确无偏见的信息,反映自身作为超国家组织的特性,并认为目前做得还很不好,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欧盟能够成功地用和平的方式让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也说明它有一定的吸引力。由28个成员国“多样性的结合”这样的合作是前所未有的,虽然前不久的英国公投决定脱欧,但这与历史、地域以及英国内政外交等很多因素有关,欧盟在公共外交上的不少做法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Anholt, S.(2005).Brandnewjustice:Howbrandingplacesandproductscanhelpthedevelopingworld.Oxford:Elsevier Butterworth-Heinemann.
Barroso, J.M.(2010).StateoftheUnion2010.Speech/10/411, Strasbourg, 7 September 2010.
Bretherton, C.& Vogler, J.(2006).TheEuropeanUnionasaglobalactor(2nd ed.).London:Routledge.
Bruter, M.(1999).Diplomacy without a state:the external deleg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JournalofEuropeanPublicPolicy, 6(2), 183-205.doi:10.1080/135017699343676
Cull, N.(2006).“PublicDiplomacy”BeforeGullion:TheEvolutionofaPhrase.USCCentreonPublicDiplomacy, Retrieved from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blog/060418_public_diplomacy_before_gullion_the_evolution_of_a_phrase/Cull, N.J.(2009).PublicDiplomacy:LessonsfromthePast.USCCentreonPublicDiplomacy, Retrieved from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 macy.org/files/legacy/publications/perspectives/CPDPerspectivesLessons.pdf
deGouveia, P.F.& Plumridge, H.(2005).EuropeanInfopolitik:DevelopingEUpublicdiplomacystrategy.London: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Duke, S.(2013).The Europeanexternal action service and public diplomacy.In Davis Cross, M.K.& Melissen, J.(Eds.),Europeanpublicdiplomacy:Softpoweratwork(pp.113-136).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European Commission.(1994).TowardaNewAsiaStrategy, Brussels.COM (94) 314 final, 13 July.
European Commission.(2005a).ActionPlantoImproveCommunicatingEuropebytheCommission, Brussels SEC(2005) 985 final, 20.7.2005.
European Commission.(2005b).Plan-DforDemocracy,DialogueandDebateBrussels, 13.10.2005.COM(2005) 494 final.
European Commission.(2007).AglanceatEUpublicdiplomacyatwork.The EU’s 5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around the world.Luxembourg: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European Union.(2012).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HandbookforEUDelegationsinThirdCountriesandto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Ref:Ares (2013)32604, 11 January 2013.
Ferrero-Waldner.(2006).The EU in the World:Towards a Communication Strategy for the European Union’s External Policy.2006-9, 329/1.
Lynch, D.(2005).Communicating Europe to the world:what public diplomacy for the EU?.EPC Working Paper No.21.
Melissen, J.(2005).Thenewpublicdiplomacy:Softpower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Melissen, J.(2011).Beyon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Clingendael Paper No.3, Retrieved fromhttp://www.clingendael.nl/sites/default/files/20111014_cdsp_paper_jmelissen.pdfPagovski, Z.Z.(2015).PublicDiplomacyofMultilateralOrganizations:TheCasesofNATO,EU,andASEAN.USCCentreonPublicDiplomacy, Retrieved from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sites/uscpublicdiplomacy.org/files/useru ploads/u33041/Public%20Diplomacy%20of%20Multilateral%20-%20Full%20June%202015.pdf
Risse, T.(2010).AcommunityofEuropeans?Transnationalidentitiesandpublicspheres.Ithaca, 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Van Ham, P.(2008).Place branding:The state of the art.TheAnnalsoftheAmericanAcademyofPoliticalandSocialScience, 616(1), 126-149.doi:10.1177/0002716207312274
VanRompuy, H.(2010).The Challenges for Europe in a Changing World.CollegeofEurope, Bruges, 25 February 2010, PCE 34/10.
(编辑:卢嘉)
Public Diplomacy i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Evaluating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Union
Li Zhang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TsinghuaUniversity)
With the entry of the era of New Public Diplomacy, the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have become public diplomacy actors in recent years as well.However, in comparison to the research on public diplomacy conducted by nation-states,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public diplomacy practice.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addressing this topic by focusing on the prac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After discussing the definition of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context of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the paper explores and evaluat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practice of public diplomacy by the European Union (EU).
European Union; public diplomacy;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张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