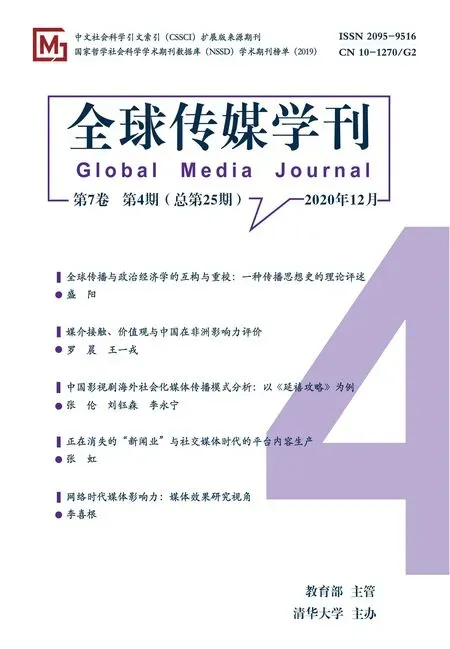论国际气候变化报道研究的发展与问题
2016-08-03陈沛然
纪 莉, 陈沛然
论国际气候变化报道研究的发展与问题
纪 莉1, 陈沛然2
本文梳理了关于国际气候变化报道的研究的发展脉络,并对国际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研究议题的变化与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论文发现国际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研究普遍缺乏“气候正义”视角和东西方对话式的研究,这也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议题研究的常见现象。
气候变化;报道研究;气候正义
DOI 10.16602/j.gmj.20160039
全球气候变化一直是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和谈判,并非如表面所见,是一个关于全球气候变化原因的科学问题的讨论,或者是一个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环境问题的争论;其本质上已经是一个涉及各国社会、政治、经济和外交的国家利益问题。
自1990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表第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报告以来,气候变化对人类的影响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就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等领域的争议捆绑在一起,成为日益具有国际性的媒介公共议题之一。国际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研究由此开始,并逐渐丰富。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与梳理,一方面让我们通过了解气候变化报道中的问题,理解如何进行有效的气候变化传播;另一方面,它也对我们在国际舆论压力下,就科学性国际公共议题提升中国的传播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一、国际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研究的发展阶段与主要成果
20世纪80年代,许多民意调查发现,欧美发达国家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担忧越来越多,关于气候变化的公众认知调查逐渐得到各界关注,气候变化议题成为满足大众媒介需要的一种议题。Kingdon(1995)在研究中提出,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议题包含问题指向(problem indicators)、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s)、信息反馈(feedback)等三个指标,这些特征能够帮助该议题获得决策者的关注,提升该议题在议程中的地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也越来越获得媒体的青睐和政府的重视,进入公共议程领域。
国际学者对此的研究有的专注于媒介传播内容及其新闻文本的分析,有的重点考察媒体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话语框架,还有的从政治学角度着力于国际气候治理规范的传播策略等。有学者认为,对公众认知、新闻文本话语框架及国际气候规范传播策略层面的探讨,构成了欧美气候变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郑保卫、王彬彬,2013)。
(一) 初始期(1980年代末—1990年代中):气候变化议题开始媒介化呈现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人类行为造成的气候变化问题开始进入到公共议程中,气候传播问题随之得到相应的关注。早期人们关注气候变化传播的视角较为狭窄,基本只是关注科学发现和对IPCC定期发布的报告等问题的相关报道。偶尔也会有研究关注到对极端气候事件以及高级别会议或者政治峰会的情况的报道(Weart,2003)。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上开始出现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较为突出的是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周期模式的研究。议题关注周期模式是Downs(1972)在针对环境问题的报道研究中提出的一种总结模式。他认为,环境问题的演进经历5个阶段。第一,前问题阶段:问题已存在,但未受到大众注意;第二,发现和预警阶段:议题忽然被赋予高度关注,从原来不被视为是问题转变为视为问题;第三,成本反思阶段:公众开始认识到问题相当复杂且不易解决;第四,公众注意力下降阶段:大众对此问题失去注意力,尽管此时问题可能尚未解决,实际情况也没有改善,而大众已将焦点转向另一新议题;第五,后问题阶段:议题逐渐退出公众视线。Downs同时强调,并不是所有公众议题都会经历这五个阶段,有些议题可能只走几步就消失了,而有些问题则会反复在第二、三、四阶段循环。
在此基础上,Ungar(1992)首先关注到全球变暖问题受关注度的起伏变化。研究发现,全球变暖的关注度的兴起与衰落与极端天气事件紧密相关。1988年夏天的异常高温天气使得全球变暖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美国、英国、德国等西方媒体“发现”了气候变化这一报道领域;但1988年气候恢复正常后,公众、政客们对此的关注也随之减弱,媒体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兴趣明显下降,对该议题的关注也从社会问题向国际外交领域迁移。
而后的研究发现也再三证实了媒介议程显著度高低变化具有循环周期模式。McComas 和 Shanahan(1999)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1980至1995年间气候变化的报道,从媒介叙事的角度对Downs的议程周期模式做了进一步的验证,并在Downs 五阶段的基础上,将议题的周期性变化总结为三个阶段:上升期 (upswing)、维持期(maintenance)和下降期(downside)。
在这个研究阶段,由于气候变化议题开始逐渐进入媒介的视野,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也多为对媒介文本的分析,通过寻找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变化周期,发现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介化过程和规律,探讨气候变化议题在媒介报道中具有的新闻报道问题。
(二) 成长期(2000—2007年):从科学传播视角审视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介报道
2000年7月,美国《公众理解科学》第九卷第三期出版专题,从政治、文化、科学、公众参与等角度探讨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的问题,学者们对于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的研究视角开始多元化。
很多研究者在对有关气候变化的争议性话题的研究中都选择了美国媒体进行研究,并对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如何建构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和争议性进行了批判。Zehr(2000)通过分析1985—1995年美国大报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发现这类报纸在报道气候变化时,将科学争议作为其最重要的主题。《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涉及全球变暖不确定性理论的气候变化报道分别占研究样本的57%和58%。Antilla(2005)也在研究中再次发现,美国报纸在报道气候变化过程中,非常强调气候变化的科学不确定性和争议性。
Brossard等(2004)的研究发现,美国媒体在气候变化报道中偏好强调戏剧性元素——冲突。展现政治家与科学家、主流科学家与气候变化怀疑论者的戏剧性冲突,成为美国媒体报道气候变化的常用手段。而学者Maxwell T.Boykoff在2007年发表多篇论文,证实美国电视新闻报道中存在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建构,并从政治、经济等方面探索背后的影响因素。
本阶段的另一个研究主题是探讨媒介在塑造公众对气候变化认知方面的作用。有学者从议程设置角度探析气候变化报道对公众的影响。Shanahan 和Good(2001)在考察纽约和华盛顿两大城市的媒介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后发现,媒体对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会影响公众对该议题的态度;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对公众的误导。Stamm等(2000)通过对华盛顿大学学生的问卷调查和访问,发现尽管媒体在促进人们认识气候变化的原因、后果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媒体报道对于公众认识气候变化存在一定的缺陷。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是否可以从科学报道的层面澄清这些误解,其能力堪忧。
(三) 快速发展阶段(2008—2010年):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通的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导致相关媒介报道急速增长
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发表后,气候变化议题的科学共识随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起来。基于科学共识之上,全球召开了一系列与气候议题相关的重要国际会议,引来了世界媒体的关注。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召开,让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达到了沸点。气候变化议题由科学争议性话题正式步入全球政治与外交话语体系,这一状况的出现让学者们在关于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介报道研究中也增加了以政治传播的视野与角度进行气候变化传播的研究。
这一阶段,政治话语体系的强化让气候变化成为全球共通性话语。不仅是经济发达地区如美国的情况受到研究者关注,而且之前较少被研究的国家,由于气候变化在本国政治话语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研究对象。
在欧洲,Federico A.Pasquare(2012)等通过对意大利《共和报》和《晚邮报》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二者有着不同的议程:《共和报》会侧重建构公众在应对气候变化中采取行动的共识,而《晚邮报》则努力将气候变化问题的紧迫性最小化。在报道关于水文地质灾害的问题时,记者更愿意关注赔偿,而不是预防。Carvalho 和Pereira(2009)关注葡萄牙媒体对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和讨论;在美洲,Good(2008)运用媒介宣传模式分析了加拿大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作为海洋岛国,新西兰成为受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国家。Kenix(2008)通过对比研究新西兰独立网站和主流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分析新西兰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在亚洲,除了在中国已经起步发展的气候变化报道研究,还有不少学者关注其他亚洲国家的发展,如Boykoff(2010)在分析印度的气候变化报道时发现,印度的媒体报道过于追求公平原则,而掩盖了气候变化的紧迫性。
另外,在研究影响媒介报道建构的要素方面,之前学者主要选择新闻规范角度,而在这一阶段,研究者们则进一步从政治、经济的角度对影响框架构建的因素进行剖析。Kathleen Hall Jamieson和Joe Capella(2008)指出:在气候变化议题以及其他环境议题上,北美“保守派媒体”受到保守派观点影响,不仅散布他们对气候科学的怀疑,而且还谴责任何政府开展法规动议,这也不断激活了“经济与环境对立”的框架。而Boykoff(2008)则在研究中发现,新闻媒体对气候变化的建构与经济利益有关。另外,不少文献也涉及市场竞争、媒介所有权、广告以及公司所有制对媒介信息建构的影响,媒体在报道中为凸显利益主体的主导地位,会导致信息出现偏差。
(四) 稳定与拓展阶段(2011— ):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研究呈现各种视角的反思与对比
随着对气候变化报道的框架分析和批判性话语分析不断丰富和成熟,对媒介的气候变化报道研究逐渐进入稳定阶段,学者们在已获证实理论的基础上,不断挖掘新的领域。
研究者们首先延续以往内容分析的模式,对各个国家的报道框架进行分析。如Eide 和Ytterstad(2011)对挪威两家报纸关于巴厘岛气候峰会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探索挪威媒体如何将气候变化议题本土化;Takahashi(2011)则通过对秘鲁媒体的气候变化报道进行研究,分析秘鲁的报道框架。除了个案研究外,还有学者从比较的角度进行跨国分析,如Tuula Teräväinen对比英国和芬兰的能源政策报道,结果发现英国媒体多批判政府的能源政策,而芬兰媒体则倾向于支持政府的政策。
除了对传统研究领域的继承和延续之外,学者们还进行了开拓、创新。
在效果研究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突破了议程设置理论的局限。例如,Hart(2011)运用Iyengar的主题式框架和片段式框架进行研究,分析在报道气候变化对北极熊的影响这个议题方面,这两种框架的使用对相关议题讨论产生的影响。所谓主题框架是就气候变化相关议题提供大致趋势和信息;而片段式框架则提供气候变化相关议题的案例分析。该研究表明,对比使用主题式框架报道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与使用片段式框架报道这类议题产生的影响,前者极为显著地提高了人们对政府承担缓解气候变化责任的政策的支持。
而在内容研究的媒介选择上,关于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研究不仅着眼于传统主流媒体,而且也开始更多比较分析不同媒体类型的气候变化报道内容。如Doyle(2011)对英国三个不同类型的报纸进行了批评性话语分析,如对《镜报》《每日邮报》《独立报》的比较分析;而Nielsen和Schmidt则对两大权威科学杂志《自然》和《科学》的网络新闻服务的文本和图像进行内容分析,对比二者采用的气候变化报道框架的策略之异同。
德国学者Irene Neverla曾表示,气候变化的宏大叙事及人类如何应对的问题将不仅作为西方国家议题,而且将作为跨国甚至全球的议题持续下去,这也势必驱动着气候变化研究朝着新的阶段推进。
二、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研究中的主要观点及其意义
随着气候变化议题的媒介化,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早已超越了科学层面的表述,成为涵盖各领域冲突与斗争的议题。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研究也集中呈现出关于气候变化报道本身具有的特点,以及观点的变迁。
(一) 气候变化媒介报道呈现出媒体在科学议题上的政治化表达
在前面关于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研究的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到,气候变化报道逐步超出科学议题报道的范畴,气候变化的议题也逐步置放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进行呈现,其话语建构受到媒体和其他利益方的人为操控。
正如Weingart(1998)所指出的:“媒体构造了自己的现实。媒体的重要性使科学在某些问题上的垄断性正在减弱。科学对于真理的判断标准正面临着媒体迎合受众的标准的挑战。虽然科学标准不会被取代,但其正在被其他的标准所补充。”
Trumbo(1996)的一项研究,针对的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篇言报》和《华尔街日报》等五家美国全国性报纸进行的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结果证实,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早期,关于气候变化的新闻,占主导地位的消息来源是政府机构和官员,而不是科学家,可见政治与气候变化从一开始就联系紧密。
Zehr(2000)更进一步指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使得科学判断的不确定性越发明显。此类问题会引发科学之外的问题,如社会道德和政治经济问题等,从而使气候变化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和难以确定。”
(二) 媒介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对公众产生了日益深远的影响
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对公众的影响,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问题。多项研究都指向一个结论,那就是: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对受众产生的效果日益显著而悠远。
1.媒体报道吸引了公众对气候变化议题的关注
根据议程设置理论,大众媒介通过提供消息和安排相关议程来左右人们对事情的关注程度,受众对事件的重视程度是与大众媒介对其强调的程度成正比的。因此,媒介对气候变化议题的议程设置也会影响大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态度与行动。
已有多项研究表明,媒体对环境议题的报道能够提高民众对某个问题的关注程度。Ader(1995)发现,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纽约时报》对环境污染的强调与民众对此议题的关注程度有正向关联。Sharples(2010)在研究中也发现,公众对气候变化的兴趣是与媒介的报道紧密相关的。媒介对气候变化现象报道得越多,人们对其关注得也就越多(Sampei & Aoyagi-Usui,2009)。
2.大众媒介是公众获取有关气候变化信息的主要渠道
许多研究还发现,大众媒介以及新闻记者已经成为目前公众获得有关全球气候变化信息最重要的来源(Wilson, 1995; Ungar, 2000; Dirikx & Gelders, 2010; Pasquaré & Oppizzi, 2012)。我们知道,在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议题上,读者缺乏直接信息或知识来指导他们独立判断。所以,作为主要信息源的媒体会直接为读者定义和塑造对现实状况的认知。较早前的研究也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是美国民众获取全球变暖信息的主要来源(Wilson,1995)。而Cothett和Durfee(2005)的研究表明,即使人们身处热浪、干旱、洪水、暴雨等环境中,媒介仍旧是人们将这些极端天气事件与全球气候变暖联系起来的主要桥梁。可见,媒体将科学知识转译成大众话语,塑造了民众关于全球变暖的经验。
尽管大众主要是从新闻媒体上获知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但是媒体所提供的气候变化信息却并不全面。有研究者认为,在过去的数十年中,新闻业在促进公众认识气候变化的真实存在方面功不可没,但是这种意识提升并没有带来更深层次的认识,即让公众知晓气候变化到底是什么,以及气候变化将会怎样(Corbett & Durfee,2004)。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时通常聚焦于围绕气候变化的政治论争以及科学家之间的论战,这事实上牺牲了气候变化的科学本质,从而导致公众对气候变化变得更加困惑甚至冷漠(McIlwaine,2013)。Hargreaves等人(2003)也发现,公众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困惑是与媒介的报道相关联的。在报道气候变化议题时,媒体本应传递更多的科学信息,然而这些信息通常都被遗失了。造成这点的主要原因,是记者们需要在这些议题中呈现科学冲突或者气候变化灾难中的恐怖情节(Cook,2007),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读者。
3.媒体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认知
气候变化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和争议性,而媒介是公众了解风险和争议的主要渠道,媒介决定风险的建构和呈现,因此媒体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风险性认知上具有决定性作用。如果没有媒介对于气候变化和核危机的报道,大部分公众也许会对它们的危害一无所知,而且它们也不会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议程。媒体对气候变化报道现象报道得越多,人们对气候变化就越关注。同样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风险的认知也受到他们自认为获得的气候变化知识程度的影响。那些认为自己很了解气候变化现象的人更倾向于认为,气候变化是地球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Special Eurobarometer 322,2009)。
Cobett和Durfee(2004)的一项研究表明,阅读那些强调争议和不确定性的文章,会减少受众对气候变化确定性的感知。过度呈现全球变暖的争议性,造成了美国民众对全球变暖的认知度长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而在一项针对意大利报纸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他们所研究的两份报纸设置了不同的议程,从而对其目标读者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份报纸试图培养的公众共识是让大家意识到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的危险影响是必要的,而另一份报纸则在潜移默化地建构另一种旨在使气候变化问题紧迫性最小化的新闻框架,从而转移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注意力(Pasquaré & Oppizzi,2012)。
除了新闻报道中的文字会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感知外,报道中所运用的图片同样会影响人们的这种感知。奥尼尔(O’Neil, 2013)发现,在气候变化报道文章中使用的大多数图片要么在读者心中强化了她所谓的远离日常生活的效果,要么是将这些议题建构为具有争议性的,从而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风险的判断。
总之,媒体与公众对气候变化论争的理解之间的密切关系表明,媒介在提供气候变化信息以及唤起人们对这一问题严重性的意识方面起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
(三) 媒体对气候变化的报道呈现出利益的多元性与博弈
媒体的新闻生产受政治规范、经济规范和新闻规范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气候变化本身是一项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议题。所以,媒体不仅会呈现气候变化的科学复杂性、不确定性、风险性,而且还会以政治新闻、经济新闻、社会新闻、科学新闻、环境新闻等形式反映其与人类社会活动广泛而深刻的联系。相应地,气候变化也就成了各种权力的角逐对象,科学家、工业界、政策制定者以及NGO组织,都试图在此议题上建立自己独特的视角。
而媒体正好为各方利益的较量和气候变化的意义建构提供了主要场所,各领域的社会行动者都将媒体视为争夺气候变化话语权的公共竞技场,并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影响气候变化的媒体再现。
尽管新闻自由、独立、公正已成为西方新闻界的主流价值观,随着全球媒介集团的不断扩张,各种资本、各种势力对新闻媒体进行渗透,甚至可以左右媒介的新闻报道。传播学的各种批判学派早已对新闻媒体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过深刻有力的揭露。在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领域,由于气候变化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及其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生态的紧密联系,各种势力对气候变化报道的影响更是明显而巨大的。Revkin(2007)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闻平衡性原则就被一些大公司用来扩大对气候变化的质疑,以及提高其不确定性,而这些公司大都是受益于化石能源的。使用化石能源释放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是全球变暖的主要肇因,那些使用化石能源的大公司必须要为全球变暖承担相应的责任。而这些公司为了逃避责任,便通过各种手段引导媒体聚焦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方面,使人们对导致气候变化的原因产生怀疑。还有研究者指出,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是与政治议程紧密联系的,这使得媒体会建构一种具有偏向性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知识以及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视角。为了维持它们的政治偏向,媒体通常还会强调或者回避对某些影响的预测。危险的气候变化问题由此被政治与意识形态所界定与驱使(Carvalho & Burgess,2005)。公众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在英国的一项调查中,被调查者们认为媒体是根据它们的政治倾向以及其他因素来塑造媒介议程的,于是常常导致它们所提供的有关气候变化的信息不被相信(Sharples,2010)。尽管在对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研究中,已有上述对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分析批判的观点。但从总体上来说,批判视野下的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研究还有待更深刻的挖掘。
(四) 媒介气候变化报道的不足与缺陷
作为一个跨领域、跨学科的主题,关于气候变化的报道具有诸多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报道本身非常难以把握。而且,研究者普遍分析认为,由于大多负责气候变化报道的记者不是专业的环境新闻记者,缺乏气候变化科学的知识和训练,又缺乏科学界的采访资源,所以记者在报道全球变暖议题时,大多造成受众对该风险严重性的误解和无知。
Nelkin(1987)认为,现在的新闻记者大多毕业于人文学科,少有受过科学训练的,有些甚至连基础的学校科学教育都没有接触过。而如今,科学领域的专业记者越来越罕见,其原因在于:现在的新闻编辑部正在不断收缩,媒介也越来越碎片化(Lockwood,2010)。在现在的新闻编辑室里,气候变化议题通常分配给普通记者,而大多数记者是不愿意报道科学话题的,因此,科学话题在媒介空间与时间中都只占很小的比例。而专业记者在气候变化报道中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尽管专业环境记者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知识要比普通记者丰富,但是他们的起点非常低。专业记者仍然会忽视许多基本的气候变化事实,例如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Wilson,2000)。
总的来说,目前对报道气候变化的记者的指摘,主要指向他们对气候变化不确定性的错误理解,以及对平衡报道原则的滥用。尽管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的确存在不确定性,科学家们也对预测其影响持十分谨慎的态度;但是,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已成为科学界的共识。而许多记者在报道气候变化议题时,依然在强调不确定性问题,甚至有些文章通篇都在讲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新闻媒体之所以这样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媒体对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原则存在误解与滥用。
Wilson(2000)认为,平衡性原则在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体育新闻中是很有用的,但是把这种手段运用在科学家已有共识的领域则会令人产生其中还有异议的印象。通过给那些在气候变化论争中的少数既得利益者以平等的空间和时间,记者们实际上建立了一种虚假的平衡,从而歪曲了科学观点(Newell,2006; Boykoff & Boykoff,2007; Boykoff & Rajan,2007)。这种虚假平衡反而是不利于公众理解气候变化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
例如,美国媒介的气候变化报道,因长期以来一味强调全球变暖的科学不确定性和争议性,而广为研究人员所诟病。Boykoff和Boykoff(2004)在对比《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等美国的主流媒体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报道时发现,在寻求信息来源的均衡时媒体会表现出一种偏见,因为这些主流媒体在报道全球变暖的事实时,总是引用反对气候变化的人士的话语,或者让议题的两面都呈现,抵消了关于气候变化具有紧迫性的科学发现。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议题在媒介上逐渐呈现,并受到媒体的关注;而媒体的气候变化的关注,也会对公众对该问题的认知产生一定的积极意义。它既能促进公众提升对该议题的关注度,增加对气候变化科学的知识与了解;还能为公众讨论该议题提供场所。但由于气候变化议题本身的复杂性、争议性,公众认知的盲目性以及媒体自身的局限性,媒体气候变化报道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误解和误导,影响公众对气候变化及其应对决策的认知。因此,媒体关于气候变化报道的相关研究尤为重要。
三、对国际气候变化报道研究成果的反思
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网络社会的来临,气候变化问题尽管已经强烈地政治化、经济化,却无法再以其坚硬的科学壁垒而游离于国际视角与公众视角之外。各种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已经形成了跨国、跨媒体的强烈势头。
(一) 气候变化报道研究中缺乏“气候正义”视角
在过去的数年间,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转变为公众议程中最重要且常见的环境问题之一(Mark et al.,2012)。它也成为新闻媒介最为关注的环境议题,而学术界对有关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的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丰富与深入。然而,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一个十分吊诡的现象,尽管气候正义的内涵、维度、原则在理论上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与精心建构,并且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基础;然而,在新闻媒介的气候变化报道中,却很少出现与“气候正义”有关的话语,同时,学者们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媒介报道时,也很少用气候正义框架对媒介文本进行分析。
所谓“气候正义”,有学者将之概括为“地球上所有物种、人类不同世代、当代人中一切国家和个人都有权平等地分享气候系统的惠益;每个国家和个人都应公平分担稳定气候系统的责任和成本;气候变化的制造者应向其受害者提供补偿,并须采取特别措施保护濒危物种”。2002年,由非政府组织提出的《巴厘岛气候正义原则》被认为是气候正义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意图是要转换“气候变化的话语框架,将其从科技争论转向关注人权与正义的道德争论”。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气候正义框架都应该成为其日益强调的媒介报道框架。
有学者认为,从四个方面来说,气候正义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重要且必要的(Baskin,2009)。首先,从气候变化的责任与其影响之间的关联来看,发达国家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负有主要责任,不论是对当前的排放流量还是历史排放存量。但是,那些最有可能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不仅包括世界上最穷的最脆弱的人群,同时也包括那些对造成这些问题负有最少责任的群体,而这些群体大多分布在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通常都缺乏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资源,当他们面临食物短缺、洪水及其他极端气候事件时,他们的恢复能力非常薄弱,同时也缺乏重建防护设施的资本。再次,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通常主张发展经济是其主要诉求,发达国家也难以驳斥这种观点,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曾经的发展路径;而发展经济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能源的大规模使用,因此,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更多的碳排放空间。最后,温室气体的排放是超越国家和边界的全球性问题,现在没有足够的大气空间供发展中国家像发达国家历史上那样排放温室气体,因此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需要一个全球性的共识,而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认为公平的时候,这种共识才有可能达成。
两位巴西学者试图评估“气候正义”话语在何种程度上被巴西媒体融入其对极端气候事件的报道分析中(Milanez & Fonseca,2012)。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与气候非正义相关的现象在巴西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气候正义话语仍然没有被这个国家的媒体广泛接受,这些媒体并没有在环境非正义事件、极端气候事件与气候变化间建立强联系。两位研究者最后提到,尽管气候正义话语在巴西媒体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研究者们仍希望这一话语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因为这一话语的使用,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首先,基于巴西在许多国际性的有关气候议题的会议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如果巴西的社会群体广泛地使用这一话语,气候正义的概念将在这些国际性论坛中得以彰显。其次,气候正义话语能提升受影响群体的主张得到重视的机会。最后,将极端气候事件归因于气候变化的影响,可以改变某些公共政策的方向。
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数年之后,在美国,一些具有批判性观点的非裔美国学者以及他们的同盟者也开始从气候正义的角度集中探讨媒介如何建构了这一灾难(Dawson,2010)。他们发现,美国媒体在报道卡特里娜飓风时,总是密切关注应对这场可怕灾难以及追踪那些幸存市民的行动;而灾难中的非裔美国人通常不会被媒体所呈现,这种结构性特征在灾难发生之前、之中、之后都因媒体报道的荒谬转换而变得稀松平常。另外,灾难中的低收入群体以及少数族裔群体通常被媒体描绘为罪犯而不是幸存者。而气候正义所要求的改变,正是针对这些现象。
最新的气候变化科学确认了在后京都议定书时代制度化的气候正义框架的重要性(Abate,2010)。随着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与严重,许多政治家开始关注全球减排的重要性,然而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至少在发达国家,对气候正义的考量还没有被嵌入实际的政策思考之中(Baskin,2009)。另外,虽然一系列国际性的气候变化会议都确认了发达国家应该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中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证据显示像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有意愿承担他们的气候责任(Dawson,2013)。这也许是西方媒体的气候变化议题报道中缺乏气候正义话语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西方媒体一直标榜自己的独立自由,但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力量对媒体的影响却是不可否认的。
许多气候正义的提倡者主张围绕全球变暖的政治与社会议题应该被解释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群正在经受最严重的气候变化结果的冲击”(de Onís,2012),气候正义应该是他们用来与发达国家进行气候谈判的重要政治与伦理武器。然而,在第三世界国家新闻媒体对有关气候变化的议题进行报道时,却同样缺乏气候正义话语的建构,这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范围内争取其气候变化权益无疑是不利的。一些新闻记者在亲临各种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大会时,实际上已经深深感受到了气候非正义现象的存在。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后期,美国大谈对中国减排行动透明度的要求,然而这一要求并不符合巴厘岛气候峰会确定的路线图的精神。当被问及美国提供资金的具体数字时,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推说将与其他发达国家分担,美国将提供“适当”的份额,引致各国记者发出笑声(孙钰,2010)。而在华沙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也是想尽办法强化“共同责任”,淡化“有区别责任”,否认“历史责任”,背弃自己承诺的责任(薄燕,2013)。发达国家在气候谈判大会上的这些言论与行动都是违背气候正义原则的,而从气候正义角度对其进行报道也正是媒体非常需要的视角。
(二) 气候变化报道研究中缺乏东西方对话式研究
尽管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环境、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伦理问题,各国媒体也都十分重视这一全球议题;然而,目前对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一国之内,而缺乏东西方对话式的比较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欧美国家的媒介研究上。虽然也有一些研究对中国、印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的气候变化媒介报道进行了考察,但从数量和质量上来看,还是不及前者。另一方面,在气候变化媒介报道的比较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对一国之内具有不同倾向的新闻媒体的对比研究(Pasquaré & Oppizzi,2012)。
由于东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议题时也会存在一些差异。对东西方媒体在报道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异同点进行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东西方国家在对待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同态度,同时也可以为东西方国家在国际气候的谈判与合作方面提供参考与借鉴。
薄燕(2013):从华沙气候大会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合作与分歧,《当代世界》,第12期,44-47页。
孙钰(2010):纷繁复扰中看真相,《中国记者》,第2期,74-75页。
郑保卫、李玉洁(2011):论气候变化与气候传播,《国际新闻界》,第11期,56-62页。
郑保卫、宫兆轩(2012):新闻媒体气候传播的功能及策略,《新闻界》,第21期,3-6页。
郑保卫、王彬彬(2013):中国气候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机遇与挑战,《东岳论丛》,第34卷(第10期),5-14页。
Abate, R.S.(2010).Public nuisance suits for the climate justice movement:The right thing and the right time.WashingtonLawReview, 85(2), 197-252.
Ader, C.R.(1995).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nda setting for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Journalismand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 72, 300-311.
Antilla, L.(2005).Climate of scepticism:US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 15(4), 338-352.doi:10.1016/j.gloenvcha.2005.08.003
Baskin, J.(2009).The impossible necessity of climate justice?.Melbourne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 10(2), 424-438.
Boykoff, M.T.& Boykoff, J.M.(2004).Balance as bias:global warming and the US prestige press.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 14(2), 125-136.doi:10.1016/j.gloenvcha.2003.10.001
Boykoff, M.T.& Boykoff, J.M.(2007).Climate change and journalistic norms:A case-study of US mass-media coverage.Geoforum, 38(6), 1190-1204.doi:10.1016/j.geoforum.2007.01.008
Boykoff, M.T.& Rajan, S.R.(2007).Signals and noise:Mass-media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the USA and the UK.EMBOReports, 8(3), 207-211.doi:10.1038/sj.embor.7400924
Boykoff, M.(2008).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discourse in UK tabloids,PoliticalGeography, 27(5), 549-569.
Boykoff, M.(2010).Indian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in a threatened journalistic ecosystem.ClimaticChange, 99(1), 17-25.doi:10.1007/s10584-010-9807-8
Brossard, D., Shanahan, J.& McComas, K.(2004).Are issue-cycles culturally constructed? A comparison of French and American coverage of global climate change.MassCommunication&Society, 7(3), 359-377.doi:10.1207/s15327 825mcs0703_6
Carvalho, A.& Burgess, J.(2005).Cultural circuits of climate change in U.K.broadsheet newspapers, 1985—2003.RiskAnalysis, 25(6), 1457-1469.doi:10.1111/j.1539-6924.2005.00692.x
Carvalho, A.& Pereira, E.(2009).Communicating climate change in Portugal:A critical analysis of journalism and beyond.In Carvalho, A.(Ed.),CommunicatingClimateChange:Discourses,MediationsandPerceptions(pp.126-156).Braga:Centro de Estudos de Comunicação e Sociedade, Universidade do Minhoo.
Cook, P.(2007).Public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greenhouse debate’.In Porter, J.M.& Phillips, P.W.B.(Eds.),PublicScienceinLiberalDemocrac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orbett, J.B.& Durfee, J.L.(2004).Testing public (Un)certainty of science: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global warming.ScienceCommunication, 26(2), 129-151.doi:10.1177/1075547004270234
Dawson, A.(2010).Climate justice:The emerging movement against green capitalism.SouthAtlanticQuarterly, 109(2), 313-338.doi:10.1215/00382876-2009-036
Dawson, A.(2013).Edward Said’s imaginative geographies and the struggle for climate justice.CollegeLiterature, 40(4), 33-51.doi:10.1353/lit.2013.0049de Onís, K.M.(2012).“Looking Both Ways”:Metaphor and the rhetorical alignment of intersectional climate justice and reproductive justice concerns.EnvironmentalCommunication, 6(3), 308-327.doi:10.1080/17524032.2012.690092
Dirikx, A.& Gelders, D.(2010).To frame is to explain:A deductive frame-analysis of Dutch and French climate change coverage during the annual UN conferences of the Parties.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19(6), 732-742.doi:10.1177/0963662509352044
Downs, A.(1972).Up and down with ecology:The “issue attention cycle”.PublicInterest, 28(1), 38-50.
Doyle, J.(2011).Acclimatizing nuclear? Climate change, nuclear power and the reframing of risk in the UK news media.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Gazette, 73(1-2), 107-125.doi:10.1177/1748048510386744
Eide, E.& Ytterstad, A.(2011).The tainted hero:Frames of domestication in Norwegian press representation of the Bali climate summit.TheInternationalJournalofPress/Politics, 16(1), 50-74.doi:10.1177/1940161210383420
SpecialEurobarometer 322.(2009).Europeans’ attitudes towards climate change.European Commission.
Good, J.E.(2008).The framing of climate change in Canadian, American and international newspapers:A media propaganda model analysis.CanadianJournalofCommunication, 33(2), 233-255.
Hargreaves, I., Lewis, J.& Speers, T.(2003).Towards a better map:Science, the public and the media.Swindon, UK: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Hart, P.S.(2011) One or many? The influence of episodic and thematic climate change frames on policy preferences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change.ScienceCommunication, 33(1), 28-51.
Ikeme, J.(2003).Equity,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sustainability:Incomplete approaches in climate change politics.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 13(3), 195-206.doi:10.1016/S0959-3780(03)00047-5
Kenix, L.J.(2008).Framing science:Climate change in the mainstream and alternative news of New Zealand.PoliticalScience, 60(1), 117-132.doi:10.1177/003231870806000110
Kingdon, J.(1995).Agendas,alternatives,andpublicpolicies(2nd, Ed.).New York:Longman.
Lockwood, A.(2010).Seeding doubt:how sceptics have used new media to delay action on climate change.Geopolitics,Histor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 2(2), 136-164.
Mark, S.C.J., Tindall, D.B.& Kelly, G.L.(2012).“Governments Have the Power”? Interpretations of climate change responsibility and solutions among Canadian environmentalists.OrganizationEnvironment, 25(1), 39-58.doi:10.1177/1086026612436979
McComas, K.& Shanahan, J.(1999).Telling stories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Measuring the impact of narratives on issue cycles.CommunicationResearch, 26(1), 30-57.doi:10.1177/009365099026001003
McIlwaine, S.(2013).Journalism, climate science and the public:towards better practices.InternationalJournalofMedia&CulturalPolitics, 9(1), 47-58.doi:10.1386/macp.9.1.47_1
Milanez, B.& Fonseca, I.F.(2012).Climate justice:framing a new discourse in Brazil.LocalEnvironment, 17(10), 1063-1073.doi:10.1080/13549839.2012.714757
Nelkin, D.(1987).The culture of science journalism.Society, 24(6), 17-25.doi:10.1007/BF02695570
Newell, P.(2006).Climateforchange:Non-stateactorsandtheglobalpoliticsofthegreenhous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Neill, S.J.(2013).Image matters:Climate change imagery in US, UK and Australian newspapers.Geoforum, 49, 10-19.doi:10.1016/j.geoforum.2013.04.030
Pasquaré, F.A.& Oppizzi, P.(2012).How do the media affect public percep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geohazards? An Italian case study.GlobalandPlanetaryChange, 90-91, 152-157.doi:10.1016/j.gloplacha.2011.05.010
Revkin, A.C.(2007).Climate change as news:challenges in communicating environmental science.In DiMento, J.F.C., & Doughman, P.(Eds.),Climatechange:Whatitmeansforus,ourchildren,andourgrandchildren(pp.139-160).Cambridge:The MIT Press.
Sampei, Y.& Aoyagi-Usui, M.(2009).Mass-media coverage, its influence on public awareness of climate-change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for Japan’s national campaign to reduc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GlobalEnvironmentalChange, 19(2), 203-212.doi:10.1016/j.gloenvcha.2008.10.005
Shanahan, J.& Good, J.(2000).Heat and hot air:influence of local temperature on journalists’ coverage of global warming.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9(3), 285-295.doi:10.1088/0963-6625/9/3/305
Sharples, D.M.(2010).Communicating climate science:Evaluating the UK public’s attitude to climate change.EarthandE-environment, 5, 185-205.
Stamm, K.R., Clark, F.& Eblacas, P.R.(2000).Mass communication and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the case of global warming.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9(3), 219-237.doi:10.1088/0963-6625/9/3/302
Takahashi, B.(2011).Framing and sources:a study of mass media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in Peru during the V ALCU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20(4), 543-557.doi:10.1177/0963662509356502
Trumbo, C.(1996).Constructing climate change:claims and frames in US news coverage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5(3), 269-283.doi:10.1088/0963-6625/5/3/006
Ungar, S.(1992).The rise and (relative) decline of global warming as a social problem.TheSociologicalQuarterly, 33(4), 483-501.doi:10.1111/j.1533-8525.1992.tb00139.x
Ungar, S.(2000).Knowledge, ignorance and the popular culture:climate change versus the ozone hol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9(3), 297-312.doi:10.1088/0963-6625/9/3/306
Weart, S.(2003).The Discovery of Rapid Climate Change.PhysicsToday, 56(8), 30-36.doi:10.1063/1.1611350
Weingart, P.(1998).Science and the media.ResearchPolicy, 27(8), 869-879.doi:10.1016/S0048-7333(98)00096-1
Wilson, K.M.(1995).Mass media as sources of global warming knowledge.MassCommunicationReview, 22, 75-89.Wilson, K.M.(2000).Drought, debate, and uncertainty:measuring reporters’ knowledge and ignorance about climate chang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9(1), 1-13.doi:10.1088/0963-6625/9/1/301
Zehr, S.C.(2000).Public representations of scientific uncertainty about global climate change.PublicUnderstandingofScience, 9(2), 85-103.doi:10.1088/0963-6625/9/2/301
(编辑:郭镇之)
O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Li Ji, Peiran Chen
(School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WuhanUniversit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cle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the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and to induce the transition of the research topics.Meanwhile, it indicates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on the coverage of climate change ignores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justice and the East-West
climate change; research on coverage; climate justice
1.纪莉: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2.陈沛然: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