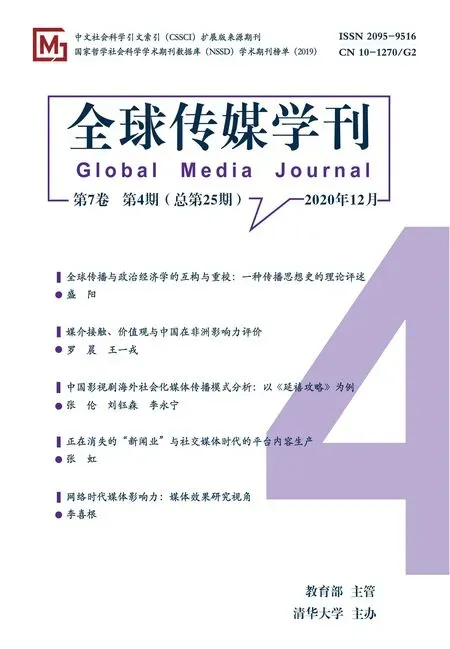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的国际制度基础
2016-08-03王明国
王明国
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的国际制度基础
王明国
重塑网络空间国际秩序是全球网络政治时代的核心议题。国际制度是国际秩序的主要组成要素,制度变迁反映了国际秩序的转型。现有网络空间秩序是互联网规范的演进产物,是国际制度扩散的客观体现,是国际法地位提升的重要领域。文章阐述了国际制度在原则规范、组织机构和法律条约层面的内涵,指出在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的关键时期,既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创建日益发挥重要作用,同时,美欧阵营与新兴阵营存在着严重的制度对立。中国需要积极发挥自身作用,推动建立新型互联网治理体系。
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转型;国际制度;全球治理
DOI 10.16602/j.gmj.20160036
网络空间是一个人为产生的全新领域。互联网的出现及其蓬勃发展日益改变并重塑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全球网络空间正改变着国际与国内、战争与和平、国家与非国家以及技术、政治和经济的原有区别,世界和平、繁荣和稳定受到网络空间关联度、内容及其认知的影响(Kremer & Müller, 2014)。在此背景下,网络空间秩序正在经历复杂的转型。
网络空间治理制度是网络空间秩序的主要支柱,是维系国际秩序有效运转和整体有序的重要保障。但是,各国在网络空间制度领域存在争论和分歧,网络空间的规范构成也不清晰,因此,网络空间国际秩序并不代表自动的和谐(Forsyth & Pope, 2014)。当前,西方国家通过对网络空间制度的主导,特别是规则制定权和议题引导力使得网络空间国际秩序体现了明显的西方霸权特征。对于网络空间制度构建而言,需要处理好主权国家参与的治理制度和私人行为体构建的治理制度间的平衡。当前,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突出表现在现有国际制度的改革和新兴国家创建各类新型会议机制。
制度存在着基础性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支撑了制度这一主体。美国斯坦福大学W.Richard Scott认为,制度包括为社会生活提供稳定和意义的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以及相关的活动与资源。制度具有多重的面相,是由符号性要素、社会活动和物质资源构成的持久社会结构(斯科特, 2010)。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要素处于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其中文化—认知要素是最深层次的要素。现有网络空间秩序是有关互联网原则与规范的演进产物,是国际机制与组织扩散的客观体现,是国际法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的现实反映。网络空间要构建共有的文化认同和身份,目前还比较困难。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从构建网络空间法律基础出发,逐步走向共有信念体系。另一方面,能否建立统一的网络空间全球法律仍然存在争论,这更反映了构建共有文化框架的困难。因而,本文认为网络空间国际秩序通常包括网络空间的原则规范、组织机构以及法律条约。只有明晰国际制度在原则规范、组织机构和法律条约三个层面的内涵,才能把握网络空间国际秩序转型的发展方向。
一、网络空间制度的规范基础
国际秩序具有主观性的理念特征。国际秩序与世界各国公认的、用来指导国际关系实践的各种行为准则和规范密不可分,而这些准则和规范并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潘忠岐,2015)。国际秩序研究尤其关注价值与规范,秩序不仅仅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状态或状况,它一般还被视为是一种价值。就其价值而言,国际秩序是为了保障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及各行为体和平相处的一种有序状态。这些价值包括维持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本身的生存,维护国家的独立,对和平的追求,对导致死亡或身体伤害的暴力行为加以限制,信守承诺,依据财产规则使所有权具有稳定性(布尔,2003)。
作为维持国际秩序运转的重要部分,国际制度同样具有规范和遵守的诉求,即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规范性制约,这体现了制度的“非中性”特征。制度规范的作用往往体现在维持国际秩序还是破坏国际秩序两个方面。在网络空间,制度规范表现在维持既有制度和变革既有制度两个方面,即维护现有治理制度的西方国家利益和变革现有制度的新兴国家利益。
网络空间现有国际制度的支配性规范主要体现了西方国家有关“互联网自由”和“开放性”的立场。长期以来,美国把谋求全球领导权作为基本的对外政策,而确立网络空间规范则是美国政府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维持全球领导地位的一项基本战略。美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是指推动和保护塑造全球性机制的管制性规范,如网络攻击、武力运用以及惩罚形式等,从而维护网络空间的构成性原则,即开放性(Kiggins,2014)。具体而言,这些规范包括保护个人隐私权、信息自由流动、言论自由和信息完整性等,试图通过支配性规范,传播美式价值观,把美国技术优势转化为霸权优势。
当前,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回归与重视是网络空间制度规范的重要转向。除联合国等主权国家政府间组织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增强之外,互联网名称和地址分配机构(ICANN)等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机制通过设置政府咨询委员会等形式构建起来与主权国家沟通协商的渠道。比如, ICANN近年来对主权原则进行重新审视。2005年,ICANN政府咨询委员会通过《关于国家代码顶级域名授权与管理的原则和指南》,相关国家代码顶级域名的最终公共政策机构取决于相关政府。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罗纳德·德贝特(Ronald J.Deibert)等人认为,全球互联网治理出现了一种所谓的“规范侵入”,即由互联网治理退回到传统的基于国家的信息控制模式。在网络空间,国家监管的最基本手段是互联网过滤或监控,以便预防跨越领土边界的在线信息泄露(Deibert & Crete-Nishihata,2012)。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60个国家已经实施互联网过滤,维护网络安全。主权规范受到重视与主权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长期努力密不可分。比如,国际电信联盟是推动网络空间主权原则和规范的重要推动力,时任国际电信联盟秘书长哈玛德·图埃甚至呼吁达成以国家为主导的网络空间军备控制条约,推动网络空间的再主权化。
网络空间规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重拾私人行为体在治理制度中的价值与地位。进入新世纪以来,联合国开始重视私人行为体在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作用。2003年,联大58/199号决议开始首次使用“攸关方”的概念。2010年,联合国信息安全政府专家组则首次提出网络合作的范围包括政府、私人行为体和市民社会,从而把市民社会作为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平等行为体。在美国,私人行为体日益和美国政府联系在一起,谷歌、微软、雅虎、韦伯森斯等互联网企业于2008年组建了“全球互联网倡议”(Global Network Initiative),试图维护言论自由和隐私。此外,很多非政府组织在网络空间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留声机工业国际联盟长期致力于从互联网上铲除非法MP3音乐文件。但是,非政府组织和私人公司的局限性有时也起到了负面的效果。比如,部分美国互联网企业可以充当政府的帮手,在政府的指使之下实施互联网审查、监管信息,阻碍合法信息或获取私人数据。
不过,网络规范在不同行为体看来具有不同的属性,导致互联网规范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比如,对于国家主体而言可能关注网络战争等安全议题,而经济领域的行为体更关注犯罪议题,市民社会组织更关注隐私权和互联网自由议题,对网络规范不同方面的关注会引发冲突(Finnemore,2011)。因此,作为行为体适当行为的集体预期,制度平台上的网络规范其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总体而言,网络空间规范是现实国际政治规范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补充。
二、网络空间制度的组织基础
国际制度与组织是网络空间秩序的支撑性力量。从国际秩序的演变来看,国际组织对于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的形成和维持具有重要的价值。当前,网络空间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在于由虚拟介质和数字空间引发的全球治理制度机构的重塑。
当前,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全面性的网络空间治理制度。当前,网络空间存在着联合国、ICANN、互联网治理论坛(IGF)、国际电信联盟(ITU)等不同治理制度。其中,ICANN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但其权力仅局限于域名和地址分配的管理方面。作为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在网络空间不具有绝对主导地位。不过,尽管没有单一的组织实施治理,但网络空间内还是存在着一套松散组合的规范与制度,它介于通过等级规范施加管理的综合制度与没有可识别的核心,且不存在相互联系的零散实践及制度之间(奈, 2012)。
网络空间治理与网络安全维护是联合国关注的重要方面。就网络空间治理而言,联大和国际电信联盟是国际社会讨论信息及互联网议题的最重要场所。就网络安全而言,联合国各个层面有关网络空间安全的内容涵盖了联合国裁军研究学会(UNIDIR)、联合国信息通讯技术促进发展世界联盟(UN-GAID)等。不过,联合国安理会对网络安全的介入仅限于联合国反恐任务实施力量任务组(CTITF)所属的反恐工作组,安理会迄今为止还没有涉及互联网安全的决议。截至目前,在联大有关决议中,仅有三份涉及网络空间安全的决议。就未来而言,在众多非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联大将在网络空间治理和网络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国际电信联盟在网络安全、互联网治理等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国际电信联盟拥有193个联合国成员,此外,还有超过700个私人企业和组织。2008年4月18日,国际电联电信标准化部门在约翰内斯堡会议上通过决议案,对网络安全进行了权威性界定(ITU, 2008)。2010年,墨西哥瓜达拉哈拉国际电信联盟会议通过181号决议,从互联网治理的角度确认了有关网络空间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有关信息通讯技术的信任建设之中(ITU, 2010)。
域名监管的功能和关键性互联网资源管理是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核心争论,这使得ICANN成为治理模式选择的争论议题。位于美国加州玛琳娜得瑞港的ICANN面临的挑战是如何选取一种治理方式,免于国家主权的羁绊,同时维持ICANN的独立并保证其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对于ICANN而言,这一挑战由来已久,至今仍未发现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由于顶级域名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同时,又具有重要的政治含义和道德特征,不少发展中国家往往把域名控制权与互联网监管和内容审查联系在一起,因而,国际社会对于美国的排他性控制一直处于质疑之中。
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ETF)、万维网联盟(W3C)以及互联网架构委员会(IAB)是网络空间技术治理的重要主体。1985年成立的国际互联网工程任务组和1994年成立的万维网联盟是互联网领域技术标准的主要制定者,也是民间社群和非政府组织在互联网治理领域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互联网标准原本只是技术性标准,但技术标准的发展演进却烙下明显的政治和经济印记。此外,互联网架构委员会的前身是1986 年美国政府建立的“互联网活动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互联网控制与配置委员会(ICCB)的继任者。简言之,互联网制度的建立源自西方国家并一直处于西方国家主导之下。
近年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网络空间治理制度,其中,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Global Commission on Internet Governance)、全球互联网合作与治理机制论坛(Panel on Global Internet Cooperation and Governance Mechanisms)是西方国家近年来新建立的互联网治理会议机制。全球互联网治理委员会由互联网治理倡议中心和英国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共同发起倡议,瑞典前任首相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任主席,致力于推动未来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的共同理解。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伊尔韦斯(Thomas Hendrik Ilves)则倡导成立全球互联网合作与治理机制论坛。与此同时,新兴国家尝试建立新型会议机制,试图增强新兴国家网络空间的话语权。其中,巴西召开的“互联网治理的未来——全球多利益相关方会议”(NETmundial)及之后创办的全球互联网治理联盟(the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Alliance),中国创办的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以及新兴国家创办的新兴国家互联网圆桌会议是比较有影响和代表性的新型互联网治理制度形式。
总之,在维护网络空间既有秩序还是推动网络空间秩序转型方面,国际组织都是支配性力量。有关网络空间治理的国际制度体系由机制倡议的多样性支配,目标是推动网络空间国际层面的合作并重新界定现有行为体发挥的作用。因而,国际制度与组织是网络空间秩序转型的基本载体。
三、网络空间制度的法律基础
当前,国际层面并不存在统一的网络空间国际法,但是一些互联网基本法律原则正在形成。国际社会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法是否存在、有无必要存在有着较激烈的争论。随着网络恐怖主义、网络攻击等网络空间安全形势的日益恶化,国际社会越来越希望能够在全球层面通过立法的形式规范网络空间秩序,构建网络安全法律。与国际公法基本原则相一致的是,网络空间的基本国际法原则包括网络主权原则、不干涉内政原则、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以及国际合作原则。
不过,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对现有国际法提出了新的挑战。挑战的核心在于属地管辖与互联网自由这两个冲突原则,这突出地体现在互联网纷争与冲突对传统中立原则和区分原则的影响。就中立原则而言,由于网络攻击路线经由中立的第三国,第三国是否具有采取应对措施的权利;就区分原则而言,由于互联网匿名性等方面的特征,导致平民和战斗人员之间、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之间的区分比较困难(王孔祥, 2015)。当前,互联网治理迫切需要国际法的一个重要依据在于网络攻击行为对于普通民众可能造成日益严重的物质、隐私等方面的危害。
当前,欧洲在网络空间立法方面走在了前列。网络犯罪具有虚拟性、专业性、扩散性和高效益性的特征,欧盟通过缔结《网络犯罪公约》试图对此进行规范。不过,该公约对网络犯罪圈划定范围过大,无法找到保障人权和打击网络犯罪的最佳平衡,以及网络犯罪管辖权模糊等方面的弊端受到指责。总体而言,网络空间权威扩散和网络安全治理不断增长的需求之间鸿沟扩大,显示出国际层面网络安全原则与规范的潜在冲突。
主权国家在网络空间行使的管辖权及网络主权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的核心。出于对西方国家在互联网技术领域处于绝对领先的警惕,发展中国家亟须通过互联网领域的国际立法维护国家网络主权。长期以来,俄罗斯致力于推动网络立法和网络军控。早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就希望能够与美国达成了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法规,避免在互联网空间中形成军备竞赛。2005年,联合国大会以177∶1的绝对票通过了俄罗斯提出的网络军控议案,但美国投了反对票。不过,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对网络空间国际立法发生了较明显的政策转型,这尤其体现在美国对联合国的平台作用及功效的评价。2010年7月,包括美、俄、中国在内的15国网络安全专家向联合国秘书长递交了就达成全球网络安全条约进行谈判的建议,以便推动更广范围的国际合作。新兴国家能够与美国在联合国层面进行有效磋商这本身就反映了美国立场的转变。
总之,法律条约在网络空间制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法律为权威机构解释网络空间规则并运用规则提供了行动指南,而条约是网络空间行为主体缔结的确立其相互权利和义务的书面协议。当前,越来越多的行为体意识到国际合作同样适用于网络空间法律制定和条约缔结。不过,网络空间制度的法律基础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美欧阵营与新兴阵营在网络空间的制度博弈
“数字鸿沟”是全球网络政治时代的基本特征,是影响国际秩序转型和重构的基本因素。“数字鸿沟”体现在构建网络空间的物理层面、逻辑层面和应用层面三个方面,发达国家在这三个方面均占据显著的主导地位。自互联网诞生之日起,美国政府就一直处于主导地位,但发达国家往往对日益严重的“数字鸿沟”视而不见。发达国家对“数字鸿沟”的忽视源于其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技术乐观主义。不过,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到2020年,世界上将有超过20亿用户使用互联网,其中90%的用户属于发展中国家,这显示出非西方世界在网络空间的崛起,进而导致网络空间显现出美欧阵营和新兴阵营之间的复杂博弈。可以说,网络空间力量对比正在出现明显的西降东升,网络空间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迁。
当前,国际社会对互联网治理机制的关注主要围绕着ICANN、ITU以及IGF,它们是不同治理主体在互联网领域施加影响的重要平台。其中,最能反映双方阵营博弈程度的是美欧阵营倚重的ICANN和新兴阵营支持的联合国两个制度平台层面上的对抗。
域名系统的监管权是近年来美欧阵营与新兴阵营争论的焦点。自1983年域名系统建立至今,域名数目已突破2亿7千万个,且域名分配构成了重要的战略资产。随着域名数量的快速增加,与域名相关的议题不断出现,域名安全漏洞在整个系统中不断出现。长期以来,域名系统一直处于美国政府的控制之下。美国商务部与ICANN在1998年签署了协议,美国对ICANN的控制由直接监管转为间接操纵。近年来,在新兴国家的改革呼吁下,ICANN出现了较明显的离心倾向。斯诺登事件后,为了平息国际社会对美国监听丑闻的愤怒,奥巴马行政当局决定放弃ICANN的监管权。乔纳森·齐特林(Jonathan Zittrain)则从ICANN的职能出发认为,由于ICANN自身并不掌管域名而不对无视或践踏舆论负责,美国则需要对此承担责任,为此,美国与ICANN签署的协议最终将予以解除(Zittrain, 2014)。不过,美国放弃监管权是一系列复杂因素作用的产物。美国的支配性权力并不是决定性的影响因素,单一根区权威、退出成本、ICANN的历史作用以及ICANN对于政府施加压力的应对措施,这些混合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能否获取关键性根区文件(Goldsmith, 2015)。2016年10月1日,美国政府与ICANN签订的职能合同正式到期失效,美国政府放弃互联网数字分配机构职能的管理权,将其移交给全球多利益相关方。
不过,美国为此次移交设置了条件,即不会把监管权移交给政府间国际组织。同时,美国也会通过其他途径对ICANN施加影响。因而,美国不会放弃网络空间的主导权。瑞恩·希金斯(Ryan Kiggins)认为美国政府把互联网定位为一个全球商业和自由主义扩张的平台,这是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金斯, 2013)。美国在网络空间议题设置、规则运作以及规则解释和再解释等方面享有重要的制度性话语权。此外,域名分配还受到技术更新速度快的影响,面临着网络中立性和宽带竞争方面的争论,特别是互联网协议4(IPv4)被互联网协议6(IPv6)所取代。当前,围绕技术层面的治理主要集中于IPv4的耗尽,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如何管理现有的地址并分配尚未使用的包括IPv6在内的地址,是事关网络空间政治版图演变的重要领域。
联合国大会尽管不是互联网治理的主要平台,但基于合法性的政治考量,美欧阵营和新兴阵营在此领域均开展了比较激烈的制度性话语权较量。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曾于2011年向第66届联大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推动解决信息交流技术扩展背景下的网络安全与稳定问题。2015年1月9日,6国再次联名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共同提交“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更新草案,作为第69届联大正式文件散发,呼吁各国以联合国为治理平台,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规则。草案通过联合国大会层面采取行动,是全球互联网治理中的新进程和权力安排方式,反映出中俄与西方国家在互联网如何治理方面的基本分歧(Nocetti, 2015)。总体上,美国对于联合国大会的相关决议,特别是俄罗斯牵头提出的决议草案均持反对立场。
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国际电信联盟是美欧阵营和新兴阵营较量的另一个重要场所。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电信联盟试图在互联网治理和程序规则制定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2014年国际电信联盟釜山会议上,俄罗斯提出国际电信联盟应该分配IP地址,而在此之前,IP地址分配由国际非政府组织负责。印度在国际电信联盟釜山会议上建议,互联网运作需进行一些重大改变,维持国家边界内的互联网通畅、民众可以通过电话式的国际电话区号获取国际互联网信息。在釜山会议的闭门磋商会上,美国放弃了国际电联委员会工作组应包括非政府组织的要求,作为回报,发展中国家撤回了有关在线隐私权、网络安全和其他互联网建议。可以说,此次会议的结果是双方反复博弈的产物。
互联网治理论坛也是联合国下属的互联网治理机构,同样反映出双方在治理制度方面的深刻分歧。互联网治理论坛既是国际社会不满美国单独主导互联网域名管理权的产物,也是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西方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软性制度组织中的长期争论导致其日益沦落成不具有权威性的论坛场所。
由于多边机制存在的纷争,美国转而倚重与西方盟国共同推动网络空间多利益攸关方治理进程,通过志同道合的治理联盟维持美欧阵营的主导地位。2015年4月17日,美国国防部公布了最新版的《美国国防部网络空间战略》(theDepartmentofDefenseCyberStrategy)。报告关注美国盟国和伙伴在防御和阻止网络攻击方面的作用,并特别提及了北约、中东和亚太主要盟国应更多地朝着这一方向努力。2015年4月,第13次美欧信息社会对话(Information Society Dialogue)在布鲁塞尔举行。在互联网治理上,美欧强调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利益攸关的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性,支持IGF作为讨论互联网核心一体化和互联网发展的有价值的、全球性的、多利益攸关方的治理平台。不过,应该看到互联网治理的多利益攸关方治理模式本质上是维持美式自由与互联网开放。
但是,美国通过建立国际制度网络加强了自身在国际社会影响力的同时,其国家利益的实现也高度依赖于其对国际规则制定权的主导以及这些规则的实施效果(高程, 2013)。对于美国而言,在网络空间长期追求一种领导战略,运用强大的软实力影响、支配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是,美国并非一种利他或仁慈的霸权。本质上,所谓的领导战略无非是美国在集体霸权的幌子下追求自身霸权罢了。
在网络空间秩序转型中,新兴阵营坚持互联网治理的国家中心原则。具体而言,坚持有关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国家主权观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网络空间是与国家物理边界相对应的虚拟边界,发展中国家希望把国家治理的条约法规延伸到网络空间。俄罗斯是新兴阵营的重要成员,也是改革现有互联网治理机制的首倡者。现有互联网治理机制与俄罗斯偏好存在两方面的冲突,一方面,早期互联网发展的非国有化遗产对互联网运作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规范产生强有力影响,但俄罗斯坚持互联网的“数字韦斯特伐利亚体系”,主权国家对在线空间拥有控制权,使其从网络间系统转向政府间系统;另一方面,美国在互联网治理领域的特权,特别是对ICANN的控制,与俄罗斯坚持网络主权的原则立场存在冲突。简而言之,俄罗斯对互联网的非国家化自由主义和美国的网络主导权心存担忧,俄罗斯有必要阻止“互联网弗兰肯斯坦问题”(Nocetti, 2015)。为此,俄罗斯支持联合国作为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平台。此外,俄罗斯在上海合作组织、集体安全组织、金砖国家等国际机构中纳入互联网相关议题,推动跨区域和地区组织在互联网治理进程中发挥作用。
总之,美欧国家与新兴国家当前围绕互联网全球治理的争论主要体现在如下五个方面:根区文件冲突升级、主权国家对互联网治理中可选择性安排的推动、网络技术架构间的冲突、互联网治理架构取得政治经济目标的共同选项、合法性话语与制度设计尝试。国际层面的这些纷争导致了原本亟须国际制度保障的网络空间建章立制进程成效不彰。
五、结束语
就未来而言,网络空间秩序由高度中心化和等级化逐步转向非中心化和多极化。美国与中俄等国在网络空间制度中的行为及其国际协商进程,对网络空间秩序的未来演进具有深远的含义。尤其是,中美两国对网络空间全球治理的发展演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美两国在互联网治理的理念、措施和后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在政治、经济和外交等多层面不断放大。本质上,中美两国在网络空间的分歧与冲突是两国长期战略互信缺失和现实政治结构性冲突在网络空间的反映与延伸。当前,中美网络空间博弈保持着“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的关系,全球网络空间政治中的中美关系既不是完全竞争性的也非完全合作性的,二者处于合作性竞争之中(沈大伟, 2015)。网络空间中美关系的未来将呈现合作、竞争和冲突共存的特点,这三种情况之间的平衡取决于这两个国家对自身国家利益的定义和优先考量、寻求共同目标并推进这些目标的能力以及处理利益和价值观分歧的水平。
总之,中美网络空间竞争是两国在现实政治中结构性矛盾、战略互信不足以及意识形态冲突与差异的反映。就网络空间中美关系而言,需要双方通过双边和多边制度平台建设,增信释疑,夯实战略共识的基础,而国际制度提供了一条构建中美网络空间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路径。当前,网络空间秩序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要成为网络空间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现有网络空间制度建设进程,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制度重构战略。当前,尤其需要思考乌镇峰会的逐步制度化议题,评估其从论坛场所转向正式化治理制度组织的可能性,探索如何将乌镇峰会的国际倡议和共识转化为有约束力的规范。总之,中国应坚持现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建设两条路径推进互联网国际制度建设,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
高程(2013):从规则视角看美国重构国际秩序的战略调整,《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2期, 81-97页。
赫德利·布尔(2003):《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原书Bull, H.[1977].Theanarchicalsociety:Astudyoforderinworldpolitics.London:Macmillan.)
潘忠岐(2015):《国际政治学理论解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瑞恩·希金斯(2013):美国互联网的身份认同、安全与监管。[美]肖恩·柯斯蒂根、杰克·佩里(编):《赛博空间与全球事务》(饶岚,梁玥等译),248-266页,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原书Costigan, S.S.& Perry, J.[Eds.][2012].Cyberspaceandglobalaffairs.UK:Ashgate Publishing, Ltd.)
沈大伟(编)(2015):《纠缠的大国:中美关系的未来》(丁超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原书Shambaugh, D.[Ed.][2012].Tangledtitans:TheUnitedStatesandChina.Lanham, MD:Rowman & Littlefield.)
W·理查德·斯科特(2010):《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原书Scott, W.R.[2001].Institutionsandorganizations:Ideasandinterests.Thousand Oak, CA:Sage.)
王孔祥(2015):《互联网治理中的国际法》,北京:法律出版社。
约瑟夫·奈(2012):《权力大未来》(王吉美译),北京:中信出版社。(原书Nye, J.S.[2011].Thefutureofpower.New York:Public Affairs Press.)
Deibert, R.J.& Grete, N.M.(2012).Global governance and the spread of cyberspace controls.GlobalGovernance, 18, 339-361.
Finnemore, M.(2011).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cyber norms in America’s cyber future:security and prosperity in the information age.Retrieved fromhttp://citizenlab.org/cybernorms2011/cultivating.pdf
Forsyth, J.W., Jr.& Pope, M.B.E.(2014).Structural causes and cyber effects:why international order is inevitable in cyberspace.StrategicStudiesQuarterly, 8(4), 112-128.
Goldsmith, J.(2015).The tricky issue of severing US “control” over ICANN.Retrieved fromhttp://www.hoover.org/research/tricky-issue-severing-us-control-over-icann
ITU.(2008).Overviewofcybersecurity.Retrieved fromhttps://www.itu.int/rec/dologin_pub.asp?lang=e&id=T-REC-X.1205-200804-I!!PDF-E&type=items
ITU.(2010).Definitions and terminology relating to building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Retrieved fromhttps://www.itu.int/osg/csd/cybersecurity/WSIS/RESOLUTION_181.pdf
Kiggins, R.D.(2014).US leadership in cyberspace:transnational cyber security and global governance.In Kremer, J.F.& Müller, B.(Eds.),Cyberspa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rospectsandchallenges(pp.161-180).London:Springer.doi:10.1007/978-3-642-37481-4_10
Kremer, J.F.& Müller, B.(Eds.)(2014).Cyberspace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Theory,prospectsandchallenges.Berlin Heidelberg:Springer.
Nocetti, J.(2015).Contest and conquest:Russia and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InternationalAffairs, 91(1), 111-130, doi:10.1111/1468-2346.12189.
Zittrain, J.(2014).No,BarackObamaisn’thandingcontroloftheinternetovertoChina:ThemisguidedfreakoutoverICANN.Retrieved from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17093/us-withdraws-icann-why-its-no-big-deal
(编辑:卢嘉)
The Founda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of Cyberspace Order Transformation
Mingguo Wang
(LawSchool,theShanghaiUniversityofInternationalBusinessandEconomics)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of cyberspace is the core issue of the global network politics.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is the main compon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reflects the trans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order.The existing cyberspace order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norm of internet, an objective embodiment of the diffus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promotion of the status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The article expound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norm, organization and legal aspects.I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the cyberspace order transition, both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Meanwhile, Euro-American camp and emerging countries camp have serious institutional oppositions.China needs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et governance system.
cyberspace; international order; transformati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global governance
王明国: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