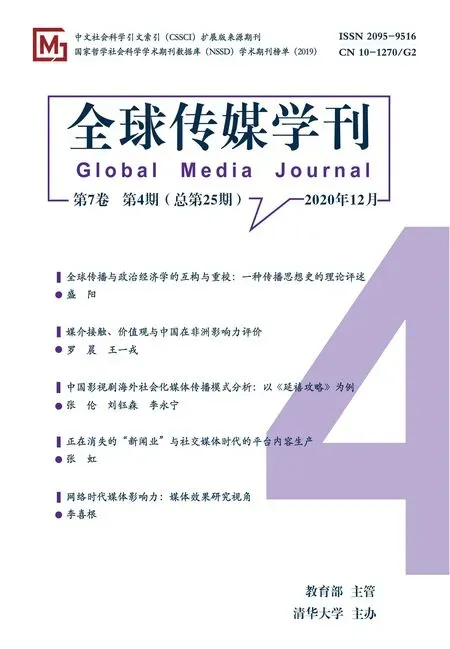全球媒介变革与意识形态安全
2016-08-03田丽
田 丽
全球媒介变革与意识形态安全
田 丽
媒体是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新闻是人类信息系统的重要元素。近年来,传媒行业风起云涌,传播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的意识形态再生产过程受到冲击与挑战。本文揭示了技术与商业模式推动下媒体变革和传播转型的现象,并分析了其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新媒体;网络传播;意识形态
DOI 10.16602/j.gmj.20160037
媒体是建构意识形态的重要工具,新闻是人类信息系统的重要元素。当前,技术与商业的联姻推动着媒介生态的改变。互联网原生新媒体异军突起,科技巨头入侵新闻业,传媒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新闻生产方式和产品形态发生蜕变;信息的跨境流动和全球传播日趋常态,受众从被动消费转向参与生产与传播,社群与小众文化逐步兴起。然而,与媒介生态与传播方式剧烈变革相适应的制度尚未建立。互联网对传统意识形态再造系统带来冲击与挑战,因此,近年来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一、传媒行业变革
近年来,传媒行业风起云涌,一方面是网络新媒体的发展势如破竹、如火如荼,另一方面是传统媒体的举步维艰、砥砺前行。互联网科技巨头们凭借资本与市场优势,以用户价值对冲内容价值,形成对传媒业步步紧逼之势头。互联网不仅在技术层面改造着媒介环境,而且以开放、共享、参与、协作的思维方式催生出众筹、众包等新闻形式。
1.科技巨头入侵新闻业
201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重量级的互联网公司,不论硬件设备生产商还是软件公司争相向新闻业扩张。5月13日,脸谱(Facebook)推出Instant Articles 功能,新闻业者可以直接在Facebook上发布新闻,而不是像之前那样仅能发送原文链接;6月8日,苹果推出聚合类网络应用“News”;谷歌(Google)在既有的“新闻实验室”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新闻业靠拢,联合推特(Twitter)推出了移动即时新闻应用“Instant news”。①互联网公司进军新闻业并不是直接从事新闻采编业务,而是提供新闻再加工或者新闻整合服务,因此通常采用与传统媒体合作的方式。传统媒体虽然并不情愿把内容提供给这些互联网公司主导的新媒体平台,但是又非常清楚经由这些平台传播的内容会获得更大的关注度。而这些互联网公司也纷纷推出广告分成政策,吸引传统媒体的进入。截至2015年9月,苹果旗下的Apple News已经吸引了包括纽约时报、路透社、CNN等在内的50多家全球一流媒体进入。庞大的用户量是互联网公司与传统媒体议价的核心能力,并通过这种合作解决了平台内容匮乏的问题,进一步提升了用户体验,巩固了优势地位。2016年第一季度,脸谱的月活跃用户数量达到16.5亿,谷歌移动版Chrome浏览器的月活跃用户数也突破10亿,互联网巨头利用用户价值换取了传统媒体的优质内容。
2.传统媒体进一步势微
2015年,中国报纸零售总量较上一年下降了41.14%,都市报类下降幅度则超过50%,电视广告的投放量也首次下降;②相比之下,中国互联网广告收入超过2000亿元,同比增长35.9%。资本市场方面,互联网原生产品高歌猛进,继BuzzFeed估值突破15亿美元后,VICE突破了20亿美元的媒体网站估值天花板,达到25亿美元。相比之下,传统媒体与之并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拥有140年历史的《华盛顿邮报》估值仅为2.5亿美元。与此同时,传统媒介集团纷纷将资本投向数字媒介市场。从2014年9月到2015年9月,包括康卡斯特、时代华纳、贝塔斯曼在内的资本方,向数字媒体领域投入近8亿美元资金。国内在媒介融合发展方面具有旗帜下意义的浙江报业集团也把网络游戏作为重要的投资领域。
3.媒介与其他产业边界模糊
互联网是重要的新媒体平台,但它不仅是媒体,还是一个集信息发布、信息交互、信息利用、信息交易于一体的平台。因此,随着新媒体业务范围的拓展,媒介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边界日渐模糊。“自媒体内容生产+社群电商消费”造就的“网红经济”是2016年中国互联网产业典型的商业模式,也是传媒业与其他业态混合发展的典型代表。此外,媒介产业内部产业链和生产要素不断重组,上下游混业发展越来越多,在国外,Netflix宣布将在原创内容制作方面投入30亿美元;在国内,腾讯公司成立了“企鹅影业”,进军网络剧、电影投资和艺人经济。
4.新闻生产与产品蜕变
作为传媒业的核心,新闻业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的推动下也悄然蜕变。移动化、视频化以及网络直播成为新的消费方式。截至 2016 年 6 月,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6.56 亿,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达到 5.18 亿。③仅以2015年“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大阅兵为例,腾讯启动网络互动直播,一日内阅兵视频点击量超过2亿,仅直播中用户数就超过2543万,其中移动用户占比接近80%。不仅在中国,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美国新闻媒体状态》报告:在50个最受欢迎的新闻网站中,有39个网站的移动端流量大于桌面端;超过七成的美国人在手机上看视频。移动新闻消费通常在通勤、等待、休闲等情景下伴随性地发生,为适应情景阅读需要,越来越碎片化。
以虚拟现实技术、无人机航拍为代表的硬件创新拓展了认知边界和新闻形式,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虚拟现实使“新闻更有力度”;而无人机航拍在天津爆炸案和“最牛违建”的报道中都显示出巨大的优势。机器人新闻把算法运用于写作、审核并指导传播,大数据被广泛用于对受众兴趣的研究和挖掘中,“算法分布”使新闻越来越个性化、智能化。最早开启与人工智能合作,让机器人参与写作的美联社,稿件的速度和质量都产生了质的飞跃。互联网思维开启新闻众筹和众包的新模式,使新闻生产不仅是媒体的活动,普通公众参与到新闻选题、策划以及生产全过程中。在国外,《卫报》开启众包新闻之先河,BBC、《纽约时报》等积极参与众包新闻网站的建设,众包新闻网站Reddit已经被提升到主流媒体的地位。尽管在技术、规制和新闻伦理层面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商榷,但新闻业的这些蜕变着实影响着社会信息与舆论环境。
二、传播方式转型
媒介生态的改变,影响着传播方式的转型。新媒体时代人们对网络传播“去中心化”“平等”“时空无限”“匿名”的认识逐步深化,对传播的转向形成新的认识。
1.被动接受与主动传播
信息过剩的年代,新闻信息接收与传播的方式发生逆转,从主动获取、被动传播转变为被动接受与积极扩散。个性化推送的形成、社交平台的发展,建构了人们获取新闻信息的新环境,人们越来越倚重机器或者社交圈推送的信息;另一方面,受众越来越不满足于成为一个被动的信息接受者,而是通过内容再生产和信息再扩散的方式形成对媒介产品的二次创作和自我扩散。网络中的各种段子,恶搞的视频、图片,以及流行的表情包都是网民参与的表现。弹幕就是最好的例证,网民一边消费视频内容,一边把自己的评论与观感反馈到产品中,构成了他人消费的内容。网民不仅参与生产,还参与到扩散当中。以美国为例,半数网民在一个月内通过脸书和推特转发新闻。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将用户通过网络连接、表达、协作、扩散的方式参与到媒介产品的再生产和传播的过程定义为“参与式文化”(Jenkins,1992)。
2.社会互动与圈层传播
社交媒体是以用户产生内容为核心,以关系传播为主要特征。社交媒体参与信息传播,使“一点上网,全网共享”的传播模式,逐步过渡演变为基于社交网络的多级扩散过程。社交媒体促进了同业、同趣、同好、同学等社交圈和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圈子内部信息的共享与流动性强,大众传播转变为以圈子为基本单位的“圈层扩散模式”。圈子之间的信息流动受到信息类型的影响,对立性的圈子之间理性沟通越来越难,每个人都因身处一定的“圈子”而受到鼓舞,不再担心被排斥,因此更加信己而排斥异见。
3.社群动力与小众文化
社交媒体为社群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契机,推动媒介文化从大众媒体时代追求的公共文化向群体文化、小众文化、亚文化转变。社群网站通过建构会员关系,推拉并举,分享情感和经历,满足会员的社交、互动与价值感需求,逐步建立起社群意识。社群意识对成员形成约束力和向心力,影响着会员的态度和行为。由于社群往往基于群体对某种“同质”性文化的追求,因而使得群体增加了这种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主流文化对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网络的开放性增加了这些文化的表现机会;网络传播的无限性提升了消费群体“长尾”的覆盖范围,从而刺激了此类文化的生命力。因此,服务于共同价值观、共同利益诉求、共同兴趣爱好、共同服务需求的垂直化、社群化的媒体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例如,弹幕网站、电竞直播、读书社区、网红电商等,这些媒体通过经营社群,拥有庞大的粉丝群,依赖粉丝的追捧刺激了非理性消费,形成粉丝经济。
三、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
媒介变革和传播转向,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不可控因素被带入再生产过程。然而,目前,我国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仍旧是工业化的产物,意识形态管理行政划分和“流水线”式分类,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和手段在新环境下力不从心。
1.在意识形态再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媒体力量越来越薄弱
传统媒体,尤其是体制内的传统媒体是我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重要力量,是弘扬正能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渠道。但是,随着传媒环境的改变,全球范围内传统媒体进入冰河期,无论在产品市场、广告市场还是资本市场都难以与新媒体匹敌。传统媒体的颓势正在从纸质媒体向广电媒体拓展,影响力的式微也在从主流人群向边缘群体扩散。传统媒体力量的削弱制约了意识形态的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此问题,把互联网等新媒体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定位于主渠道、主力军和主阵地,并积极推进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然而在实践中,媒体融合发展物理变化多、化学反应少,加法多、减法少,新媒体的作用仅仅局限于传播渠道的拓展,而落后的媒体生产力不能有效退出市场,在媒体内部,传统业务依旧是核心,人力、物力、财力难以向新媒体倾斜。
2.意识形态再生产如何吸纳新媒体激发的新生力量有待探索
新媒体促进了网民力量的崛起,社群活动积极,巨头互联网公司地位显赫,但是如何积极有效地吸纳并引导这些力量服务于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和发展正在考验管理者的能力与智慧。传统媒介环境下,媒体掌握着话语权,媒体说什么,受众就接受什么,因此管住有限的媒体,就管好了内容。现在,网民积极参与内容生产,不注重意识形态建设的方式方法就会引发“吐槽”“戏谑”等负面效应。互联网公司作为商业企业的天然逐利性,不会主动承担维护和传播主流价值的责任。值得欣慰的是中央已经做了新的理论探索。2016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网络群众路线”“线上新下同心圆”等理论,并大力倡导互联网公司履行社会责任,旨在弥补这一漏洞。
3.新闻业的蜕变消减凝聚共识的力量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1983)一书中,揭示了大众传媒制造的共识在国家和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新媒体时代的新闻业朝着碎片化、个性化、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个体或小群体对信息取舍的控制力增强,新闻信息在不同群体中有不同内容和不同重要程度的呈现,这一趋势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共识的削弱。没有共同的认识就难以产生共同的意识,最终危害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与此同时,新闻的“圈层传播”和“社交扩散”加剧了社会隔离,甚至助长了意识形态极端化。传播学中的“选择性接触理论”在新媒体时代依旧成立,由于人们总是倾向于选择与自己立场一致或相近的内容,基于算法推送的个性新闻最终让你陷入“同类”包围中,在群体影响下,越发坚持己见,而排斥异见。反观现实,就不难理解无论是宗教极端思想还是各种思潮在新媒体时代能够萌发出更大活力的原因。众筹与众包新闻把新闻的专业性、导向性向大众性、社会性让渡,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成为难免的议题,对于意识形态风险较大的国家而言是不小的挑战。
4.功能强大的新媒体平台国际化拓展将意识形态建设植于全球背景。
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新闻与媒体,还包括教育、文化等方面,目前发展越来越全面的新媒体平台在这些方面的应用和功能也越来越丰富,以至于新媒体平台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逐步超越了新闻与舆论,渗透到教育、文化、社会规范等多个领域。伴随着新媒体平台国际化,意识形态建设也随之被置于全球化背景中。意识形态建设的任务不仅包括自我再生产,还包含融入跨文化环境和抵御敌对意识入侵,即与意识形态作斗争的任务。以维基百科为例,目前它已经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是有研究表明,由于维基百科的建设和维护者主要是西方网民,在很多历史性或社会性词条的解释上就存在着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歧。
5.新媒体自生的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蚀作用
互联网的开放、去中心化结构特征衍生出“草根性”与“反权威”的网络文化,使“全民狂欢”和“草根民主”获得合法性。在狂欢中,网民解构了医生、律师、教授等专业群体,并表现出对传统政治的不信任,用草根民主的方式表达参与意愿。这一现象在西方选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充分,“草根”英雄更容易胜选,而英国在脱欧政策上的选举结果更是有力的证明。事实上,选举是民主的形式,民主的本质是反映民心,民心是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当选举被非理性操纵,选举结果不能再反映民心时,也就是民主制度面临失败的时刻。此外,垂直性、社群性媒体发展与亚文化传播形成互动机制。借助粉丝和社群,并通过与主流文化的对话与对抗,亚文化在提升存在感。亚文化对于建构文化多样性有积极意义,但是也不乏消极、颓废的文化形态,还有一些文化形态本不适于大众传播,却通过新媒体走向台前,从而产生了负面效果。
注释
① 所选用案例来源自腾讯传媒研究的《众媒时代》一书。
② 数据来源自崔保国主编的《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
③ 数据来源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崔保国(2016):《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腾讯传媒研究(2016):《众媒时代》,上海:中信出版社。
Anderson, B.(1983).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New York:Verso Books.
Jenkins, H.(1992).Textualpoachers:Televisionfansandparticipatoryculture.New York:Routledge.
(编辑:卢嘉)
Global Media Revolution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Li Tian
(SchoolofNewMedia,PekingUniversity)
Media is a crucial tool for constructing ideology, while journalism is a significant element of human information system.During recent years, media industry surged through huge waves of revolution, since communication pattern has changed profoundly.Traditional reproduction process of ideology has also been shocked and challenged.This article aims at analyzing the current phenomena of media revolution and communication’s paradigm-shift driven by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as well as discussing its influences upon the safety of ideology.
new media; internet communication; ideology
田丽: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