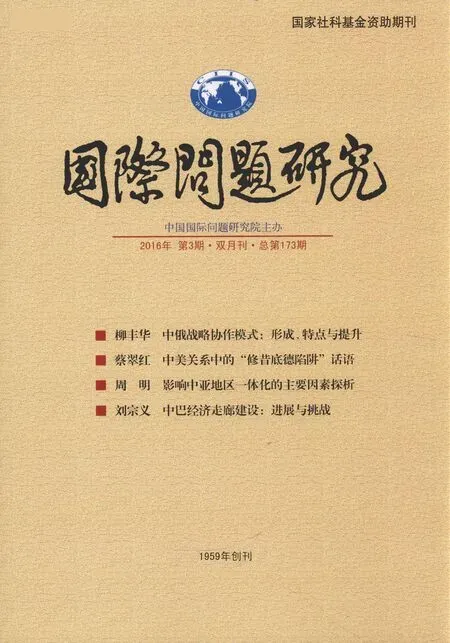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
2016-07-14蔡翠红
蔡翠红
中美关系中的“修昔底德陷阱”话语*
蔡翠红
〔提 要〕 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频繁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描述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这种历史类比存在明显的误导性,它忽视了一些保障中美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包括:在全球层面,复合相互依赖的国际环境、集体安全机制的日益刚性化、历史上战争的苦难经验;在双边层面,中美在经济相互依赖和全球治理议题等方面的“结构性共同利益”、战略竞争的“社会进化式”发展以及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此外,当前网络时代伴随的整体思维、外交透明度,以及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也是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保障。将“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与中美关系相关联对中美关系、地区形势以及世界局势都有危害,应全力避免。
〔关 键 词〕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权力转移、安全困境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修昔底德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对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战争原因的描述,认为“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修昔底德认为,一个崛起大国与既有统治霸主的竞争多数会以战争告终。换言之,“修昔底德陷阱”是指新崛起大国必然会挑战现有主导性大国,而现有主导性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从而导致战争不可避免。[2]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习近平关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构想解析”,《人民论坛》2014月2月20日。
“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关系中的应用因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太平洋地区已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而逐步成为一个显性化概念。[3]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c,” Financial Times,August 21, 2012, http://www.ft.com/intl/cms/s/0/5d695b5a-ead3-11e1-984b-00144feab49a. html#axzz3tMOTUiDh.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然而,修昔底德当年提出的这个用以阐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战争的概念是否可以应用到如今的中美关系中,以及应用过程中存在哪些错位理解等,都成为了我们应认真思考的问题。唯有将这些问题搞清楚,才能避免盲目将“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扩大化,并错误应用到中美关系中而危害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倾向。本文即循着这一思路,从全球层面、中美双边关系层面并结合网络时代特点分析“修昔底德陷阱”在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应用问题,避免这一概念成为中美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绊脚石。
一、“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扩大化倾向
对中美关系的讨论在2015年似乎集体出现了悲观倾向。4月,艾利森在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援引“修昔底德陷阱”并汇报其发现:“过去500年中,在崛起中国家挑战占统治地位大国的16个例子中,有12个的结果是战争。”[4]“Opening Statement by Dr. Graham T. Allison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at a Hearing Convened to Discuss ‘China, The US, and the Asia-Pacifc’,” April 14, 2015, http://www.armed-services.senate.gov/imo/media/doc/Allison_04-14-15.pdf.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2日)5月,美国学者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在世界中国学论坛美国分论坛上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中美关系正逼近临界点”,认为“以积极为主的美中关系的一些关键的根本性支撑受到侵蚀”。[1]David M. Lampton, “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 speech given at the conference “China’s Reform: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May 6-7, 2015, US-China Perception Мonitor, 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上网时间:2015年11月12日)6月,另一美国学者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香港美国商会午餐会的主题演讲中认为中美关系持续恶化,两国关系“越来越难达至平衡”。[2]David Shambaugh, “US-China Relations: Where to from Here?” June 15, 2015, http://www. amcham.org.hk/events/eventdetail/2206/-/us-china-relations-where-to-from-here. (上网时间:2015 年11月12日)9月底习主席访美时,艾利森再次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文章“修昔底德陷阱:美国和中国在走向战争吗?”,认为习奥会议程中不会包括这个话题,即“美国和中国发现它们在下一个十年,处于一场战争之中的可能性”。[3]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А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5/09/united-stateschina-war-thucydides-trap/406756/. (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一些学术会议也专门对此进行探讨,例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专门举行了“权力转移与亚太地区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学术会议。[4]Conference on “Power Transition and Thucydides Trap in Asia and the Pacifc”,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ugust 14, 2015, http://www.anu.edu.au/events/power-transition-and-thucydidestrap-in-asia-and-the-pacifc. (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进入2016年,在3月于北京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也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为主题,安排基辛格与前国务委员戴秉国进行了对话。基辛格指出,中美之间不存在“新崛起的大国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战争不可避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些演讲、报告、文章和会议进一步推动了中美各界人士对中美之间冲突可能性的疑虑、讨论和分析,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都助推了这一概念的扩大化使用。
“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也日益进入西方政界、学界的文字和语汇。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美国、中国和修昔底德: 北京和华盛顿如何避开通常的不信任和恐惧”。[5]Robert B. Zoellick, “U.S., China and Thucydides: How can Washington and Beijing avoid typical patterns of distrust and fear?” The National Interest, July-August 2013, http://nationalinterest. org/article/us-china-thucydides-8642.(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也接受访谈并发表文章“中国能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1]Zbigniew Brzezinski, “Can China Avoid the Thucydides Trap?”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Vol. 31, No. 2, 2014, pp.31-33.大部分这些西方话语背后隐含着对中美关系和中国威胁的担忧。不过,也有少部分声音表达了对这个概念的质疑,如詹姆斯·霍尔姆斯(James R. Holmes)在其文章“小心‘修昔底德陷阱’的陷阱:为何中美不必然是雅典和斯巴达或者一战前的英德”中,分析了当今中美关系与历史上以战争结尾的雅典—斯巴达关系和一战前英德关系的不同之处。[2]James R. Holmes, “Beware the ‘Thucydides Trap’ Trap: Why the US and China aren’t necessarily Athens and Sparta or Britain and Germany before WWI,” The Diplomat, June 13, 2013,http://www.thediplomat.com/2013 /06 /beware-the-thucydides-trap-trap.(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
在中国国内,“修昔底德陷阱”概念也似乎有越用越多的趋势。不仅媒体广泛引用此概念,而且很多学术评论也有提及。[3]例如金灿荣、叶自成、赵明昊、鲍盛钢、叶小文、彭光谦等中国学者都对“修昔底德陷阱”进行过评论分析。与西方话语隐含的“中国威胁论”思想不同的是,中国话语往往包含着澄清中国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努力,主要表现为反应式评论及分析,内容往往是对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的质疑、如何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探讨,以及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关联分析。习近平主席2014年初接受《世界邮报》创刊号的专访中也专门强调要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4]习近平:“中国崛起应避免陷修昔底德陷阱”,凤凰网,2014年1月24日,http:// 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4_01/24/33325262_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
细察这一概念的应用可以发现,当今尤其是西方对“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有如下几种扩大化使用的倾向:
第一,将普通的国际关系竞争与冲突扩大为“修昔底德陷阱”。应该说,目前对这一概念的应用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扩大化倾向则将这两种理解混淆使用。严格来说,“修昔底德陷阱”形容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而一种广义的理解则是,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变化导致冲突甚至是竞争不可避免。随着美国政界和思想界对中美关系评价的负面化倾向,加之中美关系中原本存在的竞争与冲突,一些人认为中美关系已经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之中。艾利森2012年提出“太平洋地区已出现‘修昔底德陷阱’”的论断时所用的例证其实正是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力量上升后可能与美国所产生的竞争。[1]Graham Allison, “Thucydides’s Trap Has Been Sprung in the Pacifc”.又例如一篇题为“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不愿向中国妥协”的评论文章表述了美国在遏制中国日渐上升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与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之间的两难境地。[2]Andrew S. Erickson, “Thucydides’ Trap: US Unwilling to Strike a Compromise with China,”July 29, 2015, http://sputniknews.com/politics/20150729/1025178108.html.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可见中美关系中的常态性竞争和冲突事实上被扩大为“修昔底德陷阱”。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竞争与冲突,尤其在大国之间,是世界政治的“常态”,而一般性的竞争与冲突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
第二,将现实主义观点中的“安全困境”,甚至是普遍存在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结构再分配所引发的国家间力量对比变化扩大为“修昔底德陷阱”。“安全困境”是指国家间实力对比变化引发的不安全感造成对立升级。美国学者约翰·赫兹(John H. Herz)认为,国际政治就是追逐权力的斗争,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即霸权是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佳途径。[3]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2,1950, pp. 157-158.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安全困境不仅存在于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而且存在于国际体系所有的力量对比变化中。中美关系是“安全困境”最常应用的对象,哈佛大学教授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甚至直接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安全困境之中。”[4]Alastair Iain Johnsto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Sino-US Relations: A Response to Yan Xuetong’s Superfcial Friendship Theory,”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4, No.1,2011, pp.5-29.当今国际上流行的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包括霸权争夺理论、霸权衰落理论、权力转移理论等,都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5]郑永年:“中国错误估计美衰落将致颠覆性错误”,中国社会科学网,2015年7月1日,http://ex.cssn.cn/jsx/zwjq_jsx/201507/t20150701_2057501.s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如一篇英国评论文章称:“除非中国的经济像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垮塌,或政治制度像上世纪90年代的苏联一样崩溃,中美‘修昔底德陷阱’是不可避免的。”[6]Flair Donglai Shi, “No Escaping from the Thucydides Trap,” October 9, 2015, https:// blogs.nottingham.ac.uk/chinesestudies/2015/10/09/no-escaping-from-the-thucydides-trap. (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修昔底德陷阱”成为现实主义学派扩大阐释所谓国际关系“安全困境”的又一工具。
第三,将西方的“中国威胁论”话语扩大为“修昔底德陷阱”。近两年,“修昔底德陷阱”成了各版本“中国威胁论”里的一个高频词。在修昔底德看来,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有两方面原因,即雅典的崛起和由此引发的斯巴达的恐惧。也就是说,崛起国家实力的迅速上升、霸权守成国的恐惧都可能导致冲突的发生和发展。在2015年4月向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证明时,艾利森引用了修昔底德的看法,称雅典的崛起导致占支配地位的斯巴达逐渐心生恐惧,推动它们走向战争。艾利森试图借“修昔底德陷阱”让政府充分认识到中国的威胁,正体现了西方放大中国威胁以达到一定目的的话语策略。世界上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不安、怀疑和猜忌在明显上升,“修昔底德陷阱”恰逢其时地为各种“中国威胁论”提供了扩大威胁的话语工具。例如,《纽约时报》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定义是“美国对中国日益上升的力量可能导致敌对(animosity)或进攻行为(aggression)的担忧的理论”。[1]The New York Times defnes “The Thucydides Trap” as “the theory that American anxiety about China’s increasing power might evolve into animosity and aggression”. See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31, 2011, http://schott.blogs.nytimes.com/2011/01/31/thethucydides-trap/?_r=0.(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这一定义足见“中国威胁论”被扩大化为“修昔底德陷阱”的倾向。
为什么“修昔底德陷阱”存在了数千年,这几年突然成为西方国际关系中的流行概念并有被扩大使用的趋势?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感受到了压力。正如艾利森在其“修昔底德陷阱项目”中所言,“中国的崛起挑战着美国今天在亚洲以及未来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今天的“修昔底德陷阱”。[2]“修昔底德陷阱项目”(The Thucydides Trap Project)为哈佛大学的研究项目,主持人为艾利森。根据传统现实主义观点,不管中国领导人的主观意图如何,随着中国实际能力的增强,中国必然会被认为要挑战现存美国霸权。同时,中国作为重要参与者乃至主导者的金砖国家体系、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架构也被认为是对美国主导的传统国际体系的挑战。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6”经济峰会“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分会场
其次是美国对华现实主义政策的需要。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似乎能够为美国的对华现实主义政策提供有力的历史和经验证据。而“修昔底德陷阱”推测的可能的中美战争可以为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为惠及许多利益集团的军工企业提供理论支撑。
最后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获取影响力和资源的需要。一方面,当今国际关系研究界已经难以提出创新的大理论、大思想,能够找到“修昔底德陷阱”这一借古喻今的词语不亚于一个新理论的提出,也因此必然会成为众学者专家争相剖析的对象。另一方面,“修昔底德陷阱”所预示的中美冲突能够为各大学及智库相关研究的重要性加注,从而为学术界争取更多的研究资源。
二、中美关系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中存在大量战略互疑,而且近两年似乎有增长之势。特别随着中国力量上升所自然表现出的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姿态,似乎进一步促发了一波中美关系怀疑论学者和专家,指望中美关系能轻易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思维并不容易。所以,我们需要以冷静的思维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之进行剖析,以系统的分析和确凿的理由证明这一思维在当代中美关系中的错误类比。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源自西方的这一概念,毕竟它在历史上也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它并不适合当今的中美关系。且不论中美双方为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实施的各种努力,[1]例如,为了规避军事冲突风险,2014年中美签署了有关两军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行为准则的两个备忘录。中美关系能够绕开“修昔底德陷阱”还有如下三大方面的原因。
(一)全球层面
1. “复合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环境
古希腊时期的欧洲经验并不能借用到如今的中美关系中。与历史相比较,当今出现了在修昔底德时代所没有的不同体制、不同国家之间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如体量巨大的相互投资和规模性贸易,以及全球化环境下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回顾当时的欧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仅仅维系于政治利益和民族同盟,不仅几乎没有规模性的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也没有相互雇佣劳动力的经济联系。[2]余南平:“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文汇报》2014年4月21日,第10版。同时,环境等非传统问题在跨国关系中也几乎没有任何重要地位。
如今,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或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所提的“复合相互依赖”时代。一荣不一定俱荣,但一损肯定俱损,全球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复合相互依赖的命运共同体。全球产业链分工与竞争的形成,已经将大国利益深度捆绑。任何国家之间的军事对抗损害的不仅是当事国的根本利益,也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加突出,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日益增多,国际恐怖主义、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任何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都超出任何一个国家的能力范围,需要全球共同应对。在国家间复合相互依赖的背景下,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对抗意愿大大弱化,彼此发生冲突和战争的风险亦显著降低。艾利森所举的四个最终未发生战争的案例中有三个是离现在最近的,也说明全球化时代对传统国际关系的重新塑造。
2. 集体安全机制的约束
美国前总统威尔逊曾根据民族自决和现代民主机制强调实现和平的各种先决条件,如集体安全与裁军、建立国家联盟等。也就是说,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是实现国际和平的一种机制。然而,古希腊时期缺乏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等保障共同安全的机制,甚至可以说,二战之前的国际社会都没有成形的集体安全机制。这种缺乏国际法约束的时代使武力成为最有效也是被最频繁使用的工具。这也是艾利森回顾过去500年16组关于挑战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案例中,有高达12组以战争收场的原因之一。
当今,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日益刚性化,这对约束国家间冲突有一定作用。尽管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实质约束力可能被质疑,但集体安全机制至少增加了道义约束力,以及违反的国际形象和舆论成本。同时,许多国际组织实体的兴起使国际法的强制体系更显刚性,越来越多体现“直接适用”思想的条款出现在国际组织规则中,相关立法和仲裁方式都开始具有强制性和刚性特征。尽管国际法的刚性与国内法仍无法相提并论,但国际社会依然可以借助间接手段施加影响并实现其强制性的目的,例如国际社会的组织化使制度化“制裁”的规则日益普遍。[1]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65页。这就使国家在做战略选择时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的约束,以及冒险行为可能带来的国际制裁。
3. 基于历史经验对战争的深重恐惧
历史经验使人们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希腊人总体上认为战争命中注定。事实上,有关战争不可避免的观念,往往是战争的重要原因。[2][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而且一战前,大多数欧洲人不仅没意识到战争会造成巨大破坏,甚至认为一场大战对于社会是健康和有益的锻炼。[1]陈永:“中美关系真的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吗?”,国际在线,2015年7月27日,http://gb.cri.cn/42071/2015/07/27/8211s5045151.htm。(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然而,这种乐观态度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灰飞烟灭。战场有胜负,战争无赢家,这些战争记忆使国际社会更多地倡导竞争而不是战争,注重采取合法的手段而不是暴力手段获取财富与权力,并强调制定和运用规则的合法性和制约性。
康德(Immanuel Kant)与勒德洛(Louis L. Ludlow)都认为,如果那些遭受战乱之苦的人能够直接表达意见,战争将可以显著地减少。[2]Kenneth N. Waltz, Мan, the State and War: А Theoretical Аnalys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01.历次战争的苦难代价换来的是各国政府和人民对战争的深重恐惧和对和平的极度渴望。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更多接受了历史教训,因而也变得更加冷静和理性,努力通过协商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矛盾,避免使用武力威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人。正如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修昔底德陷阱2.0:超级大国的自杀?”所预示的,[3]Patrick Porter, “Thucydides Trap 2.0: Superpower Suicide?” May 2, 2014, http://nationalinterest. org/feature/thucydides-trap-20-superpower-suicide-10352. (上网时间:2016年2月10日)中美都很清楚,“修昔底德陷阱”所预测的中美对抗不但会对中美本身的利益构成威胁,而且会对同中美两国有合作关系的所有国家乃至整个国际体系环境形成损害。
(二)双边关系层面
1. “结构性共同利益”甚于“结构性矛盾”
中美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中美社会制度不同,价值观也有差异,国家利益优先次序也不同。中美的矛盾点似乎很多,如南海问题、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网络安全等。两国日益认为对方是政治、经济、安全等各领域最主要的竞争者。但另一方面,双方的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中美的结构性共同利益正在增加,[4]夏立平:“论中美共同利益与结构性矛盾”,《太平洋学报》2003年第2期,第27-35 页。中美正在发展为“利益共同体”。[5]张业遂:“中美正发展成‘利益共同体’”,环球网,2012年10月15日,http:// world.huanqiu.com/exclusive/2012-10/3186270.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经济的盘根错节、金融的不分你我、贸易的相互依赖、人员的相互往来、领导人的互通有无、教育文化艺术的广泛交接,都会使任何不利因素在膨胀到一定程度时被挤破或压碎。[1]刘亚伟、李成、袁鹏:“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共识网,2015年6月3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603125390_all.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历史上相互争霸的国家间从未出现过如当今中美两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高度相互依存。而且,国内政治经济发展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重点,相互对抗只会妨碍各自国内的优先考虑和中心任务。[2]王缉思、仵胜奇:“破解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关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思考”,《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回顾与展望》(2013年北京论坛文集),第4页。
经济的相互依存常被认为是稳定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在《与中国冲突:可能性、后果及威慑战略》的报告中,美国兰德公司四位学者指出,中美两国经济的高度依存以及两国经济同世界经济史无前例的联系使“中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爆发军事冲突”,因为即使不考虑核战争的危险,即使双方都刻意避免使用经济武器,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都将不可避免地严重损害甚至摧毁美国经济。[3]James Dobbins, David C. Gompert, David A. Shlapak and Andrew Scobell, Conflict with China:Prospects, Consequences, and Strategies for Deterrence, Rand Corporation, October 2011,http://www.rand.org/pubs/occasional_papers/OP344.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此外,中美在全球治理议题上也存在许多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不仅是推动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不可分离的双引擎,而且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两国合作多于分歧,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协议、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共同努力,以及在伊核协议达成中的作用、在朝核问题上的相互合作等。
2.“社会进化式”战略竞争替代传统战略敌对关系
新时期的中美战略竞争没有表现为安全威胁或领土扩张的传统战略敌对关系,而是一种“社会进化式”的战略竞争。根据唐世平关于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解释,社会进化体现为社会要素基于变异—选择—遗传这一三联机制的长期性、系统性演进。在此视角下,中美两国的战略竞争是长期性、系统性的制度变迁竞赛,是一场比基础、比耐力的并肩长跑,而非有限时间内决定输赢的对抗赛。[4]Shiping Tang,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基辛格也曾用“共同进化”(co-evolution)来形容中美关系,认为中美应在合作与竞争中促进各自的利益,应实现共同进化从而走向“太平洋共同体”。[1][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515-516页。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应用到中美关系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共同进化。[2]陆克文:“国际关系也可以‘摸着石头过河’”,2015年6月28日,http://fnance. ifeng.com/a/20150628/13803308_0.shtml。(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
传统战略敌对关系一方面源于崛起大国对世界秩序的挑战。作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并非通过战争或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和领土扩张获得,而是强调用和平的方式不断融入国际秩序。[3]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第63页。汤因比(Arnold Toynbee)曾对世界各种文明的发展进行比较后指出,中国从来没有对其疆域以外表示过帝国主义野心,传统上就是一个大而不霸的东方大国。[4]叶小文:“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孔学堂》2014年8月第1期,第11页。基辛格也指出:“军事帝国主义向来就不是中国的风格。”[5]转引自[美]约翰·米勒-怀特、戴敏:《中美关系新战略:跨越零和博弈的中美双赢之路》,中信出版社,2008年,第143页。美国著名外交家傅立民(Chas W. Freeman)认为:“中国不同于德国、日本、原苏联,甚至不同于美国,因为中国不会追求类似二战前法西斯德国提出的所谓‘生存空间’,也不会追求(类似美国提的)‘天定命运’;中国不向海外输出意识形态。”[6]Chas Freeman III, “An Interest-based China Policy,” in Hans Binnendijk and Ronald Montaperto,Strategic Trends in China, Washington: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3-124.李光耀先生也曾说过,中美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因为苏联本质上是与美国争夺全球霸权,而中国只是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7]Lee Kuan Yew, The Grand Мaster’s Insights o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World,Boston: The MIT Press, 2013.因此,中国的对外战略,从根本上说是立足于国内发展目标的。
传统战略敌对关系另一方面还源于所谓的“权力转移理论”。根据国际关系研究,“主导性大国”和“崛起性大国”的力量接近同等水平,或者强弱之分不再明显的时候,权力更替可能性到达顶峰,发生争霸冲突和战争的概率大大提高。不过,尽管中美的相对实力对比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今后十年可能超过美国,但从军事和软实力资源看,美国在今后几十年中仍将领先于中国。[1]Joseph Nye, Presidential Leadership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Аmerican Era, 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另一方面,也有观点认为,美国对当前世界秩序施加了巨大影响力并从中大大受益,但还达不到权力转移理论所假定的那种支配地位。[2]Alek Chance, “The Problem with the ‘Thucydides Trap’,” May 19, 2015, http://www. chinaus-icas.org/node/72.(上网时间:2015年9月10日)今后大国强加自己偏好的能力只会进一步减弱,这将进一步减弱新兴大国强力挑战现秩序或建立平行秩序的动力。事实上,某些研究发现,根本就没有权力转移引发冲突这种现象,[3]Ibid.冲突不仅仅是权力增长差异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重要因素。根据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根本就不是不可避免的,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相对实力的变化,最多只是这场战争的间接原因或者前提条件。[4]Richard Ned Lebow, “Thucydides, Power Transition Theory, and Causes of War,” in Richard Ned Lebow and Barry S. Strauss, Hegemonic Rivalry: From Thucydides to the Nuclear Аge, Boulder:Westview Press, 1991, pp.125-165.
3. 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替代霍布斯逻辑
核威慑条件下的国家理性是中美不可能真正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核心保障。“修昔底德陷阱”并非不可避免,它之所以发生在更大程度上是不明智战略的恶果,而不宜简单归因于实力增长导致的恐惧。在毁灭性武器出现之前,无序竞争主导了国家间关系,战争和冲突是主要的权力获取方式,所以霍布斯逻辑频繁地占据着国际政治的主导地位。[5]John J. Mearsheimer, “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 No.3, 1994, p.42.
修昔底德时期的非理性对抗在现代社会早已过时。在核武器时代,尽管世界政治仍未摆脱无政府状态,但大国理性因为国家对彻底毁灭的恐惧以及保存人类文明的理智而出现,世界逐渐步入有序博弈。“核恐怖平衡”机制某种意义上转化为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战争恐怖平衡”,[6]李巍:“中美关系可以走出‘修昔底德陷阱’”,《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6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63。(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谁也不想看到一旦开战就足以导致相互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的可怕图景。中美关系也随着中国进入核大国俱乐部而进入了相对稳定的阶段,过去倾向无序博弈的政治结构转向有序博弈的政治结构。[1]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第63页。核恐怖平衡可以控制20世纪的美苏争霸走向没有军事冲突的“冷战”,也足以约束21世纪的中美关系,使之不至于误入战争邪路。
(三)网络时代特点
1.网络时代的整体思维
网络时代催生的整体思维可理解为三个层面:一是网络文化对人整体思维的塑造。一键达全球的传播速度、穿越时间限制和地理障碍的互动,直接引起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二是网络空间本身的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对行为和物质世界的整体思维。网络空间的关联态势穿透现实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使各国相互依存和关联度日渐上升,而且网络空间本身的挑战,如网络恐怖主义等网络安全问题,也需要全球共同来应对。三是共享网络空间的脆弱性所带来的整体思维。网络空间的结构特点决定了任何一个最薄弱的环节都可能成为攻击的入口。中美之间隔着浩瀚的太平洋,地理空间有所分割,但网络空间和太空技术的发展使两国重新开始共享权力空间,也使各国利益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性特点。这种整体思维有助于网络时代的理性决策,也有助于大国冲突的预防。
2. 透明度与危机预防沟通的便利
《人、国家与战争》一书指出,清晰的意图可增进各国国民之间的理解,也意味着增进和平。与之类似,通过减少失望和不安全感,进而改善对个人行为的社会调节,可以降低战争爆发的频率。[2]Kenneth N. Waltz, Мan, the State and War: А Theoretical Аnalysis, pp.42-43.在当前高度网络化的时代,世界资讯与情报的透明度、各国战略动向和政策选择的透明度都是空前的。透明度往往包括三层含义,政策透明、信息透明和交流透明。[3]滕建群:“论中国的军事透明度”,《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3期,第47页。网络对透明度的贡献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主动的透明度,即当事国对其政策及相关信息和交流的主动公开;二是被动的透明度,即网络空间的大数据和海量信息所隐含的相关信息。透明度作为信任机制建设的一部分,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国际行为体之间的误解或误判风险。
网络交流和通讯的实时有效还提供了危机预防和沟通的便利。在艾利森所提到的没有以战争为结局的数例权力转移中,交流沟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危机可以分为有敌对冲突背景的危机和偶发性危机。在当前理性思维和整体思维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际危机往往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对于有冲突背景的危机,网络提供了相关方沟通核心利益和行动意图的便利,有助于相互权衡和谈判,网络非官方、不间断的通信联络可以缓解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并寻找替代解决方案。对于由偶然性意外事故所触发的偶发性危机,网络的作用更加明显。这类危机的突发性特征极其明显,需要及时做出反应。网络交流的实时性、便捷性以及音频、视频、文字的选择多样性赋予了危机预防沟通的极大便利。
3. 社会力量对中美关系的牵制
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拉布吕耶尔(La Bruyere)认为,战争只能实现皇族的利益,和平才能使全民的真正利益得到保障。[1]Kenneth N. Waltz, Мan, the State and War: А Theoretical Аnalysis, pp.97-98.美国政治活动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也指出,人民的利益在于和平,君权是人类公敌和苦难的来源。[2]Philip S. Foner, ed., The Complete Writings of Thomas Paine, Vol.1, New York: The Citadel Press, 1945, pp.21-29.历史上战争的发动权都在于决策者,老百姓即人民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网络政治参与和政治动员的功能促进了社会力量的发展。随着网络诞生的强大网络民意监督国家权力并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网络也为普通大众迅速提供诸多外交信息,意味着大众权力的相应提升,因为信息获取是权力的重要来源;网络还推进了自媒体的诞生,以媒体的形式影响国家决策。所有这些都说明网络时代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制约和牵制。
中美关系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国家对国家的关系,还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中美外交关系不再仅仅事关政府机构和领导人,而且牵涉广大的社会力量。中美两国政府关系出现恶化时会及时得到来自社会力量的制约、调整和纠偏。[3]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第64页。“中美之间不会也不应该发生战争。两国都有鼓吹走向战争或冲突不可避免的利益集团,但是中美最大的利益集团——普通民众——反战和追求和平的动力可以击碎一切特殊利益集团的小算盘。”[1]刘亚伟、李成、袁鹏:“中美关系进入‘临界点’?”, 《国际先驱导报》2015年6月3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world/zlwj/20150603125390_all.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两国普通民众之间日益频繁深入的人文交流就像一张巨大的网,承载着中美关系的厚重,更像是无所不在的空气,维系着中美关系的“生存”。中美关系的根基最终仍然在于“沉默的大多数”。[2]王栋:“中美关系的根基在‘沉默的大多数’”,环球网,2015年6月16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5-06/6691867.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
除了上述三大层面原因,我们还需从概念提出者的思想及立场考察概念的适用性。事实上,多数人在引用艾利森所提出的中美关系“修昔底德陷阱”之说时,只是简单引用其字面观点,并未注意到他本人观点的两面性。他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想说“中美战争不可避免”,而是希望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认识到中国力量的上升及其重要意义,[3]Alek Chance, “Is Thucydides Helpful in Explaining Sino-US Relations?” The Diplomat,May 20, 2015, http://thediplomat.com/2015/05/is-thucydides-helpful-in-explaining-sino-us-relations.(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并提醒美国人警惕中美爆发战争的风险。
艾利森本人也在对这一概念进行修正。他指出,尽管四组挑战国—霸权国关系最终能够回避战争“是以双方巨大而艰难的调整为代价的,包括态度和行动两方面,而且这样的调整对霸权国更加艰难”,但中美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避开“修昔底德陷阱”。[4]郑振清:“中美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南风窗》2015年第7期,http://www. nfcmag.com/article/5439.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而在比较了当前的中美军事关系与1914年的情形后,艾利森特别以“别担心,下一场世界大战还不会到来”为题撰文。[5]Graham Allison, “Don’t Worry, the Next World War Is Not Upon Us…Yet,” http://www. defenseone.com/ideas/2014/07/dont-worry-next-world-war-not-upon-us-yet/90152. (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在列出目前形势与1914年形势的相似点(如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态势、逐渐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针对主要敌人的强大军事存在,以及相互牵扯的联盟体系)同时,这篇文章更主要地是列出了不同点,如中美的相互经济摧毁能力(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 of economies)、太空与网络空间没有国界引起的“危机不稳定”(crisis instability)、核武器的“水晶球效应”(crystal-ball effect)、中美军事实力尚无法相提并论的实质、信息技术带来的透明度以及世界政治的结构等因素。尽管作者觉得大国战争可能性依然存在,但他同时认为未来十年战争不可能发生,如果各国领导人能够以史为鉴,战争可能性会更小。
此外,对于任何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不可能穷尽事件的全部内容和所有事实,所有的历史都是简化后的版本。这可能让我们忽略一些本来不该忽略的因素,尽管历史学家也常努力呈现事情的所有原委。二是任何历史学家的著作都会受其写作时价值观、偏好及立场等诸多影响而有所选择。正如修昔底德写书的目的是探讨雅典人如何吸取战争的教训,以及批评伯里克利和民主派犯了判断上的错误,其重点也更多是呈现当时的“囚徒困境”情势。修昔底德的史书不是有意误导后人或者存在偏见,它只是说明人们对事件的认识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时代的人都在重新书写历史,[1][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3-24页。因此我们要避免简单的历史类比。
三、“修昔底德陷阱”话语的危害性与启示
中美关系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意义就是排除这一话语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的干扰和危害,因为将“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与中美关系相关联有诸多危害性,不利于中美两国积极探索以合作方式解决问题。
第一,对中美关系本身而言,“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容易引起双方的攻击性政策倾向。借古喻今能够形象直观地给世人启发,然而,过于简单化的历史类比会误导人们对当今世界的观察和理解。“糟糕的历史类比”和“错误的理论”导致中国和美国的某些当事人对对方摆出更具攻击性的立场。[2]Michael D. Swaine, Ashley J. Tellis and Avery Goldstei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redominanc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May 13, 2015, 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5/05/13/ future-of-american-predominance-in-western-pacifc/i872.(上网时间:2015年9月2日)事实上,雅典和斯巴达两国之间的战争有很多原因,艾利森片面强调雅典的扩张和斯巴达的恐惧并将“修昔底德陷阱”进一步应用到中美关系中时,片面夸大了中国崛起的威胁,忽视了斯巴达恐惧的真正原因和雅典扩张的方式,歪曲了修昔底德的本意。[1]晏绍祥:“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光明日报》2014年3月17日,第15版。所以,修昔底德不见得预见了中美冲突的陷阱,但“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却为中美关系下了个套,[2]张锋:“‘修昔底德陷阱’为中美关系下了套”,澎湃新闻网,2015年7月24日,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55634_1。(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也给中国推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带来极大阻力。
第二,对地区形势而言,“修昔底德陷阱”话语可能刺激周边国家的选边站,从而不利于中国的周边外交环境。美国“重返亚洲”政策表明了其某种程度上对中国崛起的恐惧与防范,尽管美国宣称其并非要“围堵”中国,而是“威慑”中国,防止中国破坏亚洲的现存秩序从而保障亚洲的秩序及和平。这种心理和行为如果加上“修昔底德陷阱”话语的简单化宣传极其容易刺激亚洲一些国家效仿修昔底德当年的希腊其他国家,在中美两国间选边站。尽管有些国家仍在观望,但的确有一些国家选择站在美国一边以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而这将是中国周边外交环境的极大不利因素。
第三,对世界局势而言,“修昔底德陷阱”话语会影响世界舆论,加剧阵营分化,从而影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发展。在判断国家安全的复杂问题时,从最坏的情景预设来看待对方不断增长的实力时,“修昔底德陷阱”话语的出现也是意料中的事,而且也会有一定的市场。然而不顾历史情境地对历史名词简单加以解释,再当成一个标签贴进国际时事和学术评论里,就会很武断而且危险。一旦任由这种错误认知塑造世界舆论,成为学界、媒体、公众的一种共识和习惯认识,将不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构成障碍,也是和平时代世界局势发展的极大阻力。
鉴于“修昔底德陷阱”话语的危害性,我们有必要从学理上对之进行批驳,以防中美关系被这一谬论所绑架,继而殃及未来互利共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合作发展模式。“修昔底德陷阱”并非铁律,更不必迷信,尤其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应该立足全球化和中美关系的结构特点来客观分析。从全球层面、中美双边关系层面以及网络时代的特点来看,“修昔底德陷阱”都不适用于当前的中美关系。
诚然,中美关系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但“修昔底德陷阱”毕竟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即便符合其中的条件,也不意味着理论就会自我实现。早在2005 年,约瑟夫·奈就曾指出,虽然斯巴达对经济强势崛起的雅典的担忧构成了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那场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和人的明智政策避免。[1][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第23页。中美也可以通过这些途径达至长期稳定的关系。“中美之间不会发生战争,中美之间也不应该发生战争。如果当年的美苏领导人可以避免走向战争,那么今天中美的领导人就更不用说了。”[2]刘亚伟、邓媛:“中美是时候考虑各让一步了”,第一智库,2015年6月1日,http:// 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20150604_23711. html。(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所幸的是,随着这一概念的显性化,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中美两国高层的共识。正如习近平访美时在西雅图演讲中所提到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两国应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正确方向。[3]“习近平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新华网,2015年9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5-09/23/c_1116656143.htm。(上网时间:2015年11月2日)
【完稿日期:2016-4-10】
【责任编辑:吴劭杰】
〔作者简介〕蔡翠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中图分类号〕D822.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6)3期0013-19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世纪中美关系中的网络政治研究”(项目批准号:12BGJ018)的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