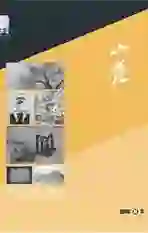格非:面对先驱的写作
2016-06-16张莉
张莉
“重构或归返中国叙事之路”这个题目让我想到了2001年。那一年,格非老师刚刚从华东师大调到清华大学,那是秋天,他为研究生开设他的第一门课。我们都很好奇,这位新锐的先锋作家会给我们讲什么。——没有讨论博尔赫斯,没有讨论马尔克斯,也没有讨论米兰·昆德拉,那个学期我们讨论的是中国小说传统,或者说是中国小说传统的财富。中国戏曲如何在一桌一椅的简单背景下表现那么激荡人心的故事?鲁迅刻画人物是如何做到如此简笔而又如此传神的?15年过去,很多具体讨论已经变得模糊,但是,那些问题却一直潜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我懵懂地意识到,那可能是他正在进行的一些思考,而这个思考深具先锋性。
2004年,当我读到《人面桃花》第一句:“父亲从楼上下来了”时,非常激动。我意识到它与我三年前的课堂讨论形成了暗在的呼应。今天看来,《人面桃花》的写作是一个开启,是另一个起点,由此,格非开始返归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却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传统。父亲留给秀米财富,但这个财富是需要破解才可以成为财富的,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它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可能就分文不值。当然,这部小说中读者也难以忘记张季元这一人物,革命者的另一种形象,很可能更接近真实的一种形象。作为革命中人,如何理解革命,如何画下我们最早对于乌托邦的想象,《人面桃花》是一个缘起。
2009年,读《山河入梦》时,我想到的是格非对历史的认知和书写是如此地别有路径。那位共和国的县长,秀米的儿子谭功达,他的情感际遇和他的抱负一样荒诞,具有某种隐喻性。但是,坦率说,当时最吸引我的是2011年出版的《春尽江南》。《春尽江南》气质优雅淳正,在细节与事件中追求一种具象的真实,但同时,小说也罕有地具有对当代社会的整体性认知。在阅读中,你会强烈意识到,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作家创造和构建了一个别样的现实,一个脱胎于当下但又比当下更触目惊心的现实。在当代中国,如何书写现实是困难的,这几乎是每一个作家的困境。格非的意义在于,他以独有的路径寻找到了谈论现实和精神疑难的方式。
从2004年到2011年,七年的时间里,格非以“江南三部曲”完成了一个整体的对于历史与现实的思考。关于革命,关于乌托邦,关于历史,关于现实,更关于世道与人心。2015年8月,在茅盾文学奖评审期间,我又用集中的方式对这部作品进行了重读。如果说以前的阅读是从《人面桃花》顺流而下,那么,那一时期,我试图从《春尽江南》逆流而上。我对三部曲有了更为深切的整体认识,我发现,每一部都有今人与古书的对话,或者说都与历史对话。
尤其对《春尽江南》的谭端午印象深刻。面对时代,他仿佛是个袖手旁观者。但是,那些对过往的念念不忘,那些他阅读的诗章和古书都表明,他在思考,也在抵抗。小说中他阅读欧阳修的《新五代史》的行为尤其令人难忘。叙述人说,那是一本衰世之作,可是,借陈寅恪说法,欧阳修几乎是用一本书的力量,使时代的风尚重返淳正。
那么,读书人端午的感受如何?“端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个地方让他时常感到触目惊心。书中提到人物的死亡,大多用‘以忧卒’三个字一笔带过。虽然只是三个字,却不免让人对那个乱世中的芸芸众生的命运,生出无穷的遐想。再有,每当作者要言那个时代发点议论,总是‘呜呼’二字开始。‘呜呼’一出,什么都说完了。或者,他什么话都还没说,先要酝酿一下情绪,为那个时代长叹一声。呜呼!”呜呼!这是当时读者的叹息,恐怕也能传达今日读者读史的感慨。
这边是古书,是我们走过的历史;另一边是此刻,是正在经历的现实。在我看来,这是《江南三部曲》隐在而迷人的结构。而现实写作中,格非读《金瓶梅》,他出版了《雪隐鹭鸶》,关于《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这是我们大家都看到的。我想,他也在读《史记》,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感言中,他梳理了茅盾、老舍、巴金、李劼人等人奠定的现代长篇叙事文学的传统;也梳理了由《水浒传》和《红楼梦》为代表的明清章回小说的传统;进而他追溯了被我们几乎快要忘记的但又深深影响我们写作的史传文学传统,在那里,《春秋》和《史记》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从而,他辨认出古人写作的抱负和宗旨,“那就是明是非、正人心、淳风俗。”由此,他回到今天,“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文学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矫正力量。文学写作不仅仅关乎娱乐和趣味,也关乎良知,关乎是非,关乎世道人心。”
一面是写下优秀文字的前人和他们构建的传统,一面是对传统进行重新理解的当代写作者。把格非十多年,或者更长时间里有关作家写作的思考并置在一起,我们将会意识到,中国叙事传统之于格非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给养,是一种勇气和力量。这也标志着,作为作家,格非深刻意识到了“个人”与“传统”的关系,他以写作思考“当代”与“传统”的关系,思考属于作家的“历史意识”。当然,这里所说的作家的“历史意识”并不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么简单和浅表。
这里的“历史意识”更接近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所说:“历史的意识是对于永久的意识,也是对于暂时的意识,也是对于永久和暂时结合起来的意识。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也就是这个意识使一个作家最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我想说的是,这些话评价格非的三十年创作之路非常恰切,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在时间长河里的地位时,他由此意识到自己与当代的重要关系,我以为,这也是这位作家之所以优秀的前提。
“因为当一个人写诗时,他最直接的读者并非他的同辈,更不是其后代,而是其先驱。是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是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 布罗茨基在《致贺拉斯书》中说。写作者的另一个使命是常常被今天的我们所忽略,即,写作者要面对那些给了他语言的人,那些给了他形式的人。那么,我们如何面对传统写作就是如何为我们的先驱写作。作为写作者,我们能否在先驱的基础上前进一小步?今天,我们常常讨论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我认为主体性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即作为后来的写作者,我们如何在传统的链条里成为我们自己。
在我看来,《江南三部曲》是承袭了中国叙事优秀传统的写作,是作家自觉面对先驱的写作。“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的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我以为,格非和《江南三部曲》中最好的部分是他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中国叙事传统中最不朽的那部分。由此,他不仅仅使自己成为中国文学传统写作中的一员,也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了优秀传统小说链条中坚固的一环。格非和他的写作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写作者在今天的写作意义,也有力地证明了写作者在我们时代的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讨论“重构与归返中国叙事之路”?当然因为中国叙事之路是我们的珍稀财富,但是,我想,这个题目也在提醒我们,每个写作者不仅仅是在面对同辈与后人而写,也是在面对我们的先驱而写。作为作家,得认识到我们是在面对先驱而写,也得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先驱而写。当然,这样的写作和思考都极具难度,每前进一小步都困难重重。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格非在内的中国写作者们,都是在那个“永久与暂时”的时间长河之中,是在行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