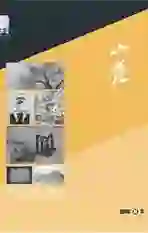豌豆秧儿
2016-06-16邵振国
邵振国
一
连秋蝉都不知道叫唤了,秋蝉都热死了。
那个热,真想把衣裳扒光,跳进鱼塘里。塘边几棵沙枣树,一些些也不知道动弹,叶儿摆也不摆一下,毒太阳下看不清是个白亮的还是个锅底黑。豌豆秧秧也像是晒死了过去,没了那青青的颜色。
她握住锄头把子在塘边豌豆地里除那些野日的草,骆驼刺、羊奶角角、拐枣、梭梭,沙海子里就这些野日的东西多!锄着锄着,懒劲上来,锄头吧嗒撇下了。锄啥呢,让它疯长去,反正不指望它长出豌豆来,再长几天就割下来喂鱼。
她往那片沙枣树荫下一坐,歇缓了。
鱼塘水面没个波纹,跟那白日头的天一个颜色,不敢多瞅,折光白刺刺地扎眼。鱼儿没个在水面上抛头露脸的,日他妈的,都死在塘底下去了!
芦苇那边,塘岸上那座苞谷秆搭的窝棚,也静得没个声气,死老汉在那里面睡晌午觉哩,睡个没时没晌。
那睡觉的不是她的老汉,而是她的雇工。本村上的人,他的大儿子叫处暑,人们就把他叫处暑爸。
雇这个老汉看鱼塘还是划得着,别看他晌午贪睡,早晨可起得早,五点钟天不亮就醒了,不光照看塘里的事,还帮她家做些农活。前些日子刚割了麦,他出力气最大,许是累了,这时候才睡得狠。
她眼前浮出她的男人,满脸的黑胡茬,朝她笑着。那胡茬硬硬的,朝她扎过来,她那汗湿的襟褂贴着奶头被拥动了一阵。
你想他了?去毬,谁想他!屋里有他跟没他一样。每年从四五月间就离了家,到肃北大水河金矿上去淘金,儿子女婿凡能干重活的都被他领了去。直到大水河结冰,矿山上冻得干不成,他才回来。这期间半年多天气见不着他的人影。
想他哩,是想他丢在家里的活。虽说农田不多,早先承包的都种不过来,可是这近十亩鱼塘要照看。麦收了二茬子豌豆要种上,不种鱼儿没个吃食;猪得喂上,不喂猪他在山里的队伍没肉吃。他那支队伍百十号人,她还得给他搞后勤,面买上、油买上、菜买上,雇一辆东风大卡车拉上去。
鱼塘里扑通一响跳起一条鱼,又钻进水里。那张黑胡茬的脸,在鱼儿跳水的地方晃动。老婆子,苦了你啦,我在外面也不清闲。外面没人再喊我“大豌豆”,改口叫我“淘金大王”!我的名字还上了报纸、电视,你也见了,呵呵呵。
早年,她男人在乡政府当个碎干部。这个乡算是敦煌县最富庶的一块洲子。泉水多、树多,风沙挡得住,粮食种得好。大豌豆能在这样一个乡上当干部让人们羡慕,她嫁给了他。不知为啥人们又送给她一个绰号,叫她豌豆秧儿。原以为他能混个乡长、书记的官做,不想他却掉下来了,让他到乡农机站当站长。可是如今各家种地,谁舍得花钱用你那拖拉机、播种机,他就又把机械都变卖了。忽一日连他那站长的碎官也被罢免,说他贪污公款。
他回到村里种田不在行,就倒腾副业,建了这么个鱼塘。早先这达是一片洼地,他自己买了一台推土机干起来,那台机子原本就是农机站的,不知怎么一倒手又回到他的手里。除此还买了一辆山地拖斗车。人们说他肯定在农机站捞肥了,不肥咋能买得起大机器。嘻嘻,真像是他早就为开金矿做“机械”准备哩,两三年鱼儿长肥的时候,他真的就把机车开往大水河去了!敦煌旅游业兴盛,大宾馆大饭店一家挨一家,鱼儿不愁卖,这鱼塘头一遭打出的千把尾鱼儿就攒足了他开矿的资金。
南湖乡养鱼的人多,乡政府后身就有三个大湖连着。离乡十里还有一处海子样的水库,叫做黄水坝,都养鱼。早先没把水面承包给私人,乡上花钱买饲料,叫个啥猪牙草、蚕粪混制的鳗食粉、增生剂,名堂多了。可大豌豆家只是个种植豌豆,沙地里种的是豌豆,麦地里套种的是豌豆,屋后的菜园子、果园子里交杂种的还是豌豆,豆秧秧缠得那苹果树都不肯结果。
白日头稍稍斜过去了些,塘面上不那么刺眼了。岸边一个人影长长地投来,噢,处暑爸睡醒了,猪似的睡足了!老汉往沙枣树这里瞅了瞅,喊道:东家,监工哩?
可不,看你睡了几个时辰!她说。
监工,不到我这窝棚里来“监工”?
哼哼,你就盼我到你那猪窝里去!
他从窝棚里抱出两捆青草,新鲜的,许是今早打来的。解开捆,沿着塘边抛撒起来。一把一把的,抛到塘面渐渐散开。难怪刚才鱼儿跳水,不是水里缺氧就是饥饿了。鲢鱼群果然在水面上争食起来。
饿得都游不动了,才喂食呀?她说。
是哩,不饿鱼日的吃得不香。他说。
喂的是啥草?
野苜蓿呗!咋,认不出?你的豌豆秧秧金贵着还没长好!
她瞅着那油亮的叶子,背面泛着些紫色,夹杂着几朵紫红的小花,莫说吃,看也耐眼。只是这大沙漠里沙生草多,苜蓿罕见,死老汉肯定是一大早又去了黄水坝打来的。十多里路,来回够老汉走的。
他渐渐走到她近旁。老汉五十来岁,但一点也不显老,身板壮实得像牛,粗胳膊粗腿,大脸膛烙着日晒色。
豌豆地锄罢了?咋不动弹?他说。
唉,日头晒死个人!她回道。
就是嘛,我说让你晚上来,日头落了来,天傍黑了来,可你又怕我在这个达达,日弄你哩!
去毬吧,老了老了,嘴上没个干净!
嘿嘿嘿,干净的有,塘里的鱼儿干净,是天天水里洗得哩,你不下水洗洗?
他说着裤管绾过大腿下了水,抱着草苜蓿往塘中间撒去。老汉干活踏实,鱼塘交给他没啥不放心。有时豆秧儿去矿山,一去就是一月半月的,回来一看,老汉一准在窝棚里守着,塘边上转达着。塘里的水清清的,不稠不污,刚倒换过新水。出闸口网不破、鱼不漏,入闸口泥不淤、草不塞。每当望见他下水抛食,两条日晒色的黑腿粗筋凸露着,她心里都想,多亏他了,下月关饷多给他加些钱!
斜阳迎面照着他,她望他的背影是黑的,黑影子边缘却亮得刺眼。
唉——,处暑爸,别往里面走,那达水深!她喊道。
他背着身子说:你不下来,光喊叫个毬哩!
她哧的一声笑了。她倒是想下去凉快,可那像个啥,农村里封建,说大豌豆家的下水,真成了豌豆秧了!
来,把那捆子给我抱过来!他喊道。
她绕到塘那边,背起那捆子草苜蓿回来,拿了根长长的杨木杆,把苜蓿散开捆丢下水,用杆子向他近处推。
待到水面撒均匀了草料,他爬上岸来。裤管连着汗襟子都湿了,贴着身板。
还不去你的窝棚里换件干的!她说。
他也往那沙枣树下一倚,说:这毒日头一会就晒干了。
他说着伸手四处寻摸,是在寻摸他的烟锅子。他知道没带着它,只是做出个寻的样子给她看。她鼻子哼了一声,起身去窝棚。
他笑了,老眼迎着斜阳眨巴着。瞅着她那有些发胖了的身子一步步离开,自语似的:唉,豆秧儿也见老了!日子不饶人哩,不饶小、不饶老!
处暑爸这辈子没喂过鱼,也不记得吃过啥河腥海鲜的。他的女人前几年生病走了,要说他的家务活比女人在世时就更忙了。务地,还得代替女人操心娃子们,虽说儿子都大了,用不着他操那份闲心思!那日,豆秧儿找到他的门上,说了帮她照看鱼塘的事,不知怎么,他瞅着这个女人家的难场,像瞅见自己的女人样,就答应了。噢,她是不容易,又要给大豌豆往山里筹粮草,又要种地、割麦,还要照看她的碎儿子念初中。他抽着烟锅子说:你是看我一个人在屋里空闲了,没了老伴,儿子走的走、另的另(分家)?
老汉没用几个月就学得一手本事。知道把猪粪、鸡粪和麦麸子搅拌搅拌做精饲料,知道起塘之后撒把草籽,塘底便生出鲥花藻……大豌豆两口儿每月给他数百元工钱——这时候的钱还非常值钱呢!这份工资,听说在广州、深圳都拿不到它。两年一起塘,还另有报酬。足了!老汉自己只有两三亩地,一年待种不待种的就收成了,每日吃喝大儿子家管顾他。现在挣钱各有各的门道,老汉在这里大小也算是个进财之道。
他的老三儿子小名叫沙窝子,是他一手拉扯大的。三儿子没跟他另过,一个灶头两双碗筷,也算是个混心的伴。世上的事情日怪,爹给人家帮工,儿子也去扛活。这两年沙窝子已不在老汉身边,他跟上大豌豆金矿上去了。
年年也是,春里走,秋末回来。沙窝子一回屋跟爹聊天:爸,你挣得多嘛我挣得多?爹说:当然是你沙窝子挣得多喽!因为他知道大豌豆给金矿上的工人的工资不薄。可沙窝子能胡倒腾,回到家把烂棉袄刺啦一撕,从那棉花絮絮里抖出好一把金粒子。爹知道那是他偷藏的私货,这要是让大豌豆知道可了不得,打呀骂呀是小事,当爹的这张老脸先就挂不住!
狗日的你再干这名堂,我打折你的腿!金矿上不要去了!他骂着儿子。
那日,在鱼塘边跟豌豆秧儿聊天,才知道沙窝子偷黄货已被大豌豆抓住过一次了。工人们收工,都得搜身,唉,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搜出沙窝子身上的私藏,大豌豆决计开除他。可千想万想,处暑爸给自家看鱼塘,这面子上过不去,才算毬了。
也是豆秧儿有心,劝说他男人。处暑爸自然领这个情意。为她家多干些活。再见到三儿子便说:你狗日的要亮清,人家对咱百好,咱不能有一差。人家东家好心照看咱爷俩做雇工,钱不少挣,这就是情意。不是情意人家哪达寻不来十个百个的,缺了你这一个!
沙窝子命薄却心不小,还嘴犟:啥叫个“雇工”,我就不爱听!有一朝我还雇佣他哩!
唉,都想当人尖尖哟!……
豌豆秧儿走过来,端着那只烟笸箩,里面盛着旱烟渣子和打火机。递给他说:抽吧!抽罢了咱俩一起把那几分豌豆地锄出来。
他望着那片地,哪里是几分,地又不规整,沿着塘四周抹抹拐拐全是豌豆,怕是几亩也有了。他咂了口烟说:好嘛,这些地锄出来,日头可就落尽了,你不怕天黑呀?
不怕,看你老鬼能做毬个啥!
二
这个古时候叫做“西域”的地界,晚上十点来钟天还大亮着。
她背着一捆锄地的草回到庄上。这草没多大用场,晒干,冬天填炕。
碎儿子已经吃罢晚饭,是他姐姐做的饭。丫头出嫁了,过来给妈妈帮忙,一忙完就又回婆家去了。饭给她留在厨房里。碎儿子说着。两眼只管盯着电视。
她问他功课做了?碎儿子只是点点头或摇摇头。再问他:今个学堂里学了些啥?他不耐烦地说:妈妈,跟你咋说,说了你也不懂!
这个碎狗日的,不懂就不能问问?看你也出息不到哪达。将来像你爹当个“山大王”的货!
说罢来到厨房,揭开锅,盛上饭,独自吃了一阵。好没个滋味。倒是吃着饭,眼前又出现那片鱼塘,月亮薄薄地印在塘内,晚风一刮月亮直动弹。还有那苞谷秆窝棚,也摇摇摆摆。
果然豌豆地没能锄完,就该到回家的时候了。那死老汉说:看,天才凉爽下来,你可要走了。她接过话来:碎儿子放学不吃喝吗?你有人送饭,我没你那福气!
可是她瞅瞅这晚间的鱼塘、风摆摆的窝棚,还真有些舍不得离开似的。若是大豌豆在这达守塘,她说不准还乐意在这茅棚子里睡一夜,闻闻那塘里的水腥味。
死老汉就是爱耍笑,帮她把草捆扶上肩,说:走哇,窝棚里不进去?
她笑着唾了一口:呸!你有本事,到我屋里来,炕给你腾开!
好,你等着,今晚上我就来喽!
南湖乡的村村落落,多半都统一规划在一条长街的两旁,一户户挨着,院门都临街,面前一条水渠,渠旁都栽树,高高的白杨树,一遇风整个一条街哗哗地响。这时她独自吃喝着,好像巴望着自家院门上能有一些响动似的。
碎儿子看完电视就在那间屋里睡了。她顶了院门销住插关,走进上房屋也熄了灯。这才把劳累了一天汗湿的褂子扒下身。当姑娘的时候还勤快地洗洗,现在也懒得顾不上了,睡吧。
她躺在炕上,却好久没能睡死,像是睡了,又醒着。或许是人的那个意识让她睡不实沉。她感觉大豌豆,在自己身边,呼呼地喘着粗气,那张脸好像这辈子没修理过,胡茬黑黑的厚厚的,大手在她身上高高低低地摩挲着。不一会,就没高没低地贴上来,贴着发出呻唤。她说:你喘得这么凶,做啥?呼呼的像牛喘气。他说:是这山里地势高,海拔四千多米。咦?她就不知道自己是在自家屋里,还是在金矿上了。
大水河,在山峡中哗哗地流淌,夜里听它回音更大。山坡上支着许多帐篷,但不是一家的,属于大豌豆的帐篷只有两三座。大豌豆就睡在其中一个帐篷里。工人们大多住“地窝子”,挖过沙的大坑,顶上搭些席子和柴草。他的队伍一百五十多人哩,全住帐篷哪供得起。
那山里,不光是他男人的这一支包工队,队伍多喽。只要你有钱,雇得起工人,你愿意雇一百人一千人全由你。各队有各自的窝,有各自划下的那片山,一条好几里长的峡谷,密密麻麻全是他们。国家在那达设了山卡子,叫做啥金矿开采管理局。凡进山挖沙的,每人办一张开采证,办一个证就得交一百五十元,一年下来,每个人还要上缴十五克税金。不管你能不能采出金子都得缴纳。淘不出金子的时候,大豌豆便急红了眼,寻死觅活的,他雇了一百五十号人,须缴纳两千二百五十克金,容易哩?有几日开采不顺当,饭都没心吃。
吃饭,石头垒个灶屋,雇两个专门做饭的男人,工人们一下工,饿狼似的拥向那达。大锅,妈日的,那个大,能煮五头牦牛!锅里胡里麻冬的一锅面疙瘩,有菜就放些,没有菜就撒把盐。每人端一碗汤饭,还给两个馍馍。
不知道饿狼们够吃不够吃,只知她上次给他们拉去两万斤面粉、一卡车白菜洋芋萝卜,还有两头猪一大桶菜籽油。咋,这么快就吃光了?两万斤粮食啊,四百袋子!是她通过各种门道收购来的,有些买来是麦子,还得自己去磨成粉。光跑这些粮食就跑细了腿,煌渠乡、孟家桥、杨家桥,她都跑过;水磨房、电磨坊,还有国营面粉厂,她都去过。面粉灰蒙白了她的头顶和眉眼。
大豌豆在敦煌县城有一个关系,那人能日弄,国家的平价粮食能倒腾些出来。那人姓梁,是县委的一个啥干部,竟然来搭伙,大豌豆的队伍里有他的股份。投资一万元。那时候正是人们叫嚷“万元户”,有钱人少之又少的时候。那几顶帐篷也是姓梁的从哪个驻军部队上日弄来的,他本事大哩!开山的家什几乎全是他日弄来的,钢钎、铁锤、炸药、雷管。除此还有一位姓张的,是哪个乡的副乡长,也算是个合伙人。山上凡属过日子的家当,锅碗瓢勺、铺铺盖盖的,都由姓张的筹措。他还带来三十个人手。
如今,大豌豆的队伍可不缺人手,千里路外的都赶来做工,有定西人、天水人、通渭人,光身子跑来,只卖把子力气。衣裳穿得那么破烂,露着皮肉。抡一天大锤,挖一天沙石,晚上睡在那冰窖似的地窝里。若受不住苦,中途走的人不开工资,大豌豆规定,须干够半年才结账付薪。
女婿在那达给他当会计,大儿子在淘金的紧要处领工。最紧要处就是淘洗金子的地方,须得人两眼死死地盯着。沙石从山上运下来,在大水河岸边一次次地过筛、淘洗,之后过水槽子,那黄橙橙的货色就过了出来。山顶上是干粗活的,钢钎、大锤、铁锨铿铿锵锵响声不住,开出的沙石顺着山溜子嘎啦啦地滚下山坡,坡下面再车拉车运,那个阵势吓人慌慌。大豌豆就整日价在那山上山下转达。那日她给他把粮食押运去,他都顾不得卸车,让她一直候到他们收工。他只是那双黑眼珠狠狠地盯了盯她。她说:你不卸车,我咋赶回去哩!天黑了,路上咋走。
夜黑了,他把那座帐篷里的人不知赶毬到什么地方,把开车的司机也安顿了。回到帐篷,就好一阵混闹。就是那野牦牛喘着粗气的不住呻唤。过了那阵子,才说些正经事:豆秧儿,你还是能干啊!那么多粮食、菜水,经手那么多钱票子,账目一笔不乱。我不留你过一夜就对不住你哩!
去毬吧!我一路上百十多里赶来,累得腰不是腰、腿不是腿,临了还受你驴腿尥蹶。她说。
嘿嘿,这山里,把人空毬子着!他说。
那么你爱金子哩!
唉,金子也招人爱哩!……
他抚摸着她湿透的下面,说:那顶帐篷里住的姓梁的,私藏了金子,以为我不知道。哼,狗日的等着,最后才跟他算账!
你留心,你的老命让人要了去!
他?呵呵,把他跟姓张的两个拴在一起,也没有我这根毬把子粗!姓梁的不就是一万元股份嘛,给他抽掉,看老子能过不?
你还是别扯破脸,当心逼急了动刀子!
噢,我见过得多喽!我见过动刀的,还见过把人捆绑了扔到这山后头喂了狼。见过这山体滑坡,把上千口人埋在山下,大水河常有几具死驴一样的尸体漂下来。还见过为了私藏,把金圪垯吞到肚里,结果两眼一瞪圆,死毬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谁让你淘金哩!不过你别怕,我的人手多,四下里都有眼睛。
处暑爸的老三咋样?他爹让咱多照看着些。
唉,这个沙窝子,早先还贴己着哩,就是那次搜了他,伤了脸。原来我让他在水槽子上溜金,也是个技术活,学手儿本事。狗日的不正经,我把他调到筛沙上去了。吃喝上没亏他,那次他生病,我让做饭的顿顿给他单做,碗里的油花花漂上,还卧上两个鸡蛋。说实话,我自己都没这样单吃过。
忽然觉得他挺受苦,睡在这阴潮的麦草地铺上。便说:怕你睡久了会落下骨头上的病。
他笑了笑说:毬,啥病也没有,不信你揣一揣我的骨头壮不壮。说着拉起她的手去揣摩,却拉到了他的那个下面,她一把甩开了手。
他嘿嘿嘿地笑着,问:沙窝子的爹还尽力着哩?
嗯,夜夜守在那窝棚里。有个偷儿来,想撒一网,老汉提着马灯就走出了窝棚,塘边上一站高声喊叫:“哎——,野日的家伙,做啥着哩!”
他这样守夜,你咋知道?他问。
咦,怪毬,老汉守夜,我就不兴转达着瞅瞅?
不知怎么大豌豆那里就又胀硬了,他一轱辘又伏上她那高高低低的身子……
豆秧儿翻了个身,月光投进她家的窗格子,投在她那马鞍子样的腰胯上,那么寂静。噢,死老汉的荤话,刺激得人想事情,想了这么一摞车!
她依旧瞅见那片鱼塘,塘边的沙枣树,树影子黑魆魆地投在塘内。那老汉这会子睡了吧?似乎瞅见那盏马灯,挂在那达,好像离这达不很远,把她这间屋也照亮了似的。
三
第二天一早,不等到太阳毒起来,处暑老汉便把豌豆地全都锄干净了。
锄下来的草打成捆,等东家来了让她背上去。唉,豆秧儿过日子细详,钱越多就越细详了!他念叨着。
忽然记起几十年前,那时她家境困难。她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一张年轻轻的脸。一次乡上派工,去阳关植树。阳关林场,那是县、乡多年打造的一片绿洲。早先那达很荒芜,离乡上二十多公里,大沙漠隔断着。那达有座不高的山,叫做墩墩山,山顶上立着一墩汉代留下来的烽燧。植树就在那山下面。挖的树坑可是不少,一排又一排,村民们撒得密密麻麻。挖了半日,口渴,便往有人家的地方寻去。走到那片沙丘,他住了脚,竟忘记自己是去寻水喝了。因为那个沙窝的几丛芦苇畔蹲着一个女人,正在挖沙葱。沙葱稀少,她不时起起伏伏地挪动地方,她的身影动态很耐人的眼睛。人啊,虽然那时他已经有了大儿子处暑,可不知怎么,在天地间只有一个男人碰上一个女人,四下杳无人迹的时候,那心窝里会生出些非分之想的。
他停在沙丘顶子上瞅望着,那件蓝底素花的袄褂裹着她的腰身儿,那颜色、碎碎的花子直到今天还像是记得。瞅着又坐下来,瞅她一铲铲地割那野日的东西,东寻一撮、西寻一堆,割倒后捋顺茬口,整齐地放进背篓。沙葱,这野日的东西可以腌菜吃,不过家境好些的不吃它。她可能是阳关村谁家的丫头或是女人,他想。她已经发现他坐在沙丘顶上,若是个胆小的女人,就走开了,但是她没有离开。好像她知道处暑爸这样的人,也只是瞅瞅,做不了个啥事情!她抬起脸庞,反倒笑了,笑得他那样动心动肉的。她的脸庞和她的腰身儿一样,的确是个漂亮的女人的。她一笑,处暑爸自己就脸红了,不知道自己看人家做啥。好在她搭话了:是来植树的吧?在哪个村上?他回答:北工。她一听,就更咧弯了嘴唇、嘴角。好像她知道,北工村就在乡政府近旁,那块洲子富庶些。他这才搭讪:挖野日的哩?站起来拍拍腚上的沙粒,走了。
不多久大豌豆成亲,处暑爸被请去喝酒,一看,他竟然还记得她,那个挖沙葱的丫头!怪不得她当时咧弯了嘴唇子笑。
早晨的豌豆地格外好看,特别是锄干净之后,那豌豆秧秧像公鸡尾巴上的毛,亮豁得很哩!折射着绿里透蓝的金灿灿的阳光,叶儿圆圆巧巧、成双成对排在茎子两边,开着白色的碎花儿。
处暑老汉打草捆不用绳,三把两把将那披肩草搓成辫,用起来比麻绳结实。等她来,让她把锄下来的草背上去。他又念叨着。
那女人打草绳比他在行,她能用拐枣茎子搓绳,结实得像皮条绳。早年她爹为人家拉骆驼,贩药材,用的绳全是她搓的。
她爹可不如她有本事,骆驼是人家的,药材是人家的,他只管拉脚。从南湖乡拉到新疆一个啥地方。新疆那地方再接上脚,拉到伊朗国、俄罗斯,路长哩!那药材的产地也不近,在嘉峪关,离这达四五百公里。那边山上长着大黄、羌活。不知是沙海子路太长,累倒了,还是途中遇到沙尘暴,她亲爹死了。后来她娘带着她另嫁了人,家落在阳关。
处暑老汉把草捆提到地头边显眼处放下。望了望庄子的方向,又说:等她来,让她背上去。
看看她没有来。手脚不能停,停下来觉得闷惶惶的。他走进窝棚,取出一袋精饲料,倒进笸箩,开始喂鱼儿。伸出手,试试风向,没风。一撒料,却又有些风。咋回事,果真老了?老皮试不出个冷暖了?精饲料不敢混撒,浪费不起。麦麸子掺和着胡萝卜粉、黄豆面、鸡儿粪,金贵哩!
他沿着塘边走着撒着,鱼儿追着他投在水面上的影子。那粗粗的胳膊,厚厚的胸膛,还有他那张脸,不像有多老,不像那些老汉瘦肌麻干,他的这副身板若到金矿上去干,也照样试伙。一阵风来,水面上的影子吹皱毬了。
建鱼塘的时候,他便被请来帮工。大豌豆请来的人可是不少。他女人天天做十多人的吃喝,用桶子盛装,扁担挑到工地上来。饭盛到碗里,让她的儿女给大家端到手上。有个好说笑的说:去,叫你娘端来!人们便一阵笑。这女人在庄子里惹人眼哩!她果然亲手端上来了,大哥小叔地称呼着说:只要你把塘挖深些,我天天给你伺候!那个鬼日的却说:你的那个“塘”还不够深么,再深,你家掌柜的那根锨把子能够得着?大家喝——地笑掉了牙。
塘建成了,水注满了,大豌豆不知还有啥事工地上脱不开手,派处暑爸和他女人一起去买鱼苗。处暑爸说:怪毬,咋不派个旁人去,专挑个老汉!是看我这锨把子不中用了?
卖鱼苗的地方就在黄水坝,十多里路,老汉不识个鱼死鱼活,但跟那女人同坐在一辆40型拖拉机的车斗里,心里受活。看见黄水村的景色格外入眼,好一片绿幽幽的草滩,溪水一道道在滩头上涌流,都是些露头泉。白带子似的,长长地从上滩流到下滩。几头骡马在那达啃草,相互臀蛋子上嗅嗅,静悄悄的。
拖拉机上坡,绕上水库大坝。那一片蓝盈盈的海子,像是天倒过来了。沿途全是数百年的柳树,树荫厚密。她坐在车帮上说:处暑爸,现在凉爽了吧?他说:凉爽,凉爽。只见那日头的光影,明明暗暗地落在她脸上、高隆隆的胸脯子上。唉,多少年他不记得自己心里这么畅快过。
到了地方,豆秧儿跟卖鱼苗的人争了起来。她嫌那两桶鱼苗水多苗子少。那人说:我们从来就是这么个卖法。不能像捞干饭一样把鱼儿捞在桶里,鱼苗稠了缺氧不得活。她说:那也不能卖水呀!我看你这两桶就没有一万尾鱼娃子!你给我捞稠些,回去死了我自己负责。那人又说:你说尾数不够,那你就数!时辰还不能大,鱼儿日弄死了算你的!
呵呵呵,那显然是数不了,数不清楚!可是豆秧儿还真的拿起了网罩子,一罩十尾百尾地数着。看她那吃力的样子,那个人笑了,同情地说:好了好了,我再给你加些“稠的”,你不数了!豆秧儿自己也笑起来。那笑容正像是多年前在沙窝里一样。
处暑爸和开车的一起把两大桶鱼苗抬到车上。拖拉机突突突地发动出声,她扭回头跟那个人说:哎——,下次我来,你还给我把“干饭”捞上!
拖拉机驶出养殖场,路经水库那蓝色的海子,那里面不知有多少万尾鱼儿。只见靠岸边的芦苇荡子里栖息着水鸟,旋飞着鱼鹰,喳喳地叫着,像豆秧儿的笑声。
一路下坡,车比来时开得快些,有风,而且车后卷起尘土。她却脱了外面的襟褂,裸露着两条白嫩的胳膊,不时伸进桶里搅动。车上站不稳,她还趔趄着身子。老汉心上顶撞着个啥东西,瞅她那扎眼的光膀子说:你搅毬个啥哩?她说:不是说稠了缺氧嘛,我给它造些氧。要是回去真死了,钱是小,还让他笑话我!老汉这才知道自己心上“缺氧了”!她又一趔趄,白胳膊水淋淋地搭在了他的脖颈上。老汉倏地一怔,唉,你做啥,不站稳当!她看他慌张的样子,又笑出那水鸟的声音,说:我把你老汉搂抱了一下,能咋?他说:能咋,大豌豆把你两条嫩胳膊一刀砍了去哩!……
老汉朝庄子方向又望了望。噢,她还没有来!
心想,她或许进城为她男人张罗粮草,金矿上又没吃喝了?要么就是张罗这一塘鱼,寻个买主,鱼儿们都长大了!
他撒尽了那大笸箩里的精饲料,把笸箩在腿面上磕了磕,一些碎渣也抛进塘内。
看看日头已经偏过正午,一会儿他大儿子家的就该给他送饭来了。不知今天有啥新鲜的吃喝么?总是那一陶罐汤饭,上面一碟菜,两个馍,也不换换口?
回到茅棚,脱下汗褂子,往棚壁上一挂,让它晒晒汗气。钻进棚内,抱起一罐子凉茶咕咚咚喝了两口。刚一进来,这棚内有些黑,眼皮子眨巴半晌瞅不准个家什。茶罐子在土盘的灶头上放稳当,便一头倒在地铺上歇息。
地铺,下面是麦草上面是羊毡,躺在那达仰脸瞅着窝棚顶子。苞谷秆子晒得干干的,叶子干奓着,一遇到一些风,就沙沙地响个不住。噢,他在这茅屋里躺了多少日子了!
除了老大家的来送饭,没人来这达。茅屋外面那白刺刺的太阳光射入门洞,当他瞅见儿媳妇的身影子出现在那达,会感到这茅屋里立时增添了些活气。
不过有时候他也回老大家里去吃喝,特别是晚上那一顿饭,肯回去。吃罢了转达转达再回来。唉,送饭的时候一久,难免有些烦人,不情愿的样子。
他望着门洞,依旧是那白刺刺的光投进来,几缕沙土随着那热辣辣的风吹进来。
忽然,一个身影儿立在那达,但不像是老大家的。那影子很好看,窈窈窕窕,丰丰满满。
她个儿不很高,用不着躬身哈腰就走进门洞。手上像是提着啥好吃好喝,直走到灶台那达,把吃喝一样样摆上去,一碟卤肉、猪肝、猪肠,还有一碟油焖豌豆。他的眸子一直跟着她的身影,她那躬腰在灶台前的样子,那达光线很暗,只有棚壁秫秸缝隙透来一缕光,抹在她头发梢儿上。
咋,敢是犒劳老汉哩?嘿嘿,有酒没有?
有,让你喝个够!晚上再请你去屋里喝。
怎么,掌柜的回来了?
他不回来,我就不兴请请你?嘻嘻……
他眨巴着眼皮,再看那达,只有那秫秸缝隙穿来的光,照着苞谷叶子。
吃罢晌饭,老汉又该猪似的睡觉了。
睡吧,睡醒来还要干活。还得把那豌豆地浇上水,要不然毒太阳会把青青的豌豆秧秧全都晒日踏。拿把锨去改渠,把渠水引进地里。等她来,一看,草也锄了,水也浇了,嘿嘿……
他在草铺上打了个滚,合上眼皮。但眼皮子前面仍明亮亮的,像是渠被扒开了豁口,水汩汩地流淌,湿透了那片绿莹莹的豌豆秧秧。
四
又过了十多天,豆秧秧长成,到了收割的时候。
妈日的,长得那个茂盛,叶子稠得透不进风、钻不进日头。茎子指头般粗,一根根曲曲弯弯缠缠绕绕,密得分不出垄,蔓儿上大多结出豆荚,摘一颗尝尝,一股嫩嫩的豆腥味。
她蹲在地里,蹲得腿有些麻木,沙地蒸腾着热辣辣的潮气,割一会胳膊上就渗出一层汗珠儿。她瞅瞅地埂子那边,处暑老汉在那达割着。
老汉靠近塘边,有些树荫,或许不很晒热。他割下来一抱,随手撇进鱼塘,也便站起来走走,活动活动腿脚。
哎——,老汉,你是喂鱼嘛,还是割豌豆哩?她朝他喊了一声。
嘿嘿,豌豆也割,鱼儿也喂。咋,嫌我镰把子不连紧了?他说笑着。
我说,咱早割罢了早歇缓,可你日日踏踏没个利索,还想等着月亮出来?
唉,月亮等不出来了,今个是古历的多少?月缺哩!早歇缓,你又不备一桌酒菜,我到哪达歇缓?
好,今个一定请你到我家,炕桌摆上一席。你吃罢了两腿一伸展,就歇缓,咋样?
那可是好,你把炕桌拾掇掉,再躺在我边里。
对,就是那样。
好,那咱就快快地割。
格格格。她笑着。
豌豆秧秧一片片割倒,敛成捆。收割这东西没个早晚,不像割麦,麦黄几天割不倒便糟踏在地里。这货见青就能割,再长个十天半月也不怕长老,反正是结不出豆子的秧秧,迟早喂鱼。
当日头沉向西边,斜斜地照过来的时候,鱼塘这边的豌豆地就全都割干净了。
她那件襟褂,无论是胸前还是脊背后全印着一坨坨汗湿,贴着身子。她疲乏地提着镰刀走过来,走到树荫下。老汉早把他的汗褂子脱去,撇在沙地上,只穿了个背夹子挎着肩,倚着沙枣树抽烟。见她那脸庞晒热得红扑扑的,仍冒着热气。
坐下歇缓!老汉说了一声。
她坐在他近旁。
你也没个抽烟的事干,他说。用烟锅指了指沙地上摆的茶水罐子,喝些吧?
没碗,要喝只能抱起罐子喝。她像老汉一样抱起它嘴对着罐口咕咚咚喝了一阵。那凉茶不知道是啥茶叶熬的,苦掉了舌头。
大豌豆没有回来照看照看?他问。
有个啥照看头,她说。不为拉吃喝,谁舍得雇车空跑,雇一趟东风卡车八百元!
那山里也没个啥消息捎回来?
咋,你想你的沙窝子了?
老汉吸了口烟,吱——地吸出声音。半晌才说:我们老少俩,有个啥念想!只是让娃子挣些钱,为他自己寻个媳妇。
还没个人家?
没有,你又不帮着张罗!过去的地主,还管顾长工们娶老婆哩,嘿嘿嘿。这娃就是贪些,再没个别的不好。他娘去得早,没看护上他,当爹的嘛又能知道他多少冷热。
她忽地心上酸楚楚地一动弹。说:好吧,你的沙窝子的婚事我包了!不光是给他寻个好人家,还像送儿子一样给他一份子。
她说着往老汉脸上瞅了瞅,见他那黑楚楚的额头纹笑咧了咧。
这季节,听说那山里阴雨天气多,常有些塌塌落落的?他说。
哎哟,看你操的这心,我的儿子女婿都在那达,也没像你这样!她说。
嘿嘿嘿,你嘴上说哩,怕是心上比哪个的念想都多!儿子女婿不说了,想掌柜的了吧?
去毬,我没那闲心。这多年,一个人惯了,跟你老汉一样!
她说着,眼睛直愣愣地望着刚割罢的豌豆地,豆秧捆子一捆捆摆在那达,晚日头照着那阳面亮亮的。
收拾吧,今个就割这些,够鱼儿吃几天了。
她走到地里拎起几捆豆秧捆子往窝棚走。处暑老汉也跟着起身,收捆子。
不多时,捆子都拎到了棚屋里。这窝棚看着小,使唤起来却大,装些草料倒还有地方。她拎捆子进来,棚内光暗,猛乍乍还有些黑眼睛,过一会眼睛才渐渐亮了。捆子全码摞在最里边,离开灶台,更远离些老汉睡觉的地铺。那股子草腥味怕不好闻,她想。
老汉笑说:嘿,我偏偏爱闻这股子味,摞不下的就放在铺边上,那个角角。
你这个草铺,潮不?她问。
毬,沙海子里哪有个潮地方,干燥得像燃着了一把火!
她笑了笑,却仍觉得他睡在这达受累了。又问:那么硌不?铺得薄厚?
老汉觉着日怪,问这么详细做啥!一笑说:你不躺下试试?
她忽地脸颊一热,呆瞅了他一会儿。毬子,试试又咋!她一扭腰身,扑通躺了下去。觉着这铺,还算厚实舒服,并不觉着硌硬。
处暑老汉一看她真的躺下了,那个姿势竟在他心上咯噔一下。像是那只茶水罐子没放稳当,倒毬了。
他眨巴着眼皮子,想把眼睛转到一边去,可不知咋,咋也使唤不动。他窘窘地笑问道:硌嘛还是潮?
她说:不硌也不潮。你老汉睡在这个窝窝里舒坦哩!
他说:舒坦,也说不上,照看鱼儿方便些。
她不知咋想,心上又一阵酸楚感觉。许是记起刚才聊天,说起沙窝子的婚事,他额头皱纹那样一咧动。
她仍躺着,没有起身。老汉也忘了自己寻个坐处,坐在灶台上,或是坐在刚刚提进来的豌豆秧捆子上,没有,他就那么呆滞地站在那达。棚屋顶子毕竟不高,苞谷叶子刮擦着他的头顶,似乎发出那干燥的沙沙的响声。秫秸缝隙透来的光,照见他肩膀上的汗渍还没褪尽。
他身子一颤,老眼更扫见她胸襟那达湿漉漉的隆起的地方,厚实实的轻轻地动弹着,仿佛又望见那个割沙葱的丫头!
你坐呀?她说。
他这才一屁股坐在跟她迎面的几捆豆秧秧上。
酒、肉,屋里都有,今晚去我家吃吧。
嘿嘿,东家真的要犒劳长工哩?
哼哼,你老汉一句一个“东家”地混叫,叫得人心上怪难场,好像我亏了你!
东家就是东家,谁说你亏我了。你能在我这棚棚里,呆这半晌,就是不亏我。
她身子上忽地一阵滚热,伴着那酸楚楚的滋味。
那为啥我叫你去家里吃喝,你不去?
呵呵,等大豌豆回来我再去。他回来款待得更丰盛些,嘿嘿,今个就算毬了!
她忽地站起身,咋,非得大豌豆,豆秧儿就请不动你?
不是那个话……他不知道该说啥好,忙把话题往旁处扯:只要你惦记着我的三娃子,我,我就领情了。
我刚才说了,一定给他找个好丫头,你不信我的话?
咋不信,不信我就不会二次张口。
老汉,你的心事大哩!
不大,嘿嘿,不敢大……
她不知啥时已走近那几捆豆秧秧,站在他近旁。
你,你咋就不敢……?
他闻到她身子的那股味,汗味,夹杂着豌豆秧那清丝丝的味。
豆秧儿,你怕是想,想让我把你丢进塘里喂鱼了!
那你就丢,丢吧!丢吧……
她的身子一软,他一把将她搂抱在那达。
那几捆子新割来的豆秧,仍是那般湿漉漉的,茎叶挺挺的,像长在地里一样。叶儿圆圆巧巧,间或还有几朵白花,茅棚里些许光亮,也能看清它那秀色……
五
酒席准备好了,老汉却没有来。
晚上,果然没有月亮。忽然听院门吱扭——响了一声,不一会,走进上房屋来的却是她男人大豌豆。
他脸色难堪,把手里一只黑色皮包啪地一声丢在炕上。
咋了?你咋这早晚回来,没见你事先捎个信来!
他不吭声,坐在那达抽烟。黑胡茬似乎生得更长了。
你先吃些吧,她指了指炕桌上的酒菜。这是为处暑老汉预备的,请他他没有来。
老汉在哪达?他这才抬起眼问道。
还在茅棚里守着哩,咋了?
他重重地吁了口气,摆摆手,让她把酒菜撤掉。她拾掇着,搬起炕桌,这时她才想到肯定是山里出啥事了,她的儿子,女婿?!
到底咋了?你咋不说话!
明天再说吧!……
他熄了灯,滚倒在炕上。她触摸到他那黑胡茬的脸上有了泪湿。
不行!你非得今晚告诉我,是不是咱的老大……她不敢问下去。
咱的娃都好着,只是,只是处暑老汉的沙窝子,吞了金了!
啥——?!
他以为吞到肚里还能屙出来!我刚从县医院回来,没,没抢救过来……
她呜——地一声痛号,却又紧紧地咬住嘴唇,像是怕让处暑老汉听见。
出事的时候我不在跟前,管事的人说他又藏了金,搜他,他就……大豌豆低声说着。
嗯嗯嗯嗯……她强抑着啜泣,泪眼又望见那夜色中的鱼塘、茅棚,刚割罢的豌豆地,忽地一阵晕厥,便啥也不知道了。
不知道第二天将是个啥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