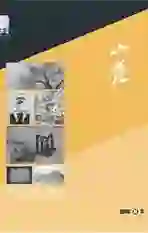乌金肺
2016-06-16刘庆邦
刘庆邦
睡觉,对康新民来说,现在成了一个问题。吃、喝、拉、撒、睡,这五条都是必须的,少了哪一条都不行。前四条问题都不大,康新民每天进行得还可以,只是第五条睡觉有些麻烦,构成了他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康新民年轻时的睡觉能力好得很,甚至有一些嗜睡。瞌睡上来,他倒头便睡,一睡就是十万八千里。他睡觉不择地方,土垃窝里,柴草堆里,都能睡得很香。他熟睡时,天上打雷,他听不见。有人用草穗儿拨弄他的鼻孔,他都不醒。那么有人捏住了他的鼻子,不让呼吸了,看他还怎么睡。好嘛,把他的鼻子捏住了,他把嘴张开了,改用另一个呼吸道吸气出气,照睡不误。
康新民现在瞌睡少了吗?不,他成天昏昏沉沉,瞌睡似乎比以前还多。他真想痛痛快快睡上一觉,睡他个地老天荒,海枯石烂。可是不行啊,不管他怎么努力,就是睡不着,整夜整夜都睡不着。他站着的时候瞌睡得摇摇晃晃,眼看就要摔倒,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他的上下眼皮是合着的,仅从眼皮上看,他是睡觉的状态。可合上眼皮与睡觉是两码事。眼皮想开就开,想合就合,可以掌控。而睡觉就不是自己所能掌控,不是想睡就能睡着。比如眼皮是两扇门,人们把门关上了,不等于人不在里面活动。有时门关得越严,人上蹿下跳,在里面活动得越厉害。康新民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他的眼皮之门虽说是关着的,但里面两个圆圆的眼珠子,像是地球和月球,老在不停地转动,一会儿明了,一会儿暗了;一会儿地震了,一会儿发水了,搅得他老是不得安宁。
他不只是睡不着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他躺在床上还出不来气,不管是仰卧,侧卧,还是趴卧,都呼吸困难。他躺下刚想睡着,突然间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掐得他喘不过气来。求生的本能使他挣扎了一下,一口气才回来了,总算没有死掉。
夜里不能睡觉怎么办呢,康新民只能悄悄来到院子里,在院子里站一会儿。这年的春节过去了,元宵节也过去了,但正月还没有结束。月亮从不圆到圆,又从团圆到半圆,现在只剩下弯弯的一块。月亮不是很圆,边缘像是发生了霉变,生出一些细细的绒毛。从月亮所处的位置来看,这会儿应该是后半夜。在朦胧的月光中,他看得最多的是他家的房子。他看着看着就走了神,走神走到不知名的地方。回过神来,他接着看房子,老也看不够。他家的房子是两层小楼,一层五间,二层五间,钢筋水泥为基础,混砖砌墙,预制板盖顶,结实得很。一层二层都建有廊厦,往厦檐下面一站,下雨下雪都不怕。他家以前的成分是地主,爷爷是地主分子,爹是地主分子,他被说成是地主羔子。听他娘讲,他家以前是有楼的,是两层楼。后来闹了革命,地主分子一被打倒,他们家的楼房就充了公,成了生产队的队部。再后来,生产队盖饲养室需要砖头和房檩,就把楼房扒掉了。楼房是全村惟一一座楼房,楼房扒掉以后,村里再也没有了楼房。他们一家被从楼房里赶出来后,只能住在两间坯座草顶的趴趴屋里。康新民就是在趴趴屋里出生的,从没见过他家以前的楼房是啥样子。眼前的楼房,是康新民用外出打工挣回的钱,一手盖起来的。他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的钱都用在了盖楼房上。当年一听说他要盖楼房,村里人几乎惊掉了下巴。有人说他借盖楼房报复村干部,有人说老地主借孙子的身体还魂,又回来了。还有人私下里劝他,说树大招风,盖楼房太显眼了,会招人眼气。可康新民下定了决心,他就是要盖楼房,就是要争一口气。他说他的钱是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都浸满了汗水,他问心无愧。平地起楼,人们远远地就把康新民的楼房看到了。也就是几十年的时间,村里从有楼到没了楼,从没了楼又起了楼,是康新民把这个村楼的历史重新衔接起来。这时村里的舆论也有了一些变化,说看看吧,人家地主家的后代就是勤快,就是能吃苦,就是聪明,就是会创业。村里人甚至上溯到康家的前辈,说其实康新民的祖爷爷、爷爷和爹,也都是好人,都是勤劳的人,因为他们勤劳,才置了地,盖了楼,积累了财富。康新民想听的就是这样的话。上级为他家摘掉地主帽子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村里人有这样的认识和说法,才使康新民感觉到了真正的平反。
楼房立起来之后,康新民很快就娶到了老婆。结婚不到三年,老婆生下了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正当康新民家的日子如石榴开花越来越红火时,正当康新民继续打工挣钱,准备将来为儿子娶媳妇时,他的身体却不行了。具体来说,是他的肺不行了,动不动就气短,就喘上气来。康新民记得,他爹就有这样的毛病。他爹的病说是哮喘,又说是支气管炎,他到底也不知道爹得的是什么病。他只记得,爹的两个膀尖越来越高,脖子越来越短,一次感冒之后,爹的一口气就没了。康新民原以为,他的毛病跟爹是一样的,是遗传基因在作祟。他到镇上的医院看过,也吃了不少药。但吃药没有使他的病情有丝毫减轻,反而加重了。镇上的医生建议他到县医院检查。他到县医院拍了片子,病才得到了确诊。医生让他看片子之前,先跟他交谈了几句,问他是不是下过煤窑?他说下过。医生问他下了多少年,他想了想,说有十来年吧。医生说这就对了。医生这才拿起片子指给他看,说他得的是职业病,也叫煤肺病。你看你看,你的肺都变成黑的了,都变成两块煤了。康新民以前从没有看见过自己的肺,肺在胸腔子里装着,他对自己的肺是忽略的。他只见过一些动物的肺,知道动物的肺是粉红的。而他的肺却成了黑的。他听到过黑心人的说法,却没有听过黑肺人的说法。医生的诊断让他有些不爽,他问医生,那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治疗?医生的回答是没办法治疗。医生又说,煤窑是不能再下了,重活儿也不能再干了,只有好好休息,好好享福。医生看出他情绪低落,大概是为了让他放松些,还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你去挖煤,谁让你去贪污人家的煤呢!一贪污不要紧,想还给人家都还不成了。
老婆从楼里出来了,对康新民说:新民,夜里冷,你不能老在外面站着。医生说你的病最怕感冒,你要冻着就不好了。
过了雨水季节,地下的潮气开始上升,天气不再是干冷,变成了湿冷。特别是到了后半夜,又是雾又是水的,湿冷的气息更浓。有夜鸟在飞行,翅膀显得有些滞重。不知从谁家院子里,传来一两声狗叫。康新民说:没事儿,我穿得厚,不冷。说了没事儿,他却咳嗽起来。他一咳嗽,喉咙眼里就喀喀的,像卡了什么东西。可他咳了一阵,什么都没咳出来。
看看,冻着了吧,赶快回屋里暖暖。老婆说着,过来扶住他的一只胳膊,把他往屋里扶。
他不让老婆扶他,说松开我,我还没有老成那样。
你的岁数是不老,只是力气不跟你了,别再逞强了。老婆没有松开他,坚持把他扶到床边,为他脱掉棉鞋,让他上床。老婆说:好了,睡一会儿吧,老不睡觉怎么得了!
与白天和黑夜对应,人需要吃饭,也需要睡觉。不吃饭就没有能量,生命就不能维持。同样,人老也不睡觉,也活不下去。康新民躺着是睡不成了,他现在想睡一会儿,只能采用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跪在床上,撅着屁股,头抵在床铺上。另一种办法是他坐在床上,老婆坐在他前面,他的两只手搭在老婆的肩膀上,头抵着老婆的后脖梗。这两种办法都是老婆帮他试出来的。通过试验,他总结出来了,他的肺不能平放,什么都不能靠,后背不能靠,前胸也不能靠,靠什么都会受到挤压,都出不来气。只有把肺提溜起来,提溜得悬空着,四面不靠,才可能得到一点点呼吸,才能睡一会儿。前一种办法,身体的平衡不太好掌握,往往是他刚睡着,身体一歪,就倒下来。一倒下来,他就醒了。而后一种办法,由于老婆的配合,实行起来比较有保证。
康新民的一双手搭在老婆的两只肩膀上,一闻到老婆身上的气息,难免想起他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那时候,他使用老婆使用得太狠了,简直像在井下挖煤一样。挖煤需要打钻,他就在老婆身上打钻;挖煤需要放炮,他就在老婆身体里放炮;挖煤需要用大斗子铁锨一锨一锨往外挖,他挖老婆也挖得格外来劲,有时连挖一夜的情况也是有的。现在老婆还是老婆,他还是他;老婆还需要他,他也需要老婆,可他一点儿都挖不动了。别说使用老婆了,他连想都不敢想。过去他以为人想点儿什么不用花力气,想怎么想,就怎么想,想得云天雾地都可以。现在他算是知道了,连想点儿什么都需要花气力啊!人没有了气力,连想都想不起啊!
老婆说:肺要是能换就好了,我把我的肺换给你一叶子。
我可不跟你换,我的肺里装的都是金子。
怎么说?
你没听人家说嘛,乌金乌金,煤就是金子。我肺里装满了煤,不就成了金肺嘛!
我听说金子特别沉,人的肚子里是不能装金子的,怪不得你的肺成了这样。我明天去赶集,再去医院给你买一袋氧气回来。
康新民不说话了。
你不要舍不得钱,人的命比钱重要。
我看你还是嫌我死得慢,要想让我死得快一点儿,你就买。氧气也是一种药,康新民去镇上医院看病时,医生用开药的处方给他开过氧气,老婆也去医院给他买过氧气。氧气不就是空气之一种嘛,以前康新民从来不把空气当回事,空气看不见,抓不着,好像空气从来不存在一样。他万万没有想到,空气也是值钱的东西,把空气收集起来也能卖钱。拿买一袋子氧气来说,要花好几十块钱呢。别看一袋子氧气那么轻,它的价钱顶得上整整一鱼鳞袋子小麦的价钱。一袋子小麦磨成面,够他们全家人吃半个月的。而一袋子氧气呢,他省着省着,只吸三四个钟头就完了。照这样的吸法,谁会吸得起。他存得是还有一些钱,但两个孩子都在上学,花钱的日子长着呢,花钱的地方多着呢,如果把钱换成气儿消费掉,孩子上学怎么办!康新民说着有些生气,又吭吭地咳嗽起来。他既然生了气,气应该多一些才是呀,不料他越是生气,越是气少。看来生气不增加气,而是消耗气。他一咳嗽,全身都在震动,以致他的脑袋像油锤一样锤在老婆的后脖梗上,锤了一锤又一锤。
老婆咬牙坚持着,不敢再说话,也不敢动。
康新民的娘在东间屋里睡,娘七十多岁了,耳朵还不聋。康新民一咳嗽,娘就听见了,娘呻吟了一声,说遭罪呀,遭罪呀!自从康新民的肺出了毛病,娘心里就一直不平。过去戴着地主帽子时,一家人被无形的帽子压得抬不起头来,喘不过气来,都跟着遭罪。熬呀,熬呀,总算熬到摘去了地主帽子,争气的儿子也挣到了钱,盖起了楼房,谁知道呢,我的老天爷,儿子的身体却出了毛病。人说老天爷最公平,娘觉得老天爷太不公平,出了那个井,又进了这个井,老天爷就是不让人有好日子过。
康家做饭不再烧煤。或许是因为煤存在康新民的肺里,使他们对煤有一种忌讳。或许是因为康新民闻不得烧煤的气味,一闻就出不来气。反正他们家一天三顿饭都是烧柴火,一点儿煤都不烧。他们这里是平原,没有煤矿,煤都是从几百里远的山区运过来的。几十年前,煤对他们来说可是好东西,稀罕东西。别看煤是黑的,拿一斤细白细白的白面,都换不到一斤煤。那时各家各户都无煤可烧,只有在生产队的打铁炉子里才能看到煤。黑黑的煤块子,一经点燃,拉动风箱一吹,煤块子就变得通红通红。把铁块子放进煤火里烧,不一会儿,黑色的铁块子也变得通红通红,真是好看!康新民小时候爱看煤火在炉子里一跳一跳的样子,还喜欢闻煤在燃烧时所散发出来的香味。真的,康新民在燃烧的煤里的确闻到了一股一股的香味,他不用特意吸鼻子,香味就沁入到他肺腑里去了。他拣起一小块煤,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没烧过的煤不敢拣,他只能从烧过的煤里拣出了一小块炼成琉璃的煤渣,闻来闻去,玩来玩去,玩了好长时间。
因为对煤有这么好的印象,后来有机会下到煤窑里看到那么多的煤,他才格外欣喜,挖煤挖得格外卖力。用小簸箕一样的大斗子铁锨挖一锨煤,他就想,这一锨煤,够我们家烧好几天的。挖一天煤,他估算了一下,他一天挖的煤够全村人烧一个月的。一个月挖下来,他把煤换算成了砖头,要是用他挖的煤到砖瓦窑上换砖头的话,盖一座楼房足够了。康新民还想到,挖煤比种庄稼来钱快多了。哪样庄稼都得长好几个月才能收割,打下粮食也卖不了多少钱。而煤是现成,弄到井上就能换回不少钱。他哪是挖煤,简直是在挖钱啊!崩煤的炮声刚刚响过,工作面浓浓的炮烟子和稠得打脸的煤尘尚未散去,他就冲进工作面去了,开始架棚子,攉煤。有人怕炮烟子,他不怕,他闻着炮烟子也有一股子香味。有人不愿让汹涌的煤尘扑到嘴里,干活儿时尽量闭着嘴。他觉得无所谓,吃点煤怕什么,下班洗澡时把煤吐出来就是了。他常常干得大汗淋漓,身上的毛孔都张开着,嘴巴和鼻子也张开着。包工头见他干得好,就表扬他,让别的挖煤的人都向他学习。得到包工头的表扬,他难免有一些感动。在生产队里干活儿时,他也从来不偷懒,不耍滑,干活儿干得也很好。可因为他家是地主成分,他本人是地主羔子,表扬不可能轮到他头上。得到了表扬,康新民挖煤挖得更来劲。窑上实行的是计量工资,谁挖的煤多,挣的工资就多。为了多挣工资,康新民一个班都舍不得歇,月月都是满班。
康新民只知道煤尘能扑到嘴里,钻进喉咙里,跑到肚子里,从不知道煤尘会被吸到肺里。肚子上下都有通道,煤尘跑到肚子里,在肚子那里是存不住的,要么吐出来,要么排出来。煤尘到了肺里就麻烦了。肺像是一条死胡同,煤尘只能进,不能出。或者说两个肺叶子像是两只口袋,东西可以装进口袋里,想把东西从口袋里取出来就难了。当康新民知道了煤尘可以通过气管和支气管吸进肺里,已经晚了,他的肺里已经吸进了不少煤尘,日积月累,煤尘已经在他肺里沉淀下来。原来他肺上有很多气泡,每个气泡里装的都是气体。现在他肺上的气泡变得很充实,每个气泡里都填满了物质性的煤。甚至可以说,那些煤都是优质煤,不用洗选,发热量就很高。他的肺原来软得像海绵,富有弹性。现在他的肺硬得像石头,一点儿弹性都没有了。
对于康新民来说,黑夜很长,白天也很长。在大长的白天,他也只能是坐着或站着。他不能多走动,也不能多说话。不管是走动,还是说话,都需要气力。气力气力,有气才有力,没有了气,就没了力。过去他不懂,以为人的力量长在肌肉上,肌肉发达,人的力量就大。现在他才明白了,人活一口气,人的力量全在气里。院子里,一只公鸡在追一只母鸡。母鸡跑得很快,公鸡跑得更快,公鸡到底还是骑到了母鸡背上。公鸡得胜之后,很是自豪地叫了一声。公鸡的行为很是让康新民羡慕,他现在连一只公鸡所具有的气力都没有了。
院子一角有一口压水井,康新民的弟弟康新生正在压动压井的手柄,从井里往上抽水。楼房建成后,康新民立即请人在院子里打了这口压水井。康新民领风气之先,在村里盖楼房的,他是第一人;在村里打压水井的,他还是第一人。以前,村里人吃水都是到村南的那口井里去挑,全村人共用一口。挑水要走一段路不说,水还不是很干净。打了压水井就好了,不出院子就能从地下抽出水来,而且水清凌凌的,喝到嘴里又凉又甜。压水井打好后,抽水大都由康新民操作。他不必用两只手摁手柄,只须一只手,就把抽水的皮碗子摁得呼呼响,水头蹿得老高。康新民的个头并不是很高,但他长得结实,是全村有名的大力士。麦子打完了,要把石磙推到场院边上立起来。有人两只手上去,脸憋得通红,都不能把石磙立起来。康新民过来了,他说他试试。他一只手抠住石磙的下沿,只用一口气,吭地就把石磙掀得站立起来。从坑里刨可以作肥料用的坑泥,用铁锨把坑泥从坑底甩到岸上。坑泥又沉又粘,从低处甩到高处不是很容易。有的力气小的男劳力,只能把坑泥甩到坑的半坡。而康新民呢,每次都能把满满一铁锨坑泥甩到岸上。有一次,康新民没把力气掌握好,嗖地一下子,坑泥飞到岸边的树上去了。树上有一个老鸹窝,把老鸹吓得呱呱直叫。现在康新民不行了,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彻底完蛋了。别说让他掀石磙了,他似乎连掀锅盖的力气都没有了。别说让他甩坑泥了,撒完了尿,他好像连甩甩尿鸡子都甩得少气无力。那么,家里还有一些重活怎么办呢?亏得康新民还有一个弟弟,他不能干的活儿,只能由弟弟代替。
不看弟弟压水还好些,看弟弟压水,康新民实在替弟弟着急。弟弟一只手摁不动压水的手柄,只得两只手都上去摁。弟弟摁得很慢,抽出来的水在水簸箕里流得很细,放在水簸箕口接水的小桶半天都接不满。不管水流得有多细,压水井的铁制水筒子里不能缺水,一旦缺了水,水筒子里的水就降下去,里面都成了空气。要是想压出水来,得重新往井筒子里的皮碗子上面倒引水,由于引水的密闭作用,才能保证抽出来的是水,而不是空气。弟弟的两只手摁了一会儿手柄,张着嘴在那里喘气,弟弟的气力似乎也不够用了。为了使水不致断流,弟弟只能把小肚子也压在铁手柄上,借助身体的重量,把手柄压下去。看着弟弟那费劲的样子,康新民真想过去一把将弟弟拉开,他自己去压水。可是不行啊,他哪里还有拉开弟弟和压水的气力呢!
康新民感到痛心的不仅是他自己,还有他的同胞弟弟康新生。康新民到煤窑挖煤挣到了钱,盖了房子,成了家,他希望弟弟跟他一样,也能尽快挣钱盖房,自立门户。爹去世了,康新民作为当哥的,他觉得他有责任帮助弟弟成家立业。于是有一年过罢春节,康新民也把弟弟带到煤窑里去了,让弟弟跟他一块儿干。他以为自己干了一件好事,其实是干了一件坏事。他以为是一个便宜,其实是一个当。吃苦耐劳的弟弟跟他一样,也把煤尘吸到肺里去了,弟弟的肺也变成了黑色的煤肺。只不过弟弟的病情比他稍稍轻一些,低一个级别,他的尘肺病是三期,弟弟是二期。弟弟呼吸起来不像他那么费劲,体力活儿还能干一些。弟弟的身体成了这样,老婆是找不到了,只能跟他这个当哥的一块儿过。
听本村在外面当干部的人回来说,像康家兄弟这样得职业病的情况,应该到挖过煤的小煤窑那里要求赔偿,每人获赔二十万或三十万,都是有可能的。听了干部的话,康新民有些动心,心想,要是能得到一些赔偿,就算自己花不成,留给老婆孩子也是好的。肺不行连累得他的腿也不行了,他已经没能力外出,只能让弟弟到小煤窑去问一问。弟弟去了几天回来了,说那个小煤窑没有了,井架子拉倒了,井筒子也炸塌了,只剩下一个黑洞洞的洞口,洞口周围长满了荒草。弟弟听人说,那个小煤窑属于非法开采,是上级派人把煤窑炸掉的。至于那个小煤窑主,谁都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
康新生去小煤窑讨赔偿,娘抱了很大希望。见二儿子空着手两只手回来,娘失望地哭起来,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他不埋怨人,只埋怨老天爷。她的埋怨还是老一套,还是把戴着地主帽子时和现在一起埋怨。她说老天爷呀,过去俺家的日子不好过,眼巴前儿俺家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俺家两个儿子的肺都坏了,家里老的老,小的小,今后的日子咋过呀!老天爷呀,你咋不睁开眼可怜可怜我的两个儿子呢!难道你的肺也坏了吗!
初春的天气真是变幻不定,冷冷暖暖,暖暖冷冷,让人无所适从。农历过了二月二,龙的头都抬起来了,却又下起了雪。雪下得还不小,铺了天,又盖地。杏花本来就要开了,雪花一开,就把杏花给盖了。患尘肺病的人经不起忽热忽冷,下雪天寒气袭来,康新民连用来咳嗽的气似乎都没有了。不管是站着,还是趴着,跪着;不管他是头朝上,还是头朝下,都呼不出多少气,也吸不进多少气。他把嘴巴和鼻孔都张到最大限度,甚至连身上的汗毛孔好像都打开了,仍无济于事。他的脸憋得黑紫,紫得他的脸好像也变成了一块煤。由于憋气,他的眼珠子越鼓越高,似乎眼看就要从眼眶里掉下来。他的眼睛还能看见自己的老婆,还想跟老婆说话,就是说不出话来。康新民真恨自己啊,恨不得把自己的肺扒出来,喂狗吃。又一想,连狗都不吃他的肺啊!康新民心中也有不平的地方。村里的那些懒人,人家都活得好好的。就是因为他太勤快了,太能干活儿了,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这个世界不需要勤快人了吗?难道人越勤快就越遭殃吗?
康新民的老婆悄悄把康新生叫到一边,让他赶快到镇上为康新民买一袋氧气。她知道,丈夫不愿再花钱买氧气,不想让家里重新返贫。可是,她实在不忍心眼看着忠厚的丈夫离她而去,丈夫能够多活半天也好啊!
冒着大雪,康新生到镇上的医院为哥哥买回了一袋氧气。在回家的路上,走在雪地里的康新生已累得气喘吁吁,跌跌撞撞。他跌倒了,趴在雪地里喘口气,再爬起来往家里赶。他怀里紧紧抱着那袋子鼓鼓囊囊的氧气,如同抱着哥哥的肺。他在心里呼喊着:哥,哥,你别急着走,你千万要等着我啊!要是康新生打开氧气袋子吸上两口氧气,他走得可能会稳当些,也快一些,因为他也是尘肺病患者。可康新生只想着哥哥,吸氧气的事他想都没想。
然而,康新民拒绝再吸氧气,看见氧气袋子,他摆了一下手,头一歪,就死去了。
雪还在下,树上、柴火垛上、房顶上都是白的。
娘哭得更痛心痛肺些。她的哭诉没有什么新观点,只是埋怨老天爷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了自己:你咋还不死呢,不该死的死了,你还活着干啥呢!
康新民去世一段时间后,在村民的撮合下,康新生和嫂子结了婚。哥哥死了,嫂子不愿离家,便和弟弟结了婚,这不算什么稀罕事。
乌金虽好,到了人的肺里就不好了。康新生哪里知道,人的肺一旦变成了乌金肺,一旦呼吸困难,就做不成男人了,一次都做不成了。
结果,结婚第三天,康新生就上吊自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