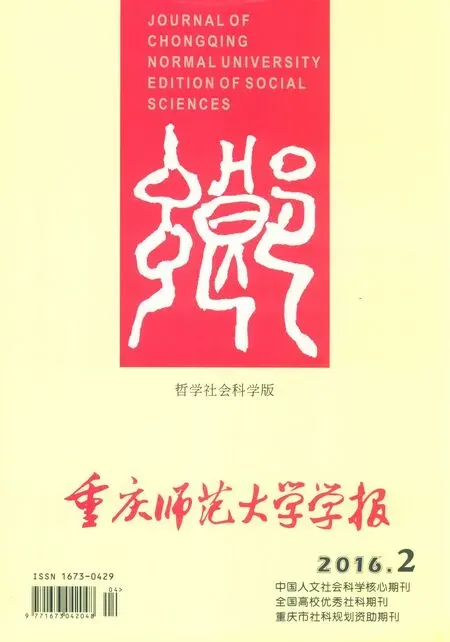明代夔州府教育述论
2016-06-13唐春生杨强强
唐 春 生 杨 强 强
(1.重庆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 400047;2.甘肃省秦安县桥南中学,甘肃 秦安 741600)
明代夔州府教育述论
唐春生1杨强强2
(1.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重庆400047;2.甘肃省秦安县桥南中学,甘肃秦安741600)
摘要:明代夔州府,处于朝廷与蜀地联系的“中间地带”,形势险要。明廷为加强对川东夔州辖区的管理,以地方教育设施的重建为契机,辅之以书籍、图画的“颁赐”,将“中央之手”伸入地方社会。由此个案,可见国家与地方在教育事业中的动态关系。
关键词:明代;夔州府;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就存在着社会控制与反控制的思潮。文化人的这种价值取向,代表了一个国家精英阶层的意识走向。纵观秦以来的封建君主,文化专制在思想领域并非专门针对读书人,统治者注重对社会上两部分人的“控制”,一是少数人,如余英时先生所说的“知识阶层”[1]1,即“社会精英”,二是“普通大众”,即老百姓。对上层知识分子推行官方主导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典型的是“学而优则仕”的功利诱导;而对于社会下层(以农民为代表),则是“愚民”政策,体现在地方教育的官方主导上。
纵观大明帝国,其统治深深打上开国君主的烙印。就明代的文化政策而言,虽和历朝历代一脉相承,但由于时代性、君主意志的差异性,从而折射出其文化风教的独特性。“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2]卷69《选举志一》,1675。太祖朱元璋深谙治国之道,说:“四民之中,士最为贵……最为贵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3]卷5,274在朱元璋眼里,士人应以“为君用”为终极目标。因此,天下读书人的教育问题成为封建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
一、师生规模与教育基础设施
明代主管教育的最高行政机构是礼部,礼部下设仪制郎中一职,“分掌诸礼文、宗封、贡举、学校之事”[2]卷72《职官志一》,1746。在地方,各级政府负责管理地方教育。明太祖“诏郡县立儒学,设教授、学正、教谕、训导有差,廪给诸生”,“府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俱设训导,府四,州三,县二”[4]卷3洪武二年十月辛卯,401。有明一代,全国共有府140,州93,县1138,明太祖在洪武初年就规定:“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县以次减十。”[2]卷69《选举志一》,1675就全国而言,据商传教授估算,按照地方儒学的设教编制,府有教官5人,州4人,县3人计算,应有教官4486人,加上边地军事卫所,安抚司、宣抚司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全国教官人数在4500~5000之间。这些教官管理着5万以上的生员,如按全国5000万人口计算,生员的比例在0.1%~0.2%之间[5]209。假设地方学员满额,正德年间,夔州府应有教员41人,“廪膳生员(官方固定的生员)”280人,按全夔州府102710[6]卷4《户口》,81人计算,生员比例为0.2%,反映出夔州地方官方生员的入学比率与全国基本一致,如果将“增广生员、附学生员(地方官学固定生员外增加的学员)”、“乡里学舍生员(社学、私塾、家馆等生员)”计算在内,夔州府生员入学比率将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明代官方学校除了教官与生员外,还有大量的基础管理配套设施,这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洪武四年(1371),夔州府学建立。成化十年(1474),废奉节(夔州府治所在地)县学,因城隍庙“逼近府学”,郡守吕晟便将庙宇迁至奉节县学旧址。弘治十三年(1497),郡守杨奇又拓展学校,“规模制度”因而“冠于别郡”[6]卷6《学校》,109。在地方教育机构规模壮大的同时,基础设施也更加完善。夔州府、县学管理设施如下:

表1.1 正德年间夔州府学基础设施
据《正德夔州府志》卷6《学校》,第109~110页。

表1.2 正德年间夔州府地方县学基础设施
续表

名称教育设施备注大宁县儒学建始县儒学文庙五间、戟门、棂星门各三间、明伦堂五间、二斋(崇德、广业)、仪门、儒学门各三间、教谕宅、训导宅二(各二间)、射圃、社学文庙五间、戟门、棂星门、明伦堂三间、二斋(诚意、正心)、仪门三间、儒学门三间、教谕宅、训导宅二(各三间)、射圃、社学
据正德《夔州府志》卷6《学校》,第110~113页。
表1.1、表1.2反映出明代地方教育有着较为规范的配套设施,府学、县学层级分明。如上文所述,生员的数量决定了学校的级别和设施的完善度,夔州府学无疑是当地最高的官方教育机构。明代的地方教育设施按其用途可分为两部分:
一是由文庙、戟门、棂星门、明伦堂、射圃等构成的“象征性礼制”的场所。生员在学校除了阅读“尊经阁”藏书、撰写道德文章外,还须亲身参与严格且繁琐的各种典礼,每天早晚在堂上行“恭揖礼”,参加文庙祀典,“规整的祭器”、“庄严的形式”会对生员留下更为深刻的印象。还有“射学”,“遇朔望,习射于射圃,树鹄置射位,初三十步,加至九十步。每耦二人,各挟四矢,以次相继。长官主射,射毕,中的饮三爵,中采二爵”[7]卷78《学校·学规》,1241。正德年间,夔州十二所县学都有“射圃”场所,我们虽不清楚“射学”的内容与洪武时期有何区别,但是这种古老的“学习项目”在明中期地方学校仍在延续;这些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为书本所没有,“庙貌器数以严礼,经籍斋舍以讲道,射以观德”,最终使学校达到“张教化、明人伦”[8]卷上《学校》的目的。
二是由学田、馔堂、宰牲房、学仓、教谕宅、训导宅构成的生活设施。朱元璋规定:“师生月廪食米,人六斗,有司给以鱼肉。”[2]卷69《选举志一》,1686在一系列的制度保障下,学员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才能正常进行。梁山县学中,还保留有“学田”作为学校日常用度的补贴。在明代,学田属于“官田”的范畴,是不能买卖的国家所有土地,但通过对其它十二所学校财产的考察,再结合明代中期以来的“官田”私有化“运动”,以及四川地区民田占绝对地位的史实,可以推测,在嘉靖年间,夔州府、县“学田”有可能已经私有化,梁山县学“官田”属于特殊现象,并没有普遍的代表性。
此外,明廷中都察院掌管全国的教育监察,实行中央巡按御史与省级按察使双重监督体制。如正统元年(1436),设提督学校官管理地方学政,主要负责考察生员、举行岁考、惩办违纪者。[2]卷75《职官四》,1851总之,明代的教育管理比较的严格,其专业化、制度化的趋势明显。
二、官学、私学、书院共存的办学格局
明代的教育有官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分。“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2]卷69《选举志一》,1675上至国子监,下至县学都是国家主导的官方教育机构,以灌输儒家思想、培养各级官员为目标。除此之外,地方上遍布着私人教育的私塾、家馆等。这其中最特殊的是书院教育(明代书院教育机构地位特殊,有官方主持的,也有私人主持的,情况复杂,明代夔州府辖区书院性质在方志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书院不单纯是宣扬教化的地方,也是学术中心,晚明书院甚至成为国家政治的“风向标”,如顾廷龙等人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对晚明政局影响深远。在对夔州府地方教育的论述中,本文以官私教育机构、书院、书籍等为切入点,进行重点阐述。
(一)官私教育机构
朱元璋曾言:“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2]卷69《选举志一》,1686“盖无地而不设之学,无人而不纳之教。”[2]卷69《选举志一》,1675洪武四年(1371),四川地区逐步纳入帝国的版图后,蜀地的教育也迅速恢复起来。据表2.1,夔州府地方教育机构,其辖区的十二县(属州)除东乡县学、太平县学建于成化、正德年间,其它包括府学在内的11处学校都是在洪武四年至洪武十八年(1371-1385)建立的,反映出明廷对地方教育的高度重视,而学校创建的最终目的是“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2]卷69《选举志一》,1675。据蓝勇教授统计,明代夔州府共考取进士28名,其中云阳县有2名。[9]107

表2.1 夔州府学校建立情况
据嘉靖《四川总志》卷10《夔州府·学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99~200页。
“学校所设,崇祀圣贤,造就人材,为风化政治之源,所系甚重。其所修废,在有司知所轻重耳。”[9]卷13《学校志一》,427洪武年间新宁知县陈秉彝,成化年间万县知县徐熙、梁山知县吴珏、东乡知县吴新、大昌知县魏琎,弘治年间的夔州郡守杨奇,正德年间的吴潜等人都是地方教育事业的积极“倡导者”,他们重视当地教育,或是为了宣扬德化,或是为了博得声誉,但无疑都对地方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各地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洪武时期确立的府、县官学“体制性缺陷”日益显露(特别是对生员人数的限制),不利于教育的推广,而地方半官方的“社学”正好弥补这一缺陷。洪武八年(1375)“诏有司立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10]卷60《社学》。社学即“乡里则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学,愿读书者……以百家姓氏千文为首,继及以经史律算之属”[11] 外编卷22,1151-1153。可以试想一下,在洪武、永乐、正统、成化、弘治年间,由于朝廷的提倡,在最基层的乡里遍布着大大小小的社学,它们将朝廷的意志宣扬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不过,到明中期,就全国教育发展的趋势而言,官学由于与科举的密切关系而得以“强势”,私塾、家馆等民间教育形式发展迅速,社学却已渐渐衰退。从夔州府的情况看,9个县保留了社学,由此可以推断,夔州府境内的社学可能作为官方教育的补充依然在发挥一定的作用,或者仅仅作为一种地方“符号”而存在,没有淡出百姓的视野。
(二)书院
书院是有别于一般学校的高级教育机构,兼讲学与学术交流为一体。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立尼山、洙泗二书院”[4]卷3洪武元年十一月甲辰,377,这是明代书院设立的最早记录。四川地区的书院发展,胡昭曦先生做过详细的考证,梳理了各个时期书院发展演变的过程,代表性的有宋代北岩书院、元代紫岩书院、明代南轩书院、清代尊经书院等;元代时四川有书院11所,占全国的3.6%(全国296所),在各省排位第7;明代四川有书院90所,占全国的5.2%(全国1699所),列全国第8位[12]48-49。钱穆先生曾对宋明的“书院制度与讲学风气”有着高度的评价:“书院的开始,多在名山胜地,有社会私人捐资修筑。……但书院教育的超政治而独立的讲学之风格,是始终保持的。”[13]189
除了官学、私学外,夔州府还存在一定数目的书院。由于文献记载的模糊性,很难对部分书院是公办还是民办做出准确的判断。下面我们对夔州府书院的设置列表于下:

表2.2 夔州府书院统计
续表

书院名称创建时间地 点备 注集贤书院夔龙书院嘉靖十三年(1534)知县欧纂中建。明时建立(具体时间不详)。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学西。在夔州府治(今重庆奉节)。少陵书院(杜少陵草堂)凤山书院不详不详在夔州府(今重庆奉节)治东十一里。大宁县(今)凤凰山上。据《正德夔州府志》卷6《书院》静晖书院不详不详据《嘉靖四川总志》卷10《夔州府·学校》。
据正德《夔州府志》、嘉靖《四川总志》《四川书院史》制。
由表2.2可知夔州府共有9所书院,正德年间建立了1所,嘉靖年间建立了3所,万历年间设有1所,其他4所没有具体的设立年代,胡昭曦先生统计了6所,缺少陵书院、凤山书院、静晖书院。总体而言,夔州府的书院设立集中在明中期(特别是嘉靖、万历年间),这与全国书院建设的“第三次复兴期”(第一次为正统年间、第二次为成化年间)是一致的。在9所书院中,夔州府治所在地奉节县有3所(仰高书院、夔龙书院、少陵书院),这与“高级地方政区”的级别、经济的发展、人口的数量有密切的关系。
夔州府的书院从明代一直延续至清代,例如清代奉节县境内有少陵书院、峨麓书院[14]卷18《学校》。书院相较于官学、私塾、社学等有其特殊性,没有固定的师生,全国各地之人可以慕名而来,这主要取决于书院的名气和“山长”(书院的主持人)的名望。历史上,书院除承担教学工作外,还成了各地学者学术讲座、交流的平台。
三、颁赐书籍:教学内容的依据
明代官方儒学、私人性质的家学、族学、书院,以及半官方的社学都是封建国家培养人才的场所,而“官方规定的书籍”则是传播知识的最重要载体,更是“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定传递者”[15]210。
由于书籍作为知识的载体,引领着社会思潮的走向,因此历代统治者对社会上流通的书籍都很关注。洪武皇帝在位的30多年间,深知武功、谋略足以戡乱,但治国的关键在于对知识以及“读书人”的控制与引导。在朱元璋倡导的民众所读书籍中,有传统的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又有法律条文及其礼仪文献,更具特色的是“劝谕”诏令,这些书籍几乎涉及到臣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教民榜文”中关于“太祖六谕”的宣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16]卷8《教民榜文》,这主要针对的是乡间的老百姓,让他们安分守己,以利于地方的稳定;读书人则在各级学校接受正规的教育,程朱理学是他们读书考试的核心内容。太祖以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也颁赐书籍于府、州、县,如“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2]卷70《选举志二》,1694。官方颁赐的书籍有以下几类:一是儒家经典,有《四书大全》36卷,《五经大全》68卷,《性理大全》70卷,《四书集注》(朱熹)26卷;二是法律、行政及礼仪文献,包含《大明令》(1368年)1卷,《皇明祖训》(1373年)1卷,《大明律》(1397年)30卷,《诸司掌职》(1393年)10卷 ,《射礼集要》1卷,《大明会典》(1503年)180卷,《大明集礼》(1370、1530年)53卷;三是劝谕文献,其中有《大诰》(1385—1387年) 1卷,《教民榜文》(1398年)1卷,《劝善书》(1407年)19卷,《为善阴骘》(1419年)2卷,《孝顺事实》(1420年)2卷,《五伦书》(1443年)62卷;四是嘉靖仪礼,含《大礼集仪》(1525年)4卷,《明伦大典》(1528年)24卷,《大狱录》(1528年);五是地理、历史文献,有《大明一统志》(1461年)90卷,《大学衍义补》(邱濬,1506年)160卷,《资治通鉴纲目》(朱熹)(成化年间,1465-1487)59卷。[15]209-210
除上列书籍外,还有《礼仪定式》《表笺式》《新官到任须知》《韵会定式》《科举程式》《朔望行香体式》等[17]卷5《艺文志》,后代继任者还陆续颁布地理、历史等文献,作为地方官方藏书的补充。在弘治《句容县志》中还记载了其他的官方书籍,包括《宇宙通志》一百本、《彰善录》二本、《汉书》四十本、《文献通考》六十本、《逆臣录》六本、《皇明制书》八本;[18]卷2《儒学·国朝颁降官书》,嘉靖《建平县志》记载有《钦明大狱录》二本、《山堂考索》十七本、《学史》二本;[19]卷3《儒学·本学贮库官书》湖南慈利县于永乐十二年(1414)、十七年(1419)、十八年(1420)等年份由朝廷颁赐书籍,其中有《考工记》四本、《行移体式》一本;正统十二年(1447)又一次颁降了书籍[20]卷11《学校·书籍》。
对图书的管理,明代各地特地修建“尊经阁”、“御书楼”、“官书库”、崇文阁、聚奎阁、文昌阁、藏经阁等藏书机构。据卜正民先生研究,明代地方藏书楼一般都集中在官学中,学校藏书楼多称为“尊经阁”[21]210。对于图书的管理与使用问题,从方志史料可以推断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洪武、永乐时期颁赐于地方的图书,至万历时期,“(书籍)但岁久散佚,存着无几”[20]卷11《学校·书籍》。
具体到夔州府地方教育教学内容,现有文献中惟云阳的情况记载最详,故以此地为例来加以探讨。云阳东临奉节县,西接万州,南至湖北恩施,北到巫溪县,作为标准的县级设置,在川东具有代表性。通过分析嘉靖时期云阳的教育事业,可以掌握明中期地方文化治理的情况。明代的府设置“教授一名,训导四人;掌教诲所属生员”[2]卷75《职官四》,1850。在县设置“训导二员、司吏一名,主管教育”[8]卷上《创设五·设官》。
明代正德年间,云阳县的官方藏书,通过表3.1反映出,除了大部头的“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2]卷70《选举志二》,1693外,还有特制的“图”,如“乡饮酒礼图”[7]卷79《礼部三十七·乡饮酒礼》、“朝祭服图”[7]卷61《礼部十九·冠服二·祭服》等,图与书相辅相成,图悬挂于墙,而书存于“御书楼”[8]卷上《学校》,而拥有官方颁赐的书籍是官学的重要标志。云阳县的官方藏书可能还有其他没有记载的,县志中特别列举出16种“书册”,是为突出这些书籍在官方教学中的重要性,更是中央文化政策渗入地方的突出表现。三部《大全》(《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的问世,不仅加强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统一”,也为科举考试提供了钦定的教材。自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朱棣命礼部将官方书籍颁行至全国的各级学校,《大全》便成为莘莘学子步入仕途前所必修的科目。至明代中后期,随着图书出版业的技术进步,出现了一些印刷书籍的中心(如闽南地区),商业利润的诱使,加快了书籍的普及速度。

表3.1 明政府“钦颁”云阳县的图书
据嘉靖《云阳县志》卷上《钦颁书籍》。
据周绍民研究,明初曾将书籍颁赐至府、县,府的藏书不超过2000册(其中还包括地方捐赠与购买的),县的藏书更少,以供学生使用[22]119。云阳县的情况正好与之相符,官方文化的传播与封建政府的主导不可分割,而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对以书籍为主要媒介的文化传播作用也不可忽视。
四、结语
大明帝国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相较于文教发达的江南富庶之地,僻处西南一隅的夔州在当时并不起眼,因为大明帝国地域辽阔,四川辖区内就有13府(成都、保宁、顺庆、夔州、叙州、龙安、马湖、镇雄、乌蒙、乌撒、东川),而在全国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140府[2]卷40《地理志一》,882。相较于全国,结合夔州府当地的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就其文化教育而言,可能没有“典型性”。尽管如此,通过对明代洪武至正德时期的学校建设、书籍管理政策进行“重构”,仍能体现出国家对地方文化事业的渗透、管理。地方与中央往往是区域史研究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纯粹的脱离彼此的论述都难免陷入武断与“特殊化”的误区中。我们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一)明代夔州辖区11县的学校建设,主要集中在洪武四年至洪武七年(1371~1374)期间,建学校9所,占整个夔州府学校总数的70℅。由于这时期四川地区刚归附不久,学校的重建与四川辖区的管理同步进行,反映出国家对地方文化教育的重视。在明洪武以后,地方学校的建设多和地方辖区的调整有关系,如正德年间设立的太平县学。
(二)明代夔州府的文化教育内容的依据,与官方认可的书籍有密切的关系。结合云阳县的案例,其中在洪武、永乐年间,朝廷都“颁赐”书籍(图),干涉地方的文化走向,以期将地方文教引入政府的“轨道”。其中的书籍主要分为几类:涉及科举的儒家经典,关系地方民风民俗的礼仪教化书籍,还包含地理、历史方面的图书。其中云阳县出现的御赐“图画”,在明代的地方志中较为少见。
(三)明代国家重视对教育事业的监督与管理,基层教育设施比较完善,国家通过颁赐书籍、考试等方式,将读书人禁锢在程朱理学的牢笼里,这对“后封建时期”的科技文化走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 [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 [明]余继登.皇朝典故纪闻[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4] [明]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 商传.明代文化史[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
[6] (嘉靖)建平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
[7] [明]申时行等.明会典[Z].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万历)慈利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
[9] 何向东,习光辉等校注.新修潼川府志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7.
[10] [明]王圻.续文献通考[M].济南:齐鲁书社,1997.
[11] [清]全祖望.鲒埼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2] 胡昭曦.四川书院的发展与改制[J].中华文化论坛,2000,(3).
[13] 胡昭曦.四川书院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
[14] (光绪)奉节县志[M].四川省奉节县县志编纂委员会重印本,1985.
[15] [加]卜正民著,陈时龙译.明代的社会与国家[M].安徽:黄山书社,2009.
[16] [明]张卤辑.皇明制书[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17] [明]黄润玉.成化宁波府简要志[M].四明张氏约园刊本.
[18] (弘治)句容县志[M].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
[19] (正德)夔州府志[M].天一阁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
[20] (嘉靖)云阳县志[M].天一阁明代地方志选刊影印本.
[21] 蓝勇.西南历史文化地理[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22] [美]周绍民著,何朝晖译.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力]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 of Kuizhou in Ming Dynasty
Tang Chunsheng,Yang Qiangqia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Society, Chongqing Normal Univesity, Chongqing400047;Qiaonan Middle School of Tai’an County, Gansu 742600, Chian)Qiaonan Middle School, Qin’an County, Gansu,741600
Abstract:Kuizhou in Ming dynasty located between Sichuan and Beijing, occupied an impotant positi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Kuizhou in eastern part of Sichuan through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local education facilities, supplemented by awarded books and picture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society can be detected in this case.
Keywords:Ming dynasty; Kuizhou;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5-12-21
作者简介:唐春生(1964—)男,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杨强强(1987—)男,甘肃省秦安县桥南初级中学教师,历史学硕士。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2—004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