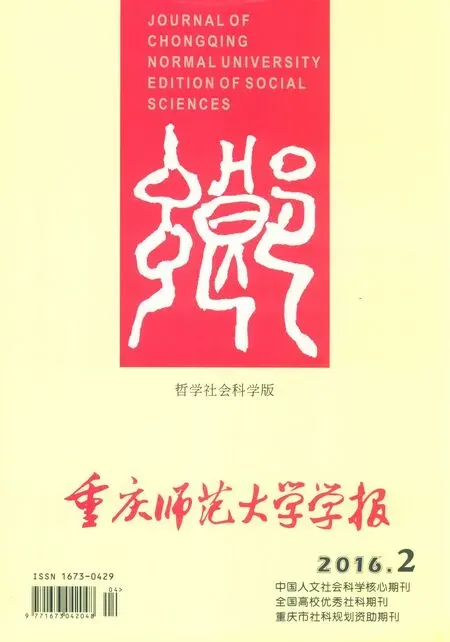抗战时期修筑川滇铁路的意义及其艰难历程
2016-06-13唐靖王亦秋
唐 靖 王 亦 秋
(昭通学院 管理学院,云南 昭通 657000)
抗战时期修筑川滇铁路的意义及其艰难历程
唐靖王亦秋
(昭通学院管理学院,云南昭通657000)
摘要:抗战军兴,沿海交通干线相继沦陷敌手,当时的南京中央及地方川滇黔三省政府均对修筑川滇铁路的前景抱有热切的期望,将其视之为联络抗战心脏及繁荣地方经济的大动脉,国民政府不惜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想尽办法,通过国库拨款、公债发行、向外国借款等多种方式,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1938年开始实际的勘测、施工,但却因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而最终壮志未酬,仅完成昆明至曲靖沾益段便被迫停工,成为中国八年抗战漫长苦难历程的缩影。
关键词:抗日战争;川滇铁路;叙昆铁路
在西南铁路修筑史上,曾经有过一条晚清时期便已筹建、抗战时期曾被寄予民族复兴厚望并再次着手勘测修筑,但却因种种原因而只建成部份地段的铁路,这便是川滇铁路。这条铁路在清末规划中命名为滇蜀铁路,抗战时期因拟先修筑其中的叙府(今四川宜宾)至昆明路段,因而也常被称为叙昆铁路。抗战军兴,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沦陷敌手,沿海铁路干线也先后被日占据,云南成为西南大后方,但又交通不便,军运迟滞。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首先应求军事与交通之配合,故有兴建川滇铁路之议,由交通部与四川省政府、云南省政府联合组织川滇铁路公司理事会,并首先成立叙昆铁路工程局主办其事。该路段起自四川叙府,中经盐津、昭通、威宁、宣威、曲靖而至昆明。当时的南京中央政府决定,三年建筑此路完成,连接印缅出海口与陪都重庆、天府四川,开发沿线矿产,藉以支撑抗战军需。这条计划中的抗战大动脉,在1938年开始实际的勘测、施工,但却因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而中途挫折,仅完成昆明至曲靖沾益段便被迫停工,成为中国八年抗战漫长苦难历程的缩影。目前学界尚乏专门论著涉及该路建设的起因及过程,本文略作梳理如下。
一、抗战前后国人对修建川滇铁路的价值认识
南京国民政府素来号称以三民主义立国,重要事务无不秉承其先总理孙中山的教诲。而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就有专节对开发西南边疆的富饶矿产作过畅想,指出近代工业“最重要之原质者,是为钢铁”,而“四川、云南等地方之铁矿,亦可次第开采”;而“四川、云南与扬子江一带,皆中国铜产最盛之区。由政府开采之铜矿在于云南北角之昭通者,经已数世纪之久矣。中国向来通用之钱币,几乎全赖云南铜矿以制造之……中国将来之工业发达,用铜之途必增至百倍”,加之云南个旧之锡矿等项事业,均应通行考察,投资开发,依国际发展计划经营开采,挖掘其实际利益。[1]389-392
但要开发西南矿产,交通实为第一要义。为了沟通川滇,自秦时已开五尺道,汉后续修南夷道、石门道。1814年,史蒂芬孙发明蒸汽机车,标志着人类开始进入铁路时代。云南虽僻处国家西南,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被动卷入。英、法两国殖民者,在侵占了缅甸越南后,即向资源丰富的中国云南进逼,策划从西南打开中国后门。法国在取得滇越铁路的建筑权后,英国亦欲援“利益均沾”之例,企图从缅甸修建一条铁路进入云南,实现与长江流域的铁路相连接的侵略计划。但云南地方有感于滇越铁路主权丧失,力谋补救,遂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组成“滇蜀铁路公司”,“急议修筑滇蜀铁路,官商合办,筹集盐、粮各股”[2]22,同时还开办铁道学堂,勘定路线,未雨绸缪选送学生赴比利时学习铁道工程。后因“革命风潮云起,政府变更,主管意见纷歧,遂致迁延贻误,经济交通大受损害。[3]1024
对时人而言,川滇铁道的价值“在云南为向内联系之大动脉,在全国为向外活动之头臂筋。关系军事、经济、文化、交通、国防周密,民生繁荣、内外结合,至重且大,早宜全力完成”。比较起修复中的滇越铁路和拟建中的滇缅铁路来,川滇铁路的重要性“有过之无不及”,因为“以贫瘠之云南,位于国防前线,若不使向内联系之大动脉畅通,虽滇越、滇缅两铁道即刻完成,亦仅局部交通之便利,尚不足言建国图存。”[3]1024
如果说以上言论出自于云南志书,其地方倾向性值得怀疑的话,那么在国统区《游击》这样因抗战而兴的杂志上,一位非云南籍的作者对修建滇蜀铁路(即川滇铁路)重要性的强调,就更加引人注意。该文作者分析,武汉之所以一度成为抗战中国的心脏,在于其独特的交通位置,即东西方向有长江,南北方向则有平汉、粤汉铁路,有这两条大动脉的贯穿,使其在抗战初期“总算极尽吐故纳新之能事”,仅广西一省,至少有四十万军队通过粤汉铁路输送至前线,其他如军火、机器、货物等,无不靠这条铁路运输,全面抗战才得以支撑。但眼前风云突变,长江被封锁,平汉路被切断,广州、武汉失陷从形势上看也只是时间问题,武汉这颗抗战的心脏便有完全停动的危险。这样,中国的抗战前途岂不渺茫?作者认为:“欲求最后胜利,尤非持久不可”,真正问题不在于武汉之能否坚持,而在于武汉失守后“有没有第二个心脏来替代,有没有第二条大动脉来贯穿这个新心脏”?随后作者进一步分析说,位于天府之国的重庆,已然是抗战的新心脏,而在规划中的滇蜀铁路则是连接出海口与天府之国的大动脉,“这条铁路一旦成功,那么这个新心脏,就可永远活泼泼地跳跃”着了,因为它有如下的重要性:第一,代替原粤汉路的地位;第二,东达重庆,西达成都,连接抗战的经济政治中心;第三,通向天府之国,内地经济充分周转,进出口得以保持平衡,丰富物资可源源出口;第四,铁路所经各地矿产丰富,具有极高的经济与战略价值。更重要的是,这条铁路已经进入实际的运行阶段。全路估计需款一亿,由中央与地方分担。中央为早日成路,已拨款一千万,川滇两省亦合筹五百万,并已派队测量,完成之期,当不在远。最后,作者以乐观的口吻欢呼道:“新的心脏,已完成;新的动脉,已兴筑。读者们,武汉即使不保,我们又何必着急或悲观呢!”[4]
相类似的另一文章也评论说:“际此抗战紧急之秋,后防的交通,关系战局至深至巨,尤以国际交通线,更为重要。政府有鉴及此,早已计划修筑川滇铁道,以与滇越铁道连接,直达安南,免被敌军封锁海口,有断绝国际关系之虞。兹修筑川滇铁道理事会,将在昆明开幕,商讨一切事宜,川省政府闻已内定派刘航琛、甘绩镛二氏前往参加,同时并组织勘测队,勘测路线,日内即可分头出发。并悉关于修筑川滇铁道的经费和材料诸问题,已有具体办法。倘此路能于最短期完成之,则敌人拟断我国际关系与国际接济之企图,完全粉碎。”[5]
此后抗战形势急转直下,川滇铁路未能按计划修筑,使以上作者的乐观预期落空,但川滇铁路的价值并未因抗战外因的结束而被否定。在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上,凌均吾等24位代表联名提案,要求政府依照原定计划将叙昆铁路继续从速修筑,使其早竟全功。各代表提出该案的理由也基于这一铁路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此路南端由昆明延长与滇越滇缅铁路接轨,对于海外交通,至为便利;北端由叙府延长与成渝铁路接轨,所有上下川南数十余县物产,均可由此路输出,将来更进而与天成铁路(天水至成都)衔接,则所关更不仅西南一隅,即西北各省之物资运输,由此可添一重要海口,而此路沿线地方之工商农矿,其繁荣发展,殆不可限量矣,于斯时也,西南西北各省与海外交通,不但可以缩短里程,且可以减少时日,推而至于文化之沟通,经济之调剂,政情之观摩,消息之传达,尤属利莫大焉。”有见于此,国民政府战后还都南京,蒋介石在离川时临别赠言,曾向川人承诺“叙昆铁路之积极继续建筑,实有不容稍缓之势”,将在“短期内完成此路”,“俾资发展西南交通,增进川滇实业,俾战后凋疲之民众经济藉以改善,元气得以恢复”。可见,川滇铁路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抗战的功利需要,也非“狭意之地区利益”,“洵有助于整个之国计民生”。[6]
二、川滇铁路公司的成立及其性质
如上所述,重庆在抗战军兴后成为战时首都,考虑到由长江上游接通昆明的铁路,可以使重庆能借一段水路与国际铁路交通联系,具有重大的战略价值,因而铁道部于1937年底与四川及云南两省政府商定,组织川滇铁路公司,由川滇两省各出资五百万元,中央出资一千万元,另由交通部洽商材料借款及不足之工款,兴筑川滇铁路。[7]336
1938年1月21日,国民政府公布《特许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十四条,申明川滇铁路公司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经铁道部转呈行政院呈请国民政府特许组织”。公司经铁道部核准,先行建筑及经营自昆明至叙府的铁路干线,以及其延长线暨其他应需之支线、铁道部核准建筑及经营其他的铁路路线,所以当时媒体亦多称此铁路为“叙昆铁路”。《条例》第四、五条规定,公司营业期限定为三十年,股本总额为国币二千万元,分为二十万股,每股一百元。其中,铁道部认十万股,云南省政府、四川省政府各认五万股,将来如须增加股本,由公司理事会议决,呈请核准后另行募集。云南省政府、四川省政府所认股款可以募集商股;铁道部及云南、四川两省政府所认官股,亦可随时售归商股。[8]
需要注意的是,川滇铁路公司《条例》之所以冠以“特许”二字,主要还是因为其组织与发起的形式,与国民政府于此前的1929年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施行之《公司法》有相冲突之处。《公司法》明文规定,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不少于7人,且公司内部应设董事会、监事会一干组织。[9]223-262而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战时特定时空条件下产生的特种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为交通部及云南、四川省政府三方;它也不设董事会,而是改设理事会;理事会设理事9至11人,其中铁道部指派3人,财政部指派1人,云南、四川省政府各指派2人,嗣后公司增加资本或增加商股时,理事人数可按比例增加。公司设监事3人,由铁道部和云南、四川两省政府各指派1人,将来如果增加商股,监事亦可按比例增加。
可见,川滇铁路公司不仅在经营行业和范围上具有“特许经营”的含义,同时在管理结构上也有着与普通股份有限公司不一样的地方,主要表现为在国有参股企业以“股份有限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创办公司时,其发起人数过少而不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此外,它不设董事会作为日常的决策机构,也不选举董事和董事长,而只是设立一个理事会,并由出资三方各指派若干理事组成。基于这些因素,严格上它并不能算是一种“合法”的企业组织形式。但考虑到抗战时期及特种行业的特殊性,因而只能以“特许”的方式,由国民政府出面,促成其事。[10]344-346川滇铁路公司的“特许”《条例》,实际上基本仿照湘桂铁路公司的章程。“湘桂铁路因有理事会之设置,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深切合作,进行之速,实开吾国铁路历史之先例。故川滇铁路公司理事会之组织,完全取法于湘桂铁路。”[11]279此后,国民政府考虑到因抗战需要而必须经“特许”才能组织成立的公司越来越多,于是便另颁《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12]250-252,算是真正解决了公司设置的法理矛盾。
《特许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经行政院通过后,即于1938年9月正式成立川滇铁路公司理事会,由铁道部长张嘉璈兼任理事长,沈昌任当然理事兼总经理;常务理事为陆崇仁(云南省财政厅)和甘绩镛(四川省财政厅长);理事除张嘉璈之外,还包括徐济(重庆交通部)、萨福均(昆明叙昆铁路工程局)、曾养甫(昆明滇缅铁路督办公署)、徐堪(重庆财政部)、缪嘉铭(昆明富滇新银行)、龚自知(昆明云南省教育厅)、何北衡(成都四川省政府)等七人。监事由韦以黻(重庆交通部技监室)、张邦翰(昆明云南省建设厅)、潘昌猷(成都四川省政府公司)三人组成。[13]278-279理事会随即设立叙昆铁路工程局,以沈昌为局长,着手一切筹备事宜。1942年9月8日,沈昌脑溢血病故,[14]由萨福均继任局长。公司总部及工程局最早设立于昆明小东门外灵光街薛家巷清门寺(现桃源小学),因地处偏僻小巷,对外联系不便,便迁移至金碧路三益里(现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斜对面);不久,又搬至东郊外11公里的小石坝办公。[15]402
由于川滇铁路公司理、监事散居数省,因而延至1938年10月2日,才齐集昆明,召开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标志公司的正式成立。1940年6月22日,公司又遵照《特许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备具文件,呈请国民政府经济部登记注册,在法律程序上为成立画上了句号。[16]278-279
三、川滇铁路的路线勘测
川滇铁路因跨越川滇黔三省,所经多为山岳地带,工程相当困难,此前历经多次勘测,所选路线各有不同。《中国测绘史》中记载: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十六年(1900)和宣统二年(1910),先后经英、法和美国测量人员勘测,选出三条线路。[17]597虽然在不同文献中,对这三条线路具体走向有不同的说法,但比较来看,凌鸿勋氏《中国铁道志》中所说较为准确可信,即:1896年英人测勘,系取昆明经嵩明、曲靖、宣威、威宁、毕节、叙永、纳溪,而至泸县,共长约930公里,后称东线;1900年法国军官测勘者,系由昆明沿牛栏江经昭通横江,而达叙府,长约660余公里,后称中线;1938年筹建川滇铁路公司,计划先修筑叙府(今宜宾)至昆明之间路段,四川省政府会同交通部复测,初定由昆明经嵩明、寻甸、功山、巧家、雷波、屏山、沿金沙江而至叙府,全程约为863公里,是为西线。交通部注重于抗战期间如何联络川黔滇三省铁路并能最快联络贯通,因而还复勘此前所曾放弃英人勘测之线,一度决定由昆明至威宁采取东线,由威宁至叙府则拟采取西线,兼顾中央计划以及地方要求。但由于川滇两省府各有其主张,所以对从威宁至叙府一段路线如何走向,尚未能作最后决定。[7]333-334
需要补充的是,1910年美国工程师勘测的线路,与前载三条线路的中线大致相同,均以滇东北重镇昭通为必经点,这在清末报刊中可以得到验证,例如当年的《民立报》就曾报导:云南滇蜀铁路筹办数年,只因款无着落,未有进展;后经正式聘请美国工程师哈莱、多克士二人勘测路线,“现已勘到昭通府属”,预计次年勘测工作可望完成,“似此滇蜀铁道稍有谋修之基础”[18]。《申报》亦载:“滇蜀铁路一线关系重大,该省官绅已设立滇蜀铁路公司办理一切”,并已聘用美国工程师二名勘测路线,以至于昭通府。此次滇蜀路有东西两线:东线从省城出发经宣威入贵州省威宁,折经滇省昭通府之鲁甸,再北向过大关老鸦滩,以达川省叙府;西线则经东川府至江底,沿牛栏江支流入鲁甸,直抵昭通府,与东线会合。前者地势平缓,工程稍易;后者江水磅礴,山势峻耸,施工困难,但沿路物产富饶,“东川之铅铜,沿线之煤,较之东线不可同日而语”。因为两线各有利弊,故一时颇难取舍。[19]
时隔近三十年,当年的“滇蜀铁路”也更名为“川滇铁路”,事涉三省,且必须应对抗战急需,因而对于路线问题便须重新勘定。四川云南又均为多山省份,山高谷深,道路险阻,路线勘测的目的,正是为了寻求适当的地形,实现铁路建筑的经济快捷以及沿线地区社会效益的拉动。为此,四川与云南两省在确定具体路线时便有不同的想法。本次路线勘测,主要由四川省建设厅负责筹备组建勘测队,成员由西部科学院常隆庆及四川省政府顾问刘宗陶率领,勘测费定为一万五千元。按照四川前省主席刘湘等人的意思,叙昆铁路分为干、支线,其中干线又可分为三大段:宜宾至雷波为第一大段,雷波至巧家为第二大段,巧家至昆明为第三大段。1938年1月19日,川滇铁路测勘总队开始工作,全队员工伕役六十余人自宜宾出发勘测,利用金沙江两岸地形,以江床为坡度标准,并考虑历史最高水位以免水患。[20]测勘前后历时四个月,由宜宾,向屏山、雷波、永善县属之黄华镇,溯金沙江上行,至云南巧家,迳达昆明。3月后,勘测队离开昆明回程,经昭通,沿横江河而下,取道安边镇返宜宾,中途拟由巧家渡金沙江至会理、西昌测勘一条支线。[21]勘测结果上报后,经行营综合考虑,决定川滇铁路全段同时兴工修筑。[22]叙昆铁路工程局局长沈昌在第一次川滇铁路理事会上也报告说:“本路共有三线:(一)中线经昭通;(二)西线沿金沙江而行;(三)东线接近黔省。几经踏勘,以如能接近西康,确有经济价值,但太偏西,不能兼顾贵阳。中线最短,但昭通高原经过不易,且工程较为困难,现决定采用由昆明经曲靖、宣威以达贵州之威宁,转而向西至大湾子,以入西线之一部分而至叙府,共计总长不满八百公里。”[23]282
从以上材料可知,此次由四川省政府主导的勘测,有意拉长川南屏山、雷波一线,但却避开了川滇交通咽喉的昭通,这固然减少了施工的难度,但其经济战略价值却逊色不少,也为云南省政府难以接受。晚清时期曾被派赴比利时留学工程的陈一得先生就认为,叙昆铁路线的“中心昭通为滇东重镇,物产丰富,商务繁盛。东接筑泸公路,西连金江凉山,开发荒区,固结民族,利益甚大。惟由昭通高原下降至宜宾江岸,地势倾斜颇急,赖可就洒鱼、大关、盐津唯一河谷顺流自南向北,绝无横阻山系,可免开凿山洞之劳。工程虽属艰巨,较诸他线易于兴工”[3]。经云南省政府及主席龙云的力争,国民政府交通部还是决定依照晚清以来多次踏勘结果,以经过昭通的路线为准,于是派员会同叙昆铁路局负责人员重新进行勘查。
当时被指派参与其事的浦汉英就此回忆说:“叙昆铁路改经昭通一案,前经地方民众联名请愿,蒙中央俯予采纳,由局派专门人员,分勘威昭及昭大二段。”由于昭通海拔高出四面地区四、五百公尺,两岸山势复杂险峭,因此铁路线经过昭通确有技术上的困难,工程也相应艰巨,号称叙昆铁路“全线症结所在”。此前美国工程师多莱代勘路线,在大关高桥一带费时三十余日进行勘测,在由昭通坝子向大关方面下降时用了许多之字拐(即倒行线),将路线延长十八公里降至河滨,经过山洞甚多,工程复杂,且“倒行线对于行车殊多不便,早经交通部明令禁用”。本次叙昆铁路工程局由一位副局长主持,于4月26日至5月5日间,在“请愿团代表李伯文、蒋敬之、李仲纪、浦汉英诸先生”陪同下自昭通起程赴实地踏勘,重新选线,“中央及地方民众所期望之昭大段”最终“选定由高桥经中营、大沙地、而至安家田坝一线”。曲折迂回之处,则用螺旋线形式,从高桥至青龙洞一带路线由东岸顺山盘旋而下,与多莱旧线隔河相对,“既不袭外人故辙,而路线复较优越”,“不特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增加相当之重要性,即建筑经费以及完工时期亦将大为缩减”,“转瞬测量完竣,开工赶筑,完成通车,可计日而待也。”[24]99-101继沈昌而任工程局局长的萨福均也通报说:“本路威宁以北路线,原定沿戈魁河经彝良而达大湾子,计一百七十七公里,以交通不便人烟稀少,而工程又极艰巨,施工亦有困难,并以昭通等县绅耆请求改经昭通,经派员勘测威宁、昭通、大湾子比较线,是项勘测工作于二十九年六月间开始,三十年四月间完成,较原线约长八十三公里,施工较易,隧道工程虽巨,然御土墙、桥涵及石方工程均可减轻,经呈奉部令,准予采用新比较线。”[25]
大略言之,叙昆铁路跨越云、贵、川三省,除昆明附近一段依照此前国民政府铁道部贵昆测量队勘测路线施行定测外,其余路线分别由7个测量队自1938年1月开始进行初测、定测工作。经过比选,最终推荐宜宾溯横江,经盐津、大湾子、彝良、昭通至威宁,再由宣威、曲靖至昆明,系为中线与东线结合的方案。这条铁路不仅在战时具有军事价值,也对发展西南三省地方经济有相当大的影响。贵州方面就表示,这一铁路的修通,使“威宁之铜,水城之煤、铁与牧畜事业,毕节、大定、黔西之优良煤田,可大量开发,且为本省由南至西北沟通路线,不仅对于国防上有其重要性,其在经济上之价值,实拥有无尽藏之资源。”[26]147
四、川滇铁路开工修筑及借款问题
1938年10月,川滇铁路开始施工招标,工程划分为小段发包给工程商。由于川滇铁路路线争执主要在北段,南段部分并无分歧,因而自南段决定路线后,便于1938年12月25日,正式举行了叙昆、滇缅铁路的开工仪式。[27]叙昆铁路由云、贵、川三省先后开工修筑,设十五个总段担负施工任务,交包商及民工承办(桥涵及隧道工程采取发包)。工程局人才济济,多为富有铁路建设实践经验的技术人员。最初计划建筑标准如下:1.钢轨轨距:定为1米。2.路基宽度:定为4.4米,路堤高度超过6米,用4.8米。填土边坡用1∶1.5。挖土用1∶1或1∶1,5,挖软石用1∶3/4或1∶1/2,挖硬石用1∶1/4或1∶1/8。3.永久式桥涵,如钢筋混凝土及砖石建筑物等,概照中华十六级载重设计。上部之工字梁、钢钣梁、钢桁梁及钢架墩等钢料部分,除特殊情况外,亦照中华十六级载重设计。4.路线最陡坡度:一般地段20编,山岭区25编。5.路线最小半径:一般地区为164米,山岭区115米。[15]
之所以依然沿用米轨而非标准轨距,主要是为了方便与同样一公尺轨距的滇越路连接,同时也考虑到本路工程困难,而战时款料两绌,不得不在工程上降低标准,采用狭轨。但即使如此,仍然难以满足工程所需,叙昆铁路建设很快就不得不采用拆东补西的方法勉力维持。尚在1937年筹备阶段,国民政府中央即已令四川省政府将修建成渝铁路的材料,移作兴建叙昆铁路之用。[28]1939年2月,川滇铁路公司呈请云南省政府实行征工,但沿线征工不力,加之米价上涨,筑路人数甚少。当年10月,云南省府责成公路总局在1939年底前要完成各项工程的16%,1940年累计完成32%。1940年9月,因法属越南允许日军假道,我国即将滇越铁路滇段河口大桥破坏。自后滇越交通阻塞,我方乃将滇越路河口至碧色寨路轨移铺叙昆铁路昆明至曲靖段。10月10日铺轨到大板桥,11月9日铺轨到杨林,于1941年3月20日(另一说为4月1日)铺轨到曲靖,全长162公里,并使用原滇越铁路机车车辆,立即开办营业。[7]335
由于上述“战时款料两绌”这一根本障碍,叙昆铁路单靠本国财力、物力,已经明显难以为继,争取外国借款并以之进口必要的铁路器材,成为推进铁路建设的主要途径。为解决筑路资金缺口,早在1938年初,交通部即开始为此路寻求外国贷款。交通部曾由中国建设银公司出面,分别与英、法两方洽商合作,英法两国银行团也都向国民政府表示有贷款的意愿。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宋子安对此合作抱有极大的信心,称“在本公司的斡旋下,使英、法获得平等而密切的合作关系,这在中国的国际铁路投资史上还是第一次”[29]824。嗣后,因法银团在抗战前即与中国建设银公司有投资成渝铁路和贵昆铁路的合作,双方此前早已接洽借款,英国便放弃对叙昆铁路的贷款权。1939年8月,法银团会同中国建设银公司提出借款大纲及合同草案;1939年12月1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财政部部长及交通部部长为代表,与巴黎和兰银行、雷槎兄弟公司、东方汇理银行及中法工商银行联合组成的法国银行团,正式签订了《叙昆铁路借款合同》,中国建设银公司参与其事。
《叙昆铁路借款合同》一共18条,其中第一条规定,除川滇铁路公司和国民政府负责筹措建设费9 000万元国币之外,由法国银行团向国民政府提供4.8亿法郎的借款,以供给建筑叙昆铁路所需之材料及设备,另由中国建设银公司承借国币3 000万元。以上款项分八次发给期票,年息7厘。借款自第四年起偿还,满十五年时还清,以普通盐余及叙昆铁路收入、沿线矿产等为担保,并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监督施行。合同后续条款详细规定了借款期票发行办法、借款担保、偿还日期及铁路修筑的期限等相关问题。法国银行团声明,因欧战已起,支付款项及提供设备难保不受战局影响,但仍将努力保证供给全部材料。我国担心法方不能如期交货,因而在合同中订明:如法方不能按期交货,我方可从其他渠道获取材料以保证施工正常进行,待恢复正常后,再由法方交付同类材抖,其标准由中国定之。[30]
根据《叙昆铁路借款合同》的规定,法国银行团在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同时,为了保障其利益,银行团获得与国民政府经济部合作开发铁路沿线两边各50公里范围矿产的权利,因而于1939年12月13日签订《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规定由我方资源委员会设立沿线探矿工程处,以交通部和经济部各出资二百万元为限,其余所需材料由法方材料借款内供给八百万法郎。如探矿结果认为有开采之价值,再由法银团与银公司依照中国矿业法组织公司开采。[31]这两个合同的签订,一方面可藉铁路以开发西南资源,一方面可藉资源之开发以供给路款,增加路方将来偿付贷款的能力。
上述项两合同签订之后,欧战已趋紧张,法国也积极备战,英国则要求法国接济铜料,因而借款合同虽然成立,但核准手续及事实履行成为严重问题。中经各方努力,合同延至1940年3月1日始由双方批准生效。正当向法方订购材料之际,国际战争局势恶化,筑路材料未及订购,仅于越南购运一批水泥及炸药,计价款、运费共为112.9万余法郎。财政部则按约拨汇香港东方汇理及中法工商银行付息基金暨其他费用共计175.4万法郎。[32]224稍后,日军在海防登陆,假道越南以切断滇越交通。法方也以欧洲战事正紧、自需钢料为由而爽约,合同无法继续履行,自后材料即无法由越南运入昆明,中法双方年余以来的努力付诸流水。[33]321交通部于同年7月1日宣布暂行中止合同。由于从合同生效至中止合同仅有4个月时间,中国动用仅有零星材料价款、运费,合112.9万余法郎,还有预付的筹备费3万镑。[34]219
五、川滇铁路停工及部分路段的营运
在对外借款及材料进口遇阻的同时,叙昆铁路段的修筑面临无法破解的障碍。由于隧道工程与石方工程非常繁重,当地工人招雇不易,征工成绩亦不佳,进行滞缓。其后曲靖以北勉强继续动工。蒋介石曾指令云南省主席龙云继续拆除滇越铁路芷村至西洱段,轨料移铺曲靖至沾益路段,并拆除个碧石铁路路轨移铺滇缅铁路,但均遭滇南绅商强烈反对而未果。因此后材料再无法凑集,宣威以北工程被迫于1940年9月停工。除昆明北至曲靖段160公里已于1941年3月铺轨通车外,曲靖至宣威103公里桥涵路基工程均已竣工,宣威至威宁段168公里土石方与重点桥梁隧道、宜宾附近5公里范围土石方及涵渠半途而废。[35]134-135款项方面,1938年用款约六百万元,1939年约用二千八百五十万元,1940年约用三干一百八十余万元,1941年约用三千四百六十万元,全部工程约已完成百分之三十九。[7]335-336嗣后总计,从1938年12月25日开工到1942年底,叙昆铁路完成路基土石方1185万立方米,桥梁2 162米,涵渠875座,隧道363延米。本路自开工至停工,共用去投资计法币10 795万元。全线于民国31年(1942年)底停工时,完成的工程量如下表:[15]

工程项目单 位全线设计总数量实际完成数量完成百分比%路基土石方万立方3,9501,30433桥 梁米6,9762,09631涵 渠道2,50087535隧 道米/座16,510/120363/32.2
为便于铁路运输与沾益机场空运衔接,1944年6月1日由昆明铺轨至沾益,累计正线铺轨173.4公里,所用铺轨材料,均利用河口至碧色寨段拆下的旧钢轨铺筑。至此,抗战时期叙昆铁路建设便全线停工。
由于川滇铁路昆曲段修筑于抗战军兴以后,铺轨之时又值滇越路线中断,所有重要机件如水柜、地磅、转车盘等均无法输入,加之战时经费拮据,不得不因陋就简采用临时设备,[36]因而面临着两大困难:一则设备短缺,机车车辆为数甚少,且大多陈旧,无法增补,运量自然受限;另则自国际陆路交通断绝以后,器材配件无法内运,国内仅有的存储已罗掘殆尽,维修困难程度十倍于以往,使运输的困难雪上加霜。尽管如此,自1941年4月曲靖通车后,客货营业仍然日渐发达;加之时值非常,军运与国家物资运输接踵而至,“其数量之激增,实远较战前一般铁路为甚”。该路对于抗战后期盟军军用品、军队及旅客运输起到不小的作用。1943年度内,共计运输部队161列,9万余人,军用品4万余吨,旅客105万余人,货物21万余吨。“对于旅客及普通货物之运输,虽尚无力满足各方之需要,然对于军运,迄未延误,各方面较上年均有进展。”[37]另据统计,1943年至1945年昆明曲靖段累计完成旅客周转量2.53亿人·公里,货物周转量6 560万吨公里,运送士兵46万人次,开行军车807列。[35]134-135
1945年,抗战即将进入反攻阶段,昆曲段运输能力远不能适应军运及商运需要,美国方面屡次提出增加运量,交通部也要求于该年9月底将运量增至每月八千吨,12月底时续增至一万二千吨。但由于机车及铁路设备陈旧,这一愿望并未实现。[38]同时,由于抗战时期通货膨胀,法币贬值过快,川滇铁路客货运费虽经多次提价,[25]但仍处于亏损经营状态。[36]不过从另一方面也显示出昆曲段营运的繁忙,这样的景象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方才结束。
六、余论
川滇铁路叙昆段于1938年12月底由云、贵、川三省先后开工修筑,下设十五个总段担负施工任务,交包商及民工承办,桥涵及隧道工程则采取发包形式进行,最终于1942年后陆续停工。其中以云南省完成的工程量为最多,昆明至沾益一段全部工程均已完成,沾益至宣威一段,桥涵及路基土石方均已完成,仅差铺轨,宣威至贵州威宁一段,完成三座隧道及部分土石方和桥涵。四川境内则仅叙府至安边一段略有开工,完成不多的工程量后便停工了。
之所以落得如此结局,盖因种种不可克服的战时困难所造成。至于抗战军兴时的南京中央及地方川滇黔三省政府而言,却对修筑川滇铁路的前景抱有热切的期望。国民政府不惜在财政极其拮据的情况下想尽办法,通过国库拨款、公债发行、向外国借款等多种方式,为铁路建设筹集资金。据学者的统计,从1937年7月至1938年底,国民政府拨出建设专款4 100万元,其中四分之三即用于修建或筹建包括叙昆和滇缅在内的多条后方铁路。从1939年开始,交通部又增加交通建设专款,从1939到1945年交通建设专款分别为11 800万元、14 700万元、33 600万元、127 400万元、86 700万元、668 300万元、524 700万元。[39]112-113即使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对交通建设的投资在各项建设投资中也占了非常高的比例:1937~1938年为34%,1939~1945年度分别为65%、80%、72%、73%、65%、73%。[40]83综合来看,1939年后历年对交通建设的投资均占到总投资的65%以上,可见国民政府对西部交通设施建设的重视。
此外,由于川滇铁路涉及对外借款,中法双方并因此签订借款合同和采矿合同,规定了共同开发沿线矿产的具体事项,因而从一开始便引发人们对主权问题的敏感和担忧。作为两份合同签字当事人之一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刘景山,在晚年受访时就坦承,有些人看了这两个合同,不明底细,说:“不得了,法国人侵略到云南的路矿了。”他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指明“路矿两方的主权均属我国,一切是企业合作,不至像从前借款筑路大权旁落于外人之手”。[41]119揆诸合同文本,刘氏之说并非为虚。以《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为例,其第二条第一款就载明:“本合同所称之矿权,不论属何种类,均应给予中国公司,亦只能为中国公司所得。”在遵守中国各种法规的前提下,中国中央政府、省政府及中国私人均可投资建立此类开发性公司,以“协助政府开发叙昆铁路经行地带之矿业,以发展此区域之经济”。[42]可见虽然身处财政极端困难的抗战时期,主权意识还是非常明确,并无损国家利益。川滇铁路最终壮志未酬,实际折射了中国抗战的艰难背影。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建国方略[G]//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李春龙,江燕点校.新纂云南通志第4册[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
[3] 陈一得.叙昆铁道路线之一瞥[G]//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续云南通志长编(中册).云南省地方志编篡委员会,1986.
[4] 陶正耀.从汉口危急谈到正在建筑中之滇蜀铁路[J].游击,1938,(6).
[5] 川滇铁路行将修筑[J].统一评论,1938年第5卷第4期.
[6] 凌代表均吾等廿四人提 为叙昆铁路停工已久拟请政府依照原定计划从速继续建筑早竟全功由(提案第六五六号)[H].国民大会秘书处编.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提案原文.国民大会秘书处1947年印.
[7] 凌鸿勋.中国铁路志[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
[8] 川滇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条例[J].四川经济月刊,1938年第9卷第4期.
[9] 吴经熊校勘.袖珍六法全书[M].社会法学编译出版社,1935.
[10] 张忠民,朱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
[11] 川滇铁路公司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纪录[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12] 特种股份有限公司条例[G]//中华民国法规辑要(第2册).中央训练团1941年编印.
[13] 川滇铁路公司理监事名单[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14] 川滇铁路公司总经理沈昌逝世[J].抗战与交通,1942,(91).
[15] 姜一鹍.叙昆铁路修筑情况[C]//杨实.抗战时期西南的交通.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
[16] 川滇铁路公司为请注册并恳转咨经济部登记呈[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17] 《中国测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测绘史第1卷(先秦-元代)、第2卷(明代-民国)[M]. 北京:测绘出版社,2002.
[18] 云南通信[N].民立报,1910-11-12.
[19] 滇蜀铁路开始着手[N].申报,1911-02-11.
[20] 川滇铁路叙昆线测勘经过[J].四川月报,1938年第12卷第3,4期.
[21] 川滇铁路定期开筑[J].西南导报,1938年第1卷 第1期.
[22] 川滇路勘测工作积极进行[J].四川月报,1938年第12卷第2期.
[23] 川滇铁路公司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纪录[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24] 浦汉英.昭通地区的交通历史概况[G]//昭通市政协委员会文史资料编辑室编.昭通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1986年内部印刷.
[25] 萨福均.最近三年来之川滇铁路概况[J].交通建设,1943年第1卷第3期.
[26] 叙昆铁路筑威段对本省经济建设之重要性[G]//贵阳市志办《金筑丛书》编辑室编.民国贵阳经济. 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
[27] 建造滇省两大铁路:龙云主席领导高级省府人员行破土礼[J].展望,1939,(2).
[28] 省府筹建川滇铁路[J].四川月报,1937年第11卷 第5期.
[29] 宓汝成.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0] 叙昆铁路借款合同[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31] 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32] 财政科学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册[M].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
[33] 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34] 马陵合.外债与民国时期经济变迁[M].合肥: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35] 云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云南省志卷34《铁道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
[36] 萨福均.川滇滇越两铁路状况[J].交通建设,1944年第2卷第1期.
[37] 川滇铁路卅二年度业务行政报告书[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第10册. 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38] 萨福均.川滇铁路及滇越铁路近况(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本部国父纪念周报告[J].交通建设,1945年第3卷第2期.
[39] 金士宣.铁路与抗战及建设[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40] 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M]. 北京:文史出版社,1986.
[41] 沈云龙.刘景山先生访问纪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
[42] 叙昆铁路矿业合作合同[G]//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外交》.北京:档案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朱丕智]
The Meaning and Difficult Process of Sichuan-Yunnan Railway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ang Jing, Wang Yiqiu
(School of Management,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657000, China)
Abstract:When the Anti-Japanese War began, coastal transportation routes fall in the hands of the Japanese army in succession. Then the Nanking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provincial government of Sichuan-Yunnan-Guizhou have fervent expectation on the prospec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chuan-Yunnan railway, which was regarded as the artery that connected the heart and prosperous the local econom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lthough under extremely financial constraints,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struggled to find ways such as the state treasury, bonds issued, foreign borrowing and other means to raise funds for the railway construction. The Suifu-kunming railway entered the actual survey, construction phase in 1938, but because of the situation worsened and forced to shut down eventually when completed the section from Kunming to Zhanyi County. The difficult process was miniature of China’s suffering in eight-year war.
Keywords:Anti-Japanese War;Sichuan-Yunnan railway;Sui Fu-kunming railway
收稿日期:2016-02-03
作者简介:唐靖(1972—),男,昭通学院管理学院,历史学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2—0034—09
王亦秋(1978—),女,昭通学院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史、云南地方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