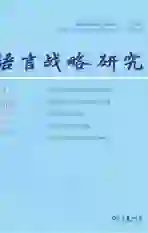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维度
2016-05-30卢德平
提 要 理想或成功的汉语国际传播,实质是具有厚度的传播过程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每一次生产和再生产,都需要以这种文本的内在连贯性、一致性、统一性为重要条件。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解体力量都程度不同地威胁到一种连贯、一致、统一的传播过程文本的形成,从而造成传播不成功的结果。但是,这种传播文本的非连贯性和不一致性并非毫无意义,也不只是存在消极作用。这些文本解体力量对于对话者达成理解和共识所需要的文本连贯性和一致性构成了障碍,而这种障碍本身蕴含着克服障碍的意义,激发起追求互动新奇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者的对话兴趣,使得汉语国际传播本身拥有母语共同体成员之间日常互动实践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汉语母语携带者与对象国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各类交际实践中障碍最多,共识最难达成,但也是一种具有张力和新奇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也最容易转变为意义丰富、魅力无穷的交流。
关键词 汉语国际传播;社会互动;传播方式;线性语言;厚度文本
Abstract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address the issues concerning Chinese language overseas spread from a theoretic perspective. An idealized or successful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ught to be taken as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 communicative process text, which has a complex set of meaningful layers rather than a linear mode of speech. Each textual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is regulated or even controlled largely by its immanent consistency, coherency and unity. However, a variety of deconstructive factors can pose a threat to the formation of this consistent, coherent and unitary text of communicative process, to the extent that it may lead to an unsuccessful communication. Nonetheless, such inconsistency and incoherency of communicative text are by no means meaningless or negative. Although these deconstructive forces are barriers to a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or consensus to be reached between participants of a dialogue, they are bound to be necessary for overcoming the barriers, and to stimulate an urge to converse across cultures and communities. This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ve situation therefore has a special significance different from what one may appreciate in a mother tongue setting. Carriers of Chinese as a mother tongue may face toughest barriers and lowest agreement in communicating with an alien partner, but also a tensest and most astonishing communication, which is likely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meaningful and attractive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Chines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social interaction; communicative mode; linear language; thick text
一、真相与本质
目前汉语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具有多声部特点,不同的行动主体都在参与其内涵的建构,表达着自身的立场,而各种声音和立场产生的回声,使得汉语国际传播这一概念被多重映射之后不仅产生了内涵的歧义、界定的困难,最关键的是,许多以汉语国际传播名义阐释的现象已经远远超出了汉语国际传播的范畴,甚至超出一般传播的范畴。在此情况下,汉语国际传播无论是概念还是行动,均存在真相和假象叠加的问题。接近或逼近汉语国际传播的真相,不是要在这个问题上确立什么唯我独尊的话语权,对各种视角或观点进行筛选,并做出对我有利的选择,而是要还原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动、传播过程所具有的内在规律。当然,一种尊重传播规律的汉语国际传播行动所产生的传播效果,要远远大于偏离或无视传播规律的传播行动。
1.当前汉语国际传播运动
中国目前所推行的汉语国际传播实质上是一种政府和民间合作实施的传播运动,其出发点是推介中国的传统和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凸显了传播主体的意志。其基本传播出发点不是传播对象需要听什么,而是传播主体想讲什么,或者说,是传播主体通过传播手段和传播过程去吸引传播对象来听我讲。也就是说,在目前的汉语国际传播中推力因素远远大于拉力因素(卢德平 2016)。这样一种以传播主体为主导的议程设置方式,不能说不是一种有效的传播,但确实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对话性互动过程有着很大的区别。一种宏观的传播运动,如果不能转化为微观的人际互动实践,或者通过这样的微观互动实践去具象化传播主体的意志,那么所谓的汉语国际传播就始终处于一种悬置状态,所传播出去的仅仅是需要传播的信息,而没有实现传播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形式所具有的丰富意义,也无法保证这些传播出去的信息被传播对象所接纳。目前的一些汉语国际传播活动表明,国内通行的政治沟通和社会沟通的单向、单通道模式(俞可平 1988),很大程度上被复制到汉语国际传播运动中,而国情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治理方式的区别,都对简单复制这种传播方式的有效性构成挑战。
在以传播主体的意志为主导的汉语国际传播格局下,围绕着汉语国际传播中汉语言符号的传播存在着一些假象,同时,把汉语言符号的输出或传播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又派生出关于汉语传播本质的假象。仅就汉语言符号本身而言,这些假象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认为汉语国际传播就是把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汉语想法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由此实现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现实的对外传播。第二,认为通过在海外广设汉语教学点就可以实现汉语在对象国的广泛使用和传播。
2.传播的悬置性与日常社会生活
不可否认,从语言的符号特质判断,把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输出去,可经由汉语符号去指涉汉语之外的非语言因素,即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现实。但这种汉语传播观实质是把汉语扩散和汉语交际两种传播方式混为一谈,认为汉语具有符号系统的自足性,自身足以表达和传递中国人作为主体的所有意向性和中国社会的所有外部客观现实,而不必考虑日常生活中的汉语交际者生动的个体特性,从而悬置了汉语传播对对象国日常生活的介入。从理论上讲,汉语的符号性只能说明作为符号系统的汉语音义兼备,形式和内容耦合,并且指涉汉语之外由社会、文化、历史、现实构成的语言之外的“他者”。换言之,关于“他者”的观念业已成为汉语的语义成分,浓缩并沉淀于汉语之中,构成了汉语的表达潜能。但汉语的符号性只是汉语进入日常生活交流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进入交流或交际,语言的言说主体必须出现于交际场景,而这个言说主体是生动和具体的个体,而非集团表现意义上的抽象言说主体;即使言说主体拥有交流的意向性,如果交际对象对言说主体的意向性不感兴趣,没有和言说主体分享意向性、共建意义世界的驱动,那么交流或交际仍然无法实现。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语言符号传播出去,甚至为交际双方所理解,也不能构成面对面的语言互动,不能成为日常生活的社会实践形态。即使在同为母语的环境中,这种语言互动和交际不成立的例子也随处可见。可见语言进入日常交流或交际,尚需生动具体的交际者具有共享交际意向,共建意义世界的社会心理驱动这一重要条件。上述社会心理驱动条件在理论上要求前置于汉语传播过程,而在实际的汉语国际传播行动和政策中,这个在目前实践上未能形成的前置条件反而被设定为汉语国际传播的目标,从而构成理论上的错位,决定了目前汉语国际传播游离开对象国日常社会交际的悬置性特点。
显然,汉语传播如果不能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具体生动的言说主体必然缺位,在此条件下,这样的汉语传播实质等同于汉语书面语的传播,而不是作为社会实践形态意义上汉语的传播。即使通过孔子学院等途径面向外国人开设汉语课程,所传播的汉语仍然停留于符号体系的转介,而不能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这是目前大部分汉语国际传播实践的真相。这个真相如同英语、法语、德语、日语等传播到中国,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并没有进入传播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其实质不过是书面语的传播或课堂的封闭性语言练习。如果从语言传播是一种社会实践,是人际面对面的社会互动,并由此构建和营造一种共享的意义世界这一角度理解,上述汉语传播还不是真正的语言传播,而不过是汉语符号体系的转介。
当然,能进入日常社会生活,成为人际面对面互动的社会实践的语言只有母语或替代性母语。替代性母语的形成只有通过权力强制或殖民剥夺两条途径才能实现。符号体系转介意义上的汉语传播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只是在于:汉语国际传播可能难以避免世界上一些主要语言的国际传播结局,即永远排除在对象国日常生活场域之外。这其实触及汉语国际传播的限度问题。汉语国际传播的限度决定了作为外语的汉语与作为母语的汉语呈现出不同的功能路径。作为母语的汉语,其口语和书面语扮演着平行和同等重要的角色,口语的价值在于日常社会生活实践,而书面语的价值则主要行使集体文化记忆的职能(李宇明 2016)。在汉语母语中,书面语并非口语的单纯转译。汉语作为外语向非汉语母语地区或国家传播,由于无法像母语一样进入日常社会交际实践,因此难以形成对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贡献,其口语功能主要表现为学习汉语书面文献的阶梯。这一定律的例外是:当中国人个体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且背景存在促成汉语作为交际语码首选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强势因素,则汉语获得进入对象国部分日常生活语境的条件。但这种状况又以大量中国人出现于对象国多种日常社会生活为前提。如果这样的话,汉语国际传播则会蒙上“霸权”的阴影。
3.符号体系与互动实践的理论整合
从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的思考到语言是一种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实践的认识,反映了关于语言本质特性的两个认识阶段。索绪尔语言符号学说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代表了前一种认识的高峰;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Wittgenstein 1958)、奥斯汀(Austin 1962)、塞尔(Searle 1969)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米德(Mead 1972)之后所形成的哲学社会学的符号互动论,则代表了后一种认识的高峰。
但是,以上述任何一种认识为唯一理论出发点来界定汉语传播概念,制定汉语国际传播的政策,实施汉语国际传播的行动,都不可避免带来认识和实践的双重偏差。以前一种结构主义的语言观为汉语国际传播的理论基础,则必然认为汉语本身形义兼备,是自足的系统,由此认为汉语国际传播等同于将汉语这套符号系统输出到不通行汉语的地区或国家,汉语所承载的中国人的集体意识、文化记忆、社会制度、传统习俗就能同步输出,进而认为汉语国际传播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不可否认,这样的认识和实践存在着一定的理论合理性,即立足于汉语作为一种符号系统的理论思路,解决了汉语传播的语言符号地位问题,但无法确立汉语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理论依据,也无法回答汉语国际传播限度的问题,以及在汉语传播实践上的悬置性问题。以后一种理论线索为汉语传播的唯一理论依据,也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日常社会生活对于交际者置身于具体的语言互动语境的现实性要求,在作为母语使用者的中国人不能大规模进入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对于跨越国境且以外语状态出现的汉语国际传播,构成几乎难以逾越的实践障碍,并在理论上存在过于倚重语境变异、缺乏对宏观背景规则有效指涉的问题。但后一种理论思路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重要启示:汉语国际传播应从传播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包括具体生动的语言交流者的当下现实开始,由此出发才谈得上关于传统、历史、文化等宏观背景的历时维度的传播。
语言拥有“分离”(detachment)和“整合”(integration)的辩证能力(Berger & Luckmann 1966),
即反映社会生活经验,但又超越于情景化的经验偶然性,从偶发的经验片段中分离出来,而形成对各种相关经验的概括、抽象、范畴化的“分离”能力,以及将时空遥远的不在场经验眼前化的“整合”能力。语言的两种能力的辩证结合,为上述两种理论思路的整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正是由于包括汉语言在内的任何一种语言符号系统能够将语言共同体的各种情境化的实践经验类型化、范畴化,并形成语言的语义场系统,从而可以在传播语言符号体系的同时,同步传播出相关的语义场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掌握一门语言就相当于掌握了一种文化,掌握了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经验系统,而语言扩散所谋求的通过语言符号体系的传播实现文化系统的传播,在语言的“分离”能力中寻找到理论合理化的来源。但语言的“分离”功能仅仅提供了理论可能,不等于实践的成功。语言的“整合”作用诉求的恰恰是以“分离”能力为前提的语言交际实践的成功途径。语言这种“整合”能力根本上体现为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互动实践,将遥远、不在场以及通过“分离”能力获得的概括化、范畴化经验,变成在场、具体、情境化,而这一实现反映了语言符号从全民语言意义上的范畴化系统转变为面对面人际互动过程中的情境结合,转变为个性色彩附加的语言实践。进入人际互动的语言传播实践,语言的一切抽象、概括的经验范畴都开始获得确切的指涉、主体的界定,以及与特定话题的结合。从理论到实践的这个转变实质上体现了语言传播的两种理论思路的结合。上述两种关于语言和语言传播本质特性的重要理论思路的结合,意味着规则和过程、背景和现实、个体和社会的有机整合,这可能才是确立汉语国际传播理论基础的正确方法。
二、方式和路径
1.两种传播方式:从扩散到交际
与上述两种理论思路相对应,国际上关于语言传播的研究基本上围绕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在“语言扩散”(language spread)的意义上探讨所谓语言传播的过程、规律及结果(Gumperz 1962;Fishman 1991;Ferguson 1993;Nichols 1997,2008);另一条是在“语言交际”(linguistic communication)的意义上将语言传播置于人际面对面互动的框架下考察语言在社会互动中的功能和作用(Mead 1972;Goffman 1974;Blumer 1986)。
前一条线索旨在探讨语言在地理上的扩散结果,即一定的语言从甲地扩散到乙地,是否完全替代了乙地原先通行的语言,或两种语言仅仅并存于一定的社会场域,或两种语言以社会语体的有序分布,流行于不同的社会群体,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社会活动。后一条线索旨在考察社会成员如何在日常生活的互动过程中以语言建构出对话的意义世界,并通过对话者内在经验的语言外化过程而实现对话者相互间经验和意义的共享(Schutz 1962),由此透视社会结构、社会过程的成立条件(Goffman 1974)。这两条线索并非完全平行,而是相互影响,使得语言传播呈现出非常复杂的状态。“语言扩散”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为最高目标,使之构成语言传播的最终形态,但在母语之外,一种外部植入的语言变体如要实现这一传播目标,在传播策略上则不可回避其“殖民”或“霸权”模式,从而在语言传播过程中卷入语言外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即使就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交际而言,语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构成进入对话和交际的社会成员展示其主体人格、分享彼此经验和情感的社会行动过程本身,而不是服务于其他目的的工具。
维特根斯坦说:“想象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Wittgenstein 1958:§19:8)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和交际实质上是一回事,语言与人的社会性和社会交往过程几乎等同。目前语言研究领域所提出的语言交际的两种基本模式——“信息模式”(The Message Model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和“推断模式”(The Inferential Model of Linguistic Communication)(Akmajian et al. 2001),已经成为语言传播研究领域的经典范式,深刻影响着人们对于语言传播基本规律的认识。在这两种基本模式的框架下,对于语言传播、语言交际的理论阐述带有明显的语言学偏向,从而遮蔽了这一外化的语言现象所包含的非语言因素及其社会性本质。
汉语国际传播同样体现出语言传播的一般规律。但目前无论学术界,还是相关的政策部门,对于语言传播的两种形态或方式,即“语言扩散”和“语言交际”,存在着理论和政策的双重混同,对于二者处于何种关系也未做深入分析,因而无法界定在“语言扩散”意义上的汉语传播,以及在日常生活场域的“语言交际”之中有可能遭遇到的传播制约。当然,汉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作为外部植入的语言,在放弃“殖民”或“霸权”模式的条件下,虽然难以进入对象国的日常社会生活,但从语言传播的理论可能性考察,仍然在政治、文化、经贸、教育等领域存在着很大的传播空间。这样的汉语传播具有社会群体的限定性,而非全民语言所要求的那种周延所有社会成员的语言传播模式。由此可以看出,汉语国际传播虽然存在着一般语言传播的规律性特征,但又不同于母语共同体内部的语言传播,或标准语在方言区的传播,而更多体现出跨民族、跨国界的跨文化传播的典型特征。汉语国际传播从理论走向实践,也意味着从理论模式向政策路径的转换,而这样的转换需要一种适用于跨文化语言传播实践的理论解释。
2.推拉因素及其延展半径
我们认为,需要把汉语传播作为一种系统和过程,以“语言扩散”和“语言交际”作为汉语传播的两种形态或方式,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解释汉语传播的内在规律,并围绕汉语传播过程中的推拉因素,来勾画一个相对符合语言传播规律、具有前瞻性价值的政策框架。“语言扩散”意义上的汉语传播主要属于宏观层次的问题,具有超越于日常交际实践的悬置性特点。目前汉语传播政策的推介性举措,包括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宣传,更多体现了悬置状态下推力因素的作用。但汉语传播需要进入对象国的特定社会群体和社会空间,呈现出汉语传播的中观维度。汉语传播的中观层次主要表现为地理空间、社会空间、职场空间三个主要语言场域。汉语传播的微观层次,主要体现为个体语言学习者的日常汉语交际实践。与宏观的悬置性特点不同,中观和微观层次的汉语传播更多体现了“语言交际”意义上的汉语传播规律。
从宏观到中观,并最终实现于微观层次,反映了汉语传播从“语言扩散”到“语言交际”两种形态或方式的转化过程。三个层次在理论和实践上依次表现出源自中方的汉语传播的推力因素逐渐弱化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对象国内生的汉语传播拉力因素逐渐强化的过程。换句话说,在推介中国文化、经济、历史等内容的宏观国家行动层面,汉语传播的推力因素表现得最明显,具有显著的规模效应,但这种宏观的推力因素未必能及时和直接转化为汉语在对象国特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空间的传播,更不能直接预测日常生活场域的个体汉语学习者的汉语交际实践。也就是说,宏观层面的推力因素如果要有效转化为一定的社会群体或社会空间的汉语传播,以及个体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力,需要同时在中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培育对象国汉语交际实践的拉力因素,而仅靠宏观层面的强势推介,单纯增加推力因素,显然无法达成这一结果。当然,对象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宏观维度也可能产生一些拉力因素,但这种宏观拉力因素往往和源自中国的宏观推力因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呼应关系,其中部分宏观拉力因素会转化为中观和微观维度的拉力因素,但未必全部都能转化。相应地,汉语国际传播政策的路径优化实质体现为:第一,如何延长推力因素的传递过程,即最大限度实现从宏观到中观,直至微观的延伸,而推力因素传递过程的延伸,并非仅仅依靠加大推力作用就可以理想地实现。第二,如何使源自中国的推力因素转化为源自对象国的拉力因素,从而实现汉语传播从国家之间的“语言扩散”向对象国日常生活场域的“语言交际”的转化。
三、内在张力及其消解
1.体系冲突与经验兼容
语言交际是社会互动的重要呈现形态,汉语国际传播要获得充分的生活现实性,而不是停留于概念设计或课堂模拟,就必须在具体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展示其交际特性。任何汉语国际传播策略只有放在异域日常交际的场景中才能检验其有效性。任何一种语言共同体内部的日常语言交际均以其母语享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因为母语确立并巩固着社会互动规则,由特定语言共同体内部成员所认可、采纳、遵循。因此,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汉语,走出汉民族语言共同体,试图进入对象国以自身母语所营造的语言共同体,这个语言传播策略本身就存在着极高的风险和挑战。这一策略的内在困难在于:在输出汉语语言的同时,必然会同步输出汉语在汉民族语言共同体内部所确立和巩固的社会文化规则,而这一套规则体系要么与对象国母语世界的规则体系整合为一,要么与之并行存在。前一种结果体现了汉语国际传播充分成功的路径,后一种结果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传播成功。但两种情况均存在着来自对象国母语的抵制,这个抵制不仅在于对象国母语使用者对汉语强势传播威胁到母语日常交际地位的担忧,也来自汉语和对象国母语两种语言之间所存在的无法兼容的体系性张力。
不过,语言的传播往往并非由语言本身所决定,而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语言携带者的移动性,特别是具有强势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语言携带者的移动性(王建勤 2016)。不是语言要跨出语言共同体的边界向外传播,而是语言携带者跨出了语言共同体的边界,以言说者的语言身份而形成了语言对外扩散和传播的实用性动机。语言从来都是满足于母语的地位,满足于在一定的语言共同体内部循环和流动,并以和共同体疆域外的异邦语言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来维护自身的结构稳定性。目前汉语国际传播的现实条件是:越来越多的汉语母语携带者走出了汉语共同体疆域,来到了异域语言共同体;同时,越来越多的异域语言携带者来到了汉语语言共同体内部。但是,这两类语言携带者的流动性只是汉语国际传播成立的必要条件之一,而非全部。
汉语母语携带者虽然来到特定的异域语言共同体,但如果汉语母语携带者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与对象国语言共同体相比不具优势,则可能更多被对象国母语共同体所同化,而无法履行汉语国际传播的功能;如果汉语母语携带者所到达的异域语言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上与汉语母语携带者相比不具优势,则汉语的国际传播存在着很大的空间。另一方面,异域母语携带者来到汉语共同体,如果其母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因素相对于汉语的对应因素具有优势,且汉语共同体内部存在大量外语学习者与其交流,则汉语学习不构成强大压力。如果异域母语携带者需要深度了解汉语共同体所确立和巩固的社会文化规则体系,或自愿契合汉语共同体内部,则存在汉语国际传播的可能(李宇明 2012)。汉语的这两种国际传播存在着本质差异:一种是汉语从母语共同体向异域语言共同体的移位,另一种则是在汉语共同体内部对非共同体成员的传播。前一种传播存在着汉语和异域语言之间的体系性冲突问题,后者则表现为异域语言携带者个体在具体的汉语学习过程中对于两种语码转换和兼容的经验,而不构成体系性冲突。对于汉语国际传播所产生的汉语和异域语言之间的体系性冲突问题的应对具有较高的政策价值,而对于个体汉语学习经验的研究则更多具有对外汉语教学方法和策略上的实践意义。
从跨文化语言传播的政策实践的角度看,汉语的扩散和传播还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第一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的推广政策与汉语扩散和传播有可能形成冲突;第二是英语根深蒂固的国际地位及其广泛影响与汉语扩散和传播可能构成冲突;第三是相关国家和地区民族语言推广实践和英语在教育体系中的普遍性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叠加力量,与汉语扩散和传播可能构成冲突。
2.冲突的化解及其可行路径
正是由于汉语在对象国传播存在着与异域语言的体系性冲突,随着汉语母语携带者向对象国日常社会生活多种场域的移动,这种冲突表现得日趋激烈,因此,减缓这种冲突成为汉语国际传播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者两方面寻找线索:一是汉语词汇在对象国母语的扩散,形成大量的汉语借词,有助于对象国母语使用者提高对中国话题的兴趣,实现异邦想象的意义,从而减缓汉语和对象国母语在体系上的冲突;二是在对象国母语使用者中增加学习汉语者的数量和规模,通过大量的语言使用者个体的语言转换和兼容经验,减缓汉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与对象国母语的体系性冲突。无论采用哪一种方法,都注定这一过程将是非常漫长的。在这一漫长的整合过程中,人们首先看到的是汉语与对象国母语在多个生活场域的非系统性并行状态。在放弃整合策略的前提下,汉语国际传播的效果可能主要由这种非系统性并行状态来衡量和检验。
就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层次而言,汉语通过国际传播实现与对象国母语的整合,最大的突破口在词汇。语音和语法两个平面的系统性和统一性规律决定了对象国母语对于汉语在这两个层次的整合存在着强大的排斥力量,实际上也难有成功的可能。而语言传播史上大量借词的出现,充分证明词汇的输出和整合相对容易,也是语言传播过程的主要结果。汉语国际传播中的词汇传播,根本上是汉语语义场向对象国母语共同体的传播。在这个语义场里面存在着中国的话题、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特征,以及中国人通过汉语母语所表达和形成的对于这些话题的态度和立场。就采用拼音文字系统的一部分对象国母语而言,汉语借词的出现和传播在汉语语音的非系统性移植方面存在着内在的便利,这种便利性经由汉语口语路径最终落实于对象国书面语,从而获得持久的传播。借词的传播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对象国母语并非汉语国际传播的单纯的抵制力量,在一定意义上也承载着汉语国际传播的职能。认识到这一点,可能会产生汉语国际传播的一个新的视角。迄今人们所坚持认为的汉语与对象国母语之间存在体系性冲突的观点,需要转换为汉语与对象国母语的有限兼容和借鉴的视角。这种理论和实践的可能性存在于汉语词汇的对外扩散。换言之,汉语国际传播的现实路径不是始自语音和语法教学,而是始自词汇的对外渗透。这个视角的转换,可能为回避汉语国际传播中的语音和语法层面的系统性冲突开辟出一个新的突破口。
即使是汉语与对象国母语在一定的日常生活场域的并行状态,也始自移动着的汉语母语携带者在对象国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有意义的交际情境,让对象国的社会成员产生加入这一有意义的交际情境的兴趣,并由此形成以汉语为对话平台的社会交际实践。形成这样有意义的汉语交际情境的条件是多方面的。首先,要求汉语母语携带者是一个既能表达又能倾听的对话者。其次,汉语所承载的中国话题在交际过程中足以吸引对象国社会成员的兴趣,使得围绕相关的中国话题构成的汉语交际活动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言语事件。再次,对象国社会成员对于这样的汉语交际情境的意义界定,又和自身的日常社会生活发生着内在的关联。
四、从线性语言到厚度文本
1.语言与文本
巴尔特区分了动态立体的文本(text)与静态平面的作品(work),指出了前者的过程性和行动性特点。这一区分的方法论价值对透视日常交际意义上的汉语国际传播极富启发。巴尔特说:“作品是能够看到的(在书店里,在书目里,在考试大纲里),而文本则是一种论证过程,是依据一定的规则(或反抗一定的规则)而言说的;作品可以握于手中,而文本则依存于语言,仅仅存在于话语的运动之中(或毋宁说,正是由于文本知其为文本而成其为文本)。”(Barthes 1977:157)“文本只能存在于差异之中(并非说个别性),对文本的阅读是瞬时性的(这就使得任何所谓的归纳-演绎型文本科学成为幻象——文本没有‘语法),而是和引用、参照、回声、文化的语言(什么语言不是文化的语言?),无论是以前的,还是同时代的,完全编织在一起,这些东西在一个巨大的立体声中穿越着文本。每一个文本都处于互文状态,其本身就介于另一个文本之间;互文不应和文本的起源混淆:试图寻找一部作品的‘起源‘影响,都会堕入谱系的神话;构成文本的引用是匿名,无踪迹的,但已经被阅读过:它们是不加引号的引用。”(Barthes 1977:160)
异域语境中的汉语交际表现为听得见、可实录的汉语会话流,但从人际互动的意义上考察,实质是一种动态、立体、互文性质的文本呈现。线性的汉语言符号构成了文本呈现的平台,而在这个平台上呈现,并深深嵌入这一语言符号流的恰恰是中外对话者由此建立的人际关系。这种人际关系的确立始自语言,但归结为指涉社会现实时视角和态度的共享、面对面交流时双方主体人格的展示和接纳,以及聚焦特定话题时彼此价值和兴趣指向的兼容。因此,我们说,在人际互动意义上的汉语国际传播已经远远超越了语言符号的线性限制,成为包括交际过程中参与者的对视和接触、交际场合的社会文化参照、交际双方的情感和人格呈现、交流内容的主题设置以及交流节奏的控制等要素在内的一种立体文本。这也是我们所说的汉语国际传播始自汉语言符号,但终于中外人际关系的基本意义。
2.文本的维度及其支撑因素
汉语国际传播的文本性不同于文学理论所说的文学作品的多声部构成和作品内涵的跨时空引用,但这种文本的动态性、过程性、异质性、交互性的基本特征,恰恰说明了以交际者面对面为首要条件,以生动的个体风格为交流魅力,以对中国现实和历史的参照和想象为远程背景,以对匿名或有名的诸种意见和态度的有意识或无意识引用为观点支撑,由此构成的语言传播是一种依赖于语言符号但又超越于语言符号的社会行动,其立体的厚度,正是线性的汉语言符号所不能充分解释的。
汉语国际传播的文本构成依托于汉语言,并以其作为运行的平台,但语言外的其他类型的符号,如对话者的体态、表情,对话者的个人言语风格(停顿、重复、口音、惯用句式、常用词语等),对话场景的类型特征,对话的时空设置,以及对话者的社会属性等,又构成传播文本的支撑因素,为每一个(或每一次)交流文本赋予了色彩和边际,使之不同于其他传播文本,同时又维持着每一次个性化文本的内在统一性。所依托的汉语言符号,通过语言的范畴化体系,反映了中国人日常经验的类型化结果,其抽象的共通性是一种语言系统通行于熟悉和陌生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主要依据。但进入具体的对话过程,这种抽象的符号系统才开始获得具体性和生动性,才从全民语言体系转化为具体的传播过程文本的运行平台,对话者的个性化贡献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伴随着从范畴化、类型化的全民语言向个性化文本平台的转换,汉语言符号体系也被同步编织进文本的内在组织,成为传播文本的内在成分,体现出语言自身的价值,以及转变为文本构成内容的价值(江怡 2016)。因此,在日常汉语国际传播的言语事件中,我们看到文本的语言平台对整个言语事件的周延力量,且据此容易将相关的传播活动判断为语言传播;而语言活动对整个传播文本的渗透,也设定了这种传播文本本质上是属于语言性的,而非其他类型的社会合作行动。
也正是通过面对面人际交流而形成的动态传播文本,伴随着交流者的相遇而在场,又伴随着交流者的退出而隐身,从而使这种传播文本具有典型的情境性、瞬时性,但在交流者面对面相遇的同时,人们获得了对于对方的直觉性把握,并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对于彼此的观点、态度、情感获得了直觉基础上的反思和确认的机会,从而实现彼此的沟通和理解(Gadamer 2004:383—492)。汉语言符号系统如果不进入这样具体、生动的传播过程,显然仅仅是一套悬置性的抽象规则体系,而悬置性的抽象规则体系的着陆点恰恰在于这种生动、动态、过程性的传播文本。着陆后的汉语言符号去除了悬置状态下的匿名性,而成为有姓名有角色的具体的交流者的叙述、问答、解释、承诺、期待(Schutz 1962)。交流者在显示其对话主体性的同时,并不把对方作为一种客体或另一个无关的主体,而是通过交流确立了一种共同主体(co-subject)的关系(Levinas 1999)。这种共同主体关系的确立恰恰指向了汉语国际传播的核心目标。汉语国际传播的文本性而非单纯语言符号的线性特点,与这种共同主体关系的确立和维系,存在着理论上的逻辑关联。在具体的汉语国际传播状态下,来自中方的汉语母语携带者不能把对象国的对话者视为单向展示、推介、劝说的对象,不是把中国的一切输出去就实现了上述意义上的汉语国际传播,也不是和对象国的交流对象处于平行线状态,一中一外,各自表述。
也正是由于交流过程的文本性特点,哈贝马斯(Habermas 1998)认为交流至少包括三个基本维度,即对外部世界的指涉维度、交流主体的表达维度和交流双方的互动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划分,说明了汉语言符号在进入日常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已经由作为全民语言所拥有的对于中国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指涉功能,而获得了具体交流主体的表达功能,以及交流者之间在面对面的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互动意义。汉语传播过程的这种多维度特性,决定了传播本身的厚度文本性,而传播文本的有效性又直接决定了汉语国际传播的有效性。汉语国际传播有效性受损或弱化,根本上是由于线性汉语符号系统的悬置状态未能转换为具体的交流者之间的互动过程,未能实现语言符号的指涉维度之外的主体表达维度和互动维度所具有的重要职能。
3.文本有效性与文本解体力量
汉语国际传播文本的有效性并非仅仅将线性的汉语言符号转换为具体的人际互动实践就可以自动形成,并且汉语在走出母语共同体之后所呈现的异域汉语传播,在具体的传播实践中,必将面临在母语共同体内部传播不可能出现的新问题,而这些问题对于汉语国际传播文本的有效性成立条件构成深刻的挑战。汉语国际传播实践的交际失效或无效,不过是传播文本失去有效性的归结。
威胁到汉语国际传播文本有效性的因素主要有:
第一,汉语母语携带者在具体的交流过程中对于全民语言意义上的汉语言符号的个性化应用,包括语音层次的口音、节奏、重音(强调),词汇层次的边缘意义或色彩意义的个性化附加,语法层次对部分句型或句式的高频度使用,如此等等所表现出来的个人言语风格,与对象国汉语学习者借助词典、语法手册、课堂练习所掌握的全民语言意义上的汉语言符号的规则体系,发生着现实的错位。这样的错位不仅会影响交流双方对于对话主题的共识性理解,也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对象国对话者基于自己的汉语学习经验而对中国历史和现实形成的信念。汉语言符号在交际实践中的这些错位,对于汉语国际传播中的交际语言平台会产生程度不同的解体作用,使得具体的互动过程失去了语言的依托,危及传播过程文本构成的语言基础。
第二,支撑传播文本的对话者的表情和体态、对话场景的类型特征、对话的时空坐标以及对话者的社会属性表征等非语言符号元素,汉语母语携带者和对象国对话者之间存在跨文化差异,容易造成双方判断和解读的错位,对于传播过程文本的内在一致性构成解体作用,使这种具有厚度的传播过程文本出现杂音,形成肢解文本整体性的力量。
第三,围绕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对话主题或话题,在话题的熟悉性、与对话双方兴趣的关联性,以及对这些主题或话题所涉及的社会行动、事实、事件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汉语母语携带者和对象国交流者之间存在着跨文化差异,抑制着传播过程文本的生产能动性,使得传播过程难以通过交流或对话而发育成有厚度的文本,也难以在后续的交际场合再生产这种传播过程文本。这种缺乏再生产能动性的文本更多表现为一种冻结而非动态和有活力的文本,所包容的主题或内涵也同步冻结,失去了再生产、再叙述、再讨论直至形成共识的动力。
4.解体的辩证性与传播的魅力
理想或成功的汉语国际传播,实质是具有厚度的传播过程文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每一次生产和再生产,都需要以这种文本的内在连贯性、一致性、统一性为重要条件。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各种解体力量都程度不同地威胁到一种连贯、一致、统一的传播过程文本的形成,从而造成传播不成功的结果。
但是,这种传播文本的非连贯性和不一致性并非毫无意义,也不只是存在消极作用。对话话题的陌生性,汉语母语携带者特有的言语风格和非言语符号装置,面对跨文化沟通场景,对于对话者达成理解和共识所需要的文本连贯性和一致性构成了障碍,但这种障碍本身蕴含着克服障碍的意义,激发起追求互动新奇的跨文化传播实践者的对话兴趣,使得汉语国际传播本身拥有母语共同体成员之间日常互动实践所不具有的特殊意义。超越传播文本的解体因素,克服互动过程中的各种障碍,使汉语国际传播的跨文化互动意义彰显出来,并由此构建更高层次上的汉语国际传播过程文本,实现超越母语交际的文本连贯性和统一性,才是汉语国际传播的魅力所在。与熟悉者的交流,障碍最少,共识也最容易达成,但也是一种缺乏张力和新奇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也最容易转变为一种公式化的交流,转变为身体的问候、季节的寒暄,而汉语母语携带者与对象国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在各类交际实践中障碍最多,共识最难达成,但也是一种具有张力和新奇的交流,在很多情况下也最容易转变为意义丰富、魅力无穷的交流。
参考文献
江 怡 2016 《略论语言与价值的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
李宇明 2012 《当代中国语言生活中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李宇明 2016 《语言生活与语言生活研究》,《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卢德平 2016 《汉语国际传播的推拉因素:一个框架性思考》,《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王建勤 2016 《“一带一路”与汉语传播:历史思考、现实机遇与战略规划》,《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俞可平 1988 《论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基本特征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政治学研究》第3期。
Akmajian, Adrian, Richard A. Demers, Ann K. Farmer, and Robert M. Harnish. 2001.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Austin, John Langshaw. 1962.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rthes, Roland. 1977. Image Music Text. London: Fontana Press.
Berger, Peter Ludwig and Thomas Luckmann. 1966.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o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Blumer, Herbert. 1986. Symbolic Interactionism: Perspective and Metho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erguson, Charles Albert. 1993. The Language Factor in National Development.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35(1), 124-129.
Fishman, Joshua Aaron. 1991. Reversing Language Shif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Assistance to Threatened Languages.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Ltd.
Gadamer, Hans-Georg. 2004.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Continuum Publishing Group.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Bost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Gumperz, John Joseph. 1962. Types of Linguistic Communities. Anthropological Linguistics 4(1), 28-40.
Habermas, Jurgen. 1998. On the Pragmatics of Communic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Levinas, Emmanuel. 1999. Alterity and Transcendence.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Mead, George Herbert. 1972.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ichols, Johanna. 1997. Modeling Ancient Population Structures and Movement in Linguistic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6, 359-384.
Nichols, Johanna. 2008. Language Spread Rates and Prehistoric American Migration Rates. Current Anthropology 49(6), 1109-1117.
Schutz, Alfred. 1962. Collected Papers I.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Searle, John. 1969. Speech Acts: 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London: Syndics of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ittgenstein, Ludwig. 1958.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