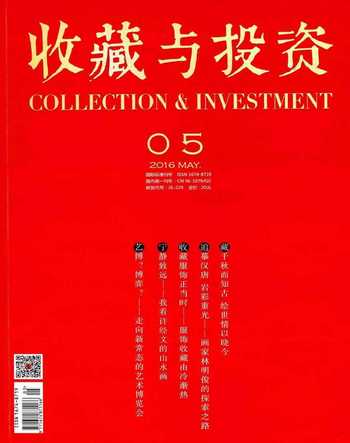元画淋漓说大痴
2016-05-30李安源
李安源



在文人画的历史上,论宗派,王维是先祖;论技法,董源是坐标;论具体而微的影响,则非黄公望莫属。这是由于,在中国画史上,将文人画“董巨”一脉的水墨蕴藉,发挥至淋漓之境者,唯有黄公望当之无愧。董其昌为南宗画的渊源排宗列次,推王维,举董源,而真正落在现实中寻找精神归属与技法依据的,还是黄公望。时年39岁的董其昌,见到《富春山居图》,可谓惊为天作,自谓“展之得三丈许,应接不暇”、“心脾俱畅”,甚至发出孩子一般的惊呼:“吾师乎,吾师乎,一丘五岳,都具是矣。”在明清两代,黄公望的影响,可以说是冠绝千古,无人超越,乃至画坛有“家家大痴,人人子久”之俚言。
黄公望(1269一约1354),字子久,号大痴道人,又号一峰道人,江苏常熟人。其人本姓陆,名坚,出继永嘉(今温州)黄氏之义子,遂改姓名。青年曾为浙西吏使、中台察院掾吏,属于低级官僚,后仕途多艰,因罪入狱,出狱后决别仕进,加入全真教。先流寓松江,以卜算卖画维持生计,后迁徙杭州,往来于吴兴、富春、苏州、松江、荆溪、无锡等地,往来酬答的友人则有杨维桢、曹知白、张雨等,还曾向赵吴兴请教过画法上的问题。于政治上遇到挫折以后,黄公望借全真教进行自我平衡,以稀释内心的苦楚和精神上的伤痕,这也是元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共同志向。不过,对于宗教观念相对淡漠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宗教的皈依往往并不能使他们真正解脱现实的人生烦恼,倒是文艺包括诗文、绘画的创作,才使他们能面对社会现实的同时,又构成对社会现实的某种超越,比如元人杨维桢《跋君山吹笛图》中写道:“予往年与大痴道人扁舟东西泖间,或乘兴涉海抵小金山,道人出所制小铁笛,命予吹《洞庭曲》道人自歌《小海》和之,不知风作水横,舟楫挥舞,鱼龙悲啸也。道人已先去,余犹随风澒洞中,便若此,竞与世隔绝。”(《东维子文集》卷二十八)
黄公望的性情与生活状态,在其中年之后愈发高蹈而超逸,晚明嘉兴文人李日华,对黄公望也是推崇备至,他有段精彩的描述,谓之“独坐乱山丛木间,意态忽忽,人不测其为何,以及每往泖中通海处,看急流轰浪,虽风雨骤至而不顾”,其将黄公望物我俱忘的精神状态,描写得甚为生动。其实,这种精神气质,在元代并非黄公望之独有,在倪瓒、吴镇等人身上也时有体现,这说明了元人所共有的纵身大化、超离现实的人生态度。黄公望最终没有以宗教的功德传后,而是以艺术造诣名世,也正说明艺术较之宗教,对于中国古代的失意文人更具有提炼人生境界的意义。正如虞堪在《题大痴道人黄子久画<关山叠嶂图>》中所云:“老痴作画便痴绝,画山画树画若铁。想从忆昔少年游,饱在燕山度霜雪。重关复道压层峦,万水千山咫尺看。只今无复黄知命,脱去人间行路难。”(《希澹园诗集》卷一)
“元四家”中,黄公望被后人视为“冠冕”,这不仅由于他的年岁较长,而且较之于其他三家,对于董巨画派而言,他更具有“正宗法脉”的意义。而且,对于明清画家而言,黄公望的绘画更具有“经典图式”的意义。此如清人王麓台所言:“画法莫备于宋,至元人搜抉其义蕴,洗发其精神,实处转松,奇中有淡,而真趣乃出。四家各有真髓,其中逸致横生,天机透露,大痴尤精进头陀也。”(《麓台画跋》)再如恽寿平云:“子久《富春山》卷,全宗董源,间以高、米,凡云林、叔明、仲圭,诸法略备。凡十数峰,一峰一状,数百树,一树一态,雄秀苍莽,变化极矣。”(《南田论画》)上述种种,便是就其对于后人的“典范图式”意义而言。
黄公望的绘画风格,大体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浅绛设色,山多矾头,笔势豪迈;另一种是水墨渲淡,皴法较少,笔意简远俊逸。而其共同特点,在于布景用笔,疏密有致,渴润兼备,能于浑厚中饶逋峭,苍莽中见娟妍,纤细处气益宏,填塞处境愈廓。其笔墨之外的荒率浑沦之气,虽然不可模拟,但其林壑、位置、云烟、渲染,无不有条不紊,层次清晰,从而提供给了后学者一种可学而至的规矩准则。在黄公望的传世画迹中,《富春山居图》卷可谓拔得头筹,即便在整个中国山水画史上,该作也是屈指可数的旷世杰作之一。
《富春山居图》为纸本水墨,系黄公望于至正七年(1347)应无用师之请而作,历时数年才告竣工,系大痴78岁高龄之后的铭心之作。卷末自识:“至正七年,仆归富春山居,无用师偕往。暇日于南楼援笔写成此卷,兴之所至,不觉亹亹布置如许。逐旋填札,阅三四载未得完备,盖因留在山中,而云游在外故尔。今特取回行李中,早晚得暇。当为着笔。无用过虑有巧取豪夺者,俾先识卷末庶使知其成就之难也。”据此可知其创作的缘由,而题识时为1350年,尚未毕工,究竟完成于何年,已经不得而知。
在《富春山居图》中,画家将江南旖旎委婉的山水化以纯粹的水墨写出,画作中,层峦起伏,井然有序,水平树静,风和日丽,村居掩映在山麓林间,时有钓者放舟江心,有富春山水之神而不囿于其形,俨然是世外桃源的理想境界,这也正是黄公望烟云供养的精神寄托所在。在该作中,画家技法用长披麻皴,松柔道迈,秀润处显出厚实的力量,而遒迈处又有灵动的韵致。《富春山居图》传世有两卷,结构笔法大致相类,题识却相异。一卷为无用师本,亦即上文所述,现起首一段已经失去;另一卷为子明本,则缺末尾一段。无用本首段之失,相传因清初藏者吴同卿于临终时欲以卷相殉,取以付火,被其亲属抢出,自著火处剪去一段,即此卷首段,称为《剩山图》,又称“烬余本”。乾隆时期,子明本进入宫廷内府,弘历皇帝定为真迹;后来无用本又至,则被定为伪作。至嘉庆时胡敬等编《石渠宝笈三编》,认无用本为真,子明本为伪,遂成定论,而乾隆以真为假、以假为真的附庸风雅,也成了鉴藏史上的一个笑话。近年来,台湾徐复观先生再翻旧案,以子明本为真,无用本为伪,学术界并不以为然,迄至台湾学者傅申又著文拨乱反正,此段公案才得以终结。
除《富春山居图》外,黄公望的作品传世甚多。如其《九峰雪霁图》轴,为绢本水墨,画于至正九年(1349)大痴81岁。该作画面描绘冬季景致,可分三层:近处平坡冰河,寒柯碎石;中景孤峰兀立,密林中掩藏人家;远景为刀削斧劈般的雪峰直刺寒空。全画布局满而实,但由于山石纯用空勾,几乎不加皴擦,所以仍富于空灵之感。天空与冰河以较浓的水墨晕染,烘托出冰山雪峰的明净萧森,正是所谓“借地为雪”的典型画法。方硬沉着的笔道和山石结体,更加凸现了凛冽的寒冷气氛,在黄公望的创作中可谓别具一格。《九峰雪霁图》的画面意象,与《富春山居图》中活跳葱郁的气息全然有别,其整饬与冷寂的气质,则将人带人一个庄严肃穆的冰雪世界。画面中,空间似乎在一个瞬间被节气所冻结,万籁俱寂,高山大岭,天浑水暗,一切都是那么的肃穆与虚渺,不由使人从内心生发出一种“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的凄美意象。
再如其《天池石壁图》轴,为绢本浅绛设色,作于至正元年(1341)。据高启《题天池石壁图小引》,黄公望曾为其弟子李可道画过《天池石壁图》,应与此图有一定关联。天池石壁为吴中道教灵窟,黄公望曾数度游此。此图章法繁复紧密,山形重叠,但由于围绕中宫铺陈,所以不但不见散乱,反而有一种扶摇直上的天矫之势,将景致由平远推向高远,显得十分雄浑。近景长松挺拔,松荫后茅舍隐现,循笔势而上,山峰右掖出一池,池上起陡壁,壁隙有瀑水下注,是为“天池石壁”。画法用赭色点染,墨青合染,即所谓浅绛画法,是黄公望的首创,或以为其长期生活在虞山,所产赭石特佳而有此创格,其特色在于,平淡天真中见高华流丽,所以达其浑厚之意,华滋之气。
在元四家中,以黄公望在明清文人画家中的影响为最巨。不过,如果就画品而论,他其实并不如倪瓒,也不如高克恭。后者虽被后人推重为逸品,可谓文人画的最高品格,但是由于倪瓒的画品过于孤高,高克恭的画派又容易流为率易,局限性均较大,都不具备“正宗法派”和“典范图式”的意义。因此,尽管黄画有时略嫌“细碎”、“刻划”乃至有“纵横习气(董其昌《画禅室随笔》),但站在中庸的立场上,人们宁愿“吾师乎!吾师乎!”地对黄公望顶礼膜拜,从而在明清之际形成了“家家大痴,人人一峰”的画史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