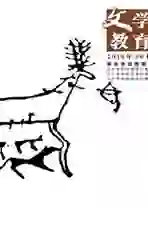一个小说家成熟的三个标志
2016-05-14石华鹏
石华鹏,文学评论家。200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2005年结业于鲁迅文学院第五届高级研讨(文学理论与评论家)班。1998年开始写作,在《文艺报》《文学自由谈》《文学报》《长江文艺》《文学教育》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评论100余万字,出版随笔集《鼓山寻秋》《每个人都是一个时代》,评论集《新世纪中国散文佳作选评》《故事背后的秘密》。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六届冰心散文理论奖、首届“文学报·新批评”优秀评论新人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现任《福建文学》副主编。副编审。
天才除外,每个成功小说家大抵走过一条不成熟到成熟的写作路子。不成熟期一般包含幼稚、模仿、摸索、徘徊等几个阶段,成熟期包含醒悟、成熟、丰富等几个阶段,每个阶段因人而异而长短不一、表现不一。
小说写作者众,不是每个人都会成功,“成熟”是一道门,推开并跨过去,算是真正地登文学之堂入小说之室了,而绝大多数者穷其经年,也都在“成熟”之门外徘徊,所以成熟既是一种写作目标,也是一种写作标尺。一个小说家只有迈入成熟之阶段,写作才能散发出真正的自由和意义出来。一个成熟的小说家至少有这样几个写作品质:强大的小说思维力;敏锐的叙述节奏感;自己的语言气息。如果说某个小说家拥有了这样一些“品质”,那他已经是成熟的小说家了。
所谓的成熟小说家的写作品质,脱胎于小说家成熟的作品,那些成熟的作品所透露出来的信息和特性,其共性和抽象性暗示了这样几方面。
一.强大的小说思维力。
何为小说思维力?就是用小说这样一种形式来思考人事、思考世界,并发现哪里有小说的能力。哪里有小说?哪里没有小说?这是从事小说写作的大事儿。如果你对别人说我在写小说,但你并不知道哪里有小说,而是将自己或他人乏善可陈的生活流水账或人生流水账当小说复述给别人听,读者要么焦虑无比,要么转头就走,因为这不是小说。
生活似海,深广无边,吞吐万物,并不是每滴海水每个海湾都是小说,只有那些或大或小的浪花、或急或缓的潜流,亦或疯狂的海啸才是小说。一个小说家的本事,就是去寻找和发现那些浪花、潜流,或者海啸,并将它们用虚构的面孔讲述出来,这种寻找和发现的能力就是小说思维力。
“用小说来思考”不同于“小说构思”,“小说构思”是对小说内部的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人物等方面的具体设想,而“用小说来思考”是在进入小说内部之前的对生活、对人事、对世界的宏大感受和宏大分析——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样的事件具备了成为小说的可能,小说写作者能敏锐而模糊地感觉到:这里有小说,而那里无小说。
虽然这种小说思维力隐秘而梦幻,藏在作者都可能意识不到的内心一角,但这种思维力的强大或弱小,会直接决定一部作品的出色与平庸。这种能力在作者那里或许藏得住,但在作品里显露无疑,从很多出色的作品里我们能“窥视”出小说家强大的小说思维力。
比如像马尔克斯、卡尔维诺这些大作家自然不必说了,他们的小说显示出他们强大的小说思维力。马尔克斯总能找到完成一部小说最需要的东西——诸如《百年孤独》中置身于时间之中的“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中一场持续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天的爱的激情。卡尔维诺则总能为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找到现实的根基——诸如《树上的男爵》中把人送到树上去让他一辈子不下来,因为人可能是从树上下来的。无论人的孤独、爱的激情,还是让人在树上生活一辈子,这些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们为小说找到的叙述动力,如果找不到这种强大的叙述动力,小说很难成为伟大的作品,而这种寻找叙述动力的能力其实就是一个小说家的小说思维力。
再像如今少被人提起的“短篇王”俄罗斯的列斯科夫、巴别尔等人,即使在小小的短篇里,也能看到他们强大的小说思维力。列斯科夫对故事冲突的热衷,诸如在《理发师》中作者发现自由都是戴着枷锁的,这种发现构成小说动力;巴别尔用静态的战后场景来写战争的残酷,他的《红色骑兵军》中的每个故事都在讲述“每个残阳都在滴着血”……
小说思维力其实代表着一个作家内心的深刻程度,他对人、对事、对世界的深刻的困惑与洞悉,都附着在小说上,并将其带向不可度量的极致。小说思维力有多强大,小说便走多远。
二.敏锐的叙述节奏感。
读一些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小说,其过程总觉得有些不爽,不畅快,不是“隔”(隔一层)就是“硌”(如饭里头吃到沙子),完全没有朱熹说的“读书之乐乐如何?数点梅花天地间”的惬意感觉。
想想,问题可能出在那些小说没能解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两个问题,一是行进,二是停留。就像游人走入一个风景点,这个风景点在设计布置上,既要吸引游人的脚步,继续走下去,又要让游人不时驻足,品玩欣赏。对小说而言,行进就是故事节奏,停留就是叙事张力。
读者好不容易选择以阅读小说的方式来度过时光,所以他们会用早已养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经验对小说提出苛刻要求,要求小说故事不仅舒缓有度地往前推进,而且要像磁铁牢牢吸住铁钉一样,既吸引住他们的眼球也吸引住他们的内心。
有人说读者的注意力是夏天的一只冰激凌,小说要在冰激凌融化之前把读者搞定,此话确有一定道理。吸住读者眼球的是故事节奏,吸住读者内心的是叙事张力,就是语言和细节中渗透出来的东西(如陌生感、氛围、真实感等)能让读者回味。故事行进快了,细节疏了,读者不满足,就感觉“隔”;故事行进慢了,叙事停留久了,读者没耐心,就感觉“硌”。最终,故事情节的缓急和叙事语言及细节的疏密成为小说能否征服读者的重要武器。
对读者来说,行进和停留是两个问题,而对写作者来说,其实是一个问题——即小说的节奏感:故事的节奏和语句的节奏。小说的长、短、缓、急和轻、重、疏、密等节奏处理应该说由小说自身内容、题旨、人物等内部要素天传神授般地自然决定,实际上在众多的小说写作实践中,小说节奏是由作者一手把握控制的,作者像羊倌挥舞手中鞭子驱赶羊群一样任意处置小说节奏,读者往往不买帐。由小说内部要素决定节奏的小说比由小说外部要素——作者决定节奏的小说来得自然、惬意,所以就导致了两种绝然不同的写作情形,一种是一部小说早已存在那里,它的完成只是偶然选择某个作者而已,另一种是作者的勤奋或其他因素使然,没有多少快意地完成了一篇小说。
这样说,是不是把小说的节奏问题推向了不可言说的玄秘地步了呢?可以这样说,也不可这样说,这或许正是小说创作与小说阅读互不相干又互为交叉的两个问题吧。
说得玄乎,并不意味着小说阅读的“隔”和“硌”没有解决之道,依我的感觉,作者做到了“透”——把场面、感受、细节写透了;做到了“顺”——顺着人或物写,避免叙述视角混乱,这样,小说阅读的行进与停留的问题大致迎刃而解了。
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小说家的叙述节奏感是否敏锐,将决定小说的影响力和传播效果。使人着迷是一个小说家应具有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而敏锐的叙述节奏感是小说使人着迷的关键。
三.自己的语言气息。
搜寻阅读记忆库我们发现,每个成熟的小说家,其语言都有自己的气息和味道。多年过去了,鲁迅先生简约丰厚而辣味突出、沈从文古朴传神而雅气十足、张爱玲色彩浓厚音调婉转而藏华丽阴郁之气的语言味道,如承载乡愁记忆的食物那般总让人无法忘怀。小说语言堪称一件奇妙的东西:同样的故事,同样的文字,出自不同写作者笔下,就会沾染各自不同的气息和味道。语言是写作者的表达“基因”和叙述“指纹”。
那么这种独特的语言气息和味道来自哪里呢?来自成熟的小说作者。表面看,是来自作者的字词选择习惯,说话句式的长短、特质,以及所受阅读物和其他作家的影响。实质上这种气息和味道来自更深层面,小说家陈忠实说:“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挖掘人内心的情感,只有这样的句子,才称得上属于自己的句子。”他认为,作家对社会、对生活的理解是一种独立的声音,是把个性蕴藏在文字里边的能力。而正是这种“独立的声音”才形成了每个作家不同的语言气息和味道。
美国小说家卡佛在回答“是什么创造出一篇小说中的张力”时说:“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具体的语句连接在一起的方式,这组成了小说里可见的部分。但同样重要的是那些被省略的部分,被暗示的部分,那些事物平静光滑的表面下的风景。”
两位成熟小说家告诉我们:用语的习惯和独特的见识,构成了小说家独有的语言气息的来源。而在那些还不算成熟的小说家身上,因为用语习惯的摇摆和独特见识的欠缺,所以他们的语言很难形成自己的气息和味道。
别相信一个小说家的语言气息是天生的、是与生俱来的。海明威在谈创作经验时,说了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其实是寻找自己的表达腔调、自己的语言气味、自己的文学个性的过程。寻找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方法,当哪一天找到了,一个小说家便迈进了成熟的门槛。
小说的语言已经被我们谈成了一篇没有尽头的文章,以至于谈论语言时我们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语言既可以谈得很“近”——每个字每个词每句话;也可以谈得很“远”——事关思想、存在、哲学等问题。或许语言只是个感觉,用五官去感受它的气息、味道便可以了。
以上提到的三方面的写作品质,构成了小说家的成熟之本,这一提法与清代诗学家叶燮提出的“诗人之本”不谋而合,他说“诗人之本”有四: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萎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他说的写作者的“才”“胆”“识”“力”大致应和了小说的思维力、叙述节奏感和语言气息等。
那么,一个小说家成熟了就一定会写出流传千古的佳作吗?也许会,也许不会,因为这是另一个无法预料的复杂问题,但是做到这样几方面的成熟,至少是出佳作的前提了。
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或者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我们处理问题的两种方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有时可见论者的学识、学养,但多数是迂腐、啰嗦;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时可见论者的智慧、灼见,但多数是肤浅、滑稽。但是面对一百句两百句话都无法说清的复杂问题时,尽管要冒肤浅的危险,我还是愿意将其简单化,因为“化繁为简”有时能帮我们迅速抵达问题的核心和根本,让我们的表达清晰明了,如果幸运的话,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说不定会有“一针见血”“一剑封喉”的简单化效果出来。
比如面对“小说写作”这样一个异常复杂的文学问题,我更愿意用“复杂问题简单化”的方式来处理。既然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既然一百个读者有一百个哈姆雷特,那么我们何必再成为一个多余的“公、婆”或者一个多余的“哈姆雷特”呢,不如单刀直入亮出自己的“刀法”来。所以当有朋友提出“何为一个成熟的小说家”的问题时,我愿意将问题简单化,认为一个小说家是否成熟,大致有三个标志:一是强大的小说思维力;二是敏锐的叙述节奏感;三是自己的语言气息。如果某个小说家具备了这三点,在我看来他已经是成熟的小说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