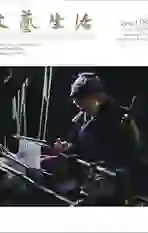浅谈高居翰之《江岸送别》
2016-05-14刘泓艺
刘泓艺
摘 要:高居翰的《江岸送别》以“他者”眼光及追究探究精神,展开了详细的细节论述,跳出以往自说自话的圈子。注重“系脉联系”和对画面构成的分析。同时,注意到以地方派别归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复杂性和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作画题材和风格之间的相关性,且引入了其他领域之视角,显示了异于传统的深入思考的空间。
关键词:图像研究;社会背景;时代风格;个人风格;生活形态;心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J2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3-0124-04
在《江岸送别》的中文序言中,高居翰说道:“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在开拓各种研究方法,想要让各种‘外因——诸如理论、历史遗迹等中国文化中的其他面向——跟中国绘画的作品产生联系.但在当时,我毕竟还是罗樾指导下的学生,所以在研究的方法上,仍以画家的生平结合其画作题材,并考虑其风格作为根基。至于风格的研究,则是探讨画家个人的风格,以及从较大的层面,来探讨各种风格传统或宗派的发展脉络,乃至于各个时代的风格断代等等,及至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撰写《江岸送别》时,已经变得比较专注于其他问题,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只局限于上述那些问题而已。” 以此观之,《江岸送别》确是其学术生涯中的重大转变。
《江岸送别》以分章叙述的方式,以“明初“画院”与浙派、 吴派的起源:沈周及其前辈、浙派晚期、南京及其他地区的逸格画家、苏州职业画家、文征明及其追随者:十六世纪的吴派六个章节展开叙述。书中探讨明代初期与中期的绘画发展,对浙派宽广而细腻的分析,格外让人印象深刻。注意到以地方派别归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复杂性;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作画题材和风格之间的相关性
一、高居翰写作风格及比较
石守谦在《风格与世变》引用了高居翰在其一篇学术论文中一段关于史学观的论述,“我们不应相信有任何的公式,可以在探讨一件作品的风格与其外在因素之间,指明或暗示某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创作者心灵所特具的“复杂与不可预测”性质,即使研究者想尽办法“将他一生之经历与其环境状况及事件联系起来,并且推测画家对其之反应,仍然无法充分地去说明他的画作。”通读全书,很难遇见不拘形似、气韵生动等惯常用来形容中国画的词语,高居翰更愿意用理性客观的文字分析画面构成。
方闻等学者注重艺术品自身分析,比如通过题材、空间手法、色彩关系、形式语言等来逐层分析其特质,寻找个性化的部分。而高居翰,注重政治、社会和经济对艺术的影响,并不完全属于风格分析的范畴。“高居翰认为中国绘画史研究必须以视觉方法为中心。所谓‘视觉方法,就是强调图像与视觉研究的主导意义。对于致力于‘文字文本研究,而忽略视觉研究的方法,高居翰颇不以为然,认为这是一种错误观念,提倡以图像为研究核心”。
本书的叙述,基本从传承和流派角度分析不同画家的笔墨风格,注重“系脉联系”和对画面构成的分析。同时,注意到以地方派别归类艺术家的重要性;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分野的复杂性;明代画家的社会地位与其作画题材和风格之间的相关性。
二、客观评价浙派
本书第一和第三章中均叙述了浙派。选取的浙派画作,确有让人重新审视浙派的效用。没有历史上画评家略偏激的言辞,对其可取之处给予肯定。对晚期浙派画家丰富多变的人格特质、令人愉悦的艺术行径和波西米亚式的人生经历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高居翰可以摒除画评家“气格卑下”等评价的干扰,还原出他眼中浙派所呈现的画面。在介绍浙派晚期画家吴伟的时,本书提到了落魄文化家这一模式,吴伟与之类似。这一模式下的文人都曾有科举落第的经历,转而以绘画谋生。
虽受过正统教育却无以进入官僚体系,有一定才识,却无禄位。这造成了社会角色和地位的不确定性,其内心对自身社会角色和地位的认同也乏定式。因此产生出孤僻不合群的态度非意料之外。对传统或成规也多采取鄙夷态度。本书后来介绍的“扬州八怪和徐渭也属这一模式。
落魄文人这一模式下的画家,并未因其落第经历而被质疑,反而人们认为正是这一经历,让他们得以有机会在绘画等其他领域有所施展,并给予此类画家一定的赞誉。可能因此世上少了一位平庸的官员,而多了一位卓著的艺术家。政治前途上的不幸,却是艺术道路上的幸运。书中对落魄文人画家吴伟的的叙述,其粗放一类的画风似在个性特征里找到了根源。通过对吴伟鄙夷权贵,个性不羁的描绘,本书勾勒出了落魄文人画家更为清晰的剪影。将浙派的吴伟归为落魄文人画家一类,与“扬州八怪”等同属一类,本身也是对吴伟的客观对待。
吴伟的《二仙图》属其人物画粗放一类。线条遒劲老辣,有多处突然转折,忽粗忽细。前方仙人略诡谲的笑和后方仙人显内敛的神情,耐人寻味。画面极富力量感的线条为主题的呈现,增加了形式上的分量感。书中接着选取属于细腻作品一类的《美人图》。难得一见的吴伟的细腻温和画法。画纸中央有一女子伫立,微颔首,轻托琴。她侧着身,似乎是有意识地避开了从画纸外射入的目光。空荡的背景,女子的动态轻微,难辨识是欲向前踱步,还是停在原处。吴伟笔墨中的情感特征添上了温和且忧郁迟疑的成分,和其最为人所知的粗放风格形成反差。
高居翰选择吴伟粗放人物画的佳作《二仙图》的同时,不忘将《美人图》纳入写作。即使其细腻型风格不那么为人知知晓,并不妨碍作者企图展示吴伟更全面风格的想法。书中选有戴进和吴伟的两幅主题相似的作品,分别是《秋江渔艇图》和《渔乐图》。《秋江渔艇图》受到了吴镇的影响,采用了漫画式的粗线描法。画中的渔人并不像吴镇所描述的文人隐士那样,坐在河面上静思默想,起码有些渔人正忙着捕鱼谋生。有自然随性的效果,但事事物物却又安排妥当。戴进在抒发和法度之间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渔乐图》 描绘渔村忙碌的生活,渔夫和家人忙着工作,并享受生活中片刻之乐。不见吴镇《渔夫图》中渔夫悠然垂钓的适意情态。吴伟采用粗犷有力的笔法,近似现代的速写,不是工笔而是写意画的一次尝试。“随着彼时节奏而自由发挥,让笔法的顿挫支配其勾勒形象的能力。”①二者作品作比,吴伟的笔法比戴进的更为轻松不受拘束,而戴进画面中呈现的的秩序感较吴画明显,但戴进对疏放和法度之间的把握优于吴伟。吴伟对戴进的继承和发展,由此比较可见一斑。
写到“邪学派”画家张路时,高居翰更态度鲜明地表示“这幅画(指《人物图》)与张路的其他作品应该能让我们重新评估画评界对他的贬抑,。”赏罢《人物图》,我便较能理解为何高氏会略显愤懑得出以上言辞。“画家的笔触柔和,图样也不那么大胆。张路使用这种亲切的形式,来表现墨色、宽度、湿度以及力道,好让他的笔触能曲尽精微。他的线条奔驰,运笔紧凑纷繁。”两个人物向前微倾的姿势及专注的神情,使画面笼着融融的氛围感。
读罢浙派晚期这一章节,浙派在读者心中构建起更为全面的印象,产生更为客观的评价变得自然可行。但其对浙派衰落原因的叙述,多提及浙派末期画家的自身因素,对其他客观因素却鲜有涉及。身处画派发展历史上的末流,是张路、蒋嵩等无法选择的,将原因仅归结于主观因素,显然略片面。对比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其实是颇勤勉而节约,可以称的上励精图治。但此时明朝已腐朽至极,尽管励精图治,有力挽狂澜之志,也终无回天之力。由此观之,对待浙派之没落应充分考虑主客观因素的综合作用。即末期画家自身因素和不同艺术品位的群体势力的竞争等客观因素综合考虑。
三、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
谈及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惯常会将个人风格置于时代风格的羽翼之下,至少个人风格中的多数成分被认为符合时代风格。如清初“四王”引导着仿古风气,并一直践行。按传统审美模式的心理定式,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他们的个人风格融入了时代风格并为之影响。
本书第四章介绍的徐渭,却是疏离时代主流风格的一个。徐渭不亲近吴派或浙派,根本不是传统派常讨论的画家,因其画作纯系自发与兴来神到之笔,完全独立于固有模式与既有传统之外,被打上特立独行的标签。但从其体现的个人风格与时代风格的疏离,却不妨碍徐渭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创立和对新形式的探索。
明代花鸟画以水墨写意为主, 但工整艳丽的花鸟画也相当盛行。而徐渭将写意花鸟画发展推向新阶段,在后世发展中,写意花鸟较工笔花鸟占据更重要地位。在徐渭前的时期,两种花鸟画都较为盛行,无明显一种对另一种的压倒。正是徐渭向并存的另一风格发出挑战,为写意花鸟的发展注入源动力。
如果说苏州绘画的一般特色是较人文的、诗意的,南京的绘画则是与当地的通俗文学息息相通:偏好叙述性主题:喜爱描绘人物与其出的情景:以及喜欢各种看陈是戏剧性的效果等等。②明朝时期活动主要苏州和南京的绘画流派,如吴派和浙派,其主流大抵符合一般特色。徐渭的写意风格比吴派山水浓郁诗意氛围显得更为恣意不羁,也异于浙派晚期画家企图以活泼而硬朗的笔调,消解实质的物形的做法。徐渭《杂画图卷》中的牡丹以不规则的斑斑水墨晕染,仿佛是随意至兴而落笔,背景未着一墨。不见前人在着重刻画花卉的艳丽娇嫩的着力,却赋予牡丹相似于梅和菊的高逸清雅气质。高居翰评价“这幅画史少数不费力、且近乎奇迹般地把视觉形象转变为笔墨的中国画之一,对于主题及其潜在本质和视觉的特色,也有深深的投入。”没有沈周《憨憨泉》中融融的氛围感,笔触亦迥异于沈氏宽湿而确定的笔触。
戴进《竹石菊图》是院体风格的佳作。山石的轮廓以侧锋勾勒,正面用淡墨细致渲染。竹子双勾填色,并着以淡墨。画面展现出严谨细腻的风貌。较徐渭之作品,多了工巧和更多人工雕琢的成分。不意在分二者孰优孰劣,戴氏作品的刻画入微,形象逼真,着实让人印象深刻。徐氏作品中呈现的少人工痕迹的自然状态,同样使人触动。
相较于吴伟的《渔乐图》,徐渭《墨葡萄图》中流露出更明显的经人格化的形象特征及喻意性。《渔乐图》中一改较常见的静思垂钓形象,代之以富于动态的生产活动形象。画中人物或侧身,或俯身,目光与从画外投入的目光并无交接。作者没有试图邀观者进入其中。中国画的自觉意识在徐渭处,得以更不加掩饰地晓畅抒发。不依靠物质外形的精细刻画,徐氏大写意作品中的花卉植物伸展得格外恣意,如《墨葡萄图》中的葡萄形象,远比自然环境中的显得富于个性。在藤蔓的不被束缚的伸展中,徐氏找到了情感共鸣。葡萄藤的在纸面呈现的生长状态,或许正是徐氏渴盼企及的生命状态,伸展生长间似裹挟着某种气力,冲破束缚,得以自由徜徉。墨葡萄明显是用块而有力的笔触点画而成,无法一一辨认轮廓。自然环境中若想觅到生长的如此富于个性的葡萄藤,想必非易事。或许徐渭的纸面是其最佳的伸展之处,或许它只在徐氏的纸面中,才得以生长的这般恣意。
明朝的早中晚期,有相异的花鸟画审美趣味,花鸟画的主流风貌随着历史演进而变化。不完全因袭前面时期的主流风格,创立极具个人特色的风格并探索新形式,在吸收之上加以创造,徐渭的开拓精神大致于此。
然而,企图完全脱离时代背景和时代风格,具有一定难度。既身处某一时代环境,似乎注定难以完全遗世而独立。可并不意味着展露个性,试图与时代风格偏离的努力就收效甚微。徐渭在对前期主流风格在延续的基础上有所疏离,并在相互碰撞中愈显闪光处。徐渭特立独行的个人风格与时代主流风格的疏离,并没有成为创作的阻碍。徐渭的实例体现出,在一定程度上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的疏离,未尝不益于艺术家的创作活动。
四、画家的生活形态与画风倾向
在本书第四章第四节的开端,高居翰便说在前面几章中,多次提及画家的社会地位与画风的有联系。自古以来,中国的画论家和画史学者一直假定二者间有必然联系,通常认为一个人成长发展的环境总存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期待。接下来,高居翰也提及“近年来,一些西方学者却趋向于确切否定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艺术的说法。他们质疑,艺术家的业余或职业身份是否真能决定其风格,浙、吴两排的区分是否相当明确而且有用?”
不同的人身处不同的环境和阶级,接受的社会期待不同,因此个人对身份的期许和认同也会相异。社会期待及自我的身份和文化认同,成为画家无形的标签。同为吴派的文徵明和唐寅不可能互换画风,尽管二者尚且身处相对近似的文化氛围。分属吴派和浙派的沈周和吴伟,互换画风之可能性则更微。
文徵明因其父文林与沈周相识,因此师从沈周学习。唐寅并无此良好的学习机会,因结识文徵明才得以一同前往学习。唐寅的父亲曾预言唐寅“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印证了其日后中南京结缘而年少成名。可能是出身商业家庭之缘故,唐寅对社会事务的洞察比文徵明敏锐。虽民间流传的关于唐寅的风流轶事中,不少有附会之嫌,但与其不避讳表现自己好色好酒的性情不无关系。而文徵明显然不属于年少便才华毕露之人,应考多次,却终不得一举人。
以唐寅的《秋风纨扇图》和文徵明的《兰竹图》作比。《秋风纨扇图》中以仕女轻托扇,微颔首,眉宇间隐约流露出幽怨抑郁的情绪,与《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外貌描述“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有神似之处。画家或许不意在刻画仕女哀怨的情态,而意欲传达一种既试图贴近却无奈疏离之感。画中试图传达的,可以对应于唐寅的人生经历和心境。致仕之道路幻灭后的怅惘,却还不至于完全消解入世的情绪。同时,对不公平遭遇的慨叹,以致生出远离世俗的想法。唐寅未完全消解入世的想法,同时免不了因科举科举舞弊案心生避世情绪,这可能是画中仕女显得既贴近又疏离的深层原因之一。文徵明之《兰竹图》似乎是其严谨正直,洁身自好的人格之物化象征。竹的形象挺直而劲健,兰叶飘逸中显疏朗,赋予兰竹以人格化特征,二者生长环境环境给人以荒率冷寂之感。画面整体晓畅而古朴。
沈周吴伟二人的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有自然性格不同、文化性格不同和家庭背景不同。吴伟年少时,因父亲去世而成为孤儿,后来又意味地方官员抚养长大。其意在仕进,却仕途无望。沈周的高祖父于元末时已经奠定了嘉业,其祖父、父亲等都过着如隐退文士一般的生活。沈周醉心生活于山清水秀的苏州温柔乡,无心仕进。而二者成长的文化氛围自是迥异的。沈周素来敦厚、温和而淡泊名利,吴伟则是具有颇典型的波西米亚式不羁狂狷气质,自性格而论,二者作品风格的产生缘由,可窥见一斑。作品风格中以部分取决于性格,性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又对看待处理事物的角度和层次产生影响。沈周作品中敦厚平和的意趣和吴伟粗放型作品中可感的动荡氛围,无不是性格性情的外化体现。
沈周的风格必须符合其社会地位,而吴伟则又他另外的社会地位对其风格产生影响。吴伟有中内在的波西米亚式的不羁气质,其最为人所知的绰号“小仙”这体现了时人对他的评价,孙然并非很严格地将吴伟比喻为道教仙人,正科现实出诗人对他的砍伐,以及不因循传统、不沾世俗的人格特质。③这些特质似乎是深入其骨髓的,成为其人生和性格的底色。在观其画前,如对其性格特质加以了解,似乎可增添解读的欲望和深层面向。吴伟一类画家博学却无禄位,自易生出一种与世不相融的态度,对世俗之事常显露睥睨之态。相似的例子,有清朝的“扬州八怪”,明朝的徐渭等。看似是社会上的异类,实则是颇具想法主见的人,对传统和成规表现出或多或少的反叛及不屑。并较常人更感触敏锐而富于观察力。
以沈周的《憨憨泉》和吴伟的《渔乐图》作比。前者中,以湿笔点染而成的树叶,或疏或密,丰富了画面肌理。占据画面大部分空间的树木,跟人以敦厚坚实之感。悠闲的文士在憨憨泉附近漫步,笔墨宽阔而随意,画面具有诗意和融融的氛围感。看似平淡,却不乏可读性。吴伟的《长江万里图》主要描绘长江沿途的壮丽云山、幽谷山村等,最先攫住观者的是画面莫可名状的气势感,气势动荡而不至混乱,笔触松动却不乏秩序感,具有超越画面尺幅的时空容量。
若以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观点“苦难显才华,好运隐天资”和某些浪漫主义式的”文穷而后工”来看,沈周安稳平顺的人生经历,无法造就卓著的艺术家。吴伟不乏波折起伏的人生经历,却颇符合某些观念中画家成长模式的预想设定。从书中吴伟这一小节多次讲到其狂狷不羁,不囿常规的逸闻,似可看出高氏对其独特性格特质实则具有一定兴趣。其逸闻能以带有褒扬意味流传至今,可见其性格特质和不拘一格的行径反倒是成为某种标签,变为促成其成功的因素之一,并增添了后世历代观者的解读意欲和兴趣。沈周和吴伟的生活形态,自身性情和所受的社会期待,产生了深入骨髓的影响。
但这并不意味着带有社会地位标签或职业标签的画家没有尝试进入对方的领域。“不论文人画家的技巧如何熟练,都不可能逾越自己的领域,而进入技巧晚熟的职业画家及其所承袭的绘画风格范畴之中,否则,必会招致不利的批评。而职业画家在某种程度上,纵然已经受到‘业余风格的不当影响,但也无法借此展现他真正高超的画技。”④作文文人画家的钱选,其作品不乏对山石以一笔一笔地皴,树叶也可见一点一点的点染笔法,刻画入微似乎略有工巧之嫌。但他是作为初变革南宋画风的先行者,克服了南宋画风之流弊,广泛汲取晋唐以来多方面的艺术营养。其画作总是在力图体现文人情趣,流露才思,提倡“士气”为意旨创作的,属于文人画之范畴。
传统思维模式下,女性画家的作品总会不自觉地被贴上女性特征的标签加以观赏解读。观者也易惯常以为女性画家的题材或多或少局限于富于女性柔和纤弱特征的事物。但并不意味着,诸如女性画家就不能摆脱所谓的标签进行创作。意大利17世纪的女性画家阿特米希亚·津迪勒奇是卡拉瓦乔风格的追随者,其作品《尤滴割下霍洛费讷的头》选取了完全不同于男性画家的视角,呈现割下头颅这最为血腥的一刻。阿特米希亚没有因循这一题材的传统诠释,尤滴的女仆没有被描述为一个老迈的被动的妇人,而是一个富有行动力和力量感的年轻女性。其画作被公认为具有男性气概。阿特米西亚自己曾说:“在这个女性的灵魂中隐含着凯撒的精神。”该画用侧光和黑暗为背景,烘托出恐怖血腥的场景,展现出父权主义下女性的激烈抗争。此实例证明画家之风格也的确确存在异于特定社会期待的情况。
画家的生活形态,自身性情和受到的社会期待,会对其创作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画家本人可能是自知的,也可能是不自知。依佛洛依德的潜意识理论,画家以符合上述因素的方式进行创作,不一定全是来自于理性的思考,而是来自于潜在的动力。
五、引入精神分析之视域
徐渭早年绘制的葡萄,物形明晰而有剔透之貌。经历牢狱一事后,徐渭的葡萄大部分都是由恣意放纵的笔墨点画而成,难以一一辨认葡萄的物形,有些地方就用大小不一的墨块表示。墨葡萄无疑是画家错乱心灵的流露。比之于表现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蒙克的《呐喊》,画面中心人物是一个几近骷髅形象,面目模糊,只能辨认出其概念化的五官。躯干在不安的扭动,似在竭力发出惊叫,惊叫声仿佛可以穿透画面而来。桥的尽头伫立着两个面目更为模糊人,挺立的身影与主要人物同样形成对比。画面上部,橙红色的晚霞氤氲在空中,扭曲而动荡,并没有呈现以往晚霞给人的平静闲适的印象。画面上,虽没有任何具体物象暗示这一惊叫被何引发,亦没有任何暗示不良情绪的物象,整幅画却笼罩在莫可名状的压抑氛围中。
观徐渭作品,若不事先了解其的生平,观者不一定会由画中猜到徐氏的悲剧命运和性格。“如果选择一西方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还可能轻易地从画作来判断出画家是个才情洋溢,极为善感,但基本正常的人。”⑤徐渭意在抒发而非传达不安的情绪,这可能是画作效果的关键。“画家把创作当作是排除心中苦恼的渠道,因此绘画对他而言,乃是治疗而非病兆的象征。”⑥书中选取的《杂花图卷》的牡丹部分,。以不规则斑斑水墨晕染,仿佛毫无计划一般,完全是兴之所至,情之所溢的外化体现。片片花瓣并不能清晰的一一辨认轮廓,却不影响整体视觉形象的呈现。
由较黑墨色扩散开来表现的花瓣,其垂坠感和轻微的弹性,似乎可感。若说院体风格的牡丹蕴含浓厚的人工精心呵护的痕迹,徐渭的水墨牡丹则好似生在在自然环境中。不见娇媚,却多了疏朗坚韧的气质。其这样解释创作缘由:“牡丹为富贵花王,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勾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寠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亦弗相似也。”言辞中依稀可读出忧愤,并以自嘲式的口吻称自身是穷人,相宜于梅竹。但在徐氏心中,梅竹岂是所谓的“穷人”足够相配的。其高逸的格调,更相宜于虽乏于物质资料,却内心安适富足,自拥一方精神空间的士人。再对比王蒙的《青卞隐居图》,观者更易生出惴惴不安而惊惶的情绪。以往观山水画,观者试图寻觅一条足以欣赏景致的探幽之路,边悠游边体味。在《青卞隐居》中,显然这种努力失败了。美国学者罗樾形容这幅画构图“不是描绘崇山叠岭,却像一个恐怖事件中的火喷景象”。高居翰发觉,它“在空间和形态上明显不循常理,用光有纷乱的人为感觉”。在繁密的树林中,有一人曳杖而行。山峦起伏变化,山势逶迤而上,似乎裹挟着某种内在的力量,却又努力压抑着,使不至于过度显露。目光所及的远处,坐落着数间茅屋,屋内有一隐士抱膝而坐,醉心于自己的内心世界。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充塞整个画幅的布景和重视“气势”的表现。有一种气脉的流动感,层峦叠嶂,逶迤上升,甚至让人倍觉逼仄难以喘息。
高居翰在此引入了西方心理学角度加以分析,拓宽了对作品的理解视域。自古以来,绘画与人类心理活动就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梵·高的《星月夜》以高度夸张变形的形象和强烈的视觉对比,传达出内心的动荡不安和心绪起伏。他无处安放和宣泄的情感,借由画布上的星空得以流露。可以说,梵·高用绘画拯救了自己。杰克逊·波洛克将绘画看成一种自发性的活动,其创作不作事先规划,作画亦没有固定位置,偏爱在画布四周随意走动,以反复的无意识的动作画成复杂难辨、线条错乱的网。其作品记录了他作画时直接的身体运动,记录了心灵轨迹之变化。
由此,还可联想至绘画疗法,让绘画者透过绘画的创作过程,利用非语言工具,将混乱的心绪、不解的感受导入清晰、有趣的状态。可将潜意识内压抑的感情与冲突呈现出来,并且在绘画的过程中获得抒解与满足,而达到诊断与治疗的效果。其理论依据主要有荣格的和弗洛伊德的心理动力学。
若用佛洛依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观徐渭,其风格有自我和超我之成分。自我这个概念是许多心理学学派所建构的关键概念,虽然各派的用法不尽相同,但大致上是指个人有意识的部分。徐渭作品中个人意兴的流露,具有兴之所至情之所溢,需一种渠道以宣泄,所以诉诸于笔端的意味。超我成分则体现在其放逸狂狷却不混乱,畅快洗练而不失内蕴的表达。表面上试图挣脱束缚,打破陈规,实则也暗含某种内在的秩序感和自省意味。一如超我指导自我,限制本我的效用,徐氏画作中内蕴的自省气质和豁达意味,让作品不会呈现令人不悦之貌,试图超脱束缚却不至于脱缰混乱。绘画艺术的两大核心因素,分别作用于个人之内和人际之间。个人之内体现为自由性、自在性和自发性。人际之间表现为能引起心灵能量的共鸣、共感和共振。徐氏于内治疗了心灵,于外则触发后世经历有经历相同者的情感共鸣。
与西方心理学分析相结合,可以为中国画家的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添上心理学的注释,以此贴近画家心灵和创作当下的心境。高居翰引入西方心理学之方法,达到为观者拓宽解读作品之视域的效果。
“他者”眼光需要有追究探究精神,需要细节论述的展开,跳出以往自说自话的圈子,以显示其异于传统的深入思考的空间。阅读完高居翰的《江岸送别》,可以感觉到以上正是他努力企及的,他的确达到了。
注释:
①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100.
②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94.
③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95.
④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175.
⑤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174.
⑥高居翰.江岸送别[M].北京:三联书店,2014: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