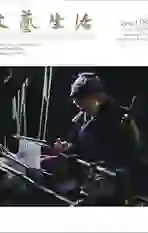比对《城南旧事》评萧红《小城三月》的儿童视角
2016-05-14戴艺贝
戴艺贝
摘 要:萧红的《小城三月》是典型的以儿童视角来叙事的作品,但与同样用此视角写作成的《城南旧事》相比,儿童所承担的情节分量不同,也因此呈现出了具有萧红精神的独特样貌。
关键词:儿童视角;城南旧事;小城三月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23-0017-02
“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的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孩子一样大大咧咧地看天看地、又纤细敏感地计量着生活里分毫的乐趣,读着这样的句子,你也就知道——是萧红来了。
有评论家称:“童年记忆使萧红一直没有长大,一直保留着小女儿心态。”似乎在她回忆性的笔下,蹦跶着的始终是那个跟在祖父后头东一脚西一脚瞎闹的娃娃。说“一直没有长大”其实不然,在《小城三月》中我们就能明显感觉到这是一个正向少女转变的孩童,她会弹奏乐器了、愿意一家家店逛着去挑花边和绒绳鞋了、也上学读书了;但“一直保留着小女儿心态”倒的确如此,在这部作品中也通过“儿童视角叙述”这一萧红惯用也擅用的手法而崭露无遗。
儿童视角的使用,首先易于向读者展示成人目光易忽略的细节。兴许是个子小的缘故,似乎看天格外悠悠远远、看地格外结实细致,山不是山水不是水的,风景都有一种别致的鲜活——翠姨坟头草籽已发了芽,常有白色的山羊从淡青色的坟头跑过;春天也快步跑着像人能看见似的,刚在耳边吹一句“我来了呵”即刻便又跑走。兴许是没什么正事的缘故,看人便能定定心心地上下打量,人在孩子面前也没什么正事,于是也便除去平日里的装模作样、是怎样就怎样地被打量,言行细小之处都显出一种让人直记到心里去的动人——翠姨的妹妹永远合着“应有尽有”的原则、芜杂地被衣服穿着;翠姨则是那么得体窈窕,就连拿樱桃也只敢怜惜地用指尖轻捏。兴许是能无所拘束、撒野胡跑的缘故,才易于不经意时撞见在人前本羞怯地舒展不开的眉眼,虽只有一些难以捕捉的纤薄表象却让人开始揣度这下面暗自汹涌的情感澜波——翠姨跑进了里屋,哥哥便好久好久地看着那帘子;打完网球的大伙儿都散去了,惟有翠姨对着夜色里哈尔滨的市影遥远地痴望;哥哥讲故事的时候翠姨总比他人听得更留心,但那“显然”是因为翠姨年纪与之接近所以更能理解罢了;哥哥与翠姨说话也不是平日“对啦对啦”的随意,那客气的“是的是的”也“显然”是因为翠姨是客人且名分大罢了……
萧红虽然通过儿童视角悄悄揭示了翠姨悲剧性的爱情,但在整个过程中“我”只是观察着、叹息着,并没有扮演一个产生实际效用的角色,这与林海音笔下承担了情节重任的儿童“英子”极为不同。
《城南旧事》同样因儿童视角叙事而活泼有趣、清新隽永,但其中几章节粗糙点概括便可以说是“孩子好心办坏事”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孩子是如此举足轻重。譬如在将秀贞与妞儿(小桂子)的关系向读者点明前,英子不仅有许多比如“妞儿,不,小桂子在哪儿呢?我刚说的?”这样莫名的人物混乱或面孔重叠,在听不同人讲述同一事件时还总是迷糊觉察到“我好像听过这个故事,是谁讲的呢?还说大清早就把那孩子包裹包裹扔到齐化门城根去?也许我是做梦,我现在常常做梦……”似乎在孩子潜意识里,这一切线索人物都已经串联完整并有了一个棱角鲜明的轮廓,只等她什么时候把那层蒙尘的白布揭开即可。
林海音用儿童视角来草蛇灰线地埋下伏笔的确很有朦胧又似是而非的悠远感,这样安排的最大妙处在我看来是能引发读者心情的复杂和无奈。悲剧的产生你找不到可以责怪的人——孩子当然不是悲剧的制造者、事件中即使身份灰暗如小偷的悲剧角色也因与小英子的交流而展露出作为“人”的善——让人联想到柴静曾写的,没有“好人”与“坏人”之分,只有“做了好事的人”与“做了坏事的人”。明明可以温情、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就像孩子能察觉到成人未曾察觉的人之善、孩子同样不会无视人之错——对于孩子来说,凌驾于对错好坏之上的,或许是“真”,他们没有那个判断选择的概念,只有一种如实的本能。但如此布置的缺陷也较为明显:一方面,潜意识如此敏锐、现实表现又如此迟钝,二者不免有些落差,读者在这暗示下很容易先于英子猜出整个脉络、却只能看着这傻孩子一天到晚做梦似的仍不明白,实在让人心急;另一方面,孩子承载的故事分量实在太重了,不仅在潜意识里整合了线索、揭示了人物身份与关系,她不经思虑的一次次决定也直接影响了故事走向和人物命运,就悲剧的产生来说,虽不能说她要“负责任”但已不能说是“无辜”的了。
相比之下,《小城三月》中的“我”则更像从平常日子里走出来的孩子——对于他人生活不会起到任何决定性的影响,而是像普通儿童那样不寻求理解、不担负责任、不揭示深刻内涵、只坦白而真诚地叙述着自己的所见所想。“我有一个姨,和我的堂哥哥大概是恋爱了。”孩子很早就瞅出了端倪,但那又如何呢?既不见她笑嘻嘻地将横隔在两人之间的窗纸戳破、也不见她“打小报告”似的去母亲那儿邀功——只要她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或许哥哥就能明白女儿家永远不能用自己唇舌吐露的心事、而非“提起翠姨的常常流泪,也不知她为什么死”,或许母亲就能劝阻那桩把翠姨逼上绝路的婚事、而非叹惋道“要是她一定不愿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们当我说……”或许翠姨悲剧性的命运便能就此改变。然而孩子始终只是在一旁无心地瞥见而已。
不附加情节任务的视角也许与生活中儿童似懂非懂的真实状态更贴近,也让读者有了许多靠自身揣摩而顿生的乐趣,但《小城三月》的儿童视角还有两处值得推敲的地方。一方面正如前文提到的,“我”是一个正向少女转变的孩童,相比于《呼兰河传》里懵懂稚嫩的想法,作品中“我”则偶尔流露出一些成人性的感触——“我很想装出大人的样子来安慰她,但是没有等到找出什么适当的话来,泪便流出来了”、“耳边的风呜呜的啸着,从天上倾下来的大雪迷乱了我们的眼睛,远远的天隐在云雾里,我默默的祝福翠姨快快买到可爱的绒绳鞋,我从心里愿意她得救……”兴许这些感触并不完全来自“我”在情节当下的见闻,兴许还融入了作者在回忆这些隔着岁月风尘的沧桑世事时难以抑制的慨叹,但看着一向对翠姨暗藏的情愫并无不太上心的孩童突然对其身世、对其婚姻、对其隐秘的绝望都感知敏锐,未免有些突兀。另一方面,儿童视角并不是上帝视角或全知视角,采用何种方式叙写一些儿童不在场的事件是很值得细细揣摩的,萧红在《小城三月》中有一段非常明显的儿童不在场叙事——“哥哥正想,翠姨在什么地方?翠姨大概听出什么人来了,她就在里边说:请进来。哥哥进去了,坐在翠姨的枕边,他要去摸一摸翠姨的前额,是否发热,他说:好了点吗?他刚一伸出手去,翠姨就突然的拉了他的手,而且大声的哭起来了,好像一颗心也哭出来了似的。哥哥没有准备,就很害怕,不知道说什么作什么。他不知道现在应该是保护翠姨的地位,还是保护自己的地位。同时听得见外边已经有人来了,就要开门进来了。一定是翠姨的祖父……”这段情节只发生于哥哥和翠姨两人之间,翠姨不久就去世了、哥哥也始终是茫然状态,“我”从何得知那些细微的带着体温的动作、又从何听得翠姨那“我心里很安静,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悱恻之言呢?当然,相比于交代翠姨临终那一番话语的重要性,如何交代实在是一个小之又小的问题;且细想如果为了交代无碍而安排第三个人比如“我”在场,翠姨最后又一定无法像与哥哥独处时那样尽情吐露自己的情绪,因此这也只是读来有些顿挫罢了,并不影响整个情节的叙述与作品的卓越。
萧红笔下的儿童视角从《呼兰河传》到《小城三月》一脉相承,“我”的年龄也许渐渐增长,但因为始终没有在情节中承担任何重负、而始终表现出孩子一样的懵懂无辜,也正因如此,萧红笔下的人事都更显出一种命运既定、人力无法催生或扭转的无奈感。无论“我”年龄几许,始终保有一颗敏感真诚而不刻意介入什么的童心,或许这也是萧红的珍贵之处。
参考文献:
[1]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2]林海音.城南旧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