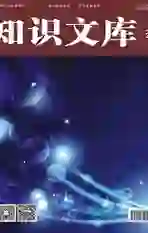辽宁建昌东大杖子陶礼器墓葬研究
2016-04-29赵鹏
辽宁建昌地处辽西丘陵山地,燕山余脉延伸至此。该地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是古代联系中原与东北的交通枢纽,中原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相互碰撞于此。战国晚期,该地纳入到燕国的版图,《史记》110卷《匈奴列傳》记载:“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在此之前此地一直为东胡人所有。东大杖子墓地便位于建昌西南大凌河上游,墓地的年代应早于燕设五郡的时间,然而墓地中却包含大量燕文化的因素。其中M40与M47更是整个墓地中规模最为庞大,规格也最高的墓葬,其土的大量仿铜陶礼器无论从形制与纹饰上都具有浓厚的燕文化特征,其中M40中带墓道的形制更是这一时期东北地区所独有。
一、东大杖子M40出土器物及年代
M40位于墓地的东部,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墓葬区域。墓葬为带墓道的土坑竖穴墓,墓道位于墓穴的西部,自原地表至西部外椁顶,呈斜坡状。墓圹开口一下有生土二层台与三层台,在东部二层台的中间放置大量动物头骨。
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燕国仿铜陶礼器,器型有鼎、豆、壶、盘、钫、簋、盨、罐、灯,其中鼎、豆、壶、盘为典型战国燕墓的器物组合。与燕文化中心文化区燕下都九女台M16与东斗城M29出土器物相比东大杖子M40出土的陶鼎M40:4,器盖圆形隆顶,四周俯卧着三只短尾兽形钮,器身子口内敛,腹部较鼓,圜底,整体形制与东斗村M29:7相似,而较之九女台M16出土的Ⅱ式鼎,鼎身腹部稍浅,底部也较为突出,且鼎足也相对较高。陶盖豆M40:30与东斗城M29:3、九女台Ⅱ式豆相似,唯独豆盖上鸟形捉手不同于后者的细高捉手,M40:30豆盘与豆盖扣合后较之M29:3更为扁圆与九女台Ⅱ式豆相同。陶壶M40:8形制与东斗村M29:14相同,圆形盖隆顶,在壶盖的边缘均匀分布着三个鸟形钮,器身侈口方唇,长颈微束,溜肩鼓腹,喇叭形圈足,圈足较高,器身肩部附有对称辅首。而较之九女台M16Ⅱ式壶圈足更长,器盖上的鸟形钮也更为高大,整体瘦高,而M16Ⅱ式壶则略显矮胖。陶盘,三墓出土陶盘形制相似,皆为浅腹,折腹外缘突出,两长方形附耳,圈足。根据战国燕墓仿铜陶礼器的演变规律鼎盖由平渐隆,鼎足由细高渐矮粗。壶盖钮与圈足皆由高大向矮小发展,壶腹重心由上至下偏移。可知东大杖子M40的年代应早于九女台M16,而与东斗城M29时间相仿。然而就三座墓葬的形制以及出土器物整体形制以及纹饰来来看,特别是M40与M16均有出土带方形底座的陶簋与带圈足的陶盨等,三座墓葬应处在同一时代,但是M40较之M16时间要早。郑军雷先生在对战国燕墓进行分期时,将九女台M16与东斗村M29归为战国燕墓第二期,并认为九女台M16出土的陶匜匜口较M29更加鼓圆,盖豆豆柄较M29出土盖豆豆柄略显短粗,陶盘盘身较之M29出土陶盘也显得略深。所以综合来看尽管两者为同一时代,但M16略晚于M29。这也从侧面证明我们对M40时间的推定。
郑军雷先生认为第二期的燕墓开始以陶礼器替代铜礼器,鼎、豆、壶、盘、匜等陶礼器直接模仿铜礼器,制作较为细致、逼真,第二期应与第一期时间相差不远。通过对一期的铜礼器形制与纹饰的分析,他认为第一期的年代应为春战之际,而第二期则为战国早期,我认为这样的推断是合理的。由上文可知东大杖子M40应与东斗村M29时间相仿而早于九女台M16,那所以M40的年代也应为战国早期。
二、东大杖子M47的出土器物及年代
M47位于东大杖子墓地的东部,位置也相对比较独立,与M40相隔15米左右。在整个墓地,M47墓葬规格仅次于M40,墓葬中也出土大量陶礼器。M47出土陶器的器物组合与M40相似,但较之M40多出了陶匜、陶尊两种器型。从出土器物的形制演变上看,M40在年代上应早于M47。且从陶器的陶系来看,M47出土的陶器均为泥制陶,我们已知燕国战国早期的陶器以夹砂灰陶为主,泥制陶次之,而到了战国中期乃至晚期,泥制灰陶开始超越夹砂灰陶成为主流,所以M47的年代应晚于战国早期。在M47墓葬中还出土两件陶方壶,方形壶盖,盖上有十瓣莲瓣式捉手,器身方唇、侈口、长颈、弧腹,方圈足外撇。颈部两侧各有两个对称圆孔,两侧各插一兽形立耳。整体形制与辛庄头M30Ⅱ式方壶类似,但M30Ⅱ式方壶较之M47出土方壶显得更为矮胖,M47方壶腹部重心偏上,所以M47方壶所处年代上应早于M30Ⅱ式方壶,辛头庄M30所处的年代为战国晚期,那么M47应早于战国晚期。M47出土的陶匜(M47:26),匜口较之怀柔城北Ⅰ式匜更接近于圆形,但又不似怀柔城北Ⅲ式匜那般近乎于圆形。底部无足平底,与怀柔城北Ⅲ式匜相似,流为半筒状长度也与怀柔城北Ⅰ式匜相当。郑军雷先生认为北京怀柔城北墓地中陶匜的演变序列应是Ⅱ式→Ⅰ式→Ⅲ式,那么东大杖子M47出土陶匜应为Ⅰ式匜向Ⅲ式匜过度时期的产物。M47出土陶鼎(M47:7),鼎深较浅,腹部较鼓,底部为平底,三足为蹄形足较为短粗,鼎耳近似于圆形耳,且紧贴鼎身。依照郑军雷先生对燕墓陶器演变规律的看法,M47出土的陶鼎从形制上看年代偏晚。整体来看,M47出土陶鼎近似圆形的鼎耳紧贴鼎身,鼎足短粗的特性与怀柔Ⅱ式鼎类似,但鼎耳竖直向上,不同于怀柔Ⅱ式鼎外斜向上的风格应早于怀柔Ⅱ式鼎。通过将M47出土的陶匜与陶鼎与怀柔城北同类器物的对比,结合郑军雷先生对战国燕墓的分期,M47的年代应于怀柔Ⅰ式匜组(M40、M50、M54、M64、M41)相近,而早于怀柔Ⅲ式匜组(M25)。郑军雷先生将怀柔Ⅰ式匜组划分为第四期,年代推定为战国中晚期。结合之前的推论,那么东大杖子M47的时代也应于此相近,为战国中晚期。
三、小结
自召公封蓟以来,燕国雄踞北方七百年,在继承西周文化的基础上又间接的吸收了当地商朝遗民以及张家园上层文化的某些因素。自东周以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与融合,燕文化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体。自战国早期开始燕国墓葬中仿铜陶礼器逐渐替代铜礼器成为墓葬随葬品的主流,在器型上也逐步形成了鼎、豆、壶、盘、匜为主的墓葬随葬品组合。东大杖子战国墓地紧邻燕国辖区,M40、M47墓葬中出土的仿铜陶礼器的组合和形制皆与燕文化中心区域的同类器物相似,尽管个别稍有不同也只是因为时间及地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总体来说M40与M47其文化的核心因素还是燕文化。这一点使得M40、M47与墓地中其他墓葬区别开来,墓地中多数墓葬尽管同样包含燕文化的因素,比如墓葬中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明显便是燕国器物,但当地土著文化也同样丰富,比如墓葬出土的东北系青铜曲刃剑、矮领垂腹式陶罐等等,全不似M40、M47这般燕文化完全占据主流。
我们知道燕国在此设立右北平郡之前,此地一直为东胡人所有,尽管如此依然有大批的燕国人由于国内战乱等原因迁移至此,他们接受东胡的管辖但依然保留自己独特的文化。也正是由于他们前期对东北地区的开发才使得后期燕国能在贤将秦开带领下一举击破东胡设置郡县。同时东胡在春秋战国时期占据着东北大部分地区,势力极为强悍,燕国在昭王之前,国小地窄,面对强大的东胡要获得安定,自然需要送有身份的人到这里“为质与胡”。以东大杖子M40与M47墓葬的规格以及丰富的燕文化元素,可以做出大胆的推断,M40与M47的墓主人或许应是战国时期燕国为了安抚北方,送到该地作为人质的燕国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