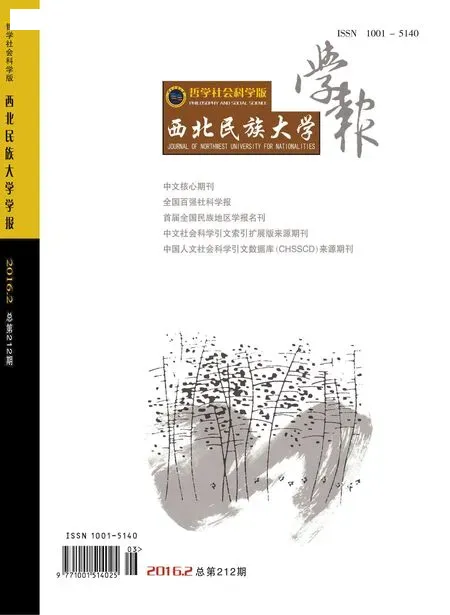苏童的“归路”与“迷途”——以《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2016-04-19杨国伟马玥玥
杨国伟,马玥玥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2.西南大学 附属中学,重庆 400715)
苏童的“归路”与“迷途”
——以《河岸》《黄雀记》为中心
杨国伟1,马玥玥2
(1.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2.西南大学 附属中学,重庆 400715)
[摘要]20世纪80年代末以降,苏童开始有意识地从先锋小说阵营中“撤退”,小说创作上主动承袭和回归到旧有文学中完整故事情节、相对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相对明确的主题意蕴等叙事方式上来,这些转型给苏童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但是,长篇《河岸》和《黄雀记》缺乏对造成历史悲剧元素的深度追问,直接导致其文本主旨意蕴上的漂浮不定,简约和平面化了的历史悲剧也难以给人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同时,叙述者几近毫无价值判断尺度的心理宣泄取代了文本故事的密度,也在削弱着小说文本的厚重感。而对自我文本故事的有意戏仿,又直接导致苏童众多文本故事的类型化和模式化。而造成这些方面的不足,主要原因在于苏童眷恋不舍的先锋叙事理念和创作资源的匮乏。
[关键词]苏童;创作转型;价值尺度;《河岸》;《黄雀记》
在当代中国文坛上,苏童的创作成就举世瞩目,以“先锋作家”进入文学史的方式,苏童始终以一位举足轻重的作家占居其中。不论是早期那些令人目不暇接的短篇,还是近几年不断努力的长篇创作,苏童始终显示出一位名作家兢兢业业和不断追求超越自我的野心。毫无疑问,这也是每一位作家不断提高和变换转型的职责与追求所在。苏童早期创作具有明显的先锋文学游戏化、符号化等特征,其中《一九三四年的逃亡》以“马原式”的先锋先验性,使苏童顺利获取加入先锋文学大军的珍贵门票。但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苏童有意识地避开先锋文学只求叙述艺术上的成就不问文本意旨的偏向,有意追溯“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的历史以及有意探寻造成历史与现实之悲剧的元素。由此,“回归”与“转型”成为学界阐释苏童文学创作的关键词之一,苏童作品的经典化道路也由此变得越来越宽敞和通畅,标志着国内最高文艺殊荣的两大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也向苏童抛去了橄榄枝。2010年,苏童的短篇小说《茨菰》荣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这是苏童的创作首次在国内得到的比较权威的肯定;2015年8月,苏童的长篇《黄雀记》成功获取代表国内最高文学成就的茅盾文学奖。这些殊荣均是苏童逐渐从先锋作家阵营中分离出来,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主动变革之后所取得的。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这样的事实:苏童的转型不仅给先锋文学出路提供了一个范例,同时也给他自己带来了荣耀(当然,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每一位有志气的作家并不以获奖作为此生之职志,包括苏童在内)。然而,众声喧哗之后,我们依旧有必要重估苏童的转型,尽量从多方面、多角度上重新发现苏童转型过后的价值尺度,毕竟文艺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从来都是一条曲曲折折的道路,只有经得起不同声音的考验,经典才成为可能。
一
长期以来,苏童以其出色的才情、温婉的情愫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发生在枫杨树乡和香椿树街上的故事。苏童几十年的努力和才华几乎人尽皆知,阅读苏童的作品,我们往往被那些带有浪漫气息的情调和那些带有诗歌艺术张力的语言所着迷。不得不承认苏童是语言修饰的能手,由此他的文风带给了我们与众不同的快感。不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阅读苏童的作品总能给人以飨宴般的感受。这是多年来我喜欢阅读苏童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在此方面,很显然苏童俘获了众多读者的芳心。然而,快感过后我们总是感到某种失落。因为,除了能从语言上找到快感之外,我们往往又感到苏童的作品总是缺少点什么。如果说苏童早期那些被冠之以先锋先验性的作品因其先验性本质而应该被理解,那么,被认为是苏童转型后创作的作品中依然给人这样的感觉就难以服众。
当前,学界主要从这些方面来推崇和赞赏苏童多年来回归和转型的努力。一是苏童的文学创作在叙事上主动承继了旧有文学有完整故事情节、有明确的文本旨意等叙事模式,苏童已经从先锋文学阵营中“谨慎的撤退”[1]。由此,苏童的创作风格得以合理的改变,这种撤退给苏童的文学创作开拓了一片新天地。二是苏童的创作经历了一个由“我”到“他”的叙事视角上的蜕变,这种转变是苏童“一次成功艺术的转换,与之相适应的苏童的风格由繁丰走向简洁、由峭丽走向平实,中国传统小说的‘白描’经其改变之后生成出新的光泽和气韵”[2]。另一方面学界则从苏童小说故事发生地层面上来理解,即苏童回归了香椿树街和枫杨树乡的故事叙述,但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而是要站在普世价值的意义高度上,去审视这两个故事源地,尽管苏童坚持认为“我从来没离开过”[3]这个地方。王宏图在《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一文中便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苏童的新作《黄雀记》可视为他在漫长的创作历程中经过诸多不无艰难的探索后一部回归性的作品,即回归到他初登文坛时大展身手的‘香椿树街’世界——它在苏童构筑的整个文学版图中与‘枫杨树乡’一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4]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从文学地域发生学上来简单地理解苏童的这种回归,正如苏童自己所说的:“我描绘勾勒的这条香椿树街,最终不是某个南方地域的版图,是生活的气象,更是人与世界的集体线条。我想象的这条街不仅仅是一条物理意义上的街道,它的化学意义是至高无上的。我固守香椿树街,因为我相信,只要努力,可以把整个世界整个人类搬到这条街上来。”[5]因此,不管苏童是“固守”还是“回归”香椿树街、枫杨树乡,其目的和意义都不是单一平面的,正如沈从文通过对湘西世界的书写来审视和建构民族文化以及湘西世界人性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通过书写马孔多来检视印第安文化一样。
的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主动回归后苏童的作品与早期先锋之作有着明显的变化和差别。鲜明的主题意蕴、饱满的人物形象以及旧有文学叙事方式的承袭,表明人们缠绕在苏童身上的荣耀并非浪得虚名,而是受之无愧。譬如,获得鲁奖的短篇《茨菰》体现出了苏童在先锋转型之后获得的出类拔萃成绩:作品含有深刻而丰富的主题意蕴,不仅对造成顾彩袖悲剧故事进行了深度的批判,同时也对所谓“热心人”进行伦理性的批判,由此体现了作者在先锋重叙述上的创作理念和创作经验上的极大转变;从叙述视角上讲,作家虽以“我”作为视角,但是叙述的却是“他者”的故事,而非“我”本身,“我”在文中只不过是故事的一个“观察者”,甚至是一个具有明显价值取向功能的隐含作者,这就明显与作家前期的作品拉开了距离;作品成功地塑造了顾彩袖这个角色,并通过这一人物形象,展现了顾庄与城里人的各种不同品质,这无疑是苏童告别先锋符号化人物的一个仪式;同时,作品还在城与乡的二元相较批判中丰富了文本的主题意蕴。
长篇小说创作方面,转型过后的苏童也显示出其过人的才识,在铺陈细腻、清风扑面的语言文字中铺展着他的文学世界。作品《米》对人性恶的赤裸裸的展现,《河岸》中对文革时代异化了人性的白描以及荣获第九届茅奖的《黄雀记》中对20世纪80年代末至新世纪之初各种荒诞事件的投影,让我们看到了苏童从先锋小说转变而来的成就。一是小说故事叙述不再是片段化的,形式主义已不再是其至高至上的目标,一个个具有连续而完整故事情节的文本,不仅增强了它的可读性,也在丰富着它的旨意。二是在典型环境中成功塑造了典型的人物形象,在五龙(《米》)、库东亮(《河岸》)、保润(《黄雀记》)等人物身上,我们既看到了其鲜明的人物个性特征,看到了赤裸裸的人性之善恶,也看到了人物对于自我悲剧命运的挣扎与抵拒。三是在某种程度上良好地处理了文学与历史、现实的关系,历史、现实捉弄着人物的命运。历史与现实的荒诞造成了故事、人物的悲剧,它们既是故事的重要元素,也是悲剧的重要背景。凡此种种,苏童成为一个游刃有余地徜徉于香椿树街或者枫杨树乡历史时空中的作家,他双手紧握密钥,一层一层地剖开其神秘的历史面纱。
苏童的这些主动转型和谨慎撤退,导致了学界在给其作品及本人进行文学史定位时,遇到了一个到底是先锋之作、先锋作家抑或是新历史小说、新历史小说家这样的难题,甚至是在先锋与新历史之间相互抬杠着。譬如,刘洪霞在《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一文中,经过梳理当代文学史上不同的苏童命名方式后指出,“在新历史小说的潮流中,苏童是很突出的一位作家”[6]。而叶砺华则认为“苏童后期的创作转型并不是割断同先锋文学的全部价值联系,他所弃绝的仅是先锋文学的外在形式,内在的意义蕴涵则不仅给予保留,而且得到了很大发展”[7]。从这两种近乎对立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在面对苏童及其创作上所遇到的尴尬选择。
但是,我们的文学批评不必也不应该拘泥于一个作家的流派属性,因为作家流派归属并不总是一定的,他们也许既属于这个文学流派,又属于另外一个文学流派,又或许同属于两个,甚至几个文学流派之中,一个既定的文学流派只是我们评介作家的暂时界定而已。因此,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避免文学史上遇到的这种尴尬。对于苏童而言,关注他转型之后其创作的价值尺度,或许比专注于流派归属这个泥泞中更为紧迫和重要。
二
无疑,诚如前述,苏童主动转型之后的成就是可喜的。然而,问题也随之而来,自由穿梭于香椿树街或者枫杨树乡历史时空中的苏童,其文本意旨、人物形象、文本叙事等构成文本的关键要素能给我们多少解读、推敲和阐释的可能?尤其在他的长篇中,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的拉长和加大是否就代表了叙事密度的增强?一言以蔽之,苏童转型后的作品,在整体上到底具有多大的价值尺度?在我看来,苏童的长篇并没有给人以气势如虹之感,像我这样阅读速度相对比较慢的读者,苏童的任何一部长篇都可以在3个小时之内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看完,但阅读感受很快如同水过鸭背般消失殆尽。当然苏童作品从来以灵气逼人、简洁顺畅的语言示人,这是我们能够快速阅读苏童作品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些小说自身存在的多种缺憾或许才是“很快忘记”的根源。
首先,在苏童的长篇小说中,缺乏对造成历史悲剧元素的深度追问往往直接导致文本主旨意蕴上的漂浮不定,简约和平面化了的历史悲剧也就难以给人心灵上的共鸣和震撼。《河岸》叙述的是在“文革”那个异化了人性的特殊年代里一个家族的历史浮沉。这显然是一个悲剧,一个从灵魂到身体都被历史所异化和摧残的历史与个体悲剧。这本来是一个作家可以恣意发挥的创作题材,然而,文本却在流离的历史时空中“迷失”。
一方面,文本缺乏对历史的叩问,而仅是在叙述欲望之中戏谑性地重复着历史现实的荒诞与生命个体的迷惘。散发式(开放式)的故事结局虽说是对历史不可知的一种言说方式,但某种程度上也导致文本意义指向的不确定性。本来,作为关联文本线性叙事的重要人物之一的英雄人物邓少香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形象,然而,作品中却忽略了邓少香身份调查的最后结果,因此,邓少香难以正名,这便直接导致读者对库文轩家族悲剧发生的合法性提供了质疑的可能。被下放到船上的库文轩,年轻时也是劣迹斑斑。应该承认,库文轩的悲剧是因为作为烈属地位被质疑而直接导致的,这里面存在值得人们同情和惋惜的一面,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又难以原谅他年轻时骄奢淫逸以及所犯下的种种桃色错误。库文轩的悲剧,既然存在特殊时代所致的一面,又有罪有应得的一面,这就形成一组并行相悖的紧张关系,它直接导致文本批判指向的不明朗,更削弱了文本对荒诞历史以及人性恶的批判的力度。在这个内在二元对立的人物形象上,我们似乎很难辨析整个文本是在批判时代的扭曲和荒唐,还是在惩罚一个犯下历史性错误的人物。
如果说库文轩被下放到船上之后所奉行的禁欲主义,甚至不惜挥刀自宫的行为是对他的应有惩戒,那么,他以同样的禁欲要求来监督库东亮又是否合理合法,一代人的过错,是否还需要下一代来持续他的救赎,这便产生了文本另一方面的缺失,个体命运到底应该由谁来掌握。如果说库文轩的悲剧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历史性过错以及历史不同权力运作和争斗的结果,那么,导致库东亮最后的悲剧又是什么,库东亮不被允许上岸的直接导火索是因为他偷偷运回被人们推倒了的纪念碑,但是,在此之前,他每次上岸时间的长短也都是在父亲的允许和控制之下的,那么,作为自由个体的库东亮,他的自由在哪里。文本最后让一个傻子扁金来对库东亮宣布此后不允许上岸活动,这是在讽刺权力中心意志的滑稽可笑?文本的戛然而止让我们难以乐观地预测,因为,只要邓少香的身份不能明了,那么这个问题就难以解决。但是,小说故事叙述恰恰在这个关节点上停止了。傻子扁金既然是一个傻子,他自己都难以代表自己,那就更难以代表一个荒诞时代的那种特殊权力,然而,被傻子宣布的“判决”却又被执行了。在这个文本中,苏童似乎在强迫着去运用自己并不太熟稔的讽刺手段,然而,所谓强扭的瓜不会甜,我们也只能静静地看完,不悲不喜,没有丝毫涟漪。虽说喜剧不一定必须要仰天大笑,而悲剧也不一定必须要痛哭流涕,但不悲不喜、不哭不闹、不痛不痒或许也是文本叙事效果中的最大缺憾。
然而,这种主题意蕴的游离状态在最新获得茅奖的长篇《黄雀记》中依然持续着。保润“捆”了仙女给自己带来了牢狱之灾,这其中有他过错的一面,也是两个家庭背后权力较量的悲剧性结果。问题在于,如果说《黄雀记》中保润熟稔的捆绑术象征着历史与荒唐是被权力意志所捆绑的话,那么,捆绑过后是什么?保润以“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方式,在婚礼当天杀死柳生,难道就是解开历史结绳的合法路径?退一万步讲,即便历史的悲剧是因保润“捆绑”仙女而引发,因此对保润牢狱惩罚是合理合法的,但是,对于柳生罪恶的惩罚和救赎,难道还要保润去完成,更何况保润的做法本身就是一种再次犯法。难道保润的10年冤狱还不足以救赎自己,可是,悲剧就那样发生了。保润最后还是杀掉柳生,从某种程度上,他复仇成功了,也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获取了解脱,但也因此走进一个无法原谅和自拔的漩涡之中沉沦了自己。而作为历史悲剧的真正肇事者,柳生从始至终都不曾忘记他那酒足饭饱思淫欲的思想,也不曾主动终止他那龌蹉的行径。在小说文本中,柳生的淫乱行径却不断被放大,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人之本性的难移,就算在去监狱探望保润归来的路上,柳生依旧带着爷爷要去按摩店嫖娼一番,在这种近乎暖昧、平和的叙述姿态中,对历史与悲剧的价值批判尺度被苏童有意无意地放逐。柳生最后被保润杀掉,又变成一桩难断的冤案。
同样的道理,文本对造成保润个人历史悲剧的白小姐(仙女)和对造成白小姐个人悲剧的庞老板的惩罚(批判)也是混乱不清的。对庞老板而言,如果强说小说有批判,那么,或许只能牵强地借助他那位双腿残废的老婆来完成。可是,那已是在认识白小姐之前的家庭实际。庞老板对白小姐造成的伤害,最后还是一毛不拔地就将之打发了,虽然柳生曾经帮助白小姐去寻找庞老板算账一番,可是,当看到那个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的庞太太的时候,白小姐放弃了那个念头。白小姐的弃权或许可以让她自己得到自我精神上的解救。然而,庞太太手中的那本赋予救赎象征意义的《圣经》,在作家闪烁其词的叙述中或许庞老板翻都没翻过吧!由此,文本对庞老板的惩戒又体现在哪里,庞老板玩弄白小姐的罪孽又该如何看待?而对于白小姐本身,虽然在文本的最后,象征着耻婴、怒婴的红脸婴儿的出生或许算是对她这一生因虚荣而不惜以身体为代价的生存方式的惩戒,但是,在众人的指责之后,她还是悄然地出走了,逃脱了,重获自由了。因此,不管是救赎,抑或是惩罚之于白小姐,文本都是以一副失败的面孔示人。可是,谁来给保润自由,如果说,历史是荒唐的,那么,谁来反思这段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种种冤孽。由此,阅读苏童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往往给人以一种在一个悲剧性的社会空间中众人皆醉之感。
其次,在叙述上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虽得到拉长与扩充,但故事密度并没有得到相应增强,这就削弱了小说文本的厚重感。在苏童的长篇中,一方面为了填充那绵延的历史时间长度,叙述者往往通过叙事人物那不伦不类的议论、抒情等心理宣泄来完成。《河岸》中时常由库文轩旁白出来的那些悲愤情怀,既不能推动文本故事的发展,也不是叙述者或者批判或者颂扬立场的侧面说辞,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叙述者叙述欲望的体现,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就像是叙述者游戏性的心理喷发而已。从叙事时间角度上看,《河岸》与《黄雀记》都将故事时间放置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间之中,但是,时序上的模糊使得小说在叙述历史故事的过程中出现文本现实生活同历史现实生活错位的现象。譬如在《黄雀记》中,显然文本是将故事时间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至新旧世纪之交这一时段中,然而,许多极具现代的东西(例如手机),在这个作为逍遥法外的香椿树街小商贩柳生那里早已不足为奇,这就应该值得怀疑。当然,文学并不等同于历史,而故事时间并不一定严格地等于文本时间,文本时间也并不一定要完全遵循故事时间,但问题在于,如果文本故事前后既定的时间秩序和历史生活实况明显出现差错,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违背了这个既定时间中的故事秩序和逻辑。或许苏童是想以蒙太奇的手法取胜,但是,蒙太奇也并不等同于混淆既定的故事时间中的故事秩序。在文本叙事过程中,苏童为了避免这样的叙事尴尬而使用了一套模糊的叙事时间,然而,这或许正是苏童对那个“世界的非理性的认同”[8]。
另一方面,或许由于作家着意写的是一部长篇之作,而叙事时间又过于绵延,为此,作家就不得不制造出一些故事来。可是,这些故事与整个文本的悲剧性往往又没有太大的关联。《黄雀记》中小说开头那被苏童淋漓尽致书写的关于爷爷照相癖好的故事,乃至爷爷为了找回家族那个装有祖先尸骨的手电筒而闹得整个香椿树街满城风雨,大家都在挖街掘地寻找的闹剧,事实上与整个小说文本悲剧起源和叙事动力并没有什么关系,它更像是苏童为了长篇之作硬生生地拼贴上去的一些生活碎片而已,使得文本显得不伦不类。甚至,在关于白小姐与庞老板的故事中,由于混乱、模糊的时间意识,使得整个故事变得虚无缥缈。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白小姐当初是坐着飞机去找台商庞老板的,并且因为庞老板害怕被老婆发现,才不敢带白小姐到自己别墅而住进酒店的,可是到后来柳生陪同白小姐去找庞老板“算账”的时候,文本瞬间便转了一个360度的弯,似乎庞老板在香椿树街上也还有一套别墅了。可见,小说在细节书写并没有做到成功处理,一切均是在模糊的、非理性的状态之下进行的。
如果说,象征意义是文本的一个重要体现,那么,它的象征至少应该指向文本最后的旨意。然而,在《黄雀记》中,保润的捆绑术之于文本的象征意义并没有发挥出来。可以说,它甚至是叙事者玩弄叙事的一个手段而已。保润的捆绑术在小说叙事中出现的频率极高,然而,不管是民主结,还是法制结,抑或是其他的什么结,小说都不能更好地指向那个保润悲剧性的结果。因此,被保润所熟稔的“绳结”叙事,也就显得累赘和多余。换句话说,整个小说如果我们大胆地抽掉关于爷爷的闹剧以及保润的捆绑术,似乎对文本故事的完整性,乃至文本的终极关怀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不论是《河岸》,还是《黄雀记》,苏童都将叙事空间置于一个宏大的历史社会空间之中,然而,这些具有悲剧性的社会空间中,苏童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多重想象的可能。因为,在空间叙事过程中,被叙事人物(如《河岸》中的“我”,《黄雀记》中的保润、柳生、白小姐)那些喋喋不休的心理宣泄占据了整个空间,而社会空间的悲剧众生相却总是一闪而过。在《河岸》中,当船民们带着被母亲遗弃的慧仙到岸上去找赵春堂书记的时候,叙述者随意地以库东亮的心理独白替代了“岸上”这个悲剧社会的丑陋面相。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作为一组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的“河”与“岸”,小说的处理也是简单而草率的。库文轩最后背上纪念碑投河自尽,看似一个悲壮的举动——只有河水,方可洗涤这个黑暗的社会现实。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河面上船民们的生活也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想,河水也不曾洗涤过他们,慧仙初到船上的时候,各家各户的算计依然鲜活地存在着,而童养媳这一封建陋习在船民们那里也是根深蒂固的。因此,不管是河面上,还是在岸上,都是一个混乱不清的现实,也就难以形成相互比照的艺术效果。
第三,对自我文本故事的有意戏仿或许也是苏童这些年小说创作致命的弱点之一,因为它直接导致了文本故事的类型化和模式化。《黄雀记》中直接导致保润和柳生的悲剧源于一桩强奸案,而《河岸》中库文轩的悲剧根源中也有他年轻时的风流史,两个不同的文本,一个似曾相识的悲剧导火索,这难道仅仅是纯属巧合而已。同样,《茨菰》中直接引发革命者顾彩袖出逃的是她那被家人订下的婚事,而《河岸》中慧仙的决意逃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她那无意间意识到的看似收养的“童养媳”的身份。凡此种种,苏童多年来转型创作虽成绩斐然,但其中之不足也是难以掩盖和无视的。
三
先锋文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风靡期之后,在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之间,逐渐走上了回归之路。旧有文学的叙事传统刺激着先锋作家走向回归的道路,对小说技艺的把玩不再是先锋作家钟情的东西。余华、苏童等先锋作家纷纷调转了创作方向。然而,正如现在我们看到的,努力与愿景之间依旧存在遥远的距离,是什么让先锋文学的转型如此艰难,是什么让苏童的创作走上“迷途”,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
首先,马克思哲学告诉我们,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只是事物发展的条件。从这个层面上看,苏童念兹在兹的先锋叙事理念或许才是根本原因。早在2003年的时候,苏童就曾经说过:“在二十年的写作实践之后,我渐渐有一个深切的体验,没有一种写作姿态天生是先进的,没有一种事前确立的写作姿态可以确立作品的写作高度和写作质量,至于说到先锋立场,我对它的态度似乎越来越暧昧了。我很矛盾,一方面我赞赏所有的独特的反世俗的写作。另一方面我又觉得预设的‘先锋’姿态是有害的,它像一种病毒一样会损害一个健康自然的作品的生理组织——如果一个作品有生理组织的话。我理解‘先锋’更多地把其理解为一种写作姿态,如果说文学场是个竞技场,先锋大概是个跑姿特别、步伐节奏与他人不同的选手,他必将是引人注目的,但问题也将随之而来,他跑得快吗,他的成绩好吗?谁也没法确定。这时候我当然也茫然失措。于是我想先锋不先锋也许是不重要的,好比万河奔流入大海,问题不在于你是一条什么颜色什么流向的河流,而在于你是一条河流还是一条小溪还是一方池塘,问题在于你是否已经让自己像一条河一样奔流起来。”[9]在这里,我们不难发现苏童创作姿态上的迷茫与困惑,苏童既然发现先锋立场的“有害”之处,却又坚持暧昧的态度,因此,苏童的创作情感依附本身就不明晰。虽然,作家的创作行为不可能在一套公式之下进行,但是,也不代表仅以先锋的“写作姿态”,在一个失却的价值判断尺度下完成。

其次,改革开放以降,伴随着经济和文化全球化的急遽推进,文化的多样化与多元化形成了多元价值取向。在某种程度上,多元文化价值固然给我们带来相对广阔而自由的价值判断空间,但是,过分依赖多元又容易流于“无元”的价值判断状态。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每个人都有质疑和获取答案的权利,然而雾霭却总是遮蔽着即将到来的那一米阳光。于是,在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状态之中,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价值趋向都将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挑战。由此,一种各打五十大板的“江湖”批判意识便在苏童的创作观念中形成并付诸实践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看,历史的不可知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也是当代作家创作过程中所面临的极大精神困扰之一。对人性,人的价值和自由,人的生存和发展,人之过去、现在与未来如何存在等关于人类本质的文学精神资源的空前匮乏和无意观照,也在左右着当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过程,苏童只是其中之一。于是,一切都成为库东亮心中时常念叨着的“空屁”而已。既然一切历史均是虚无的,在一个虚无主义泛滥的语境下,库东亮的屁股上不可能再现具有甄别烈属意义的鱼尾纹,“空屁”自然地成为苏童《河岸》悲剧发生的导火索,而悲剧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和难以避免的。
此外,苏童的自我身份焦虑在这个消费时代和众媒体时代中并没有因为主动转型而得到缓解,反而被不断扩大化。“获得茅盾文学奖,我很高兴。一方面,我盼望得奖,另一方面,我考虑更多的是自己今后的路应该怎样走,应该选择怎样的创作方式,这个问题比得奖之后的高兴更重要”[12]。“盼望得奖”,不仅是作家盼望得到主流意识的肯定,某种程度上也是作家对“得奖”目标的某种期盼和奋斗方向,这是当代作家与现代作家最大的精神区别与写作困恼。在现代作家彼岸,稿酬制度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沉思等刺激着他们的持续创作;而在当代作家此岸,稿酬之外还添加了许多奖项等主流价值的评判,似乎唯有获奖才能证明自己的存在感,这是当代作家的荣耀,也是当代作家的精神牢笼,苏童或许还不能免俗。
平心而论,时至今日,我依然坚信苏童早年与周新民的对话中所说的“我只喜欢自己短篇小说,我的中长篇小说,完全满意的没有”[13]这句话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尽管多年来苏童的长篇努力成就了与众不同的审美风,给我们带来不同凡响的审美感受。
参考文献:
[1]陈晓明.表意的焦虑[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96.
[2]王干.苏童意象[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1).
[3]苏童.我写《黄雀记》[J].鸭绿江(上半月版),2014,(4).
[4][5]王宏图.转型后的回归——从《黄雀记》想起的[J].南方文坛,2013,(6).
[6]刘洪霞.文学史对苏童的不同命名[J].文艺争鸣,2007,(4).
[7]叶砺华.新潮的洄流——评苏童的创作转型及其价值意义[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2,(3).
[8]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86.
[9]苏童.关于写作姿态的感想[J].时代文学,2003,(1).
[10]苏童.苏童创作自述[J].小说评论,2004,(2).
[11]苏童,张学昕.回忆·想象·叙述·写作的发生[J].当代作家评论,2005,(6).
[12]刘颋,刘秀娟.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感言[N].文艺报,2015-08-17.
[13]周新民,苏童.打开人性的皱折——苏童访谈录[J].小说评论,2004,(2).
(责任编辑李晓丽责任校对李晓丽)
[中图分类号]I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40(2016)02-0152-07
[作者简介]杨国伟(1984—),男(壮族),广西德保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马玥玥(1985—),女(土家族),重庆石柱人,西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少数民族视野下的沈从文、老舍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3YJC751061)
[收稿日期]2015-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