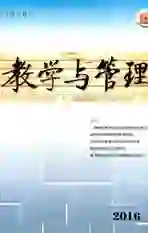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虚拟情境的优化
2016-04-18杨亚凡
杨亚凡
摘要虚拟情境具有针对性、可控性、游戏性的特点,发挥着独特的教育优势。但在实践中由于“虚拟性”与“生活性”的二元结构、青少年学生在情境中的“旁观者”的心理距离、对情境中教师权威的误读,因而降低了虚拟情境教育的时效性。应从道德教育情境的“生活化”、丰富青少年学生德育中虚拟情境的教育内涵、重构虚拟情境中的教师权威、保持虚拟情境的“双面性”和“时鲜性”来探讨虚拟情境的优化,这对当代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兼具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青少年学生 道德教育 虚拟情境 优化
情境是“从认知的角度说明行为者与环境、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1]。情境资源可以将青少年学生引入并亲身体验某种特定情境,让其受到情境的暗示和感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接受、认同并内化情境资源所隐含的教育信息以及特定的价值观念,最终激发青少年学生的正确道德行为。虚拟情境是“人们根据事先预想,为了实现某种意图或目标而人为创设的一种场景”[2]。一般来讲,学校教育比较重视创设某种特定情境,即虚拟情境。虚拟情境由于具有假想性、封闭性、人为性、间接性以及体验效果的短暂性,在实践中常常会出现青少年学生道德信念不持久、知行脱节等状况,从而引发虚拟情境“不能引发真实的道德冲突,并导致真实的道德行为”[3]的微词。学校有意识地创设的典型环境,在激发其学习兴趣、教育的可控性、教育资源的节约等方面是其他教育方式难以取代的,从此意义上讲,在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实践中有其长期存在的必要性和客观性。但是如果在操作环节中要趋利避害,实现对虚拟情境的优化,达到提高教育效果的目的,就必须对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中的虚拟情境于德育的独特意义、运用“失当”的原因进行剖析,进而引导虚拟情境优势的发挥。
一、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虚拟情境的教育意义
1.虚拟情境的针对性
虚拟情境创设应满足两个条件:其一是存在某种目的和需要;其二经过人为的创设和优化。这两个条件蕴藏着情境中教育者的意识、价值观。在教育者的既定目标下,对特定的环境、地点、人物、事件的组织,以及对道德虚拟场景中要求青少年学生做出的分析、判断、选择、行为都贯穿着特定的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环境中虚拟情境的创设会把青少年学生的认知结构、感情需求、原有的知识、技能、学习动机、态度以及年龄、心理特征等纳入情境因素,情节设定时也是有意识地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场景作为情境教育的素材与背景,通过情境体验和虚拟经历,激发青少年学生对教育者设定的教育主题的关注与兴趣,实现从注意力的吸引到情感的共鸣再到反思中的感悟,最后到既定的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
2.虚拟情境的可控性
虚拟情境是由教育者根据教育目标、对象、内容而创设的微观、封闭的环境,具有明显的人为调控性特点。教育目标规定了情境设置时不论是人物设计还是环境、场地的选择,实践的情节发展、促成青少年道德认知和道德行为的事件分析,问题设置都要围绕目标设定,都要有明晰的教育意识或者特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念。在这样的体系中,如果青少年学生背离教育者设定的既定观念和价值观时,都会通过情境中的舆论压力、争辩讨论或是教师的引导和正面结论来得到及时的纠正。另一方面,虚拟情境教学一个较为明显的优势就是改变传统道德教育中教师的灌输式教育,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利用情境中的各组合要素激起他们的强烈情绪和情感共鸣,进而形成一种心理倾向,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态度、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产生影响,在人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中,把整个虚拟情境的操作纳入教育者的可控和主导的状态。
3.虚拟情境的“游戏”性
虚拟,顾名思义是没有真实发生的,在情境的设置上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余地。虚拟情境给青少年学生提供了一个体验空间和可能性。情境参与或是角色扮演都让青少年学生有一种置身于“游戏”中的感觉,他们会比关注课本更加关注事件本身及背后的暗示性信息,因为“所谓有效的学习,就是知识的获得是从事有目的的活动的结果,而不是应付学校功课的结果”[4]。虚拟情境的角色扮演游戏符合青少年学生好奇的心理特点。在“有我之境”中,才能最快地了解角色在情境中的地位及与其他角色的关系,“教材中原有的逻辑的、抽象的符号化了的内容,一下子变得那样生动、形象、真切”[5]。青少年学生可以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进行学习,体验新颖、有趣的材料、内容、角色,进入角色,体验角色,评价角色的心理轨迹和内心矛盾,进而产生对角色的知觉和情感共鸣,收到照本宣科无法企及的教育效果。
二、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虚拟情境的运用“失当”
只有对虚拟情境设置中的弱化因素进行分析,才能充分释放虚拟情境对青少年学生道德的教育功能,促进青少年学生道德的知行合一。
1.虚拟情境的“虚拟性”与“生活性”的二元结构
学校长期的道德教育实践多数是在学校范围内完成的,哪怕有课堂外的社会实践,也都是在既定的、缺乏变化的实践场地开展,青少年学生容易对虚拟情境产生“不真实”的感知。从心理暗示角度讲,由于虚拟环境是教育者按照教育目的设计的道德模拟场景,青少年学生在其中是一个扮演者或演示者,“这种虚拟情境具有‘游戏的’或‘戏剧的’性质,情境中的所有人都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2],他们在情境中的道德认知和道德判断及道德选择都是按照教育者规定的“常理”去完成,只有这样,他们才不会在情境中遭到舆论的压力,并获得教师的赞许。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境容易使教科书处于失语状态。同时,大多虚拟情境的设置过于理性化反而与青少年的生活渐行渐远,加上情境设置程序化导致的话语失真,其结果就是青少年学生道德学习的虚拟情境与真正的生活产生了鸿沟,形成各自独立的二元体系,道德教育的效果遭到消解。
2.虚拟情境中“旁观者”角色的心理距离
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中,虚拟情境作为一种间接的道德学习方式,大多属于“旁观者”情境。旁观者情境中,青少年学生作为局外人处于事态之外,与事件的发生、进展以及结果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青少年学生会产生“道德行为与我无关”、“不用对道德活动负直接责任”的心态,他们有很大可能表现出与作为当事人情境中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情绪反应和行为模式,这就容易产生一种与教育者设计教育情境时要实现的教育目标截然不同的后果。即使设计得再逼真的情境,青少年学生在其中都会以一种旁观者的心理角色保持心理距离,在产生对道德情境知觉、移情后,直接跳过道德判断、责任意识判断,切换到行为模式的选择,最终导出道德行为。在这样的心理过程中,青少年学生明白不用去考虑道德行为的代价和后果,出于对教师权威、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要做出符合“道德常理”、让教师满意的行为即可,从而错过了道德学习的内化阶段,导致他们人性的弱化、责任的匮乏、道德关怀的缺失。
3.虚拟情境中教师权威的误用
虚拟情境教育中,教师被社会、学校赋予了威权,在这种威权下,“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形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都是我们所必需的,而不管社会组织以及生产和产品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是怎样的”[6]。但是,传统意义的教师权威无论从意义、地位、内涵和价值上讲都存在着嬗变的需要。在多数虚拟情境的青少年学生道德教育中,常常会因为对教师权威的误读而产生一些实践中的困惑:其一,对教师个人权威与教师权威的混淆。青少年学生往往容易把教师群体中的个体教师看成是道德知识的“上位者”、道德规则的来源和道德“完人”、“圣人”,个体教师的道德判断标准就会成为学生的判断标准,教师认为“善”的就是“善”的,教师对青少年学生个体的评判就成为代表道德权威的道德评判。青少年个体会在虚拟情境中表现出功利主义,即“在潜在的外力驱使或环境暗示下,压制自己的言说本意,说一些套话、空话”[7],从而失去了对道德的选择、判断和个人动机的产生。其二,教师权威与形式权威的混用。形式权威是国家、社会赋予教师对学生施行管控的一种强制力,教师给出的道德判断、道德规范的权威性是不容质疑的,学生的道德逆反行为被看作是青少年学生对教师威严的挑战,师生关系演变成为命令与服从、教授与接受的关系,违背了其道德养成规律,反而催生了青少年学生的叛逆和逆反心理,在对教师形式权威的畏惧下,做出不是其自身的信仰所驱动的道德行为。
三、青少年道德教育虚拟情境的优化
作为一种人类学习的间接方式,虚拟情境可以为青少年学习者在未来类似情境下的行为反应提供线索。青少年学生身处其中,可以试图通过角色假设和转化来对道德活动进行观察、体验,在教师的诱导下积累道德生活经验,进而提炼、内化为自己的理解。因此,须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虚拟情境进行优化。
1.道德教育情境的“生活化”
在虚拟情境创设时,首先要保持人性化的情境设置理念,“生活过程本该以一种自然且自由的方式展开”,须扭转“把生活过程制度化了,由此在总体上破坏了生活过程”[8]的认识。善于在情境中将青少年学生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产生关联性,并在对道德生活的反思、追求中培养“特立独行、清醒从容、有所执着、敢于担待、‘立于天地之间’的道德人格”[9];其次,就是赋予虚拟情境以生活化的特征,即情境构建须源于生活、反映生活。当然,生活化的虚拟情境不等同于要将情境要素变成一堆关于生活琐碎的大拼盘。这里的“生活”应是经过教育者规划、提炼并上升为理性的生活。因此技术上要避免德育情境在走向生活的过程中滑向随意化、庸俗化和形式化。将虚拟情境生活化的终极意义在于在生活化的情境中青少年个体自觉的道德情感的唤醒、内在价值的选择,否则,只会让虚拟情境教育在“回归生活”中背离教育初衷。
2.丰富青少年学生德育中虚拟情境的教育内涵
青少年学生是改造自身的主体,每个主体都有自己的思想、感情,不是单纯的知识接收器。虚拟情境的创设最终是要促使青少年个体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须尊重青少年学生的主体性精神、地位、人格和主体权利,青少年个体是有个性、有批判、有情感的健全人,不应在程式化的情境设置中剥夺他们对道德现象、道德规范做出独立的思考、解读的权利,要促使情境创设中隐含的道德知识、道德信息、价值观念入耳入心,成为促进道德行为的内化力。
3.教师权威在教育情境中的重构
青少年学生虚拟情境道德教育中不能没有权威,以至于其失去对权威的信仰和敬畏,其一,要转变虚拟情境下的传统教师角色,教师在虚拟情境下的道德教育不是强制力;教师不应只是道德知识的“上位者”和道德准则的制定者,还应该是虚拟情境中青少年学生学习的组织者、管理者、合作者;在教育语言上,少用“你必须”、“你要”等指令模式,应给予青少年学生思考、质疑、批判的空间;教师还应“勤修师德以身立教”,通过教师自身的道德权威、行为、师德魅力让青少年学生产生对权威的尊重,触动其心灵。
4.保持虚拟情境的“双面性”和“时鲜性”
作为具有一般性的道德法则和规范,道德原则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但是当一般性的道德原则遭遇到具体的情境时,就会出现不同的道德行为。我国深刻的社会转型催生了形形色色的道德现象和多元价值观,青少年学生通过学校、家庭、社交圈的现实道德生活创设虚拟情境时,教育者却对林林总总的社会道德现象加以删减、加工、编辑,让青少年学生对虚拟情境中的教育理念难以产生认同感。因此,创设教育情境时,要坚持“正面”和“负面”相结合的原则,既向青少年学生呈现正统、正面的道德规范,也要敢于呈现负面情境;要摈弃那些脱离社会实际的内容,用青少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社会普遍关注和热议的道德内容纳入虚拟情境构思中,保持情境内容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以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参考文献
[1]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
[2] 沈嘉祺.情境与道德教育[J].全球教育展望,2006(6).
[3] 傅维利.真实的道德冲突与学生的道德成长[J].教育研究,2005(3).
[4] 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5] 李吉林.为全面提高儿童素质探索一条有效途径—从情境教学到情境教育的探索与思考(下)[J].教育研究,1997(4).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 沈又红.话语失真:走向理性批判的门槛—兼论教育学话语失真极其改造[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5(5).
[8] 克里夫·贝克.优化学校教育—一种价值的观点[M].戚万学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吴宇戈.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的当代价值及途径探析[J].社科纵横,2007(8).
【责任编辑 杨 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