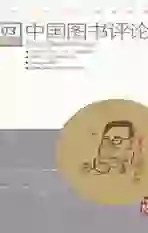“漂来”:孙健敏小说里的主体让渡与文化翻译
2016-04-15李晖
李晖
【导读】它们挪借现有的翻译名称,或再现历史场景,并模拟历史上的翻译行为,是为了凸显文化差异和不适,并对以“翻译”为象征的资本全球化时代“等值交换”模式的质疑。它起到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尼兰雅娜推崇的“异质前景化”翻译(foregroundingof heterogeneity)。所谓异质前景化翻译,是借助于自然和不自然、熟悉与陌生化相掺杂的译入语,将殖民时期语词的单一、通顺、固定的文化意义进行多样化。这是以本土多元文化为中心,对单向输入、西方文化价值主导式翻译的一种逆向解构。
“时代忧患”,是孙健敏“漂来”系列小说里的一个中心主题。从他的《消散之地》,到2015年新作《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这个主题不仅形成了持续清晰的发展,而且还借助于进一步复杂化的叙事技巧和文化翻译策略,实现了全面深入的内向观照。
读者只需稍加留意,就会意识到故事里的“漂来城”,实际上影射了现代资本全球扩张、殖民化时代的上海。这个虚拟的地名,不仅在意象上接近真实世界里的对应本名,而且更确切地象征了以海上贸易为基础、以外来强势文化为主导、以资本增殖为主旋律的畸形现代化进程。伴随这一进程的,是一个民族和众多个体的屈辱、希望、挣扎、奋进与幻灭。“漂来”一词,让人充分体会到由远及近、由外向内的变化潮流趋势,以及动荡不安的隐忧。
在《消散之地》的平行叙事里,处于庸碌生存状态的八卦杂志记者“我”,对身边灵异现象的不安,与真正的小说主人公唐喻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风潮中的民族忧患感,形成了两种时代精神的鲜明反讽。随着两条叙事线索的平行发展、呼应与衔接,在灵异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也逐步显现:百年前曾经隆重登场的一场时代大戏,在衰朽政治的权力博弈中戛然而止,最终沉沦隐没于都市商业住宅的地基下。不同时代、文化背景和社会阶层的人物命运,交织出奇妙的因缘际会,揭示了庸常生活覆盖的深层历史结构,提醒着遗忘与记忆之间微妙而无法断舍的关联。然而,到了《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里(以下简称《七个夜晚》),这种时代精神和民族意识的表述,却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被动展开、人物主体性(subjectivity)的不断迁移和转换,以及叙述视角的复杂多元化,变得暧昧模糊。曾经蓬勃生发出忧患情怀、民族责任感与技术探索精神的主体意识,变成了作品的焦虑和审视对象。“时代忧患”,竟然转化为引发忧患的原因本身。小说里的反派角色高桥说过一句极其犬儒的话:“你的革命就是一场催眠。”(孙健敏,2015:25)这句话既概括了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幻灭状态,也折射出幻灭者对于时代忧患的意义隐忧。
然而,《七个夜晚》正是凭借着人物主体身份的分裂迁移,以及认知眼光的游移不定,最终升华成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自我反思。作者试图通过叙事而努力拨开历史虚无感的迷雾遮蔽,并切入历史的内核,来勾勒出个人存在与意识的底构纹理。如果说《消散之地》是从特定文化和历史意识的角度,对胎死腹中的“中国现代化”进行的具体想象与表现,那么《七个夜晚》则围绕着现代主义者的哲学关注层面,尤其是对主体统一性(integrityofsubjectivity)的关注,而展开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彰显出作者身处的后现代社会的思维感知特征。
这些思维感知特征,在小说里主要有两方面的体现:一是主体的意识碎片化、记忆缀段性和身份异化感;二是人物角色和时空关系的交错混淆。尤其是小说里几个关键人物的主体身份,在叙事过程中被未知的外部力量连续让渡。再加上诸多事件之间因果链条的裂隙,就使得他们自我意识的统一整合被不断地阻隔延宕。作品的叙事任务,作者对主体意识和历史本质的反思,则在这一系列的主体让渡与裂变过程中铺展开来。从语言特色手段上看,作者巧妙采用的文化翻译策略,对于整体叙事的建构,起到了关键的辅助作用。
《七个夜晚》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第二部分虽然各自命名为“时间:梦”和“时间:现实”,但实际上是按照1912年至1937年的顺序记述。这是现代主义的全盛阶段,也是中西方两种不同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碰撞冲突的年代。第三部分的时间被命名为“不存在”,意味着叙事时间的随机跳跃和空间化过程。实际上主要涵盖了1937年至1945年二战结束,其中还零星穿插了1972年中美建交和1898年漂来城开埠时期的记述。小说总体的时间范围,是现代主义的全盛和衰败结束时期。作者从中敏锐地捕捉到“主体统一性”这个现代主义话题,并展开了独特的思考和表现。回溯一下现代主义思想史,就可以看到:主体的自主统一性,在康德之前尚未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尖锐问题。然而从施莱格尔强调“美”与道德和真理的分离、艺术感知的时间性(temporality),再到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自主统一的主体观念日益遭到质疑。人们开始认识到:主体之外的“关系与变化”,往往是“以超出主体掌控的模式而运作”,继而影响到主体自身属性的界定,以及主体在应对这些“关系与变化”时的模式。主体在应对过程中,往往可能“屈服于他者,并丧失身份。”(Bowie,2003:64—65)这就像纵横叱咤于黑道的传奇人物卢阿大在临死前看到的:“所谓江湖老大,只是一系列行为处事的习俗,被他们控制的人也控制着他们,决定他们是谁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身边那些唯命是从的下属、保镖和仆佣。”(孙健敏,2015:266)
小说里反复出现的主体分裂与让渡,始终遵循着一个魔幻化、表象化的基本模式:随着情节推移和场景跳转,某个人物被相继赋予不同的躯体、身份和姓名,并且拥有自己也并不完全知情的历史过往。然而他们在当下必须要做出个人选择,并且展开新一轮的行动。例如,主人公在出场时还是白皮肤的“孔菲斯·洛克菲勒”;在第一章结束后,就成了另一个捷克裔建筑设计师季泽克;后来又变成了黄种人面孔、五官酷肖孔菲斯的“孔亦丘”(绰号“阿菲斯”)。全书的三部分共分七章,对应着标题里的“七个夜晚”。每一章分为若干小节,在叙事手法上的总体模式是:外部叙述者轮番切换进入角色内心,并以单一视角展开叙述。值得注意的是,主人公在经历了身份转换后,作者仍然使用“孔菲斯”的统一名称,来标注孔菲斯、季泽克和孔亦丘的不同视角下展开的叙述章节。这不仅是为了阅读的方便,更表明了小说外部叙述者的假设前提:人物可以在“梦”“真实”和“不存在”的差异时空里拥有不同身份,却仍是名义上的统一主体。女主人公“莉莉”的七次出现,分别是以莉莉、芳芳、小雪、娜娜等不同角色身份。她们都是老鸨罗夫人豢养的风尘女子,并且在开篇时曾经同时出现过。她们被确定为同一主体,是因为孔菲斯-季泽克-孔亦丘能够看到她们脖颈上“藤蔓一样的发根”。也就是说,当孔菲斯们在自己的残留记忆里获取身份认证,并形成判断后,她们的主体性就立刻转化为“莉莉”。至于“莉莉”的镜像人物“莲生”,则没有这样的特征。莲生在去世后仍然以影子的形式而存在,因为她的主体本质,即是莉莉的影像。另一个比较奇妙的主体分裂与转换,发生在昔日京剧名角汪德龄的身上。她在一夜之间毫无征兆地完成性别转换,从而“唤醒”了身体里沉睡的男人,并成为一名不妥协的革命者。但她/他却只能通过《夜舞》这本八卦杂志来了解自己作为男子的过往,而杂志里的记叙与她/他自己的记忆则完全不符。“他不知这是否就是唐先生所说的历史,没有真相,只有各种意外和传说。”(孙健敏,2015:112—113)他和昔日恋人蒋桂芳各自重新喜爱并准备迎娶的两个女人,其实是彼此的镜像。他们拟定共同举办的婚礼,原本可以成为主体分裂变异后再次聚合的象征。然而,这场婚礼最后却演变成了一场象征着完全决裂的血腥屠杀。这种镜像对应模式,后来又衍生出抗战时期组织暗杀的芳芳和玲玲。这些情节无疑是对“四·一二”大屠杀、“宁汉合流”、汪伪统治和地下抗日等历史事件的密集影射,但作者将它们变成了带有诡异气息的“历史”,和主体分裂异化的寓言。这种主体身份的分裂让渡,在小说的第三部分更是达到了极其繁复和暧昧不明的程度。在故事临近结尾处,莲生的影子对孔菲斯说:“莉莉是不是莲生,不取决于莲生,而取决于你。”(孙健敏,2015:296)但孔菲斯在这一次已经无法判断,只好将问题悬置。而“悬置”,则是小说结尾处着重表现的主题。它也是作者在故事里对主体分裂问题而给予的最终回应。
这些名义上归属于同一主体的单独角色,各自都拥有确定的身份属性。随着同一主体在不同情节里的身份改变、视角切换和意识叠加,读者渐渐会对这种貌似不言而喻、其实只是小说外部叙述者假定的主体“同一性”产生质疑。其实作者(有别于小说的外部叙述者)在小说开头,就已经通过时间的错置而留下了伏笔:“他觉得第一次到漂来,应该是在1912年。他其实是1925年被人从法国瑟堡港送上船的。”小说的第一、第二章,等于是从1912年一直“追述”到1919年。第三章的开头,当“他”再次以孔菲斯的身份到漂来的时候,是“1927年7月3日,也是他第一次在真实中到达漂来”(孙健敏,2015:2,94)。然而第三章的结束方式,居然还是与前两章雷同:主人公在昏然欲睡的状态下进入下一个梦境,也就是下一个时空。可见所谓的“真实”,只是外部叙述者的描述。它和角色的个人意识及记忆一样,从本质上说并不完全可靠。由于整体叙事的启动,是以故事开篇错置的时间链条开始,随后的叙述内容,也都包含在外部叙述者从这个时间点进入的可能世界。一旦这个模拟全知的外部叙述者在时空意识上出现谬误,那么他所叙述的可能世界,从一开始就只能是幻觉。孔菲斯在“梦”时间的第二章变成了季泽克。这个季泽克在第二部分的“现实”时间里继续存在,从而裂变为另一个独立角色。他与孔菲斯有几次相逢的机会,但却从未真正照面。在第三部分的“不存在”时间里,犹太富商埃利斯的玛丽莲别墅,名义上是季泽克在主持设计,实际上却是孔亦丘的作品。在新一轮的内战开始前,孔亦丘拿到埃利斯给他办的美国护照,身份又变成了“孔菲斯·洛克菲勒”。作者在此留下的暗示可能是:孔菲斯可以不断地接受身份让渡,但他如果在某一特定时空与自己的不同分身相遇,就会造成时序统一的因果世界的坍塌。这意味着,小说外部叙述者假定的主体统一性,始终存在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同一主体的迁移让渡,往往是被动的、毫无缘由、不可拒绝的。小说里反复出现魔咒般的话语:“你其实不是你”,既是对人物角色,也是对读者的不断提醒。主体被让渡以后,其他时空范围内的可能身份,对于当下自我的稳定存在,永远都是一种隐患和威胁。“你其实不是你”,意味着主体永远面临着解体的危险。
应该说,当读者对角色的主体统一性产生质疑之时,恰恰是理解作者真实意图的开始。与小说叙事行动同步展开的,不仅是作者关于主体完整恒定性的反思。同样成为反思对象的,还有主体在历史进程中有意识、无意识行为的意义连贯性。
与这种反思性质的叙事相辅相成的,是作者在字面和隐喻层面刻意采取的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一种以相对隐蔽的方式,移植外来语言文化的特定意象、主题和思维结构。例如标题里与死亡、救赎和重生相关的“七”“夜晚”和“莉莉”,以及现代主义小说典型的意识流和多视角平行叙事手法。另一种文化翻译策略,则是直接挪用众所周知的文化符号,对真实的历史进行模拟、再现和戏仿,在虚实情境之间跌宕跳转,从而形成“在场感”与“出戏感”的矛盾并存。例如,孔菲斯、洛克菲勒、季泽克、玛丽莲·梦露、小罗伯特·唐尼、科波拉叔叔、伍迪·艾伦、休·格兰特这些容易导致时代错乱的角色名称,以及泰坦尼克号、摄影术、橡皮股票、人造丝、柏帛丽这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名称译法。
之所以称之为文化翻译,是因为它们都并非普通意义上的语言对译。首先,它们的主要目标并不是要形成语意的等值对应(equivalence),并促进两个异质语言群体的有效沟通;其次,它们挪借现有的翻译名称,或再现历史场景,并模拟历史上的翻译行为,是为了凸显文化差异和不适,并对以“翻译”为象征的资本全球化时代“等值交换”模式的质疑。它起到的作用,有些类似于尼兰雅娜推崇的“异质前景化”翻译(foregroundingofheterogeneity)。所谓异质前景化翻译,是借助于自然和不自然、熟悉与陌生化相掺杂的译入语,将殖民时期语词的单一、通顺、固定的文化意义进行多样化。这是以本土多元文化为中心,对单向输入、西方文化价值主导式翻译的一种逆向解构。(Niranjana,1992:80—81,186)《七个夜晚》在不同的故事情境下,采用特定的文化翻译手段,帮助实现了角色的身份定位,并完成了意义的嵌置与自我解构、中西互为异域的情调渲染、对工业化社会价值的反讽、对本土文化的揭蔽与魔幻式表现。这些都为表现主体的被动让渡,以及对主体性的反思提供了契机。
以小说标题为例。“莉莉”(Lily)的名字与圣母马利亚的象征物“百合”相同,在一定程度上近似于基督教的圣洁与救赎寓意。小说结尾处,又暗含了“池塘”睡莲(waterlily)的意象。睡莲既与佛教的莲花意象相似,又有本质不同。它所寓居的池塘代表着生命的母体。小说里的“池塘”共有两处:一是莉莉的镜像人物莲生寄身的低级舞厅“池塘”;另一处则是结尾“莉莉自叙”里的“眼泪池塘”。眼泪池塘之水,来源于漂来城的原始神癨:莉莉的母亲土地娘娘。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打破了土地娘娘苦心维持的平衡。漂来城的现代化进程,即以开埠元勋麦边勋爵下令屠杀乌鸦的象征场面开始:“乌鸦头还是在被源源不断地送来,最后失望的苦力和流民们将它们扔进了漂来江。整整三天,漂来江里流的不是水,而是黑压压的乌鸦头……有多少乌鸦失去脑袋,未来漂来城里就会有多少人死去。乌鸦其实不是乌鸦,而是人类的灵魂”。(孙健敏,2015:307)土地娘娘为此流下的泪水,汇成了池塘。它象征着无尽的怜悯,是对包括自身在内的被凌辱者、被损害者、被异化者的集体哀悼。土地娘娘“意外”而“错误”地生下白皮肤、蓝眼睛的莉莉,意味着殖民主义对本土文化的强暴结合,是耻辱的见证。然而,唯独莉莉才拥有“妈妈特有的神性印记”,因此被她视为必然的继承者,是“她做过的最美的梦”,尽管“她无法知道这梦最后会变成什么”。这种选择,导致了神癨家族内部的纷争。土地娘娘认为自己的时代已经结束。她任由另外两个女儿被善于做梦的狐仙和鬼仙带走收养,并且与莉莉分别,留下她独自把握自己未知的将来。莉莉在分别时流下的眼泪,汇入母亲留下的池塘,意味着她将继续这怜悯与梦想的神圣使命。
“七个夜晚”,代表了莉莉一次次的死亡和转世分身(avatar)。作者以这七个夜晚作为中心场景,将生命的流转轮回,浓缩在七个截断性(episodic)的时间范围内,并将事件放置在欲望与资本汇集的公共空间:租界。“夜晚”在西方文学主题里,往往和忧郁(melancholy)结合在一起,并引发对于死亡的思考。小说章节的叙述,宛如无数支流汇入主流,连绵不绝。熟悉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读者会发现,这种平行连续的多视角叙事手法,以及“七”这个数字隐含的死亡与再生寓意,颇像是对现代主义作家弗吉妮亚·伍尔夫,尤其是其代表作《达洛维夫人》的致敬。《七个夜晚》的平行叙事结构,相似于《达洛维夫人》的“隧道沟通”(tunneling,伍尔夫语)手法。有趣的是,《七个夜晚》里被埃利斯和小罗伯特在逃难中偶然发现的“逃生密道”,是唐喻当年留下的浩大地下工程。这个地道,在故事当中是一个极其明显的隐喻。当然它还可以寓示作者的叙事结构设计。
标题里相对容易被忽略的,是“七”这个数字。伍尔夫笔下跳窗自杀的塞普蒂默斯(Septimus),名字就是“七”的意思。分析者认为,对于达洛维夫人来说,塞普蒂默斯等于替代她实现了求死的意愿。同时他也是伍尔夫的另一分身:伍尔夫在家排行第七,联系到她后来的自杀,可见这个人物的命名并非凭空而来。《达洛维夫人》里的关键意象具有明显的“圣礼式”(sacramental)意味(René,1965:23—31)。从基督教的仪式传统来看,神秘数字“七”与“七圣礼”密切有关。“圣礼”的拉丁文为sacramentum,源于希腊语mysterion,意思是“神秘”。它最早是欧洲经院哲学家伦巴第人彼得(PeterLombard)确定的洗礼、圣餐、坚信礼、忏悔礼、婚礼等七种宗教仪式,后来延伸为上帝向选民显示其存在的迹象。(Brown&Flores,254—255)莉莉代表着未被政治化的边缘地方神癨和自然精神,是最顽强的生命意识的寄托。但神庙丧失、母亲离去、耻辱未洗,导致她流离失所,并寓居于不同的女性身体之内。孔菲斯能够与她在幼年时邂逅,并在记忆里对她的神性印记“藤蔓般的发根”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象,意味着他已经是这种神秘意义的“选民”。他同样要经过七次仪式化的相逢,才可以亲证莉莉向他传递的神癨本相。因此在小说结尾处,唐喻在孔菲斯完成任务后兑现许诺的方式,是送给他一张照片。照片里是娘娘庙的神像,“脸和他第一次见到的莉莉长得一模一样”(孙健敏,2015:305)。
再看主人公“孔菲斯·洛克菲勒”这个别扭的名字,更是属于明显的异质前景化翻译。小说里显示他的真实身份是神秘人物唐喻的侄子,生下来患有白化病,自幼就被老洛克菲勒领养。这个名字,是西方眼光里的东方文化标识与现代资本符号的生硬结合。“洛克菲勒”寓示了现代资本,而“孔菲斯”的名字,则在第三章“第一次在真实中到达漂来”时,由他本人给出解释:“这是中国人的孔夫子在英文里的译名。一个人既然叫这名字,不来趟中国,就太说不过去了。”但实际上,这只是以邵洵美为原型的邵介慧刚刚告诉他的知识。他自己对这个名字的深意却一无所知。(孙健敏,2015:98)这个名字还反映出东西方命名方式和价值观的冲突:西方人以圣人而命名新生儿,是对圣人的尊奉;中国人的名讳禁忌,则不可能允许这种近乎亵圣的命名方法。即使是全真教祖师丘处机,因为与孔子的名字犯讳,清雍正帝甚至还专门下诏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名称,改“丘处机”为“邱处机”。其实,“孔菲斯”这个中文回译式的写法,还是对前几年国内翻译界“门修斯”事件的戏仿:孟子的英文译名Mencius被误译成了蹩脚的“门修斯”,一时间传为笑谈。小说采用这种戏仿译法,一方面有助于突显出中西眼光的差异隔阂,另一方面也是对自我殖民化倾向的暗讽。不仅如此,因为这样的命名,孔菲斯与莉莉的因缘,就像是模拟了莉莉母亲在以往无数朝代里与“书生”的因缘结合。这实际上寓意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与地方文化和乡村自然的结合。只不过,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国新生的知识分子刚一出生,就会不可避免地患上“白化病”。所幸的是,他们也会凭借着历史记忆,一次次回返寻找原初的、本能情感式的文化亲缘。
如前所述,小说里频繁出现与历史真实和当时译法相符的工业产品名称,同时还掺杂了不少时空错置的西方电影人物,甚至当代电影里的角色名称。尤其是与制造梦幻相关的现代照相摄影术及相关译名,它充分寓示了光影色相带给人的虚假真实感,或玛丽莲别墅代表的“死循环”。不得不说,这种戏仿有时候显得过于密集和直接,虽然有助于获得作者希望的“脱榫感”,但多少有些降低了阅读时连贯性的愉悦。总体来说,在揭露了工业时代的欲望泛滥和空幻本质的同时,这些直接挪用的译名人物,也暗中讽刺了当今物质社会的虚空追求。更重要的是,读者在意象的淫靡与荒诞中,对叙事的幻觉本质,乃至于对主体的统一真实性产生警醒和思考。例如,代表着欲望、性无能和空虚的埃利斯,他的秘密嗜好之一就是拍摄各种色情照片。而那些面对他相机镜头的人,很容易呈现出异化和人格分裂倾向。白俄罗斯难民娜塔莎为给家人和同胞筹集钱款而主动勾搭埃利斯,初始动机里确实包含着无私的成分。但在埃利斯的镜头前,她却自甘沦落为一件性感的物品,并贪恋这种堕落感觉。蒋桂芳在刚刚饰演完穆桂英以后,为了完成政治交易,去埃利斯的摄影室拍裸照。在感到无比屈辱的同时,却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愉悦:“他知道在那黑乎乎的机器里,从里到外,每个毛孔都在昭示,他一定是个女人。”(孙健敏,2015:28)有意思的是,他后来并未继续发展这种女性潜质,而是演变成为男权社会的成功人物和绝对主导者。作者故意将这种性别逆转的结局,留给了与他相恋相杀、原本是女儿身的汪德龄。这种以欲望投射和身体异化为特征的窥视行为,在小说的不同场合里反复出现。它也是小说叙事行为的自我镜像。尤其是那些直接挪用的电影人物名称,既象征着小说内部色相世界的本质,拉近了“梦”世界、“真实”世界和“不存在”世界的距离,同时又增加了现实读者的意识从虚拟世界里“出局”的概率。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角色让渡”背后的真正推动力量。小说里多次出现舟船和接引人的意象。例如开篇时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孔菲斯多次乘坐来中国的邮轮、汪德龄变身后暂时寓居的船,以及娜塔莎父亲停滞在港口外的“鬼船”。接引人的典型代表,是身穿黑衣、鬼魅般出现的唐喻,还有无所不知、“狐妖似的”罗夫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娼妓形象而陆续出现的莉莉,也同样是接引人。这些接引人的任务目标各不相同,但存在着一些表面上的共同点。例如,外部叙述者不断进入其他主次要人物的内心展开叙述,却极少进入这些接引人的内心(莉莉的自述是例外,这一方面证明她接引指向的目标是她本身;另一方面,这段内容是小说里唯一使用楷体字的部分,或许是在暗示着另一个全知叙述者的声音。这个声音可能只是属于故事内的莉莉,也可能是代表另一个时空序列的外部叙述者)。另外,从接引人的角色属性看,当叙述者纯粹从外部对他们进行描述时,他们的本性既可以说是神秘莫测,也可以说是空性。只有莉莉的本性,在小说最后的自述里,呈现为“怜悯”和“梦想”。
这些接引者背后的推动力量又是什么?唐喻似乎是最终的操局者,是能够随时展开自主行动或置身事外的自由意志代表。但如果从他的行动方向来看,他与所有角色人物并无太大不同,都是受到了欲望的作用推动。差别只在于他的欲望处于道德体系的更高层面。而欲望本身又像是商品,它们相互之间的流通置换,有时并不受人的意志左右。与唐喻坚定不移的家国情怀相反衬的,是莲生的弟弟席路生:“五光十色如梦如幻的事物不断涌入心底,置换着那些他本以为会坚不可摧的国仇家恨。他恐慌起来,到处找人诉说那些他本打算永远藏在心底的悲愤,但说得越多,和记忆相伴的炽热情感就越是暗淡。最后为了证明这情感的真实性,他下了决心,要去行动。”(孙健敏,2015:287)但这次坚决勇敢的行动,却以他无谓的死亡而告终。从这段描述里,可以看到小说外部叙述者对所有人物角色的欲望,都显现出平等之观。个体的卑微欲望,或许影响到历史的进程。而企图推动或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例如,唐喻、汪德龄、高桥等人,他们的欲望未必就不是一场空幻。
然而,没有欲望,就不会产生行动,也就不会有悲欢离合,最终更不会形成故事。人的欲望不可中止,正如故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你其实不是你”。如果主体在不断的分裂和让渡中只留下空壳形式,那么“我” 的内容是什么?小说结尾处, 其实已经隐约给出了答案:一切有情众生,生存即是苦。我们在欲望中迷失自我,也只能在反思欲望中认识自我,并努力寻找主体的统一。孔亦丘在给埃利斯设计玛丽莲别墅时,要求“边动工边设计,这样房子在完成前,对设计师本人来说, 也同样是悬念” (孙健敏,2015:277)。但是,这间建筑注定不会完工。它在象征着虚幻欲望的同时,还象征着真相的循环自证和意义的永远“悬置”。因为它是存在的本质。
在孔亦丘亲手杀死高桥的第二天,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代表着漂来城最后一批殖民者的消亡。唐喻告诉孔亦丘(孔菲斯),只有杀死高桥,他才可以和莉莉重逢。但这个并未兑现的重逢,成为小说的“悬置” 结尾。玛丽莲别墅,成为小说叙事本体的象征。唯一明确的是,在小说结尾处,莉莉已经洗净耻辱,取代母亲而成为新的地方神癨。
“莉莉” 这个新神癨的名字,在本质上是后殖民时代语言和文化身份的“杂合”(hybridity)产物,并且具有“跨国与翻译” (transnationalandtranslational)的属性。(Bhabha,1994:5)这个“白皮肤、蓝眼睛”的混血形象,这个充满无限悲悯与梦想的边缘神癨,这个曾经是被抛弃者的耻辱形象, 她那
注释
[1]孙健敏:《消散之地》,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
[2]孙健敏:《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
[3]Bhabha,Homi.TheLocationofCulture(London&NewYork:Routledge,1994).
[4]Bowie,Andrew.AestheticsandSubjectivity:FromKanttoNietzsche(Manchester&NewYork:ManchesterUniv.Press,2003).
[5]Brown,StephenF.&JuanCarlos Flores.HistoricalDictionaryofMedieval PhilosophyandTheology(Lanham,Toronto,Plymouth:TheScarecrowPress,Inc.,2007),254—255.
[6]Fortin,RenéE..“SacramentalImageryinMrs.Dalloway”.Renascence:Eassays onValuesinLiterature,Vol.18,Issue1,Autumn1965,23—31.
[7]Niranjana,Tejaswini.Siting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andthe PostcolonialContext(Berkeley:Univ.ofCaliforniaPress,1992).
[8]Zahavi,Dan.SubjectivityandSelfhood:InvestigatingtheFirstPersonPerspective(London&Cambridge:TheMITPress,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