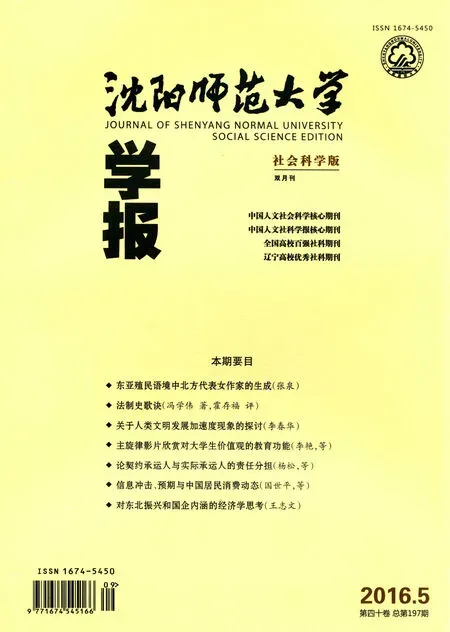东亚殖民语境中北方代表女作家的生成——简论北京时期的梅娘
2016-04-13张泉
张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266109)
东亚殖民语境中北方代表女作家的生成——简论北京时期的梅娘
张泉
(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北京266109)
1941年5月,梅娘从大阪移居北京沦陷区后,进入了另一个创作的巅峰期。这个时期,梅娘的外国文学以翻译日本文学中的虚构作品为主,侧重女性和家庭问题。在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同时,进入长篇小说领域。这些小说以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书写“满洲”大家庭的兴衰史,以及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命运和女人的命运,透露出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和女权主义意识,在梅娘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殖民地/宗主国行旅小说《小妇人》意在描绘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踽踽独行的知识青年的进路和出路,是东亚殖民文学场域中的一个分析殖民地民情世态/国家民族,实况/隐喻的绝佳文本。对于个别涉及时政的作品,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梅娘;北京沦陷区;文学翻译;沦陷区文学史
梅娘于1941年5月从大阪移居北京沦陷区。在京期间,她基本上是一位独立作家,仅短期兼任《妇女杂志》嘱托(顾问)。少量的职务写作,留下了时代的痕迹,却也保留了一窥当年家庭手工艺、女童孤儿院、博览会、高校女生状况等沦陷期社会状况的第一手资料。这个时期,梅娘的外国文学翻译也转向女性和家庭问题,以日本文学中的虚构作品为主。北京四年间,梅娘的小说与沦陷区的直接政治现实拉开一定距离,以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著称。1941和1942年,各发表中短篇小说五篇,其中的《侏儒》《鱼》《旅》《黄昏之献》《雨夜》和《一个蚌》六篇,结集为《鱼》①梅娘:《鱼》,短篇小说集,由北京新民印书馆于1943年出版,为北京新民印书馆编辑的“新进作家集”丛书中的第二集。。《蟹》《春到人间》《阳春小曲》三篇,与1943年发表的《小广告里面的故事》《动手术之前》、1944年发表的《行路难》一起,结集为《蟹》②梅娘:《蟹》,中短篇小说集,由北京武德报社于1944出版,为华北作家协会编辑的“华北文艺丛书”之五。。长篇小说有《小妇人》(1944年)和《夜合花开》(1944—1945年),均未刊完。还出版了大量的儿童读物。日本文学翻译有中、长篇小说《母之青春》《母系家族》③《母之青春》刊于《民众报》,1942年8月1日至9月7日。《母系家族》刊于《妇女杂志》3卷11期至4卷9期,1942年11月至1943年9月。,以及短篇小说、随笔。
一、日本“风俗小说”翻译及其对梅娘的影响
《母之青春》的作者丹羽文雄(1904—2005年)是日本“风俗小说”代表作家。他战前的小说大多描写被封建家庭制度抛弃的不幸妇女,主人公大致分为两类人:生母和老板娘。《母之青春》属于前者,以一个出走在外的母亲和一个抱养的女儿的曲折经历为主线,描写儿女不同的心性和情爱。七七事变后,丹羽文雄发表了《未归的中队》《上海的暴风雨》《变化的街》等“战争文学”。
梅娘没有翻译丹羽文雄的“战争文学”,而是选择了他“转向以前的最末一篇关于男女问题的创作”——《母之青春》。对此,梅娘做了明确的说明:因为这篇小说“从男女的爱欲间而追求社会的伦理问题”[1]。半个多世纪之后,梅娘在回忆文中又做了类似的陈述:
从日本回到北京之后,我翻译了丹羽文雄的《母之青春》,是在一种既志愿又无奈的情绪下执笔的。丹羽是日本命名为“笔部队”的成员之一,他为战争摇旗呐喊,我不愿译他的这类作品,他又是“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主持人之一,我选择《母之青春》,因为书中讲的是母女两人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这和我的主题相近。我还有一点私心,想《母之青春》也许能够冲淡中国人对丹羽战争文学的厌恶吧!包括我在内[2]。
《母系家族》的作者石川达三(1905—1985年),曾获得芥川文学奖。战后,石川达三担任过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长、日本笔会会长等职,著有25卷《石川达三全集》(东京:新潮社,1972)。
1937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29日,石川达三作为《中央公论》的特派作家抵达南京,实地采访之后,发表了报告文学《活着的士兵》(1938年)。由于作品中出现“皇军士兵杀戮及掠夺非战斗人员、纪律松散等情节”,客观上揭穿了侵华战争的真相。为此,石川达三被日本军部判处有期徒刑四个月,缓期三年执行。《活着的士兵》一时间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文学事件,中国很快出现了好几个译本。石川达三为了改变个人处境,第二年很快又发表了为侵华战争张目的《武汉作战》。梅娘不提这些作品,只介绍他的《结婚的生态》《人生画帖》《转落的诗集》等风俗小说:
石川氏的小说,是以表现男性与女性的自我,及男性女性企图征服对方,并且追求调和这两种形态为骨干的主角,只是被社会压抑了的女性,石川氏用他的生花妙笔替这些不幸的女人呼求着理解,幽述着阴郁,反抗着社会待遇的不平,也嘲笑了女人的愚昧[3]。
梅娘的分析与认知,堪称鞭辟入里。作为日本风俗小说代表作之一,《母系家族》的背景是一座公益公寓,专门收容失去生活来源的母亲们。在这个舞台上,展开了各类女人在恋爱、婚姻、家庭纠葛中的众生相。也处在情感漩涡中的主人公律师高村从救助实践中认识到,他开办的这座公寓无法成为改变女人命运的避难所。于是他开始进军政界,期望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推进“母子保护法”,把女性地位问题从个人奋斗升华到社会保障的层面之上。高村最后成功当选议员,并获得美满爱情。这样的题材、观念,正与梅娘的女权主义立场相契合。
文学翻译,无论对象是作家还是作品,都不可能面面俱到。译事注定是一种选择。总的来说,梅娘在北京沦陷区的文学翻译活动,避开了官方话语,游离于殖民地文化统制,成功地与她个人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志趣形成互动。这或许是由于,梅娘文学创作中一贯的女权意识和女性关怀,使得她在选择翻译对象时,自觉不自觉地把重心放在妇女生活和女性解放的题材和主题之上。反过来,通过翻译活动,梅娘对域外的女性文学和妇女题材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并有所借鉴。梅娘在北京沦陷后期的小说创作,注重叙事结构,以及典型环境中的人物塑造,在保持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同时,又融入了纯文学构成要素。这正是日本的风俗小说在由传统向现代转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二、中短篇小说艺术的成熟
梅娘的短篇小说艺术有了长足提高。广泛受到好评的《侏儒》以刚柔相济的独特女性视角,通过一个被恶意扼杀的私生子短暂的生命史,展示人世间的不平,堪称梅娘的代表作①梅娘的《侏儒》于1941年10月,由北京《中国文艺》刊发(5卷2期)。。《行路难》发表于文坛迅速解体的沦陷末期,评价不多。小说作于1943年冬季,写叙事女主人公走夜路回家途中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路遇醉鬼、穷汉。恐惧之中,穷汉无意中为“我”解围,排除了醉汉把“我”当作“马路天使”的骚扰。“我”急于摆脱可能会伤害我的穷汉,高价要得正准备收车的人力车。此“浪费”钱之举激怒了穷汉。他大声说:“我本来没预备劫你,你与其给三轮车十块钱换这样一小段的车坐,不如把你底钱赏给我,我摸得准这于你并没什么了不起的损害。”[4]接着,一把抢走了“我”的钱包。而“我”从穷汉留下的豆饼包装纸上的留言得知,处于绝境中的穷汉可能正准备自戕。在回家途中,“我”对于抢劫者没有愤怒,有的是祝愿、反思和同情,并为自己所想感到“羞耻”。戏剧性的结局所流泻出的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与梅娘的《侏儒》异曲同工。《黎明的喜剧》②刊于华北作家协会编辑的“作家生活”连刊之一《黎明的喜剧》(1944年11月)。是一篇人物速写,描写一位走街串巷的贩菜老人,为生活所迫,做“窝主”,收购帮佣从主人家里偷出来的衣服。此场景无意中被“我”看到。念他不但老而且非常疲惫瘦弱,他的脸露着可怜的菜色,念他长期以来菜卖得比较便宜,分量也很公道,叙事者“我”虽然恶作剧地揭穿了他,却平静地放了他一马。从这几篇小说可以见出,城市普罗大众不堪的和难堪的生存状态,更多地进入了梅娘的虚构作品。
男权社会里的女性命运,仍是梅娘的关注点。《小广告里面的故事》以一则征婚启事开篇,而隐藏在征婚广告背后的故事是,为躲避战乱投奔姨父母的“我”,被他们用来充作骗取钱财的诱饵。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淋漓尽致地吐露出世态的炎凉,以及沦陷区年轻女性存活之艰难。《动手术之前》也使用第一人称。主人公是一位被丈夫冷落的少妇,被丈夫的朋友趁机侵犯,不幸罹患性病。她曾在住宅区邂逅过一位医生,并未说过话。绝望的少妇,在想象中向这位医生喋喋不休,倾诉身体和精神所遭受的双重创伤。两篇小说均直白地在男权社会中大胆宣泄女性私语。《旅》以情节的安排见长,仍以第一人称叙事,恬淡地讲述在火车上耳闻目睹的一幕活剧。《春到人间》构思独特,显示出作者驾驭短篇的才力。《黄昏之献》侧重心理剖析,讽刺的笔触指向吃软饭的低俗中年男子。这些作品在不知不觉之中揭示出,形形色色的婚姻、家庭悲剧的重压,都落在了孤立无援的柔弱女子身上。
完成于“满洲国”和日本的《蚌》(1939年)、《蟹》(1941年)、《鱼》(1941年),均在北京时期发表。三篇小说的情节和人物没有直接的关联性。不过,“满洲”大家庭的兴衰史和女人命运的书写,以及共通的女权主义萌芽将它们有机连接在一起,可以称之为“水族系列小说”,在梅娘的创作中,具有重要意义。
《蚌》③梅娘的《一个蚌》首发新京(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编印的《满洲文艺》第1辑(1942年9月)。收入左蒂编的《女作家创作选》(新京:文化社,1943)时,更名为《蚌》。中的女主人公梅丽是东北一位赋闲显宦巨贾的庶出女。在家庭内部,她是大家庭妻妾倾轧争斗的牺牲品。在社会上,她所服务的税务总局的同事心怀叵测,设下圈套败坏她的名誉,逼她就范。在内部、外部生存空间的挤压下,梅丽孤立无援,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呐喊:“与其卖给一个男人去做太太,去做室内的安琪儿,还不如去做野妓,不如去做马路天使”。她终敌不过家庭和社会构筑的樊笼,在心灵和肉体遭到重创之后,只能发出绝望的诘问:什么地方有给女人留着的路呢?《鱼》中的芬压抑不住少女青春期的渴望:单恋高中部的国文教员受挫,很快失身于已婚纨绔子弟林省民并诞下男婴。寂寞的芬不甘作外室的屈辱:“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它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5]在封闭的环境中,她的拼死抗争,不过是转而追求她遇到的另一个有妻室的暧昧男人,结果遭拒。《蟹》④梅娘的《蟹》最初在《华文大阪每日》上连载,7卷5期至12期,1941年9月1日至12月15日。以少女玲为线索,试图勾勒出近代闯关东流民的发家史,新一代与老一辈之间在日本占领背景中的冲突与决裂,以及东北传统大家庭在殖民期的衰败与解体。玲受到俄文书籍的影响,蔑视大家庭中的庸碌险诈的成年人。她摒弃借助婚姻实现女性独立的现代出走套路,决心离开大家庭进入大世界。三篇小说的标题颇具意味。“蚌”属于软体动物门,隐喻青年知识女性的弱势。“鱼”作为水生变温脊椎动物,冲击力有所提高,但生存能力并不比蚌大多少。甲壳动物“蟹”比鱼蚌强大,在诗人的笔下它“怒目横行与虎争”,正与玲对于衰败家庭的洞见和对于出走的期待相契合。这是梅娘创作中经久不衰的东北沦陷区家族/女性议题。
三、进入长篇小说领域
《小妇人》的主人公是北平一对追求婚姻自由的恋人。袁良和凤凰未婚先孕,决然出走。小说讲述他们私奔到“遥远的满洲去建设他们底小家”[6]的历程。《夜合花开》断断续续刊北京《中华周报》1卷1期至2卷34期(1944年9月24日至1945年8月19日),描写沦陷区平民女子嫁入豪门后的少奶奶生活,涉及性别差异、情感欲望、自由恋爱、等级门户等。这些现象和议题在阶级社会中普遍存在,但在殖民语境中,呈现出别样的表现和意义。因此,两部作品尽管是残篇,但在梅娘殖民期的创作中,仍占有重要位置。
以写出走的《小妇人》为例。对于任何时空中的出走者来说,他们首先都要面对的,是非常现实的柴米油盐问题。袁良入职“满洲国”小学,并未能进入学以致用的大领域。低微的收入,职场的失意,消磨了袁良初恋的激情。他很快出轨校长夫人,经常夜不归宿。这既满足了他的欲望又能使他在学校职场获得利益。生存的压力,现实与理想的落差,使得袁良的性情发生变化。他开始对妻子凤凰甚至对情人频频施暴。凤凰也从热恋少女变身为生儿育子的小妇人,在生活困顿和被丈夫冷落的双重困境中,由愤怒、绝望转为麻木、迷茫,终于领悟到:原来“真的爱,不是一见钟情,不是几经风波的那样小说里所描绘的,也不是两人朝夕相厮守,难舍难分的。那是得要整个牺牲自己,完全接纳对方,使两个人的自我化成一个共有的‘我’才行,这是一件太艰巨的工作。”[7]袁良既迷恋情人的魅力,又对妻子深感歉疚。两难之中,他辞掉“满洲国”小学教职,再次出走。这一次,他只身前往日本当中文教员。在日本,孤寂的袁良不断投书凤凰,表达忏悔,恳求她携子到日本团聚。凤凰知道自己还爱着袁良,但选择了暂时寄居闺蜜家。在《娜拉走后怎样》(1923年)中,鲁迅曾断言,为爱而出走的女性不是自甘堕落就是返回原地。凤凰开始思念父亲,反省自己的私奔对老父造成的伤害,却也无意走回头路重返故乡的大家庭。凤凰也曾自忖:“与其关在一间小屋子里为一个不懂爱情的男人做妻子,受着贫穷的折磨,倒不如到这里来做舞女,至少,总可以在装饰中显露着美丽,用美丽来换取享受,而用不着受一点挟制。”[7]但她并未付诸行动。沦陷区的凤凰没有落入鲁迅预设的两种结局,给读者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也丰富了现代文学中的出走女性人物众生相画廊。或许,《小妇人》的开放性结局是由其未完成状态造成的。
袁良源于情的第一个移居地是“满洲国”。他把爱情至上开启的新的人生憧憬,同已经沦为殖民地的“满洲”青年未来的美好前途联动:“满洲的青年一定在彷徨,这是每一个大动乱后必有的现象”[6]。他因有凤凰相伴而踌躇满志:他一定能够大有作为,“用他底热情去安定那些彷徨的大众,他要领导他们进入真美、真善的境界中”,这样,“他和凤凰的崇高的爱情才真正地达到了他们所以相爱的饱和点。”[6]而结果却是,爱情很快搁浅,拯救动乱中的“满洲”青年民众的宏愿随之破灭。“满洲”青年在大动乱之后的无归属感的彷徨,只能照旧延续。
困于情的第二个移居地是日本。东京到处是宣传日满亲善的“大陆的色彩”:“满洲国”皇帝来访问过,“百货店的窗饰绘着大陆的秋天,广告画上画着饱满的金黄的大豆,咖啡店里挂着李香兰的放大照片,播音机在唱着‘何日君再来’”。在学校里,“汉文成了必修课了,北京话成了最时髦的语言。年轻的男女留学生都憧憬着去开发大陆,梦着那遍地黄金的肥沃的国度。”袁良觉得,许多日本人发现“他是来自满洲或中国的时候”,会“用诧异的眼光”看着他。他觉得周围“异国”的人与他无关,“他被孤独的寂寞吞进去,失去了所有的人生的快乐。”他渴望遇见“和他同种族的人,一个和他说着同样语言的人,他渴望着说说故乡的语言,用故乡的语言来互相酬答,他觉得他像哑子一样地夹在那杂沓的快乐的人流之中,失去了说话的机能而渴于表达意见。”[8]
在东京街头与萍水相逢的当地商人喝酒时,酒兴正酣的商人问袁良是“满洲”人还是中国人。袁良点头敷衍,不置可否。日本商人大谈他在学“满洲”话,准备到“满洲”做买卖,“把“满洲”的大豆运往世界的各个地方去。”他认为,“这样的大买卖一定要日本人来做,日本人有这样的魄力,日本人最公正、正直。”并且,将经济掠夺行径上升为日式东方殖民主义:
“这是协和”,商人接续着,他兴奋得忘掉了他底酒杯,他一边写着一边作着手式,这是亲善,我们是兄弟之邦,要像兄弟样地共事。满洲人没有力量开发实业,日本人有,日本去开发,这是帮助满洲人。满洲和日本共存共荣。大家一块吃饭[8]。
贩酒的老头儿也帮腔道:“日本人最公正,正直,而且最爱帮助别人。”[8]小说接着话锋一转,描写虽然无声、却并非无言的袁良:
这酒怎样也不能代替袁良心中的山葡萄酒。商人和卖酒的老头底快乐的、被烟酒和兴奋的感情染红了的脸,和袁良苍白的寂寞的脸成了一个明显的对照。袁良想离开那儿,他心里被酒引出来的哀愁使得他完全失去了再在这小车子中停下去的兴趣。
他咬下来铁棍上的最后的一块鸡肉,他没有觉到肉香,他付了钱,在商人殷殷的话别里,无言地走了出来[8]。
日本的清酒取代不了家乡的地方酒。日本烤鸡肉也失去了肉香。日本商人对于袁良是“满洲”人还是中国人的好奇,或许并无恶意。但袁良拒绝回答。对此,可以有多种解读。不承认两者间的差异,也是可能的阐释方向之一。小说在“满洲人好”“满洲人真好”的啧啧称美声中,淡出“满洲或中国”选项,罗列种种“日满亲善表面化”的现象,直言袁良在宗主国“失去了所有的人生的快乐”。上述种种,既真实表达了殖民地青年对宗主国的真情实感,也形象地反映出“共荣圈”内的殖民/社会关系。宗主国“兴奋”“染红了的脸”,殖民地“苍白的寂寞的脸”;宗主国的“殷殷”,殖民地的“无言”;宗主国“快乐”,殖民地“哀愁”,正是这种关系和情感的自然反应。
据此,《小妇人》不是鸳鸯蝴蝶派风格的言情小说①梅娘的《小妇人》“这部小说沿袭了沦陷区鸳鸯蝴蝶派的创作路子”。见王劲松:《殖民异化与文学演进——侵华时期满洲中日女作家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223页。。它生动、形象地演绎了“中华民国”一对理想主义的私奔情侣,在殖民地/宗主国的旅行冒险。他们和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孙柔嘉一样,在旅程中不断碰壁,在内在和外在冲突之中,既有精神危机也有躬身自省。由于语境的不同,《围城》重在刻画民国期文人学士群像,构建现代中国西化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小妇人》意在描绘在“大东亚共荣圈”内踽踽独行的知识青年的进路和出路,是东亚殖民文学场域中的一个分析殖民地民情世态/国家民族,实况/隐喻的绝佳文本。
四、少数涉及时政的文本辨析
据不完全统计,梅娘1945年以前的作品达百万余字,其中涉及时政的有三篇,均发表在《妇女杂志》上。《访外交部长褚民谊先生》(1942年3卷5期)、《大东亚博览会》(3卷6期),属新闻报道。《四月二十九日对日广播——为日本女性祝福》(6卷5、6期合刊,1945年6月),一篇官样文章。此外,散文《佐藤太太》《我底随想与日本》②梅娘:《佐藤太太》,日本大阪外国语学校《支那及支那语》1941年4月号;梅娘:《我底随想与日本》,日本大阪《华文每日》12卷11期,1944年11月1日。,记述了她在大阪的侨居生活。这不多的几篇,展现了跨域复杂作家的另一个面向,如何评价,值得探究。
比如,有当代论著对梅娘的广播稿作了这样的评价:“流露出对日本物质文明的羡慕”,继而又“煽动、鼓噪日本妇女为侵略战争效劳”;距离抗战胜利只有两个月了,“沉溺于决战亢奋中的沦陷区文人,包括柳龙光、梅娘在内,未能预测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即将失败”,所以才写这样的广播稿;从“频繁出现的词汇,如‘国家民族’‘国防’‘国家的战斗的力量’‘国家民族社会的责任’等,可以看出,作家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发生了混淆和迷失”③王劲松:《殖民异化与文学演进——侵华时期满洲中日女作家比较研究》,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第199页,第200-201页。也有较为缓和的批评:“到了日本败象已露的1945年6月,梅娘反而发表了从‘女性的处境’之普遍性出发、鼓励日本妇女继续为大东亚战争恪尽职守的广播讲话。她呼吁在日本铁蹄下生活的女性超越民族国家的界限,与敌国女性联盟,但其目标并非指向女性解放,而是大东亚战争,这向来被视为梅娘混乱的民族认同的证据。”陈言:《战争时期石川达三的创作在中国的流博与变异——兼论梅娘对他的理解与迎拒》,北京《外国文学评论》2015年2期,第216页。。这近乎政治宣判式的评语,不失为一家之言。但需要注意的是,时政文的言说语境。
首先,新闻报道、无线电收音机广播稿,是新闻管制的产物。作为知名作家,个人介入还是不介入的选择余地、个人言还是不言的表达空间,极其有限。
其次,在侵华战争末期,日军战线漫长,大批军力、人员、物资调往太平洋战场,内地沦陷区国家机器渐趋停摆。华北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捉襟见肘、濒临崩溃,文化机构、报刊陆续关闭,从业人员从高层到基层,纷纷另谋出路④参见张泉的《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一书第九章《满系的离散:移居北京沦陷区》第一节《武德报社的转型与柳龙光》中的柳龙光的出场与退场部分。该著作即将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他们也成为各路抗战建国力量争取的对象。仅以柳龙光负责的作家协会的核心活跃成员王石子、黄道明⑤黄道明,笔名木君,为华北沦陷文坛理论家,曾任新民会中央总会宣传局科长、华北作家协会副干事长、《新进》月刊社长等职。该刊于1941年11月30日创刊,1943年12月倒闭。黄道明失业。等人为例,从1943年11月开始,他们就谋划离开北京、脱离日伪政权。到1944年11月,王石子终于凑齐川资,携家眷踏上移居重庆的千难万险之路⑥王石子20世纪50年代“交代历史”的手稿,藏其后代王三洋处。参见《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张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第六章《官方文场与资深作家》第五节《其他作家》中的王石子部分。。不存在“未能预测到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即将失败”的所谓“忽值山河改”这一意外情境。
美国轰炸机从1942年4月20日开始,对日本的军事工业城市实施轰炸,日本本土固若金汤的神话被打破。随着轰炸的持续,就连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包括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也对日本帝国及其殖民事业陷入绝望:
他们在街头巷尾纷纷议论向朝鲜、“满洲”、日本撤退的事。完造在书店的茶席上向客人们建议说:“如果撤退的话,不脱离日本国籍是不行的,而且也没有必要撤退到‘满洲’或朝鲜,可以渡过黑龙江到苏联去。”[9]
1945年初,美国空军更是加大轰炸力度。3月9日夜晚的东京大轰炸,两个小时将城市的1/4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超过五个月后的广岛原子弹爆炸(1945年8月6日)。具有国际化社会关系和视野的柳龙光,很难对“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即将失败”的行政状况及街谈巷议充耳不闻①胡兰成(1906—1981年)曾任汪精卫南京任行政院宣传部政务次长。还担任过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要职。1943年12月7日,因所写文章中有“日本必败、南京政府必亡”的预测,被投入监狱。在日本友人的斡旋下,四十八天后,胡兰成写悔过书获释。从此,他脱离伪政权官场,得以成为张爱玲名义上的第一任丈夫,并因此而闻名于世。参见张泉:《中国沦陷区文学的内容与性质之辩——试析几篇“商榷”文章中的史实差错》,收入张泉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史料与研究》第1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7年出版。。如果这一点成立,在对柳龙光、梅娘所谓的“决战亢奋”作解读时,“故作姿态”可能也会被列为选项之一。
第三,广播稿中出现有“国家民族”等语词。据此,批评论著认定,广播稿形式上的署名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发生了混淆和迷失……难以分辨出殖民与被殖民关系上的国家民族立场”。这样的论证模式,过于简单化。但仅从字面上的逻辑来看,也没有太大的问题。问题出在这一推定的理论依据之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国家被认知、被制度化的过程中,‘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从对日本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向往,对日本妇女的钦慕,到对日本文化中心的介入,这一渐进趋势,反映了受殖主体被文化殖民的心理过程。”[10]即广播稿署名人“被文化殖民”的过程。这一推定难以成立的原因是,对于所依据理论的使用有误。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1983年)一书所建构的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论述,脱离传统史学,另起炉灶,是对经典民族国家史的补充,对于重新思考二战之后的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源头、形成和发展的诸问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安德森提出,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是“现代”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具体到殖民地民族主义,他认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这种侧重想象的构建历史叙事的方式,以预设的理论为主导,大量使用非客体的抽样文献,不重视系统的地理疆域、行政机制以及政治、经济、军事制约等史实依据。这样,如果用“想象的共同体”方法实际撰写民族国家通史时,就会带来许多问题。当然,问题最多也不过是想象的整齐划一、突出建构、忽略丰富性、缺乏完整性、因而难以成为脉络清楚的信史而已。不过,如果机械套用安德森的理论,或者发展这个理论,用它来解析中国沦陷区、特别是沦陷区文学、沦陷区作家,就把安德森理论中的主客体的关系颠倒了。这样,对沦陷区作家作品的误判和误读就在所避免。从美国学者杜赞奇的“满洲国”论述个案可以见出,当“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叙事用于中国沦陷区时,所构建出来的历史离历史的真实的距离有多远②参见张泉的《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第一章《日据区文学跨域流动政治研究关键词》中的第四节《杜赞奇的满洲国“本真性”想象的失真》。。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否适用于战时、战前时期,即世界体制殖民期的被殖民地区,特别是中国抗战时期的日本占领区、日本占领区里的中国作家,是一个需要重新研究的课题,不是一个引经据典的问题。
简而言之,安德森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只是对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原因的一种推测,不是研判战时沦陷区作家是否“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发生了混淆和迷失”的证据或依据。在沦陷区作家“国家民族的认同”的判定问题上,可实际操作的证据或依据清清楚楚③参见张泉的《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第十一章《日据区文学研究方法问题:整体与局部》中的第二节《公民守则:汉奸文人与汉奸文学的界定》。,搬出安德森,文不对题,于事无补。
回到1945年6月1日发表的广播稿。安德森“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旨在对民族的形成问题提出一种另类解释方式,不在意某个个人的想象。假如一定要创造性地将其运用于沦陷区里的某个个人对国家认同的选择,就发生了另一个误解安德森原意的新问题。因为日本本来就是一个民族国家。套用安德森的理论来从政治上界定广播稿署名人的国族认同状况的时候,需要找寻的是,署名人认同沦陷区伪政权是独立“民族国家”的证据,而不是捕风捉影的“对日本文化中心的介入”:广播稿“奉日本文化为圭皋的文化特征,体现了日占区亲日文人对本土文化价值取向的颠覆和建构日本意识形态的国家想象。在认同和颠覆之间的文化选择,表明了受殖主体民族文化身份发生了危机。”[10]这一推断方式,颠倒了“想象的政治共同体”的原始论证逻辑。
除此之外,需要追问的还有:“日本文化中心”在哪里?谁能够“介入”?怎样算“介入”?退一步说,偏于北京沦陷区一隅,失业,无业,自说自话,没有听众,无人喝彩……也算“介入”吗?也算“主流”吗?仅凭日本战败前夕一两篇特殊情况下的时文中的只言片语,就对梅娘在北方沦陷区从文十二载的历史做出上述断语,未免有些轻松和轻率了。
至于1944年11月3日,在南京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梅娘与火野苇平用不同语言朗读大会宣言的问题[10],需要作历史的分析。
与在东京举办的第一次、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相比,这次南京大会的领导人、议程、议题,也包括大会宣言,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其最大的变化是:大会的领导人之一,是中共安排的地工人员①参见张泉的《殖民主义与离散文学——“满洲国”满系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政治》第二节《柳龙光与日据区文坛政治》。;在大会上,中国作家敢于我行我素,日方几乎失去了掌控力;大会宣言的基调也从往年的狂妄的战争叫嚣转为骗人的团结协作。根本原因在于,11月10日汪精卫刚刚在日本病死,多数人已对伪政权最后的结局有更明晰的判断。此时朗读大会宣言之举,是否“凸显了作家本人自我人格问题”,有研判的余地。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举代表不了“日占区中国文人殖民化的症候”。因为,“‘大东亚文学’口号虽然叫嚣了几年,也进行了一些活动,特别是成功地组织了三次大会,但它的性质、纲领一直是含混抽象的,更没有所期望的创作成果。它只不过体现了日本法西斯文人力图使文学更有效地服务于‘国策’的一种强烈愿望,对沦陷区文学的发展没有实质性的影响。但它确实给中国沦陷区形形色色的人物提供了一个在文学舞台上进行表演的场所,其中,有认贼作父的钻营者,有丧失民族气节的愚氓,也有一些头脑清晰、创作态度认真的作家,他们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或主动或被动地陷入这个泥潭。‘大东亚文学’是日本对中国沦陷区进行政治控制的奴化宣传口号,应当加以揭露和批判。但是对于参与者或卷入者,则不宜一概而论。”[11]特别是,参与者中,还有一批隶属于国民政府、中共以及各派政治势力的地下工作者,还有独立反日作家。
[1]梅娘.丹羽文雄介绍[N].民众报,1942-08-01(4).
[2]梅娘.我与日本文学[M]//侯健飞.梅娘近作及书简.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169.
[3]梅娘.石川达三氏小说介绍[J].妇女杂志,1942(11):51.
[4]梅娘.行路难[J].妇女杂志,1944(2):23.
[5]梅娘.鱼[J].中国文艺,1941(5):43.
[6]梅娘.小妇人·双燕篇[J].中国文学,1944(1):31.
[7]梅娘.小妇人·夜行篇[J].中国文学,1944(2):66.
[8]梅娘.小妇人·异国篇[J].中国文学,1944(8):20-23.
[9]小泽正元.内山完造传[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45.
[10]王劲松.殖民异化与文学演进——侵华时期满洲中日女作家比较研究[D].成都:四川大学,2007.
[11]张泉.抗战时期的华北文学[M].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78.
Female Representative Writers in the Context of East Asia Colonial Period——A Study Focusing on Mei Niang During the Period of Peking Government
Zhang Quan
(Institute of Literature,Beij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266109)
Mei Niang started another height of writing power after moving to Peking Occupied Area from Japan in May 1941,when her works focusing on fictions about feminism and domestic issues.From a unique vision,she wrote both short and long novels telling stories about the rise and fall of big families in Manchukuo of China.In her novels,it described the fates of women and women who were humiliated,which showed humanitarianism and feminism.The colonial novel Little Woman aimed to present a way for educated youth to break away from the so called Great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It was a good text version for studying the colonial situation in the literature field of East Asia Colony.In terms of the works about politics,specific cases should be considered accordingly.
Mei Niang;Peking Occupied Area;literary translation;history of literature in the Occupied Area
I206.6
A
1674-5450(2016)05-0001-07
2016-06-11
张泉,男,江苏宝应人,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与殖民地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詹丽责任校对:杨抱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