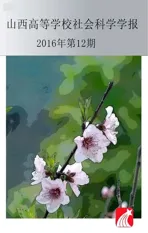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
——关于陈学明教授意义世界理论的思考
2016-04-13庞桂甲山西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太谷030801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91
庞桂甲(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探寻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
——关于陈学明教授意义世界理论的思考
庞桂甲
(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陈学明教授着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代社会的理论意蕴,以期解决当代社会人内在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他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批判现代社会,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人性的扭曲和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另一方面立足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意蕴和生态学意蕴,结合当前西方文明和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着力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意义世界”理论。他始终以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怀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为中国道路能够为人类开创新的存在方式提供一条现实路径。
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陈学明;“意义世界”;中国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陈学明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经过多年积淀,成为当今学术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学者之一。近年来,陈学明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楔入点,发掘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理论意蕴,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体系。他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学意蕴和生态学意蕴,如异化理论、劳动解放理论、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与自然和谐理论,形成了他“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和“天人合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为主要内容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理论。
一、以异化理论为武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社会
在陈学明看来,马克思主义异化理论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社会的“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则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他认为,异化理论以前所未有的理论洞察力揭示了资本驱动的现代社会的本来面目,揭示了人的异化的社会根源,为指引人类的未来,提供了一把钥匙;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则立足人的本质,构建了真正符合人的本质需要和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为人类寻找新的存在方式指明了方向。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最大的罪恶就是把人的劳动变成异化的人,人成了异化的人,人际关系变成了异化的关系。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苏联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其后来的思想是不同的,马克思的异化思想不过是马克思早年的思想,到了马克思的后期就渐渐放弃了异化理论。陈学明明确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虽然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异化理论经历了一个不断充实完善的过程,但是作为成熟的理论形态的异化理论是贯穿马克思思想的始终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分析阶级社会的重要理论工具之一,不能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形态割裂开来。因此,他既不认同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认为的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的巅峰的观点,也不认同苏联学者认为的异化理论只是马克思早期的不成熟的思想的观点。陈学明说:“不要认为马克思只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早期著作中才高扬人类劳动的旗帜,实际上,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以及对劳动对人生意义的阐述贯穿于他的全部一生的理论研究和斗争实践之中。”[1]348他认为异化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社会的现实,而且在当今世界,异化理论在揭示人类面临的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和自然危机的时候具有无比深刻的理论力量,在现代社会争取民众,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影响方面具有很大的理论优势,因此异化理论在当今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陈学明的观点更有说服力。例如,马克思在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揭示了资本逻辑驱动下“现实世界”的种种异化现象之后,他说:“我们的一切发明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2]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社会的“现实世界”内部包含着深刻的矛盾,最终让有生命的人变成了无生命的物质力量,而让愚钝的物质力量变成了生命!马克思还揭示了异化现象的根源在于“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对抗”。陈学明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本来面目的揭示和分析不仅是科学、深刻的,而且到今天也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的对抗并没有消除,马克思所揭示的现象到现代社会不仅没有消除,而且在很多方面还恶化了。
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在当代极具现实意义,它能够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和各种社会精神危机的根源。他忧虑地看到人类在过去已严重地步入了“生活的误区”,人类无意识地陷入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科学主义、个人主义等作为生活准则的陷阱当中。在这样的陷阱中,人成了对生活失去批判意识的“单向度的人”,社会成为技术理性支配的“单向度的社会”。这直接导致了人的功能和动物功能的颠倒,“出现了随着人类的进程人类不是越来越远离动物性而是越来越返回动物性的悲剧”[1]370。陈学明认为,真正能够解释这种社会现象根本原因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其中就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异化理论;真正能够指引现代人类走出这种“生活的误区”的也只有马克思主义。他说:“马克思所提出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上仍是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境界,它不仅崇高而且科学。”[1]370马克思主义是价值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它既代表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也能够为实现这种应然状态提供现实路径。
陈学明认为,人的异化首先体现在劳动的异化,体现人本质的劳动成了压抑人的异化劳动。在资本社会,人的劳动的过程是个强迫的痛苦的过程,人像逃避瘟疫一样尽可能地逃避劳动,而在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人又陷入动物欲望的泛滥中不能自拔。现代社会的人,某种程度上是劳动过程中的物化的人与劳动之外的动物化的人的结合。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与人的关系、人的内在精神世界都发生了异化,人悲剧性地远离了人的本质。这样的存在方式,显然不能是人理想的、应然的存在方式。
陈学明认为,造成现代社会人的异化的根源在于资本,解决异化现象的根本在于超越资本和消灭资本。他说:“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文明,……本质上都是以对抗和冲突为根本特征的文明形态和文明发展模式,‘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人成为‘经济人’,人的能力本身也成为资本,成为能够占有资本的资本。”[1]29-30正是以资本逻辑为原则的现代社会模式实现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全面联系和全面发展,为人类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的存在状态准备了物质前提,然而同时也导致了人的内在关系、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异化,已经触及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环境底线和社会底线。“生存还是毁灭?”已经成为摆在人类面前的现实问题。是改弦易辙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还是按照现行发展模式一条道路走到黑,在不远的将来堕入毁灭的深渊?每一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现实选择。总之,陈学明认为,要扬弃人的异化,实现人内在关系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谐、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只能是超越资本,超越现代文明的发展模式,构建全新的“意义世界”。
二、以马克思主义人学和生态学理论为指导探寻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
陈学明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批判为马克思创立全新的社会制度安排创造了前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贡献不仅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更在于它为人类构建了一个全新的“意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批判性的,更是建构性的,是批判与建构的统一。这个“意义世界”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安排,更是人类摆脱现代性危机后实现的全新的存在方式。
(一)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包含人学和生态学两个维度
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构建的“意义世界”包括全面发展的人、劳动回归成为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质公平、自由人的联合五个方面[3]3。他认为这五个方面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有机统一体,是人类社会的应然状态和价值目标。实现了这些具体目标的社会也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类的一种全新的存在状态和社会模式。只有在这种存在方式中,人才能够真正实现人内在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和天人关系的和谐。这五个方面实际上蕴含着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人学和生态学两个维度。
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核心层面是“以人为本”,“意义世界”能够消除人的内在紧张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人学维度。陈学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诠释了人本思想。他认为提倡“以人为本”,首先要搞清楚“以什么样的人为本”。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以人为本”,一定要区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观与中国传统的人本观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权观。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应该是“以总体的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本”。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是对当代社会“人的异化”的扬弃,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说:“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4]在陈学明看来,马克思真正认识到人的本质在于人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不是抽象的空想的全面性,而是在现实的社会关系和观念关系中体现的全面性。要真正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就必须要在现实社会关系和观念关系中实现人的全面性,也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在社会关系中异化的消除,实现人的全面性,也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在观念关系中的异化的消除,实现人的内在丰富性。陈学明说:“在马克思那里,共产主义既表征一种合乎人性的,即使人的生命真正获得意义的存在模式,又是为保证这种存在模式得以实现而设想的一种特定社会制度安排。”[3]42这种社会制度安排,或者说这种存在模式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他认为《共产党宣言》中宣示的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意义世界”中处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特别是个人与集体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这种存在模式中其出发点是“现实中的、有生命的、从事实际活动的个人”,它尊重人的感性存在,因而能够避免集体吞没个人,共同利益排挤个人利益[3]43。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实现了“集体的个人”与“个人的集体”的统一,共产主义社会是充分尊重满足个人自我发展需要的联合体,是充分满足个人本质需要的自由联合体。
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第二个层面是“天人合一”,这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生态学维度。在这里,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消除,实现了真正的、高层次的“天人合一”,实现了“第二自然”的和谐。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根源在于资本的无限扩张本性。自然的承载力是有限的,而资本的扩张冲动是无限的,资本驱动着每一个人向自然索取,每一个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在资本驱动的社会,个人和企业如果不按照资本逻辑运作就无法生存。正是资本,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并可能导致人类的毁灭。陈学明认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正确地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资本的扩张,而且从根本上找到了自然危机的解决之道——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自然主义”和“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的统一,是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它超越了中国传统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因为中国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农业社会的“天人合一”思想,它建立在反对现代化和工业化基础之上,实际上是浪漫主义的幻想;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更加彻底,要回到无知无识、懵懵懂懂的原初社会当中去,这种“天人合一”是排除了人性回复到动物性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缺失了人的天人合一”,当然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共产主义的“天人合一”是高层次的、真正的天人合一,它并不简单否定工业化和现代化,而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最终超越这种发展模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天人合一”既不否定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就,也不停留在如今的发展模式之上,而是要超越这种发展模式。陈学明认为:“马克思基于他的感性活动原则和实践思维方式,用其毕生的心血,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人类正确地处理与自然界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确立了基本原则,从人与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角度为人类构建了一个‘意义世界’。”[3]32-33共产主义的“天人合一”既能够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满足人的本质需要,也能够消除人和自然的对立,是最高层次的、具有可行性的天人合一。
(二)陈学明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了当今影响甚大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的生态观
陈学明首先回应了二战后影响很大的生态中心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批评。在他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的思想的批评是站不住的。他认为“人造的自然”或者说“第二自然”是“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必然性的体现”,“把自然界与‘好’,而把技术、人类文化与‘坏’联系在一起是错误,人类完全能够创造出一个比自然给予的世界更好的世界”[3]36。所谓“第一自然”是“好”的,经过人改造的“第二自然”是不好的观点是肤浅的。他坚持人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只能是按照“人的尺度”,而不可能按照其他的尺度,如“动物的尺度”。生态中心主义者完全抛弃“人的尺度”,否定“第二自然”,幻想回到不受人影响的“第一自然”的状态中去,在逻辑上说不通,在现实上不可能。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坚持“人的尺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正确的,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也只能是立足于“人的尺度”。
与此同时,陈学明也不赞成后现代主义者看待资本、工业、科技和现代化的方式。陈学明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观点认为:虽然我们要深刻地看到当今社会的种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驱动的以工业和科技进步为显著标志的现代化带来的,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工业、科技、现代化乃至资本的历史合理性。否定它们的历史合理性无益于人类找到解决当今社会危机和自然危机的道路。后现代主义者的反现代性的批判只能是无力的呼喊,而不是真正解决的办法。
(三)陈学明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方面,陈学明的探索是立足于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后半期社会发展的新实际来思考人类存在方式的应然状态的,这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立足于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不同。在20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以更加复杂的方式存在,资本主义阶级的统治披上“合理性”的外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更加严密和隐蔽。与此同时,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现象以更加严重和更加复杂的方式存在于现代社会。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人与自然的紧张,在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变得更加严重,以致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陈学明认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必须要重视和发掘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意蕴和生态学理论意蕴,结合20世纪后半叶至今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吸引广大的无产阶级为构建新的社会制度安排和人的存在方式而奋斗。
另一方面,陈学明在探索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的时候能够参考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为他的思想提供了现实资源,所以他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汲取了很多中国的实践经验。他始终怀着对人类命运的关切来考察中国道路问题,认为中国道路将对人类文明的全新发展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他认为,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在于他是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条道路不承认资本是永恒的,只承认资本的历史合理性。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注重把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结合起来。总之,中国道路只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利用资本发展生产力,不以资本的无限发展为目标,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陈学明认为,这条道路能够规避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天人关系和人内在关系的扭曲,能够为现代化所困扰的全球发展提供一条新的路径。
三、以全球性的视野审视中国道路的意义
陈学明所进行的思考和探索可以归结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另一个问题是“人类向何处去”。而且,他始终是在“人类向何处去”的视域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陈学明认为,中国正在践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对中国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可能为人类开辟一条全新的道路。这条道路是通向人内在关系、人际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和谐统一的共产主义存在方式的。中国道路为人类由当前的“现实世界”向马克思主义所构建的“意义世界”的迈进提供了一条现实路径。中国道路之所以有此可能,正在于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为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危机的根源并建构了一套全新的科学的“意义世界”。马克思主义不像很多资本主义拥护者和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的那样已经“过时”和“消亡”,更不是中国发展的“负面资产”,而恰恰是中国道路优越性的根本所在,是中国道路具有普遍意义的根本所在,是人类希望之所在。
在陈学明看来,揭示中国道路的全球意义,首先是要坚定中国道路的自信,如果连自己对自己的道路都不自信,何谈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启示和借鉴呢?要坚定中国道路的自信,必须是要客观理性看待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既不能有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对西方文明的偏见,也要清楚地看到,现代西方文明确实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他说:“上个世纪后半期由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弊端所引发的危机此起彼落,一场对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和反叛已在西方世界展开,现代西方工业文明决堤了。”[3]77陈学明警告:“如果我们把现代西方工业文明照搬过来,我们要付出重大代价,而这种代价我们是承受不起的,很可能西方文明中优秀的东西我们还没有充分享受到,而代价却已把自己葬送了。”[3]76-77
陈学明认为以资本主义发展为内在驱动力的西方现代化各种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资本破坏了人内在关系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以及天人关系的和谐。因此,中国道路一定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对待资本,而不能任由资本无限制的膨胀。这样具有全球意义、普遍意义的中国道路只能是发展资本、利用资本并节制资本、超越资本,最终终结资本的道路。中国人民并不能被动地等待资本“历史合理性”的消失,而应该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精神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主动地消解资本的“历史合理性”,提前为资本的终结做好准备。这是中国道路的独特之处,也是中国道路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所在。
那么,在今天中国人究竟应当如何看待资本呢?陈学明认为,回答这个问题同样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第一,我们应当看到,资本给当今的中国带来了经济增长、物质财富增加等正面效应,同时也要看到资本有着愈演愈烈的负面作用。第二,我们还应看到,我们尽管可以限制资本的一些负面作用,但改变不了资本的本性,解决现代性的危机只能是消灭资本本身。第三,我们应当看到,资本目前在中国的存在只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并不具有永恒的合理性,我们最终要实现对资本的超越。要看到资本当前的“历史合理性”,但绝对不能把资本原则和资本逻辑绝对化,把资本的合理性永恒化,似乎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离不开资本的统治。最后,我们不能等到资本的合理性“自动消失”才去超越资本,而应该在现阶段就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最终消灭资本,实现新的社会发展模式做准备。中国道路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区别正在于中国道路在利用资本驱动发展的同时是明确超越资本、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的。有没有超越资本和现行发展模式的勇气,有没有实现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安排和新的存在方式的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
陈学明同时强调,不可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看作是截然分开的两个阶段,而要用辩证法的观点看到资本的扬弃正在资本的发展过程之中。他说:“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最终是要扬弃异化的,但是这种扬弃正是孕育在异化的生成与展开的过程之中。马克思并不把异化的消灭寄托在等异化充分展开,完全与人性对立之后,而是强调当异化还具有必然性、人的存在还离不开异化之时,已经把握了历史必然性的人类就应该思考和着手去扬弃异化。对待异化是这样,对待资本同样如此,我们应当把资本的生成与展现同资本的扬弃视为是同一个过程。”[5]211他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在现代性上还不如西方国家充分发展的中国,中国人面对资本的态度具有“复杂性”。“我们既要考虑如何充分地利用资本,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正面效应,又要思考如何不能像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那样去利用资本,而是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又要超越资本,在利用资本与超越资本之间保持一种合理的张力。”[5]216他认为可喜的是,中国政府目前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正是在努力地保持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的一种合理的张力,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和贯彻资本原则和资本逻辑。而这正是中国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体现。
总之,陈学明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以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发展的目标,对资本的利用和发展始终保持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警觉,只承认资本的历史合理性,能够把利用资本和超越资本结合起来,能够把长远目标与眼前利益结合起来,所以能够不陷入资本无限膨胀的疯狂当中,能够让人类走出欲望无限膨胀的漩涡,是人类通向理想的社会状态和存在方式的一条现实路径。
综上所述,陈学明是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与执着情怀,怀着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困境的强烈关注,怀着对运用马克思主义阐释现代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强大冲劲以及人类必将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顺利前行的乐观主义精神,进行他的理论探索的。他的追寻和探索既有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术立场,又有着热切的现实关怀;既有着对中国道路的坚定自信,又有着对人类命运的乐观展望。正是这样的气质,使得他的著述洋溢着浓郁和蓬勃的生命气息和精神跃动。
陈学明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世界理论紧扣时代主题和社会现实,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以资本为原则的现代社会的批判,积极吸收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成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成果,以马克思主义人本观和生态观为核心构建了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世界”。他始终是在“人类向何处去”的视域下思考“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层问题的,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对中国道路的探索紧密结合起来。这使得他的思考一方面有全球性视域的理论高度,另一方面也有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支撑。他认为,中国道路能够为解决“人类向何处去”这样的全球性问题提供一把钥匙,中国道路也因而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并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理论论证,他的理论探索既有着对当代文明社会种种弊端的深切忧思,也有着对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实现的乐观主义精神,更有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因而,他的理论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陈学明.情系马克思:陈学明讲演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80.
[3] 陈学明.永远的马克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6.
[5] 陈学明.中国正道[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Exploring "Meaning World" in Marxism ——ConsiderationsaboutProfessorCHENXueming′stheoryof"MeaningWorld"
PANG Guijia
(School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SchoolofMarxism,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Beijing100091,China)
Professor CHEN Xueming tries his best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of Marxism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intending to solve the internal relation between contemporary social men,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s and the high tens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On the one hand, he adopts the dissimilation of Marxism to criticize contemporary society, revealing the distortion of humanity and tensions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that capitalist society brings.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humanology and ecology theory of Marxism and combining contemporary West and the reality in China, he attempts to explore "Meaning World" in Marxism and forms his own complete "Meaning World" theory. At the same time, he adopts a perspective that puts human future and destiny in the first place to reconsider the social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 thinks that Chinese Road can provide a realistic approach for setting up a new existing mode of humans.
Marxism;theory about dissimilation;CHEN Xueming;"Meaning World";Chinese Road
2016-09-06
庞桂甲(1986-),男,安徽庐江人,山西农业大学讲师;中央党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10.16396/j.cnki.sxgxskxb.2016.12.004
A8
A
1008-6285(2016)12-00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