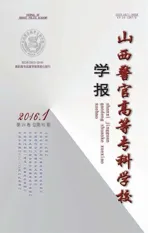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2016-04-12□杨开
□杨 开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法学研究】
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杨开
(南京师范大学 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所根据的观点如何,直接影响着中止犯的成立范围。因此,就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进行前提性研究有着重要意义。一方面,中止犯之所以减免处罚是因为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的减少;另一方面,对于中止犯刑事政策的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因此,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是以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减少为内容的刑事政策说。
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刑事政策说;法律说
根据我国《刑法》第22-24条的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相较于未遂犯与预备犯,我国刑法对于中止犯作了更为宽大的处理,其依据是什么,学理上有不同的学说。本文试图通过分析学理上的不同学说,探究减免处罚中止犯的根据,对认定中止犯的成立进行最基础的思考。
一、比较对象
中止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学理上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比较,在对象选择上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是将中止犯与既遂犯相比较,第二种思路是将中止犯与未遂犯、预备犯相比较。[1]针对第一种思路,笔者认为中止犯与既遂犯相比较,无论是在社会危害性还是在人身危险性方面都减少或消灭了,这似乎可以作为减免处罚中止犯的原因。但在笔者看来,这种观点并未从根源上认识到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而只是停留在表面。无论是预备犯、未遂犯还是中止犯相较于既遂犯而言,法律上都对其处罚较轻;而中止犯相较于预备犯与未遂犯处罚较轻。因此,研究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最恰当的比较对象应该是预备犯与未遂犯。因此,笔者认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的比较对象应是预备犯与未遂犯。
二、减免的根据
(一)学理上的观点
学理上对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有不同的学说,大体上可以分为“刑事政策说”、“法律说”与“并合说”。
1.法律说
法律说可以分为违法减少说、责任减少说和违法及责任减少说。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违法及责任减少说只是基于违法减少这一认识的责任减少,与违法减少说实质上并无不同。”[2]因此,笔者将着重讨论违法减少说与责任减少说。
2.违法减少说
违法减少说认为,中止犯罪的行为人其违法性减少,因而减免对其的处罚。违法减少说主张把故意作为违法性要素,在此前提下,认为事后的中止行为变更了违法性的评价。[3]理论上对于将故意作为违法性要素还是有责性要素还存在争议。对此,日本学者曾根威彦认为“无论是行为人自己实施中止行为,还是由第三者阻止结果的发生,在一旦发生的危险走向减少这一点并无不同。”[4]
3.责任减少说
责任减少说认为,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在于其责任的减轻。责任减少说内部比较复杂,主观主义认为:中止犯比起未遂犯来,行为人的反社会性和性格危险性要小,所以责任要小。道义责任论认为,既然行为人选择放弃犯罪,就说明非难可能性降低。规范责任论则强调:实施犯罪的决意属于责任要素,事后撤回其决定,使得非难可能性降低。[3]尽管责任减少说内部存在分歧,但一致认为行为人的责任减少或非难可能性减小。但是,由于我国并未对中止犯的动机做出要求,因此对于不是出于悔悟、怜悯等动机而中止犯罪的行为人来说,仍有成立中止犯的可能。但在责任减少说看来,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并没有降低。
4.刑事政策说
该说认为,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是刑事政策的需要。关于刑事政策说,内部又有不同的分类标准。*如张明楷认为,刑事政策说分为一般预防政策说和特殊预防政策说。参见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37。如程红认为,刑事政策说分为“黄金桥”理论、恩典褒赏说、刑罚目的说以及责任履行说。参见程红.中止犯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26-27。笔者认为,刑事政策说可以进一步分为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说和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说。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说最为著名的论述便是德国学者李斯特的见解。他认为犯罪中止为行为人架起了一座“黄金桥”。特殊预防政策说认为,对中止犯减免处罚是因为其人身危险性降低或消灭,所以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而相应地减轻或免除处罚。笔者不赞成将刑事政策说分为“黄金桥”理论、恩典褒赏说、刑罚目的说以及责任履行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点理由:第一,无论是基于一般预防的刑事政策的考虑还是基于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的考虑都可以看作是对于行为人中止犯罪的一种奖励与褒赏。因此将恩典褒赏说作为刑事政策说的一种并不合适。正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所说:“为了奖励这种中止行为,刑法向行为人显示了‘只要终止,便对未遂犯之刑予以必要性地减轻或免除’这种恩典。因而该观点又称为褒奖说。”[2]281第二,刑罚目的说将中止犯的立法理由求之于刑罚目的的消灭,即在行为人中止犯罪的场合,立法者视之为所意图的刑罚目的得以消灭,[5]但是这种观点似乎与现实情况并不相符。因此,笔者认为将刑事政策说分为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的刑事政策说更为合理。
自刑事政策说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德国学者耶赛克指出:“对于中止犯即便有不处罚的规定,但在决定性的瞬间却并不能影响行为人的决定,更何况居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了解这样的规定。法院实务表明,在中止犯的情形下,所有可能的动机均发挥不同程度的作用,但因考虑免除已经实现的刑罚而中止犯罪的,则从来没有过。”[6]耶赛克也指出,若认为刑事政策说是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唯一根据,则会产生两个问题:第一,对于不知道该刑事政策的行为人是否同样适用减免处罚的规定;第二,事实上,又有多少行为人是因为纯粹意义上的刑事政策对于行为人的这种奖励而中止犯罪。不可否认的是,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对知道政策的行为人适用减免处罚的规定,而对不知的行为人则不适用,有违平等地适用刑法这一基本原则,背离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基本的法治观念。至于第二个问题,刑事政策说的提出者似乎是以“人是理性动物”为前提的。但是设想一个行为人进行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想将犯罪进行到底的。即使其中止犯罪,可能会有不同的原因,但绝不可能是纯粹基于刑事政策上的考虑。也有学者指出,作为刑事政策说的起源国家的德国,对犯罪中止是不处罚的,因此,犯罪中止制度可以说是犯罪人改悔的“黄金之桥”。相反地,在我国,对于中止犯并不是不处罚,而仅仅是必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已。因此,对于行为人而言,犯罪中止是犯罪人迷途知返的“银桥或者铜桥”而已。[7]
(二)笔者的观点
笔者认为,对于刑事政策说的理解不能停留于表面,而应深入其中,探究在刑事政策上减免对中止犯的处罚背后的原因在于什么。我国学者李立众认为“立法者之所以能够采取这一刑事政策,是以行为人客观上消灭了既遂危险(违法性减少)、主观上出于本人意愿(有责性减少)为事实基础的。”[1]刑事政策上对于中止犯作出宽大处理是因为行为人违法性减少或有责性减少或违法性与有责性减少。如此看来,在这个意义上的刑事政策说与并合说*并合说包括违法责任减少说、刑事政策说和违法责任减少说、刑事政策说和违法减少说、刑事政策说和责任减少说。在这里笔者指的并合说是最广意义上的并合说,即刑事政策说和违法责任减少说。的不同在于,刑事政策说是否可以作为单一的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在笔者看来,并不存在行为人违法性与有责性都没有减少,仅根据刑事政策而减免处罚的情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并不能成立中止犯,也就不能减免对其的处罚。
因此,无论行为人是否知道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还是行为人是否出于刑事政策而中止犯罪,都不影响在成立中止犯的情况下对行为人减免处罚。
犯罪中止分为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与造成损害的中止。结合上文对犯罪中止比较对象的分析,笔者认为可以有四种比较的可能:造成损害的中止与预备、造成损害的中止与未遂、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与预备和没有造成损害的中止与未遂。由于预备与未遂的区分标准为着手,而着手意味着行为人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紧迫的危险。因此在预备的情况下,行为人并没有对法益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另一方面,未遂可以分为造成一定侵害结果的未遂与未造成侵害结果的未遂。所以在上述四种情况中,造成损害的中止与预备两者之间进行比较来说明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是最有意义的。因为在犯罪预备的情况下,行为人没有着手,即没有对法益造成现实紧迫的危险;而造成损害的中止的情况下,行为人已经着手且造成一定损害。根据法律的规定,对于预备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那么在对预备犯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假设行为人触犯的罪名只有一个量刑幅度),而中止犯应当减轻处罚的场合更具有比较的意义。在笔者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中止犯的处罚轻于预备犯的原因在于:第一,行为人的违法性减少;第二,行为人的有责性减少。
1.中止犯的违法性
笔者赞成从达成既遂的盖然性的角度来论证中止犯的违法性轻于预备犯的观点。我国学者王昭武认为:“预备犯之所以未能进一步发展至试行阶段乃至既遂,完全是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被‘偶然地’阻止。[4]换言之,行为人从犯罪预备发展到犯罪既遂的盖然性高于犯罪中止。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中止犯造成了损害的结果,但损害不会继续扩大至既遂的程度,只是停留在这一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的可能性。相较而言,预备犯尽管没有着手,但其向既遂发展仍存在可能,因为其是被打断的,而不是自愿的。因此,从盖然性的角度来看,中止的违法性少于预备的违法性。不难想象,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驳:造成损害的中止毕竟对法益造成了现实的损害,而预备却连对法益现实紧迫的危险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预备的违法性少于中止的违法性。笔者认为,如果是从现实对法益的侵害的角度来看,上述观点会是有力的反驳,但是在这里要明确两点:第一,笔者这里讨论的场合是最极端的情况,对于预备犯完全有可能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第二,从盖然性的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但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并不仅仅是在于其违法性,还在于其有责性。
2.中止犯的有责性
这里所说的有责性是从行为人特殊预防的角度去考虑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小。张明楷指出“这里所称的非难程度减少或责任减少,并不是指行为人对已经造成的违法事实的责任减少(这种责任是不可能减少的),只是意味着对行为人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的减少。”[8]同样,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驳:倘若行为人并不是出于“金盆洗手”的原因中止犯罪,那么行为人的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并没有减少。笔者认为,虽然从一个长时间观察行为人的角度来看,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仍然存在,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并没有减少;但若仅仅从该次特定犯罪的角度来看,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减小,其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减弱。在犯罪预备与造成损害的犯罪中止的场合,成立犯罪预备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明显大于犯罪中止的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因此,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减少。另一方面,笔者认为,若探究刑事政策说的根源就会发现,制定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刑事政策正是因为行为人违法性与有责性的减少。因此以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减少为基础的刑事政策说与违法责任减少的并合说并无本质区别。正如张明楷所说:“违法性减少说与责任减少说,都直接左右犯罪中止的具体成立条件;政策说或许难以直接左右犯罪中止的具体成立条件,但有利于从宏观上放宽犯罪中止的认定”。[8]事实上刑事政策说与法律说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政策说是法律说的基础,法律说是政策说的具体体现与补强。[4]
三、结语
中止犯的成立与否对行为人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决定着是否对其适用减免处罚的规定。而探讨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有利于更好地认定中止犯的成立。因此,笔者探析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对中止犯的成立作最基础的思考。中止犯减免处罚可以说是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我国之所以制定这一刑事政策正是基于行为人违法性或有责性的减少。因此,笔者主张以违法性或有责性减少为内容的刑事政策说为我国对中止犯减免处罚的根据。
[1]李立众.中止犯减免处罚根据及其意义[J].法学研究,2008(4):126-143.
[2]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2版.王昭武,刘明祥,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282.
[3]周光权.刑法总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6.
[4]王昭武.论中止犯的性质及其对成立要件的制约[J].清华法学,2013(5):71-85.
[5]程红.中止犯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35.
[6]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总论)[M].徐久生,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644.
[7]黎宏.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252.
[8]张明楷.刑法学[M].4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38.
(责任编辑:王战军)
Foundation for Free of Punishment to the Discontinued Crime
YANG Kai
(School of Law,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00,China)
How the ideas that the punishment to the discontinued crime could be reduced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scope of the discontinued crime directly? So it is important to do premise research on free of punishment to the discontinued crime. On one hand, Free of punishment to the discontinued crime is because of the reduction of doer’s illegality and liabil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understanding to the criminal policy on discontinued crime can not be apparent. So the foundation for free of punishment to the discontinued crime is the statement in criminal policy that the reduction of illegality and liability is the content of it.
discontinued crime; free of punishment; foundation; statement in criminal policy; statement in law
2015-11-11
杨开(1991-),女,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
D924.13
A
1671-685X(2016)01-002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