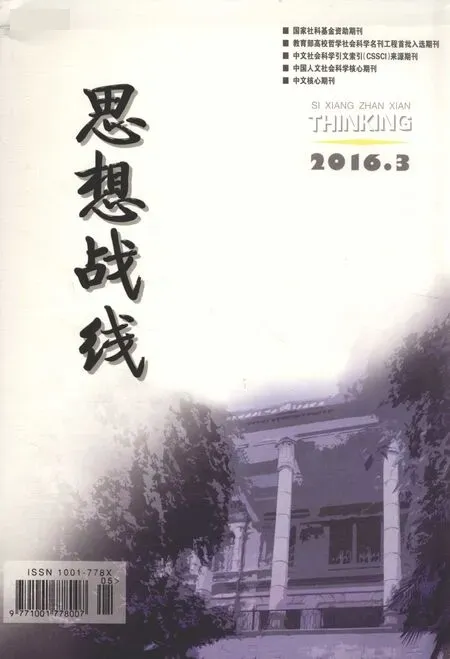在经世与逍遥之间:“儒道互补”心灵结构的外史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2016-04-11董云川沈云都
董云川,沈云都
在经世与逍遥之间:“儒道互补”心灵结构的外史逻辑及其当代意义
董云川,沈云都①
摘要:目前学界关于“儒道互补”问题的研究,均致力于在哲学上寻找其内在的基础。然而事实上,“儒道互补”并不具有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石,更不成其为一套严格的实践哲学;其仅仅是日常意义上的一种生活变通或实践智慧。儒、道两家各自为对方留了一个“开口”,从而保证了“互补”在实践上的可能性,因此儒道互补的真实经验是“外史”而不是“内史”。辨清这一点,对我们重新反思现代生活的一维性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儒道互补;外史;实践智慧;孔子;庄子
海内外学界关于“儒道互补”问题的研究,始终面临一个聚讼不休的理论难点:儒家和道家在话语上实现体系性整合的基础,到底是什么?这一点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困难,是因为:要整合儒道,就不可避免地要把儒、道两家学说,视为某一更高实体(例如“大道”)在具体语境下的两种特殊呈现形式。于是,“寻找‘儒道互补’之哲学基础”的问题,实际上要求研究者在儒、道两家的话语之外,对“大道”本身进行原发性的哲学创述。而无论这个创述能否服人,研究者都已经不是在“寻找”,而是在“构建”了。从而,对“儒道互补”的实然考证,也就转变为一种应然阐发。也就是说,从事这一研究,本身就注定了其研究目的的滑脱。因此,“儒道互补”的内史逻辑,也就是从思想史内部寻找“儒道互补”在哲学上的基点或内核,这一路径在深层次上是自我悖反的。但是,一旦放弃所谓的“理论基石”,承认“儒道互补”在哲学上没有也不需要一个真实的概念内核,而仅仅是人在日常实践中的一种“无奈的变通”,从而把“儒道互补”放在人的日常实践这一“外史逻辑”中来看待,问题将会截然不同。
一、“儒道互补”内史逻辑研究路径的一个个案
冯友兰曾经断言:“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它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页。李泽厚也在《美的历程》中,提及《庄子》对待生命的审美态度正好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一致”。*李泽厚:《美的历程》,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53页。这一论断,在现代思想中率先提出了“儒道互补”的问题。而从文化渊源的角度讲,如董平教授所指出,正是由于西周王制崩坏,导致了“王官之学,散于百家”,才会形成儒、道等东周诸子之学,因此说“儒道互补”具有文化血统同源的基础(例如儒、道等诸子各家均把“大道”作为共同崇奉的一个关键范畴),是可能的。*董平:《“儒道互补”原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问题是,董平教授继而认为,在儒家看来,“大道”既是存在的本体,也是道德的本体,所以儒家的生命价值,必须通过世俗的道德践行来实现;而道家则为“大道”脱去了世间价值的附着,直接把“道”还原为生命本身,即让个体生命“穿越社会的丛棘而实现心灵的自我转向”,因此,人根本不需要世俗性的道德自我完成。这样,儒、道两家的关系,就被描绘成了人的“社会化”与“个人化”这两种“人性本身所固有的两种倾向与能力”,或者“个体在其自身的生活世界中对‘道’进行实践的两种可能的方式或途径”。*董平:《“儒道互补”原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9期。
此论固然有其启发性,但它搁置了一个关键性的论证环节,即:相反未必相成。如果儒、道两家仅仅拥有同一个文化背景或源头,而它们在“大道”的本质和实现方式上的看法相互抵牾,那么,所谓的“儒道互补”是如何“补”到一处去的?这种“互补”对个人生活实践本身的意义何在?除了哲学家能够在“儒道互补”的意义上认识人性的多面之外,普通人还在何种层面上需要“儒道互补”?——总之,我们没有从中看到“儒道互补”的生活性和实践性,因此,这样的“互补”,既不真实,也不迫切。
仅从思想史或“内史”的角度看,北宋理学确实颇多援引道家本体论以补儒家形而上阐述之不足,这也是一个事实。除了周敦颐之外,尤其突出的例子是张载对道家“太虚”概念的借用,其直接的目的固然是对儒家自董仲舒以来把“天”过分实体化和此岸化倾向的一种纠正,以突出“人鲜识天,天竟不可方体”*张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第177页。的超经验性, 把“天”与“太虚”等同起来,从而使儒家之“道”几近于道家之“非常道”;*林乐昌:《论张载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借鉴与融通》,《哲学研究》2013年第2期。但更引人注意的是,此说将道家的形上概念移植到儒家思想体系的内部,似乎使“天”的社会性和经验性变得单薄甚至消弭,这往往被视为“儒道互补”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标志性证据之一。但是,这种表面的靠近,并不能弥合儒道之间本质的分歧。因为在张载那里,所谓“天”或“太虚”的社会性消减,其实是一个假象,他真实的主张是“虚者,仁之源”。*转引自林乐昌《论张载对道家思想资源的借鉴与融通》,《哲学研究》2013年第2期。这与程颢、程颐所说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河南程氏遗书》卷第11)的论述,是相互呼应的。他们都主张,“仁”是从“天”或“太虚”那里直接化育、感应而来,此论实际上把儒家的道德范畴推向本体层面,这与老子“天地不仁”(《道德经》5章)的去道德化的方向,是无法调和的。由此类推,任何一种在思想史的“内史”逻辑中推论“儒道互补”的观点,都应谨慎对待儒道两家之间表面上的概念借用与实质上的方向差异。
那么,“儒道互补”的“内史”逻辑有没有经验验证呢?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元代大儒刘因的“儒家隐逸主义”。在《与政府书》中,他勇于拒绝忽必烈政权对他出仕的邀请,这无疑轰动了当时的学界,以致于陶宗仪《辍耕录》专门杜撰了刘因与另一位儒学宗师许衡之间的一场“争论”:许衡认为儒士不出仕则“道不行”,刘因则反驳说儒士轻易出仕则“道不尊”。*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页。但是,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刘因斥责老子的“退守”实则掩含着某种不露痕迹的自私而狡黠的个人权谋,掩护那些欲迎还拒的奸巧之辈以一己之私践踏道德的秩序;至于庄周“化蝶”则是逃避现世道德实践的痛苦。与之不同,刘因本人的避世,是基于儒士的自尊,而这就需要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刘因的斋号“静修”,典出诸葛亮“静以修身”,暗示了他的隐逸与诸葛亮相似,是为了捍卫儒士精神上的自守和高洁,而不是道家的拒绝现世。*杜维明:《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8页。可见,“儒道互补”在经验上的“例证”往往似是而非。
需要解释的是:一方面,“同源”不等于“互补”,否则东周百家在“同源”的基础上排列组合起来,我们将不知要面对多少种“互补性”,而且这其实没什么实际的价值;另一方面,既然儒、道两家无论是对“道”本身的阐述,还是关于“道”在人与万物之间实现同一的方式,都迥然不同,那么,即使儒道两家都承认“道是人性与世间万物的同一”这一点,但显然,他们对这一点的理解完全不同,这也就不足以为“儒道互补”提供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何况,如果抛开“道”在人与天地万物之间实现同一的具体方式不谈,那么这个“同一”,还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吗?
对此,董平教授显然是有所察觉的。所以,他在论文的结尾部分突然表现出一种峰回路转的新倾向,即:“个体随其实际生活境遇的转变,关于‘道’本身的价值认同也可能随之而发生转变”,他说这才是“儒道互补”的真相。此说的确更切近中国历史上“儒道互补”的真实经验,即把“儒道互补”落实在个体生命上,而不是在哲学观念中。但是,这个观点还是没有摆脱一个困境,即:它暗示,在理论层面还应该建构一个高于儒道两家的新的制高点。不论是由儒入道,还是由道入儒,个体生命在不同境遇中的转换,都不过是“大道”在人与万物相互统一的方式上的转换,而不是“大道”本身的转换。这样一来,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他们所阐发的,就不是“道”本身,而仅仅是“道”的众多运行形态之一,这既是儒、道两家分歧的根源,也可以说恰恰是分歧本身暗示了儒、道两家之上还应该有一个更高的“合题”来统一这一分歧。那么,儒道之间与其说是“互补”关系,不如说是“鹬蚌”关系,只能期待某个“第三方”来化解二者的对立。最反讽的是,到了这一步,持此论的学者往往只能亲自站出来充当这个高于儒、道的第三方,因为纵观中国思想史,这样的第三方根本不存在。
究其实,问题出在: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回答,“儒道互补”到底是在什么意义上的互补?如果它是一种学术结构或思想结构上的互补,那么,当我们无法找到这两大体系在核心范畴“道”(既包括“道”本身究竟是社会实践性的还是纯粹个人化的,也包括“道的实现方式”问题)上的根本共识的时候,就只能像董平教授一样,同时承认儒、道的片面性,从而使儒道“互补”于“作者我”的第三方言说。
但是,如果它不是仅对哲学家成立的互补,而只是“生活中的人”在日常心灵处境中的互补,那么,它就未必需要一个严格而真实的概念内核,也不需要围绕这个内核建立起一套完整、严格的论证系统,而只要允许中国士人能够自由出入于儒道之间,也就够了。
这就需要两个条件,也是本文的两个假设:首先,儒家和道家都向对方开一个“口子”,作为人们“出入儒道之间”的准行证,而不需要为两大思想体系勉强找到一个哲学上妥协或整合的基点。其次,把“儒道互补”仅仅视为一个心灵结构,意味着“我”在统合外来经验的时候,有一个可儒可道、可彰可隐、因时而化的双向心灵,所以“儒道互补”不是发现一个高于儒、道的新的精神顶点,而仅仅是把儒、道两种立身态度,在具体个人的心灵经验中变通地衔接起来。
如果我们能够核实这两个假设,那么我们也就可以断定:“儒道互补”的确是中国士人的实践智慧,却并非一种“实践哲学”。
二、由道入儒:庄子对现世人伦的不否定态度
道家的理想是“逍遥”,它要求“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庄子·逍遥游》),认为人只有弃绝功业,物我两忘,才能正于天地,无羁无待,乘御六气,以游无穷。所以,一般来说,道家,特别是道家的“逍遥”思想,应该是否定人的社会维度的。那么,道家的“逍遥”能够在哪里开一个“口子”通向儒家呢?
在通行的观点看来,道家之所以选择“出世”,乃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世界丑陋且不可改化。尽管道家思想家之间也有分歧,例如庄子的“鲲鹏搏风”倾向于对世俗现实的主动超越与摆脱,而郭象的“物任其性”*郭庆藩:《庄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页。则倾向于对纷纷世事的被动承受与顺应,二者固然有实质性的区别,有学者认为这是道家学派内部“逍遥”思想的两个不同方向;*刘笑敢:《庄子与郭象——超越的逍遥与足性的逍遥》,2005年洛杉矶“Engaging in Freedom”研讨会交流发言稿。但是,就他们两派对现实世事的失望态度和“不干预”立场而言,则似乎是一致的,这一点也长期被认为是“逍遥”思想的前提。这种态度与儒家“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扬厉之风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现世情怀,其迥异之处,判若皂白。
问题是,在现实中,道家的大学问家介入现世功业者,却比比皆是。例如近代道家研究的大师、云南大学教授刘文典,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是老资格的“反封建革命家”;尔后又历任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颇膺俗务之繁;再是顶撞蒋介石,力拒日寇伪职,传为一时之盛;甚而曾经秉持“经世致用”的态度,将其毕生的考据功夫运用于日本研究,以图制夷制寇,气节凛然;20世纪50年代初期,则在全国上下一片欢欣鼓舞的氛围下,宣称要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教授”。*章玉政:《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大师及其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无独有偶,当代另一位杰出的道家哲学研究者陈鼓应先生,一样有强烈的现世关怀,曾经因为积极参与“保钓”运动和组织学生运动而与台湾当局抗争24年之久,同样是昂然入世,奋不顾身,颇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醇儒”之风。
由此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猜测:道家的积极入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那么道家思想内部有没有包含着鼓励或至少谅解入世的因素,从而为刘文典、陈鼓应等人提供文化上的可能性?
其实,原初道家对现世的鄙夷态度,可能被后世所夸大和绝对化。例如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德经》34章)即大道是弥漫、流布在世间一切角落的,而世界本身的意义就在于运承和发扬大道。庄子答东郭子的著名言论“道在屎溺”(《庄子·外篇·知北游》),也表明,即使世界上最微贱如屎溺者,“道”也运行其中。这些思想,与儒家“道不远人”(《中庸》36章)的论断,有相互切近的地方,都在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对现世日常生活的肯定和重视。况且庄子对中国人的某些基本人伦也至少保持着认可的态度,而后人把这些基本的思想支点完全划归儒家,其实不妥。例如庄子说:“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庄子·人世间》)人只能在“爱亲”和“事君”等等社会秩序之下,才能“安命”;甚至他断言:“养亲”,也就是赡养父母,乃是个人“养生”的一项重要功夫。(《庄子·养生主》)也许正是因为有这些鼓励或至少谅解“入世”的思想因素,所以在后来的道教内部,甚至曾经出现过净明道这样的流派,直接以“忠孝”等典型的儒家“入世”话语来重新建构道家的教义。这些都至少说明,从一开始,道家就并不完全弃绝现世,也不否定现世对于“道”的论证价值,而仅仅是不主张人们完全陷溺于现世的功名之中而已。
在这一点上,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庄子·逍遥游》开篇的“大小之辩”。“蜩”和“学鸠”等作为“小知”或“小年”而嘲笑鲲鹏的辛苦和忍耐,后者在“九万里风”未起之时,先要“培风”,必定要等到“去以六月息”,方能搏风而起,是把自身置于现世的经验性条件之下,从而达到了“大知”或“大年”(《庄子·逍遥游》)。所以,如鲲鹏一般在现世或世俗的经验世界中坚韧而奋起,尽管对于庄子来说仍然停留在“有所待”的境界,并且相对于世界之大,仍然不过是毫末之微,远不能达到“其远而无所至极”的终极性精神绝旨;但是因为其大,相对于蜩、鸠、朝菌、蟪蛄等之小者,也为庄子所肯可。这也大致表达了现世日常世界在庄子价值光谱中的位置。
与之不同,那些弃尘世于不顾的“出世”主张,在庄子看来,反而不一定妥当。弃世而出,是为“隐士”,如《论语》中记载的荷蓧丈人。这些人虽然“身在江海之上”(《庄子·让王》),离群索居,得“大林丘山之善”,但是在儒家看来,他们搁置自己在现世间的基本人伦谱系,从“人之为人”的伦常识别系统中把自己硬生生抠离出来,结果“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其实,庄子对隐士的态度也是否定的,这一点,粗看之下也与儒家接近,因为隐士弃绝了前文所提到的“爱亲”“事君”这些基本的立身养生之法,当然也就无从“安命”(《庄子·人世间》)。这就是为什么像中山公子牟这样的隐者,会强烈地涌起一种“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庄子·让王》)的深深的空虚和焦虑。显然,庄子对隐士们的心灵结构之缺乏安顿,有着入木三分的洞见。
当然,与儒家毕竟不同,庄子的“逍遥”与这个此岸世界之间,还是存在一条鲜明的界限。究其根本,最关键的区别,在于庄子的“逍遥”与孔子的“乐处”之间的分歧。《论语》中说,曾点的志向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个想法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认可,甚至说出“吾与点也”这样的话。(《论语·先进》)这段对白,被后人断定为孔子“乐处”思想的经典表述之一。对此,朱熹指出:在这里,孔子的境界是“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因之“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乐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0页。也就是说,孔子或曾点的“乐”,是与天地及世间万物相互充融、流润、和畅的结果,这种“乐”是“在世间”的。但是,庄子对待世间人伦的态度,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人世间》)。所以他在“现世人伦”面前表现出来的,不仅不是“乐处”,反而是一种深深无奈的苦闷。所以,说到底,道家“逍遥”所向往的,还是一种对现世人间的“离去”或“摆脱”,是打破个体对外物的依赖状态(“匹之”)的“无功”“无名”甚至“无我”的自由脱缚。逍遥者留给人世间的,毕竟只是一个蹁跹的背影。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庄子之反对弃世而去的隐士,又与儒家不同。儒家如子路,是比较勇武直率的,所以他对隐士责之以“乱大伦”;而庄子则曲折、委婉得多,因为他打心底里怀疑这个世界是否值得挽救,甚至认为试图挽救世界的这个企图本身就可能导致世界变得更糟,也就是所谓“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庄子·人间世》)。由此看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思想家要么用中庸的“致广大而尽精微”来统摄道家的“逍遥”,*陆长庚:《南华真经副墨》卷1,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1964年。要么用孟子的道德之心来统摄道家的逍遥,*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上)——开放的心灵与审美的心境》,《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说到底都是南辕北辙。实际上,道家在本质上断定圣人或“逍遥者”最终是要摆脱世界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这种摆脱必须是真正精神上的超越和高拔,而不能仅仅是形式上的、廉价的“逃避”。所以他说圣人应该是“隐,故不自隐”(《庄子·缮性》),就是说:你要真是圣人,真能做到“逍遥”,那么你的心灵或精神应该早已从这世间脱化而去,达到了“坐忘”(《庄子·大宗师》)“心斋”(《庄子·人世间》)的境界,以至于“唯道集虚”,自由自在。这样,你也就完全可以继续从容地栖居于这个纷闹的人间,并与之相望相安,却不受“贪”“智”等世间成心和机心的戕害;而不必多此一举地躲到山林、江湖中去愤世嫉俗,故作高深。
所以,儒家发誓要在人世间重建天下人的精神和人文的故乡;与之不同,庄子眼中“逍遥”的人,他们虽然身处世间,却并不把这尘世看做是心灵上可以安顿的家园。这就不难理解,“逍遥”者在人世间自然而然地摆出了一副云游异乡、“生亦何欢死亦何苦”的模样。也就是说,道家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思想体系里论证或包含过儒家的合理性,更不打算与儒家相互“补”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只不过是说,道家从一开始就抱有并不完全放弃现世人伦的态度,这一点打开了道家亦可“经世致用”的门径。
三、“君子卷而怀之”作为由儒入道的开口
反过来,儒家的思想体系中,同样从一开始就暗含着与其刚烈、奋进的姿态截然不同的另一面。
儒家“我与天理同流”的现世情怀,使他们决心用一己的道德光辉和精神力量,来拥抱并挽救苦难多舛的人世间。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悲剧性自信,加上儒者要独自重建现世精神秩序的大菩提心,尽管足以震撼千年之后的读者,但在彼时彼境之下,却往往是悲壮而无果的。结果,就连个守大门的仓倌,都知道孔子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论语·宪问》)。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庄子》里提到的那只“知进不知却”(《庄子·人世间》)、一力挥臂挡车的螳螂。我们不妨说,这个典故很有可能是道家对儒家的一次充满敬意的嘲笑。
其实,守大门的保安毕竟没有看透圣人,孔子本人并不真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曾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就是说,在孔子看来,史鱼这个人仅仅是“直”,还谈不上“君子”,因为无论现世生活有没有向善的希望,他都只会像箭矢一样笔直不曲;但是蘧伯玉却堪称君子,因为他在现世失道的时候,就把自己蜷缩、藏匿了起来。在这里,孔子已经为儒家指出了一条应对理想失败的柔性道路。但是,后儒显然极端化了史鱼,却错过了蘧伯玉,这才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了。这样一来,庄子锐利地看到,(孔子之后的)儒家“不知却”的人格固然勇壮而高洁,却并非没有它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它在面对失败的时候没有退路,而这种失败的概率偏偏又是极高,因为儒家用个人道德光辉来改化整个世界的理想从一开始就过于宏大。大约与庄子同时代的儒家人物屈原,在政治失意和理想受挫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正是这种乏力和惊慌:“浮云陈而蔽晦兮,使日月乎无光;忠臣忠而欲谏兮,谗谀毁而在旁。”(《楚辞·七谏》)最后,当他所依持的个人道德光辉被证明不足以照彻人世间的浓厚黑暗时,这位语言大师只能用投江这一无言的方式,来承认其精神结构的坍塌。从此以后,“芳草美人”就成了儒家的一个深深的无奈,因为屈原之死证明了孔子之后退化了的儒家的短处:追求成功无门,克服失败无力。
直到屈原死后大约400年,儒家“知进不知却”的性格,在遭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惨痛挫折之后,才终于断折式地趋向了“却”的维度,那就是东汉的党锢之祸。士子们直言上谏要求杜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引发了外戚和宦官的全面报复,致使一大批文坛、学界耄宿遭到杀身甚至诛族的厄运,一时间血色染红了文坛。*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21页。至此,自比“芳草”却横遭犁锄的儒生,在屠刀的引导下不得不“却”,终于大部队“却”到林泉之下,开始了儒学史上一个隐遁江湖、“卷而怀之”的时代。直到这时,孔子关于“君子”的辩证预言,才以最不幸的方式重新获得验证,尽管是以孔子所反对的“隐逸”形式。
反观道家的“逍遥”。其实根据学者的考证,目前所见最早使用“逍遥”一词的,不是道家,反而是儒家。*陈鼓应:《〈庄子〉内篇的心学(上)——开放的心灵与审美的心境》,《哲学研究》2009年第2期。但是,恰恰是在道家这里,由“逍遥”而开辟出了一条“以游无穷”的内在超越之路,这与儒家一定要在现世的寻常日用之中实现“性与天道”(《论语·公冶长》)的外在超越之路,二者正好相反。具体来说,在道家,特别是在庄子这里,从现世的“安命”,经由“齐物”而达到超越性的“逍遥”,二者是微妙衔接但又严格区分的二元向度,*刘笑敢:《两种逍遥与两种自由》,《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而儒家则坚持在一元的现世之中达到精神上的“成圣”,所以有意避免道家的这种二元切分。因此,无论黑格尔对孔子的评价有多么愚蠢,他关于孔子是个“世间智者”的判断,如果从“在世的一元性超越”这个意义上讲,则仍然是深刻的。*[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130页。事实上,对于传统中国人士的心灵世界而言,辨别儒家和道家何者更高明是没有意义的,相反,“儒道互补”才是性命交关的平衡结构。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儒家的现世情怀建立在过于崇高的个人道德自信之上,而道家坐忘集虚的“逍遥”理想则恰恰为儒家烁光耀焰、奋袂昂扬、焚身以赴的挺进姿态,铺设了一条退路。士人也因此而不必继续像屈原一样,在现世的黯淡和丑陋面前,除了沉江就无路可去(这也许是中国的思想大师们在屈原之后自杀者为数极少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了“儒道互补”的平衡结构之后,他们可以如苏轼所说的那样“合则留不合则去”,从而成功地卸去了儒家“不成功则成仁”的一维命运。结果,以王阳明为典型,“出入释老、归本孔孟”,最终成为中国士人的一般心灵结构,而笔者同意白奚先生的观点,即:在“释老”与“孔孟”之间,“儒道互补”又充当着“三教合流”的基础。*白奚:《孔老异路与儒道互补》,《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
由此可见,中国士人由儒入道,也和“由道入儒”一样,并不是建立在儒道两家的什么共同理论“基石”之上,而仅仅是因为儒道两家为对方的理论体系各开了一个“口子”。也就是说,“儒道互补”在儒家这一面,也和在庄子那里一样,并没有、也不需要完整的哲学论证,而只有在无奈处境中的灵活、变通。这样一来,儒道两家在各自的文化人格轴心的周围,就“相向而行”地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交集,共享着“经世”与“出世”的种种选项。正是这种变通的态度,不仅使得儒家重新接近于孔子“有道则仕、无道则卷而怀之”的君子本旨,而不是一味地冲撞现实;也不仅使道家能够在现世的人伦社会内部即可“安命”甚至“逍遥”;更重要的是,撇开儒道之分,它使得中国士人在“进退变通”之间既保全性命,又安顿心灵。这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上“超越儒道”的理论开拓,不如说是一种实践上圆融老练的生活智慧。
所以,“儒道互补”不是一个严格的实践哲学命题,相反,它仅仅存在于日用的生活阅历之中,是饱含人生经验的实践智慧。它并不意味着道家承认了“经世”的全部要求,反过来,儒家的“卷而怀之”也不可能全盘接受“逍遥”的旨趣。首先,从道家的方面看,现世的功业无非是“安命”的一个条件,“安命”是为了“齐物”,而“齐物”是为了“逍遥”,这正如本文前面部分所提到的鲲鹏,在“搏风”未济之前先要“培风”一样。所以现世的一切功业都不可视为道家人生的归凭,也不可能为道者的心灵提供最终的归属。同样的,从儒家的方面看,“卷而怀之”不过是一时的权宜,君子在精神上最终的归属还在于经世,所以笑傲林泉、泛舟江湖,只在“穷则独善其身”之时才可取;但只有耿介直声于庙堂、蹈矩行规于殿阁的“慎戒”,才是醇儒的真实理想。所以即使“卷而怀之”,儒家也不可能放弃其在现世日用中实现超越、在“尊德性而道问学”中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境界追求。
再进一步,既然“儒道互补”并没有一个真实的理论内核,那么,哲学家想要从“儒道互补”的生活经验中,追索出“儒道互补”的思想理路或“内史”脉络,就是缘木求鱼。孔子、庄子或者其他儒、道两家的大师,他们仅仅是承认了对方立场在经验上的有效,而没有、也不可能论证对方思想体系的合理性。只不过,正是因为这种相互承认的态度,使得后世的中国士人,在两种无奈——道家不得不践履现世人伦的无奈,以及儒家不得不经常“卷而怀之”的无奈——的面前,可以自由出入于儒道两边而不背弃各自真实的立身态度。所以,“儒道互补”只有实践上的可能性,而没有哲学上的应然性。
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的问题:从哲学或思想发展的“内史”角度上寻找“儒道互补”的理论支点,最后必然发现这个支点既不真实,也不迫切,结果论者不得不亲自出面,以“高于儒道”的姿态来填补自己生硬设置出来的这个法官席。相反,如果仅仅在世俗阅历或人生智慧的角度来理解“儒道互补”的“外史”逻辑,即在没有一个内在的、实践哲学内核的情况下,仅仅从生活日用的变通意义上理解中国士人心灵在应对外物处境变故时的进退张弛,从而获得心灵处境上的平衡和谐,则“心灵”就扮演了儒、道之间权变、衔接的那个关节点。这不仅是中国士人心灵的真实经验,也是在种种人生无奈之下,中国人避免与命运正面撞击的非哲学的、日用的实践智慧。实际上,传统文化人格中那个“济世”与“自济”的微妙的默契,既可以风发扬厉,也可以散发扁舟;既可以“遨游太虚”,也可以“天理同流”。由此可见,中国士人在处理“奋身入世”与“游于无穷”之间张力方面的经验,折射出他们“儒道互补”的双向心灵。
四、结语
今天,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对现代化理解的重心,日渐从“物”转向于“人”。与一个国家有多少飞机大炮、多少国民生产总值相比,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应该具有怎样的心灵结构,而这个心灵结构又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确保人在现代化面前持续地获得内心的平衡和幸福?这是更高层次的现代化问题。
而现代化思想的宗师,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韦伯,对现代化弊病的最严重警告就在于:在现世功利目标之上的一切超越性价值都遭到了“祛魅”,达到目的的手段与目的本身之间的关系被经济学化了的计算思维所置换,人因此丧失了价值审问的意识;这种纯粹数学性的效率原则,居然自行塑造出了一种极度偏执的日常生活的合理性,即“形式合理性”。人对这种不顾一切的“最大化之拜物教”,既没有评价的能力,也没有拒绝的可能,所以这样的合理性不接受怀疑和质问,因此并不是“实质的合理性”。*[德]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06~108页。这样的合理性,导致现代人牢牢陷入计算思维的“铁笼”,饱尝丧失终极价值和在无根性中浮流之苦。
更有甚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大师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与以往所有的“人统治人”的社会不同,在资本社会中运行的是一种“无人”(Niemand)的统治。*[德]霍克海默,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从中产生出一种对社会的“自动顺从(Automation conformity)机制”,人在这种机制的暗中引导下,“沿着符合社会所期望的行为轨道成长起来”。*[德]霍耐特:《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童建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页。继之而起的新批判理论大师哈贝马斯,也断定人的“生活世界”被策略性和计算性的权力与资本系统所“殖民化”。*Habermas,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ume 2,translated by Thomas McCarthy,Boston:Beacon Press,1987,p.388.此外各家各派关于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思想经验不胜枚举,但它们都大体认可:现代人精神困顿的原因之一是现世层面的极速扩张造成了对超越层面的严重挤压,导致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只剩下“现世”这单一向度。美国的公民宗教,致力于在一个“上帝死了”的世界里重新寻找世俗生活中的神圣感,*[美]贝拉:《美国的公民宗教》,陈勇译,《原道》2006年12月。何尝不是这种挤压下的一个反应?
总的来看,正如布迪厄所发现,人不自觉地被卷入现代社会体制之中,由此带来现代社会的“社会性覆盖个人性”的结果,造成了现代人普遍的苦难感。*郭于华:《作为历史见证的“受苦人”的讲述》,《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1期。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于它在人的心灵结构上是“有进无退”的。它以人的独立性作为社会契约和现代宪政伦理构建的出发点,结果却适得其反,把个人空前深重地嵌入到社会网络之中,以至于人们甚至不知道在深深地、然后是更深地“进”入社会之外,还有什么“退”路。在没有指向的匆忙和意义退场的焦虑中,现代人都在“抓紧生活”却都感受不到生活的生动性。
可以肯定,现代社会是一个前所未见的强大社会。这个社会的力量在于它以“个人自由”之名,却使人丧失了自由憧憬“别样生活”的想象,且不自知。所以,现代人比以往任何时代的人们都更加迫切地需要知道自己在现代时空中的处境,而又比任何时代的人们更加难以确切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一需要。恰如弗洛姆所说:现代人都是在追求所谓的“自身利益”的时候,却自己遮蔽了“真实自我(real-self)的需要”。*[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36页。(译文根据E.Fromm,Man for Himself, Rinehart,1947有所改动。)究其根源,正是因为人被这个强大的“现世”所深深地绑缚,所以我们才更加需要一个通往反思的“口子”,以便依靠对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的经验,至少是想象,来缓冲现世的无处不在的焦虑。
那么,假设我们能够在现代语境里,转化和再植“儒道互补”的心灵结构,也许我们就或者能够更加超然地与这个我们未必喜欢的世界相安无事地共处下去,而不为它的功利原则所轻易占据;或者能够在高歌勇进、昂然入世的同时,坚守住内心对微小而生动的生活细节的诗意情怀。并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经世”与“逍遥”之间的自由转换,不一定非要诉诸一个严谨的哲学论证系统,既然它的关键点不在哲学思考上,而在生活实践上。也许,这才是“儒道互补”心灵结构在现代社会中的要义所在。
(责任编辑廖国强)
作者简介:①董云川,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云都,云南大学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云南农业大学“百名”学术技术带头人、副研究员(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