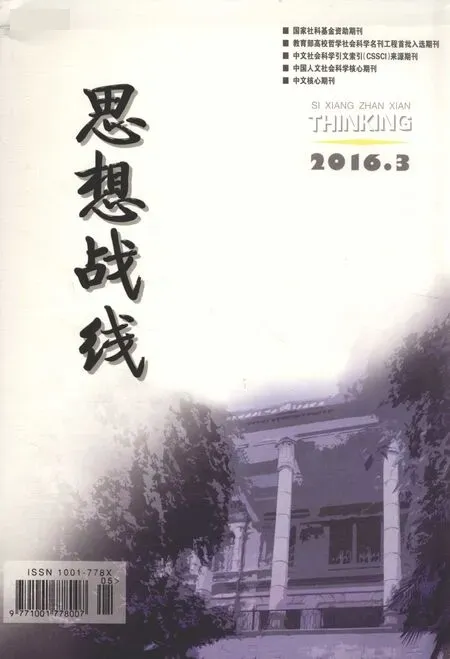谢尔曼·阿莱克西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我表征与身份重构
2016-04-11王玲,普慧
王 玲,普 慧
谢尔曼·阿莱克西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我表征与身份重构
王玲,普慧①
摘要:谢尔曼·阿莱克西通过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的对抗表征,不仅颠覆长期以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殖民话语和刻板表征,而且批判许多其他美国印第安作家沿用和表现的“归家”范式,以及保留地为中心的部落保守主义,表明他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真实形象与身份重构的新视角和立场。阿莱克西进而通过自我表征,真实重构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新型身份——“兼职印第安人”和“现代游牧民”,他们能自如往来于两种文化之间,既不单纯受限于印第安部落传统文化的预期,也不一味附庸白人主流文化的强权。小说为我们研究21世纪美国社会的跨文化接触和关系开辟了新视窗。
关键词:谢尔曼·阿莱克西;《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对抗表征;自我表征;身份重构
一、引言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美国印第安人的民族意识开始空前觉醒,在美国文坛逐渐涌现出一批具有影响力的知名印第安作家,并开启了印第安文艺复兴之路。美国印第安文学的复兴与发展表明,当代美国印第安作家已不再是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附庸者,或是对过去殖民历史的无助哀悼者;相反,他们以更加积极、主动的姿态书写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与现状,对美国主流社会实施的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做出有力回击,努力寻找和确立自己在当代美国社会的新身份与话语权。
生于1966年的谢尔曼·阿莱克西(Sherman Alexie)作为新生代美国印第安作家,已在美国文坛产生重大影响,代表新一代美国印第安作家的立场与声音。2007年出版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是阿莱克西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出版后立即引起强烈反响,荣获包括2007年度美国国家图书奖青年文学奖(the 2007 U.S. National Book Award for Young People’s Literature)在内的共32项大奖。2010年该小说的首个中文译本被发行,译著名为《我就是要挑战这个世界》。小说主要记叙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印第安少年朱尼尔(Junior),只身离开印第安保留地并去到一所白人学校学习和成长的经历。因为朱尼尔从印第安保留地到美国白人社会的跨越,不仅只是地理位置的迁移,而且他同时要面对文化差异、种族歧视和族人误解给他带来的多重挑战,所以这一跨界经历使得他成为既被印第安部落族人误解又被白人主流社会疏离的“边缘人”。在美国白人主流文化的包围与冲击下,朱尼尔的“自识”与“他识”形成鲜明的对比,边缘化的处境使得其“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更为突显。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男主人公的经历多半也是作家本人的亲身经历,可以说阿莱克西本人同样有过这种被双重边缘化的痛苦经历与自我奋争,这样的人生洗礼成为作家日后写作的源头活水。
由于阿莱克西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独特的创作风格,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正引起学界和批评家的关注与争议。首先,该小说所反映的美国印第安人的身份问题是评论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阿莱克西对美国印第安族裔身份与印第安部落传统文化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态度和立场,有别于之前的许多其他美国印第安作家。例如,印第安女作家莱斯利·马蒙·西尔科(Leslie Marmon Silko)是美国“印第安文学复兴”运动中的一位领军人物,以她为代表的印第安作家普遍把“归家”确立为小说的主题,并认为回归保留地、回归部落传统是印第安文化身份认同和种族生存及延续的关键所在。然而,阿莱克西并没有沿袭使用美国印第安文学中这种传统的“归家”范式,其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大多是勇敢的越界者,敢于跨越印第安保留地的界限和打破印第安部落保守传统的禁锢,以开放的心态去了解和接受异文化的客观存在。西方有评论家认为,这体现了阿莱克西试图打破族群和文化边界而主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倾向。
其次,阿莱克西的小说所引起的争议还缘于作家对美国印第安保留地生活状况和印第安人形象的独特描写。美国印第安批评家格劳利亚·伯德(Gloria Bird)认为,阿莱克西夸大了保留地的绝望氛围,强化了白人心目中的印第安人刻板形象,他指责阿莱克西是在利用部落文化取悦白人读者,缺少对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Gloria Bird,“The Exaggeration of Despair in Sherman Alexie’s Reservation Blues”,Wicazo Sa Review,no.11(1995),p.50.但与此同时,西方也有批评家不赞同伯德的这一观点,认为阿莱克西的描写基本上忠实于保留地的现状。如詹姆斯·霍华德·考克斯(James Howard Cox)就与伯德持相反观点,他认为,实际上阿莱克西在其作品中解构并颠覆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建构的印第安人刻板形象。*James H.Cox.Muting White Noise: Native American and European American Novel Traditions, Norma: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2006,p.11.总之,目前西方评论家们对阿莱克西的小说褒贬不一,这也正体现了其小说的研究价值所在,而其小说中对美国印第安人形象的重塑和族裔身份的重构,仍是评论界关注与争论的焦点。
二、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表征”理论
由文化研究之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的“表征”(representation)概念是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霍尔将表征界定为“通过语言产生意义”,这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表征某物,即描述和摹状它;其二是指象征、代表意义。*[英]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6页。霍尔认为,在表征中人们运用各种不同的语言符号与他人进行意义交流,表征过程的有关各方均参与“意义的争夺”,而且表征从来不是中立的,它总是与“权力、统治、偏好、歧视和排斥”密切相关。*Birgitta Hoijer, “Social Representations Theory: A New Theory for Media Research”, Nordicom Review, no. 32 (2011), p. 8.
文化表征在文化身份的确立、族群的认同、自我形象的建构与重塑这一系列过程中均起着重要作用,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自我认知、社会认知和身份形成。社会对某一群体的表征往往影响和制约其他群体对该群体的态度和看法,也影响和制约该群体的自我认同。表征是群体内部以及群体之间互动的结果,并体现出群体之间不均衡的权力关系,是对话语权的争夺,霍尔也称之为“表征政治学”。*[英] 斯图亚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7页。在表征的过程中,强势群体通常掌控更多的话语权,而弱势群体只有通过解构和对抗强势群体对自己的失实表征,才能建构积极、完整、真实的形象与身份。
美国白人主流社会通过对话语权和文化符号的长期掌控,往往主观地给印第安人贴上了各式各样的虚拟标签,建立了一系列关于印第安人形象的“定型化”(stereotype) 的负面文化表征,使得印第安文化被模式化为一种异质文化而被消费,严重影响了印第安人树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获得公正的社会认知。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也激发了美国印第安人主体意识的逐渐觉醒,以阿莱克西为代表的一部分美国印第安年轻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生存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均已发生深刻变革,印第安人只有通过积极、主动的自我表征,而不是被具有文化强权或种族优越感的“他者”(others)进行失实或歪曲表征,才能在当代美国社会中自由和主动地发声,重构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新型形象和真实身份。因此,阿莱克西开始以自己独特的主位视角和立场开展表征实践,不仅批判和颠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形象的定型化、模式化、刻板化的失实或歪曲表征,而且尝试在21世纪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荣的新语境下,去重新定义和自我表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美国印第安年轻一代。
三、阿莱克西对抗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刻板表征以颠覆其殖民话语
长期以来,世人对美国印第安人的认知大部分来自于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形象的表征。例如,1826年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James Fenimore Cooper)的小说《最后一个莫西干人》(The Last of the Mohicans)、1991年奥斯卡获奖影片《与狼共舞》 (Dances with Wolves)、迪斯尼经典动画片《风中奇缘》(Pocahontas)等,这类美国主流文学、影视作品,都试图拼凑式地刻画出一幅幅“什么是印第安人”的画面,常把印第安人的形象和身份片面或贬低地表征为“红皮肤”“部落”“酋长”“未开化的野蛮人”“即将消失的种族”等文化符号。这一系列文化表征并不是单纯、客观的真实记录,而是从美国白人的角度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审视和评价,体现着表征发起者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具体而言就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为主体的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因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并不是美洲大陆的原住民,他们将印第安原住民表征为“嗜血的土著”“未开化的野蛮人”和“即将消失的种族”,旨在为自己在美洲大陆的殖民扩张提供“依据”,这些表征与“天定命运论”(the Manifest Destiny)等表述一样,都是要试图证明白人占有美洲大陆的“合理性”,体现出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的强权思维。而一些看似中立的表征实际上也同样带有种族倾向性,如“红皮肤”强调作为种族归属表征符号的肤色,并将这一形象符号固化为判断印第安人的标准特征。这些过时、贬低、表面化的表征,或是浪漫化或是刻意歪曲、刻板化印第安人的形象,试图突显相对于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而言的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强调美国印第安人永远是处于美国主流文化和西方文明之外的“他者”。这类表征不仅没有反映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面貌与现实状况,而且阻碍他们获取和秉持积极的自我形象与文化认同,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我身份建构造成消极和负面的影响。
在美国主流社会的话语体系中,“消失的印第安人”可以说是印第安人诸多形象中最为核心和根深蒂固的表征。“消失”首先意指印第安人已经在美国白人的殖民扩张中消亡,其次意指印第安传统文化已经没落并终将被白人主流文化所同化或取代。这类表征的刻画向世人传达了这样一种误导的形象信息:印第安人要么已经消亡,要么已经被美国主流社会所同化,在当今美国社会已不存在真正的印第安人。美国印第安文化的存在仅限于博物馆里展出的历史文物之中,或是作为一种被浪漫化的符号偶尔出现于美国文学和影视作品之中,供人娱乐。
在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印第安少年朱尼尔在白人学校的第一次出现给全校师生带来震惊,这正体现了白人对印第安人存在状态的错误认知。如小说中描述,朱尼尔的到来就犹如“不明飞行物”(UFO)或是“大脚怪”的出现一样,令他的白人同学感到惊奇和不可思议,因为他们未曾想到会在现实生活中遇见活生生的印第安人。在他们的认知和意识当中,多数印第安人早已销声匿迹,成为历史和遗迹。阿莱克西在小说中巧妙地揭露了白人的这种认知和心态,并以不同的方式对其殖民话语提出质疑,对其失实表征进行颠覆。例如,当朱尼尔与他父亲谈论感恩节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一直觉得印第安人庆祝感恩节是件好笑的事情。没错,第一次欢庆感恩节时,印第安人与清教徒还是好朋友;但几年之后,清教徒就开始杀戮印第安人。
“嘿,爸爸”,我问道:“我们印第安人感恩的是什么呢?”
我们感谢他们没有把我们全都杀死。*Sherman Alexie,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 New York:Little Brown,2007,p.102.
阿莱克西通过这种黑色幽默和反讽的方式,旨在说明美国建国和扩张的历史实际上也是印第安人被驱赶和杀戮的血泪史。美国印第安人被逐渐排挤到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地域、文化、心理和政治等层面的边缘,并在主流社会的强权话语体系中,被表征和刻画为阻碍现代文明进程的“他者”形象。美国白人殖民者不仅通过残暴杀戮、强制同化的方式,而且通过殖民话语等各种显性和隐性的方式,企图使印第安人及其文化在美国彻底消失。但即便如此,印第安人仍继续在美国的土地上顽强地生存着。小说通过日记形式记叙一位印第安少年朱尼尔孤身前往白人学校学习和成长的经历,正是要揭穿和驳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所持有的刻板偏见和失实表征,强调印第安人并没有在美国社会完全“消失”的事实。
印第安少年朱尼尔在美国白人学校的出现颠覆了“消失的印第安人”这一刻板形象表征,但是接下来主人公还将面临多重挑战。陌生的新环境、白人同学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和种族主义者的冷嘲热讽都让初到白人学校的朱尼尔感到胆怯和不适,但他清醒地认识到,回归印第安保留地只会让他遭受更多的嘲讽,这再次证明印第安人要在美国白人社会立足的无能、窘境和进退两难。因此,朱尼尔没有选择退却和“消失”,相反,在之后的学习和生活中,他发现自己并不比许多白人同学差,不是白人失实表征的“劣等民族”的刻板形象。通过勤奋好学和积极努力,朱尼尔逐渐赢得白人同学和老师们的认可,入选白人学校的篮球队,交到很多白人朋友,白人女孩佩尼洛普(Penelope)还乐意成为他的女朋友。此外,他还发现,美国白人社会虽然很富裕,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疏远,白人家长很少有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而在印第安部落中,族人之间彼此熟悉,关系亲密,多数家庭虽不富裕,但家长却能经常陪伴孩子左右。主人公的跨文化经历和体验使他逐渐认识到,其实两种文化之间有很多值得互相借鉴和彼此学习之处,而生活在两种文化之中的孩子,不论种族、肤色、贫富的差异,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奋斗。因此,仅仅通过文化“他者”模式化的表征去评判一个种族或是其中一个成员优秀与否是非常荒谬的。小说中男主人公的经历还证明:印第安人并不是一些美国白人作家笔下注定要消失的印第安土著、无法在现代社会立足的野蛮人,或被边缘化的“他者”;只要能把握机会,敢于尝试,不懈努力,印第安人也可以在美国主流社会崭露头角,获得认可和成功。
四、阿莱克西以自我表征重构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新型身份
印第安传统和祖先之地是当代许多美国印第安作家用以定义印第安人身份的核心要素,他们认为,背离传统、离开部落都会导致印第安人的身份危机,因此在现当代很多美国印第安文学作品中,逐渐形成和发展了这样一种“归家”叙述范式:离开部落和保留地的美国印第安人在经历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的冷遇和疏离之后,又重返保留地,回归部落传统,通过与本族人的重聚和神圣的部落典仪以弥合内心的伤痛,最终重寻身份和心灵的归属。这种“归家”范式为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N.Scott Momaday)在其荣获1969年度普利策奖的小说《黎明之屋》(House Made of Dawn,1969年)中首创,继而在詹姆斯·韦尔奇(James Welch)的小说《血中冬季》(Winter in the Blood,1974年)和莱斯利·西尔科的小说《典仪》(Ceremony,1977年)中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这些美国印第安作家都在各自作品中试图建构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印第安保留地,把保留地描写为印第安人的传统归属、情感归属和文化身份归属的终极所在。
阿莱克西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不仅鞭挞了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及其文化的种族偏见,而且批判了当代一些美国印第安保守主义者试图回归传统、回归保留地的冲动。在小说中,很多固守传统的美国印第安人把离开保留地视为对部落的背叛。朱尼尔离开保留地前往白人学校的举动,受到本部落印第安人的敌视,许多族人把他视为叛徒,他曾经最好的朋友罗迪也因此与他反目成仇并对他大打出手。像主人公这样离开印第安部落,去美国城市白人社会谋求更多受教育机会、发展机遇和更好生活方式的当代印第安人,通常被戏称为“苹果人”。*“苹果人”暗喻红皮白心,常用于形容那些虽拥有印第安人的族源和外表但却离开印第安部落、背弃其传统的美国印第安人。朱尼尔受到印第安族人的孤立之后,也曾陷入身份危机,并认为自己是一个“兼职印第安人”,处于两种文化之间无处归属。但不论是来自主流社会白人的种族歧视还是来自印第安部落本族人的误解都无法让朱尼尔退缩,因为他深知留在印第安保留地只会让他停滞不前,发展受限,最终扼杀他的梦想与追求。在保留地的寄宿学校里,白人老师皮先生(Mr.P)曾鼓励朱尼尔离开保留地,并忏悔式地直言道:
我刚开始在这里教书的时候,就被教导要用这样的方法教育你们,我们得把印第安人杀死。
你真的把印第安人杀了?
不,不,那是夸张的说法。我们并没有真的把印第安人杀死。我们是要让你们放弃做印第安人,放弃你们的音乐、传说、语言、舞蹈和所有的一切,并不是真的杀死印第安人,而是消灭印第安文化。*Sherman Alexie,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New York:Little Brown,2007,p.42.
在阿莱克西的笔下,印第安保留地并非像很多其他美国印第安作家所描写的如田园诗般美好。作家本人在斯波坎保留地出生并长大,他清楚地知道保留地里存在着印第安人的贫困、酗酒、失业、教育落后等现实问题。在阿莱克西看来,印第安保留地正是美国殖民统治的产物,他曾评论道:
保留区本来是用来作为监狱的,你知道吗?印第安人被迫搬进保留区,在里面老死,从这个世界销声匿迹。但因为种种原因,印第安人遗忘了保留区原本是用来当作死亡集中营,我认为他们(白人殖民者)真正的目的仍然是:杀死印第安人。*Nancy J.Peterson,Conversations with Sherman Alexie,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2009,p.171.
纵观美国历史,正如美国历史经典著作《展望美洲:英国人的北美殖民化计划1580-1640》(Envisioning America:English Plans for the Colonization of North America 1580-1640,1995年)的标题所明示,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上都早已预设和企图实施殖民化,隔离和固化美国印第安人,在空间上只允许他们生活于贫穷、落后的保留地之内,在时间上认为他们只属于历史和蒙昧,难于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独立生存和发展。鉴于此,阿莱克西通过其小说反映自己与众不同的立场和看法:印第安人走出保留地,打破白人所设定的地域界限和文化时空限度,这并不意味着背叛印第安部落与传统,反而象征着反抗和超越白人的殖民统治、种族限定和地域隔离,这也代表当代美国印第安人谋求生存与发展新方式的尝试和努力。
在美国白人殖民统治的数百年间,印第安本土文化已经呈现出一种杂糅性,即便是在保留地之内,印第安人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都因不同程度地受到白人主流文化的冲击和影响而已有所改变。此外,美国印第安人经历了社会、文化和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据统计,1900年时,仅有0.4%的美国印第安人居住在美国城市地区。而到1950年,这个比例增长到13.4%。之后到1990年,已经有高达56.2%的美国印第安人移居到美国城市。*Russell Thornton,“Tribal Membership Requirements and the Demography of ‘Old’ and ‘New’ Native Americans”,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vol.7,no.9(1997),p.33.这些统计数据表明,美国城市地区印第安人口的数量已急剧增长,超过一半的美国印第安人现已移居到保留地之外生活,而这些印第安人迫切需要重新理解和定义自己的“印第安性”或“印第安特质”(Indianness)。因此,阿莱克西不是描写那些生活在贫穷落后、被边缘化的保留地并固守传统的印第安人,而是转而关注当代美国印第安人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美国主流社会的经历与困境,以及他们在多元文化冲击下的转变、调适和发展历程。阿莱克西通过其小说反映出自己的观点:美国印第安人对白人主流社会及其文化的排斥与疏离很容易导致他们回归纯净本土文化的冲动,这种诉求可以理解,但却是不现实的,也难以实现,因为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印第安本土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和现实。
在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阿莱克西蓄意塑造了一个普通印第安男孩而非成年人作为主人公,因为他没有受到世俗的熏染,没有成年人的成见,所以他对外界受教育机会和文明进步的渴望与追求,体现和代表了21世纪新一代美国印第安年轻人的本能需求和纯真诉求。作家特别关注那些生活于两种文化和两个世界之间的美国印第安人,并对二元对立的身份建构模式提出质疑。他并没有使用非此即彼或二元对立的方式,而是塑造了一个真实可信的具有双面性的当代美国印第安少年形象:他时而胆怯,时而勇敢;他时刻牢记自己的族源和归属,并努力建立和维护与部落祖先、传统和印第安性的联系与纽带,但他也像很多白人少年一样,希望努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因此他想走出落后的保留地,寻求平等的受教育权益和发展机遇,尝试现代新生活和异文化体验。只是白人种族主义者和印第安部落保守主义者的双重反对和阻挠,使得他的这步跨越行走得尤为艰难,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追求,而是坚信自己,坚韧地追逐自己的梦想。正如朱尼尔自己所总结的那样:
我了解,我可能是个孤独的印第安男孩,但我并不寂寞。外面有几百万人像我一样离开了生长的地方,追寻着自己的梦想。我知道,没错,我是个斯波坎印第安人,我属于这个部落,但是同时我也属于美国移民的部落,属于篮球队员的部落,也属于书虫的部落……这真是一场大觉大悟。*Sherman Alexie, 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New York:Little Brown,2007,p.217.
小说主人公朱尼尔的跨界经历曾让他陷入身份危机,但与之前的或当代其他的美国印第安作家不同,阿莱克西并没有让主人公重回印第安保留地去寻求身份归属和心灵慰藉,而是让他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学会成长与跨文化调适。当朱尼尔离开印第安部落以后,一方面他在白人学校努力学习,证明自己可以像白人同学一样优秀,另一方面他也试图让部落族人理解他的追求与奋争,重新接纳他,他一直努力谋求与同族好友罗迪重归于好。他尝试用写邮件、绘画、谈心等方式,让罗迪和其他部落族人理解、认可和接受他的自主选择。在之后与朱尼尔的一次谈话中,罗迪这样评价道:
印第安人的祖辈都是游牧民,他们四处游历以寻找食物、水源和放牧的草地。我一直预感你(朱尼尔)有一天会离开,离开我们去走遍天下。你是一个游牧民,你将会游历世界。*Sherman Alexie,The Absolutely True Diary of a Part-Time Indian,New York:Little Brown,2007,p.229.
在遭受白人入侵和殖民统治之前,印第安原住民并没有“保留地”的概念,美洲大陆都是印第安人的家园,而印第安祖先们过着四处游历、打猎放牧的自由生活。但到现代,印第安人已不再是游牧民,他们被白人圈定在狭小、落后的保留地内,偶尔的越界都可能伴随着质疑和风险。但是罗迪认为,朱尼尔敢于冲破保留地的界限去外界寻找更好的机会,他才是当代真正的印第安人勇士。印第安人的家园不应是偏安一隅、贫穷落后、泯灭梦想的保留地,真正的印第安人也不应保守地禁锢于保留地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像印第安人的祖先一样,朱尼尔也可以走出去到处游历,甚至可以到美洲以外的世界去追寻更多的生活体验和更好的发展机遇。罗迪的这番话语不仅重拾印第安人的历史记忆,而且“现代游牧民”这一形象表征,使朱尼尔再次与印第安传统和印第安性建立起联系,让他意识到自己从保留地出走并不意味着背叛。这样一来,朱尼尔便从无家可归的无根状态和部落“叛徒”的心理负罪感中解脱出来,能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自己的跨界经历和新型身份定位。作为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兼职印第安人”,他不再迷失,而是像印第安祖先一样自由地四处游历,自如往来和栖息于两种文化之间。这种追寻与印第安传统文化的联系并结合异文化体验的生活方式,让朱尼尔看到两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同时也丰富了他的跨文化成长经历。
肤色和种族只是印第安少年朱尼尔身份表征的一个方面,但绝非定义和衡量其身份的惟一指征。通过自我表征为“兼职印第安人”和“现代游牧民”的新型形象和身份,阿莱克西努力对抗美国白人主流文化对两个种族与两种文化的截然分界和对印第安人的殖民话语及刻板表征,寻找它们之间的连接点和跨文化调适性,并从主位表现和研究的视角,以自我表征的方式揭开白人种族主义者、印第安人部落保守主义者给印第安人蒙上的层层面纱,从而还原和再现了一个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真实形象。
五、结语
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充分体现了新生代美国印第安作家阿莱克西对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自我表征与身份重构的独特视野。作家不仅颠覆了长期以来美国白人主流社会对印第安人的殖民话语和刻板表征,而且否定了许多其他美国印第安作家在他们作品中所沿用和表现的“归家”范式,批判了他们所提倡的一味回归传统、回归和守护保留地的部落保守主义观点。
文化表征和身份认同在特定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生成和起作用。在阿莱克西看来,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形象表征和身份重构,不应一味停留或局限于对过去历史和印第安传统的缅怀与留恋,而应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变迁而与时俱进和不断更新。当今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给印第安人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给他们的形象表征和身份重构带来更多可能性。像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离开印第安保留地前往白人主流社会谋求发展和进步的美国印第安人,在数量上已经远远超过仍留守于保留地的印第安人,*Russell Thornton,“Tribal Membership Requirements and the Demography of ‘Old’ and ‘New’ Native Americans”,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vol.7,no.9(1997),p.33.他们经历了从在保留地固守传统和孤立生存,到走进美国主流社会学习和发展以更新自我的重要转折。因此,如果再用“消失”“归家”“苹果人”“叛徒”等话语和表征去定义当今的美国印第安人,那显然是不合时宜和不准确的。在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中,阿莱克西通过建构新型的自我表征,真实重构了当代美国印第安人的新型身份——“兼职印第安人”和“现代游牧民”,他们能够自如往来于两种文化之间,既不单纯受限于印第安部落传统文化的预期,也不一味附庸白人主流文化的强权。阿莱克西的这一自我表征为读者了解当今美国印第安人的真实现状、新型形象和身份提供了新的维度。
对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的研究涉及三个方面:被研究的两种“他者”文化和学者的文化诠释,这总能引发激动人心的理智挑战和具有价值的洞察。某一文化群体与“他者”的对抗可能会打破曾经共享的、不言自明的秩序,也可能会引发创造性的文化调适和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变迁。从这些意义上来审视阿莱克西的小说《一个兼职印第安人绝对真实的日记》,为我们透过美国主流社会白人与跨界印第安人的互动,以此研究21世纪美国社会中的跨文化接触和跨文化关系开辟了新的视窗。
(责任编辑张健)
基金项目:①云南大学首批“青年英才培育计划”阶段性成果;2015年度国家留学基金资助阶段性成果;2013年度云南大学研究生优秀教材《英语跨文化交际:理论与体验》建设项目阶段性成果;2015年度云南省哲学社科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云南民族音乐舞蹈图像文化艺术的资源保护、产业开发与国际交流研究”阶段性成果(A2015ZDZ001)
作者简介:王玲,云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美国圣路易斯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访问学者、讲座教授(云南 昆明,650091);普慧,昆明医科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教(云南 昆明,65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