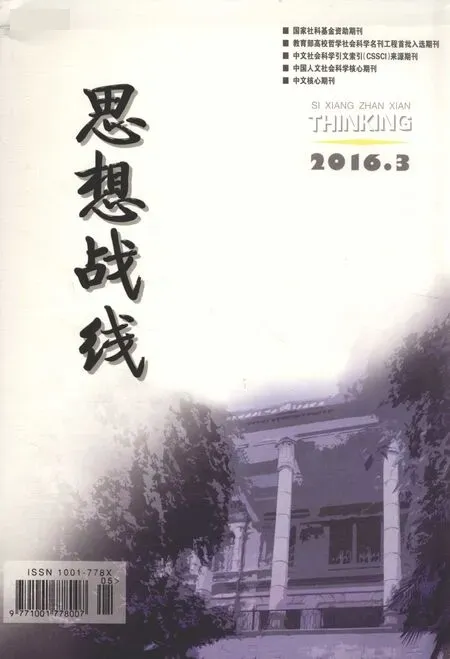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2016-04-11马琦
马 琦
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与社会治理
马琦①
摘要:水利纠纷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之一,解决水利纠纷是地方官府社会治理的重要职责。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却不亚于内地发达地区,类型多样,原因复杂。云南地方官府一方面根据“旧规”“旧制”等原则保护农户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规行为,达到维护已有水利秩序的目的,这与内地无异;另一方面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适时调整,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水情与地情,不断完善灌溉制度,减少纠纷的产生,履行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
关键词: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纠纷;社会治理
水利纠纷是水利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方向,也是探讨水利与区域社会互动关系的良好介质。云贵高原地处西南边疆,湖泊众多,滨湖平坝是最重要的农业区域,沿湖河流的水利开发历史悠久。明清以来,内地移民大量涌入边疆,耕地快速增加,水资源日益匮乏,水利纠纷事件频发。因此,本文拟以滇池坝区为例,通过档案、碑刻、方志中的众多水利纠纷案例,考察明清时期云贵高原的水利纠纷,探讨其类型、分布、原因及其解决纠纷的原则与方式,揭示政府在解决水利纠纷、维护水利秩序过程中的作用,以期扩大中国水利社会史研究的地域样本,丰富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知。
一、水利纠纷的数量与时空分布
滇池地处云南省中部昆明城西南郊,滨湖平坝区面积763.6平方公里(高程1 886米)。滇池坝区是云南省的核心经济区,农田水利开发历史悠久。*参见于希谦,于希贤《滇池地区水利发展简史》,《经济问题探索》1981年第2期。但滇池流域大规模水系治理则始于元代,如修筑松华坝、治理盘龙江及开挖海口河。
明清时期,在政府提倡和资助下,小型水利工程大量修筑。如乾隆二年(1737年),上谕:“云南跬步皆山,不通舟楫,田号雷鸣,(水利)不可不急讲也。凡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道光《云南通志稿》卷53《水利一》,道光十五年刻本。同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檄文中所列滇中已修水利工程达100余处,并称:
凡有可以兴修之处,务使水无遗泽,地无旷土,兴修工竣,将情形绘图贴说,及每年如何分灌,如何岁修,可以灌溉若干田地,逐一造册具报,其各属具报已修之水利,及已修未报者,亦即令其照此一体造册具报。*陈宏谋:《培远堂偶存稿》卷4《详请通查兴修水利详》,乾隆刻本。
即已建水利工程均有配套的水规和岁修章程,以此规范水利秩序。
随着水利工程数量的增加,“岁修”和“水规”等管理规章制度的出现,滇池流域水利体系基本形成。正如董雁伟所言,清代云南修建的水利设施都订有分水制度,在滇池、洱海等主要流域,水源的分配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董雁伟:《清代云南水权的分配与管理初探》,《思想战线》2014年第5期。此外,还出现了专门性的水利著作,如黄士杰的《云南省城六河图说》、孙冉翁的《盘龙江水利图说》和徐勰的《晋宁水利论》。*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台北文成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绪六年重刊本;孙冉翁:《盘龙江水利图说》,云南省图藏道光抄本;徐勰:《晋宁水利论》,道光《晋宁州志》卷14《艺文志》,1936年铅印本。
与此同时,随着人口的增加和耕地的扩大,滇池流域水资源日益匮乏,水利纠纷频出。清代乾隆年间钱沣所写《六河歌》中对昆明六河沿岸旱时霸水、抢水、堵水,涝时排水灌淹邻田等现象有生动的描写,如“群亩逞黠拥为利,乘春筑坝夯还硪,要遮新涨使横散,去清留浊谁禁诃,夏涨踵至坝虽倒,明年又筑人则那”;“塞河罪首从无科,能令田从海底涌”。*钱沣:《钱南园遗集》卷2《六河歌为陈云巌观察作》,云南省文史研究馆整理《云南丛书》第2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影印云南图书馆藏版,第13476~13477页。
就笔者所搜集的资料而言,有关明代滇池流域水利纠纷的记载仅有两例:一是《云南府昆明县为乞均水利以苏民困事碑》(又称《石鼻里水利碑》),*碑文见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编撰委员会《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1988年编印,第68~70页。记载嘉靖、隆庆时期昆明县石鼻里村民控告沐府田庄霸占水源及官府判决结果。二是《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该碑现立于昆明市官渡区官渡镇昆明市碑林博物馆内。记载崇祯七年(1634年)昆明县官渡里官渡、旧门溪、大耳等村设立分水石底事,提及此前各村水利纠纷事件。这可能与文献散佚、记载缺失及碑刻损毁有关。清代滇池流域水利纠纷记载众多,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清代档案,笔者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滇池流域因水利纠纷导致命案的刑部题本17件;二是民间碑刻,笔者近两年寻访乡间水利碑刻11通,大多涉及水利纠纷事件;三是方志,存留至今的清代、民国地方志中,记载水利纠纷事件7起。
纵观37份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纠纷案例,从时间上看,主要集中于清代中期,以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最多。这固然与记载、统计不全有关,但是,清代中期,随着内地移民的增加,滇池坝区耕地扩大,尤其是水田面积增加,导致农业灌溉用水日益紧张,这是水利纠纷增多的主要因素。如道光《昆明县志》中记载了该县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和道光十六年(1836年)民田、屯田、官田、公样田、马料田等各类水田面积数据,水田总数从64 892亩增至164 005亩,140余年间增加了1.5倍。*道光《昆明县志》卷3《赋役志》,光绪三十七年刻本。
从发生的具体地点来看,以宝象河流域最多。宝象河流域地处滇池东北部、昆明城东南部,发源于官渡区大板桥,经大石坝、小板桥、官渡,至宝丰注入滇池,全长48公里,流域面积344.3平方公里,是滇池坝区主要灌区之一。*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第29卷《水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41~151页。乾隆《云南通志》云:“宝象河,在城南二十里,……,东南田亩咸资分溉。”*乾隆《云南通志》卷13《水利》,乾隆元年刻本。但“此河情形,自三河黄龙潭下合流之处,俱系田低河高,开沟灌溉;流至板桥驿城西北一带,河低田高,用车戽灌溉,例不轮排,听其长流,上下均分”,而且“此河雨水泛涨,河内不能容纳” 。*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之《宝象河图说》,台北:文成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绪六年刻本。因上下游引灌方式不同,并无统一水规,加之经常决堤,冲毁沟渠,以致纠纷频出。其次是马料河。马料河源于官渡区海子村东,经呈贡洛羊、小古城,止官渡区回龙村入滇池,全长20.2公里。*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第29卷《水利》,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76页。与宝象河不同,“此河情形,田多水少,不敷灌溉;田高水低,素少冲决;上游水尚充足,下游水渐艰难”。*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之《马料河图说》,台北:文成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绪六年刻本。虽然水规刊载明确,但“下游有沿河三十六村,因得水艰难”,经常与上游倪家营等4村争水。
其次为金汁河、盘龙江、捞鱼河等流域。金汁河自松华坝分盘龙江水,沿东部山脚南行,由金马寺折向西,至吴井桥西南流,于福保村入滇池。该河为人工开凿的灌溉河流,是滇池坝区最大灌区的主要河流。《云南省城六河图说》载:“此河情形,自松华坝起,系就山开河,东岸田高水底,近者间用车戽,灌溉甚少;西岸水高田低,沿河俱修涵洞,放水入田,水足封闭,灌溉甚多。”*黄士杰:《云南省城六河图说》之《金汁河图说》,台北:文成出版社,1974年影印光绪六年刻本。崔尊彝亦言:“昆明六河,盘龙江为大,分为金汁河。盘龙江水流低于田,有闸以束之,分水由金汁河循山而行,东菑数万田畴,咸资灌溉,利莫大焉。”*崔尊彝:《重修松华坝开挖盘龙江金汁河并新建各桥碑记》,民国《新纂云南通志》(第7册)卷139《农业考二》,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点校本,第19页。金汁河虽然灌溉面积大于宝象河,但水利纠纷却相对较少。这是因为该河早在雍正十三年(1735年)就确立全河上下游一体的灌溉用水制度,上下五排轮流分灌,以杜纷争。捞鱼河流域的水利纠纷主要集中于上游的过山沟,皆因水规不清所致,后文将作为个案详细考察。
虽然这些案例保留至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这些案例发生的时空分布,一方面反映了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中期,滇池流域因人口、耕地增加,导致农业灌溉用水整体不足,争水频现;而不同地区灌溉用水制度是否完善,上下游能否统一调配,也是影响水利纠纷事件发生频度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受地形、水系等因素影响,滇池流域水利灌溉体系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
二、水利纠纷的原因及其类型
水利纠纷是指不同的单位或个人因为对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管理、保护等意见不一致而产生的争执。如果争执升级,可能引发打斗,或者导致命案,则成为水案。明清时期滇池流域的水利纠纷按其诱因可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个体或群体违反已有分水、用水制度或固有惯例,损人利己,引发纠纷,被称为“偷水”“盗水”或“霸水”。这类事件在滇池地区所占比重最大,且形式多样。最为典型的是个体农户虽明知分水、用水制度中所定的灌溉顺序和用水量,但因天旱救苗心切,争先引水灌溉,或超时截留,损害别人利益,导致两相争执,这样的案例不下10余起。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正月二十六日,昆明县左卫人贾如贤沿河引水灌溉,塘水围满之时,邻村呈贡县小古城村人尹发将坝挖开,将水放入自己田地,两相争执,致尹发因伤身亡。*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四日,署理云南巡抚诺穆亲《题为审理云南县民贾如贤因灌溉纠纷伤毙尹发案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6668-012。昆明县板桥里“阿腊村田亩向来开沟引水灌溉,公议分作南北两段,按日轮流放水”,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五月十四日轮北段放水首日,南段村民“非起盛偷挖水口”,被北段村民非自能等殴伤致死。*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为会审昆明县民非自能等因灌田纠纷共殴非起盛身死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7662-004。昆明县高峤里“李正珑与祝勇义同村居住,素好无嫌,该村有水塘一口,系自然山泉,合村田亩俱赖此塘灌溉,向来公共轮放,不许私泄,每年村众公议一人看守水口,乾隆五十七年轮应李正珑看管,闰四月二十五日祝勇义因己田需水,欲求先放,李正珑不允,祝勇义因其不肯通融”,相互争斗导致命案。*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云南巡抚谭尚忠《题为审理昆明县民李正珑因放水灌田纠纷伤毙祝勇义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8084-019。昆明县珥琮里人罗阿郎与高李氏、高宝元邻村居住“该处向有河水一道,按排引放灌田,设有水头经管,每遇放水之期,水头开放,嘉庆十五年二月初四日,罗阿郎同罗彩、罗幅庆及高李氏往田放水,因水头未到,高李氏先欲放水,罗阿郎不允,高李氏不依,致相口角”,罗阿郎被高宝元殴伤致死。*嘉庆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董浩、刑部尚书长麟《题为会审昆明县民高宝元因放水起畔踢死罗阿郎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9336-010。昆明县人杨际太、杨洪仁“邻村居住,素识无嫌,杨际太家地土与杨洪仁家田亩毗连,旁有公共水沟一道,向系轮流灌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十三日,轮应杨际太引灌,携锄前往工作,迨后杨洪仁声称田苗干涸,欲将沟水截放,杨际太不依混骂,杨洪仁携打”,致杨洪仁身死。*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南巡抚吴其濬《题为审理昆明县民杨际太因灌溉田禾伤毙杨洪仁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11687-018。更有甚者,如隆庆六年(1572年),昆明县城西石鼻里村民角应高等呈告:
村居城西石鼻,相连沐府庄田,麓间有源,均灌田亩,……嘉靖十一二等年,有家人张时泰等,仗倚营充、参随、管庄、听用等役,持势每月栽插,将水霸占轮放,兼行倒卖肥己。民无涓滴,如遇亢旱,荒者十帘八九,致使栽插失时,久绝依源。*万历元年,云南府昆明县《为乞均水利以苏民困事》(即《石鼻里水利碑》),见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编撰委员会《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1988年编印,第68~70页。
这一地区“均灌田亩”的制度早已存在,但沐府家人恃强霸水,引起公愤。
为了自己田亩能够及时灌溉,有的村庄或农户不惜破坏或改变原有闸坝、沟渠、堰塘、涵洞等水利设施,罔顾他人利益,私自变更分水、用水制度。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昆明县人徐汝恩等在洛龙河西子河边偷挖沟渠,欲引水灌溉本村田亩,但西子河水灌区早已确定,仅为呈贡县县前、梅子、斗南等村田亩,并不涉及昆明县地,故此次偷挖行为被呈贡县民阻止。*刘世熼:《呈贡县申详分水文》,光绪《呈贡县志》卷7《艺文》,光绪十一年刻本。再如昆明县苴里甲尾新旧二村与白水塘村地处马料河上游,引导小白龙潭水入沿山沟灌溉,道光十八年(1838年)七月,因天旱争水,水塘村村民李翠私自毁坏涵洞,将水全部运入过山沟,霸水灌溉,新旧二村村民李如林则填堵小白龙潭井泉,断绝水源,以示抗争,均不顾原有旧规,破坏灌溉秩序。*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昆明县《告示碑》,该碑立于官渡区阿拉乡大普连宝洪寺。还有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昆明县塔密左等村恃强在马料河上新开灌溉沟渠,致使马料河南岸漾水沟水源减少,呈贡县倪家营等沿河村民具控塔密左等村“恃众逞刁,新开河道”。*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昆明县、呈贡县《勿易成规碑》,该碑立于呈贡县洛羊镇倪家营村宝乐庵。
不仅是争水灌溉,洩水排涝亦有纠纷。如昆明县大树营村人常奉与罗中邻村居住,“素无嫌隙,两人田亩相连,常奉之田在上,罗中之田在下,常奉田水向由罗中田中消放,嘉庆四年五月十五日夜大雨,常奉恐田禾被淹,携锄往田,挖埂放水,罗中适至,不容挖放,常奉以舍此别无消路,嘱其再往下放,罗中不依,互相争言”,致罗中受伤身死。*嘉庆四年十一月初六日,云南巡抚初彭龄《题为审理昆明县民常奉因挖埂放水起畔相争殴伤罗中身死一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8698-019。再如昆明县杨有富与陈洪邻村居住,“道光十二年六月初一二等日,大雨时行,杨有富因田苗被水浸淹,无处宣泄,于初三日早将陈洪田埂挖开,引水下沟,适陈洪雇杨湛、杨成、杨添才往田工作,陈洪见而拦阻,杨有富告以前情,并许俟水泄竣,即行修还,陈洪恐碍田苗,不肯应允,杨有富斥其毫无田邻情分,陈洪不依,致相争角”,杨有富被伤身死。*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户部尚书管理刑部事务王鼎、刑部尚书明山《题为会审云南昆明县民杨湛等因挖埂放水纷争欧毙杨有富一案依律分别定拟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11057-012。水田排泄,上满下放,久已成规。但部分农户为保护自家田苗,置邻田于不顾,导致纠纷甚至命案。
这类事件所涉区域基本都有明确的分水、用水规则以及违反规则的惩罚措施。一般违规纠纷多由水头、巡水等乡村基层水利组织进行调解,并按水规中明确规定的措施进行惩戒。只有调解无效、冲突升级,甚至导致命案的情况下,才会上诉官府处理。以上案例就是这类事件的极端表现。
第二类纠纷是部分村庄或民户认为原有分水、用水制度不公平、不合理,通过建议、上诉或抵制来改变旧制,以维护、扩大或新增自己的灌溉权益,但却与认同旧制的民户或村庄产生利益冲突,称为争水或抢水。如宝象河流域,“宝象河自小板桥分沠,古制中竖月牙尖,以三七分引水,一入官渡十四村,人户用水七分,一入旧门溪四村,人户用水三分,上有大耳村沟口,用一瓦之水”,但因水利失修,“利害不均,其旧门溪河底辄底,水势尽泄下流,官渡河底高亢,毫无半点济渴”。崇祯七年(1634年),官渡等14村建议在宝象河建闸,均分水源入官渡河,“旧门溪民虑其专壅于上,是以群共而争也”,*崇祯八年三月,云南府清军水利厅《宝象河平水石底碑记》,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坚决反对均分水利。再如金汁河流域,雍正十二年(1734年)规定灌溉夏水自四月初一日起,上下五排挨次轮放,“头排放水一昼夜,二排放水二昼夜,三四五排各按排数,计日轮放”周而复始。如果四月初一日河中无水,头排农田无法灌溉,“须半月之久”才能再次轮灌。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因天旱河水稀少,头排军民灌田心切,耆民赵君庆等呈讼:“每年栽插夏水,以得水之日为始,盖恐雨泽衍期,不能以四月初一日为准。”*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云南府水利厅《金汁河头排军民呈讼水规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金汁河民众又呈讼,认为夏税“轮派之说于五月初一日始行”,*咸丰十一年春月,云南府《永垂不朽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显然是欲改变原有灌溉秩序。还有马料河流域,上游倪家营等4村与下游下五碑等村分马料河支渠汪洋沟水灌溉,但分流之处年久失修,汪洋沟沟底淤积,来水减少。道光十一年(1831年)倪家营等村筑坝截水,下五碑等村为了维护四分用水权,偷挖闸坝,两相互控。*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呈贡县《为出示遵守事》,该碑立于呈贡县洛羊镇倪家营村宝乐庵。
田地、水源、水利设施等因素的变化不仅导致旧有水规范围内的用水不均,甚至引起水规范围外村庄对用水权的争夺。如晋宁县大河下游白白坝子河,“引灌金沙十五村田,旧分河水之三,其七则归下河七十五村,日久淤废,村农失利,争讼连年”。*道光《晋宁州志》卷5《赋役志·水利》,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因疏于维护,原有水利设施功能弱化,三分之水不敷灌溉,导致金沙等15村抢夺下游75村用水份额。再如过山沟。乾隆元年、二年(1736年、1737年)间曾有三岔口与柏枝营等村争控分水,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兴隆营又与诸村争水。按当时过山沟水规,“至上下柏枝营设立水坪一座,分为左右两沟,除左沟分水三分系中庄、缪家营、郎家营三村积塘灌溉,上纳沟粮六升,其右沟分水七分系段家营、上下柏枝营、白龙潭、吴杰营、王家营、渠卜场、洛龙河、大水塘、回子营积塘灌泡豆麦陆地秧苗,公纳沟粮一斗九升,并设水长一人,巡查分放”。其中并无兴隆营,但该村据“明时半截碑文”,称该村原有过山沟七分水灌溉。水规范围内其他村庄反驳:残碑“其中语句不全,本难断章取义,且不在设立水坪左右分水两沟之处,又不在现在分放之普家嘴,乃在兴隆营以下之太平关,自是先年另有南、北二沟,其在本地,久已变迁,与柏枝营等村现在所争沟水马牛无涉”,“又况完纳沟粮,修挖沟枧,每年皆柏枝营等村承办,兴隆营等村并不出力帮办,尤不应准其水利”。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下游丰乐村又以“冬水仅放七八日,不敷灌泡豆麦”为由,上诉官府,欲扩大过山沟右沟冬水用水权。*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赵怀锷《详准奉批过山沟九村分水日期文》,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同样,乾隆至光绪之间,北沟用水权在“中庄、缪家营、郎家营”3村外,又增加了郑家营。*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第三类是上下游、高低田之间因灌溉与排涝冲突所导致的纠纷。这类事件或因制度本身没有协调、兼顾用水和排水所致,或因民众疏于维护水利设施而产生。如呈贡县高家庄与灵源村水利案,“高家庄外有大河一道,从梁王山发源,自南由东绕北,汇入昆阳大海,高家庄同灵源村俱坐落大河西岸,灵源村向于河边开挖水沟一道,沟口树立石闸,每年秋分启闸引放河水蓄积堰塘,灌溉田亩,春分闭闸引流归海”。但石闸年久坍塌,“灵源村未经修理,以致沙石随留壅积,沟身淤高,大雨时节,沟水浸溢,高家庄田埂偶被浸淹”。高家庄“高标起意率领村人将灵源村沟道填塞,并将伊家人武三尸棺埋于闸口,两造互争。”虽“前经官断,令灵源村照依古规修闸开沟”,但高家庄不服判决,高标屡次率众阻挠。嘉庆十五年(1810年)九月初十日,灵源村人李谷柱约同村赵尚礼等13人,“于旧沟之下另开新沟”,时值高家庄村民高文钟等16人在庙内酬神,担心本村田亩被挖坏,携带柴刀、铁锤、菜刀、木棍等器具前往阻拦,两相大打出手,导致4死10余伤。*嘉庆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云南巡抚孙玉庭《题为审理呈贡县高文秀等因阻开沟引水纠纷欧毙李谷柱等四命一案分别按律定拟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9530-016。呈贡县马金铺镇灵源村(今名马金铺)、高家庄同居梁王河西岸,灵源村在河边设闸开沟,引水入堰塘(今化城塘)灌溉,但年久失修,闸坝坍塌、沟身淤高,使梁王河水位抬升,淹没下游高家庄田亩;高家庄阻挠开沟,不顾灵源村灌溉需求,导致为上下游之间灌溉与防涝之争。再如昆明县广南卫、义路村水利案。“广南卫、义路村田业昆连,中有迤南大路一条,其路之上田属义路村,路之下田属广南卫,两村放水插秧,均由宝象河放水灌溉。此河自高而下,中有迤南大路之石榴园桥洞一所。”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初五日, “广南卫士民在石榴园地方筑闸积水,淹坏义村田内之小春,义路村众将闸拆毁”,并控告广南卫私造闸枋。*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昆明县《告示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
第四类是分水、用水制度不完善或没有制度的地区引发的纠纷。如昆明县乌龙村与前卫村争水案,“两村有公共箐河一条,河中原筑古坝一座,前卫村田在上游,地势较高,乌龙村田在下游,地势较低,每岁栽插,以前两村议定,于古坝下另筑沙坝,蓄水引灌,向来先尽前卫村栽插完竣,开坝放水,灌溉乌龙村田亩,历久无异”。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前卫村因栽插禾苗稍迟,拖延放水,乌龙村人控告至官府,断令“仍照旧规,轮放引灌,前卫民不得截水故延,乌龙村民亦不得先自拆坝”。道光十四年(1834年)五月初,前卫村栽插未完,亦未开坝放水。乌龙村田亩干涸,怀疑前卫村“违断故延”。初三日,乌龙村民众开沙坝放水,与前卫村人发生冲突,导致1死1伤。*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七日,户部尚书管理刑部事务王鼎、刑部尚书成格《题为会审云南昆明县民李连因栽插争水伤毙李欲案依律分别定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11131-024。再如呈贡县过山沟。前文所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丰乐村争分过山沟水案中,知县赵怀锷按照节令将南沟水分配于各村,“但按照节令出卯时交水已为平允,惜节令又有长短,水期因而多寡”,致使纷争不断。至光绪年间,过山沟冬水用水权更加细化,如“立冬小雪、大雪期短一日者,吴杰营、大王家营、柏枝营三村各认四个时辰,冬至、小寒期短一日者,白龙潭、大水塘、回子营三村同认,又大寒至立春三日期短一日者,大小洛龙河、丰乐村三村同认”。*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编者按,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过山沟南沟纷争不断,北沟亦争控不断。光绪二年(1876年),北沟诸村争水,呈贡县令郑扬芳勘断,按节令将用水具体日期分配于各村:
每年八月初一日起,缪家营放水十日,郎家营放水十日,中庄放水十日,周而复始,放足九十日,至冬月内归郑家营放水三日,该三村又照前轮放九十日,至立春后归郑家营放水三日,以后仍三村轮放,每逢交替,以日出卯时为定。*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随着新的分水、用水制度的制定及已有制度的完善,这类事件逐渐减少。
此外,还有一些水利纠纷与农田灌溉并无直接关系。如巡河权。呈贡县安江村与晋宁州接界,共用淤泥河之水灌溉,修挖此河,由安江村出夫295名。安江田少夫多,晋宁田多夫少,巡河之役由晋宁人充任。“乾隆四十九年,(晋宁)州民宋朝举具呈,妄替巡河与安江”;“乾隆五十三年,(晋宁)州民钱国佐、宋大经又妄替巡河与安江”。*《永革巡河碑记》,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晋宁人屡次具呈,欲将巡河之役转嫁给呈贡县安江村,但均未能如愿。再如水利工程修护,海口河疏浚工程,历来由昆明、呈贡、晋宁、昆阳4州县协同,按年挑挖。道光十九年(1839年),“忽有昆阳州工书舞弊,将呈贡应挖尖山箐子河有普安闸之名,遂将普安闸子河旁首段混名为新旧普安二滩,私立石椿,以昆阳应挖之大河移害呈贡挑挖”。*道光十九年,云南府《为给示永垂事》,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昆阳违反旧有挑挖分工,将自己应行挑挖工段转嫁给呈贡,逃避工役,经呈贡县民上诉得以纠正。
三、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方式、原则与目的
水利纠纷是中国传统时代基层社会中较为突出的矛盾现象。随着纠纷扩大,冲突升级,进而引发群体斗殴,甚至导致命案,则会严重影响基层社会秩序。因此,妥善地解决争端、协调双方关系,既是历史上国家对灌溉水资源利用进行调控的表现,*萧正洪:《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也是国家治理基层社会的主要任务。前文所述明清时期滇池流域众多水利纠纷的解决,均有当地官府介入其中,这正是国家治理边疆基层社会的表现。根据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纠纷的类型、原因及大小,云南地方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方式、结果也不尽相同。
对于个体农户盗水、偷水等常见水利纠纷,因其水规中已有明确的惩罚措施,一般由巡水、水头等乡村水利组织进行处理,轻者告诫,重则惩罚。只有当纠纷扩大,或导致命案,才由乡约、里长等上禀官府,官府派员勘验,除将凶手正法外,再次重申已有水规,维持原有的灌溉秩序。如前文所述第一种类型中的案例,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昆明县板桥里阿拉村偷水案,除将凶手正法外,“所争田水,饬令照旧按日轮放,不得再有争执,致滋事端”;*乾隆四十七年五月二十三日,大学士管理刑部事务英廉《题为会审昆明县民非自能等因灌田纠纷共殴非起盛身死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7662-004。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昆明县高峤里争水案,除将凶手正法外,“该村水塘仍令照旧轮灌,严禁私放,以杜争端理”;*乾隆五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云南巡抚谭尚忠《题为审理昆明县民李正珑因放水灌田纠纷伤毙祝勇义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8084-019。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昆明县人杨际太因争水案,除将凶手正法外,“该处沟水饬令仍照旧规轮放,以杜争端”。*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南巡抚吴其濬《题为审理昆明县民杨际太因灌溉田禾伤毙杨洪仁案依律拟绞监候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11687-018。笔者所搜明清滇池流域17起水利命案的处理结果,均是如此。
对于私自破坏、更改水利设施进行偷水或盗水事件,官府断令恢复原有设施,坚持旧有分配格局,维护已有灌溉秩序。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昆明县人徐汝恩等在洛龙河偷挖沟渠,由当时呈贡县知县率众填平。*刘世熼《呈贡县申详分水文》,光绪《呈贡县志》卷7《艺文》,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再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昆明县苴里结尾新旧二村与白水塘村争水案,官府“断令李翠并生员邓联华、武生毕朝相等,将挖坏涵硐,用石版二块,一块凿硐三寸,安砌半升口涵硐,一块凿硐二寸,安砌捺肆不琢涵硐,分水灌溉二村田亩,并于田尾栽石椿,涵洞所放之水不得过石椿之外,至挖坏沿山沟,着令两造拨给人夫,公同修理照旧,仍令分放黄龙潭之水十分之一,再挖坏小白龙潭并井泉,着李如林等自行淘围开挖”。*道光十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昆明县《告示碑》,该碑立于官渡区阿拉乡大普连宝洪寺。以及同治五年(1866年),昆明县塔密左村强行在马料河上新开沟渠,官府“断令将新河照旧填灭,按照古规沟河宽窄断给水分”。*同治五年八月初十日,昆明县、呈贡县《勿易成规碑》,该碑立于呈贡县洛羊镇倪家营村宝乐庵。
对于因分水、用水制度不公平、不合理导致的争水、抢水、霸水事件,官府大多能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如雍正五年(1727年),晋宁县大河下游的白白坝子河争水纠纷,沿河金沙等15村原于下游“三七分水”,因不敷灌溉才与下游引起纷争,但官府勘定:
金沙等村于大河内筑一小坝,仅高闸口一尺,留龙口八尺;冬春水微,许于五日内启闸放水一昼夜,滋润豆麦,余四日则闭之,使水尽入下河;夏秋水涨,则尽启闸板交官,不许私闭,使各子河分泄洪流,以免傍溢。*道光《晋宁州志》卷5《赋役志·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
结果金沙等村所用冬春水分减少为二分。再如金汁河,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头排军民因灌田争讼心切,官府传集各排民众协商,考虑到实在情形,对已有水规进行微调,规定“每年栽插夏秋,如遇雨泽衍期,应照前议,以得水之日为始,挨次轮放,如雨畅时行,仍以四月初一日为始”。*乾隆五十九年三月二十日,云南府水利厅《金汁河头排军民呈讼水规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咸丰十一年(1861年),金汁河民众又呈讼,但官府认为“无水规案据”,仍“照古旧例,自四月初一日寅时起,放上下头排一昼夜”。*咸丰十一年春月,云南府《永垂不朽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金汁河两次纠纷相似,皆因金汁河来水的时间、大小发生变化,导致原有水规与实际灌溉需求不符,但官府处理的结果却截然相反,前面调整水规,后面维护旧制。还有马料河流域,道光十一年(1831年)倪家营等村与下五碑等村水利案,结果呈贡县知县每年自捐养廉银,让民众代为挑挖汪洋沟,平息纷争。*道光十一年六月十五日,呈贡县《为出示遵守事》,该碑立于呈贡县洛羊镇倪家营村宝乐庵。挑挖汪洋沟乃下五碑等村事,却由县令自掏腰包,可谓难得。
当然这类事件中,官府亦有坚持原有分水、用水格局,维护已有灌溉秩序的案例。如前文所言隆庆年间昆明石鼻里水利案,沐府庄户恃强霸水,官府“断将前项水利不分清潢,各照田亩多寡,分为宽狭二股,各流灌溉,以免争紊。如遇潢水泛涨,照旧依古,下河流海,不许阻冲民田”。*万历元年,云南府昆明县《为乞均水利以苏民困事》(即《石鼻里水利碑》),见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编撰委员会《昆明市西山区文物志》,1988年编印,第68—70页。明显照依古规,维护旧制。又如崇祯七年(1634年)昆明县小板桥官渡河、旧门溪河分水纠纷。此次纠纷源于宝象河支流官渡河、旧门溪河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导致水利不均,官渡等村欲改变原有水利体系,以符分水之实,维护用水权益。旧门溪等村担心官渡河独霸水利,坚决反对。官府为杜纷争,以官渡、旧门溪两河等高、等宽水底,落实“三七分水”旧制。
对水规范围外村庄获取用水权的事件,官府会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分水的时间与水量,如过山沟。乾隆三十年(1765年)兴隆营又与过山沟诸村争水案,兴隆营并不在旧有水规之中,官府虽称:“按粮田之多寡分派,殊属游移,于案不合”,但“念兴隆营等村向来惟春间分放三分,仍准其照旧,于立春三日后在普家嘴分放三分,以资灌溉。”*乾隆三十年十一月初六日,呈贡县《为截水害命事》,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虽不清楚兴隆营与官府的关系,即使与旧规不合,但兴隆营最终取得过山沟左沟春水的用水权,与中庄、缪家营、郎家营3村同分过山沟三分之水,将“向来惟春间分放三分”的事实变成了官府认定的水规。此后,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过山沟右沟冬水水规中又新增了下游丰乐村,“冬水仅放七八日” ,*嘉庆二十四年十月初三日,赵怀锷《详准奉批过山沟九村分水日期文》,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与段家营、上下柏枝营、白龙潭、吴杰营、王家营、渠卜场、洛龙河、大水塘、回子营等9村一起使用过山沟水灌溉。同样,在光绪年间的文献记载中,北沟用水权在“中庄、缪家营、郎家营”3村外,又增加了郑家营村。*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兴隆营、丰乐村、郑家营3村本在过山沟水规范围之外,但自乾隆三十年(1765年)至光绪初年,此3村均获得过山沟的用水权。当然,并非所有水规范围外的用水要求都被官府认可。如道光十七年(1837年)昆明县滥坝争水案,官府“断令各照旧规”,斥责远离滥坝的白庙村“不得妄争水道”,并修订水规。其中规定:“无水之田,均不得偷挖”,但“如二村俱放完,由二甲长公同,与放毗连之田,获息充公”;“各处田亩放完,如遇旱年,苗水无论江登、下坝,当通融救润。”*道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昆明县《永垂不朽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从官府的判决看是维护旧制,滥坝用水权由波罗、牛圈2村独占,但修订的水规表明在坝水有余、2村灌溉完毕的情况下,兼顾周围其他村庄农田灌溉,反映出2村对滥坝水的优先权。
上下游、高低田之间灌溉、排涝纠纷,官府一般坚持旧制,维护既定水利秩序。如嘉庆十五年(1810年)呈贡县高家庄与灵源村水利纠纷,第一次官断,“令灵源村照依古规修闸开沟”;高家庄不服判决,阻挠灵源村挑挖沟渠,导致群体性斗殴,4死1伤,官府再次断决:“高标因灵源村人不修沟闸,只应控理,轻率人填塞沟道,并将伊家人武三尸棺埋于闸口,拦堵水路,使其不敢复开,已属恃强滋事,迨经官讯断,令开沟修闸,并无屈仰。”*嘉庆十六年三月三十日,云南巡抚孙玉庭《题为审理呈贡县高文秀等因阻开沟引水纠纷欧毙李谷柱等四命一案分别按律定拟请旨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09530-016。显然,官府坚持旧制,维持原断。官府断令灵源村修闸开沟,不但恢复旧制,且可从根源上解决问题,但高家庄抗断翻控,阻挠开沟,导致群体性互斗命案。再如昆明县广南卫与义路村水利案,官府断令:“至小满后,义路村先分水三天三夜,广南卫后分水三天三夜,轮流照放。”*光绪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昆明县《告示碑》,该碑立于昆明市碑林博物馆。此判决虽然平息了用水纷争,但未涉及上下游、高低田之间灌溉与排涝的协调问题。
对于水规不完善或没有水规的地区,官府通过对水利纠纷的处理,进一步完善分水制度,构建水利秩序。如道光十一年(1831年)昆明县乌龙村与前卫村争水案,官府断令“仍照旧规,轮放引灌,前卫民不得截水故延,乌龙村民亦不得先自拆坝”。*道光十五年闰六月十七日,户部尚书管理刑部事务王鼎、刑部尚书成格《题为会审云南昆明县民李连因栽插争水伤毙李欲案依律分别定拟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号:02-01-07-11131-024。但两村分居上下游,“上满下流”的分水规定并不明确,乌龙村灌溉时间和水量并无明确界定,前卫村无从判断乌龙村是否“截水故延”,又不能“先自拆坝”。水量丰沛之年尚可相安无事,一旦河水稀少,势必导致纷争。再如呈贡县过山沟。前文所述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丰乐村争分过山沟水案中,知县赵怀锷按照节令将南沟水分配于各村,但每年时令长短不一,致使纷争不断。至光绪年间,过山沟冬水用水权更加细化,如“立冬小雪、大雪期短一日者,吴杰营、大王家营、柏枝营三村各认四个时辰,冬至、小寒期短一日者,白龙潭、大水塘、回子营三村同认,又大寒至立春三日期短一日者,大小洛龙河、丰乐村三村同认”。*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编者按,云南省图书馆藏本。过山沟南沟纷争不断,北沟亦争控不断。光绪二年(1876年),北沟诸村争水,呈贡县令郑扬芳勘断,按节令将用水具体日期分配于各村:“每年八月初一日起,缪家营放水十日,郎家营放水十日,中庄放水十日,周而复始,放足九十日,至冬月内归郑家营放水三日,该三村又照前轮放九十日,至立春后归郑家营放水三日,以后仍三村轮放,每逢交替,以日出卯时为定”。*光绪《呈贡县志》卷8《续修·水利》,云南省图书馆藏本。在水利纠纷过程中,从南沟到北沟,从冬水到春水,从节令到时辰,过山沟水规亦在不断完善。
从以上水利纠纷的处理过程来看,明清时期云南地方官府解决滇池流域绝大多数水利纠纷的评判依据是该地区早已形成、民众公认的分水、用水制度,即水规或水册,如“照旧按日轮放”“照旧轮灌”“照旧规轮放”“照依古规”“照旧依古”等。往往在水利纠纷判决的最后,官府均要强调不得违反旧规。因为旧规中有无水分及水分多少是判定水利纠纷责任的最重要依据,是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重要原则。遵守旧规不仅是官府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的认可,而且也表达了官府承认以旧规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区域水利秩序,维护旧制即是维护已有的水利秩序,这应该是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目的所在。对于违反规定、破坏水利秩序的偷水、盗水、霸水、抢水等行为,由官府进行制裁,以保护其他人的用水权益。因为维护水利秩序、化解社会矛盾也是官府治理基层社会的职责所在。
四、结语
本文所述的水利纠纷案例多达37件,主要集中于滇池东岸的宝象河、马料河、捞鱼河等区域,反映出明清时期滇池流域因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导致用水矛盾日趋激烈。虽然云贵高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与内地不同,但水利纠纷的激烈程度不亚于山陕、西北、江南等发达地区。云南地方官府积极介入水利纠纷的处理,根据不同的原因和类型采取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制裁违反水规的行为,保护其他农户正当的用水权益。正如熊元斌所言:地方官府“对侵犯别人利益而引起纠纷的自私行为采取了制裁的手段,保护受害者的利益”;“在地方事务管理中,运用行政手段干预水利民事纠纷,并且直接采取了某些强制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国家权力的功能,维护了合法利益。”*熊元斌:《清代浙江地区水利纠纷及其解决的办法》,《中国农史》1988年第3期。
在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过程中,大多根据已有“旧规”或“旧制”来勘断,即遵循早已形成、民众公认的分水、用水制度的原则。这与前近代山西等地水权争端中的 “率由旧章”行事原则异曲同工,采取这样的原则不仅是政府面对制度变革的被动应对及文化安排的结果,*张俊峰:《率由旧章:前近代分河流域若干泉域水权争端中的行事原则》,《史林》2008年第2期。更为重要的是维护原有分水、用水制度构建起来的水利秩序。因为地方水利秩序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协调各种矛盾,如果旧有水利秩序崩溃,短期内将爆发更多的水利纠纷,引起基层社会秩序混乱,这与官府治理基层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同时,根据水情、地情的变化,云南地方政府对已有分水、用水制度进行适度调整,平衡不同用水主体之间的矛盾,完善水利灌溉秩序,这也是明清时期滇池流域地方官府解决水利纠纷的重要特征。
(责任编辑廖国强)
基金项目:①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云南高原历史地理研究”阶段性成果(X3145801);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明清时期滇池流域水利社会史研究” 阶段性成果(YB2015062)
作者简介:马琦,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博士(云南 昆明,65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