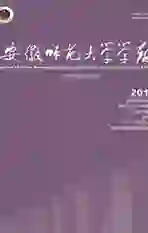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何以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
2016-12-14何卫平
何卫平
关键词:解释学;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实践智慧;伽达默尔
摘要:邵华的新著《实践智慧与解释学》,基于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揭示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点具体落实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和对康德实践哲学的补充方面。
中图分类号:08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16)03-0291-03
邵华博士的新著《实践智慧与解释学》于近期出版,这本书主要围绕伽达默尔的思想,对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作了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是目前国内有关这个主题的第一部系统专著,值得关注。
我们知道,实践哲学贯穿于伽达默尔思想的始终,而不是他后期(《真理与方法》之后)才转向这个领域的。这条漫长的路应当追溯到1923年,当时,在马堡大学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伽达默尔来到弗莱堡,参加了海德格尔主持的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的研讨班,聆听了关于“实际性的解释学”的讲座,这一经历奠定了他今后的学术方向。晚年的伽达默尔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解释学就是实践哲学”。这可视为他一生研究哲学解释学的一个基本概括和总结,仿佛一位大艺术家经历了“少而工,老而淡”的阶段,这句话看似平易,却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涵,伽达默尔的整个学术生涯都在充实这一内涵,甚至可以说,在他那里,实践哲学实际上充当了第一哲学。
实践哲学的核心就是实践智慧,而且实践智慧不仅是实践哲学的核心,也是解释学的核心,这些是在伽达默尔那里才被突显出来,因此可视为他的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因为传统解释学在反思上是缺乏这一维度的,这当然同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分不开。众所周知,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理论智慧和实践智慧之间做出区分,是亚里士多德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他以前的哲学家,无论是苏格拉底,还是柏拉图,都没有明确做出这样的区分,而这对后来哲学的发展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尤其西方人文主义哲学传统,包括解释学的传统都应当追溯到这里。伽达默尔曾经谈到,相对科学主义,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实践哲学”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传统的第二条线索”,它通向现代精神科学及其为之奠基的解释学,在这里,实践哲学不仅是解释学的方法论的范式,而且就是它的实际根据(参见伽达默尔《诠释学Ⅱ: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10-611页,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伽达默尔思想的这一走向伴随一个大背景。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主要是欧陆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在新康德主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复兴:本体论的复兴、实践哲学的复兴、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和修辞学的复兴。这些复兴有着内在的联系,海德格尔前期的存在哲学通向实践哲学,而实践哲学的复兴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复兴是一致的,至于修辞学的复兴实际上也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分不开。这些复兴在当代人文主义哲学包括解释学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些影响都能在伽达默尔身上明显地看到,它们构成我们理解其思想的重要背景。
受海德格尔的推动,伽达默尔后来发展出自己的哲学解释学,它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解释学结合的产物,但又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这里的“新”意味着不是简单地回到古代,而是适应时代要求所提供的一种“升级版”的亚里士多德主义。邵华博士的这本专著让我们具体地看到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何以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作者是通过实践智慧与解释学的关系的探讨来加以呈现的。
由这个关系所反映出的伽达默尔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新”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立足于当代现象学运动;另一个是对康德思想批判性的吸收、补充。关于第一个方面,本书前两章作了明确的交待和具体的梳理,它是结合着“实践智慧”内涵的分析展开的,令人印象深刻。我们看到,上个世纪,大陆(主要是德国)的亚里士多德的复兴与英美不约而同,但还是有差别的(正如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在英美哲学和在大陆哲学那里的内涵不同一样),它被纳入现象学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启者虽然是胡塞尔,但他的天才学生海德格尔后来居上,在运动中的影响超过了胡塞尔,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海德格尔实现了现象学运动的三个转向:本体论的转向、解释学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而这些都是胡塞尔所未曾达到的。作为海德格尔最亲近的弟子伽达默尔继承了这个方向。当海德格尔将现象学运动推进到本体论,必然会走向生活世界。所以,海德格尔弗莱堡早期开设的一系列课程都与生存论的现象学有关,包括他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读。因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主要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其实就是人的哲学,所谈论的就是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通过“解释学处境”将其同“实际性的解释学”联系起来,这种解释学超出了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的范围。不过“转向”后的海德格尔(弗莱堡晚期)就不再怎么提亚里士多德了,而伽达默尔一生都非常重视亚里士多德,关注实践哲学。他的解释学思想是沿着一种新亚里土多德主义的方向展开的。这方面的成功导致他在海德格尔之后,同阿伦特一样,成为德国亚里士多德复兴运动的最重要代表。只不过阿伦特是从政治哲学切入的,伽达默尔是从解释学切入的。
伽达默尔沿着海德格尔前期的此在论现象学、胡塞尔后期的“生活世界”的现象学,进一步接续人文主义传统和与之相关的解释学传统,如施莱尔马赫、德罗伊森、狄尔泰等人的思想,并打通与西方实践哲学传统的联系,而且上溯至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以此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三版后记中说的哲学解释学所参与的我们这个世纪的哲学运动,实际上指的就是现象学运动,“这种哲学运动旨在克服片面指向科学事实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对于新康德主义和当时的实证主义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第546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知识和实践智慧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伽达默尔的重视。
哲学解释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之“新”,还有另一方面的表现,那就是对康德的批判性的吸收和补充。这在本书的第三至五章作了集中的揭示,它主要是结合着实践智慧内涵的三个方面——善、实践的考虑和伦理来谈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被伽达默尔视为实践哲学核心的实践智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很重要,但在康德那里并不重要,正如“友谊”的概念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康德伦理学中不占重要地位一样,这是康德先验论立场的必然结果。在后者眼里,“实践智慧”或“明智”(Klugkeit)只是人在与物打交道和与人打交道中的一些实用技巧或实用原则,它反映的是人的利益、欲望的需求,而不是基于善良意志的义务原则,它表现为假言命令,而不是定言命令,所以它只属于人的一般的实践理性,而不属于纯粹实践理性,与理想的道德无关。因此,在康德那里,实践理性并不等于实践智慧,而在伽达默尔那里,二者成了一回事,这是两种不同的论域下得出的不同结论。
虽然伽达默尔更多基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立场,但他后来已意识到,在实践哲学上,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路子和康德主义的路子都有片面性,相互融合才是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它对于未来的实践哲学具有重要意义。伽达默尔所预示的这个方向,为后人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启示。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融合,现在看来,不仅具有重要的实践哲学的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解释学的意义,邵华博士牢牢抓住了这一点,并做了细致的阐发,这是本书的一个重要的闪光点。他强调伽达默尔最终力图综合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观点来发展自己的解释学,体现了一种正反合的否定之否定,这种看法是有根据、有道理的。对此,结合伽达默尔的一贯风格也不难理解。这个被西方学者称为没有“绝对精神”的黑格尔主义者,思想一向不温不火,不走极端,而是致中和。就这一点而言,也体现出他的解释学的辩证法倾向。当然,伽达默尔始终是在一种新的视域下,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实践智慧)为核心,来建构自己的解释学的,即便吸收了康德的一些思想,也不是平均的对待,因为从根本上讲,伽达默尔是反对康德先验论的哲学立场的,这就决定了总体上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性质,而非新康德主义的性质。
本书最后一章,上升到一个更高的高度,那就是对实践智慧作普遍哲学意义的把握。这里牵涉到重新回到关于“实践”的理解,它超出康德的狭隘性,涉及到人的感性活动、自由选择、具体的善和整体的善,并围绕着实践智慧与实践哲学、精神科学、解释学以及修辞学之间的关系来展开,它涵盖人的整个生活世界,所关联的是人文主义这条线。这条线自维柯以来,开始与科学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立,而科学主义这条线一直占上风。作为现象学运动一个分支的哲学解释学则让人认识到,现在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到“实践”的名下,这个实践不应是近代以来被科技所扭曲了的实践,而是真正的实践。晚年的伽达默尔说得好,“种种唤起意识的形式都来自于实践,离开了实践将是纯粹的虚无。这就是从解释学的问题出发所重新证明的知识和科学的特殊意义”(第28页)。由这个角度生发开来,实践哲学在伽达默尔那里的确真正成了第一哲学,一切都需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才能谈,才能找到其合理性的定位,而从解释学的角度来展开这一点,既体现了伽达默尔思想的重要特色,也反映出他独到的学术贡献。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国内学术界开始注意到解释学与实践哲学关系的探讨,迄今为止已出的成果不算少,然而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如何具体通向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这个过程中,实践智慧到底起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色,它与解释学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却缺少全面、系统的考察,即便在这方面有所论述,往往也是零散的、比较空泛的,很多意义及历史背景尚未得到深入的挖掘。邵华博士在这个领域做出了扎实、重要的推进。此书将伽达默尔与亚里士多德的关系集中于解释学与实践智慧之间的关系来把握,内容十分丰富,连带出一系列重要的问题,如:实践、实践知识、共同体、语言、人文科学、人文精神、人文传统、反科学主义、真理、修辞、消除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等等,尤其是将实践智慧与伽达默尔所提及的人文主义的四个基本概念——教化、共通感、判断力和趣味——联系起来认识,十分重要。总之,这本书真正做到了以小见大,达到了“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的效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将康德作为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补充纳入到伽达默尔解释学的理解,一改过去人们读《真理与方法》第一部分所易获得的印象,具有启发性。的确,时至今日,在实践哲学的范围内,单纯的康德主义或亚里士多德主义似乎都有自己的“短板”,都难令人完全满意,康德实践理性的“刚性”和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柔性”的结合,可能是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这是伽达默尔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当然,如何进一步落实到解释学领域,这方面仍需要作者今后进一步深入钻研,以达到更加全面的理解和认识,相信这个方向是大有前途的,也是可以与国际接轨的。
责任编辑:陆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