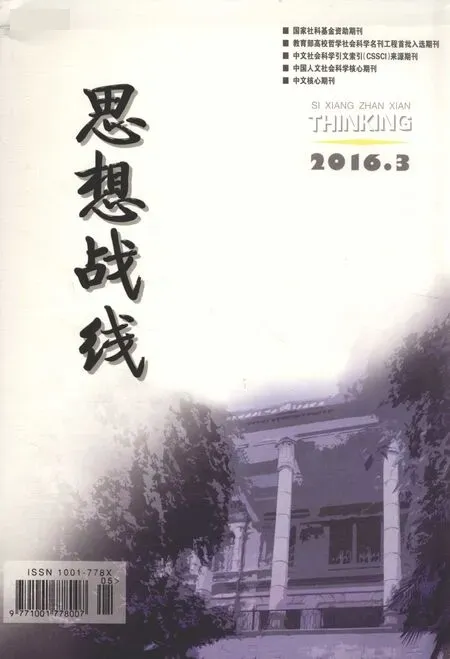论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
2016-04-11王汶成
王汶成,高 岩
论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
王汶成,高岩①
摘要:话语在成为话语之前有一个语用过程,而研究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就是研究其语用过程的独特性。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一切话语都有共同的语用目的——“指涉意义”,而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则在于“以审美的方式指涉意义”,或者说,在于指义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文学话语不像非文学话语那样直接,而是间接地指涉意义,即采用种种语用手段在话语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设置某种“间隔”,从而造成一种语义含混的审美效果。其中最重要的语用手段就是“以虚构模拟现实”。文学话语以其创构的虚拟世界激发起读者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又反过来改变旧现实和创建新现实。
关键词:文学话语;语用特性;审美地指涉意义
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是用来说话的,说话者运用所掌握的语言系统说出的话,就是所谓的话语。所以,话语在成之为话语之前必有一个语言运用的过程,也就是从每个人习得的语言库存中“选词造句”的过程,正是通过这个过程,话语从无形的可能变为有形的现实。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必须先学好一种语言才能用这种语言说话,事实上,学习语言与使用语言是同时并举、交互作用的。但是,具体到每一次说话的个别情况,则一定是使用语言在前,说出话语在后。就像一个婴儿第一次用母语叫出“妈妈!”这句话,那是因为这个婴儿已学会了发出和使用“妈妈”这个词。正因如此,我们探讨文学话语就先从语用问题开始。
一、语用意义、语用规则、语用特性
语用问题在索绪尔的语言学里基本没有位置,因为索绪尔主张的是研究符号系统的“语言的语言学”,至于语用问题则归入“言语的语言学”,不在他的语言学研究对象之列。*参见[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42页。维特根斯坦是最早揭示语言运用的重大意义的语言哲学家之一,他指出,语言只有在被使用的时候,才有了生命,才能实际地表达一个意义。他说:“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67页。这倒不是说这个词在未被使用时没有意义,每一个词都有其固有的意义,但那只是一种语言学的意义,一种在字典里都可以查到的字面的意义,这一意义正是它可以被使用的依据。维特根斯坦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一个语词只有在具体的使用中,才在其语言学的意义之上又被赋予了一种有活力的意义、一种起着实际表达力的意义,可以称为语用学的意义或话语意义。例如,面对一只狂吠的狗,我给随我走的孩子提醒道:“狗!”。在这里我用了“狗”这个词,绝不只是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告诉孩子这是一只犬科食肉动物,而是警示这个孩子别让这只狂叫的狗袭击了他。所以,更为重要的不是词语的语言学意义,而是词语在使用中的意义,也就是它的语用意义或话语意义。即如分析哲学家塞尔所说的:“语句的语言学意义所起的作用使说话人能够在说话时运用语句来意谓某种东西。说话人的话语意义对于我们分析语言的功能的目的来说是首要的意义概念。”*[美]约翰·塞尔:《心灵、语言和社会》,李步楼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第137页。可以看出,对话语来说,语言的运用同所运用的语言本身同等重要,它是话语及其意义得以确立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维特根斯坦这一观点的启发下,后来的语言哲学家,诸如巴赫金、奥斯汀、格赖斯等等,都着力研究语言运用的问题,并最终促成了专门研究语言运用的学科——语用学(pragmatics)的产生。
语用学理论认为,说话者用语言说话不是任意妄为的,必须要遵守一定的规则。这里说的规则,主要还不是指语法规则,而是指语用规则,即说话者如何运用语言的方法,简称语言的“用法”。也就是说,人们用语言说话,不仅要遵守语法规则,还要遵守语用规则,要满足一定的用法上的要求。比如说,见了熟人问好,虽是很简单的一句话,但也要考虑选择合适的“用法”,给长辈、给平辈以致给晚辈问好,在“用法”上都有很大差别,不能不分场合地乱说一气,则达不到问好的目的。维特根斯坦认为,每一种语言游戏都在显示着一种对语言的用法,不同的语言游戏有不同的语言用法。人的活动和生活形式是无限多样的,语言游戏也是无限多样的,语言的用法也是无限多样的。他说道:“我们叫做‘符号’‘词’‘句子’的东西有无数种用法。”*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57页。巴赫金也认为,“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都与语言的使用相关联。显而易见,使用语言的性质和形式,也像人类的活动领域似的多种多样”“语言的运用范围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参见[俄]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第189页。据此推论,文学活动中的话语当然也是语言的一种独特用法,研究文学话语的语用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弄清楚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
巴赫金还特别指出,一种话语的语用特性取决于这一话语的特殊的语用条件和目的。他是这样说的:“这些表述不仅以自身的内容(话题内容),不仅以语言风格,即对词汇、句子和语法等语言手段的选择,而且首先以自身的布局结构来反映每一活动领域的特殊条件和目的。”*[俄]巴赫金:《文本 对话与人文》,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0页。从这段话可以见出:一是所谓的语用特性主要体现在特殊的“话题内容”“语言手段”(修辞等)“布局结构”三个方面;二是所有这三个方面又是由话语活动的“特殊的条件和目的”决定的。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话语怎样使用语言(语用特性)取决于它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语言(语用环境),以及它使用语言要做什么(语用目的)。因此,在说明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之前,有必要先探究一下文学话语的语用目的何在。而探究这个问题显然又关涉到语言的功能问题。
二、所有话语共同的语用目的
我们知道,索绪尔开创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在后来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新的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将结构研究与功能研究结合起来,并于20世纪20年代形成了以俄国语言学家雅各布森为代表的功能语言学派(也称为布拉格学派),后又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了英国语言学家韩德礼创立的系统功能语言学。所有这些新生的语言学派都以语言的功能为主要研究对象,都构建了一系列关于语言功能的理论。雅各布森曾提出过语言六功能说,即指称功能、表情功能、意动功能、交际功能、元语言功能、审美功能;*参见[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83~86页。韩德礼则区分了三种语言功能: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谋篇功能。*参见张德禄《功能文体学》,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4~55页。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更为细致地划分了语言的功能,他总共列出了“交流思想”“情感表达”“社交功能”“声音的力量”“控制现实”“记录事实”“思维工具”“认同功能”等八种功能。*参见[英]戴维·克里斯特尔《剑桥语言百科全书》,潘炳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4~17页。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生存和发展所涉及的三大关系,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关系,都离不开语言,都要靠语言这个中介建立实际联系。人认识自然,无论是事物的命名、事实的说明、概念的推衍、思想的表达,都要凭借语言来实现。人与人的社会交际活动,从最简单的见面问好、日常会话,到复杂的法庭辩论、会议演讲、文章写作,都是语言在起着关键的作用。人的自我交流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没有语言参与其中,人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所想做出任何反应。维特根斯坦就说过:“‘思索’在这里应该是指某种与‘自言自语’差不多的事情。”*涂纪亮:《语言哲学名著选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62页。正因如此,语言学家们对语言功能所作的分类研究自然就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用意义。我们从这些研究中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虽然语言的功能五花八门,不可计量,但所有这些功能都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功能之上,这就是语言的描述事态、表情达意的功能,我们姑且将这种功能称为语言的指义功能。我们无论在何种场合出于何种目的说出的每一句话,都首先要表达一个意思,要指向于一个意义,其次才谈得上其他的功能和作用。比如一句简单的话“请拿过那本书来”,对这句话来说,最紧要的一点就是,它试图利用语言的“指义功能”表达一个意思,以便让对方明白需要拿过来的到底是哪本书以及这本书在什么地方,弄清这些之后,这句话才可能起到请求对方拿过那本书来的“意动功能”。这就是说,在语言的诸多功能中,指义功能是基本功能,其他意动功能都必须由这一功能衍生出来或附着于这一功能之上,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既然所有使用语言的话语都一定指向于一个意义,那么,包括文学话语在内的一切话语就具有了同一个语用目的,这就是指涉意义的目的。这里说的指涉意义,可以是指示一个事物、陈述一个事实、说明一个概念、讲述一个故事、论证一个想法、抒发一种情感,等等不一,但都体现为指涉一种意义这个同样的目的,这也决定了一切说出的话语都具有同样的一种语用共性。英国语言学家查理曼将这种语用共性称为“语言共核”。他说:“文学文体的力量来源于‘语言共核’,连最具‘文学性’的特征也来源于‘语言共核’。文学偏离常规并不会破坏它与‘语言共核’使用者的交流。”*[英]雷蒙德·查理曼:《语言学与文学》,王士跃等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16页。这里说的“文学性特征”“文学偏离常规”属于文学话语独具的语用特性,我们以后再讲。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由于语言共核的存在,由于共具同一个语用目的,文学话语与日常话语、科学话语等不同的话语之间,就有了相通之处。这种相通之处使得它们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界限分明的,而经常出现相互渗透、相互交错的情况。“新批评”后期的代表人物韦勒克就曾说过,把文学的、日常的和科学的这几种话语在用法上严格区分开来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不同,他没有专门隶属于自己的媒介,在语言用法上无疑地存在着许多混合的形式和微妙的转折变化。”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的语言用法之间的区别是流动性的,没有绝对的界限。”*参见[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10页、第13页。由此看来,那种试图将文学话语、日常话语、科学话语截然区分开来的观点是不妥当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这几种话语都共有同一个语言内核,都同样指向于一个意义,都同样利用语言的指义功能来实现自己的语用目的。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所抱有的这种特定的语用目的,因为这几种话语虽有共同的语用目的,但又有它们各自特定的语用目的,因而,对某种最适合它们的语用目的的语言功能“情有独钟”,并将其摆到首位而加以利用,由此就形成了它们各自的语用特性。诚如俄国语言学家日尔蒙斯基所说:“如果把语言形式当做‘活动’去审查它的结构,那么我们就能发现,语言有多种目的意向,这些意向决定着词的选择和组词的基本原则。”*[俄]日尔蒙斯基:《诗学的任务》,载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方珊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18页。这就是说,每一种话语都有共同的语用目的,同时还有着自己特有的语用目的,正是这个特有的语用目的决定着这一话语的语用特性。
三、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在于“以审美的方式指涉意义”
那么,文学话语特有的语用目的是什么呢?一个小说家创作一部小说,或者一个诗人写出一首诗歌,他是为了什么呢?一是为了表达他的某种思想和情感,这是实现语言的指义功能,属于所有话语共同的语用目的;二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种审美的愉快,这是实现语言的审美功能,属于文学话语独具的语用目的。前文提到雅各布森的语言六功能说,其中就论及语言的审美功能。现在,我们可以参照他的这一理论,将他说的六个功能进一步归纳并合为两大功能:一大功能是作为语言的基本功能的指义功能(包括他说的指称功能、表情功能和元语言功能),另一大功能是附立于指义功能之上的诸多效果功能,而审美功能即是这诸多效果功能中的一种。我们认为,文学话语以指义功能作为它与其他话语所共有的语用目的,以审美功能作为它自身特有的语用目的。前者为最终的语用目的,后者为直接的语用目的,最终语用目的的实现要以直接的语用目的之实现为前提,两个语用目的的这种内在关联,就构成了巴赫金所说的决定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的“条件和目的”。据此,我们可以把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确定为通过审美的效果达到指涉意义,或者说,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就是指义性与审美性的统一。
我们关于文学话语语用特性的观点主要借鉴了当代的话语理论和语用学理论,因而与传统的内容主义观点不同,也与现代的形式主义观点有异。传统观点的主要倾向是把文学话语当做传递思想内容的形式载体来理解的,因而它最为看重的是语言的指义功能,要求在运用语言时应该让词语尽量准确、清晰、顺畅地表达思想内容,至于所用词语的审美效果并不重要,甚至可有可无。这种观点在我国先秦思想家那里表现得尤为突出。比如,孔子虽主张“文质彬彬”,但却强调“辞达而已矣”,认为“巧言乱听”“巧言令色,鲜矣仁”。*语出《论语》“雍也”“卫灵公”“学而”等篇,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载《诸子集成》第1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125页、第349页、第345页、第5页。老子更是把“信言”与“美言”对立起来,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断语。*语出《老子》第81章,见王弼《老子道德经》,载《诸子集成》第3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47页。韩非子则直接从政治需要提出:“喜淫辞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语出《韩非子》“亡征”篇,见王先慎《韩非子集解》,载《诸子集成》第5册,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版,第78页。可见,在传统理论看来,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仅在于其指义性,而其审美性则遭到怀疑乃至排斥。我们的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文学话语直接的语用目的就是审美效果的追求,文学话语只有通过审美效果的获得,才能实现其指涉意义的目的。因此,我们理解的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中,虽然审美性要以指义性为旨归,但指义性又必须以审美性为前提。
在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问题上,现代形式主义的观点则强调语言运用在文学话语中的本体地位,认为语言运用就是文学话语之为文学话语的本质之所在。比如,俄国形式主义者就提出,文学话语的语用特点正在于以“反常化”的手法凸现语言形式本身,产生所谓“惊震”的审美效果,文学话语的全部语用手段,都是为了制造这种审美效果,而与再现和认识现实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样,在现代形式主义那里,审美性成为了文学话语的惟一的语用特性,而指义性则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因而也不是非有不可的。我们与形式主义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因为,我们是将审美性与指义性联系起来来理解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的。一方面,我们认为审美性是指义性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我们又认为审美性必须以指义性为指向。虽然审美性和指义性都是文学话语的语用目的,但审美性是直接目的,指义性是最终目的,两个语用目的之间实际上有一种前因与后果的关系。现代形式主义的问题就是仅强调审美性这个前因式的目的,而掩蔽了指义性这个后果式的目的。事实上,当我们说一首诗或一篇文学话语具有审美效果时,绝不是仅仅因为这首诗语音的韵律和谐和节奏的悦耳动听,而是因为在这种悦耳的韵律和节奏中,我们领会到了一种思想和情感的意义。如果这首诗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声音组合,即使这种声音组合再悦耳动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话语的审美效果。因为凡话语必有意义,文学话语的审美效果只能在意义的领会中才能产生。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我们将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界定为审美性与指义性的有机统一,并将这种统一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文学话语的语用特性就是以审美的方式指涉意义。
四、“审美地指涉意义”的语用学解释
现在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如何理解文学话语的这种语用特性?什么是“审美地指涉意义”?简捷地说,“审美地指涉意义”就是指:文学话语在表达他所表达的意义之时,不是像非文学话语那样直接地表达这一意义,而是间接地表达这一意义。在我们的这个解释里,“间接地”就等同于“审美地”,“间接地”指涉意义就是“审美地”指涉意义。文学话语总是采用种种语用手段在它的“能指”(语言表达)与“所指”(语言表达所指涉的意义)之间设置某种“间隔”,使得意义的表达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迂回的、被延迟的和受阻碍的,从而造成一种语义的含混、含糊、含蓄的特殊审美效果。文学话语之所以运用各种语用手段来间接地指涉意义,就是为了制造出这种语义模糊或言外之意的审美效果,这是文学话语最突出的语用特点,也是文学话语与非文学话语在语言用法上的根本区别。非文学话语,特别是科学话语,追求意义表达的准确性、明晰性,即从词语到词语所表达的意思(或者说从词语的能指到所指)之间越直接、越明快、越没有阻碍越好,尽管这个指标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很难完全达到。例如,用科学话语表述“三角形的三内角之和等于180度”这一几何定理,只需直接将这个定理的内容说得尽可能的明白清楚即可,不需要且不允许使用任何修饰的词语和比喻的说法。然而,文学话语则与此截然相反,它所要求的不是语言表达的直接性和透明度,而是语言表达与要表达的意义之间的延宕和阻隔。只有这样,文学话语才创造出了一种语用模糊、语义含蓄的审美效果。
但是,这里又有一个问题需要解释,这就是,间接地指涉意义为什么就能造成语义含蓄的审美效果呢?要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借用美国语用学家格赖斯(H.B.Grice)在1967年提出的“会话含义”(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学说。*参见俞东明《什么是语用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3页。格赖斯发现,在言语交际活动中,谈话的双方总是共同默守着一个潜在的规则展开会话,他把这个潜在的规则叫做会话的“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就是说,人们为了交际的成功,在会话中总是趋向于相互配合,参与会话的每一方都尽量准确而适当地提供对方要求的信息,也尽量准确而适当地理解对方所提供的信息。格赖斯又把这个合作原则细分为四条准则:一是数量准则,即所说的话应该如交谈目的所要求的那样详尽,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二是质量准则,即尽可能说真话,不说自知虚假的话,不说证据不足的话;三是关系准则,即所说的话要切题,要前后关联;四是方式准则,即说话要尽量明白清楚,简练而有条理,避免表达上的晦涩和歧义。格赖斯同时指出,完全严格遵守四条准则的言语交际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实际的会话交际往往或多或少地违反这些准则,这就造成了“会话含义”的产生。所谓“会话含义”就是指说出的话里含有模糊不清、难以确定的意义内容。*参见俞东明《什么是语用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76页。例如,我问你:“你身体好吗?”你却回答:“我正在读书。”你显然是答非所问,违反了“合作原则”,你回答的话里就有了“会话含义”,使我不好理解你到底想说什么意思,我和你的谈话也就难以为继了。后来的英国语言学家利奇(G.H.Leech)又提出了“礼貌原则”(politeness principle)作为对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的补充。他指出,人们违反合作原则而使自己的话语产生会话含义,在很多时候,并非因为无意的过失,而是有意而为的,其中最常见的情况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参见俞东明《什么是语用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举个例子,假设一个病人的病情危重,很可能死去,病人的亲属问医生:“病人的情况怎么样?”医生回答说:“对不起,我们已经尽力了。”在这个回答里,医生为了照顾病人亲属的心情,不忍心让他太难过,有意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关联准则,说了一句意思含糊的话。但病人的亲属马上就能理解医生话里隐含的意思(会话含义),知道病人已经生命垂危了。这就是利奇所说的礼貌原则,它揭示了一个重要的语用现象,有时人们为了某种语用目的而故意违背一些语用规则。
上述的语用学理论提示我们注意到,文学话语间接地表达含蓄意指的语用特性,其实就是对合作原则诸准则的有意违反。因为我们发现所有故意违反合作原则诸准则而产生会话含义的话语,都是意图间接或曲折地表达意义,都导致隐晦的或含混的意指。比如前面举的那个医生回答病人亲属的话,就是委婉地、也就是间接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从而使他的话里隐含着一种言外之意。只不过文学话语故意违反合作原则的诸准则,并不是像日常话语那样出于礼貌原则,而是为了给读者造成一种审美的效果。例如,李煜的那句著名的词:“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诗人在这句词里没有直接说他的愁多么多,而是用了一个比喻间接地表达了他的意思。从语用的合作原则看,诗人的这种间接表达是同时违反了数量、质量、方式等准则。但诗人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他为的是让自己要表达的意思更加隐蔽含蓄,让读者用更多的想象来揣摩他的这个意思,这是诗人有意制造的审美效果。美国当代哲学家乔纳森·卡勒(Jonathan Culler)也注意到了文学话语故意违反会话合作原则的这种语用特性,他说,“交流基于一条根本的程式,即参加者的相互配合”,而“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合作原则是‘超保护’的,我们可以忍受许多晦涩费解和明确不切题的东西,而不认为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读者也想当然地认为在文学当中,语言的费解、不通,肯定也是为了一定的交流目的。所以他们不像在其他语境中那样断定是发言人或者作者没有配合,而是努力去理解那些复杂的语言成分,而这些成分对那些为深入交流而设立的有效原则常常是全然不顾的”。*参见[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28页。所以,从语用学的角度看,文学话语间接地表达含蓄意指的语用特性恰恰是有意违反会话的合作原则的结果。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必须说明,文学话语在间接地表达含蓄意指时使用了哪些具体的语用手段呢?总体来说,文学话语使用的具体语用手段多种多样,不能也不必一一罗列,但可以将这诸多具体语用手段归纳为以下三种类型。其一是通过凸显语言自身来指涉意义,或者说,语言通过指涉自身来指涉意义。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歌话语讲究语音的韵律和节奏,通过悦耳的韵律和节奏吸引读者,由此诱使读者领会诗歌话语的意义。其二是在言语与意义之间插入一个形象,也就是用言语描写形象,用形象指涉意义。譬如中国的古典诗歌追求意境的创造,这里的“意境”就是用语言描绘的一个有声有色的形象世界,而诗歌所表达的意义就蕴含在这个形象世界里。再譬如小说话语也往往是通过塑造人物形象来曲折地传达思想意义的。其三是通过虚构一个假想情境来折射现实情境和表达关于现实的思想。这里的意思是说,文学话语并不直接描述现实,而是述说一个虚构情景,并以此模拟出现实情景,从而间接地暗示出某种关于现实的思想。正如乔纳森·卡勒所指出的,“文学作品是一个语言活动过程,这个过程设计出一个虚构的世界”“文学的虚构性使其语言区别于其他语境中的语言,并且使作品与真实世界的关系成为一个可以解释的问题”。*[美]乔纳森·卡勒《当代学术入门:文学理论》,李平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3页、第34页。文学话语以其创构的虚拟世界激发起读者的创造性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又反过来改变旧现实和创建新现实。这也许正是由文学话语生发的审美效果所体现出的最强有力的建构功能。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①王汶成,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岩,山东政法学院副教授(山东 济南,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