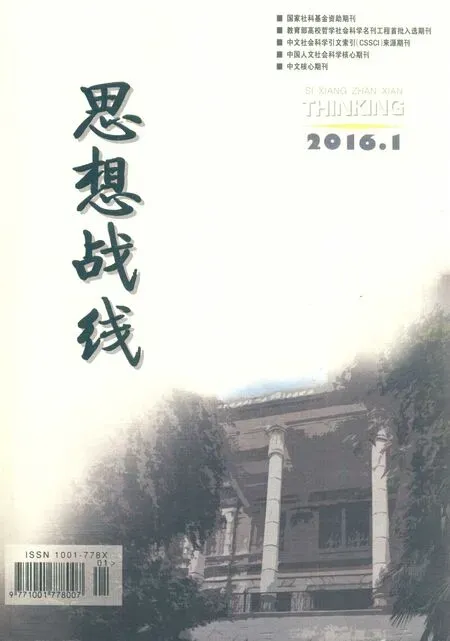“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的单行条例功能
2016-04-11沈寿文
沈寿文
“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的单行条例功能
沈寿文①
摘要:从单行条例制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看,单行条例在内容上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用以展现民族自治地方“民族”特色的特殊法规。在“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自治区和自治县单行条例的功能集中体现了“优惠照顾”目标,而自治州行使单行条例制定权,正是填补自治州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前,没有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缺陷;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是自治州单行条例功能发生变迁的重要转折点。
关键词:“优惠照顾理论”;自治州;单行条例;功能
“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制定的调整本自治地方某方面事务的规范性文件。……单行条例是民族自治地方行使某一方面自治权的具体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flsyywd/xianfa/2001-08/01/content_140409.htm。然而,作为立国之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下称《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下称《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下称《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基本法律为什么要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单行条例的制定权?单行条例到底有何实际功能?单行条例的功能是否是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尽管学术界多年来对单行条例有过大量的研究,但迄今为止,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象般的清晰和明确。
一、单行条例制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基础
按照《宪法》(2004年)第116条、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第19条和《立法法》(2015年)第75条关于“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规定,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制定“单行条例”的“事实”(条件)依据与制定“自治条例”的“事实”(条件)依据是相同的,是民族自治地方的“民族”要素(尤其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和“地方”要素的结合,而且“民族要素”是第一位的,正如有研究所说的:“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而言,很重要的便是体现当地的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而且,就民族特点与地方特点而言,民族特点应该是第一位的,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立法属于特殊性地方立法,比一般地方立法享有更大的自主性。既要体现地方特色,更要突出其民族特征。‘民族性’是自治立法的核心,也是自治立法与一般地方立法的区别所在。如果没有‘民族性’的存在,不仅不可能存在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就连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没有存在的必要。”*康耀坤等:《中国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因此,按照这种观点,考验实践中颁布的单行条例是否符合这种法律性文件的性质,“民族”内容便是核心的指标。*类似观点参见张世珊《关于制定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韦苇《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单行条例的思考》,《贵州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程建《论单行条例——从内蒙古自治区单行条例立法现存问题谈起》,《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周鹄昌《单行条例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熊文钊等《试论单行条例及其变通规定的制定》,《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等。
然而,上述观点是否真的具有法律文本依据和事实基础?一方面,就法律文本的依据看,主要有《宪法》(2004年)第116条、《立法法》(2015年)第75条、《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第90条。在上述条文中,单行条例制定的所谓“民族”特色,在文本的表述上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然而,“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显然并不是单指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特点,而是“当地”(即民族自治地方)所有“民族”总体上的特点,实质上也就是“当地”(即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情况。单行条例制定的这一依据,根源于对民族区域自治主体的正确界定之上。在这个问题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王培英同志指出:“《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都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 设立自治机关, 行使自治权。’这里表述得十分清楚、毫无疑义,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是‘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而非哪一个‘民族’。邓小平提出‘要使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这段文字最初是‘要使各民族真正实行民族区域自治’。《邓小平文选》的这一处重要修改, 其要旨就是要准确论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问题。”*王培英:《论自治条例单行条例的法律地位》,《思想战线》2000年第6期。正因如此,以“民族”特色(尤其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体民族)来衡量单行条例的内容,并不具备充分的法律文本上的依据。
另一方面,就事实基础看,单行条例在实践中反映出“民族”特色不足的特点,也与上述观点相左。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自1994年至2014年制定的17部单行条例为例,按照上述观点,红河州绝大多数单行条例便存在“民族”特色不明显的“弊病”。在这17部单行条例中,除了1999年制定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教育条例》内容上直接涉及“民族”要素外,其他16部单行条例与“民族”没有必然的关系,它们分别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异龙湖管理条例》(1994年)、《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1995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林业管理条例》(1995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建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条例》(1996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水资源管理条例》(1997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农村合作医疗条例》(2001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金湖管理条例》(2001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发展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条例》(2006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城市管理条例》(2007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五里冲水库保护条例》(2007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条例》(2007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气象条例》(2009)、《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哈尼梯田保护管理条例》(2012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州历史风貌街区和风貌建筑保护条例》(201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红河州建水紫陶产业发展条例》(2014年)、《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豆制品产业发展条例》(2014年)。红河州单行条例的这种状况,与全国各个民族自治地方的单行条例在内容上“民族”特色不明显基本一致。按照张文山教授的研究,就全国范围看,单行条例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9个领域39个类别:“一是教育、科技、文化领域,具体是教育管理、民族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与扫除文盲、科技管理、民族文化、民族语文、档案管理、文物管理、名胜景区管理;二是经济管理领域,具体是工业管理、农业与农村管理、林业管理、畜牧业管理、渔业管理、水利水电与库区管理、贸易管理、公路管理、旅游管理、邮电通讯管理;三是行政管理领域,具体是城乡规划与城镇管理、开发区管理、防灾减灾;四是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领域,具体是土地资源管理、经济林木管理与生物化石等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五是财政管理;六是风俗习惯;七是人口、卫生领域,具体是计划生育、流动人口与暂住人口管理、农村合作医疗、地方病防治与计划免疫、医药管理;八是劳动、未成年人保护;九是法制与监督领域,具体是法制工作、监督工作、社会治安治理禁毒工作。”*张文山:《通往自治的桥梁——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56页。显然,除了“民族教育”“民族文化”“民族语文”等少数类别外,绝大多数的内容与“民族”并没有直接关系。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没有多少“民族”特色的单行条例,在内容上与地方性法规类似,往往比较具体,条文具有比较强的可操作性。比如在红河州的单行条例中,无论是湖泊水库的管理保护,还是城市,以及历史风貌街区和风貌建筑的保护,还是自然资源的保护,或者某一产业的保护等等,单行条例的条文均有具体的规范和较强的可操作性。
单行条例的上述状况表明:单行条例在内容上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用以展现民族自治地方“民族”特色的特殊法规。这种未必体现“民族”特色的特殊法规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有着什么样的功能,仍然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二、“优惠照顾理论”范式下的单行条例功能定位
理解单行条例的功能,存在“地方自治”“民族共治”和“优惠照顾”三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一方面,“地方自治理论”从“民族区域自治”出现“自治”一词的字面含义出发,以国际意义上的“地方自治”来解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包括单行条例制定权在内的民族区域自治权。该理论范式认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上是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的“分权”(Decentralization)制度,包括单行条例制定权在内的“自治法规”制定权在本质上是地方自治立法权。比如,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定性上,有研究认为,“当代中国的地方制度表现为在宪法规定的基本原则之下,实施不同形式的地方自治。这些地方自治的主要形式有: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自治、城镇居民自治与村民自治,此外,中国一般地方制度下也包含着一定事务的自治”。*田芳:《地方自治法律制度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又如,有研究认为,“正确划分中央与民族地区的权限问题,对多民族国家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国是单一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利, 对于中央集权来说,是民族自治地方分权”。*李瑞:《试析自治权行使的制约因素》,《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0年第6期。类似观点参见宋才发《自治权的立法自治权及自治条例问题研究》,《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吴宗金《中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学》(第二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3页;王允武等《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分权的法律实证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田钒平《民族自治地方自治立法权限的法律实证研究》,《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9年第1期;潘弘祥《自治立法的宪政困境及路径选择》,《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等。然而,由于地方自治的本质是在宪法或者法律所划定的权限范围内,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当局(地方自治机关)代表所辖区域居民,“以地方之人、地方之财、办地方之事”。从国家权力的纵向配置上看,地方自治以中央与地方权力制度化划分为前提。换言之,哪些公共权力属于中央专有、哪些公共权力属于地方专有、哪些公共权力属于中央和地方共有,是通过法制化的机制(由宪法或者法律)加以明确规定的;当二者之间发生权力纠纷时——比如地方认为中央侵夺了它的专有权力,或者中央认为地方侵夺了它的专有权力——便需要一套解决权力纠纷的救济机制(也就是违宪审查机制)。如果严格按照“地方自治理论”范式解读单行条例的话,那么单行条例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在(论者所设想的)法定“分权”范围内,不受中央和上级机关干预的、自主规定民族自治地方某一方面事务的“地方自治法规”;单行条例的主要功能便是实施地方自治、自主落实特定地方居民的意志。
另一方面,“民族共治理论”以现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践为基础,发现现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规定并不是单纯的“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中国的少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不是民族社会组织的自治,也不是民族领土单位的自治,而是把少数民族的自治权体现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地方管理之中,自治地方的管理又以有关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民主协商为原则,即实行少数民族地方自治与民族共治相结合的民族政治制度”。*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在“民族共治理论”看来,“自治”与“共治”是构建多民族国家民族政治权力结构的两块基石,……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一种“后自治”民族政治制度,它的基本特征是以民族杂居地区的自治为基础,通过各民族对国家和地方的共治追求各民族的共和,这种“共治”是由民族杂居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这种“复数”(多个民族)的“民族区域”所决定的。*朱伦:《民族共治论——对当代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事实的认识》,《世界民族》2001年第4期。在“自治”与“共治”的关系上,“民族共治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仅仅是手段,目标是实现中国各民族对国家平等的共同治理(共治)。*雍海宾等:《民族共治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学思考》,《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民族共治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单行条例的论述,但在此问题上,这一理论与“地方自治理论”有着共同的前提预设,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意义上的“自治”就是国际社会意义上、以中央和地方“分权”(Decentralization)为前提的地方自治。*朱伦指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实行民族地方自治的关键是划定自治地方权限,保证自治地方依法行使这些权限。自治地方的权限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说从来源上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赋予自治地方单独行使的专有权限;二是国家与自治地方共同行使的共有权限;三是国家委托自治地方有限行使的代行权限。但无论哪种权限,它都不是自治地方固有的,而是来自国家授权,它的存在和行使是以保证国家内部主权统一为前提的。”参见朱伦《达赖集团的“大藏区高度自治”主张评析(上)——兼论民族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发展》,《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只不过“地方自治理论”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定性为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事务,“自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而“民族共治理论”则认为,少数民族“自主”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自主”管理本地方事务仅仅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个方面,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有各个民族,以及代表各个民族的一级地方政权机关(自治机关同时是一级地方政权机关)参与国家治理的另一个方面,因而,“自治”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乌力更:《民族自治与民族共治——权利与少数民族》,《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由此,按照“民族共治理论”,在单行条例的解读上,与“地方自治理论”有着基本相同的立场。
然而,由于《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本质上并不是地方自治制度(而是国家对特定地方的优惠照顾制度),《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立法法》所确立的中国立法体制并不是“分权”(而是“分工”),*参见沈寿文《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性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因而,单行条例的功能无法从“地方自治理论”和“民族共治理论”范式得到令人信服的解读。而“优惠照顾理论”范式既有明确的法律文本依据,也符合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包括单行条例制定权)的实践。
从功能的角度上看,《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为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照顾权利提供了一个基点,甚至单行条例的制定权本身便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授权的产物,是优惠和照顾的体现之一。民族自治地方——特别是从与设区的市同级的自治州,以及与县、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同级的自治县两个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这种优惠和照顾在1984年民族区域自治法制定时,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可以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它意味着,自治州和自治县拥有了一般的设区的市以及县、不设区的市和市辖区所没有的“自治”立法权。然而,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央对一般地方不断放权——比如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不断下放给一定层级的地方(省会城市、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等等),导致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这种优惠和照顾相比较中央对一般地方而有所淡化。*沈寿文:《自治机关“自治权”与非“自治权”关系之解读》,《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即便如此,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0条关于“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的规定,通过一般授权,赋予民族自治地方机关对“上级国家机关的决定、决议、命令和指示”一定条件的“变通”执行权,或者“停止”执行权;《立法法》第75条第二款关于“单行条例可以依照当地民族的特点,对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但不得违背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不得对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专门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规定作出变通规定”的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等法律专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制定变通的或者补充的规定”,则通过单行法律的特别授权,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采取一定的形式(特别是通过单行条例的形式),在一定条件下作出“变通”规定或者“补充”规定的权力,均是中央对民族自治地方优惠和照顾的体现。
从“优惠照顾理论”出发,可以有效地解释实践中单行条例“民族”特色不鲜明的现象。从功能的角度上看,赋予优惠和照顾的事实条件是民族自治地方“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然而,在理解这一条件时,如前所述,“当地民族”并不仅仅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它同样包括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其他民族;这就意味着,“当地民族”的提法实际上也就是“当地各族人民”的整体情况,也就是“当地的实际情况”。因而,单行条例是否一定要有“民族”特色——尤其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的特色,实际上并不必要。云南省红河州颁布的17部单行条例,乃至全国各个民族自治地方颁布的众多的单行条例所呈现出来的普遍缺乏“民族”特色的共同特征,正是客观条件使然。如果一味地追求“民族”特色,便极大地限制了单行条例的规范内容。其实,不仅云南省红河州涉及异龙湖管理、矿产资源管理、林业管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水资源管理、农村合作医疗规范、个旧金湖管理、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发展、个旧城市管理、五里冲水库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工会规范、气象管理、历史风貌街区和风貌建筑保护、建水紫陶产业发展、石屏豆制品产业发展等单行条例,与“民族”特色并没何必然关系;而且,国内其他民族自治地方制定的单行条例也同样普遍缺乏“民族”特色,恰恰是单行条例能够真正发挥一定功能的需要。换言之,在当前立法体制之下,由于改革开放后中央对一般地方的不断放权(特别是立法权的不断下放),民族自治地方——尤其是自治州——行使单行条例制定权,正是填补自治州在2015年《立法法》修正前*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第72条第五款规定:“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依照本条第二款规定行使设区的市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职权。自治州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依照前款规定确定。”没有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缺陷。这就是为什么自治州和自治县单行条例规范的内容十分广泛;单行条例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类似,具备了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同样可以有效解释有的学者所批评的“从目前情况上看,不论是自治条例还是单行条例,自治区都是一个盲点,没有一件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这是一个令人十分困惑与费解的现象”*张文山:《通往自治的桥梁——自治条例与单行条例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75页。的缘由,因为,自治区的人大及其常委会本身便具备独立的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本身具备独立的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而在功能上替代地方性法规的单行条例须经上级国家机关批准(自治区的单行条例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才能生效),因而,在自治区这一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与自治州和自治县相比,制定单行条例便缺乏功能上的需求。
从总体上看,《民族区域自治法》与其他法律(比如《立法法》)一起,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制定权,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优惠和照顾的性质。然而,《民族区域自治法》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用以确定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中央)对特殊地方(民族自治地方)优惠和照顾制度的框架,被认为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总章程”;而自治条例则是具体民族自治地方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章程”,规定的内容同样是框架性和原则性的。由于优惠和照顾作为一项长期的制度设计,因而,对于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而言的优惠和照顾内容,在性质上属于“积极权利”,需要持续地、不断地实施,故全国人大可以通过立法(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创设包括自治区在内的各个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和照顾内容;自治条例则是具体民族自治地方贯彻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综合性法律文件,从优惠照顾的本质上看,它仅能对包括本级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在内的国家机关和下级国家机关承担起对民族自治地方的优惠和照顾义务(责任),无权规定上级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的义务(责任)。而优惠照顾的本质决定了自治条例文本不得不使用与《民族区域自治法》类似的大量模糊的“程度性”术语;不得不将优惠照顾的内容留待更低层级的法律性文件加以贯彻实施。与自治条例不同,单行条例尽管本身便是《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和相关法律赋予民族自治地方的一项优惠和照顾权力,但在现行立法体制之下,单行条例的主要功能在于弥补2015年《立法法》修正前一些层级的民族自治地方(比如自治州)没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的缺憾,因而,单行条例无论是规范的内容、调整的范围、文本的可操作性、“民族”特色缺乏等,均与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十分类似。就其规范的内容而言,与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优惠照顾制度的本质没有必然的关系;但就其获得的“自治”立法权本身而言,则是民族区域自治这一优惠照顾制度的产物和体现。
三、2015《立法法》与单行条例功能变迁
2015年《立法法》的修改是单行条例功能发生变迁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修正后的《立法法》赋予了自治州与设区的市相同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权,这就减缓了《立法法》修改前自治州由于没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因而需要通过制定单行条例来解决需要通过“立法”加以解决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自治州的单行条例在功能上成为与自治州同一级别行政建制的设区的市地方性法规的替代品,或许也因此即将成为历史。就自治州的单行条例而言,由于修正后的《立法法》将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范围限定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立法法》第72条第二款),因而,今后自治州单行条例的功能之一,就是在自治州地方性法规制定范围之外发挥作用,即:当自治州地方性法规无权规定时,单行条例便有了用武之地;此外,自治州的单行条例的另一功能是依法变通有关的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就自治县和自治区的单行条例而言,2015年修正后的《立法法》并不影响这两个层级单行条例的功能。这是因为:由于县、市辖区、不设区的市均没有立法权,所以,自治县的单行条例自始至终都较为明确地体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于国家对特定地方的“优惠照顾”,自治县的单行条例有着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法规(比如依法变通法律、法规)的功能,因而《立法法》修改后,仍然可能出台大量的自治县单行条例;而自治区的单行条例,由于自治区同时有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自治区并不存在像《立法法》修正前的自治州那样,通过颁布单行条例来弥补缺乏地方性法规的需要。
(责任编辑 甘霆浩)
作者简介:沈寿文,云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云南 昆明,650091)。
基金项目:①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边疆民族事务治理法治化研究”阶段性成果(15BFX0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