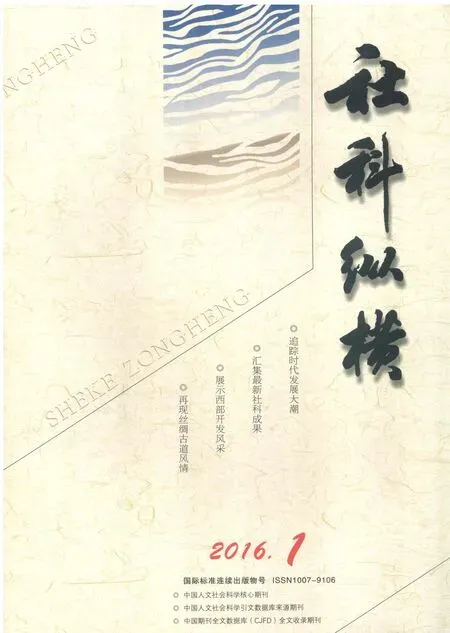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与知识的新基石
2016-04-10刘满华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泰州225300
刘满华(泰州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 泰州 225300)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与知识的新基石
刘满华
(泰州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泰州225300)
【内容摘要】本体是传统文化的基石,是理性的终极追求、情感意志的最终依托。人对本体具有天然的探索追求与终极依赖,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具有主体在场特性、共时与历时性、同一性与多样性等特征,满足当代文化的整体一致性追求,符合时代文化与精神发展需要,能建构、引导新型文化形态。
【关键词】百姓日用即道存在本体理性基石王艮海德格尔
*本文为“王艮思想生活化与消费文化建设研究”(TZYBS- 14- 6)。
一、理性与情感意志对本体的痴迷与依恋
关于形而上学或本体论作为哲学的知识体系可以追述到古希腊,第一个为其下定义的却是德国哲学家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 1754):“本体是关于各种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如‘是’以及‘是’之成为一和善,在这个抽象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产生出偶然、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本体就是“是者之本质的必然真理的演绎。”[1](P189)这个定义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普遍接受,是形而上学的核心或基石。本体与本体论在近代哲学中成为显学,“本体与本体论是一对悠久而宽泛不一的概念,有的本体或本体论着重讨论世界的根据、本原、始基,有的专门研究‘神’,有的主要探讨物质或精神,也有以人的生存和幸福为根本出发点,介绍和评价人学本体。”[2](P4)
“本体或本体论是理性无限膨胀的结果,也是其有限性的无奈。理性使你相信地球的存在是源于另一个存在。”[3](P14)
理性的天职是认识世界,并确定这种认识与客观对象的一致性,达到对世界规律认识,即获得真理。真理的知识就像地图,而“知识的地图”就像对世界同比缩小的复制。认识本身不能实现这种复制,同时,关于世界的真理性认识并不都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于是逻辑推理就诞生了。理性依据原因来推知、论证结果,那么无限推演的结果,关于世界的最后因即本体的出现就显得自然而合理。同时,最后因也是理性有限性的表现。康德现实又睿智的表述了理性这种无限欲望与自身有限性:“本体论起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4](P164)。然而康德却像其他理性主义者千方百计地赋予“本体”以永恒不变威望一样,赋予物自体以永恒不变的威望[5](P9),尽管规定这种自在之物是无法认识的。柏拉图的“理式”、黑格尔的“理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理”、“心性”与“百姓日用即道”无不体现理性的这种追求与无奈。中国文化中的本体与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区别主要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始终是主客合一的整体,没有西方文化中的主客、理性与感性的划分。
本体或本体论也是情感欲望寻求秩序与终极寄托的结果。人们通常把本体归结于理性的认知本能,却忽略了本体也是情感欲望或者精神与灵魂的天然追求。人们依据想象创造了上帝、真主、佛陀来统摄世界,把灵魂与生命交付给这些最后因的制造者或掌控者,求得合理的生命秩序与幸福人生。
本体产生的另一种原因或需要源自文化的建构特性与同一性需要。自从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文化产生于社会实践,二者相互推进。而社会与文化需要引领,建构文化就成了先贤与思想家、学者的职责。社会文化理论需要假设、推理与论证,其合理的部分,具有正价值的部分为人们接受,并加以传承。这些理论因为有益于人类生存与进步,人们相信这些理论揭示了自然或人类社会的真理,又因为这些理论有“本体”的支撑,并在逻辑推论中加以证实,所以被称为文化与信念的核心。于是,合乎情理与逻辑的结论就产生了:只要找到世界的最后依据即本体,关于宇宙的一切知识体系与真理就一劳永逸地得到确定。学者们殚精竭虑,寻找构成世界的本体,建构理论体系,引导文化走向;由于本体的唯一性,依据本体建构的理论自然具有同一性。这种美好愿望或理论体系给予人们巨大的鼓舞与勇气,人们确信能够掌握世界,对未来产生无限期盼,现世今生也有了精神寄托,并按照这种理论设计生存、奋斗。
二、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借用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的著作《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的书名,作为标题,说明传统文化范式与本体论的时代遭遇与现状。
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当代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开启了人类发展的能力与冲动的魔咒。这种发展意识与速度导致永恒的变化,致使每一个体和社会生活方式都处于不断变动与创新的过程之中。反过来,这种变化的速度与方式迫使每一个体、组织、国家不得不拼命革新、发展,目的仅仅为了社会集体和个体能够生存下去;任何人如果不根据自己的意志主动地变化,就会成为市场统治者无情地强加于人的那些变化的被动牺牲品。[6](P121)人们必须学会忘记那些曾经存在过的稳定关系与价值体系及其标准。长久一来,传统的精英们始终的渴望与努力的理想——长期不变的稳定,成为缓慢死亡的魔咒与标志。
现代人的本意试图成为现代化的客体与主体,努力掌握现代世界并把它改造为自己的新家园。然而,这种努力与愿望最终变成摧毁一切束缚主体欲望的现实与陈规的无终结革命,传统的价值观被摧毁,神圣的东西被亵渎,人类在虚无与赤裸中恢复了人的本来面目,换来了自由与平等,带来了机遇与选择的可能。
启蒙运动与证据主义首先对传统信仰的“本体”——上帝进行彻底批判。“证据主义主张一种信念只有在一个人拥有充分的证据、论据或理由时,这个信念对他才是合理的。……如果启蒙运动对有神论证据的评价是正确的,那么证据主义的假设就是信仰上帝是非理性的。”“知识分子中,对上帝的信仰自18世纪启蒙运动起就几经磨难。启蒙运动告诫大众用理智驱除迷信和轻信,甚至有人声称宗教信仰走到了尽头。启蒙时期的英雄们从知识上猛烈地批判宗教信仰的合理性。”[3](P2)时代并没有听从康德的忠告,通过理性为信仰留下适当的空间,而是彻底否定信仰的合理性。实证主义告诫人们,只有经过科学证明了的东西才是真理,其他所有的信念、经验都是虚伪的、荒谬的谎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理性启蒙与实证主义取得无与伦比成就,在思想文化领域获得核心地位。
不久,形而上学、科学、理性以及实证主义又遭到清算。“我们没有被告知我们的感觉来自何处。由于我们的感觉是在一个一致的秩序中给予我们的,这就是一个要求有某种答案的问题。”[7](P65)在从安瑟伦至今本体论证明的漫长历史中,看上去最好的情况也不能令人信服,这种证明的每个版本要么包含着这样那样的逻辑错误,要么依赖于我们不能证实为真的前提。因此,我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究竟为什么有物质存在?)的答案。[7](P161)证明必然存在物的存在是做不到的,“做不到这一点要么是因为(1)没有必然的存在物,要么是因为(2)尽管有必然的存在物,但没有办法证明它的存在,要么是因为(3)有一种对必然存在物的证明,只是我们根本没有获得发现它的思维工具。[7](P185)当代,不仅信仰被否定,本体论被清算,甚至所有传统文化体系都遭到解构。米歇尔·福柯认为,对西方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解构表明:关于世界秩序的真理体系、关于社会权利体系的正当性标准的规范体系,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关系的社会道德体系,虽然从逻辑上表明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符合逻辑和理性的原则。但是,实际上这一切都是知识在力图建构人的主体地位。与福柯一样,德勒兹、拉康和德里达认为,主体也只是形而上学思维的一种幻象与虚构,是一种异化了的主体。真正的主体是人的自发性本能欲望,是生命的本能冲动,是生存的真正原动力。理性在人的主体性与本质中丧失了主导地位。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一书中,从启蒙运动依据的错误原则开始,到中世纪的人类普遍历史概念,再到现代人性论的形而上学基础,利奥塔从方法论到理论根基对以往认可的观念进行了深刻剖析与反驳,并针对启蒙运动思想家关于普遍人性和个人解放的“后设论述”进行多方面批判。人性丧失了抽象性与普遍性,强调主体在场性与现实性。
西方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来,“以寻求个人自由为基本目标的新人文主义一直是西方各国社会和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成为近现代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的思想基础,而且贯穿于所有的社会制度、组织原则和政策之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8](P63)然而,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思想家不断揭露和批判新人文主义所鼓吹的个人主体性所隐含的反人性实质,以及抽象人性论。这些思想家包括后来的马克思、弗洛伊德等人。比如,尼采以“神的死亡”口号,向将人隶属于神的古典人文主义发出挑战,同时不遗余力将人从新人文主义的理性束缚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原初本能与情感欲望,达到完全回归自然的目的。
思想家们针对标准的多元性,批判理性标准的唯一性,批判理性原则对非理性、反理性拒斥,清算理性的抽象性与稳定性。同时,近现代思想家彻底批判了由理性主义统摄的形而上学的衍生物——罗格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
三、“上帝”死后的迷茫
现代和后现代的批判锋芒几乎触及了传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人类赖以生存的思想文化与体制体无完肤,满目疮痍,新的文化与体制形态却遥遥无期。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上帝已宣告死亡,人们并没有得到解脱,反而像无边海洋中的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茫然无措地摇荡,人们惊恐、无望、焦虑、虚无。奇怪的是,那些高举时代大旗的鼓手们对焦虑、恐慌的人们视而不见,并不想为芸芸众生指明前进的方向,寻求一块安生立命的坚实家园,反而越战越勇,一个劲的批判,批判,哪怕是沿着他们的思想刚刚生成的立足之地,甚至生成这种稳定之地的方向与苗头都不放过。他们好像刻意让时代,让大众永远处于这种迷茫、焦虑、惊恐与虚无的状态之中。据说这就是时代的宿命,这就是后现代精神。这不禁让人想起赵丽蓉在小品中教人学探戈,她那认真态度与气势让人坚信,“探戈就是趟呀趟着走,两步一扭腰,三步一回头,然后你再趟呀趟着走。”最后,专家派头十足地告诉崇拜者,“这就是探戈”。
那么,后现代文化内涵与诉求是什么呢?所谓的后现代文化,首先表现为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指的是一种思想或思维方式,创作实践的一种表达策略。这种策略“实际上表现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种悖论,其目的在于揭示传统文化本身的危机的不可救药,在于显示传统艺术深陷绝境的无可奈何的状况以及后现代本身的悖论。”[8](P4)其表现形式为:异质性、多元主义、含混不清、不连续、随意性、叛逆、变形、变态,目的是达到反整合、离心、差异、解构、位移、脱节、解除定义、消失、分解、非神秘化、去合法化、消除总体化等效果。据说这是一种难于预料的然而又具有创造性的“能在”;它是各种潜能的储备库,也是朝向各种可能的变化的神秘密码解构的缩影。后现代文化的另一特征是荒谬化。“所谓荒谬,就是没有规则,没有主次之分,没有目的,没有固定的方法,没有理想的完满形式,没有主体客体的区分及其同一;只有不断地区分,不断地差异化,……渴望在无穷无尽的探索中,因筋疲力尽而满足的那种状态。”[8](P12)
在后现代主义看来,20世纪末,当人类社会文化的繁荣和现代化的同时,彻底地暴露出西方文化的荒谬性,后现代主义正视现实,并揭露理性和荒谬同是人类文化建设中所设计、制造和生产出来的双胞胎。后现代主义者把理性主义所造成的荒谬膨胀化,都归因于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理性主义和传统语言中心主义在现代阶段的发展,归因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语言知识论述的人为荒谬化。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世界和社会系统的整体,实际上是充满着偶然性和多种多样可能的因果系列,而且这些偶然性和因果系列又是相互交错的,无固定方向,也无固定秩序。这样,后现代主义具有染指一切的倾向,力图以其不可捉摸的策略,颠覆现代社会和文化的灵魂与形式,并怀抱野心地试图影响现代的未来。
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的要义归纳为三点:首先,“科学知识是一种论述”,但当代社会的科学论述,已经同古典的和传统的西方近代知识论述有根本区别。知识论述模式和方法的变化,正是后现代社会到来的一个最重要指标。其次,后现代这个词并没有固定的定义,也不明确指涉某一确定的历史时期。最后,后现代这个词警示我们:在现代性之中存在着某种颓废的事物。这些颓废倾向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尤其是产生了正当化问题的新转变。
当代思想家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可谓淋漓尽致,鞭辟入里,深刻而全面,却让人不知所措,令人更加惶恐不安。
四、百姓日用即道与存在论:思想与知识的新基石
人本无固定不变的本质,也没有赋予他什么现成的本质,而是从他的自由和他所在的历史条件中造成自己的本质。正如奥特加·加塞特所说,人无本性,惟有历史。这就是人之不同于事物的一个主要方面,而事物有固定的本性或本质。同样,世界本没有文化,有了人才有了文化;世界也无所谓“本体”与原则,人类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才设想本体,建构文化。
人为什么是理性的?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已经是理性的,人的理性与情感意志需要本体支撑,更重要的是人类文化需要建构与引领。批判传统文化的荒谬性,指出存在的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为了使人更加幸福、文明的生活,需要建立新的文明。
那么,如何建构符合当代社会经济与生活的文化呢?这可能是数代人思考的问题。不过有两个方向性问题应当是明确的,其一是中西文化融合,寻找文化交集;其二是确立当代文明的基石。
传统儒学、理学言说的“道”是抽象的“道”,圣贤之人才能领会、掌握;王阳明认为“心外无理”,心就是道,知心则知道。王艮继承儒家“仁学”的“本体”论哲学思想,出发点同样是宇宙一体、天道自然、一体归仁、生命感通、生生和谐与天下大同。但王艮坚持“道”就存在于“百姓日用”之中,否定“道”的先验性与抽象性,正确地揭示了“道”的内含与来源。王艮认为“能知能行便是道”,“道”就像童子奉茶,不假思索,也不滞缓,是良知在此时此境下的顺势之举,“道”就是人性、人类情感在日常生活中本能反应。这样,凡是关注百姓日用生活的思想感情,密切百姓生命、生活的知识、道理都是道。
王艮认为人的欲望是自然赋予的禀性,具有天然合理性。人追求至道与快乐,合乎自然规律,即顺人意、应天理。但王艮坚决反对“私欲、造言乱道”的恶欲,要求人们不要为“恶欲”束缚,做到“知本”、“知止”。
海德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针锋相对,以人生此在的唯一性、实际性以及不确定性为武器,从根本上颠覆了关于人的生存问题的提法,改变了对人的根本态度和看法,主张从具体的个人的此在出发去分析、解剖人的存在问题。当下既是当场呈现的人生结构,是最自然和最本真的生存,也是最珍贵的生存。这就是此在。海德格尔通过此在,即个体当时当地的具体生活情境,通过具体的生存环境中呈现的人生结构揭示人生奥秘与本质,即“首先与通过所是的那样”显示其“存在”[9]。“首先与通常所是的那样”就是此在通常的日常生活所显示的存在者。这种日常生活结构就是“此在——在世”(Sein- in- der- Welt des Daseins)的那种“亲在”结构。“常人是一种生存论环节、并作为原始现象而属于此在之积极状态。”[9](P129)“本真的自己存在是常人的一种生存变式,而常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论上的东西。”[9](P130)
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拥有符合时代发展方向与需要的相近或相同的内涵:第一,它们都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海德格尔存在论是西方现代思想文化矛盾尖锐对立的新思想不必说,“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产生于明中叶的商品经济,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重复,阻隔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他们都不是理性主义者,也不是强调本能欲望与情感意志的反理性主义者,而是强调人的整体性与综合性。第三,二者都反对抽象的、普遍的本体论,拥戴具体的、现实的本体观。第四,他们都认为时代文化、人生意义的探求都需要本体支撑,文化需要建构,时代及其思想文化需要引领。他们都确信人的本质、生命的意义存在于此情此景的日常生活之中。第五,他们都从具体的活生生的个体出发,探求生命的本质、意义。他们都反对先验的、抽象的人性与传统理性主义生命观、价值观,赞成亲在的具体的人性、理性与生命本质。第六,他们都强调多样性,每一个体都有此在的价值。在此在与百姓日用面前人人平等。第七,他们探索本体的目的是为了人们获得“诗意栖居”的自在的幸福人生。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M].(第四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译文中把“是”译作“有”).
[2]谢维营等著.本体论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美]凯利·詹姆斯·克拉克著.唐安译.重返理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张志伟主编.唐安译.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美]理查德·罗蒂著.张国清译.后形而上学希望[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6][美]马歇尔·伯曼著.徐大建,张辑译.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性体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7][美]彼得·范·因瓦根著.宫睿译.形而上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高宣扬著.后现代:思想与艺术的悖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9]Heidegger,M,Sein ubd Zeit.Tübingen:Max Neimeyer Verlag.1979[1927]:16。
*作者简介:刘满华(1964—),男,泰州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副教授,文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B248.3;B516.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106(2016)01- 0134-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