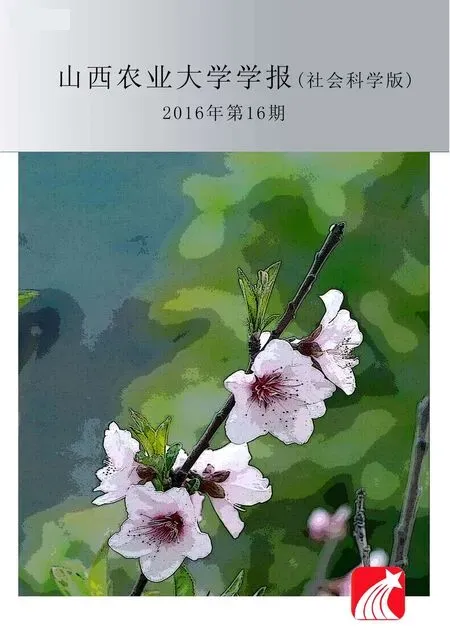近代青年审美心理变迁探析
——以山西铭贤学校为中心的考察
2016-04-04庞桂甲李卫朝
庞桂甲,李卫朝
(1.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2.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近代青年审美心理变迁探析
——以山西铭贤学校为中心的考察
庞桂甲1,2,李卫朝1
(1.山西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谷 030801;2.中共中央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91)
中国近代青年审美心理的变迁深刻地折射了社会时代的变化,通过他们的文艺作品,我们得以窥见他们的内心世界,掌握社会变迁与审美心理之间的内在关系。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随着救亡、革命潮流越来越汹涌,青年人的审美心态先后了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后的沉郁之美、大革命时期的青春之美、“九·一八”事变的悲壮之美以及全面抗战爆发后的雄壮之美几个阶段,总体上呈现出从优美向崇高演变的趋势。与此同时,他们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上表现为对暮性人格和奴性的批判,对青春人格和英雄人格的追求。
铭贤学校;审美心理;优美;崇高;理想人格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的命运几经潮起潮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十分深刻,它深深影响了地处山西中部的铭贤学校青年学子的心灵,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心理。我们将通过对这一时期山西铭贤学校(抗战时期一路南迁至四川省金堂县)青年师生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诗歌、话剧等)的考察,来梳理他们审美心理的变迁史,以期把握审美心理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规律。
一、国运衰颓时期的沉郁之美
中国近代青年的审美心理和他们创造的审美意象深深渗透着他们对自己人生和国家命运的深层思考,“我向何处去”的人生困惑与“中国向何处去”深层忧思紧密结合在一起,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心理,使得他们通过文学作品所展现出来的审美意象并不是单纯的情感表现,而是充满了深沉的哲理感和历史感。这在20世纪20年代铭贤青年学子的审美意象中就呈现出一种沉郁之美。
从文化根源上来说,这种哲理感也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仁”在他们身上的体现。叶郎教授认为“沉郁”的文化内涵就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仁”,它体现的是对人世沧桑的深刻体验和对人生疾苦的深厚同情。[1]这种情感在国衰家颓的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显得格外浓郁,深刻影响了当时的青年学子。
1920年,还处于青年时代的宗白华先生就深刻揭示了当时青年人的精神世界:“现在中国有许多的青年,实处于一种很可注意的状态,就是对于旧学术、旧思想、旧信条都还没有获着,心界中突然产生了一种空虚,思想情绪没有着落,行为举措没有标准,搔首踯躅,不知怎么才好,这就是普通所谓‘青年的烦闷’。”[2]宗白华先生正好道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大革命运动起来之前中国青年的精神状况——黎明前的烦闷!
一方面,是青年学子们对“我向何处去”的人生迷惘。在这些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作者自己对人生的迷茫。“黝暮沈沈,凉霭森森,疏星闪烁地洒嵌着苍蓝天空;寂寞的万籁,退归了睡乡去,孤寂的我,已经荡漾在碧海穹苍里了。……难题太多了,哪能一一地解答呢?省心些吧,希望即是糊涂之果那……”[3](《夜幕下》佈克作)中国的社会问题太多,一一解决的希望是那么的遥远。与国家命运相连的人生也显得“朦胧”了。“呀——,茫茫然生何所至,渺渺乎死将何适;朦胧的人生,本是乱丝般的秘密所织成的呀!”[3](《悼文骏》佈克作)“我们的世界是已经老了!在这世界中任重道远的人类已经是风霜满脸,尘垢满身。他们疲乏的眼睛所看见的一切,只是罪恶,机诈,苦痛,空虚。”[4]宗白华先生的这句话用在当时的青年学子身上是再合适不过。宗白华先生既表达了对这种暮性人格——人不老心已老的“老人”的不满,又表达了对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
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也到处充满着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深切忧思。沉郁之美的“仁”在青年身上的体现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和对国民生计的牵挂。“战地居民想必已逃避一空了,让出地方好为两军争雄。战争本来是武人的正经事,小民不得不弃家失业暂在异乡保他们残民去了。然而这西风冷夜寒霜沾地的时节,他们露宿山林岂不冻死吗?”[5](《太谷钟》白序之作)国运如此,民生如此,希望在哪里呢?“我忽然又想起:内争不已到了财穷力痛的时候,恐怕战争也许会休止了。及至外力侵来,实行国际共管政策;到了那时也许再无军阀的影儿,一般地都作了韩民第二。”[6]“中国向何处去”“我向何处去”的双重追问也深刻影响着近代青年关于人格美的态度,塑造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在近代青年学子心中,“中国向何处去”的关怀始终是和“我向何处去”的思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之后,很多青年难以适应现实的沉闷,他们既不找到自己人生的出路,也找不到救国救民的出路。革命的激情被长久黑暗的现实逐渐磨灭,而被五四呼唤起的个体意识,在黑暗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的躁动不安,他们对死气沉沉的暮性人格格外不满。“一切都黑黯黯底,天上只有星光闪烁,城中还剩白塔寺的灯光,好似在捉迷藏是的,一明一灭,在那里照顾太谷城中酣睡的居民。”[5]可想而知,在作者看来,酣睡的不仅是太谷城中的居民,而是所有的中国人。“咳!我们国民生活真盲目啊!今日我和你打,明日你和他杀,过了两天你们和好又与我战。打来打去,闹的国败民穷,试问彼此本心也不能答出‘所为何来?’”[5]
对“酣睡的居民”的不满实际上是对暮性人格的抨击,也蕴含了对新的自由人格的追求。“我可爱的同学们,寒假期又近了,不要把他在游逛里消去,不要在赌博场送掉,不要在温柔乡牺牲,不要忘了做人的道理,不要忘了一般可怜的同胞。”[5](《如何利用假期的光阴》陈宗宝作)可见,颓唐和暮气毕竟只是表面的,在它们下面澎湃着的是汹涌而热切的对人民的热爱!只是他们一时看不到希望,一时失望而已。一旦他们找着了希望,这些颓唐立即会一扫而空。这正是宗白华所说的“黎明前的烦闷”的真正的意蕴。青年人的“烦闷”不仅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而且体现出对新的理想人格的追求,他们不满意暮气沉沉的颓废人格,他们呼唤朝气蓬勃的“新青年”,这样的呼唤终于迎来了大革命的交响。
二、大革命洪流中的青春之美
经历了浓重的黑暗之后,以五卅运动为开端,以国民大革命为巅峰,中国开始走向新一轮的革命高潮。这次革命洪流席卷一切,那些关心国事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一扫五四新文化运动沉寂后的沉闷,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着革命的旋律。
在这一时期,“中国向何处去”“我向何处去”的双重追问仍然渗透在青年学子们的意象世界中。只不过同20世纪20年代的迷茫不同,大革命让青年人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也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向何处去”“我向何处去”似乎已经找到了解答的钥匙。他们对国家和自己的人生都充满了希望,他们的审美心灵变得清澈,他们的审美意象充满了青春的色彩。在革命高潮迭起的历史背景下,身边的自然景色也开始洋溢着青春的色彩。如:
“大块底文章,经营地多么有趣!阳春底烟景,布置地多么美丽!”[6](《春暮》禅心作)
“桃华飘扬兮·着我衣裙·丁香盛开兮·扑鼻芬芳·林檎含葩兮·怒而未放·榆梅长苞兮·笑靥馨香·姚黄魏紫·嫣红姹绿·婀娜娉婷·斗艳争芳·此青莲所谓之阳春烟景·大块文章也……其日天气清和·极目无云·吾等载行载歌·载歌载兴·于焉而奔于焉而困·三三五五·前呼后应·夹道垂杨·笑脸迎人·沿途青草笑容欣欣。”[6](《太原旅行记》程希曾作)
“春风带着消息来了!高浮着屋顶上的树梢,已经由紫而绿,由绿而青了;摇曳着河畔的细柳,也已经缀上了柔嫩的繁叶,掩映‘在春江水暖’的河里,好像长裾细带的舞女,对着明镜,呈出他无限婀娜的娇态来。唉!‘春’在人间已到了青年期了。”[6](《田野游记》林文林作)
新的革命思想打开了苦闷青年人的心扉,使得他们能够以热切的眼光欣赏这个世界。虽然当时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但是这不妨碍他们心情舒畅,欣然自然风光,体味人间美好,因为大革命给他们带来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而他们正处于革命的激流之中。在这些青年人看来,不仅是时节上的春天来到了,国家民族的春天来到了,是革命、是孙中山、是从前的人们眼中的“底层人民”给了国家新的希望。热爱生活,热爱自然只是他们追求的一面,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面。他们更需要的是革命、斗争和做事,将自己有限的青春投入无限的革命事业中去!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刚觉醒的青年知识者敏感期很快就过去,残酷的中国现代史的血腥斗争和内忧外患(军阀混战、五卅惨案、北伐战争……),很快就打碎了年轻人那种种温情脉脉的人生探索和多愁善感。严峻的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很快就舍弃天真的纯朴和自我的悲欢,无论是博爱的幻想、哲理的追求、朦胧的憧憬、狂暴的呼喊……,都显得幼稚和空洞。”[7]他们热爱生活、勇于实践,积极投身于革命与建设的潮流之中,他们的作品无疑受到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理想人格呼唤的影响,洋溢着朝气蓬勃的青春之美。
因此,这些青年人要与过去的拖拖拉拉、多愁善感的“暮气”决裂了,他们再一次地以“朝气”的态度拥抱生活,他们热烈地追求朝气蓬勃、充满实践精神的自由人格——“新青年”。
他们一方面猛烈批判老气横秋的暮性人格——“病夫”。“在中国人的脑筋里,都认定了鸦片烟,吗啡针,是两种害人的毒物。但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中国尚有一种有影无形,吮人精血的传统病菌。它的魔力比鸦片还大,比吗啡针还毒……这就是我们所常听见的‘朝气暮气’四字……在我国旧文学中处处皆有泣血坠泪的遗迹。现今的青年作品更都是些惨调悲歌,这足可表明我们青年受的影响太大,得病太深了。像这样的时而欣慰,时而颓丧,时而倩笑,时而悲歌,忧多乐少的人生,怎能不悲观与失望?怎样不沦为病夫?”[6](《青春和现在》杨瑛作)青年们已经开始对当时颓废的精神状况进行反省了,他们认为青年精神的颓废直接与国家命运的衰败息息相关,在他们心中,个体的“小我”始终是和民族的“大我”融为一体的。
另一方面,他们热情地追求朝气蓬勃的青春人格——“新青年”。他们以热情洋溢地呼吁到:“诸位!青年人!我们一生都是‘青春’,我们要死在‘少年’之中,我们一日有生,在此一日之内,当大努其力,不因时变景迁,风物凄凉就消磨我们作事读书的志气。”[8]“永远捉住‘青春’!时时努力‘现在’!”生命的青春是有限的,但是精神的青春是无限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们可以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存在无限美好可能的革命潮流中,去彰显无限的热情,书写有限的青春。大革命给了他们新的希望,大革命像灯塔一样指明了他们的人生方向,改变了他们审视这个世界的眼光,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热情地拥抱大革命,大革命运动激发了他们新的革命精神。“吾们国民当推翻那军阀的个人革命,去拥护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中国全民族的革命,吾们当实地去努力奋斗完成辛亥革命所没有办完的事,按照革命天然的趋势,去促进其成功,就是先由种族革命而政治革命,有政治革命而社会革命。”[9](《双十节与革命》尹致祥作)
大革命同样激发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体担当意识,他们呼唤有“正气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人格,改造中国的知识阶级。“一,民族的衰亡,以知识阶级为先河。二,中国今日的知识阶级却是衰颓了。三,欲救中国不外培养知识阶级的正气和牺牲精神。”[9](《谁是救中国者》凌旭作)这样的呼唤同样寄托着他们对理想人格——新青年的追求。这种青春人格是对传统的老气横秋的暮性人格的反抗,也是近代以来人性解放潮流的产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青年”理想人格呼唤的产物。
三、民族危亡关头的悲壮之美
“九·一八”事变骤起,日军的残暴与国民政府的无能迅速改变了青年们消沉的审美心态,悲壮的阳刚之美一下子被激发出来。阳刚之美因不同的文化背景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在西方是希腊文化、希伯来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熏陶下产生的“崇高”,在中国是儒家文化滋养下产生的“壮美”。20世纪30年代,日本开始大规模实施其灭亡中国的既定计划,中华民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的时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所激发出来的阳刚之美既有近于康德所说的“崇高”,也有更近于中国传统的“壮美”。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壮美在雄健、刚强之时,不脱内在的涵韵,寓刚强于和婉之中。
崇高感的根源在于人类的尊严和精神,也就是人之所以是人的本质。康德认为:“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以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9]所谓“另一种类抵抗能力”就是审美主体——人类的超越精神。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近代中国读书人往往以涵养“中正平和”之气奉为人生圭臬,缺乏一种豪杰精神和英雄气概,这种气质自然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审美心胸。近世以来一些有识之士曾严厉抨击过这种偏于阴柔的审美气质。20世纪30年代后,中国遭遇空前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强烈的危机感打破了他们原本对“中正平和”人生态度的追求,点燃了他们的激情,他们的审美心态也逐渐从优美走向崇高。
抗战期间,面对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中国似乎无战胜之可能。正是这步步紧逼的强大敌对力量,反而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超越精神——这就是康德所说的“另一种类抵抗力量”!他们不畏惧牺牲和死亡,只要能和对象——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和对抗!他们甚至并不畏惧国家的灭亡,但是他们不能接受不抗争就灭亡!因此他们讴歌即使国破家亡,也要斗争到底的壮士田横。 “朋友啊!亲爱的朋友!这民族,好似判决了的死囚;国家也长久的沉沦,也将要危亡。”[10]“我们的流血,是为民族的复兴,请再不要诅咒战争,或避免战争。当着大战之火在烈焰熊熊的时候……我们应当去尽量的泼油,添薪。”[10]在崇高、壮美的意象世界中,高尚、圣洁的灵魂美尤为人们所赞叹。直面失败的田横,气吞山河的岳飞成为青年学子崇拜的对象。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面对强大的外力毫不屈服,直至死亡。这种对灵魂美的赞赏也反映出他们对英雄人格的追求。
残酷的战争现实和民族危机,使得当时的青年学子对崇高的呼唤蕴含着浓厚的悲壮色彩,悲壮之美成为这一时期它们文学作品的主流意象。他们特别欣赏田横、荆轲那种悲剧性的崇高美,那种含笑赴死的从容英雄气概、豪杰精神。他们宁愿选择悲壮的毁灭,也不愿选择含辱的偷生。这样英雄的结局不管结果是成功还是失败,其行为本身就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美感。悲剧与崇高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学子的审美视阈中融为一体,成为涌向美之路的阶梯。
这些青年学子,他们血气方刚,激情燃烧,面对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他们无暇理论的思考,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抗争。如果说郭丕桢所作的话剧《国魂》创造的意象世界更近于西方的“崇高”的话,那么,黄振镛作的《满江红》、王问奇作的《游子吟》等则更近于中国的“壮美”。
“倚马雄关,按长剑,双眦欲裂。风骤起,惊沙刺脸,鬼声呜咽,满地燐光飞远近,无端触起愁千叠。好男儿,休负此头颅,希先烈。山河碎,谁补结。誓杀敌,心如铁。乘长风早将毛锥抛却。战罢归来还一笑,任情共赏深闺月。问苍生谁解战时艰,头如雪。”[10](《满江红》黄振镛作)“倚马”“雄关”“长剑”“骤风”“惊沙”等等都是阳刚之美的意象,而后作者笔锋骤转,“一笑”“深闺月”等意象一出,又显得无限深情。只有儒家文化,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将如此阳刚之美寓于如此温婉之深情中。
“淙淙清流湍飞急,枝头小鸟不住啼,茫茫何处是归路?暮色渐荒迷。关山万重空相忆,忍使骨肉生流离,怅望天涯孤鸿零,何日言归期?”[11](《游子吟》王问奇词,马革顺曲,1935年)这首《游子吟》中,作者由个人的旅途颠簸,想到同处战乱之中的同胞的“骨肉流离”,同样透出一股悲凉沧桑之感。
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上,他们唾弃奴性人格,呼唤不畏死亡、敢于战斗的英雄人格。他们对同胞奴性的憎恶更甚于对敌人残暴的愤怒!他们反抗“身奴”,但是他们更加激烈地批判“心奴”。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外敌的奴役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自己内在的“心奴”,只有破除内在的“心奴”,我们才能够不被外族奴役。因此他们无情地嘲笑“懦夫”。“我们所遭受的时代,是弱者应该被强者践踏,我们所遇到的环境,是枯竭无一滴水的泥沙。那些哀哭乞怜的像猫嘴里的耗子,像树枝上乱叫的乌鸦,这种懦弱的表现,徒使敌人轻蔑,咨嗟……是的,我们只有牺牲,奋斗决不要再惹人轻蔑,咨嗟。”[10]“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幸运,毋宁说是奴隶们又添了些绳索。这样漆黑的世界啊,奴隶们都带着练锁!”[10](《国魂》郭丕桢作)他们极端鄙视只会“哀哭乞怜”或“乱叫”的懦夫,表达了他们对奴颜卑膝、安于现状、浑浑噩噩的奴性人格的嘲讽,也表达了他们对不畏强敌、蔑视死亡的英雄人格的追求。近代以来,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倡充满自我意识、进取精神、竞争意识的自由人格。20世纪30年代对“壮士”和“英雄”人格的推崇,无疑也是这种思潮的表现。他们对“壮士”和“英雄”这类英雄人格的推崇既是对四平八稳、调和持中的“圣人”和“醇儒”的儒家传统理想人格的叛逆,是对彷徨迷茫、萎靡不振的暮性人格的唾弃,更是对安于现状、浑浑噩噩的奴性人格的抗议。他们对自甘为奴隶的奴性人格的批判既是近代民族精神的产物,更是近代以来破除心奴、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思潮的产物。
总之,全面抗战前夜,激愤的青年学子们一方面在文学作品中把战争、自然、人生、民族等的崇高意象与崇高境界融为一体,构建了以民族战争为意象核心的悲壮的意象世界。 这种意象是对战争的渴望,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抨击,一旦战争爆发,将以不可遏止的力量转化成战斗的力量。
另一方面,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也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圣人”或“醇儒”,更不是当时一些文人鼓噪的“才子佳人”,他们猛烈抨击安于现状、浑浑噩噩的奴性人格,他们呼唤不畏强暴、勇于战斗、正视死亡的英雄人格。这种英雄人格一面是对外族奴役的反抗,更是对自己内在“心奴”的反抗,而且后者更加深刻和彻底。这种英雄人格敢于张扬自己的个性,敢于表达自己的爱恨情仇,敢于迎战各种的专制强权,凸显了意志的力量,凸显了人格的魅力。青年学子们对英雄人格的追求固然是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精神的刺激,也是近代以来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精神熏陶的产物,同时传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家情怀也深深积淀在这种理想人格的塑造中。
四、抗日战争中的雄壮之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青年学子的审美心理又一次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迅速形成,青年学子们为这局面所鼓舞,他们无比坚信:虽然胜利的道路还很遥远,虽然胜利的道路还很艰辛,但是黑暗之后必将迎来胜利的荣光。这样,乐观精神一下子渗透了他们的审美心理。同样属于阳刚之美,但是“悲”的因素逐渐淡去,而“壮”的因子日益成长,洋溢着乐观精神的雄壮之美迅速取代带有悲剧色彩的悲壮之美,成为铭贤青年师生的主流审美心态!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也由悲剧性的壮士变成能够取得最终胜利的英雄。
“艰苦启蒙,豪华未变,校厂砂工几度见。‘立方社’结难题解,‘民先队’聚校庭院。急先锋躯,好学生面,校园内外秘宣遍。离校借枪武器握,游击儿女群山转。”[12](《踏莎行》许志奋,1937年)
“长天寥落璧天高,铭贤儿女意气豪。群空代北多良马,铁尽山西铸宝刀。势巍巍崇岳欲倒,浪汹汹万壑方潮。惟有百炼擎天柱,不怕山倾与海嚎。”[12](《铭贤儿女歌》贾麟炳,1938年)
“校抵关中依旧开,群贤辛苦育英才。早将天下兴亡任,共负仔肩义不辞。南渡匆匆虽草创,旧恨新仇誓不忘。黄昏训诲尚谆谆,鸡鸣起舞何荡荡!横磨日砺扫妖氛,胜利歌声终须唱。”[12](《青灯斗室沉香侧》吴连城,1938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的诗歌同样是阳刚之美,但是已经很少有“九·一八”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前青年学子文学作品中那种悲剧色彩,荆轲、田横、岳飞那种悲剧性结局的微妙预感在这些诗歌中再难找到。虽然日寇的乌云笼罩中华大地,但他们依然歌颂祖国的伟大,他们对民族的自信丝毫没有动摇。同样是黄沙白草,马革裹尸,但是他们相信自己个人的牺牲能够换来最后的胜利,而不是像田横五百壮士那样走向悲壮的失败结局,“露营荒郊,剑光透帷刀出鞘,运筹帷幄,杀敌何待晨晓。黄沙白草,掩映赤血染战袍,是好男儿,尸需马革包。送君今朝,从军远征显英豪,不歼强獠,誓莫还见父老”[11](《厉壮士行》吴烈秋词)“尧舜禹汤文武孔孟,历代君王哲士英雄,肇造华夏启迪亚东,江山成一统。四千万里丰饶疆土,三四万万优秀民众,天府之国岂容侵凌,恢复旧光荣”[11](《爱国歌》作者佚名,王文辅修订)。
他们渴望战斗,所以热情地歌颂激烈战斗的场景,“遍地甲帐重重,满天战鼓咚咚,将帅奋勇士卒争能。排山倒海汹汹,冲锋陷阵远击近攻,连营结寨蚁聚蜂囤”,因为他们相信惨烈的战斗之后,胜利属于自己,属于祖国,“威福强敌报捷立功,克日庆生平”[11](《爱国歌》作者佚名,王文辅修订)。
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上,他们要把这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崇高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洪流中去,实现自我的超越,成为“英雄”,成为“壮士”,立德、立功、立言。“大地春回,晴空万里净无暇。江山如画,趁吾贞健好年华,思潮澎湃,激荡兴嗟,念兴亡有责,何以为家,木兰从军、良玉杀贼,不羡鹿车。谁是英雄,谁是壮士,开天辟地,挥戈落日。立德、立功、立言,我爱她,我爱她,我爱我的中华!”[11](《大地春回》)他们渴望成为“英雄”、成为“壮士”,寄托了他们对自由人格的追求。此时,他们心目中的理想人格不仅拥有“挥戈落日”的伟力,而且要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还要有“不羡鹿车”、淡泊名利的境界,这样的英雄是真正的英雄。这时候,他们心中的理想人格同样是英雄和壮士,但是已经不同于之前悲剧性的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英雄,而是拥有伟力的、最终必将战胜敌人的英雄。
这种新的理想人格有三重精神维度:一,这种新的理想人格虽然抛弃了儒家正统的“圣人”和“醇儒”的人格理想,体现了中国近代人格追求的平民化趋势,但是它并没有彻底否定儒家文化,而是接受了儒家文化的“狂狷”和“仁道”维度,继承了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豪杰之气,这体现了新理想人格的传统文化维度;二,在大军压境、亡国灭种的关头,四平八稳、中正平和的“圣人”、“醇儒”确乎有点不合时宜,不畏强敌、不怕牺牲的英雄人格应运而生,也体现了民族精神在自由人格追求中的直接影响,这是新理想人格的近代民族精神维度;三,相较而言,近代青年学子自由人格的追求的最深层的原因是近代人文主义思潮,他们鄙视自甘为奴隶的奴性人格,视破除“心奴”为摆脱“身奴”的前提,积极张扬自我个性。这种英雄人格不仅是敢于和强大的外敌较量的人,而且是不受传统伦理教条束缚,个性得到解放的人,是能够运用自己的理性、敢于彰显自己的意志,善于表达自己情感的人,这是新理想人格的近代人文精神维度。
五、结论
习近平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13]中国近代青年学生审美心理的变迁深刻地折射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通过梳理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铭贤学子的文学作品我们发现,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深刻影响着青年学子们的审美心理,他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意象里始终渗透着“中国向何处去”和“我向何处去”的双重追问。而且,他们始终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视域下进行“我向何处去”的人生思考的。
首先,在这些文学作品所呈现的审美意象中,我们可以看见作者的个体的“小我”与国家民族的“大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向何处去”的真理探索和“我向何处去”的人生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小我”的审美心灵始终是超越自我、走向“大我”的。近代青年学子的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怀着高度的敏感,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冷暖时刻牵挂着他们的心灵,他们观照这个世界的时候始终渗透着“中国向何处去的”的深层忧思,这使得他们的审美拥有比较深沉的哲理感。在20世纪20年代充满着颓废迷茫的消沉感,大革命期间满怀着朝气蓬勃的青春感,“九·一八”事变后的他们的文学作品渗透着悲壮愤懑的悲剧感,而到了抗日战争期间他们的作品则充满着充实自信的自得感。
其次,在审美风格上,近代青年学子由优美逐渐走向崇高。五四新文化运动落潮之后的沉郁之美,渐变为大革命运动中的青春之美,革命失败后经历了短暂的消沉,“九·一八”事变激起了青年学生的悲剧感和崇高感,这种审美心态既有西方式的崇高,也有中国式的悲壮,“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再一次合作,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形成,悲壮之美转而成为洋溢着乐观精神的雄壮之美。可见,随着革命的潮流越来越汹涌,近代中国青年的审美心态总体上有从优美走向崇高的趋势。
最后,在理想人格的追求上,近代青年学子一方面对暮性人格和奴性人格进行无情的抨击,另一方面表达了对青春人格和英雄人格的热烈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对迷茫消沉、唉声叹气病夫般的暮性人格的不满,大革命期间对青春、朝气、阳光的青春人格——“新青年”的呼唤;而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们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自甘奴役、浑浑噩噩的奴性人格的抨击,以及他们对不畏强权、正视死亡的英雄人格的追求。这种新的理想人格是近代以来个性解放在民族危亡的时候新的人格形态,是个性解放的近代要求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情怀融合的产物,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和民族救亡思想结合的产物。
[1]叶郎.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375.
[2]宗白华.宗白华全集(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178.
[3]铭贤学校.铭贤校刊(北京图书馆影印本)(第一卷·第一期)[M].太谷: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校刊社,1924.
[4]宗白华.宗白华全集(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26.
[5]铭贤学校.铭贤校刊(北京图书馆影印本)(第一卷·第二期)[M].太谷: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校刊社,1924.
[6]铭贤学校.铭贤校刊(北京图书馆影印本)(第二卷·第一期)[M].太谷: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校刊社,1925.
[7]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241.
[8]铭贤学校.铭贤校刊(北京图书馆影印本)(第二卷·第二期)[M].太谷:山西太谷铭贤学校校刊社,1925.
[9]康德.判断力批判[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5:101.
[10]铭贤学校.铭贤学报(创刊号)[M].太谷:铭贤学校学报委员会,1936(7).
[11]信德俭,温永峰,方亮,等.真知力行 学以事人——山西铭贤学校办学评述[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389,389,387,387,387,389.
[12]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53辑)[M].太原:山西文史资料服务部,1987:36,132,135.
[13]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N].人民日报,2014-10-16(001).
(编辑:武云侠)
Research on the changes of aesthetic mentality for modern youth——study taking Shanxi Oberlin Sansi Memorial School as a center
Pang Guijia1,2,Li Weichao1
(1.SchoolofMarxism,ShanxiAgriculturalUniversity,Taigu030801,China;2.SchoolofMarxism,PartySchooloftheCentralCommitteeofCPC,Beijing100091,China)
The transitio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youth's aesthetic mentality reflected the profound social changes. Through their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we are capable of getting a glimpse of their inner world, ident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hanges and aesthetic mentality. In the 1930s and 1940s, with the growing revolution trend of saving the nation, young people's aesthetic psychology experienced several periods, including the depressed beauty after the May 4th New Cultural Movement, the youth beauty in th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the tragic beauty in the rear of the September 18th Incident as well as the majestic beaut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which showed an overall trend from gentleness to loftiness. Meanwhile,they, in pursuit of the ideal personality, criticized twilight personality and servility, and favored youth and hero personality.
Oberlin Shansi Memorial Association; Aesthetic mentality; Beautiful; Sublime; Ideal personality
K25
A
1671-816X(2016)12-0894-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