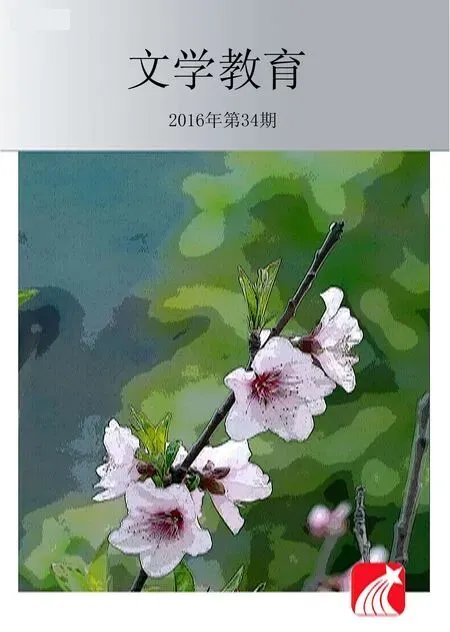论杨自俭翻译和重译《印度之行》时的视域融合
2016-04-03孙玲玲
孙玲玲
论杨自俭翻译和重译《印度之行》时的视域融合
孙玲玲
以杨自俭对福斯特的长篇小说《印度之行》的翻译和重译为中心,通过研究杨自俭在翻译与重译中所作的修改,从文学阐释学角度分析这一行为中的两个视域及其融合的过程,探究译本背后所体现的先见性与历史语境,从而对视域融合中译者的主体性有所理解。
杨自俭印度之行视域融合文学阐释学
阐释学在二十世纪时激起了研究的热潮,海德格尔对阐释学起了转折性的关键作用,加达默尔在其基础上对历史阐释进行深入研究,形成自己的系统思想。理解是文学阐释学的核心[1]248视域融合是理解的关键,理解是将两个视域融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视域,从而产生新的阐释。
《印度之行》[2]是英国作家E. M.福斯特所写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声望最大的一部小说,他致力于探索人的心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几次访问印度,认为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度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衬托出英国人性格中的缺陷与殖民统治的粗暴。杨自俭[3]两次翻译《印度之行》融合了他不同时期对福斯特思想的理解,他也在视域融合中形成了新的重译版的《印度之行》。
一.《印度之行》的译本与理解中的视域融合
加达默尔认为文学阐释学的理论原则包括理解的历史性、视界融合和效果历史。视域就是看视的领域,它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的所能看到的一切。[4]8按照加达默尔的说法,理解者和解释者的视域不是封闭和孤立的,它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理解者和解释者的任务就是扩大自己的视域,使它与其他视域相交融,形成视域融合。
杨自俭所翻译的《印度之行》主要内容是:英国妇女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去看望在印度昌德拉普担任法官的朗尼,朗尼是穆尔夫人的儿子也是阿德拉小姐的未婚夫。在印度医生阿齐兹带穆尔夫人和阿德拉小姐去游览具有印度风情的马拉巴山洞时,阿德拉小姐因为陌生的山洞景象产生混乱脑中出现回声,误以为阿齐兹要非礼她,从而将他告上法庭,最终清醒之后在法庭上承认阿齐兹无罪的故事。福斯特以这一件小事来写英国与印度、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来说明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联结之路还很漫长。
《印度之行》在国内有四个译本,有漓江出版社的张丁周、李东平译;杨自俭、邵翠英分别于1990年安徽文艺出版社2003年译林出版社的两个版本;以及季文娜翻译的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于2008年出版的版本。文章主要分析杨自俭于1990年翻译的和2003年重译过程中体现的他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第一视域和第二视域,以及在文学阐释学角度下的视域融合。
二.杨自俭的翻译与视域融合中的实践
关于视域融合中的视域,殷鼎在《理解的命运》中这样理解,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是由两个视域融合在一起,加达默尔从海德格尔处承接过“前理解”和及其三个方面的内涵——先有、先见、先知,将其置于视域之下,形成殷鼎所理解的第一视域。第二视域即作者创建文本所存在的特定历史语境。我们的理解与阐释就从在第一视域--理解的起点上到达第二视域。杨自俭在翻译与重译的过程中就分别体现了第一视域与第二视域,并在理解基础上形成视域融合后的《印度之行》。
杨自俭在1990年《印度之行》出版之后就发现许多不满意、没理解和译错的地方,因此在重译之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如阅读福斯特的散文选、福斯特传记、其他评论福斯特及其作品的文章,查看涉及背景的著作如《印度文化史》《古印度神话》等,对小说中关于印度、宗教、神话的理解也都有了进一步的加深。与此同时他对所要翻译的《印度之行》的内容也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和了解,这是2003年重译后比之前理解更深的地方。从阐释学角度看,对文本所存在的历史语境的理解属于第二视域,属于阐释学中所说的被解释者的内容,杨自俭对《印度之行》内容理解的加深说明了,在1990年和2003年版本的《印度之行》中,虽然文本所反映的内容是一致的,但由于译者理解水平或知识水平的差异,对文本产生不同程度上的误读,从而使阐释者杨自俭自身在不同时期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程度的理解。
杨自俭在重译的过程中也对文本翻译作了许多改正:如文本中Chandraporewasneverlarge orbeautiful,buttwohundred yearsagoitlayonthe roadbetweenUpperIndia, thenimperial,andthesea, andthefinehousesdate fromthatperiod.这句话中的thenimperial在1990年额译本中译成:那时已是英国的领地。2003年的译本中改成:那时还是莫卧儿帝国。因为根据当时的历史福斯特完成小说是在1924年,200年前是1724年,那时还是莫卧儿帝国时期(1526-1857),印度还没有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一事实对文中英国与印度之间的殖民关系有很大联系,福斯特一直强调人与人的联结,联结的基础是平等,希望运用人与人之间的联结达成英国与印度之间的和平相处,在印度的英国人与当地的印度人和谐交往。殖民地这一历史时间的长短,决定了两国之间的人民之间隔阂的深浅。正如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中所说:“寻找和决定细节,需要最严格的挑选。”[5]146福斯特在写《印度之行》时中对山洞这一细节的刻画成为影响英印人民交往的关键,杨自俭在重译时也注重对一些细节的探究,因此才会对一些文本翻译作了细节的修改,使译本更符合福斯特所要表达的思想,同时是读者也更能理解作者想要传达的精神。从阐释学角度看,第一视域中包括先见,同时第一视域又是从逝去的历史延伸而来的阐释主体存在的当下视域,包括通过语言传递到阐释者当下的整个历史语境。杨自俭重译《印度之行》的第一视域包括从文本所在的当时19世纪一二十年代到2003年整个历史文化氛围,以及这一氛围对杨自俭本身的渗透所形成的先见。这一语境与杨自俭在1990年译《印度之行》时相比也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说明了杨自俭本身作为阐释者对文本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正,也体现了理解的历史性。
根据阐释学的理论,理解是从第一视域起步而达到第二视域,在这一意义层面上达成两个视域的融合。杨自俭在90年译本中是在从文本所在的一二十年代通过语言传递一直到90年代的第一视域形成自己理解的起点与第二视域的被解释者的内容产生联系从而形成视域融合。2003年的重译本也是从第一视域走向第二视域达成视域融合形成自己的阐释。因为杨自俭的重译本在第一视域的先见性和第二视域的内容上都和1990年的译本相比都有所进步,所以在视域融合上的重译本对《印度之行》的阐释也是有所发展的。
三.结语
正如所说:“‘阐释’就是‘误读’,而‘误读’又是思者的思想源泉。”[6]47在翻译基础上的重新理解与阐释,既体现了译者自身的理解的不同时期的视域与融合,又体现了文学阐释学中的偏见与误读,在此基础上形成对文本意义的追寻。杨自俭翻译的重译的过程既是对自己的理解发展与审视的过程,也是对《印度之行》文本的原初意义和对福斯特的终极关怀探究的过程,因此杨自俭翻译和重译过程中的视域融合便有了价值的依托和探索的意义。
[1]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英]E.M.福斯特著.杨自俭,邵翠英译.印度之行[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3]杨自俭.关于重译《印度之行》的几个问题 [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5): 48-53.
[4][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5][俄]康巴乌斯托夫斯基著.李时译.金蔷薇[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6]杨乃文.偏见与误读——文学阐释学的哲学反思 [M].文艺争鸣,1996(03): 40-49.
(作者介绍:孙玲玲,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4级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欧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