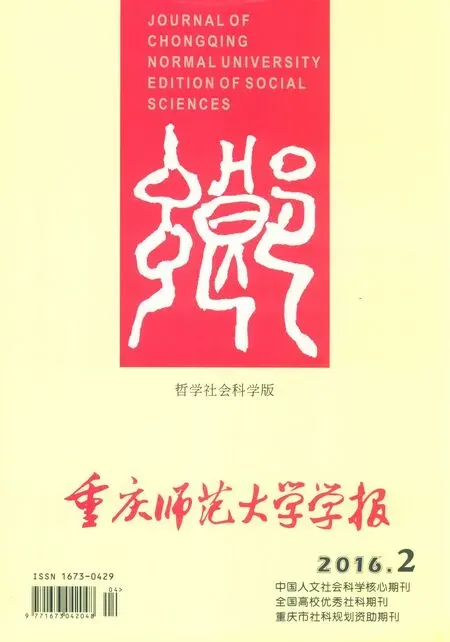理性视野下的语言存在论
2016-03-30肖福平
肖 福 平
(西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39)
理性视野下的语言存在论
肖福平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成都610039)
摘要:在我们将自然世界视为理性主体的表象世界时,自然语言或语言现象就作为了这种表象世界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理性存在的原因世界必然地提供着这种表象世界的先验理性基础,提供着语言现象经验的先验理性基础,即一种作为先验形式的语言原因存在;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统一实质就是理性存在的统一;先验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的对立和统一因为回到理性存在过程而成为可能。
关键词:语言; 理性; 先验
如果语言存在只是属于自然的过程,只是贯彻着自然过程的因果连接关系,那语言存在的内容就同所有自然界的存在物一样都要成为现代科学的研究对象,或曰“语言科学”的对象。在语言存在问题上,现代科学发展的无所不至几乎要将知识体系以及认识领域覆盖到作为理性主体之语言存在的全部,其结局似乎就是“语言科学”之语言对象对于理性之语言存在的全面取代,并造成语言存在问题探讨的经验实在转向,而且是一种决定意义上的转向,语言存在的世界也随着这样的转向而缺失自身存在的理性原因根据。然而,语言存在的彻底自然对象化除了企图将语言存在的经验可能性扩大到它所有的领域之外,其本身并不意味着语言存在之纯粹理性原因的消亡,即理性世界的先验语言原因总是要作为语言现象存在及其经验发生的绝对条件,从对象性意义上来讲,它要作为一种被康德定义为“等于x的一般的某种东西”[1]32的存在,否则,语言存在的自然对象化本身及现象成果就会什么也不是。语言存在的一切自然现象形式和一切作为认知成果的语言知识形式都只能是关于理性主体存在原因的结果世界。因此,不论我们如何强调语言作为自然对象的存在,作为理性主体的原因存在永远被前置在了语言经验发生的一切过程中;语言存在的自然过程仅仅是一种理性主体存在的必然性结果,作为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一定要回到理性存在自身,即回到语言存在的纯粹先验形式规定上来,语言存在的自然经验才是可能的,语言存在的自然显现才是可知的。尽管研究自然语言对象的科学之路可以不断地带来语言存在之自然形式合乎于内在先验形式的展示说明,但这样的“说明”不可能带来先验语言形式本身的自然对象化,即语言存在总是要体现为理性原因存在的非经验过程。在康德那里,理性存在的统一是作为先验形式与经验自然的统一,而语言存在作为这种统一中的必然产生,它一定要体现两种不同的原因性存在及其作用,即体现着自然语言现象的因果决定(如语言经验的各种语法规律)与纯粹语言形式的原因性规定,从而使得自然语言现象的条件限制和理性的纯粹语言形式规定成为一种理性存在统一的“事实”。因此,基于康德理性观的语言主体性地位思考应该成为我们走出语言异化并回归理性存在之语言统一世界的有效途径。
一、理性与理性存在的统一
在此,我们需要涉及以下问题的说明:“理性存在的统一”“语言的必然产生”,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建立。
首先,这里的“理性存在的统一”基于了康德先验哲学的思想,而非任何他人的理论或观点。因此,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我们总是在走进康德的先验哲学领域,立足于先验哲学中的“理性存在的统一”。当然,要想获得一个清晰而又令人信服的“统一”说明,并为自然语言现象的存在原因标示出必然的理性源泉,我们无法绕过“理性”或“理性存在”的问题;只有在认清“理性”或“理性存在”应该是什么的条件下,我们才会有可能去说明“理性存在统一”的情形,以及“语言存在统一”的情形。在康德的先验哲学里,“理性”被视为了一种“应该”的能力,一种具有天赋特征的能力,一种纯粹的能力,“纯粹理性,作为一种纯粹智性的能力,并不服从时间形式,因此也不服从在时间中连续的条件。”[2]475面对这样一种“能力”对象(如果我们能够面对),那理性就可以加以判断,名曰“理性存在”,其实,“纯粹”意义上的“理性存在”并不为我们所认知,倘若我们要对这样的“对象”加以分析和确定,那我们的工作就只能成为一种纯粹思辨的活动,要么借助于时空的先天形式,要么借助于想象的先验图式,但这样的纯粹思辨活动在“是什么”的判定上并不能提供任何知识性的成果,不管它是否借用了自然物对象的知识,还是借用了自然语言现象的知识,以及其他经验对象的知识,所以,在我们面对“理性”这种能力的判定时,我们无疑是要宣称这种能力存在的肯定判断,但又绝不是经验过程的那种知识性判断,只有理解这一观点,我们方可更好地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也只有立足于这一观点,我们才会在“理性存在”、以及“语言存在”的问题上取得相应“存在”之真。一方面,关于“理性存在”的肯定其实就是关于超越自然之原因世界的必然承认,是关于自然世界得以如此呈现和经验之理性根据的承认;另一方面,它又明确地导致了两种存在形式的划分:理性的纯粹形式与理性的经验形式(自然过程的表象形式)。显然,任何缺失“理性存在”的世界或过程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不用说关于自然物的知识和语言的知识,康德也因此视“理性存在”为自明的“事实”。当然,理性的“事实”在被加以经验过程的关注时会显得不是那么遥远和纯粹,因为我们很清楚:理性的“事实”只能依托于经验的事实,只能依托于人作为理性主体存在的事实,否则,我们关注“理性”的“纯粹”将会无路可行,更不必说去探讨理性存在的统一。因此,理性的“事实”不仅仅关涉纯粹形式的无限存在,而且也关涉自然过程的有限存在。倘如理性的“事实”不能凭借纯粹形式的世界本身得以说明和肯定,那解决的办法就只有另寻他途,即寻找一种能够秉承理性和表象自然世界的限制性理性存在,毋容置疑,这样的存在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尽管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唯一性在康德的先验哲学里是不能加以确定的,但在“理性”、“理性存在”、“理性存在特征”、“理性存在的统一”、“语言存在统一”等问题的展开背后,人作为有限理性存在必然是一个起点或基础;如果说“理性”为一种纯粹的智性能力存在,那人的“此在”就应该是洞悉这种能力的有效存在,或者说,只有从人的“此在”出发,我们才能获得“理性”或“理性存在统一”的真,并以此为契机去“朝向”作为理性纯粹形式的存在和去面对这种形式下的表象世界;只要“理性存在统一”的真表现为了人的“此在”的真,“理性存在统一”的普遍性地位就能够在有限理性的存在对象那里获得体现和满足,进而获得关于纯粹形式与表象世界的关系存在。
人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既不可能是单一的自然过程,也不可能是绝对的智性过程,人的“此在”过程总是要体现着纯粹世界与经验对象世界的统一,前者的能力联系于人所拥有的先验理性形式,后者联系于合乎先验形式的表象世界的对象,两者的统一由于人的“此在”事实而得以实现。因此,在我们自身存在的统一中,既有源自理性的先验形式存在,又有经验直观中的自然世界存在,后者总是作为前者存在及其应用的表象世界,或者称之为现象的世界。根据先验哲学的观点,我们所经验的自然世界并未表明这样的世界本身是什么,一切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都只不过是关于理性存在下的直观表象的认知结果,所以,作为经验对象的知识在先验哲学的认识论里并非就是关于对象本身的认识,而是关于自然物作为理性存在之表象的认识。尽管我们习惯地将这样的“表象”看成物自身,看成自然的“客观”,但这种“客观”只能是产生于理性存在的主观形式条件下的“客观”,是关于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下的“客观”,而非物自身的“客观”,“客体既然给我的感性提供表象,当这些表象的连接被理智概念规定成为普遍有效时,它就通过这个关系而被规定成为对象,而且判断就是客观的了”,[3]160“自然只是被我们作为现象来认识”。[4]35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既可以表现为感性层次的纯粹直观形式,也可以表现为知性阶段的纯粹知性概念形式,以及作为先天综合存在的先验图式等,与其说我们的知识内容是关于自然世界的,不如说是我们自身作为理性存在的必然,当然,这种“必然”的展示和说明必须借助于经验的过程或自然对象;至于说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为何如此表象自然、呈现自然和联系自然,那问题就变得难以解决了,不过,康德在这一问题上还是为我们设定了这样一个原因前提,即:理性不仅是纯粹的理性,而且也是实践的理性,理性的实践地位便成为理性存在与自然统一的根本所在,实践理性的特征及其规定作用的说明因此成为了康德哲学思想构建的重要内容。
在我们分析了理性存在的统一问题之后,我们便可以比较清楚地意识到所有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所有关于自然统一的现象、所有关于自然过程的语言现象和言说活动都应该属于理性存在规定的作用结果。不论是关于自然世界的对象、事件、过程,还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特征、关系、状态,它们作为人的“此在”的知识对象都必须是先验直观形式下的表象存在。既然是表象的“对象”,那这样的自然世界就不一定是它本身所是的存在,而是我们所“提供”的存在,意识到这一点非常关键,它能够在解释对象世界的普遍性、统一性和共同性等问题方面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迪,比如,我们面对的世界为何总是如此?我们面对的纷繁的自然对象为何总是具有一样的呈现模式?等等,因为我们发现不了任何例外的情况存在,哪怕是在虚假的梦里。所以,自然世界应该属于表象的世界,这种自然世界的“被表象”在体现人之“此在”过程的统一中便作为了理性存在的第一结果留存于我们自身之内,作为了“自然是什么”的第一次回答,也作为我们所拥有的纯粹知性概念形式的应用对象,从而取得关于表象之概念赋予的第二结果,或者说,取得关于表象的、基于先验综合图式的思想产生结果,并最终回到所有现象“结果”的原因存在,回到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自身而指向一个在知识意义上为“空”的纯粹之域,即纯粹理念形式的世界;当然,这里使用的“空”更多地出于纯粹逻辑结构意义的考虑,也就是不具有真假的判断。不管是哪一种或哪一阶段的“结果”,它们都在自明的理性存在统一中产生出来:要么为表象,要么为概念,要么为先验图式,要么为纯粹理念,等等,由此,我们才有了关于世界的统一和知识,有了关于知识判定的根据和标准。于是,自然世界只能是作为合乎理性之先验形式的存在,其价值也不在自然之内,两者之关系颇似于维特更斯坦所认为的那种语言与世界“同构”状况的存在,“(自然)世界的意义在世界之外,而在世界之内的东西就是如其所是,如其所发生,因而世界中没有价值”。[5]131至于说维氏的“同构”理论,我在这里不作叙说,我只想强调的是:本文的“同构”不是自然世界本身构成与理性存在形式构成的相等,而是自然世界作为表象的构成与理性存在形式的合乎一致,世界的神秘与未知在于有限理性存在超越自身限制的不可能性。总之,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或知识就应该建立在表象内容、概念内容、先验图式内容,以及理性的统摄原则的基础之上,这些内容和原则因为与先验形式的合符一致而成为了真之观念的存在,成为了人之“此在”意义的产生源泉,不但如此,它们的“所在”会因为理性的实践特征而必然地呈现于经验的过程,成为理性存在结果的知识体系。
二、“第二自然”与理性世界的语言与知识
为了区别于表象世界中的自然物对象,我们暂且将由于理性存在而被制造和表象的自然语言现象称之为“第二自然对象”,至于说在此为何取“第二自然”之词,乃是出于自然语言作为了源自理性存在之形式的对象化和外在化成果,同时,它又能与自然物一样被加以持续不断的经验直观。于是,这里的“第二自然”结果不是关于自然物对象的存在,而是关于理性主体之内在语言形式的外在呈现或自然化结果,倘如我们将从自然语言到理性主体的过程视为语言存在的“原因回溯”方向,那从理性主体到语言现象与知识结果的过程就是“原因决定”的方向,显然,不论是哪一个方向,理性主体的地位始终是一个中心、一个绝对意义上的语言现象“生产者”。如果我们将“原因回溯”开始阶段的自然语言的“被表象”视为理性存在统一的必然发生——在这一命题的证成方面,我们由于在语言经验的现实中发现不了任何的“反例”而视之为“自明”——那么,作为“原因决定”阶段的如此知识现象或语言现象的产生也应该是必然的,或许,我们在经验的层面还没有能力去言说“必然”,可我们也不会去否认:没有当下知识与语言现象的“我们”一定不会是当下的“我们”,一切关于“表象形式”、“概念形式”、“理性之先验形式”等的问题也就不会出现了,更不用说去探讨“语言存在”的意义根据了。因此,只要我们将思考的视角转到理性存在的语言经验“事实”和理性存在的纯粹原因及其实践特征上来,理性主体存在的世界里产生“第二自然”形式的知识与语言现象结果就要必然出现。在这里,“第二自然”的知识与语言是作为了现象的存在,而非某种自然世界里“物自身”或“语言自身”的存在,所以,尽管这样的“现象”在人们的眼里被视为了具有自然对象特征的东西,但人们在“现象”的所属原因根据方面还得承认“人的知识”或“人的语言”,或者说,这种“第二自然”的产生原因就在理性存在主体的自身之内,那么,我们在对知识成果与语言现象存在施予自然因果关系的联系或规律时,我们同时也在指向一种作为如此联系之根据的智性之源,即作为理性之纯粹语言形式规定的存在,尽管我们无法认知这样的智性存在作用的如何产生。倘如我们可以将无经验内容的纯粹语言形式设定为x!,其性质特征设定为f!(这里的!表明一种非经验证实的情况),那关于纯粹内容的表现就应该是:x! = f!,其先验的涵项为f!(x!),任何基于“真”的或“有效的”知识现象和语言现象一定保持着与其先验形式f!(x!)的合乎一致,保持着 x!= f! 的判定形式,尽管这样的形式之真远非我们人类的有限理性所及。当然,知识现象的真是关于自然世界认识与理性存在形式合乎一致并得以标记的认知结果,语言现象的真表现为符号标记现实与理性语言形式要求的合乎一致,作为语言现象与知识成果的呈现决定于理性存在及其统一的前提,语言现象之真并不可能脱离理性存在的原因规定(即先验语言形式的规定)而存在。
在语言现象的标记现实与认知结果之间,我们不会说标记现实先于认知结果,也不会说认知结果先于标记现实,因为两者的合符一致源于理性存在的统一,而非外在于理性主体的某种偶然的自然巧合,所以,“与认知结果的合乎一致”并未凸现或肯定这种结果对于语言现象的任何决定性地位,其根本就在于语言现象是否作为了理性主体的知识成果的正确表达,而这样的“正确表达”同认知行为的先验根据一样,它也依据了理性存在的纯粹语言原因形式。于是,语言现象的标记现实与认知结果的显现之间并非存在着本质的区分,认知的结果只能是语言现象经验中的结果,任何脱离知识成果的语言现象经验,以及任何脱离语言现象经验的知识成果都是不现实的。在“第二自然”的层面,不论是认知的结果还是符号标记的现实,它们都是作为现象对象的存在,并被赋予各自存在的系统性、规律性和客观性,然而,这一切还是改变不了它们作为“第二自然”的地位,即作为理性存在的先验形式条件下的“经验现实”存在,一种作为理性存在的“语言输出”现实。
如果抛开“(知识或语言的)先验形式是什么”的问题,如果可以超越人类自身的有限地位,我们便可以说,语言现象的本底就应该是先验语言形式存在,或者,知识现象的本底在于先验形式的知识存在。显然,我们不能完成这样的使命,我们所遭遇的就是又要回到了哲学“二元论”的思路上,从而面临要么归于“唯理论”,要么归属“经验论”的危险,但走出的“危险”的出路并非独断的、唯一的,或者说,我们关于语言或知识问题的“二元论”只是作为了分析问题统一性的“方法论”,而非要去做某种“独断”的判定。现在,为了更清晰的说明问题,我们将焦点转到语言的存在问题上来。
三、理性主体与语言存在
在上文里,我们反复提及和关注的一个对象是“语言现象”,或者说,是关于知识对象的“语言现实”,那么,这样的“语言现象”同“语言存在”的关系又该如何呢?在我们的判定“理性世界的语言必然产生”里,“语言”的意义又该作如何说明?在通常的语言实践中,我们或许未曾去关注“语言现象”与“语言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论是提及任何一方,我们所能呈现给自己就是那种被称之为“自然语言”的东西,那种为我们所思、为我们所用的符号系统,于是,“语言现象”与“语言存在”在指称对象的意义上往往就被视为了同一性概念,然而,两者的同一不可能在真正的意义上展开,否则,“语言存在”就会因为等同于“语言现象”而完全成为自然过程的对象,而要认知自然存在的“语言现象”,以及同“语言存在”的关系,我们依然摆脱不了理性主体存在的先验形式或认知形式的存在与决定,即关于“语言现象”存在与知识获取的原因根据只能是理性存在自身及其纯粹的先验形式规定,理性主体的存在统一应该成为语言现象及其知识体系存在的绝对性原因,所以,“语言存在”在作为纯粹自然对象而脱离于理性世界的原因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语自体”的存在,任何企图对“语自体”加以认知的要求都不会获得成功,这样的“语自体”当然就不会是作为人类“此在”过程所经验的语言现象真实。因此,在“语言现象”与“语言存在”的关系问题上,前者才是真正指向“第二自然”的语言标记系统、读音系统、文法系统,言语活动系统,等等,或者说,它指向的是关于知识体系所涉及的“表现系统”,正是基于这样的“表现系统”,我们才拥有了作为知识对象的自然与语言,语言哲学家们才拥有了关于知识世界的体系建构和理论建设,“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才会在语言现象的层面被加以探讨和确立,当然,作为知识意义确立的“语言存在”在这里同“语言现象”是没有差别的,它们所指向的都是关于语言存在的经验对象,是关于人类语言经验的成果现实,即关于语言的“第二自然”。
从先验哲学的“知识论”来看,只有在经验对象存在,并且被置于理性的直观作用之时,我们的“知识”方可真正有效地产生,所以,作为“知识”对象的语言必须是一种经验对象,即作为“语言现象”的存在。在这里,不管使用“语言现象”、“第二自然”,还是“知识对象的语言”,语言总是被加以了限制,或者说,关于“语言”概念的涵项式在没有限定的条件下就一定表现为一个不能确定真值的开语句形式,这样的“形式”要取得弗雷格所说的“真值”,它就必须获得对象的补充,而我们在“语言”概念上进行的限制,其实质就是在确定这样的对象范围以及对象内容,从而取得这种“语言”的知识和意义体系,以及弗雷格眼里的语言之真。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是以如此限制状态的“语言”来代替一般意义上的语言或语言存在,那我们所面对的对象仍然是一个以偏概全的结果,因为我们很清楚,限制条件下的语言或作为知识对象的语言并非语言存在的全貌,语言存在的全貌不仅仅是作为自然语言形式的存在,而且是作为带来如此自然语言形式的理性世界原因的存在,即,语言存在问题不仅仅关涉作为现象或知识对象的语言,而且关涉语言本身存在的地位与根据。语言存在问题远非一个关于自然对象形式(第二自然)的问题,从理性主体出发,世界作为了统一的存在,语言现象也具有了统一的体系,而“统一”的事实必然地拥有如此经验的理性原因根据。在语言现象的统一问题上,这样的“原因根据”又该如何取得自己的存在与展示之路呢?经验论者也许会承认这是一个问题,可又会认为是一个无实质的伪问题,在他们看来,语言现象过程及其自然的发生定会拥有其本身的原因与本身的根据,一种非理性的“语自体”的根据,于是,语言现象中的每一种结果、每一种发生、每一种关系,它们都会具备其作为现象过程的原因,不论是从微观的范围进向宏大的领域,还是从初级的层次进向高级的层次,原因的具备都会在现象的过程里被认知,而且,要说明这样的观点也显得不是那么困难,在语音学的领域、语义学的领域、语用学的领域,以及其他的作为知识体系的语言学领域,语言学家们成功地在“语言现象”的领域构建起了具有不同原因根据的知识体系,并取得了关于语言学的知识“规律或法则”,一种仅仅是基于限制性条件下的“规律和法则”,以及关于语言知识的纷繁多样的理论建设。不容置疑,语言学家在经验语言的过程里所面对的“原因根据”的确应该归于语言的范畴,然而,这样的“原因根据”知识却根本不能等同于“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答案,语言存在的原因根据也不会从此就能在知识的意义上被加以确定,就像我们确定语言、词汇、语法等知识那样去确定。显而易见,语言的存在尽管必然地拥有“语言现象”或“语言知识”的现实或经验世界,但语言存在绝非等同于这样的“语言现实”,语言现象世界的“经验根据”也绝非等同于语言存在的原因根据。作为语言存在的原因根据是我们面对语言现象如此产生和如此存在的理性主体条件,是关于语言现象的绝对整体性存在的原因根据,对于这样的原因根据,我们可以说,语言学家们在语言知识建构中所做出的有益探寻都是“朝向”它的无限进程中的一个环节,而不是关于它的认知。一旦我们进入语言存在的问题,仅仅局限于语言现象层面上的“是什么”探寻与收获就会远远不能满足问题思考的需要。一旦语言存在是可以面对的,我们就是在面对自然与语言现象、语言现象与语言形式、语言形式与理性存在统一关系的全部。当然,在提及这样的关系时,我们并非在断言双方的对立或双方之间的某种外在关系,或者说,语言形式与语言现象属于语言存在的统一,而语言存在的统一奠基于理性存在的统一。倘如我们将语言存在拒斥于理性主体之外,并视之为纯粹自然物的存在,那我们只能对这样的存在保持沉默,因为这样的语言存在将会什么也不是,更不用说关于语言存在经验的知识,这样的结果显然有悖于语言存在的真实,至少有悖于“语言现象”的真实。
不论是理性存在过程的“语言现象”,还是这一过程的自然现象知识,它们都是作为理性主体的“表象”现实,都是与理性之先验形式的合符一致的经验结果,因此,任何外在于理性主体的语言原因及其现象结果都不会带来我们人类社会所遭遇的如此存在的语言真实。正如上文所提及的那样,语言作为纯粹的自然对象只能是一种假象,最多也只不过是一种语言实践过程所创造的“第二自然”结果,其原因根据还在于理性的存在,还在于理性主体所秉承的纯粹先验形式存在。语言存在首先应该是一种纯粹理性世界的存在形式,然后才有作为该形式条件下的语言现象或知识形式,才有关于语言现象世界所展现出的共同性、一致性和普遍性特征的存在。在先验哲学里,康德理性的“先验形式说”尽管没有为纯粹语言形式画出领地,也没有提出“先验语言形式”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先验形式说”就拒斥了“先验语言形式”,首先,康德的先验形式所指向的就是理性主体的先天模式,某种拥有自然、拥有世界认知可能的纯粹先天模式,从逻辑意义而言,这样的模式应该提供了关于现实世界和可能世界的全部源泉和根据,作为理性存在世界里的语言现象及其经验根据也应该回归这样的先天形式,唯有如此,语言才能真正走向“存在的家园”。其次,先验形式涉及感性、知性和理性等方面,包括了纯粹直观形式,纯粹概念形式和纯粹理念形式等;倘如我能够对于这样的形式加以描述,那纯粹直观形式就是关于时空表现的先验图式,纯粹概念就是关于现象综合的先验图式,纯粹理念形式就是关于智性原因的超验图式,要询问这样的“图式”存在,它就只能属于一个理性的应该世界,一个被康德称之为“自明”[6]2的存在;同样,在语言存在的意义上,这种“自明”的图式就是语言现象及其知识体系得以产生的纯粹先验形式,我们暂且将“自明”的图式视为语言的纯粹形式存在,因为我们自身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无法取得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任何认知,同时,我们也无法取得任何有悖于“自明”设定下的演绎现实或结果,或者说,“自明”的先验语言形式可以不是语言认知的对象,但一定要是认知语言对象的纯粹原因根据,否则,语言现象及其知识体系的统一性、语言现象与自然世界的统一、语言现象对于理性存在的通达一致就会消失,或至少不会有当下的语言现实。实际上,在我们经验语言现象的实际中,在我们面对作为不同语言现象的表现时,如经验汉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等等,我们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意识到某种共同的东西隐藏在这些语言现象之后,它一定是“我们的”,而且一点也不会去怀疑这种共同的东西被我们人类所拥有,尽管这样的说明具有浓厚的心理因素而无法有效地服务于“自明”的语言形式存在,可它至少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先验语言形式的心理印迹。再者,关于语言存在的经验世界总是在为我们呈现语言现象的知识,或曰语音知识、或曰词汇知识、或曰句法知识,等等,我们一定不会去质疑这种语言知识的存在事实,但我们必须清楚,同任何其他自然物对象的知识一样,语言现象知识的产生根据并不是因为外在的符号系统或其他的语言现象自身,而是因为理性存在所具有的感知语言现象的先天形式或能力,所以,语言现象知识的事实不仅仅是经验层面的,而且应该是纯粹理性层面的,它是关于先验语言形式存在与规定的“事实”,或许人们会认为这种非经验的“事实”只能是一种源于思辩的假想,这样的看法对于知识对象世界而言具有合理性,但就理性存在及其语言存在的“真实”全貌而言显然有失全面。因此,语言存在问题决不仅仅是语言现象与语言知识的问题,更是关于语言存在的纯粹理性原因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将语言存在看成一个源于理性形式的过程,那语言存在的全貌就应该是一个从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到语言现象或语言经验现实的过程,而且,基于上文的分析,从理性的先验语言形式到语言现象应该是一个必然推出的过程,即理性存在的先验语言形式→语言存在的经验现实,语言的产生源于理性存在的必然。
在辨析理性主体原因与语言现象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解析了作为知识层面的语言存在,又朝向了作为纯粹形式的语言存在,前者被我们称之为语言现象,后者被称之为纯粹的先验语言形式。基于先验哲学的启示,语言现象及其经验的现实为我们所确立的就是关于这种“现实”的先验基础存在,语言存在的全貌或“真实”应该是关于语言现象与语言纯粹形式的统一,任何局限于语言现象的或局限于语言纯粹形式的探讨尽管可以在语言存在的局部问题上取得有益的成果,比如文法学家所展示的句法规律,语音学家所揭示读音规则,或者,思辨哲学家关于语言概念的纯粹形而上学的推理,存在哲学家关于语言现象的本质定义,等等,其结果要么带来关于语言存在的相对性、有限性和经验性地位展示,要么带来关于语言存在的难以确定的、纯粹的先验地位特征的说明,从通常的区分方式来看,前者联系于自然语言学的研究,强调语言存在的现象层面认知,而后者联系于理性语言学的研究,强调语言存在的先验形式,然而,任何一方的研究都不可等同于语言存在的“真实”。语言存在的“真实”可以是自然经验的,但又不仅仅是自然经验的,它在自身统一的进程中一定要不断地以“第二自然”的身份联系着自己的纯粹理性家园,如此,我们在“语言是什么?语言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上会走出语言存在研究的限制而取得更为宽广的视野,换言之,语言存在于自然知识获取的经验关怀之外更有缘起于先验形式根据的精神慰籍。
总之,不论是在理性存在的纯粹语言形式问题上,还是在语言存在的知识性地位上,关于它们“是什么”与“应该是什么”的问题成为了分析思考的基本出发点。在有关语言存在的表达里,我们可以讲“从语言中来”或“到语言中去”,其表达的逻辑主词要么为知识,要么为理性主体;如果为知识,则表明语言的知识来自于语言现象的认知,同时又应用于语言现象的认知;如果为理性主体,则表明理性主体是在语言存在的经验中展示的,任何以语言为谓词的表达式或函数式都会由于理性主体的出现而具有意义或具有真值。“语言乃人类的家园”,我们在语言的家园里的进出,我们在语言的家园中见证自然世界的呈现,同时也见证理性主体存在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李质明. 论康德的先验对象[J].中国社会科学,1982,(5).
[2] Kant, Immanuel.CritiqueofPureReason[M]. trans. Norman Kemp Smith, London: Macmillan , 1929.
[3] 康德. 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M]. 庞景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 康德. 判断力批判(上卷)[M]. 宗白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5] 王路. “可说与不可说”之说[J].河南社会科学,2006,(5).
[6] 肖福平.康德自由理念的理性基础[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4.
[责任编辑:左福生]
The United World of Reason and Its Language Being
Xiao Fup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As we take natural world as the represented one of Reason, it necessarily consists of natural language, a phenomenon of language being, and moreover, the united world of Reason necessarily owns its transcendental base for the represented one, including the transcendental base for language phenomenon, a kind of transcendental cause of language being; the unity between language’s natural form and its transcendental form is in essence the unity of Reason; the contrast and unity between language’s transcendental form and its phenomenal form become possible because of having the process of Reason’s existence.
Keywords:language; reason; transcendental form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肖福平(1962—),男,重庆璧山人,博士,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16)02—007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