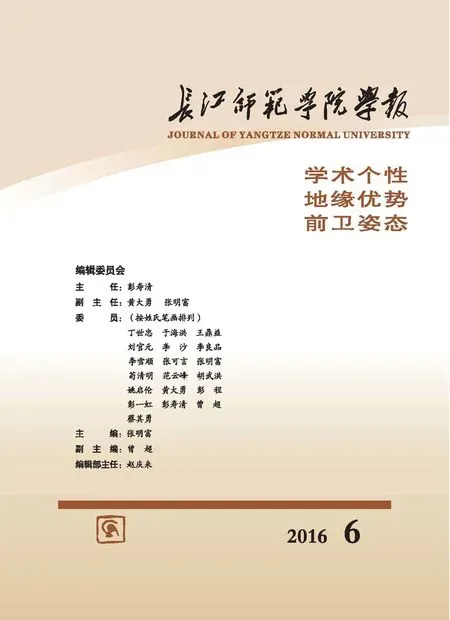创伤记忆与黑暗意识
——冉冉论
2016-03-29马玥玥
魏 巍,马玥玥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重庆 400715)
创伤记忆与黑暗意识
——冉冉论
魏 巍,马玥玥
(西南大学 中国新诗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重庆 400715)
作为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或许再也没有谁比冉冉更加关注黑暗了。如果我们结合诗人众多诗作关于黑夜以及黑夜背景的描写的话,冉冉诗歌中的黑夜就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来自于童年创伤的无意识书写。从诗歌文本来看,这种创伤记忆来自于小时候父亲在家庭中的主人地位。父亲是诗人忧伤、痛苦与屈辱的根源,这使诗人的诗歌书写呈现出对黑暗意识情有独钟的状态。记忆的创伤需要治疗、需要倾诉,尽管这种倾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说自话的哑剧。通过诗歌写作,她开始自我倾诉,倾诉自己的创伤记忆,倾诉自己作为女性的感受,也倾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她以写作的方式来对抗着创伤性记忆所强加给她的黑暗意识。
冉冉;创伤记忆;黑暗意识;倾听
一、序言
酉阳是一个土家族与苗族混居的地方,原始蛮悍的边地风光使这里的男人多有 “匪气”,女人多坚韧果决。这是一个产生——当然也可以说是生产——作家的小县城,如果说我们知道当代文学史中李亚伟所写的 《中文系》的话,以小说 《马口鱼》知名的张万新,长居成都的 “土匪”冉云飞,以及同样以诗歌闻名于世的冉仲景的话,那么,此言就不虚。冉冉同样是重庆酉阳县人,供职于重庆 《红岩》文学杂志社。现为重庆市作协副主席,《红岩》文学杂志副总编辑,副编审。她在198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诗集 《暗处的梨花》《从秋天到冬天》《空隙之地》《朱雀听》等,先后获1997年台湾薛林怀乡诗奖、2002年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4年首届艾青诗歌奖等。
在当前,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研究少之又少,而对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研究则更是屈指可数。仅仅关注已经成名成家的诗人,这对文学史写作来说是不利的;对作家们来说,这也是不公平的。每个作家都有得到研究的权利,这个权利不仅是为了与作者形成对话,也是对作家们的尊重。对冉冉的研究,不是以区域文学作为旗号来对她进行分门别类,更非为了就地取材,而是她诗歌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内涵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在屈指可数的研究文章中,有从民族性对冉冉诗歌进行分析的,有从存在主义对其进行讨论的,却鲜有从诗歌文本出发进行讨论的。这种现象不独为有关于冉冉的诗歌研究所有,在整个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中,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二、黑夜意识与童年创伤
作为少数民族女性诗人,或许再也没有谁比冉冉更加关注黑暗了。这里所谓的黑暗并非一种具体的所指,而是泛指它意味着与黑暗相关的所有事物、所有经验,比如夜晚、黑夜等。我一直在强调,不能把黑暗与光明对立起来加以审视,就如不能把女性与男性加以对立一样。为了避免从理论到文本的解剖性实践,进行理论的搬迁与旅行,我不想提倡任何女权主义理论,更不能为女性指出一条光明的康庄大道,我只是言说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女性诗学中存在的一些现状。本着这样的观念,我想就冉冉诗歌文本中的意象来展开讨论。
在当代,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尤其是诗歌写作,或许并不一定需要 “一间自己的屋子”——在这个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已经普遍流行的社会,只要你有诗意,随便一支铅笔与一张烟盒纸都可以供你写下你的感受。但是,她们一定需要一个精神的空间,这个空间能够让她们足够安静地去书写。对于冉冉来说,这个空间就是夜晚。在夜晚:
我看见自己的心像麻雀,被捉住,然后举到灯下。
黑夜向眉心聚拢。扑腾的心收拢翅膀,它愣怔着,张望着,像一堆暗火,黑夜向它聚拢。
恬静的夜晚的精灵,统治我们肉体的国王退朝了。血水像一些幼稚的鱼儿潜入子夜,飘零的脸颊悬在空中,唇颤抖在枝条上,黝黑中只有线条挤兑,而我,要做怎样的挣扎才能带上面具?
珍惜我们的天空已经离去,栖息过我们的躯体像林柯等待砍伐,所有的翅膀业已折断。夜晚,这巨大的乌黑的怪鸟一声不哼,黎明之前,它将产下病人与密布的医院。[1]
夜晚把人置于无边的遐想当中,它像 “巨大的乌黑的怪鸟一声不哼”,使人觉得异常孤独与宁静,它让人产生遐想引起回忆,同时,也让自己的身体得以放松,当身体回到自然状态,不用再戴着白日里的面具生活,紧绷着的神经开始舒展,“统治我们肉体的国王退朝”,人才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栖息地。白日间的那些精神病人在夜晚的医院里疗伤,这或许并不只是女性的一种想象,而是现代生活压抑人性的结果。
对冉冉来说,夜晚的遐想产生了诗歌。
今夜无端地想起某个词
将它写在纸上
它曾和什么词站在一起
它相邻的词又去了何处
记忆一年弱似一年
记不清与我一同认识的这个词
的还有谁——
数九寒天,身穿破衣
伏在故乡的书案
说过的话扔下
发生的事忘却
总有一天 我会怀了诀别的心情
唤起记忆深处的每一道痕迹
就像混淆于人群的我仍有人记得
——他,那腼腆的被遗忘的少年
暗地里翻动我生命的书卷
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男性诗人们不一样的是,女性诗人在黑夜里更宁愿放松自己,在冉冉的 《无端地想起某个词》中,这种放松是通过回忆达成的。通过无端地想起一个词,进而想到那个暗恋自己的腼腆少年。有些事情只适合回忆,比如逝去的爱情,比如过去的林林种种。女性细腻的情感,在黑夜这个无人察觉的空间里,悄悄地浮出水面。诗人并没有想着去寻找光明,相反,她沉浸在这种静谧的空间里,不愿离开。
黑夜里的回忆并非单一的指向某种幸福,抑或悲哀,它只是诗人凝神静思的一种方式,在不经意间,也可能会促使诗人对自己的女性文化身份进行思考。在 《冬天》组诗12与13中,诗人通过回忆母亲与祖母,有效地建构了两代女性之间的生活现状,从而为女性描绘了一个苦难的传统。
挑一个熟悉的人
共同回忆
比如母亲
她的额头摆满乱发
衣领总是敞开
气喘吁吁 她出汗
像呼吸一样从无休止
年复一年 在风中
她不停地耕种
收获的只是
饥饿与困窘
她压抑的抽泣
在夜晚被外面听见
白天 她雄心勃勃
一切又从头开始
她不怕吃苦
只怕睡眠 有始无终的睡眠
终于击败了她
如今她依偎着泥土
总算可以长久休息
操劳的母亲,并没有获得与她等量的报酬,她所收获的只是饥饿和困窘。但是,在白日里,她还必须把自己伪装成坚强的女汉子,操持家务,累得气喘吁吁。这个母亲形象,并非一个单独的个体,在诗人的老家,在整个酉阳农村,甚至全国绝大部分农村,这样一个母亲我们随时都可以遇到。白天,她们和男人一样,锄草种地,还要负担着全家一日三餐的饭菜;傍晚回家,当男人得到休息后,她们还要围着灶台转,偶尔还要忍受男人的抱怨甚至敲打。除此之外,还要操心儿女的生活,唯一能够休息的时间是在晚上。表面上,吃苦耐劳的母亲,只有在夜里才能放下自己疲惫不堪的身体,放松自己白日里紧绷的神经。但是,对生活无能为力的母亲,只能以哭泣来释放自己生活中所遭受的压抑。但是,这样的哭泣真的能够让自己休息吗?这种休息难道不是另一种辛劳吗?白天的生活让母亲身体疲累,夜晚的生活又让母亲内心忧伤,唯有死亡才能够让她们的身心彻底放松。这样的生活循环无止,就像一年的四季一样,春种秋收。她 “是儿女们的中心/她的周围是千百山民/她兴致勃勃为每一个人服务/微笑劳累 耗尽生命”(《母亲》)。
及至阅尽沧桑,母亲就会变成祖母:
还有祖母
那个倔强地沉默的女人
她的目光敏锐
行止冷漠
你永远无法知道
她所忍受的
哪些已经不堪
哪些已超越极限
在 《冬天 (十)》中,这个由母亲演变而来的祖母,仿佛已经洞晓世态人情,她忍受了一个女人所能够忍受的一生,现在只剩下沉默。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究竟隐藏着多少悲苦,她自己不说,又有谁知道?又或许,那些已经沉默的悲苦根本就没有言说的必要?只是她自己的余生用来回忆的生命的燃料?祖母的沉默,会不会也是时代女性的生命缩影?
如果我们把夜晚哭泣的母亲与暴跳如雷的父亲,再加上在父亲面前畏畏缩缩的 “我”对照起来阅读,女性所处的黑暗意识就更加明显。
现在我要坦然地
谈谈父亲
那个悭吝 沉默 坚执如牛
一直让我难以启齿的小老头
……
他令我不寒而栗
他那身打鬼子的力气
禁锢在体内成了鬼子
我亲眼看见他伸出蒲扇样的巴掌
刷刷刷劈打空气
然后对准自己的胸膛
他要毁坏它推翻它
……
他是我的父亲
我生命的源头与仓库
他是我的忧伤
我痛苦与屈辱的根源
他给了我一双饥饿的眼
给了我背叛尊严的口与手
那些年 我习惯于卑微
偶尔也想发泄 跟在他身后
总想狠狠踩一脚他的影子
可最终只能将拳头攥得发疼
吐一口长气
是的 我太羸弱了
我所有的败北都从他那里开始
我曾多次梦想
有朝一日我会战胜他
……
如果诗人是男性的话,《父亲》就是一首典型的关于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精神分析学寓言。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幼儿在性发展的对象选择时期,会向外界寻求性对象。这个对象首先就是自己的父母,男孩以母亲为对象,女孩则以父亲作为对象。小孩做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是由于自身性本能 (力比多)的驱使,一方面则是由于双亲的刺激加深了这一趋向:父亲多偏爱女儿,而母亲则更偏向儿子。在此情形下,男孩会把母亲视为自己的私有物,从而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这种情感导致他们把父亲视为自己的敌人,并想取代父亲在母亲那里的地位。同样,女孩也认为是母亲干扰了父亲对自己的感情,想要取而代之。在中国当代,也流行着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的说法。所以,弗洛伊德说:“受俄狄浦斯情结支配的性欲期的广泛普遍的结果可以因此而被看做是在自我中形成的一种沉淀物,是由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这两种认同作用构成的。”[2]
当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拉康的 “阉割”理论来对冉冉的这首诗歌进行分析,我们也可以说 “年青的女孩哪怕是在一会儿的时光中会认为自己是被阉割了,这儿阉割指的是剥夺男根的意思,并且是由某个人的行动而被剥夺的。这个人首先是她的母亲,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然后是她父亲”[3],我们可以认为 《父亲》中所表现出来的对于父亲的憎恨是因为女诗人的 “阴茎嫉妒”。极端的说,我们甚至可以把诗人 “痛苦与屈辱的根源”归结为对自己身份的 “阉割”感。父亲既给了 “我”生命,但同时,这个生命又是有别于父亲的存在,是一个让自己感觉非常卑微的生命,父亲是 “我”忧伤的理由,更是我背叛尊严的开始。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当然可以把这首诗以弗洛伊德或者拉康的理论无限制地推演下去,进行理论解剖。
但是现在,冉冉的 《父亲》完全颠覆了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一个西方理论。我们可以把 《父亲》当作“反”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文本,但是这个文本却与俄狄浦斯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纯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乡土中国的文本,这个文本紧密地联系着传统文化中的重男轻女思想。女儿不再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而父亲倒变成了女儿今生的敌人。这个悭吝、沉默、坚执如牛的父亲,让人不寒而栗,童年的生活不是在他温情脉脉的照顾之下长大,而是 “衣衫褴褛”“心虚气短”“他犟直的脖颈让我泄气/他锐利的眼光似乎要揭去我的皮”。父亲成了 “我痛苦与屈辱的根源”,以至于让我攥紧拳头恨不得揍他一顿,只是由于自己的羸弱,所以只能跟在父亲的背后狠狠地踩着他的影子以当报复。童年的 “我”,并不是想着要把父亲当作自己的情人,相反,却无数次想着什么时候才能战胜他。这个战胜父亲的梦想与是否成为母亲的情人这样的乱伦禁忌并没有任何关系,它可能只是中国乡土生活中家庭生活的一个缩写。
任何理论都不可能完全推而广之,俄狄浦斯只有一个,还是属于神话故事。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此耿耿于怀。但是,这种给家人以恐惧的男人形象却并不只是一个。在 《生气的人》中,诗人写道:
一个人把夜晚弄糟
是可能的
只要一个人
就可能把整个夜晚
弄得不可收拾
这个人没什么了不起
跟大家一样
他也是一个为了晚饭
整天劳碌的人
为了早饭
整夜酣睡的人
……
在他的周围
家人不敢说话不敢问
他们歉疚地坐下
惶恐地举箸
囫囵地咽吞
希图用他看得见的不安
来分担他的愤懑
整个夜晚
他呆在他的愤怒里
没有改变姿势
家里人睁大眼睛
战战兢兢坐卧不宁
他们在等待
等待他的爆发
那一刻 可能是在深夜
也可能是在黎明
一个随时可能发怒的男人,让家人感到不安与恐惧。在这样一种家庭里生长的小孩,怎么不会在暗地里对自己的父亲充满着报复的情感?又怎么不会感觉到自己处于黑暗当中,以及处于黑暗当中的安全感?
我们当然不必一定要把文学创作等同于现实,但是,如果我们结合诗人众多诗作关于黑夜以及黑夜背景的描写的话,冉冉诗歌中的黑夜就不再只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概念,而是一种来自于童年创伤的无意识书写。正如雅克·马利坦所言:“处在生命线上的精神的无意识和由肉体、本能、倾向、情结、被压抑的想象和愿望、创伤性回忆所构成的一个紧密的或独立存在的物力论整体的无意识。”[4]如果我们把 《父亲》与 《生气的人》结合起来做一次私人化写作的阅读,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正是因为童年时代的这个“父亲”形象造成的恐惧感,使诗人在日后的生活中倍感压抑,经受创伤的心灵也就更钟情于黑夜,也更喜欢书写黑夜里的一切:黑夜既标明了自己经受创伤的身份意识,黑夜也让诗人觉得更有安全感。
夜晚覆盖一切,遮蔽忧伤,将诗人童年所经受的创伤性记忆全部掩埋。这样,黑夜成了叙述诗人记忆的一个叙事场所,以特定的时间来隐匿逝去的自我,受创的自我以及试图抗争的自我的场所。在黑夜里讲述自己所经受的创伤,并非为了放弃自我,而是为了抚平创伤,重塑自我。正如加布里埃·施瓦布所说:“为了愈合创伤,身体和自我必须涅槃再生,语词必须与它们试图掩藏的死尸分离。”[5]
三、倾听:黑夜里的耳朵
黑夜里,眼睛将得到休息,或者说,眼睛变得无视,成为 《盲鬼》。
盲鬼 走在瓦上
纷至杳来的脚板
轻若书页
灯火就要熄灭
所有的窗帘拉拢
漆黑的眼一无所视
无视的眼使夜漆黑无边
请静静地坐着
请把远处的声音收入耳底
请扬起面孔
他失重的头颅摩擦夜气
他的耳朵望着你的耳朵
他的肩头朝向你的肩头
他的腿迈向你的腿
他的微渺的声音宛如金银
哪一场梦中 微渺是失散的家人?
在何处 我们肆意出入相互为门?
等得太焦急了
在城里 居家是唯一的游戏
我已经扮演过各种所谓的亲眷
盲鬼 盲鬼 松懈的精灵
子夜时分 请让我移居你的体内
一个人如果要在黑夜里保持住自己的世界,那么,他/她就必须能够保持住他们的世界,并沉浸在他们的世界里。对女诗人冉冉来说,她在黑暗中确认自己存在的姿态是通过 “听”来完成的。
在黑夜里,所有的眼睛都得到休息,每个人都成为盲鬼,白日里紧绷的神经才能松懈下来,我们唯有通过耳朵保持着与世界的沟通。在冉冉的诗歌中,风吹打山体的嘘嘘声、鸡在朔风中的鸣叫、母亲在夜晚里压抑的抽泣、乌鸦的聒噪 (《冬天》)、露水的嚷叫 (《露水》)、音乐的声音 (《静夜》)、胡琴的声音(《被胡琴充满的日子》)、雪落的声音 (《雪》)、打铁的声音 (《打铁》)、风吹过树叶的声音 (《山巅的乌杨》)、狗的吠叫 (《月光》)……各种各样的声音进入诗人的听觉。
傍晚落小雨
石梯伸向陡峭的黑
绾着头发沐浴
耳道里有
短促而微弱的声音
那是树叶舒张的声音
那是皮肤松弛的声音
那是空车驶过的声音
那是灯光下沉的声音
……
在 《小雨》中,傍晚的视线受阻,黑夜已经来临,诗人所感受到的是各种声音源源不断地充塞耳朵。这些声音或许能够增加一个孤独的人的存在感,让人不再感到孤独绝望。同时,它也是诗人对抗黑夜的一种生存方式。
没有星月的夜晚
老街和周围的群山一样
去向不明
大地上一团漆黑
打开黑暗拉链的
不是火柴不是手电
而是声音
火柴与手电并不能真正让这个黑暗的世界重现光明,在漆黑一团的大地上,它们只能照出有限的空间,但是声音不一样,通过谛听与交流,我们可以穿透黑暗,打开黑暗的窗口而进入另一个澄明的世界。这就是 《声音》的价值所在。
诗人所倾听到的声音并非只是一种单向的接受,它也同时意味着相互之间的交流,意味着自己与外界的沟通。在孤独的人看来,他/她自己的声音是一种脆弱的、微不足道的声音,在从小就生活在父权制的女诗人那里,自己的声音是被遮蔽掉的声音,但是她必须交流。就如巴赫金所言:“存在就意味着交际。绝对的死 (不存在)意味着再听不到声音,得不到承认,被完全遗忘 (希波吕托斯)。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人并没有自己内部的主权领土,他整个地永远地处在边界上;在他注视自身内部时,他是在看着他人的眼睛,或者说他是在用他人的眼睛来观察。”[6]如果没有交流,人便不会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只是现在,诗人的交流呈现出一种倾听的状态。并非诗人不愿与人交流,向人倾诉,而是她自己也清楚,自己的倾诉在很大程度上都只会是自己的独语、哑剧。
没有人知道我渴望倾诉
在这细雨连绵的夜晚
昏暗的光线中
我们相互凝望
它知道我将攥紧它
它知道我压抑不住痛哭
它知道镇静是多么脆弱
但它什么都不说
它知道自己没有嘴
没有手甚至没有生命
它只是凝望着我
什么都不说
……
渴望倾诉,却又没有嘴、没有手甚至没有生命,这就是 《电话》。但是,这个电话又不能完全作为一个孤立的实体,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就是诗人自己。正如王国维在 《人间词话》中所说的那样:“有我之境,以我观物,物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7]这种类似于惠能 “不是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的理论,在文学创作中并非宗教玄学,而是移情作用所致。
面对电话,它的沉默就是诗人的沉默,它想要的诉说就是诗人的诉说,或者更直接地说,这本身就是诗人的诉说。可是,诗人需要诉说什么呢?她究竟为什么压抑不住痛哭呢?这里的痛哭与母亲在夜里的抽泣 (《冬天 (九)》)有什么区别呢?从本质上来说,同为女性,这种被压抑所带来的哭泣标明了女性根深蒂固的地位。
我们可以把诗人的这种无处诉说的处境理解为不善交流的性格使然,但是,这种性格却是紧密联系着诗人的童年教育的。就像西蒙娜·波伏娃在 《第二性》中所说的,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造就的一样。因此,就算是性格原因,我们也必须把她的处境放到家庭环境中去理解。在这样的环境中,诗人感到:
失眠中 我整晚
整晚地 练我的台词
这些哑剧 要等到
临终之时 他自己演
这就是作为女性诗人的 《哑剧》,她们可以有观众,但却无法言说。台词只能在心里反复默念,至于有没有人真正能够看懂,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作为诗人,她的沉默只有通过写作才能得以呈现。
深夜
一个人静静地喝水
偶尔想起过去的事情
身体就仿佛坐上拖拉机
再不平稳
想起过去的事
手就忍不住四下摸索
我要的不是笔和纸
也不是杯里的白水
也不是一件事的过程
它是喊
我的十根指头
就像十根火柴
在拖拉机的两侧
突突突地冒烟
这就是沉默的女诗人的 《深夜》,笔和纸的简单书写已经代替不了诗人内心的压抑,面对过去的往事,诗人只有通过喊叫才能舒缓积蓄起来的压抑。这种压抑是否就是身为女人而感受到的性别压抑?抑或是童年时代父亲形象对自己造成的精神创伤?我们无从揣测,但是,多年之后,她在自述中提到的几段话却向我们敞开了她的内心世界。
镜中的那个人已不再使我厌烦,我已跟她和解。我平静地接受了她的沮丧和恐惧 (仿佛是她的姐姐或母亲),我们和平相处,有时还会相视一笑。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是我的恋人和老师,被拔高的雕像,我为她吃苦受累忍辱负重肝肠寸断。现在我成了旁观者,默默地看她从战场上归来,满身硝烟,一脸疲惫。
那战场是一个人的战场,那战争也多半是一个人的战争。多数时候,她是失败者,那并不是不够骁勇善战,而是因为,她根本就不适合争斗。失败是必然的结局。现在好了,她丢盔弃甲,不再备战,不再迎战,于是彻底消停下来——至少目前是如此……
博尔赫斯说:“镜子和交媾都是不洁的,它使人口繁殖。可我觉得镜子之妙并非增殖人口,而是产生分身,使你成为自己的观看者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距离不仅缓释了我与她的紧张,还使我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理性且不意气用事的人,一个温和宽厚的人——她的老师、母亲或者姐姐。”[8]
与镜子中的 “我”,也是镜中的 “她”的和解,意味着诗人对自己身份的再度体认。镜中的 “我”既是 “我”又不是 “我”,我打量着它,从它身上辨认出 “我”自己,而镜中的 “我”,则并不一定会把“我”当作是它自己。当 “我”成为 “我”的旁观者,是否也意味着,最终我也会变成 《冬天 (十)》中的老祖母一样?目光敏锐而又行止冷漠。
这样的一个人的战争可以找到一个属于女性的谱系,从林白的小说 《一个人的战争》,到鲁娟 (彝族)的诗歌 《一个人的战争》,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女性作为女性所体现出来的孤独与无奈。可以说,鲁娟的诗歌为冉冉的感受提供了一个注脚。
至今仍在继续,从祖母的祖母到
祖母的母亲到祖母到我
这场旷日持久的黑暗从未消除
时光的通道,她们一一走过
一千种斑斓一千种落寞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看不见地对垒
“你们的爱要坚守,而我要离开
你们的形式为喑哑,而我为辉煌
你们的天敌是别人,而我的是自己”
如今只剩下我一个人对垒,在正反两面
从未忘记背负的记忆
只是现在我要换副盔甲瓦解黑暗
镜中的 “我”,既是和解前的敌人,又是现在的自己,但无论是哪一个,都是一个被压抑的个体。在女性的谱系里面,“我”只是重复着祖母与母亲等一代代遗传下来的孤独而被压抑的历史罢了。
虽然诗人清楚地知道,“失败之母/她的灵感来自生育/她生下的女孩都是母亲”(《失败之母》),但是,既然性别已经不可改变,那么,为什么不与镜中的 “我”和解呢?一个人的战争也就意味着必然要倾听来自自己的声音,并通过这个声音与自我对话,不管这个对话是对立性的还是和解性的,因此,诗人必须书写,这种书写不只是为了产生记忆,或者忘却记忆,它同时也是确认自我的一种方式。就像她在 《流淌》中说的一样:
我身体里含着一条毒蛇
说出这句话
我又少了一点毒液
夜深打坐 我一直在流泪
又苦又咸的液汁从眼里溢出
慢慢流经嘴角 我为我的来路流
为忘却的噩梦流
为破碎复又惊喜的日子流
……
记忆的创伤需要治疗、需要倾诉,尽管这种倾诉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自说自话的哑剧,但是,除了以写作进行自我疗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消除那些忧伤的记忆呢?冉冉的倾听——来自外界也来自自己的内心——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她忧伤的童年,来自于那个她记忆中 “生气的人”,那个总是让孩子充满恐惧、让孩子感到战战兢兢的父亲,在父亲的训斥与责骂中,孩子通常只能沉默以对,不能言说也不能反抗,否则会招来父亲更大的怒火。倾听,并由此与自己对话,与大地万物产生交流,是一个从小就埋藏在心里的习惯,也是她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诗歌写作,她开始自我倾诉,倾诉自己的创伤记忆,倾诉自己作为女性的感受,也倾诉自己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她以写作的方式来对抗着创伤性记忆所强加给她的黑暗意识。
四、结语
在赵敏俐、吴思敬主编的 《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中,有研究者认为,冉冉的某些诗歌 “侧重于‘听说’过程中,一种压抑状态下的痛苦宣泄。”[9]这样的结论是比较中肯的,也是源自于文本自身的理解。孤独的人需要倾诉,通过倾诉,他们才能在孤独的环境中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并由此把自我与他人联系起来,进而确证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诗人,尤其是天性孤独的诗人,当他们没有倾诉对象的时候,就只能面向自己坦露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就是诗。更多的时候,他们要做的是倾听,倾听使他们保持着与世界的最后联系,是他们与世界交流的最后通道。因此,一旦他们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这会使他们更加恐惧。
2006年,冉冉的塞尔维亚之行,脱离母语语境后造成的失语,让她饱受了身心的双重不适。
你好,乌鸦
我是一个失去了母语和睡眠的人
整个夜晚我在多瑙河畔数我的药片
我的水杯是新的 我的时间慢下来
我呼出的气是我夜里发的芽
……
我躺在这里
赤裸得像天 我打量自己
就像打量异域的山水
异域的男人和女人
在 《异域·第一天》中,作为少数民族女性诗人的冉冉,尽管与酉阳出生的所有少数民族一样早已失去了自己的母语 (或许这种母语从来就没有真正出现过),而把汉语作为自己的母语,但是现在,失去了汉语语境的诗人再次把自己从陌生人变成了陌生人的陌生人。“我所失去的/母语故土爱人和荣誉/都不是真实的/就像我模拟的死亡/从未真正来临”(《异域·崭新的母语》)。处于陌生人之中,既无法言说,也无法倾听,诗人被彻底隔绝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
我听不懂他们的方言
叫不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
他们也茫然地看着我
但没有人问我姓甚名谁
他们当中没有我的亲戚
没有一个哪怕是间接的朋友
他们的容貌他们的表情
比一个新地方更让我陌生
我像所有失措的人那样
低下头来
我突然面对的不是他们
而是同样陌生的自己
……
我渴望熟悉他们
我会用我有过错的身体
热爱他们也善待自己
我要用我间接明亮的忧伤传递我
平静的忧伤
传递忧伤是为了将忧伤遗忘
《在陌生人中间》,女性的失语与忧伤变成了女性在陌生人中间的失语与忧伤,这种双重忧伤加深了诗人的孤独与恐惧,为了摆脱恐惧,遗忘忧伤,诗人只能返回自己的内心世界,倾听自己与自己的交流。这不是什么疯狂的神经错乱的表现,而是为了回归自我、抚平创伤的需要。
[1]冉冉.夜晚,暗处的梨花[M].成都:四川出版社,1996:152-153.
[2][奥地利]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文集(第四卷)[M].长春:吉林出版社,1998:165.
[3][法]拉康.拉康选集[M].上海:三联书店,2001:588.
[4][法]雅克·马利坦.艺术与诗中的创造性直觉[M].刘有元,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79.
[5][德]加布里埃·施瓦布.文学、权力与主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136.
[6][前苏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五卷)[M].白春仁,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378.
[7]王国维.人间词话[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2.
[8]冉冉.居家生活[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52-53.
[9]吴思敬.中国诗歌通史·当代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454-455.
[责任编辑:志 洪]
I206.7
A
1674-3652(2016)06-0064-11
2016-09-15
魏巍,男(土家族),重庆酉阳人。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