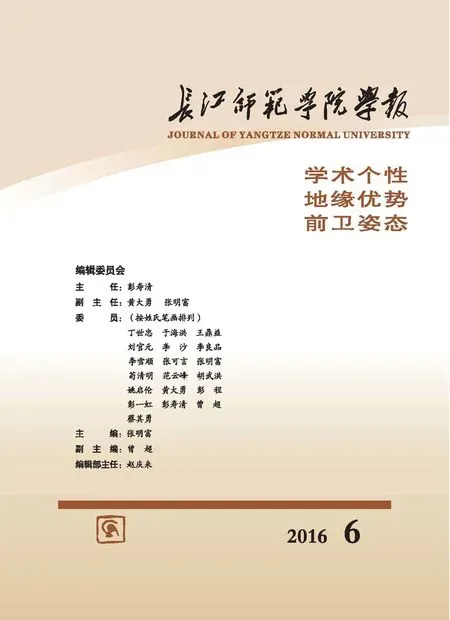明清小说男风书写中的门子与知县
2016-03-29张国培
张国培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明清小说男风书写中的门子与知县
张国培
(平顶山学院 文学院,河南 平顶山 467000)
门子与知县的性爱关系是明清小说男风书写的一种特殊模式。男风书写下的门子以色侍人,凭借知县的宠爱中饱私囊。这与历史上门子的生存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出入。历史上的门子的确已经影响县治,但罕有凭借色相达到个人目的、产生此类影响者。男风书写中所虚构的门子与知县的性爱关系反映出明清社会男风盛行的现实,其意义则在于作者对吏治腐败的讽刺。
男风;门子;虚构;讽刺
一、序言
明代后期以来社会世风日下,纵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春宫画、性爱工具等到处泛滥,毫不避讳地谈论床第之事而不以为耻,这些都是当时纵欲风气的印证。这种风气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异性间的性关系,另一部分是男性间的性关系,后者即为男风。明代纵欲风气与男风之间是互为因果的,进入清代以后,男风的公开性大大降低,市井气息也逐渐消退,但在数量和形式上的多样性方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清两代小说对男风的书写非常频繁,门子与县令就是一种典型的男风故事的模式。
门子本身是明清社会以来的职业称谓,因其职位的特点使门子与县令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特殊的关系留给小说创作很大的想象空间。明清小说中的门子参与到男风中来,成为以色侍人的小官①小官在明清两代有男妓之意。类人物,倚靠县令的宠爱和信任为所欲为,但男风书写下的门子与现实中的门子是存在较大差距的。
二、小说中的门子与知县
明清小说中对门子与知县特殊关系的书写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 《型世言》第三十回 《张继良巧窃篆·曾司训计完璧》。《型世言》是崇祯年间 (1628-1644年)刊行的话本小说集,全称 《峥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陆人龙著,全书共40篇小说。其第三十回即以门子为主题,专门创作了一个门子与知县的故事,亦可视为门子张继良的发迹史。
小说中写张继良是明朝常州无锡县门子,出身微贱,一贫彻骨。在对他的介绍中作者写到两点,其一是张继良在六七岁时读过书,认识字,有做门子的基本条件;其二是他容貌姣好。在这两点中很明显作者又在突出第二点,作者以韵语的形式细致铺写其相貌:“双眸的的凝秋水,脸娇宛宛荷花蕊。柳眉瓠齿绝妖妍,贯玉却疑陈孺子。”神态:“浅颦低笑,悄语斜身,含情弄态,故故撩人,似怨疑羞。”[1]310张继良在这方面的过人之处成为他日后发迹的一个重要资本。
张继良很幸运地碰到了何知县。何知县是一个典型的男色爱好者,遇到张继良之前他就感慨衙门中的胥吏无一如意者,而张继良的姿色令他深感满意。于是张继良从寄居的寺庙来到了衙门,身份则由一位无业游民而成为门子,很明显这个职业是何知县用来掩人耳目的。张继良作为门子的职责相当于贴身侍从,而本质则是知县的娈宠。凭借着这个身份,张继良在县衙呼风唤雨,为所欲为。
小说叙述了张继良在衙门中的以下事件。其一是辅助何知县处理日常政务,如娴熟有序地整理要紧文书、词状简札,作为顾问切中要害地回答知县的相关问题。其二是帮助何知县逃过上司检查,此事叙述最为详细。陈代巡临县,当地乡绅准备状告何知县。张继良以男色身份潜藏到陈代巡身旁,丑化当地乡绅,美化何知县;将代巡官印偷给何知县。其三是成为广州府新会县主簿。陈代巡事件后,张继良面临两个选择:跟随陈代巡去京城和继续留在何知县衙门之中。张继良选择了后者,他的权势已然超过何知县,经过一番钻营而做了官。其四是重归落泊生活。成为主簿的张继良抛弃凭借色相吃饭的官场生存方式,但仍然妄图凌驾于新知县之上,终于落得充军的下场,家眷流落广州。
在这些事件的叙述中作者并不是从门子这个职业角度来刻画张继良,而是一直在突显张继良的小官潜质及其作用。张继良的小官气质在进入县衙之前就已经彰显出来了。他曾在多个朋友家靠着姿色混饭吃,也曾在寺庙中迷惑老和尚。他能够轻松自如地做出小官姿态,勾引男性。遇到何知县时他已十六七,被人称为老扒头①老扒头多指已经过了弱冠之年却不肯戴网巾的小官,这里是为了强调张继良已经过了小官的最佳年龄。,但是在何知县、陈代巡面前仍然做出一番娇痴之态,“那答应的声儿娇细,一发动人。”“初时先把一个假老实愚弄他,次后就把娇痴戏恋他,那代巡也似得了个奇宝。”在这种情况下,张继良才能够私收贿赂,擅自处理政务,偷走代巡官印而逃脱责任追究。
在这篇小说中门子与知县所形成的关系完全超出了上下级或者主仆关系,已经成为男风关系的一种,而这种男风关系的存在空间主要在县衙之中。属于此种模式的男风书写在明清小说中还有很多。《金瓶梅》中的男风故事主要发生在书童身上。书童在成为西门庆的贴身小厮之前就是一个门子。书中写到:“本贯苏州府常熟县人,唤名小张松。原是县中门子出身,生得清俊,面如傅粉,齿白唇红;又识字会写,善能歌唱南曲。”[2]464小张松是李知县用来结交西门庆的,可以推测他深得李知县喜爱,因此才有送人的价值。书童与其他小厮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但生的美丽,而且略有文化和才艺,他能够非常自然地为西门庆提供性服务,也能够帮助西门庆整理往来书简、对西门庆应答如流,甚至还能像应伯爵一样替人在西门庆面前说句话,从中赚些银子。书童在西门庆家的所作所为明显留有门子的痕迹,由此可以断定他在李知县衙门内的作为也大致如此,也可以说他在西门庆家能够游刃有余当是得益于他的门子经历。
明末的男风小说集 《龙阳逸史》第十四回写到一个门子。这个门子不在阳间,而是在阴曹地府的阎罗王身边,名叫洪东,生前是小官出身。洪东是好人家儿女,但是被卞若源拐来当做小官卖。洪东被大老官买走后,因为大老官妻子不容,便自杀了。阎罗王见他是一个有些烈性的小官,便留在身边做了门子。做了门子的洪东并没有特别的工作任务,但深得阎罗王的喜爱,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洪东年轻漂亮,卞若源当年将他放在天字号②《龙阳逸史》第十四回提到小官分类,依据年龄和容貌将小官分为4类:“初蓄发的派了天字,发披肩的派了地字,初掳头的派了人字,老扒头派了和字。”这种分类标准在《龙阳逸史》中是统一的。发卖足以证明他有过人的姿色,而这说明洪东与阎罗王的关系也不过是阳间门子与知县的常见勾当。
清代雍正年间的 《姑妄言》有两处写到门子和知县的特殊关系。首先从直接叙事的角度说,作者将魏忠贤三代都写成了小官。魏忠贤的父亲在小说中名叫魏卯儿。卯,兔子之意,暗指魏卯儿是兔子。“这魏卯儿生得着实标致,在县中当了一名门役。”[3]404他伺候过两任知县,头一任不曾理会他,原因不详。“后来一个新任知县,系福建人,酷好男风。又因路远不曾带家眷赴任,就宠幸起他来,竟如伉俪一般,言听计从。”[3]404后一次遭际与张继良很类似,略有不同的是县衙中的 “六房书办,无一个不同他契厚”,意思就是魏卯儿不但为知县提供性服务,而且与知县手下的小吏都有性关系。因此即使知县没有宠幸他时,他仍然是吃穿用度都不愁。有了知县的宠幸当然更是不同,“数年间他也弄有二三千金之物”。可是这个来自福建的知县和张继良侍候的何知县结局完全相同,“知县因此声名大坏,被上司揭参了,革职回去。”其次从间接叙事的角度说,作者借一个不知名的人物之口讲述了江宁知县喜老爷和门子董混之事[3]123,目的是为了彰显喜老爷的惧内,以为笑话,从中得知这样一个信息:喜老爷酷好男风,一个月有20天都在书房与董混睡。董混作为门子也不过是喜老爷的贴身侍从,本质上是知县的外宠。
清朝乾嘉时期的 《何典》以鬼蜮世界的故事讽刺现实,在这部小说中也涉及到了男风现象,而男风就发生在门子和土地之间。“那土地饿杀鬼非但贪财,又极好色。他手下有个门子,叫做刘打鬼,当官名字又叫做刘莽贼,年纪不多,生得头端面正。他的母亲刘娘娘,也生来细腰长颈,甚是标致。娘儿两个,都是这饿杀鬼的婊子。”[4]53后来饿杀鬼升了城隍,接他娘两个一同上任。小说又借他人之口讽刺刘打鬼:“闻说这刘打鬼是土地老爷的汤罐弟弟,自身顾弗周全,还做别人的老婆”;“他是个小风臀,千人骑,万人压的,有甚好处?”[4]79-80凭借着与土地之间的特殊关系,刘打鬼同样拥有了参与政务的机会,他帮助活鬼疏通关系,将他救出监狱,当然也在活鬼身上发了一笔大财。刘打鬼与土地间的关系如同门子与知县,而刘打鬼身份的本质则是知县的外宠。
三、小说男风书写下的门子故事的虚构性及其意义
小说男风书写中的门子与知县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性关系,若追溯门子在古代社会的存在现状则发现,门子与知县的确具有形成这种关系的条件,但史料对此记载极少,而小说所写又颇为夸张。
门子本身是一个多义词,从先秦至明清其含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在西周时期 “门子”一词就已出现,专指卿大夫的嫡子。《文选》“补亡诗”云:“粲粲门子,如磨如错。”李善注云:“《周礼》曰:正室谓之门子。郑玄曰:正室,适子,将代父当门者。”[5]272此意后代一直沿用。战国时期,门子又指门客、食客。《韩非子·亡徵 (征)》云:“群臣为学,门子好辩。”明清时期的门子主要指供职于官府之人,尤其是县级衙门。基于此明清小说中的以色侍人的门子全部活动在县衙之中。
明清时期,州县是全国最低的行政机构。在这个基层行政机关中是设有门子一职的,他们也属于公家办事班子,职责主要是 “把门”,所把之门具体来说是知县以及县丞、典史、儒学训导等这些佐贰之职所在办公地的大门。门子的国家额定编制非常有限,小县甚至不设,并且薪水微薄。如广东揭阳县门子限定为2名,每名岁支工食银7两2钱,遇闰加银6钱[6]。清代震泽县共设4名,工食银6到7.2两[7]。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各地衙门中门子的人数皆处于超额状态。门子之所以总是超额,主要因为他们的工作并非像朝廷所预设的 “门子把门”,单纯把门的已经不能称为门子了。明代中期以来的门子更重要的职责是官府中的仆役。如 《随园随笔》“门子”条云:“今称府县侍茶者曰门子。”《陔余丛考》卷36“门子”条亦云:“今世所谓门子,乃牙 (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贱役也,古时则否。”[8]699《浪迹丛谈》“门子”条云:“今世官廨中有侍童,谓之门子,其名不古不今。”[9]253
门子这种身份的演化与县衙的建筑有着微妙的关系。以明代县衙为例,明代的县衙分前衙和后衙,前衙属于施政区,后衙属于生活区,二者之间有门墙相隔,这样后衙 (也称为内衙)便成为一个单独的院落,供知县及其家人仆役居住,其他人员不能随便进出。在知县不出后衙的情况下,行政人员想要见到知县,就必须通过中介,这个中介可能是知县的家人,也可能是门子。门子在消息的传递中基本摆脱了看门的职责,而是成了专门的递话之人,在这个位置上就有了可图之利。因此诸多门子走上了自己创收的道路,这也是很多人投身门子的原因。
门子的这种历史存在说明3点,其一是门子已经演化为必须自己创收的职业,否则没有出路;其二是门子有可以直接接触最高长官的便利条件;其三是门子在本质上已经演化为贴身侍从,但其工作地点并没有变化,仍然是官衙之内。这3个条件为门子与知县之间关系的微妙变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与门子发生性关系的官员基本都以知县的身份出现,原因在于门子的职位本身就主要存在于县衙之中,县衙中的门子通过知县发财的机会更大,更高级别的府衙等相关服侍人员很多,而门子并不是最重要的,其施展空间也受到极大的限制。
由此反观小说中的门子,他们全部处于超额状态,这些门子的创收主要有两条路,第一种是像 《红楼梦》中的门子葫芦僧,凭借聪明才智获取机会。这一类在笔记中留存下来的资料最多,如明朝刘时俊《居官水镜》所载门子刘梦斗盗取知县大印,与市中无赖姚敏捷等四处骗银;清朝方大湜 《平平言》强烈建议县衙不用门子,否则隐患无穷。第二种则是出现在男风书写中的门子。然而史料笔记对此却基本没有记载。可做旁证者有 《坚瓠集》“广集卷三”,文云:“今侍官府之美童曰门子。”但也并不针对知县。从小说以及史料来看,门子在明清县衙之内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但其中是否有一部分门子依靠姿色兴风作浪则是一个存疑的问题。
对于门子靠姿色接近知县获取信任的解说最为详细的仍然是 《型世言》,在张继良故事的入话部分作者有一番关于门子的评论,陆人龙称门子为男戎,文云:“若论如今做官,能剥削我官职,败坏我行谊。有一种男戎。男戎是什么?是如今门子。”对于门子的出身及其在官府中的所作所为陆人龙介绍得非常详细,他说:“这些人出来是小人家儿子,不大读书,晓得道理,偶然亏得这脸儿有些光景,便弄入衙门。未得时节,相与上等是书手外郎,做这副腻脸,捱他些酒食;下等是皂隶、甲首,做这个后庭,骗他银子。”“尝恐做官的喜他的颜色,可以供得我玩弄;悦他的性格,可以顺得我使令,便把他做个腹心。这番他把那一团奸诈藏在标致颜色里边,一段凶恶藏在温和体度里面。在堂上还存你些体面,一退他就做上些妖痴,插嘴帮衬。”张继良故事是对这段话的印证,丝毫没有溢出此番评论的范畴。但这段话不宜作为史料,入话和正话的关系本身就互为表里,此处既可以将正话视为入话的例证,也可以将入话看做正话的主观解说。二者加起来才是完整的话本小说,而 《型世言》的时代早已进入话本小说的独创期,入话同样属于小说创作范畴。另外张继良事件并没有出现在史料之中,这也可以佐证其当出于作者的虚构。
我们认为将门子、县令之间的关系与男风联系到一起,这是有其可资想象的基础的,这个基础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就是门子社会存在的3个特点,这3个特点为二者关系的亲密化提供了首要条件。从门子角度来说,他们可以私下与知县单独接触;从知县角度来说,他们可以摆脱来自家庭的监视,门子职位也可以作为掩饰,如 《姑妄言》中的喜知县,一个月有20天住在县衙。第二,促成这种男风书写的关键在于社会上的男风问题。从明代中叶到清代末叶,男风现象以不同形式活跃于社会之上,行之于文学书写的男风举不胜举,以小说为例,明清长篇世情小说鲜有不涉及男风书写者。基于此,明清小说作者想象出门子与知县这一类型的男风书写也就不足为奇,这是对社会男风现象的回应,但很难说是对社会真实的反映。可以对此加以佐证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在这种男风书写模式下的知县多被写成福建人,闽地男风大盛经由 《万历野获编》等笔记的渲染已经成为当时人的共识,因此从明至清小说创作者都不约而同地虚构出来自福建的知县。
明清小说作者虚构门子和知县的故事,其指向则在于官府的腐败。明清小说中关于吏治腐败的书写非常多,这方面的史料记载也很容易找到,在门子与县令的男风书写中同样非常严肃地指向了这一问题。小说中陷入男风问题的官僚自身也并不奉公守法,而是贪赃枉法,并且阴阳两个世界都是如此。《型世言》中的何知县因贪酷无比,引起全县百姓及乡绅的不满,陈代巡也并不代表正义,因贪恋张继良美色而不治其偷盗大印之罪,不追究何知县的平日所为。《龙阳逸史》和 《何典》则写阎罗王和土地。阎罗王身边的门子洪东骗取卞若源贿赂,而阎罗王置若罔闻;土地饿杀鬼正如其名,欲壑难填,两位作者以调侃的笔调讽刺了现实。
明清小说男风书写中的门子和县令是一种独特的文学存在。从社会现实来说,其存在的广泛程度有限,倚靠色相的门子在所有门子中所占比例虽然难以确定,但定然是少数的边缘性的存在。在男风的大背景之下,小说创作出门子与县令的这种特殊的男风模式,这一方面佐证了明清社会的男风问题,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作者对明清吏治腐败的不满和讽刺。
[1][明]陆人龙.型世言[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M].济南:齐鲁书社,1991.
[3][清]曹去晶.姑妄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清]张南庄.何典[M].北京:工商出版社,1981.
[5][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张妍.清代知县的“两套班子”[J].清史研究,2009(2):74-87.
[7]冯贤亮.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J].江苏社会科学,2007(6):210-217.
[8][清]赵翼.赵翼全集(第二册)[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9][清]梁章钜.浪迹丛谈[M].北京:中华书局,2007.
[责任编辑:志 洪]
I206.2
A
1674-3652(2016)06-0060-04
2016-05-29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清代小说的品花书写与士人心态研究”(2017-ZZJH-396)。
张国培,女,河北廊坊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