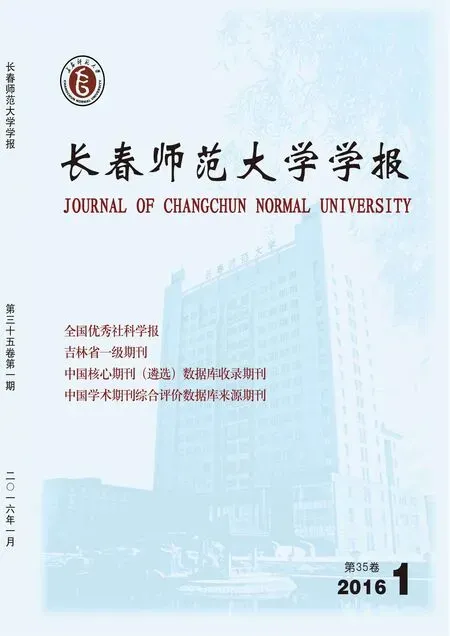《简爱》中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探析
2016-03-29苗莉珺
苗莉珺
(河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简爱》中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探析
苗莉珺
(河西学院 外国语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
[摘要]《简·爱》是一部描写女主人公追求独立自主的成长小说,但小说的背后潜藏着作者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简爱》进行重新解读,分析小说中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旨在挖掘隐藏在作品内部的帝国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关键词]《简爱》;后殖民主义;自我民族意识
小说《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正是英国殖民主义意识急速膨胀、寻求殖民霸主地位的年代。随着英国对殖民地的疯狂掠夺,其本土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对“低等”文化的蔑视丝毫不加掩饰。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小说,《简爱》隐含着作者的自我民族意识。作者以殖民者的身份审视被殖民者,以西方人的身份审视东方,以英国人的身份审视欧陆。本文从后殖民主义视角对《简爱》进行重新解读,分析小说中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旨在挖掘隐藏在作品内部的帝国主义话语,进而认识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学作品中的渗透。
一、以殖民者的身份审视被殖民者
《简爱》写于大英帝国殖民扩张鼎盛时期,而生长在这个时期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在大英帝国的国家制度、民族文化、道德价值体系的熏陶下,具有大不列颠和殖民帝国主义的意识,因此她在作品中隐性地描写了殖民扩张,流露出对帝国主义的认同和对殖民地的丑化。
伯莎·梅森是这部小说中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牙买加的克里奥尔人,是罗切斯特的合法妻子。克里奥尔人作为西印度群岛早期欧洲移民的后裔,相对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殖民统治者来说,和土著人一样是被殖民的对象。伯莎在小说中没有话语权,她的出场伴随着她那魔鬼式的使人发抖的笑声。简爱第一次在镜中看到的伯莎,“是张没有血色的脸——那是张野蛮的脸”①。简爱第二次看见伯莎是在婚礼的当天。“房子的深暗处,有一个身影在前后不停地小跑,乍一看谁也说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是人还是兽:它四肢匍匐着,像个什么怪兽似的乱抓乱嚎;可是它也穿着衣服,又浓又厚的黑发又有些斑白,蓬乱得如同马鬃一般,将头脸遮住……疯子又吼了起来。她拢开覆在脸上的乱蓬蓬的毛发,狂野地瞪着来人”。这一令人恐怖的描绘是作者采用的“非人”化叙事。作为英帝国的作者,简爱对伯莎的悲惨状况没有表现出同情,而是不自觉地将之兽性化、妖魔化,这不能不说是作者民族意识的一种隐性显现[1]。在大英帝国殖民语境下,有话语权的主体是英国人,而伯莎——这个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克里奥尔的被殖民者,从始至终都是被凝视、被观望的他者[2]。
伯莎作为一个被抛弃的异族新娘,在小说中遭受着话语的压迫,是一个被表述的他者。小说作者赋予了罗切斯特特殊的话语权,而剥夺了伯莎的话语权,让罗切斯特以男权的权势构建着对自己有利的叙事。“和我结合在一起的是我看到过的最粗野、最下流、也最腐化的天性”;“她的灵魂那么平庸无奇,那么卑鄙下流,那么小气狭隘”;“没有一个以卖淫为业的妓女会使用比她更污秽的字眼……西印度群岛薄薄的板丝毫挡不住她狼一般的嚎叫”。罗切斯特对伯莎的描述充满了厌恶和鄙视,伯莎不能为自己辩解,也无处诉说她的痛苦。勃朗特将伯莎置于丧失话语权的他者位置,意味着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充当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话语先导[3]。而伯莎的故乡——殖民地西印度群岛,在罗切斯特的眼中,其生活是低俗的、野蛮的。“一个火热的西印度之夜……空气仿佛是硫磺气……蚊子飞进来,房内到处都是凄惨的嗡嗡声。……耳边又传来疯子那尖叫般的咒骂声”;而“欧洲吹来的暖风漂洋过海……空气顿时清新了很多”,罗切斯特感到“智慧正在抚慰我”。与殖民地西印度群岛相比,欧洲的风是“清新”的,西方宗主国是高尚的、优雅的和文明的。罗切斯特的言语间充满了对殖民地的厌恶、丑化以及对英国文明的极力宣扬。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作为一个英国人,他的立场就是英国殖民者的立场,是帝国主义的立场,也是作者的立场;他的话语是英国殖民者的话语,也是作者的话语;他的尺度是帝国主义的文明尺度,也是作者的尺度。
二、以西方的身份审视东方
萨义德认为西方已创立的“东方主义”中的东方已经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带着权力属性的知识性的东方,是被西方创造出来的东方。东方主义是一种话语形式,是西方征服东方的一种文化霸权。正是基于这种东方学传统,西方在思想意识上一直贯穿着一种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与之相对照的即东方却被排挤在边缘地带,时不时扮演着一种处于劣势的他者角色。
勃朗特从传统东方主义者的角度塑造了作品中的非英国人物。除了伯莎这个脾气乖张、举止粗俗、爱好庸俗、心胸狭窄、放纵淫荡的东方人之外,英格拉姆小姐也被描述成一个东方女人。她有着“乌油油的鬈发,东方人的眼睛”,在哑谜表演中她一袭东方装束:“一条绯红的围巾像一条腰带似的系在腰间,一条绣花头巾在鬓角打了结,线条优美的胳膊裸露着,一手高高举起,扶着一个平稳而又雅致地顶在头上的大水罐。她的体型、面容、肤色和总的神态使人联想起族长时代的以色列公主”。简爱观察到,英格拉姆小姐向罗切斯特献殷勤时,“满脸堆笑”、“滥送秋波”、“左顾右盼”,“煞费苦心地故作姿态”,“千方百计地想迷住”他。东方的女人有“丰富的、肉感的、东方人的特质——一种追求艳丽华美的趣味”[4],所以,英格拉姆小姐是以东方女人的身份登场的。
东方是“感性的、纵欲的,是道德堕落、心智幼稚、缺乏理智、思维混乱、没有逻辑、不负责任、不讲信用的未成熟的民族”[5],还有奇珍异宝、丰富的物产和富丽堂皇的宫殿。因此,罗切斯特也是以东方形象登场的。在表演哑谜的那一场,他用披巾裹着身体,头上裹着穆斯林头巾。他那黑色的眼睛、黝黑的皮肤以及穆斯林的容貌都和他的装束十分相称。他有若干“漂亮得出奇”或“不讲道德”“横蛮无理”“没有脑子”的情妇,使他堕入“没有爱情只有肉欲的放荡生活”。由此可见,罗切斯特的形象在作者眼中是与堕落、富有、放纵的东方联系在一起的。
勃朗特采取的是以西方,尤其是以英国为中心的立场,用东方的特征标志他者。东方被视为“野蛮之地”,需要西方文明的“教化”[6]。所以,圣约翰借传教之名去印度“教化”殖民地人民。因为在他看来,印度人迷信、野蛮,需要教化。他去印度“改善同类——是把知识传播到无知的王国,要用和平代替战争——用自由代替束缚——用宗教代替迷信——用渴望天堂代替害怕地狱”。作为一个文明人,他“不忍”看到他们这样愚昧下去,他有义务用教义来感化、救赎他们,使他们远离野蛮,接受西方的文明。这种宗主国通过传教士进行的宗教传播,是一种对殖民地人民的文化侵略。正是这种文化侵略,掩盖了殖民主义文化扩张这一事实。然而,这样一位文化侵略者却被作者描述为一个弃绝世俗品格的宗教英雄、一位《天路历程》的圣徒,这种公然的文化侵蚀被描述成真正的灵魂救赎。
三、以英国的身份审视欧陆
欧洲在18世纪迎来了资本帝国殖民统治的第一个浪潮,英国是其中最强势的弄潮儿。英国不仅从法国手中获得北美的加拿大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新法兰西,使英属东印度公司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而且确立了英国的世界殖民霸权,成为“日不落帝国”。所以,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日渐明显——大英帝国是不可战胜的,就连其他欧洲人也是低等的。《简爱》中,法国小姑娘阿黛勒也被刻意丑化。罗切斯特认为阿黛勒虚荣,媚俗之气流动在她的血液里,融化在她的脑髓里,沉淀在她的骨髓里。因此,“我便把这个可怜虫带出了巴黎的泥坑……让她在英国乡间花园健康的土壤中,干干净净地成长”。简爱则觉得阿黛勒“有点放肆和轻浮”,她的“这种浅薄同普通英国头脑几乎格格不入,很可能是从她母亲那儿遗传来的”,但“她长大以后,健全的英国教育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她的法国式缺陷。……她已是一个讨人喜欢、懂礼貌的伙伴,和气,听话,很讲原则”。作者借罗切斯特之口,把位于欧洲大陆的法国巴黎称为“泥坑”,是肮脏的;英国的土壤是干净的、健康的;简爱也认为阿黛勒的“浅薄”是遗传的,是与英国普通人的头脑“格格不入”的。阿黛勒只有在英国干净的土壤中成长,得到“健全的英国教育”,才能纠正她法国式的“缺陷”,成为一个有礼貌、有原则的文明人。尽管作者或同时代的读者没有意识到,但这些话语形式的背后的确隐蔽着特定阶级、特定时代的政治无意识,是作者更为个人化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的体现。
在第12章中,简爱提到了她的一位欧洲同事:“格丽丝小姐终于打鼾了。她是一位笨重的威尔士女人,在此之前我对她惯常的鼻音曲除了认为讨厌,没有别的看法”。这种专门指向欧陆的民族意识并不止于阿黛勒和格丽丝小姐,简爱在谈及自己所教的莫尔顿农村学生时说:“因为英国农民同欧洲的任何农民相比较,毕竟是最有教养、最有礼貌、最有自尊的。打从那时以来,我见过一些paysannes(法语,农妇)和Bauerinnen(德语,农妇),比之莫尔顿的姑娘,就是最出色的也显得无知、粗俗和糊涂”。英国人在个人、位置、文化及语言方面的权威性,通过教育和批判机构,向他者持续不断地揭示和重复对他/她的变性的最初的征服、消灭、边缘化或自然化的过程,好像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文化根基的、普遍的、自然的事情[7]。《简爱》中欧洲大陆民众被赋予的民族意义上的劣根性,展现了作者在“个人、位置、文化及语言方面的权威性”,也是作者隐性地凸显本民族优越感的方式。
四、结语
《简爱》写于大英帝国殖民扩张的年代,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自我民族意识。从文本构成来看,文学、特别是小说,属于精神领域,它必然是时代的产物。作为宗主国的女性,勃朗特塑造了许多劣等民族的人物形象。她把殖民地的伯莎描写成吸血鬼和野兽,把欧洲大陆的民众塑造成“奇形怪状的低能儿”,把东方想象为怪异、落后和野蛮之地,无不流露出作者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因此,在多元文化互相碰撞的今天,研究帝国经典文本中的隐性自我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①本文所引的文本均出自夏洛蒂·勃朗特著、黄源深译《简爱》,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参考文献]
[1]赵轩.矜持背后的隐性自我书写——浅析勃朗特二姐妹笔下的“他者”形象[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1):105.
[2]孙玲玲.解构罗切斯特的殖民中心话语,还原阁楼上的疯女人[J].名作欣赏,2014(35):124.
[3]符海平,刘向辉.《简爱》的后殖民主义视角再解读[J].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89.
[4]霍桑红字[M].姚乃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73.
[5]周宁.东方主义:理论与论争[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17.
[6]康燕彬.《他的东方异教》与罗切斯特[J].当代外语研究,2011(11):53.
[7]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320.
Invisibl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elf in Jane Eyre
MIAO Li-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xi University, Zhangye Gansu 734000, China)
Abstract:Jane Eyre is a novel of initiation in which the author tries to describe the heroine’s pursuit of independence but the author’s invisibl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elf is concealed in the novel. Under the view of post-colonialism, this paper is to reinterpret Jane Eyre, trying to reveal the imperialism discourse hidden in the works, then to know that imperialism ideology is penetrating in the literature works.
Key words:Jane Eyre; post- colonialism; national consciousness of self
[作者简介]苗莉珺(1980- ),女,讲师,硕士,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研究。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1-0148-03
[收稿日期]201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