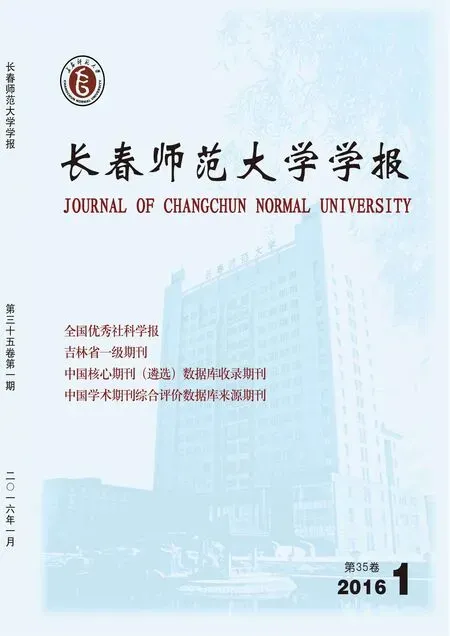简论明代士人人格的塑造
2016-03-29梁磊
梁 磊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简论明代士人人格的塑造
梁磊
(长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摘要]但凡为“士”,均以“内圣外王”为毕生的追求目标,明代的士人也是如此。有明一代士人的人格塑造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如何处理“道”与“势”之间的矛盾是困扰明代士人的主要问题,他们在探寻的过程中逐渐迷失了自我。明代的残暴政治彻底打破了士人的幻想,使明末士人的士气几乎丧失殆尽。
[关键词]道;势;人格塑造;政治暴虐;士气
“士”这一概念古已有之。商代至春秋时期,“士”为最低级的贵族阶层。士人“以研习儒学经典为手段,以参与政治为最佳生活选择,以道德修习和实现‘内圣外王’理想为最佳人生设计”[1]。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独具一格的朝代。“道”与“势”的矛盾一直困扰着明代士人的心灵,士人均以“以道佐势”为己任;君主则要“以势制道”,使士人屈服于君主的权威。明代的士人一直在寻找摆脱“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窘境的方法,但是明代残暴的政治打破了士人的幻想。明代士人人格的塑造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一、洪武至永乐时期
洪武时期推行严刑酷法,开国的功臣良将几乎被屠戮殆尽,正如解缙在为太祖所上封事中所说:“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2]416。政治的压抑使这一代的士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几乎丧失了守道抗势的勇气。
建文帝朱允炆的登基让文人迎来了转机。这位年轻的皇帝自幼饱读诗书,深受儒学熏陶,明代的士人们仿佛看到了仁治时代的曙光。但是,随后的靖难之役却将士人们推向痛苦的深渊。成祖继位,大肆杀戮建文旧臣,文人面临着或守道身死或从势弃道的尴尬境地。不论何种选择,对文人来说都是煎熬。选择前者,则身陨道消;选择后者,虽暂时保命,却也意味着放弃对道的坚守。
靖难之役给明王朝留下的最大损失就是士人对礼义廉耻即所谓“道”的放弃。经历了洪武、永乐两朝,明代的士人形成了一种妾妇心理,他们开始小心翼翼地隐藏自己的真实的情感与想法,对皇权恭顺无比。此种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明代士人固定的人格心态。
二、仁、宣至英宗时期
与洪武、永乐时期相比,仁、宣时期可谓“盛世”,士人和君主之间达成了一种短暂的和谐,道与势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一方面,到了仁宗、宣宗时代,锦衣玉食的环境使他们丧失了先祖的魄力以及手腕,他们需要得到文官集团的支持和拥戴,来帮助其处理国家日常事务;另一方面,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使得士人们感激涕零、热血沸腾,表现出了坚定的忠诚和忠心。难怪谷应泰感叹曰:“明有仁、宣,犹周有成、康,汉有文、景,庶几三代之风焉”[3]440。
但是,这种以情感为维系纽带的关系极具不稳定性。随着仁、宣以及太皇太后张氏的先后逝去,和谐局面不复存在。 英宗继位后,开始宠信宦官,打压文官集团。宦官集团相对于文官集团最大的优势在于善于察言观色,投君王所好。文官集团不论出于对道的坚守还是自身利益的考虑,都会对皇权进行或多或少的限制。
于谦之死对士人的信仰和精神是一种沉痛的打击。袁帙曾叹息曰:“己巳之变,至今可为寒心。……夫功盖天下者不赏,于公之谓也。”[4]2024袁帙虽对朝廷有诸多不满,但语气很含蓄。程敏政则毫不避讳地表达了对于谦之死的痛心和愤懑,言辞直指首恶:“故窃以为肃愍公之死虽出于亨,而主于柄臣之心,和于言官之口,裁于法吏之手,不诬也。首罪之祸,则通于天矣”[4]2023。于谦之死使士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的处境,依据自己的意愿作出两种不同的选择:“避”或“决”。“避”即躲避,远离是非,明哲保身;“决”即抉择,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迅速作出选择,尽量做到趋利避害。这是一场豪赌,赢则荣华富贵、春风得意,输则身败名裂、身死道消。
三、成化、弘治、正德时期
明宪宗较其父英宗性格相对宽容,对文官集团的谏言也能较好地采纳。《明史》赞其曰“恢恢有人君之度矣”;“仁、宣之治于斯复见”[2]181。
弘治、正德时期,士人再次复制了仁、宣至英宗时期的遭遇。弘治时代孝宗与臣子关系和睦,正德时期士人却与皇帝交恶。在皇权的打压和迫害下,士人的政治理想再次破灭,悲愤苍凉的心态油然而生。
在士人的心目中,孝宗同仁、宣二帝一样,无疑是位英明的君主。他个性温和,善于倾听臣下的意见,明白“吾不自治,谁能治吾”[4]2831的道理。《明史》也给予明孝宗极高的评价:“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成祖而外,可称者宣宗、仁宗、孝宗而已”[2]196。
孝宗一代,士人再次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随着孝宗的去世,这种曙光随之消失。武宗继位后,与文官集团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对抗。武宗行事荒诞,不喜文官集团的限制和掣肘,故而利用强大的皇权迫使士人们低头。弘治朝20年间所培养的不惧强权、舍身卫道的士气,使得士人不可能轻易向皇权低头,皇权与士气势如水火。士人在对抗皇权的过程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史书记载“贬谪、牢狱、廷杖、慷慨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触目惊心。
武宗时期,文官集团被皇权彻底压制,毫无翻身之力。士人内心的空虚和苦闷达到了无法排解的地步。很多人开始意志消沉,避世归隐,甚至采取一些更加乖张的行为来表达悲伤和无奈之情。他们或以酒买醉,“寄情诗酒自沉晦”;或放浪形骸,不拘礼法。
四、嘉靖至隆庆年间
嘉靖时期在明代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民风由淳朴转为浮靡奢侈,士风由家国天下、洁身自好变为见风使舵、毫无原则,学风更是由求实变为浮夸。“盖弘、正以前之学者,惟以笃实为宗。至正、嘉之间,乃始师心求异”。[5]
嘉靖朝伊始的“大礼议”事件对当时以及后世的士风产生了巨大影响。“大礼议”事件是指如何定位嘉靖帝生父兴献王的称谓和地位的一场争论。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和嘉靖帝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文官集团坚持继统兼继嗣的观点,主张尊兴献王为皇伯考,而尊孝宗为皇考;而嘉靖帝为兴献王独子,如果过继给孝宗,则兴献王一脉断绝。双方互不谦让,最终以文官集团的失败而落下帷幕。“至大礼议定,天子视旧臣元老真如寇雠。于是诏书每下,必怀忿疾,戾气填胸,怨言溢口”[6]。许多人当场命丧廷杖之下,更多的人被贬谪、流放,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大礼议”事件使文官集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世的许多文人对杨廷和多有诟病。但从实质上讲,“大礼仪”事件是士人之“道”与帝王之“势”的再次对抗,正如杨慎所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3]750。这是明代士人最大规模的一次“以道抗势”,也是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嘉靖帝依靠张璁、席书等文人的“人情论”击败了朱熹的“天理”,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学一统的局面。
1556年,世宗去世,穆宗继位。穆宗继位伊始,重新启用因建言而获罪的诸臣,逮方士交付法司治罪,停斋醮和例行采买,释放户部主事海瑞,“先朝政令不便者,皆以遗诏改之”[2]253。穆宗的锐意革新使士气一再受到摧折的士人看到了希望,但很快他们又失望了。穆宗仅在位六年,其间灾害、水患的记载不绝于史书,同时蒙古的俺答汗不停地骚扰明代的边境。在内忧外患的境况下,我们看到的不是君臣同心、同舟共济的感人场面。大量廷杖、贬斥的记载充斥于史书,如(隆庆二年)二月春正月乙卯,给事中石星疏陈六事,杖阙下,斥为民[2]255;(隆庆三年五月)甲寅,御史詹仰庇请罢靡费,斥为民[2]256;(隆庆三年十二月)乙丑,尚宝寺丞郑履淳以言事廷杖下狱[2]256;(隆庆四年)五月癸酉,给事中李已谏买金宝,廷杖下狱[2]257。
“嗜杀者非嗜杀敌,而实嗜杀其人”[7]。经过嘉、隆两朝的打击,明代的士气消失殆尽。
五、万历时期至明末
万历初年,神宗年幼,首辅张居正主事,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朝政为之一振。正如《明史》所说:“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2]284。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良好的局面为之一变。神宗自万历十七年始,就深居宫中,对朝政不闻不问。万历十五年“冬十月庚申,大学士申时行请发留中章奏”[2]272;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大学士赵志皋等请发留中章奏,不报”[2]277;万历二十四年“秋七月丁卯,吏部尚书孙丕扬请发推补官员章疏,不报”[2]277。万历一朝,皇帝不理政务,大臣则热衷于结帮拉派、党同伐异,朋党之争愈演愈烈。
神宗不理朝政,但朝政大权一直掌握在其手中,无人敢分其权柄。万历以后,光宗在位仅一个月,熹宗只好木工,大权完全掌握在宦官魏忠贤的手中。魏忠贤任用田尔耕、许显纯之流,大兴刑狱,虐杀反对派,“厂卫之毒极矣”[2]2333。崇祯帝虽励精图治以振朝纲,但奈何积弊难返、回天乏术。崇祯帝临死前还忿忿不平“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2]335。死节者仅大学士范景文而下数十人,这和靖难之役后士人的反应有天壤之别。
综上所述,有明一代270余年,“暴虐”一词始终贯穿于明代的政治。人主好用重典,人臣由自虐转而普遍嗜酷,“戾气”“躁竞”之气充斥于明末社会。如明末大儒顾炎武被人陷害,令他震惊和不解的是,倾陷者竟然“不但陷黄坦,陷顾宁人,而并欲陷此刻本有名之三百余人也”[8]。世道人心对“酷虐”的普遍欣赏和推崇是一种隐蔽的、不易发现的道德缺失,严重损害了士人的精神品质。面对如此情况,明末的有志之士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开始跳脱当时严酷的时代氛围,以其“守正”“坦夷”“雅量冲怀”“熙熙和易”的儒者本色,勇敢地探索解决这类“时代病”的办法和途径。
[参考文献]
[1]葛荃.权利宰制理性[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16.
[2]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谈迁.国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272.
[6]万斯同.石园文集:卷五·书杨文忠传[M]∥后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5册.影印民国二十五年张氏约园刻四明丛书第四集本:92.
[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三.穆帝[M].北京:中华书局,1975:428.
[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与人书[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3.
[作者简介]梁磊(1982- ),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历史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02(2016)01-0078-03
[收稿日期]2015-09-27